
Ma Jolie宋朝篇
欢迎来玩
对不起这次主线拖了很久,辛苦大家的耐心等待,下次一定写完再开!
后日谈预计将于3/5发布,计分统计将于清明节截止。

*注:以下内容有部分直接引用自企划原文,用“*”两端标注
沿海多奉妈祖。口口相传言,若溺于深海,其魂灵将收归于妈祖,而后可化鱼仙,此后逍遥水中。又有传,凡人若得仙缘、遇鱼仙,获仙药、居仙岛、可长生不老。
(1)
大暑将至。那些为寻鱼仙的人们赶着时候先后来到顺水客栈住下。旺季的房价总是会涨的,顺水客栈也不例外。有人对租费不满,拿着钱袋子对掌柜的叫嚷。*那掌柜的徐娘子生得年轻,二十出头,生得芙蓉似的娇柔面,说话却直白*,她头也不抬,低头边翻账本边没好气怼道:“*这顺水客栈占了个好位置,又有能对白岛事指点一二的老板,才不愁住客*,你若嫌贵便另寻良居罢!”
那人语塞,鼓着红脸拍桌喊着,你这婆娘怎么做生意的,又骂了一堆辱人的话,被徐娘子用账本扇了脸,喊人把他轰走了。
“这年头闹事的可真不少!”徐娘子轰完人,回头见众人视线皆聚焦于自己身上,气氛略沉闷了些,于是咳嗽两声,摇起圆扇,作回常态,呵呵道:“*白船总是大暑来。*众人皆为此来我客栈,作为商人,涨价自然不过。可我这客栈价格公道又良心,*屋里摆设没打折扣、中厅里凉茶管饱*,难道不比那些黑心店道德?*等过了日子,价钱自会回落。*”
她指指厅堂中央:“既然囊中羞涩,想赚些资费去白岛,不如去那厅堂露两手,既能寻个热闹,又能筹到钱,岂不两全其美?”
厅堂南北角坐着个卷毛书生,祁钰,一听这话,起劲不少:他叫了一壶清茶,*吆喝着给三十文能换个故事、五十能问他讨主意、百文可绘小像一幅。见有人来,他便往边角挪一挪,抿嘴一笑:“缺钱的人是多,但手头松快的也不少。徐娘子厚道,只抽一成,若有一二进账,房钱便不愁啦!”*
莫致远来到顺水客栈时已近晡时。客栈内宾客如云,厅堂中央热闹不已,不时有喝彩声传来。莫致远八卦,最喜听人讲故事,也爱凑热闹。他站在人群外,试图踮脚往里瞧,奈何个儿不高,前面人头攒动,压肩叠背,形成一堵人墙,密密地围着桌子,挤不进,也看不清。
不知是谁喊了声,谁替我家阿喵画张像,无论画技好坏皆有赏!人群躁动起来,摩拳擦掌,去寻笔墨。莫致远本扒着外围的人努力往里瞧,人群这一动,反把他卷了进去,一个重心不稳,摔进中央。
“这位小友可是来画像的?”莫致远被人扶起。抬眼看那人,正是方才喊话的男人:他身着一席青衣,长发细致地盘在脑后,鬓边垂下两缕微卷的乌发;皮肤白皙,额头中一点彩绘,两目细长上挑,闪着狐狸般的狡黠,形体偏瘦;身上似有海水的咸腥味,莫致远隔着一层布料,隐隐感到那扶着自己的手透出一股寒气。莫致远谢过那人,咂摸着既然来了不如就试试,有钱不赚是傻瓜,正巧自己善绘。便应了声,从身后背着的木箱中取出纸笔,问对方要画什么。
男人从身后掏出一个脑袋大的圆玻璃缸,里面盛着海水,一只鱼儿在里面游动,缸底还铺了些彩色的碎石。
“这是我家阿喵,”男人笑道,“我平素最疼他,趁此良机,想在人群中找几位能人,买几幅阿喵的画像。”
男人把鱼缸放在桌上,请莫致远落座。莫致远熟练地将宣纸铺在桌上,研墨作画。男人见他这般动作,猜他是有备而来,赶忙问道:“看小友动作娴熟,不知是否是画师?”
莫致远不好意思地挠着头:“画师算不上,只是我个人爱好罢了,平日常画。”
男人恍然大悟:“啊,原来如此。那不知小友是否会画抽象的风格?”见莫致远投来不解的目光,男人赶忙解释:“是这样的,鄙人偏爱些简约却又夸张、灵动的线条,希望你能放大鱼儿的特征,越夸张越好。”他捧着那玻璃缸说道:“你看,我家阿喵最大的特点就是这黯淡无光的死鱼眼;摆一副臭脸、像是谁欠他钱似的。我平时与他谈心,他动不动就游走、拿屁股对着我!就是不知小友能否在画作中展现这一特点?”
莫致远尴尬笑笑,心想这人还真是爱自己的宝贝鱼儿,竟能从中看出如此多门道。他贴近玻璃缸仔细观察,这鱼儿确实与常鱼不同:鱼头两边夹着两根海草,月白的鳞、光照下反着淡淡的彩光,尾鳍有四片,见莫致远盯着他,竟真的露出个无语的表情、转身背着人!
真是奇鱼,也难怪惹人宝贝。莫致远不再多想,记下鱼儿的特征后,开始作画。
抽象画不需多少气力去刻画,莫致远不消一会儿便画好了,习惯性地在画纸左下角落款。男人拿起那幅画观赏,发笑乐道:“好好好,小友真是妙手丹青,寥寥几笔便如此生动!都说艺高的画师多用左手作画,小友定也天赋异禀。这幅画我要了,这是给小友的报酬!”男人慷慨地从怀中掏出一枚银子,抛给莫致远。围观众人见他如此大方,纷纷向莫致远买笔买墨,也要露上一手;原本坐在角落的祁钰也来凑个热闹:这活动不比自己叫卖的百文画像来钱更易吗!
人群闹哄哄的,莫致远捂着赚来的钱趁乱从人缝中溜出去,绕着客堂兜转两圈,找到最外围刚吃完走人空下的小桌,坐下,边歇息边看他们吵闹。
待热度褪去,祁钰坐回角落,厅堂内安静片刻后,有人觉得无趣,便掏钱问祁钰先前喊的三十文买个故事还作不作数:“今个儿就当我请大家听书,我多拨些钱给你,你权当一次说书先生,给在座的各位说说那鱼仙的故事罢!”
祁钰一听来活儿了,笑着收下钱,学着说书先生那般从袖中取出一把折扇,“啪”地一声拍至桌面,端着嗓子讲起一段轶事来。
窗外电闪雷鸣,船只下沉的刹那,杨承圭借着这摇晃的瞬间,向前一步,试图靠她更近。一片漆黑中,那微不足道的一点光芒并不能让唐挽看清他的眼神,混沌的,或者迷茫的,她只觉得很陌生,又莫名感到悲伤,可她分明从未了解过他,为何会生出如此复杂的情绪来?她无法理解。
杨承圭伸出手,意图那般明显,唐挽知道,自己应该避开、应该拒绝,可她却仿佛被不知生自何处的情愫蛊惑,忘记了如何躲闪,任由他轻轻握住自己的手。他的指尖点在她紧攥成拳的手背,隐约可见松动的意图,于是他用叹息般的语气道:“我何曾阻止过你。”
是了,唐挽想到他们为数不多共同度过的时光,杨承圭从未干涉过她那些在父亲母亲眼中离经叛道的行为,他从来不会说不,也不会认为她奇怪。父亲指责她的时候,杨承圭往往都在场,他会试图让自己变得透明、无人在意,可唐挽总免不了被拿来与他相提并论,在父亲的指责声里,那是杨承圭唯一一次出言反对在家里堪称一手遮天的男人。
那天傍晚,他们在花园里相遇,杨承圭带来了符合她口味的糕点,彼时唐挽对他仍旧抗拒,认为这个凭空出现在自家、所有人都喜爱他的少年不安好心,但因为他白天的那些话,态度不由也软和了几分,默认他坐在自己身边。泉眼无声,檐楹落于明镜,几乎要烧起来的天空把一切都染红,杨承圭轻声对她说,阿挽,你要做你自己。语气坚定,掷地有声。
首柱荡开湖面的波纹,轻轻的碰撞唤回唐挽走丢的思绪,她看着面前的男人,杨承圭是极其善于用谎言掩盖真实想法的怪物,是危险的,是疯子,她不能信他。于是她迅速抽回手:“你也没资格阻止我。”
“航行的这两天,你可曾看见什么?”杨承圭似是料到她会如此行动,只是无奈地笑了笑,有下船的人擦肩而过,他却只是立在原地,一动不动地看着同样未有行动意图的女人,“此地与世隔绝,更是与人类社会不同,阿挽,若是迈出这一步,便当真无法回头了。”他看向身后,“你瞧见那花了吗?”
“花?什么花?”
杨承圭摇了摇头,竟不知从何处拿出一朵白色的花来,娇艳欲滴的花瓣上仿若沾着露水,又好似绝望之人的眼泪,他俯下身,靠近她,试图将那朵花轻轻别在唐挽的耳后。
“簪花作信,仙缘降临,保我平安,佑我长寿……”他忽地笑起来,只是这一次,却透露出些许的的冷意,就连那原本一直微笑着的眼睛也失了如沐春风的温度,“就像这样——”
“啪”地一声,唐挽冷着脸,毫不犹豫地拍开他的手,后退半步,任由那朵花跌落在地:“你想说什么?”
“我是想说,花虽好看,但却不一定适合。”他弯下腰,捡起那朵被地面弄脏的花,在唐挽的目光中一点一点把花瓣撕下来,他把花瓣揉成一团,揉得粉碎,往海边洒去,恍惚间如同落雪柳絮,飘在澄澈透明的海面上,露出里面漆黑得可怕的花蕊,“就像这朵花一样,里外截然不同,若仅有一面之缘,谁能看透?”
“你不想我来,不想我登船,还在此刻阻止我上岸。”唐挽看着他,“与你有关,还是与他们有关?事已至此,我没有回头路。”
“我说我不想,你就会听么?”杨承圭笑道,“你是如此固执的人。”
她越过他,越过后续的人群,径直往前方走去:“这是我的事,我不可能半途而废。”顿了顿,又回过头,“若这是你的劝告,我会记住,但不会听。”






杨承圭的手心带着寒意和湿气,猝不及防遮住她的视线,隔着薄薄一层眼皮,唐挽只觉得冰冷,眼前被漆黑遮盖,她无比清晰地听见他的声音,叹息、悲伤还有一些她无法辨识出的情绪,他道:“阿挽,不要再看了。”
她应该出手,应该拒绝,应该甩开身后这个一路追着她至此的男人,走到前方的沙滩上看个究竟,可她动弹不得。在瞥见那道耀眼光芒下诡异的、不属于自己认知里任何一种生物的、仿佛化为实体的震惊和恐惧的存在时,她便已经忘记如何前进。
细细想来,这一路的一切都是如此怪诞,仿佛路边偶有听闻的志怪小说,可话本毕竟是话本,谁能想到有朝一日竟成了眼前真实发生的事情?无论是水下拥有鱼尾的“鱼仙”,还是那道端至眼前、散发着诱人气味的汤盏,亦或者寻了一路,最后化为乌有的“芸娘”,她都有置身梦境的虚幻之感,过去不是真实的,现在不是真实的,或许将来发生的也不是真实的。只是……不真实便不能被接受?不真实便不是真实么?
她来不及胡思乱想,陌生又熟悉的声音将她飞走的魂魄归位,唐挽不得不承认,是杨承圭的声音唤回了她的神志,而后者察觉到她的变化,却并没有松开手。
很久以前,某一年的灯会,她接受杨承圭的邀约,随兄长一同结伴来到集市。唐挽并不喜欢热闹的场景和热闹的人,只默默跟在二人身后,偶尔大胆的女子前来与兄长或杨承圭搭讪,她也只是默默后退,装成不会说话的哑巴,沉默得不像是来游玩,倒像是有什么深仇大恨难以释怀。
杨承圭买了一盏漂亮的花灯给她,递到她手中时,灯芯的烛火被风吹动,映着杨承圭笑意未曾散去的脸,也留在她的瞳孔中,唐挽问他,你有许下什么愿望?杨承圭回道,我自然是许了的。她并非是会对这些事情感兴趣的人,只是觉得既然来了,既然买了,若是什么也没留下,多少有些可惜,杨承圭似是看透她的心思,笑了笑,坦白愿望的话还未说出口,意外先一步而来——鼎沸的人声中,就在他们的面前,出了命案。
离得太近,近到避无可避,唐挽循着呼声转身,杨承圭快她一步,伸手捂住她的眼睛。那个时候,他也是那么说的,用不同的语气说着同样的话,他道,阿挽,不要看。
可是现在,一切都和那日不同,没有映得夜晚明亮如白日的灯火,没有喧闹的人群,有的只是满地的白沙,和那一日在自己身边的人。
如果他还能被称作为“人”的话。
这一趟旅行并不长,但杨承圭暗示了太多,饶是唐挽再愚钝,也不可能不明白他的言外一致,何况从一开始,从兄长的重症不治而愈开始,她心里已经隐约有了猜测。
唐挽伸出手,毫不犹豫地握住他的手腕,她长期习武,双手指腹都留下练习得来的茧,此刻不偏不倚紧贴着他脉搏的位置,感受着逐渐加快的心跳,这是她的威胁,她道:“你和她是一样的么?”
“我和‘她’?”杨承圭用含糊不明的语气重复了一遍,却始终没有认真地回答,“阿挽,你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她忽然明白,她全然是被他引导至此,是他一步一步、刻意要她发现的。于是唐挽用力挣脱开,面对他,手已经自然地搭在自己的刀柄上:“你究竟要做什么?”
“现在你什么都知道了。”杨承圭却笑了,他的目光扫过这片本旖旎的海岸风光,“‘鱼仙’本就是如此残忍的东西,这里是一切的终点与尾声,也是一座沉默的、活着的坟场。你若在当初也服下那碗药汤,如今你我就是同类,只是我是如此了解你,你又怎么会上我的当呢?”
唐挽难得见他露出这样轻松的笑容,说出的话却让她毛骨悚然,他继续道:“阿挽,你知道你应该做什么。”他抬起头,与她四目相对,头一次没有躲闪,头一次如此坚定,他道:“我是害死了你家人的罪魁祸首,我把你珍视的兄长与父母都变为了我的同类,阿挽,你应该杀了我,为他们报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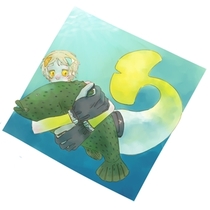
【云阙. 起】(上) 抓住那个负心人
这是来白岛之前的事了。
初夏。酒楼。朗朗乾坤。
好几个家仆打扮的人半是簇拥着一个年轻少爷。此人平民打扮,头戴青玉箍,上面雕的不是竹而是一支小花;身上穿着素衣,外披一件浅绿色的轻薄的长衫,比不上达官贵人家公子的规格,但也用料很好。他捏了把小扇,扇尾也挂着一枚花形的玉坠,其他物件都是随从们拿着,一副甩手掌柜的模样。这年轻人便是如今的林付清了。
现在的他面色红润,行动利索,一如常人;原本留在这具躯体上伤痕也几乎消失不见。但林家仍是对他严防死守。这具肉身对鱼仙来说是费了心思寻得的珍贵之物,对林家来说更是如此;找到他,求得仙药,恢复到能担起林氏之子的面子,每一步都没有十足的把握,每一步需耗费的人力物力自不用说。若非还愿这个名头实在是天经地义,好容易救回来的小子想出这种远门是万万不可能的。
当然,对这具身体如今实际的拥有者来说,这里才是遥远他乡,白岛才是家。如今的“林付清”不会担心去的路途遥远,越靠近白岛他越安心。只是这话万不可对人类说,连念头也不能被他们猜出来。
林家虽然百般希望把他留在家里,但仙药非同寻常,知道它名号的人亦知此物近乎起死回生;何况再怎样说心疼孩子,也不能太长久地把他这样年纪的男子困在后院。即使如此,平日里出门想要走动,也得跟着一圈人。这些人像棋盘上的黑子,把他牢牢地困在中间。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
学堂学子们的念书声高高低低的沿着微热的风在水面上流连,酒馆里的人们则在眉飞色舞地高谈阔论着更为生动的消息:妇人产鱼。
这个听起来十分骇人的消息,依附着含糊不清的口舌弹跳,沿着街巷一路飘荡,将林付清引到此处。虽然这个说法玄乎又吓人,但也许毕竟是在城镇中,周遭的百姓并没要对此事的真伪一探究竟,也没要拉帮结派去踹门烧家。人们更感兴趣的是那个不成体统的小丈夫—
“听了吗,那周家小子这次可真是闯了祸了!”
“那小子之前就疯疯癫癫的,好容易结了亲,老婆刚生,就闹出这么大事,唉。”
“要我说这姑娘找他就是瞎了眼。”
“听说娘家大舅拿着棒槌来坐镇了,到处找他呢…”
“他以前倒也是个正经的读书人,不知怎么就疯疯癫癫的了,搞不好是染了什么毛病。”
“他们读书人不喜欢搞什么五石散什么的吗?”
“也有人说是结交了贵人,吃了丹药,就受不了这民间苦楚了。”
---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
“可我听说,这次倒也不完全怪他,也不知道是不是他中了邪,听说他老婆生那孩子有点不对。”
“怎么不对?他之前就三天不着家的,不知去哪里鬼混,老婆生孩子也不见他,生完了他才偷摸回来看一眼,又跑的鬼影也没….”
“也不是,听说那孩子生下来倒不全是个人样,那周生喝醉了跑回来看一眼,吓得连滚带爬的跑了…”
“他怕的是那大舅子吧。”
“药铺的那王二说,看了一眼,说生的那娃娃好像是个鱼,不是个人。””
“人能生鱼?那不妖怪了吗。”
“可我听人说,锦鲤入梦,那可是好兆头,生条金锦鲤,可不是他周家祖上添光了吗。”
“但总归生了怪孩子,也不好处理吧。”
“要不,你去看一眼?”
“可别,那大舅子已在门口骂了那周生三天三夜,一副要拼命的样,我可不敢去触霉头。”
---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
林付清吃着茶听着,眼睛却看向对面一群人。为首坐着品酒的是个穿着阔气的女子,也是前呼后应,听着周围人高谈阔论。此女粉面桃腮,犹然少女,却作妇人打扮,将一身锦绣撑的十足体面,举手投足间也是当家作主的气派。这正是景颐舒,如今该被唤作齐夫人,乃是明州行商大户景氏的独生女,齐家的新妇。但与这两家打交道的人都知道,年轻一辈中,大抵是她说了算的。只是这些也不是景颐舒“本人”的能为,而是某位鱼仙入世后一手打造出的局面。人类赞叹景家千金年轻有为手段了得,对付心人来说也是如此。活用人类身份带来的附加价值,远比单纯寄宿其身要有用的多。
林付清看了她一会,那小姐便也转过头来。两人对视片刻,对彼此身份心下了然,景颐舒便指了个侍女去邀他过来。景氏、林氏,在商场上也是有头脸的世家;纵然两个小辈是初次见面,相互一报名号,便足够应酬起来了。林付清自然从善如流,过去和她拼了桌。两条鱼穿着人身,按着人的规矩客客气气的寒暄一番,不动声色的接了头。
林付清很快便看出,紧跟着她的那三个侍女也是鱼仙所附的付心人。这让他吃了一惊。景颐舒见他眼色,扬眉一笑,微微点了点头。
若是一群人中同时出现太多付心人,一旦露出马脚,难免让人疑虑;但若安排妥当,身边有同伴彼此照应,比单打独斗要便利许多。人类的身份会带来很多东西,但也有很多制约,总是福祸相依;身为鱼仙,在无数流转的记忆中,在来到人世后,他也早就明白即使对人类中更为身份尊贵的人来说,也是被各种规矩约束,不能轻易坏了章法。如何运用自己的身份,如何运筹帷幄,谁也不曾有真正的把握能不冒风险,万无一失。鱼仙如此,人类自己也是如此。
眼下,林付清看着对方把身边人安排的井井有条,认为很有必要学习。林家在全力照顾他,却也处处掣肘他。本来他选这个身份,也是看中对方有无论如何都要保他的理由;可如今他有事要做,就必须设法打破这份禁锢了。
二人又叫了点点心,一边听,一边低声聊起这桩奇谈。
“不知林少爷这事怎么看?”
“在下是途径此地,对此地不熟,这事听起来倒是有趣。那周生不像良人啊。”
景颐舒点点头,指尖在杯口上转了半圈。
“听闻他本也是好学之人,不知日前染了什么瘾,发了什么癫,性情大变。”
“哦?那不请个道士,去给他驱驱邪吗?””
“都是街坊邻居,从小看到大,说是性情大变,无非是突然胡作非为,失了男子汉的体面。”
“要真像大家所说,他弃了妻儿不顾,那确实混账。可怜那孩儿却无父照顾。”
“若那真是锦鲤孩儿,倒是他有眼无珠了。”
“自然。在下听海边人说,鱼婴诞世乃是仙人指路,要供奉才是。”
“可不是嘛。周生那妻子于氏,倒是我家铺子里个小掌柜的外甥女,说起来,也不是外人。”
“那如今能主事的也只有齐夫人您了。”
----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两人一唱一和,便起了身要到对方家里去瞧瞧。
林付清一站起来,书童便伸手扶他,一手抓着他的手肘关节,一脚不露痕迹的抵在他步前。护卫也上前两步,绕到他右侧身前,回身对他一揖,说道:“少掌柜,此等杂事,又有血光,还是三思。”
两人一左一右,不动声色地把他堵在这了。
景颐舒挑了挑眉,笑道:“哟,好好一个大男人,倒比我这小娘子要护的紧了。”
侍从一愣,不好再当面开口。林付清假意气恼地挣了一下,书童略松了手,却被他反手握住。“林付清”照着记忆里的样子对书童展颜一笑:“少爷我倒也不是做不了事。”
书童盯着着他的脸,一时说不出回话来。护卫看着他们仨人,不得指示,也只好原地不动。
景颐舒便大大方方的伸手来拉林付清,笑道:“要走就走了,光天白日,有什么好扭捏的。”
书童只得收了手,朝护卫使了个眼色。两人退回到林付清身后,不再阻止。
景颐舒的侍女们绕在身旁,不动声色的把他们微微隔开。
酒馆里仍在兴高采烈地谈着传闻,对口中的事有多少真假浑然不知。
---予羽谯谯,予尾翛翛,予室翘翘----
t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