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 Jolie宋朝篇
欢迎来玩
对不起这次主线拖了很久,辛苦大家的耐心等待,下次一定写完再开!
后日谈预计将于3/5发布,计分统计将于清明节截止。






【沙海】
唐有戍边将军圭,腊月追凶塞外,妖风卷沙骤起,圭陷石林迷阵不得出。及入夜,伸手不见五指。众军茫茫然行至寅时,忽见前方有水草洲,芳草丰美,碧波荡漾,浑不似大漠一隅。圭遣兵士探查,回报:“有鲛仙。”圭不敢信,亲上前看果有一鲛人老者居水中,白发白须,道骨仙风。见圭来,施施然作揖道:“此处仙洲,大军可栖。待明日尘定雾散,向东南方去便可出。”圭问其何居沙土中,老者答:“吾幼时,此处仍为沧海,一日替阿母寻七宝簪至此地,久寻不得,回首水路已断,不得还家,乃居于此。”众人安睡一晚,次日果然风定,圭临行谢老者,问当如何报谢,老者曰:“金银绫罗于吾何用?吾救汝等非为求报也。”圭再三问,老者终思忖言道:“汝既心诚如此,便将还家时所见第一人送来此地为吾沏茶。来时敲石林西北第三柱十下,此径方显。”圭疑犹,久久不能应,老者大笑三声曰:“既如此,只当胡话,不报也罢!”
后圭领军捉凶而返,受重赏升官还长安,未入朱雀道便见幼子侯之城门下。圭顿时心下慌慌,始终不敢将所历之事与家人言,三月未能入眠,憔悴万番,瘦如白骨,终日卧于病榻,将咽气时,方对妻子坦言。幼子闻之曰:“此有何难?受恩报德乃天纲伦理,吾去便是。”于是驾马出关。自子离去,圭竟气色渐佳,不出二月恢复如初。次年大暑,圭与妻用膳时竟见幼子返家直入内堂,问之,曰:“未见鲛仙,乃返。”圭妻忽觉幼子行无足音,看去时但见脚掌及髌飘如云似雾。幼子曰:“吾去添箸来食。”向院内去,直穿画屏花墙,竟如青烟消散,后不复见也。
【雷猴】
昔猴戏艺人养猴十余只,平日极尽打骂,若不得空,便着家犬看管。此犬机敏,知是唇亡齿寒,因此往往宽待猢狲众,偷吃胡闹之事亦是能瞒则瞒。
一日群猴商计出逃,意欲骗得锁链钥匙。家犬悻悻呜咽:“猢狲又说梦!休等那人开你猴脑才求饶。”为首老猴取一杏掷家犬:“蠢狗,你且瞧着!我原是北海震洋宫学徒,因下山时应了师父不得滥用仙法才隐忍到当今田地,今日为了孙儿不得不出手相救。”
恰逢黄梅,过午常有雨。每至此时,老猴带头长啼,众猴齐齐附和,须臾便有惊雷落下。及当落雷,总有猿啼。初几日养猴人只当巧合,继来却愈发疑心。但见雷光过一日便离此屋近几里,一周之后,忽得一阵电光闪烁,险险劈中狗食盆。
家犬怒吠几句骂道:“腌臜毛猴,差些害死你狗爹!”
老猴双手抱拳嘻嘻道歉,继而道:“今日便是最后了!”
当晚猴戏艺人半夜出恭,抬头一望月明星稀,便安心踏出屋外。正在此时,只听身后一声猿啸,竟顷刻暴雨,一道天雷自九天降,将院中老枯树一劈两半倒在艺人脚尖前。那艺人吓得裤裆湿透,连滚带爬开了猴笼,连呼:“猴爷爷饶命!”
那老猴带着众猴将将行去,家犬出门来送,疑惑道:“猢狲也会仙法,竟真有此等奇事?”
老猴从怀中掏出杏子递上,道:“何来仙法!我不过在震洋宫吃过几年桃儿果儿。”
家犬问:“既如此,何以喊得天雷?”
老猴道:“一次是巧,两次便教他人半信半疑,三次可使人确为仙法也。”
话毕,跃上邻家青瓦离去。
【█████████案】
███年██路██府载,有█报官称见有██女作凶连杀夫家自家█人纵火烧山。因派捕役,此女姓█名█,曰:山火█雷所致,夫家█口死山火,唯██幸存;问其父母,女曰:母早年██而亡,父前日仙游██去。捕役疑,然连搜█日不见尸,以██盘问,亦不变供词。女自称当日█时及█时田间劳作,往来者可证。后捕役寻得一██相士证此为实。█日遂释。后有村民言:此女█月前诞█婴,乡内皆避,██████,其夫███亦欲休之。或为██人言栽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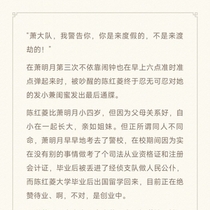
一
初见尔菁菁时他跟在哥哥后面,等着人们从尔府来的马车上下来。
先下来的是尔氏的老爷,他去同站在最前面的父亲谈话,而后下来的是一名丫鬟,下了马车后她转过身去掀开帘子,另一手伸到车门前掌心向上。很快一只更加纤细的手搭在她的手掌上。
“小心点,小姐。”
在丫鬟的叮嘱中从车里钻出一名女孩,她稍短的头发挽不成髻,便被扎成了一条俏皮的发辫,上面簮了许多小花似的装饰。只不过她看起来却远没有明艳的衣服和发型那样活泼,从她浅灰色的眼眸中林衡看到一丝疲累造成的阴翳。
“菁菁,”女孩走到尔老爷身旁,中年男人的大手握住她的小手,好像握住一枚铜钱一样容易,“可还记得权儿?”
“记得,”尔菁菁的声音很低,像空气中微不可查的一缕风,转眼便散了,但周围人仍能记得她的声音,她对林权露出微笑,好像花丛中最不起眼的小白花,但是林衡知道她是林权最喜欢的那朵花,“权哥哥。”
“菁菁妹妹,”他的哥哥几乎为他的菁菁妹妹犯了相思病,不仅每天都要同他谈起,还要反复地说尔菁菁是最好的女孩,将来也会是他最好的嫂嫂,一开始他还认真附和自己的兄长,但后来实在不堪其扰,索性每天发奋在书房里躲清闲,“上次你说喜欢南山寺庙池子里的那几尾金鲫,我让娘托人求来两尾。我带你去看,这两尾鱼在佛门池塘中游过,说不定可以保你身体健康。”
“谢谢权哥哥。不过去尔府路途遥远,这鱼还是养在你家好些,这样我也可以时常来看你。”
“看你们关系这么好我和林老爷也就放心了,”原本握着菁菁的手的大手松开了菁菁,转而抚过她的头顶,“去玩吧。权小子,你家林昭可在家?你们一同去玩。”
“昭昭在家,她在后院看鱼呢,我带菁菁和阿衡去找她。”
这会儿他的哥哥才想起自己的闷葫芦弟弟。
“菁菁,都忘了和你介绍了。这是我弟弟,上次同你提起过。”
“我记得,你们果真长得一样,”尔菁菁同他微微欠身,“见过衡哥哥。”
“好啦,寒暄也寒暄完了,昭昭在后院池塘估计早就等急了。”林权走去牵起尔菁菁的手,好像将一朵易碎的花轻轻拢在掌心,“阿衡,快跟上。”
“来了。”
他跟上他们的步伐,将大人们关于什么“水运”什么“货物”的谈话抛在身后。他们没有走得太快,或许是顾及尔菁菁的身体,也或许是他的哥哥想要为第一次来到林宅的女孩仔细介绍一番家里那些他们引以为豪的摆设,让女孩更加了解他。尔菁菁则安静地听着他的介绍,偶尔被他故作幽默的言语逗笑。而他只是跟在他们身后,墙上的树影因为微风摇晃着,路过的下人们笑着对他们行礼,他听见他们说林昭还在池塘那里。
穿过最后一扇门,后院前几日修完的池塘终于出现在他们面前。父亲不擅长侍弄花草,也不喜欢为这些玩意儿费神,池塘是母亲亲自督工建起来的,凭依在池塘后面青石雕刻成的假山,点缀在水面的荷花水草,这些都是娘带着他们去市场一一挑过。那时哥哥紧紧挨在娘的身边,跟她一起商量选用什么样的建材来雕刻假山,假山应该刻成什么形状,水里的花草又要选择什么种类,如何打理……他只是跟在后面,出售花草的商贩也养着一缸金鲫,红色的鱼儿们飘逸的尾巴在水中摇曳,他满脑子都是苏子瞻的“金鱼池边不见君,追君直过定山村”,他也想要一尾小鱼,不必是拥有美丽尾巴的金鱼,也不必是在佛门池中受过佛祖教诲的小鱼。一尾普普通通又可爱的银色小鱼就够了,它可以跟在母亲求来的那两尾小鱼身后,那会不会有点太孤独?应该给它也寻个伴。
一会儿母亲唤他的声音响了起来,他的腿还没有蹲麻,便利落地起身回到了母亲和哥哥的身边。
但是能看看哥哥的金鱼也很好,偌大的水池中两尾小鱼间或在水下划过两道红色的弧线,有时悄悄掀开水面尚未挺起腰杆的荷叶,便能看到惊慌失措逃之夭夭的鱼儿们。
要是过几天那位尔小姐来时不会把鱼儿们带走就好了。
昭昭也很喜欢这两只小鱼,这几天他们经常挤在一起蹲在石头旁边看着两条小鱼在水中嬉戏。这时他们谁都不说话,水流潺潺,微风阵阵,或许鱼儿们之间会说许多他们听不见的话。偶尔林昭会突然想起什么诗句,然后慢悠悠地说出上半句,等他接上下半句。
他很怕林昭的“突然袭击”,虽然林昭不会把此事说给父母听,但接不上妹妹的题目还是有些丢脸的。他们喜欢的诗人和书目各不相同,因此总会有他憋红了脸,就连鱼儿都看不下去一溜烟地远去的时候。好在林昭并不嘲笑他,只是笑着说:“既然衡哥哥不会,那就要从你的零花钱里出钱给我买糖吃,不然我就去告诉爹。”
给妹妹买糖吃他自然是乐意的,他也知道林昭说去告状也只是逗趣,但这样多少有些拂了面子,于是今天他在林昭开口前抢先出题。既然是精心准备林昭自然是对不上的,但女孩却要更加坦然。思虑片刻后她摇摇头,“衡哥哥果然也很厉害,我答不上。今天我给你买糖吧。”
他本来想说不用,而在那之前,林权来了。
林昭立刻站了起来向兄长走去,他在原地缓缓起身,林权冲他招招手示意他也过去。
“权哥哥,”林昭说,“是菁菁来了吗?”
“嗯,马车马上就到了,阿衡等下和我去门口等着。”
“我不用去吗?”
“爹说不用那么大张旗鼓,你在这里等我们就好。”
“好。”
“走吧,阿衡。”林权又招呼他一声。
跟着林权离开后院时林昭和他擦肩而过,他回过头,妹妹已经回到池塘旁边,从屋檐底下拖出一只板凳。
于是当他跟在林权和尔菁菁后面回来时林昭坐在板凳上,她抬起头,目光投向他们的方向,站起身露出一个明媚的笑容。
二
时间一晃便过去了。尔菁菁的身体渐渐好了许多,来林府游玩的次数也多了起来,有时甚至能在府上一连住个三两月,平时他和林权要去学堂学习,而放假的日子大人们就会带他们一同出游。比起他们兄弟二人尔菁菁和林昭相处的时间要更长,先生和父亲也会严厉地要求他们先以功课为重。
但是有时他也会察觉出尔菁菁和林昭之间并没有林权所想的姐妹情深的模样,她们用礼仪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一段他人难以察觉的距离。但或许这是他的错觉,毕竟大人们对此并不以为然,哥哥也没有对她们的关系说些什么。他们四人就这么相安无事地一同度过了几年。
细密的雨点砸在池塘的水面,那两条金鱼早已死去,后来哥哥和尔菁菁一同去市场买回了更多模样的鱼,现在鱼儿们都安静地聚拢,像荷叶下盛开的另一朵花。他没有时间像那些小鱼一样安静地在层层雨帘之外歇息,跟着下人们匆忙的脚步,被人们围住的大堂中心已经被下人们举起的昏黄的灯笼照亮,那里除了兄长还有另外一个男人。
“哥!”
两人转过头来。
“阿衡,”林权离开另外那人,迎上奔来的弟弟,“菁菁出事了,我得跟着雁征去寻她。”
“什么?”他看到林权身后的尔雁征,曾经两家的家宴上他见过尔氏的几个孩子,这应当是尔氏最小的儿子,尔菁菁最小也最亲近的哥哥。宴会上的尔氏的小少爷衣冠整齐,大笑着同下人们玩笑供自己的小妹妹取乐,而现在他却几乎浑身湿透,碎发被雨水濡湿贴在额前,眉头紧锁声音沙哑。
尔雁征摇摇头,“前几天家里女眷提议去游船,二房王氏,奶娘苏氏和菁菁都在那船上,但不想天气突变……”
“时间紧迫,消息传来时距事故估计已一天有余,阿衡,我和雁征现在就得出发,今天夜深之前还能把岸边巡视一遍。”
“那我也……”
“你得留下来,”林权立刻抬起手按在他的肩膀上,“父亲已经先我们一步去尔府了,娘会担心的。”
所以必须要有人留下来。而那个人只能是他。
“……好,”他将手放在林权的手上,自己肩上的那只手冰冷十分,“哥,多加小心。”
林权和尔雁征走后林府里渐渐恢复了平静,只是雨仍没有停下,连绵的雨声代替嘈杂的人声灌满了无人穿行的院落。母亲方才没有出来,大抵是默许了兄长做出的决定。
他穿过无人的走廊,池塘里的鱼儿们没有任何变化,它们仍旧缩在水面下一动不动,挺立的荷叶被雨水砸得东倒西歪,至于那娇弱的荷花早就落了,粉色的花瓣沉进池底的淤泥,变得不见踪影。走廊尽头的房屋亮着灯,冰冷的夜色中燃烧出一团模糊而温暖的光。那是母亲的屋子,他得去和母亲说说刚才的事。
在远处时他没能看清温暖之外的阴翳,走近时那窗边的黑暗才完全向他敞开心扉,隐约呈现出一个人形的轮廓。他也来到这冷气侵入的阴影中,雨水的味道遮掩了一切,屋檐的边缘滴滴哒哒,雨水顺着倾斜的屋顶滑落。光晕染在屋檐外面被雨滴打碎的水洼里。
“怎么不进去,”他走去牵起林昭的手,攥紧在掌心,即使他感觉自己像攥住了一块冰,“不冷吗?”
林昭背着光,他看不清她的表情,甚至因为层层叠叠的雨声,屋内并不真切的人声,他不知道是自己没有听清林昭的声音,还是林昭没有说话。他站到她的身边,从屋里传来的声音清楚了许多。其中一个是母亲,另一个是侧室的李氏。
“现在这会儿阿权应该和尔家的少爷已经走了吧,”这是李氏的声音,听起来她们也在议论尔菁菁的事,“唉,姐姐,这会儿只有咱们两个,我也只是闲聊的,您别放在心上,要是菁菁真的……”
“既然知道自己不该说就闭上嘴。”母亲的声音同林昭的手一样冷,也叫他的心凉了半截。母亲和姨娘在谈尔菁菁的事故。
他已经十六岁,而林昭也几近及笄,他们早已到了懂事的年纪,李氏虽然没有把话说完但他们已经和母亲一样知晓她究竟想说什么。
如果尔菁菁真的不幸遇难,而爹还想继续依靠婚约维持两家的关系,那就只能让林昭去嫁给尔氏的儿子。
过去尔菁菁的身体虽然不好,但没人会想到她会夭折,娇弱的女孩有惊无险地长到十二岁,只要再过三年便可和兄长完婚,即使在那之后尔菁菁去世,双方也仍存在着这样一层关系。
父亲需要这样的关系来维系和尔家的来往。尔氏老爷尔棠多年之前便已是远近闻名的富商,后来尔棠携妻子亲眷定居此地,等安置好房屋亲族,他所做第一件事便是带着各种名贵礼物登林府的门拜访。作为刚刚上任不久的新官,尔氏的助力对父亲来说是无法拒绝的,一纸儿女间的婚约,父亲可以得到尔氏在钱财上的支持与各地的人脉,尔氏需要的却只是父亲在力所能及的地方为尔氏行商加以通融。而且官商两家加以联姻,双方能够从对方那里得到的也远不止商量过的内容。如果他站在父亲的立场,大概也无法拒绝这样诱人的条件吧。
房间里再没有声音。大概是刚才被母亲决绝的态度吓到,李氏不再说话了。林昭从始至终一言不发,只是在房屋里再次发出声响之前她悄无声息地从他手中抽离她那仍没有变得温暖的手。
“昭昭……”他下意识地出声挽留她,却不知道接下来应该说什么。
林昭因为他微弱的呼唤而停下脚步,她没有回过头,“……衡哥哥,”她说,“即使我之前未曾与尔氏的少爷们说过几句话,但只要老爷的一句话,我就得嫁过去。”
“父亲不会……”
“我知道他不会,老爷和夫人都待我如同己出,所以我什么都愿意做的。这也是我的命。”
林昭迈过接连不断的雨声,穿过走廊,去往雨幕的另一边,直到消失在围墙之后。
他站在从窗户透出的光线之外,久久无法动弹。
如果这一切真的都是命数,他想,天上的各路神仙,发发慈悲,让菁菁活下来,不要让林昭离开他的身边。
不知是他的乞求起了作用,还是尔菁菁真的冥冥之中有上天庇佑,约一周后便传来了林权在河流的某个支流岸边寻得尔菁菁,两人平安无事的消息。所有人都松了口气。
那之后直到尔菁菁痊愈,林权几乎完全住在尔府照顾着尔菁菁。期间他和林昭去看过尔菁菁一次。尽管身上还有些尚未痊愈的伤痕,但少女的脸色却红润十分,与之前那个病恹恹的女孩几乎判若两人。同行的母亲和父亲对尔家人说着“祸福必然相依”的客套话,在尔家人的会话中他才听闻,尽管身体变得康健许多,但尔菁菁却似乎因为事故中伤到头颅而害上傻病。她仍能辨认出熟悉的人,却遗忘了大部分往来甚少的人,礼仪习惯也忘记许多,脑子也没有以前那么灵光。
林权看向尔菁菁的目光仍同往常一样。她仍然是他最喜欢的那朵小花。
只是他却隐约觉得有哪里不对劲,从尔菁菁的言谈举止中透露出某种怪异。她说话时次序颠倒,行走的姿态不似常人,喜好举止也同以前完全不一致。如果只是傻病会让她几乎完全变成另一个人吗?
但这兴许也是他的错觉。眼下尔菁菁平安无事,从那起事故中生还,林氏与尔氏的婚约照旧,兄长对未婚妻不离不弃成了一段佳话,林昭也不必为此献身成就一桩自己不愿的婚姻,皆大欢喜,还有比这更好的结果吗?
神仙已经应允他的愿望,他应该感到满足了。
不久,他和林昭一起去道观还愿,这时他才第一次和其他人提起自己隐秘的许愿,但他没有告诉林昭关于她的那一部分。
“原来我是第一个知道的吗,”这会儿已经入秋,吹过的阵阵微风开始捎带上一丝凉意,林昭握在一起的双手紧了紧,“那我也告诉衡哥哥一个以前我从来没说过的事吧。”
他不知道妹妹有什么隐瞒的事,他们像亲兄妹那样生活许多年,而林昭竟然还有同他和林权隐瞒的事?
“其实我和菁菁的关系算不上好。”林昭抬手将鬓角的一缕碎发拢到耳后。
“你和……菁菁吗?”
“你没有看出来吗?”林昭反问他,他答不上来了,“衡哥哥,你只是不说。你总是这样。”
“我以为你们女孩子家就是这样相处……”
林昭摇着头,“我其实是喜欢菁菁的,她的性格很好,有时也会恰到好处地说一些应时的笑话逗趣,但这也是我不喜欢她的地方。”
他没有说话。
“她好似一个人造的玩意儿,她知道面对谁应该做什么,怎么做。对我和你,她知道应该维持我们的关系,便恰到好处地展现一个朋友的姿态。而我也是一样的,”林昭自嘲似的发出一声冷笑,“我们是同类相斥啊,衡哥哥。她和我一样,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便去做了,仅此而已。”
回家后他们再没提起过这段话,今天他和林昭的谈话从此只有神仙们听到。
三
尔菁菁的身体好起来后林权便回到了林府,他的兄长仍时常去尔府探望她,只是频率却渐渐减少,一年过去时,林权待菁菁的态度已变得远不如从前,于是尔菁菁来府上的次数开始变多,更甚她出事之前。兴许是林权态度的变化让尔府的人起了疑。
表面上林权风轻云淡,仍亲昵地称呼尔菁菁为菁菁妹妹,陪同她四处游玩,但是某天他看见了站在金鱼池旁的二人,林权悄悄避开了尔菁菁伸来的手。
家里人都不知道林权和尔菁菁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父亲甚至因此将林权找去语重心长地谈话,要他不要因为菁菁害了傻病便嫌弃她,他不知道哥哥是怎么回答父亲的,只知道那天父亲发了很大的火,哥哥被赶出书房,父亲责令他不管尔菁菁变成什么样都要忍着,不然就滚出林家。
这纸婚约对父亲很重要,母亲显然也知道的。但她仍怜惜自己的儿子,只是她已然成人的儿子已经过了能轻易敞开心扉的年纪,面对母亲和父亲,林权只是皱紧眉头,闭紧嘴巴不住地摇头。
最后了解各种缘由的任务只得落在身为林权弟弟的他身上。
尽管在其他人看来他和哥哥一胎双生,是不折不扣的孪生手足,世上不会有比他们更紧密的关系,但实际上,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只是不知不觉间他和林权之间的关系也不胜从前,他们已经不是年幼时会把时间放在一起疯玩上的兄弟了。
但他仍去找了林权。
看到林权时,他的兄长背对着他站在金鱼池边,微微低下头,鱼儿们的影子从他眼中的池塘划过。他走到他身边,同他并肩而立,林权没有抬头,金鱼的尾鳍在他的眼中掀起一丝波澜。
“母亲让你来的。”
他的哥哥现在或许称得上除了父亲外最了解这个家的人了,因为他是家里的长子,他要负起对这个宅邸,对这里的一砖一石、一花一草的责任,“那你会告诉我吗?”
而他却连自己的哥哥在想什么都猜不透。
“阿衡,你只是什么都不说。你是局外人,你看得总是最清楚的。”
他心里一紧,“……兄长,慎言。”
“怎么,你是我弟弟,我还有什么不能与你说的吗?那我们可真是这世上最孤独的一对兄弟了。”
“那你是什么时候觉得菁菁不对劲的?”
“只是突然之间,我觉得自己在看着一个和菁菁长得一模一样的陌生人,”池塘里的鱼游累了,它们在池塘的角落里缩在一起,一动不动,“从前我问过菁菁是怎么分辨出你我的,或许对于菁菁来说就是这种感觉。”
“有这种可能吗?”
“所以我也想过是不是我多想,世间总不可能真有怪力乱神之事,”林权将手放在他的肩上,“总之此事你知我知,不要说与其他人听,会惹出事端。”
“我知道。那你……”
“我会自己看着办的,别担心。”
事已至此,他知道无论和林权说什么他都不会停下来的。也正如林权所说,没有证据的情况擅自说出这些事只会节外生枝,于菁菁的名声和两家关系都不好。没有必要只是因为感觉上的事就让两家生出芥蒂。
他们兄弟二人为此默契地保持沉默,不再同其他人提起他们心照不宣的怀疑,只有林权自己私下对尔菁菁进行着调查,直到父母也不再追问这些事,好像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那些惹人怀疑的事情已经不了了之。
但是在他从兄长那里得知一切真相之前,林权疯了。
“哥?”
漆黑的夜里,地面因为融化的细雪而变得湿润,林权的脚上因此沾着泥土,他只穿着一层单衣,头发没有束起,披散在肩头,当摇曳的灯火为他分去些许的光亮,他的身影反倒显得愈发单薄。
“大哥?”
不知哪条鱼在水中甩起尾鳍,水面发出被击碎的声响。
“林权!”
池边被照亮的是一张同他几乎完全一致、神色惊慌的脸,而后很快他的兄弟逃也似的远离到灯光之外,只有他站在原地等着寒冷与不安在他的心中生长。
一开始林权只是时常发愣,他越来越多地被人目睹站在后院的金鱼池前一动不动地盯着池水和金鱼,当别人唤他的名字时要好一会儿他才缓缓地反应过来,这时他的目光犹疑在来人和池水之间,像是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
恰逢母亲的生宴快到了,年终几近,朝堂之事也多了起来,父亲为此北上京城,家中大小事务便大部分落在林权身上,因此林府的人都认为林权只是休息不足。郎中开了些安神静心的药,嘱咐林权多加休息,他和林昭也为此分摊了不少活计,希望兄长能尽快恢复精神,不要在年关得病。
然而,林权的情况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好起来,府中的闲言碎语渐渐多了起来,母亲惩处了一批嚼舌根的下人,但谣言和传闻却无法就此根除,像始终无法恢复的林权。
他和林昭轮流照看着兄长,当屋子里只有他和林权时他屏退周围的下人,试着询问林权是否他这幅样子和尔菁菁有关。
有时林权能理解他的问题,他的衣袖和肩膀被林权紧紧抓住,这时林权眼底乌青,双眼布满血丝,他已许久未能顺利入睡,别人看不到的幻境和妄想紧紧裹挟住林权,使他的兄长几乎无法脱身。
但是他只是说着“竟是如此……!但我不明白,究竟是何时……阿衡,你不要去接近她……她不是尔菁菁!!”这类的胡言乱语,他不知道兄长曾经究竟看到了什么,又发现了什么秘密,唯一知道的只有这一切都与那女子有关。倘若那个与尔菁菁外貌完全一致的女子不是尔菁菁,那她又会是谁?
只是林权已经不能给他更多的解答,更多的时候他都双目放空,一动不动地盯着天花板,像休息的金鱼,忽的又开始精神失常嚷着要回到某个地方,叫喊着这里不是他的家。
在京城听闻此事的父亲甚至从京城带回了一位名医,但也未曾瞧出兄长究竟何时、为何患上这样折磨人的病来。新年来了,林权的病情仍不见起色。
子时,母亲将包了碎银子的红包挨个放到他和林昭的手中,平日里他们兄妹三人已经可以得到丰厚的零花钱,因此压岁钱只是依据习俗为他们讨个彩头,期盼来年家里能够风调雨顺。两人的红包已经分完,却还剩下一人份,那是属于林权的。没有人提起这档事,等林昭到红包,整个房间里忽然陷入一阵沉默,只有外面的爆竹声不停地响起。
林昭站起来从桌面上拿过那无人认领的红包,“我去交给权哥哥。”
母亲抬起头张开嘴,但声音尚未从她的喉咙中离开,父亲已经先一步开口,“阿衡,你跟着昭昭去。”
父亲也不知道现在的兄长究竟对家人会做出什么反应。
他和父亲对视一眼,点点头起身作揖,“孩儿知道了。”
下人为他们拿来袄子披在身上,他从下人手里接过灯笼,跟在林昭身后。穿过走廊时,升起的烟花照亮夜空,一朵谢了,另一朵又升了起来,林昭的背影在他的眼前时而清晰时而模糊。他们之间没有说一句话,等到了林权房间门口林昭才转过身来。
“我进去就好。”
“可……”
“权哥哥现在的情况还是不要看到太多人比较好。”
他没有可以用来反驳的理由,只得点点头。林昭推开门走进屋内,但没有关上门,他倚在门框旁边。周围的烟花已经停了,只有远方的爆竹声的余韵传来,房间里林昭的脚步声清晰地传来,停下。她已经走到林权的床前。
“权哥哥。”
布料的摩擦声。
“我是昭昭,新年到了,父母和姨娘给你包了红包,我拿来给你。”
“是你……是你……”林权的声音响了起来,却很快又消失不见。
远处的爆竹声也已经完全消散,完全的寂静降临在新年的深夜,直到病人的吼叫击碎了这一切。
“别过来!!你这怪物!别靠近我!!”
瓷器碎裂的声音和少女的尖叫同时响起,紧接着从走廊的另一边杂乱的脚步声越来越近,而他已经进入房间。当下人们赶到时看到的就是满脸是血的林昭倒在地上,而他则抓住林权的手臂勉强将他制服在床,他让自己的声音盖过林权的叫喊,“快把昭昭带走!来人帮我按住大哥!”
直到他离开房间去看受伤的林昭也仍能听到林权的嚎叫。
“别让她来!别让我再看见她!!她是怪物!!”
从红色纸包里滑出的碎银子散落一地,无人将它们拾起,从门口进入的月光照亮这些碎屑,好像它们是传说中人鱼的泣泪。
第二天,来为林昭检查的郎中对父母和他摇了摇头。
林昭患上了失语症。
外伤可愈,心伤难治。在大年初一父亲做出了两个决定。第一个,等正月十五后,娘要娘家探亲,她带着林昭回到娘家让林昭在外公家住上一段时间以疗养身心。至于第二个决定——
“什么?”他看着父亲,好像没有听懂他的话语,“什么……意思?您是说我来……”
“你来顶上阿权的名字,也就是你们二人要交换身份。”父亲用强硬的语气重述他的决定。
“可是我和大哥也不是完全相像的,万一被识破……”
“只要你够努力就不会。”
“但是——”
“那你想怎样?!难道要让那个样子的林昭替阿权去履行婚约吗!”吼过之后父亲似乎也觉得自己有些过于激动,他站起身走到他身边,他这才发现父亲脸上的疲态几乎无法遮掩,父亲好像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阿衡,”父亲的语气几乎在哀求了,“为父只有你了……”
他的肩膀被父亲捏得生疼,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他无法吐露任何拒绝的言语。
“孩儿……知道了。”
从那天起林府对外放出消息,长子林权患上疯病是子虚乌有的谣言,患病的其实是小儿子林衡。为了医治林衡的病,今年大暑时节,长兄林权将会携未婚妻尔菁菁乘船前往白岛为林衡求得仙药。
这是一段多么令人感动的故事,林权对患了傻病的未婚妻不离不弃,林权为自己疯魔了的弟弟去鱼仙聚集之地求药,林权,林权……只要父亲想,林权就必须是干干净净,纯洁无瑕的,这样才不会抹黑林氏的名声。
即使真正的林权被锁在房中,发着让人惊惧的疯。
十五天的年节一眨眼便过去,正月十五那天尔氏来人带着尔菁菁到林府过节,而此时他几乎已经完全成了林权的模样。尔棠没有来,带着尔菁菁一同来的是上次来找林权去寻尔菁菁的尔雁征。
席上他努力模仿着林权的样子,回忆林权和尔雁征说话时的姿态和腔调。不知是不是因为多亏了他总是旁观着,模仿林权对他来说不是什么难事。除了偶尔的破绽引来尔雁征的几句调侃,除此之外便再无其他。尔菁菁一直看着他,她面无表情,他看不透这个被他和林权千提万防的女子究竟在想什么,只是整场宴席她都没有同他说过一句话。
宴席结束后他带着尔菁菁去早先在府中为她安排好的客房,尔雁征仍在和林府的亲朋好友寒暄,他是尔氏的儿子,将来也注定会继承一部分尔氏的家业,因此大家都对这位八面玲珑的小公子怀有交好之心。下人们也多在厨房和大堂帮工,居室所在的后院反倒显得清静。
他推开门,一股暖意从门里迎接了他们,下人们已经提前将房间暖过。桌上的烛台,燃烧的蜡烛照亮了房间,这里已经整理得一尘不染,“我还得和雁征谈会儿话,菁菁,你要是累了就早些歇息吧。”
“那你不打算再陪我一会儿吗?”
“我还有要事要和雁征还有父亲相商。”
“还以为你能给我说什么有趣的事,结果压根没和我说几句话,你好没劲,和林权很像又有什么用。”
从事故中生还回来的尔菁菁从没叫过他的名字。
不,她也没叫过林昭的名字,仿佛偌大的林府她的眼中只能看得见林权。但是她是怎么知道他代替了林权的?如果她知道了,那尔雁征难道也……
“三哥好像不知道呢,就算知道了大概也不会说吧。是因为你们在玩什么游戏吗,看谁最晚发现真相?哎呀,那我输了,”尔菁菁耸耸肩,“是不是也不能告诉我林权在哪?那我可以自己找吗?”
他没有回答她任何问题,便从她面前匆匆逃走了。
林昭和母亲离开那天下了雪,细密的小雪从天上纷纷扬扬,有的细碎雪花甚至还没落地便已经消融,最后他的发丝和脸庞都已经变得湿漉漉。
“不要送了,外面冷,快点回屋吧。”母亲的手伸出车窗握着他的手,而他最终还是依依不舍地松开母亲的手,坐在母亲身旁的林昭对他挥了挥手,尽管她没有说话,但他能想到她道别的声音。
“好,母亲,路上小心。昭昭,注意身体。”
马车逐渐远去了,他站在原地望着地面的车辙逐渐延长,直到被落下的小雪盖住,他的身上也落了许多雪,很多被他的体温融化,他好像淋了一场雨。
当他回到林府里面,下人们来为他递上毛巾,但他只是摇摇头,让下人们去忙自己的。他自己一个人走着,后院的水池中,荷花已经谢了,鱼儿们仍层层围在一起,不知道是不是在取暖。
不知不觉间他走到了关着林权的那个房间,房门被沉重的锁头紧锁着,除了冰冷的金属锁,还有另一个身影在那门前。
身上同样落了雪的尔菁菁站起身穿过风雪向他走来,但她的脚步没有任何停留,只是与他擦肩而过。
但是他的心里一瞬间好像爆发了一股难以遏制的感情,似乎他已经无法忍受这一切,而尔菁菁正是这一切的元凶。
“等等!”
在他身后,尔菁菁停下脚步,扭过头来看他,神情间是他前所未见的不耐。
“你这人,没意思就罢了,怎么连点眼见都没有,难道你看不出来我现在心情很不好?”
他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名字,为什么她知道这一切却视而不见?作为林权的替代的日子他要忍受到什么时候?
“哈,尔菁菁,对你来说这个府邸里除了林权难道其他人都不重要吗?难道你连其他人的名字都记不住吗!”
“为什么,”少女仍没有笑, “我有什么必须记住你名字的理由。”
尔菁菁走了,只剩他一个人站在下雪的院子里,他失去了一切,名字,身份,现在连愤怒的力气和感情也没有了。
身后房屋的门被用力推动,锁头为此发出了挣扎的悲鸣。林权又开始发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