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 Jolie宋朝篇
欢迎来玩
对不起这次主线拖了很久,辛苦大家的耐心等待,下次一定写完再开!
后日谈预计将于3/5发布,计分统计将于清明节截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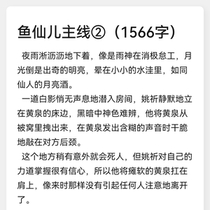

*感谢维因大人让我拉小北伶伶当背景板!
提笔在信笺末端落款,杨承圭将笔轻轻搭在笔枕一侧,谨慎又小心地把信叠起、收好,在信封正中央写下已经不能再熟悉的名字。在这之后他才缓缓起身,拿起信,往楼下走去。
已是闷热而潮湿的时节,土润溽暑,大雨时行,又因此地沿海,靠近码头,故那股如熏蒸般的湿无论如何也无法散去。好在杨承圭并不在意,即使穿着繁琐讲究,他看起来也与平日无异,没能被气候影响分毫。
在美人榻上小憩的年轻女子晃动着手里的绣花团扇,同从客房出来的杨承圭对上目光,他朝她笑笑,后者亦回以礼貌的颔首。杨承圭自是知晓她身份,此间老板娘,姓徐,往来房客都称一句“徐娘子”,近日正是码头最热闹的时节,徐娘子与此时正坐在厅堂的说书先生一唱一和,为来往入不敷出的游客提供了赚钱的法子,因而整个厅堂也跟着笙歌鼎沸起来。
杨承圭走到徐娘子身边:“劳驾,徐娘子可知这附近的驿站在何处?”
琼花玉貌的女人稍稍坐起,朝外边指了一条道:“如此这般,公子便能瞧见驿站了。”
他并非初来乍到,却是第一次在这个时间点赶上撰写这封信,朝徐娘子告别,杨承圭正欲前往,却在这空前盛况中瞥见一抹极其熟悉的身影。
有那么一瞬间,他甚至忘记自己姓甚名谁、忘记如何迈步,忘记自己的过去和所有经历,近乎魔怔地盯着不远处人群里持刀而立、身着劲装的年轻女人。
鸠车竹马曾经处,屈指可数的能够被带入坟墓的回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寄出却从未收到过的回信;那双冷漠的、冰凉的、固执的、忽视一切、无论如何也不肯落在他身上的眼睛——
本是如此珍视、容不得半分褶皱的信从他手中滑落,封面正中央是字迹工整的四个字:唐挽亲启。
唐挽在这里。
这个认知让杨承圭感到恍惚。
自唐挽离开唐府,背井离乡独自前往西南,他们约莫有四年未见。四年,她却和杨承圭记忆里的模样所差无几,又或许是他对于这个名字和身份的执念太盛,如经久不衰的烈焰,那通天的火光终是惹得老天垂怜,在重逢的这瞬予他这恩赐,让他在人群中一眼发现了唐挽。
她将手里的东西递给面前身着绿色褙子的少女,又同少女身旁的男子道了几句话,不难推测出是捡到了对方遗落的东西。说话的时候,她未曾露出片刻的笑容,就和杨承圭记忆里一样,平静如无波的湖面,瞧不见半点心绪,又偏偏在那少女露出好奇的表情时,他注意到她右手细微的变化,几乎是在少女靠近询问的同时,她右手的食指抽动了一下,擦着衣摆一晃,接着恢复到常态。
那是他铭记于心的、唐挽从小就有的小动作。
杨承圭再次确信,这个人就是唐挽,于是他第一次如此失态地跑了过去。
客栈的人群里里外外围了许多人,凑热闹的、表演的、各怀鬼胎的,杨承圭穿过他们,顾不得平日展露的教养与风度,近乎急切地想要再快一步。
越过一个人、又一个人,忽地传来巨大的欢呼声,他因移动的人群而被迫停下脚步,发现追逐的身影已然不知去向,只余下那对关系亲密的男女还在原地。
哪里还有什么唐挽?
于是那句本就没能说出口的“阿挽”也这样一同融进了这沸反盈天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