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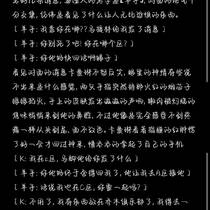

※故事分为宁纪侧和kumo侧,宁纪的故事(~1章)对应过去 / kumo的故事(~2章)对应现在
字数1843
——————
宁纪从未想过把人杀死。
但是贝斯重击在人身上的感觉过于美妙…但是贝斯是用来干这个的吗?
或许普通人一辈子都想不到贝斯和人在物理撞击上能够发出美妙的声音吧。
一开始他们还只是在游行人群边上发出不完整的噪音。主唱没有来也罢,那个吉他手真是胆小鬼…沉闷的贝斯solo连接着便携音响在礼仗公园轰鸣着。
或许有人的耳朵不够灵通,嘛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听见贝斯的沉响,于是有位不懂氛围的外国人举着反对的牌子过来满嘴粗口地喷着地道美国话,抗议宁纪操使贝斯发出的噪音。
可惜宁纪听不懂。
kumo在一旁都觉得,这等带着f开头的世界通用吵架语言已经不用翻译了吧,可是为什么还一脸懵懂地看着对方?感觉对方的牌子都要砸过来了呢?
人的肢体动作也是世界通用语言呢。
“ton”地一下,贝斯带着沉响把狼牙装饰嵌进了这个五大三粗留着胡子五官扭成一团的恶鬼面容的美国人脸庞里。
啊,已经19点了啊。
那么,该戴上面具,驱散不懂欣赏也不听话的外国人了。
——————
第一次知道贝斯还能干这个的,果然还是那件事。
本来抓着宁纪头发大喊大叫的父亲倒在地上,好像再也出不了声了。但是接下来的念头却是,得多打几下啊,要是起来了又听到那种令自己不悦、令母亲嚎哭、怎么样都无济于事的声音怎么办。只会用嘴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托进城的同学带回来的贝斯就这样砸坏了,有点可惜。无论是人还是贝斯都发不出声音来了。
…
但是现在手上这把贝斯可不一样。特地问了用最硬的木头打造的、浑然天成(?)的钝器…在挥洒完汗水后依然毫发无损。
宁纪擦了擦贝斯亮漆面上的血,还是亮晶晶的,真不错。“那个啊……杀戮日就是这种东西吧?入乡随俗?”
背景音是广播和市政警笛声响起,杀戮日真的开始了。非常有仪式感地,也不至于让宁纪觉得自己抢跑了。
但是还在演出中!擅自这样觉得的时候,不知从哪窜出来的麦克风怼了上来,这是被抓现行了吗。kumo流下一滴冷汗正准备赶人,又没料到那个女人又开始语出惊人。
“你好打扰了!在这么隆重的节日里,你们是为什么而来的呢?”
哦?日本语?虽然知道因为时差,日本在十几个小时前已经结束了杀戮日,但没想到还有媒体专门跑过来采访美国的杀戮日,而且还歪打正着采访了一个亚洲人。
坏就坏在宁纪一脸清爽地(虽然戴着面具)应对着采访——“一边杀人一边弹贝斯不觉得很好玩吗☆?”
这女人就这样说出来了啊!!!!!
——————
“像你这样招呼都不打就开始打人的外国人还在收拾的时候可不多见…”
“怎么了嘛,本地人都不介意了。你说是吧?”用下巴指指地上的大胡子,抗议人群几乎四散奔逃完了…没有人愿意在抗议游行里献上生命吧?
kumo叹了口气,收拾着被线路拽出去摔的不轻的便携音响和其他三脚架,当然知道用嘴劝这个女人是徒劳的。
“嗯——饿了啊。我们刚下飞机就来这边演出,还没有吃饭。”
“这什么狗屎演出啊…要吃饭直接去超市看看呗,这个点还想去餐厅好好吃饭?”
“呵呵,这么慷慨还是不习惯啊。”
“谦虚什么呢你这臭女人。”
乐队二人一打一闹前往超市。
——————
让人闭嘴真是门艺术。不过在杀戮日里,似乎闭嘴成为了一种习惯,对普通人来说。超市里不算安静,白天如果说是普通人在抢购物资的话,那晚上就是另一群窥伺限时打0折完全免费全靠实力的人的战斗了。
当然,货架空得很快。超市天花板上的白炽灯管闪了闪,发出已损坏的声音。传来更多声响的是2楼或者3楼的电器家居,又或是有人直奔4楼金银首饰店…多金贵的东西在这12小时里都变成小垃圾。
“啧,这地方根本没什么好吃的啊?”宁纪在熟食柜面前翻着,怎么没有鲷鱼烧?怎么没有鳗鱼饭?怎么没有天妇罗?离开了日本才知道晚上熟食半价的可怜,大阿美丽卡好像除了炸鸡汉堡薯条三明治沙拉以外真没什么算是好吃的。就算是这种节日也保持着日本人的迷之矜持,随便拿两盒就走人。
另一个角落里,kumo看见了散发着迷之气息的,柜台里满满当当放着的……鲱鱼罐头。这玩意除了极北地区以外似乎几乎没有人敢吃,尽管商场还是进货了。嚯,一看里面有几罐好过期了,简直是文物级别的气味炸弹。没人能承受的住这股远洋推广过来的妙妙小工具…能顶住这股气味杀人吗?除非戴着防毒面具,比如kumo这种人。抱着这种想法的kumo一连拿了好几罐,希望不会在包里因为低温发酵爆炸吧。
两个外国人一边揣着鲱鱼罐头一边在路边坐着吃烤鸡很少见吗?是的很少见,而且还不能把面具摘下来的情况下。




*中之人一口气写完的感觉像便秘了一个月然后突然用了开塞露,不擅长写文没有抓虫前后语序不搭是正常的。
*如果您有去其他角色的视角看过,那么我要提醒您一点:以下内容遵循大小姐的单一视角进行叙事。因此,所有事件均源于她的主观认知,事情之所以这样诠释是因为在她眼里就是这样发生的,并非客观全貌。
贝拉坐在车上,车子很颠簸,身体总是被抛起,然后又砸回到座位上,目视前方却无法聚焦——那是当然的,她们现在像是在一堆石头上蹦,视线抖得无法看清。我坐上的到底是车,还是某种刑具?贝拉想,抬眼望向后视镜,从中瞥见自己的脸,她发觉自己的神色有些疲惫,整体都因这层疲惫好似被蒙了一层灰,但是既然没有观众,自己也不用时刻保持那副神采奕奕的模样——爸爸最喜欢的、我的模样。
唉,爸爸也不在。贝拉想起来。
说到观众,现在贝拉的身边就有两个外人。一个叫米特•博伊尔,不熟,莫名其妙出现了。现在好像睡着了,也可能没在睡。自见面以来,博伊尔从未睁过眼,因此,博伊尔是否在睡觉这一点暂且存疑。而另一个:莱卡•道格拉斯,不熟,以一种比博伊尔更加莫名其妙的方式出现了。现在正在开车,对那个后视镜好像不是很在意,贝拉为了梳头发把它掰向自己的方向之后没有要求再掰回去。贝拉虽然没有学过开车,但是她也知道人们开车的时候需要后视镜,所以,道格拉斯是否在安全驾驶这一点也暂且存疑。
放在往日,这两人的存在或许还能让贝拉有所收敛。但是考虑到当前处境与之前发生的事情,自己有多么狼狈啊!
她们看到了,贝拉意识到,既然她们看到了,那她们不会再因为我而欣赏我了,如果她们从一开始就不会欣赏我,那我也没必要再给她们好脸色看。
嘴里似乎有一丝甜味,但是平淡得又感受不到,她忘记自己什么时候吃过巧克力了,应该是博伊尔给的,准确来说应该是硬塞的——这种廉价的、几乎连味道都尝不出来的巧克力!紧接着贝拉的思绪突然就顿了一下,“道格拉斯。”
“嗯?”
“博伊尔刚刚给的巧克力,你吃了吗?”
“她吃了。”博伊尔突然出声,吓了贝拉一跳,道格拉斯应和着。
贝拉斟酌着发言,“你们平时就吃这样的巧克力?我爸爸给我带过很多巧克力,但是我从未尝过这样的……口味。”
“什么意思?哎呀!你吃都吃了,别不满了,小姑娘二号。”博伊尔看起来有些郁闷,看来贝拉斟酌得还是不太到位。
“为什么是小姑娘二号。”道格拉斯疑惑着,“难道我还是小姑娘一号??”
“…………我知道你叫城之内啦…”
“我现在百分百确定你是故意的,完全的,肯定,你是,故,意,的。”
开车的时候能不能别聊天?贝拉也相当肯定决对地百分百地确定自己不想和这段对话扯上关系,她看着道格拉斯,道格拉斯似乎肢体语言相当多,每次开口都要忍着不把手从方向盘挪开,而作为替代,她总是在座位上动来动去。
但是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树欲静而风不止,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而贝拉也一直知道自己的运气不怎么样。“唉。”道格拉斯发问了,“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我下次想得知他人姓名的时候就照你这么说。”贝拉再次斟酌着发言,“劳拉。”
“哈哈哈,你肯定不叫这个吧!”道格拉斯爽朗地笑了,“你都不愿意叫我们的名字!”
看来贝拉还是斟酌得不怎么样。
“不愿意吗?”博伊尔插嘴道。
“我一开始对‘劳拉’说叫我莱卡就行,但是她紧接着就问我的全名,真是让人不知所措。”
贝拉忍不住反驳,“什么人会一上来就让对方以名字相称?你爸爸没有教过你待人之道吗?”
“我爸教过我如何待人热情。”道格拉斯皱着眉瞥了贝拉一眼,其中蕴含的许些怒意让贝拉内心某块地方瑟缩了一下,但是很快又恢复了。那又如何?贝拉想,我爸爸是最好的,如果你爸爸和我爸爸不一样,那一定是你爸爸出了问题。
出于待人之道,贝拉并没有将这些说出口。
可是道格拉斯又开口了,“你总是我爸爸、我爸爸的,你爸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
博伊尔也显得有些好奇,贝拉确信她是没话找话,两个人都是,“你妈妈呢?”
呵呵,如果你要坚持谈论这一点的话,“我爸爸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他会满足我所有的物质上与情感上的愿望,他总是能做到最好。”贝拉看向后视镜,确定自己的发型一丝不苟,“至于我妈妈,我出生后不久就死了,根本没有必要谈论她。”
博伊尔嘟囔了一句什么,没听清,但是她不再说话了,转过身去看窗外的黑不隆冬的城市夜景。而道格拉斯再次皱起了眉,再次瞥了贝拉一眼,但这回的神色更多像是疑惑而非愤怒,搞得贝拉都有些疑惑了,因为对方居然不嫉妒。“你爸……没问题吗?”
听了这句话,再怎么没反应,贝拉都要反应一下了,“你什么意思?我爸爸可是世界上最好、最强大、最完美的人。”贝拉再次强调,“同时也是我最好的爸爸。”
“我知道……”道格拉斯目视前方,“但是……”
道格拉斯没再往下说,贝拉则是分析了这句话可能存在的潜藏消息,“呵呵,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其实就是在嫉妒我有这么好的爸爸。”
道格拉斯喷了,“什么?!”道格拉斯不看路了,“你怎么会这样觉得?我可没有!你怎么会觉得全世界都想要你爸一样的爸爸!”
“这难道不是理所当然吗?”
道格拉斯否认,“不。”
贝拉否认了道格拉斯的否认,“不可能。”
道格拉斯否认了贝拉否认的道格拉斯的否认,“真的。”
贝拉冷笑,“你现在说这些就是为了遮掩你的真实意图。”
道格拉斯再三否认,“是真的,我真的不想要,我会觉得有点吓人。”
贝拉突然爆发了,“你到底什么意思?!你在否定我爸爸吗!我爸爸可是辛克莱!而我也是!我是阿拉贝拉•辛克莱!我爸爸是州长!我是州长的女儿!一直以来唯一的女儿!你怎么敢否定我的爸爸!”
“……啊。”
“啊。”
道格拉斯惊呆了,“……你爸爸是州长。”
“……什么。”
有人恍然大悟似的,但是贝拉已经有点听不出那是谁了,“哦,所以你的名字是阿拉贝拉•辛克莱?”
道格拉斯轻轻地将重量移到右侧,撞了一下,“贝拉?”
“大胆的尝试。”贝拉反应过来,她真的没力气了,“但是不准,别叫我贝拉,那个昵称只有我爸爸能叫。”
“贝拉。”
“我发誓你再叫一声我就把你从驾驶位上推下去然后我们全在这辆棺材一样的车里同归于尽在这之后我爸爸看到我的尸体就会去骚扰你的家人然后让他们全部因你的过失付出惨痛的代价。”
博伊尔也跟着闹,“贝拉。”
贝拉叹了口气,“我是认真的,博伊尔,请叫我辛克莱吧。”
道格拉斯诶了一声,“我总感觉你和我聊天态度会变得很恶劣,错觉?”
“多谢提醒?我这才意识到我们正在进行愉快的聊天。”贝拉用力地撇了一下嘴,天,道格拉斯又不看路了,她装作可怜地看向贝拉,将手伸向这边,看起来好像是妄图握手言和,“别这样嘛,我们和解吧?”
沿着袖口看上去,皮衣沾染了许多深色的血垢,贝拉觉得自己知道是因为什么沾上去的。她在道格拉斯的手上拍了一下,开车就好好开车!“看到你就让人觉得很烦躁。”
“怎么这样……”道格拉斯去好好开车了,一时间内没有人再说话。
终于安静了,贝拉感到满意,完全忘记了这场对话是她挑起来的。这不能怪她,在愤怒卷席着其他情绪退潮之后,她的大脑就再也挤不出一滴东西了,无论是过去的还是将来,所有的一切,都随着愤怒流逝了。现在,贝拉将视线从道格拉斯的皮衣上转移到博伊尔头上,而博伊尔好像是感受到了什么似的动了一下,像个毛绒玩具,贝拉不再看了。贝拉目视前方,她们现在去的地方是避难所还是教堂?她小时候的暑假经常会去瑞士那边度假,具体的位置不记得了,不过她因此学过短暂时间的意大利语,她曾经在那个地方种过一颗番茄,第二年回去发现它从一颗番茄变成了一片横向的番茄田,爸爸对此解释说因为番茄自我繁衍了,番茄就是会一生二二生三然后三生万物的,贝拉对于过往的记忆总是很模糊,通常人们会管它叫健忘,但是贝拉根本就不用记住任何事,而且关于爸爸的事,她总是能记得很清楚,所以管他呢!爸爸的朋友在那边有一个私人射击场,因此在小的时候贝拉常去射击玩,成绩相当好。可是爸爸自从贝拉某次去度假、从家里坐直升机出发到机场的时候不小心坠机了——对,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贝拉就是如此,运气极差又不至于置她死地——就再也没让贝拉自己去过瑞士了。那么那些番茄怎么办呢?一夜之间,家宅外原本种植的玫瑰变成了横向的番茄田,爸爸说他把在瑞士的番茄移植回来,那么那些玫瑰怎么办呢?变成番茄不会不雅观吗?爸爸哈哈大笑,说番茄曾经在两百年里,一直作为一种观赏植物被种在庭院里,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更何况我这么做是为了你,那更没必要担心了。于是贝拉安心了,说既然如此,那么自己是否可以食用它们,爸爸说可以,于是至今为止,贝拉仍然在食用着那些番茄。
贝拉再也没回过瑞士,再也没见过瑞士的番茄,也再也没有对着靶子进行射击了。她开始学习法语、小提琴还有如何更优雅地喝茶。快乐无忧的时间似乎一去不复返了,只有番茄仍然在庭院里,并不是说现在的贝拉就不快乐无忧了,爸爸总是会保证她会得到最好的,15岁的生日礼物,爸爸正是给了她一个惊喜,看着它,就好像回到了童年时候,再看看那些番茄,贝拉就知道只要留在爸爸的身边自己就能够得到无上的幸福。但是现实总是不及童话那般美好,爸爸带回来了“哥哥”和“妹妹”,贝拉确信一定是谁勾引了爸爸,就像在过去两百年里,番茄曾经是有毒的,画师因为太爱自己画中的番茄,最后在深情中不得不食用了有毒的观赏植物,但是——不!这回真是有毒的了!番茄里面居然千疮百孔,那些害虫们早已蜗居在此,就等着这一口呢!您的五脏六腑也会被进入您食道中的害虫腐蚀得千疮百孔的。贝拉总是担心着父亲的内脏,担心哪一天就能通过上面的孔洞看到另一个自己,就像她举起枪就能看到子弹最终去往何方。
对了,枪。贝拉恍如从梦中醒来,我爸爸给我的枪呢?
她翻找自己的包,却哪里也找不到,她知道知道掉在哪里,却再也不敢回去了。突然一阵羞耻感席卷而来,直往脑门冲去,贝拉忽然感觉自己的心跳声是那么大而又难以控制,嘴巴里的甜味愈发明显、以至于她感到自己渴得不得了,胸口像是突然从什么束缚当中挣出去不住地上下起伏着,连带着肺用力地收缩,为了回应肺部可怜的需求,她只能大口地呼吸。贝拉注意到道格拉斯已经不住地在用担忧的目光撇向这边了,博伊尔则是无所事事地盯着窗外,贝拉有些哽咽了。看什么看,不关你事!她恶毒地在心里想着,开始诅咒代替爸爸来拯救了自己的道格拉斯、让自己吃下廉价巧克力的看起来一直在睡的博伊尔,害自己来到瑟伯林的那个试图吸引爸爸注意力的害虫、世界上所有试图勾引爸爸的害虫、信号不好的手机、留在那辆烂车上的手机、不知道去了哪里的保镖以及今天发生的所有一切!她低头看,看见了混沌的、不同明暗的轮廓,她抬头看,才注意到黑暗浓重的夜空中那唯一一颗星星。贝拉没有回应道格拉斯那愈发频繁的目光,在道格拉斯开口的前一刻,贝拉终于做出反应,她抬起腿,然后用尽所有力气,那股愤怒——恨不得把这辆车抡穿那样,将自己的脚用力地砸在了地板上。
脚麻了。手也麻了,浑身都麻了。还有随之而来的疼痛。
博伊尔很惊讶,“辛克莱,你在做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对它?”
“我在做什么?!没什么!”辛克莱愤怒地尖叫,然后突然感觉陷入了疲惫,“我只是……渴了。”
博伊尔叹了口气,辛克莱内心对此产生了一点微微的愧疚,即使她不会承认。而道格拉斯则是殷勤地递上了不久前从后面翻出来的水。
f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