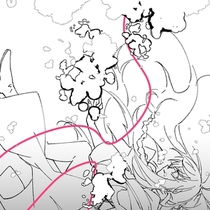字数共3K5.
“你拍一,我拍一——”女人的声音,回荡,难以抗拒。她问:“你杀过多少人?”
“不知道。”休注视着自己的手指。它们伸不直。他用力伸展,仍然伸不直。手指在发抖。他随着女人唱歌的韵律移动手臂,伸出,与她拍手,收回。这动作很熟悉。
“你拍二,我拍二——你参加过多少任务?”
“不记得了。”她看上去不满。休张张嘴,没找到应该说的话。
“你拍三,我拍三——”她笑了,休反而有些紧张。长官并不喜欢笑——不,她不是长官,他不认识这女人。她是谁?
但她先说话了。女人听上去很温和,休不想让她失望。她问:“你杀过自己人吗?”
他不想回答。
女人强调了一遍:“我命令你回答我。”
“有。”
休想闭上嘴。但他控制不了,就像控制不了手指。他又想继续回答:那是迫不得已的,当然是迫不得已的。但他还是没法控制喉咙和嘴唇。脑子失效的时候,训练就会控制身体。所以新兵要被严苛地打磨。如何开枪,如何隐蔽,如何投掷,如何在无法呼吸的时候奔跑,如何背负几十磅负重生活。现在这被打进他身体里的第二幅骨架发挥作用,他无能为力。士兵的第一天职是服从命令。
女人兴奋地睁大眼睛,将某种仪器放在眼前,正对着他。她下令:“说说你怎么杀的?”
“XXXX斯坦,XXX郡,XXXX村,20XX。任务是突袭疑似当地反抗组织据点。”休注视着那设备的圆环中心——那是简报的要求之一——开始回忆。
被风暴卷走进入魔法世界的那个姑娘叫什么来着,爱丽丝还是桃乐丝?
休实在想不起来。只记得那姑娘穿着红鞋子,带了三个跟班,打败了绿色的坏女巫,而且还是同性恋友好象征。
他哪个都不是,但确实快被飓风卷走了。比喻上的和事实上的。
加州从来没好事,十四年前他就是在这儿参的军。难道是命运指引一定要让他一生中最错误的两个决定都在这儿发生?一个毁了他的下半生,一个马上就要弄死他。
工业区绝对不是躲避风暴的好地方,但休得运气就这样。狂风携着它所有的刀刃扑进城市的时候,他就在工业区。金属相互撞击的巨大声响在自然伟力中渺不可闻。风中有树叶和海报,也有碎裂的铁皮。这里就像是个搅拌机的内部。金属、木头和塑料都凌空飞旋,撕扯着人随之舞动,裂解成片片肉泥。墙壁并不安全。金属室外楼梯被整片撕下,根部却好像卡在了哪里动弹不得,只有上半部分随风乱甩,好像商场的气球人。这太超现实了,休觉得自己应该睡一觉,就像南部农民那样,把门窗都用木板钉好然后在地下室蜷缩起来睡上一整天,再打开门时一切就都好了。
可惜今晚不该睡觉。风刮得太利,他的同伴是个傻逼——这女人发现断网后坚持拍了一会儿气窗外的恐怖景象和他的反应,然后就放弃了,正在用地下室里的杂物试图给自己絮窝。而且她的声音听上去可疑地耳熟。休觉得自己可能跟她接触过,又实在想不起来。
他只能听到暴风,呼啸声穿透水泥,如同子弹。
善感螳螂刚刚撞到了墙,正试图补妆。她有化妆品——希望别是从哪具尸体上捡来的,就差一面镜子。她不肯用自己的设备当镜子用,于是要求休献出自己的那台手机:“反正你也没在认真直播。”她这样说,但也没干直接抢。即使是她这样装疯卖傻的家伙也能理解体型差距。休姑且找了个离她远的地方坐着以示尊敬,闭目养神。
那女人稍稍安静下来,她在试图继续录像,但没有信号。休也没有,这是唯一的好事,他不用再听到那些被机械音一字一句读出的隐私了。也是坏事,这样的直播事故要是一直继续,他不仅拿不到报酬,恐怕还得赔违约金。
休通常不花时间在这种没法解决的事情上,但现在实在太有时间了。在风暴,撞击和女人的自言自语中他得保持清醒。现在他什么都愿意想一会儿,只要不是跟杀人有关。
现在可不能发疯啊,这是最不应该发疯的时候。天,要是他在那个远在中西部荒野深处远离人类的家里发疯,最多也就去荒野里屠两头野猪,然后狼狈地独自荒野行军回家。要是在这儿——满地疯子,武器和尸体随处可见,直播摄像头紧盯着法律临时允许的每一项疯狂举动的杀戮日中——那他就彻底他妈的完蛋了。
深呼吸。呼——,吸——。呼——,吸——。呼——,吸——。沉稳,缓慢,坚定。就像一只老乌龟,或者公园里打太极的中国老头。呼,吸。呼,吸。他很安全,外面的风暴保护着他,没人能穿越这卷满了刀片的飓风来到这个地下室。呼吸,呼吸。他跟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独处,即使有什么万一也只会是他杀了她而不会是反方向。呼吸。他不会动手。呼吸。所以没事。呼吸。呼吸。呼吸。
“你害怕了?”女人问。
她的声音尖利得不正常。可能是职业病,她是那些出卖自己丑态为业的家伙之一,他们说话总是疯疯癫癫的。现在不是她该说话的时候。风暴,它在渗透。冰冷的腥臭的空气沿窗缝流入舔舐他的脖颈。金属的声音,它撞在某种厚实的东西上。匕首撞上防弹插板就是这种声音。那次很惨,他差点被杀,但最后还是把对方推下了楼。防弹插板和头盔抵挡了子弹和钢筋,但那人后脑勺着地,整个颈椎都断开了。休在阳台上看着他。那颗头。它在惨叫,下面的身体在开枪。它们感觉不到彼此,但还在各自工作。
那女人好像完全不会读空气:“哦,是那个吗,PTSD?”
“跟你没关系。”休回答:“躲好,别作死。”
“不作死我来这儿干什么?”女人嗤笑他的天真:“诶,你从哪得的?战场?”
休不想说是,所以只能闭着嘴。声音还在继续。烈风飞旋,如同直升机翼撞上水泥柱,片片碎裂,扑散大片灰砾,裹挟断裂的机翼陨落如雪。滚烫的金属的味道。机油被加热到极限。蛋白质烧焦时像烤肉。轮胎和人一同尖叫。
“我猜是战场。你一看就是退役兵。你去的哪里?非洲?中东?东欧?”
她为什么就是不肯停下?疯子永远都不肯停下。他们像要用语言的重量证明自己一样永远不肯停下。那些宣言,口号,代替尖叫的辱骂,大段大段背诵的经文。
“喂,说点什么——你不说那就只能我说了!你不喜欢这样吧?让你头疼?我知道你们这种人都不喜欢噪音。”
是的,但让她闭嘴要轻松多了。
休想着,没有动。
风暴还在继续。火舌舔舐枪管,热度延伸到手心。他从没被这温度吓到过。黄铜子弹落在水泥地上叮当作响。它们还烫着,等他回来的时候就可以捡走,打孔做成装饰品,送给谁好?他没有父亲,母亲被毒品烧坏了脑子。姐姐不承认他,他没有朋友也没有宠物。他谁也没有。
“——游戏怎么样,你们喜欢游戏吧?可以舒缓神经,减少压力,之类之类的。我是说,谁不喜欢呢?那可是游戏!”她转头朝着自己的设备说:“比如,我的赞助商黑暗传说,这是一款……”
休不喜欢游戏。他是个异类。与其在电脑屏幕上开枪还不如在现实中开枪——他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那边的女人完成了口播:“所以你要不要试试,就我们俩。简单的,拍手游戏。”
“过来坐下。”
她说。他的长官,那个永远冷硬,永远没有破绽的疯子说。那家伙说话不需要用什么高压的语气,没人敢在他面前坚持己见。他的眼睛里能射出刀子。休站起来,朝长官指示的方向前进。轰隆作响。履带声,引擎像鳄鱼一样低吼,风沙。风沙钻进他的鞋子里,卡在皮肤缝隙,钻进去,永远洗不干净。他的脚趾很痛。军医给了他止痛药。他需要它们来保持清醒。
他在那里盘腿坐下,眼前是一片浑浊的黑。
“现在,跟着我做。”女人说。她听上去很陌生,但他顾不得了。
女人唱起简单的曲调,他花几秒想起应当如何动作,然后去拍她的手。慢了一拍,她没有介意。
然后她问:“你杀过自己人吗?”
“有。”休回答。
然后一切决堤。
碎肉落在身上时与石子不同,有一种异样的温柔。就好像它们并不愿意伤害谁。
它是温的,好像还是人的一部分,在皮肤上慢慢干涸。剩下的要等回到营地脱下装备的时候才能看到。有的部分挂在枪套上,因为休没有换枪而始终没有被蹭下来。有的在护具上,好像还愿意再保护他一次。有的在背包角落深处——这是他在海关才发现的。那只可怜的工作犬,对着他的背包指示出尸体。休清空背包,最后翻出那一小块肉干。只有大拇指那么点儿大。驻地极度的干燥将它保存下来,成了一枚最稀有和怪异的纪念物,并被海关收缴。
就和那些掩藏在厚重装备角落里的碎肉一样,休是直到休假后才缓缓找回那次任务全部记忆的。一切开始的很寻常。接受任务,打包,出勤。他们那时驻扎的位置不好,去哪都得路过一处很容易被埋伏的谷地,后来干脆把那片地彻底炸平,留下一大片只有履带车才能跨越的废墟。所以就算只是买点零食也得开全封闭运兵卡车。他们都习惯了。车轮超过六尺,每个人挨个爬进车厢,这金属巨棺。休总是喜欢这里头的氛围。黑暗,温暖,安静。机油和金属。有人在黑暗中保养枪械,摩擦声。装备撞上车厢。只要三次深呼吸他就能彻底平静下来,手指兴奋得发抖。
车程通常都不长。这里的人缺乏快速的交通手段,村落之间不会超过一日步行的距离,对巨大的运兵车来说天涯咫尺。下车后进攻那个据点花了几分钟,枪战,清搜整个建筑,回报等待指令。他们曾经在各种无辜的角落里发现炸弹,通常线索都是死了的队友,所以没人愿意太精细地搜查。
好吧,没几个人。
休没拉住他队里那个。
那孩子叫什么来着,休不记得他的样子了。他刚入队,急于立功,认真搜查。他检查装备的习惯不够好,休提醒过他应该更经常确认自己的防弹衣完整度,他总是不记得。棕色头发——要是金色,休会记得的。他讨厌金发。那个年轻人,他喜欢吃军队的饭(天啊!),他的床铺上有个旧平板塞满了盗版漫画,他的枪被保养的很好。他的眼睛是榛子色的。
它们被鲜血浸透。
他的脸被面罩遮着,休扯开它,确认下面的脸。他不记得它的形状了,只是惨白。其实根本不用确认,那孩子的半边身体都碎了,一半在地上,一半在休的身上。内脏在枪火洗过的地上流淌,心脏裸露在外,肺碎了。他发出不成型的嘶叫,他还能叫好几分钟。
休把一匣子弹放进他的脑子里。
没人找他的麻烦。
“……哇哦,老套。”女人说。
休猜那是不满意的意思。好吧,士兵。你得再努力点。他逼自己张开嘴,继续报告。
他满口都是风沙。
没写完,主要是感觉自己一直在找不到要如何描述一些人物心理和环境了,脑袋空空地铲过orz
滔天骇浪如一张巨口无情地吞噬陆地,暴雨压得人们喘不过气,大自然肆意向人类倾泻它的怒火,一如在《创世纪》中“诺亚方舟”的故事,上帝不会放过任何有罪之人,却也决不怜悯无罪之人。没人够能阻挡祂的审判,没有人。
洪水的消息借由通讯设备在人们之间传播,泛滥的大水令他们不得不考虑是活命要紧还是再趁着混乱多制造点闹剧;眼前是最该绷紧神经的时刻,克罗帕斯反而久违地感觉身心有所放松,她不确定是自己已经疯了,还是那帮到处作孽的疯子终于遭报应带给她的一种无法言说的痛快,好吧,反正他们都是该找的,当初搞那些事怎么就没想过现在的后果呢?
不是说她就正义心超强什么的,她只是觉得那些人随随便便就动手伤人,甚至连一个无辜的小孩子都不放过的行为太逊了。好在她找到了这个孩子暂时捱过了前面几道难关,终于只剩下唯一一个也是最关键的——在天灾面前活下去。
人祸尚且有办法协调、扭转,天降大灾则容不得半分商量,要是她能一句话劝退海浪和暴雨,她莫不是就成掌管自然的神明了。很显然她和身边的小朋友都做不到,他们只能拼尽全力找地势高且姑且坚实的建筑躲着,等待或许有又或许根本没有的救援。
无论如何,人类只有祈求自然的宽恕,保佑自己平安无事。
她也趁着这个机会尝试和那个一直缠着自己的烦人家伙联络,虽然对方确实有些烦人是没错,但如果整个德克萨斯州都面临自然灾害,想必那个白痴能不能照顾好自己都是个问题。所以她火急火燎地给对方发消息,怎么都等不来回信,急得她想跺脚,但看了眼旁边显然缺乏精力状态迷茫的诺克赫德尔,又不太好意思发脾气,只得摇了摇头坐下,希望雨尽快变小,也幸亏他们是在楼里,如果在野外,怕是被雨水浇得眼睛都睁不开,到时候都不用想有没有食物的事,直接张嘴喝个水饱算了。
比起克罗帕斯面对什么事都能从某些角度回怼吐槽的思考方式,诺克赫德尔只是静默地发呆,他可能在考虑如何在洪水中保护自己和同伴,也可能放空大脑什么都没想。意外卷入这场杀戮与逃窜的狂欢,让他没多少时间能停下来重新审视自己的想法。或许他自身的想法没那么重要,现在更优先需要确保两个人的人身安危。他知道克罗帕斯所做的行为是为了缓解压力,她必须要把那些事说出来才不至于堵在心里更难受。所以他一个不怎么擅长交流的人也在尝试性地和对方谈话,试图缓解一部分对方背负的焦虑不安。
《早安瑟伯林》节目不合时宜地插播了一条“新闻”:一名在回响屠夫店门前倒地的孕妇在好心人帮助下产出了胎儿,由于缺乏足够卫生条件,具体在之后母子二人能否平安还是未知数。
“哎。”
他听见克罗帕斯叹息一声,紧接着抱怨道:“现在他们满意了吗?满意了吧。什么狗屎无政府自由战斗,现在真正遇到困难的人连专业的医疗服务都享受不到,拜托,不会有人觉得受伤生病靠自己‘坚强的意志力’就能挺过去吧!拜托,那可是身体条件必须要有人照顾的人啊!”
之后一连串絮叨诺克赫德尔没有完全放在心上,他确实有在听,他知道这是克罗帕斯在排解心情,因此没有出声。
不知是不是错觉,雨稍微要比刚才小了一点。

1.双人卡,字数够
2.有点卡文+不知所谓侮辱智商了jpg,慢慢改吧……
一切都会过去的,瑟柏林总是如此。哪怕狂风将楼宇夷为平地,哪怕陆地变回汪洋一片,哪怕雷鸣下生命化作焦土,但灾难过后,被留下来的人们总能在这里建起新的居所,一边修复伤痛一边继续生活下去。在抵达工业区之前,林旭闲来无事随机寻来了几人,以杀戮日主播采访的名义向他们问过话。她委婉地问了每一个人为何要留在这座苦难重重的城市——故土情怀、渴望远走高飞然而没有条件、哪怕不在瑟柏林人生仍是一场苦难,她得到了形形色色的答案。
NFFA承诺过主播不会在杀戮日成为被攻击的目标,只要戴着这枚徽章,就得到了能自由平安地行走于杀戮现场的权利。但要是那些家伙为了拍摄龙卷风而一不小心被卷上了天,这可就不在政府管辖的范围之内了。原本他们就不是为了转播自然灾害而被邀请来的,显然相当一部分主播已经忘记了这件事情——对着躺在地上的尸体拍了一晚上,想必主播们和他们的观众都感觉到腻味了,现在有机会能看到活生生的人类被气流撕成碎片,他们自然不会放弃这个机会。归根结底,来这里的主播究竟有几个人是真的乖乖听话,一门心思地打算将这场举国狂欢的必要性展示给全世界看的?
“我想起来了,刚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遇到过一名同行。他完全不懂拍摄,镜头和互动都乱七八糟,经营的频道也压根没几个观众。出于好奇我就作为同行去采访了一下,他说,他是托关系拿到这枚徽章的,因为今晚只要戴好它举起手机,就能安全地活到天亮啦。”林旭一边回忆,一边轻柔地拍了拍身旁的男人,对方的手脚被紧紧困住,动弹不得,绳索的另一头被林朝握在手里。“……为了活着,为了名声,为了保护一些别的什么,大家都是为了杀戮日之后的东西奔走,我们也一样哦。对了,我问完这些以后就把他杀掉了,在你们的规定里,如果主播杀死同样身为主播的参与者,天亮以后还会被追责吗?”
男人的嘴被胶带封着,并没有办法开口,他只能面露惊惧,拼尽全力挣扎了几下——这个行为实属没什么必要,他早在几分钟前就这么做过了,结果只是像被翻了面的甲虫一样滑稽地浪费掉了不少体力。林朝虽然这么想着,却还是紧了紧手上的力道。在林旭很小的时候,他们家曾养过一只不怎么听话的博美犬,林朝也常常像这样让那小家伙老实下来,现在他用一样的方式来对待杀死了自己父母的仇人。再过不久狂风就会席卷这片区域,林旭在控制住对方的时候就关照过林朝,一定不能让他死于自然灾害,他必须在怀里这捆炸弹的作用下变得四分五裂,而同时他的死也会被他们直播给所有人:只要杀戮日存在,那就不会有谁是百分之一百安全的,谁也别想毫无顾虑安然度过这个夜晚。哪怕是被赦免过的人,哪怕是有资格赦免他人的人。
林朝知道林旭用的这个理由主要是用来宽慰身为兄长的自己,林旭本人想做的只有杀掉毁掉他们人生的这个男人。可对于林朝来说,只要是林旭想做的事情,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有没有理由他都会为对方达成,所以他认为也许得找一天和她好好谈谈,告诉她并不用这么辛苦地为自己着想太多。
字数够的,以后再修…………
北嶋久生坐回车里,拉上门,车外浓重的灰尘被带进来一点。驾驶位上,沢岛龙也还在对着笔电屏幕出神,北嶋看到他又打开了早前阿卡洛尼克给他的那封邮件。灰尘在顶灯圈出的昏黄色里盘旋,轨迹曲折而缓慢,最后落到他的嘴唇上。沢岛的眼皮翕动,手指近乎无意识地在触控板上滑动,另一只手则始终握着屏幕一片漆黑的手机。
他累了,北嶋心想。他知道他想等一通电话,或者一条短信,所以不论如何也不会闭上眼,但在龙卷风已经拦腰掰断了信号塔、他们也只能连人带车躲进工业区的厂房的现在,这更多只能算是一种甚至无意义的坚持,或者说祈祷,或者说自我安慰。
“还在想Aka问你‘会不会开门’的事情?”把椅背向后放倒,他选择用轻快点的语调,“从前她有时候就会问出这种有点刺痛的问题。前辈,我不建议你想太多。”
沢岛过了一会儿才开口。“她只是问了很多人都想问的问题。”
“而你也给出了不错的答案。‘有能力、求良知’,不是很标准吗。”
像是嗤笑的轻微声响从他的鼻子里冒出来。“现在的日子里,连警察谈这个词都很讽刺。”
“前辈谈论这个词,总比我要好,对吧?”北嶋耸耸肩,“我知道,毕竟你一直对我不放心。”
沢岛看了他一眼,目光短暂地游移,随后投向黑漆漆的窗外。“如果你的背景审查不合格,局里也不会让你进有组织犯罪科。我没有意见。”
“我理解的,意大利黑手党的后代,不被信任才正常。弃暗投明的故事哄哄市民就好了。”耳边传来从喉咙里滚出来的笑声。然后他听见北嶋放低了一点声音。“不过,前辈你也不信的话,还是有点让人难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