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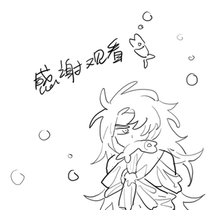

序章
对于一个曾被暗杀过一次的人而言,艾勒特的居所实在太过张扬了。他选了一处山坡上的房子,蜿蜒而上的石阶砖块铺得整整齐齐,绿荫错落有致,时令的鲜花在被安排妥当,见不到多大尘土。山脚和山腰处的居民抬头便可见到那房屋,打趣道一个瘸子竟选了这么不方便的地方,若是城郊倒也罢了,可他偏要住在山顶。 要是有人问起,他只会笑眯眯地说自己曾经打过仗,护了将官,这栋不合心意的宅子自然是别人赏的,不好拒绝,亦难变卖,只能将就着住了下来。
似乎是为了印证自己所说的话,艾勒特偌大的宅邸并没有长期的仆役和管家,他会定期请帮佣和园丁来照料他的房子,给钱时虽不小气,可也不能说是阔绰。他为人做事老实善良,一来二去,比起瞬息万变的城中事,艾勒特和他的房子就这样被人留存在记忆的角落里了。
= = =
“你……还记得吗?我在顶楼造了两座泳池,一座室内的,一座室外的。”
埃弗斯特盯着我说,“记得,给你家那条小鱼用的吧?你都不怎么让我看,说是帮佣都不知道还有个顶楼,做得真不错。”
“我本来是想建在地下室的。”
“甘愿让你的小鱼住在逼仄的地下室?”男人挑着眉哼了声,“稀奇。是谁嚷着地下室不好才买了那栋房子?玻璃温室、泳池和夜景。天啊,艾勒特,别在我面前掩盖你喜欢那条小鱼的心思,这没意义。”
我的脸在发烫。
= = =
雨落下的时候,天被刷满灰色,水滴落在玻璃温室的顶上,哒哒地打着。有时有风,将玻璃吹得吱吱作响,有时又只有雨声和阴暗的云朵,像是天真的要落下了。
往往这时候艾勒特会坐在泳池的扶手椅上,扶手椅在右边,于是我只能看到他的左脸,而那部分脸孔大部分都被眼罩和伤疤包裹起来,我看不真切,便游到他身边,讨他的话说。
我的主人——我的养父很沉默,不似是沉进发明中的沉默。雨让他坠入旧时的思绪中去。我露出疑问的神色,艾勒特便回答。他提到自己有个表弟,他的表弟有个美丽的妻子,他们很久之前就已相识。他提到夏季河边的旺盛的野草,提到秋季落下的橙黄色枯叶和即将吹到的寒风,唯独不会多提春季。他说有一个含苞欲放的春天,有鲜艳却不浓烈的花朵和阵阵海风带回幸福的滋味,有生命,有爱。他的表弟在笑,安娜贝尔也在笑。
然后他就会停下,任我如何摆尾示好他都不会多说一句。我去扯他的裤管,拉他的手,水把他的衣服拍湿,艾勒特蹲下来,轻抚我的头。
“等你长大点再告诉你吧。”
我很想说我快长大了,人鱼的生命周期和人类完全不同,我很快便会长到适合听这故事的年龄,也许是下个月,也许就是下周,你总得告诉我的。是什么让你如此悲伤?是什么让你像是要投进雨中去,要离开我了?
我想把你拉下来,看你湿透,水浸入你的衣领,进入你的伤口,你的旧伤更加疼痛。爱我。你颤抖,你想离开,但我不会让你离开。
然后我会亲吻你,在温暖的水下,你的额头,沿着鼻翼吻到嘴唇、下颌。爱我。只要我想,你便会呛水,肺被填满,会挣扎、抽搐,最后我的灵魂就会填满你的,我们会一直、一直在一起。你会一直爱我,你应当爱我。
“在想什么呢,乌尔斯?”
——没、没什么。我觉得雨好大,不知道是什么感觉。——
艾勒特笑起来,他总能读出我的意思,被雨弄得皱紧的眉头舒展开,“很难受的,衣服都会贴在身上。如果不巧,你有伤口,那溅起的泥沙会让你疼痛,布料纤维也会卡进去,等干了,可就倒霉啦。”
——不知道,干了就会疼吗?——
艾勒特望着我,眯起眼睛,有苦味泛在他的眼底,“不,伤口会一直疼。和在水里不一样,愈合的速度会很慢、很慢。”
我无法理解,若是我夺取这具躯壳,我就会理解了吗?
但这便是要让我失去他,我得到他的同时又会失去他,我该如何接受这件事呢?
“你说,我该不该给埃弗雷特找一个伙伴?”艾勒特突然问,嘴角弯起,满是恶作剧的样子,“我是不是该给他找个红发的人鱼?会唱歌的,还是像安娜贝尔那样,总是有活力的?”
——他也想养孩子吗?——
“哦,不,他不想。他想要的是……他不想要孩子,不像我。”他仿佛只是为了回答自己似的喃喃自语。
——艾勒特……为什么、——
我抓在水池边缘,实在不知道该不该表现出这种情绪。
——你为什么要我?——
男人看着我,停了许久都没有说话,我闻到他身上的药味和黄铜气味,在衬衣里,在他的发间。雨水的声音变得响亮,我听到自己的心脏在砰砰跳动,鱼尾沉进水里,温室的盆栽沙沙抖动,一切都有了惶恐的味道。
“不是我要你。”他最终说,“是你要我。”
“你很漂亮,不仅如此,你还很残忍,你符合每一条我对孩童的期望,乌尔斯。”
像是我的腹部被剖开,我的肋骨,我的脏器都暴露在他的视线之下,从肉到骨,从骨到肉。血管和经络都展开、摊平,给我爱的他不断审视。艾勒特,艾勒特,我的养父,你竟是什么都知道。
他死去的那天我穿着他的皮囊,跑出去。我用他的身体跑过只在温室里望见的街道,跑过石板和泥土,跑过我从不认识的人群。雨落在黑色的夜晚,如他所说的那般使我疼痛,无休无止。
= = =
“我要杀了它们。”
“我同意。”
“我要它们感受我的痛。”
“我支持。”
“我要把它们分开,挖掉他们的眼睛,折断它们的脊髓;我要让它们变成一片一片,刮掉,刮掉它们的所有;我要让它们哭并且笑,要让所有的情绪,所有的痛苦挤进它们的脸。它们要生病,要痛苦,要有爱并且失去,要有我们的一切。”
“我允许。”
埃弗雷特看着我,他的面孔竟有一丝艾勒特的神情。
“我们一起。”
TB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