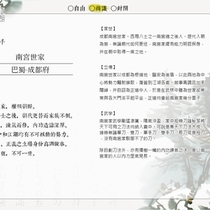【明月二】论坛开放http://orzpen.com/moon/forum.php
========================
—【明月千山】—
南宋年间,围绕着江湖百家展开的开放型日常养老企,目前一期剧情进行中。
世界观基调可参考金古梁温大师作品,真实系无玄幻。
目前企划主线已更新完毕,进入自由投稿时间。
------
企划印象BGM:
http://y.baidu.com/song/173529?pst=player&fr;=altg_new3||-1

那什么……因为实在太咸鱼了今天才想起来这边看下,然后决定把谷老头开成可以自由使用的角色,大家要跑剧情或者作为连接内容的角色都请自由使用。
m(_ _)m

狂赶进度,然而只前进了十来天(冷漠)
封印解除,写的很凌乱,差点想就此结局拉倒(吐魂)
少东家和柯叔只稍微提了一下,还是不要脸的响应了捂脸(不要报警??)
上接自己:http://elfartworld.com/works/107260/
===========================================================
1.
几日间连绵不断的雪,终是停住了。
金枝有些气闷的端着汤药从厨房出来,厨房的月娘越发没规矩,饭菜懒得做,药更是不熬,偏生费丹也不闻不问,他只能早早起来先将庭院打扫干净,再盯着小炉子熬药,中途少不得和月娘拌嘴一番,才能见她不耐烦的开始干活。
小童嘟囔着走上青石小路,手里稳稳的端着汤药,近午的阳光让冰冷的空气有了几丝暖意,他深吸了一口气再睁眼,纯澈的眼瞳被照出琥珀一般的色泽。
离除夕没剩几日了,总算有个好天气,等郎君病好了,辞了月娘才痛快呢。
金枝走近书房轻轻叩门:“郎君,药放下了,趁热喝了才好。”
虽早已习惯不会得到回应,但他依旧认真叮嘱了一句,见一早端来的早饭毫无被动过的痕迹,金枝习以为常的收好:“过会金枝再送午饭来。”
费丹好洁,园中的一切事物看着随性却很干净,这些都需要有人细心的打理,所以他很忙。
先回厨房放了东西,再到锵然堂开始一寸寸的擦拭桌椅书架,接着将每一本书上细微的浮尘细心扫去,给费丹送完午饭后,再去“映心湖”换了水,等一切都变得纤尘不染无事可做后,金枝坐在堂前发呆,看着阳光一点点从柔黄变作橘红,最后黯淡的淹没在夜色之中。
他照往日的时辰端了晚饭过来,却不见书房的灯火,低头一看,门前的汤药和午饭依旧原封不动,金枝唤了几声,又轻轻的敲了几下门,黑漆漆的房中依旧没传出熟悉的声音,他顿时慌慌张张的用力推门,岂料门内并未上闩,一下便开了,夜风灌入房内,吹的满地白宣哗哗作响。
2.
“娘子?娘子……”
朦胧的呼唤声愈发清晰,将思绪拉回现实。
阿羡眨了眨眼:“金枝呢?还是不肯来吗?”
“金枝说要留下看守园子,不肯过来。”小桂低声回答,小心翼翼的,尽管同样的话她方才已回过一遍了。
阿羡目不转睛的看着园门,这回她们不用翻墙就能出入园子,像从前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失去主人的园子于暮色中萧瑟无光,如同院门上的灯笼和白纱,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这样的结局她并不太意外,费丹本就是个痴人,最后的日子里他日以继夜的绘制了自己在万贤山庄的所见所闻,甚至还留书指明了埋骨之地,死的何其肆意。
郑曦收到消息时虽冷着脸撂下一句求仁得仁便拂袖而去,但送殡时还是来了,山风凛冽,郑曦生性畏寒,回去后就有些受凉,但这两日却和柯行之一起来过数次,虽然他们并没多说什么,但她明白其中的好意。
费丹的几位友人停留几日后也纷纷辞行,他们本是来去随心的不羁狂客,即便对月长哭,也可洒然离去。
回到羡归飞后,阿羡让累了几日的小藕小桂也去歇歇,面色如常的上了自己的“勿攒眉”小楼。
明日再给金枝送点炭火和食物过去吧,还有几日,就是除夕了……
她一边想着一边在窗旁的桌边坐下,眼神平静的看着自己的手,她的手背纤白柔润,指间却有些薄茧,不似闺阁女子的手那么柔滑。
其实她也不知自己在想些什么,脑海里似有许多影子在无声的流窜,心底涌动着难以言喻的热气,神思渐渐有些恍惚。
费丹他求仁得仁,死的不算太遗憾。
为他伤心的人很多,但他好像并不在乎。
那个雪夜的对话,她是不是错了?
因为自己又一次什么都没做,任由好友死了?
……又一次?
仅存的意识坠入无边的黑暗,极渊的最深处,是灼热的鲜红——————
“没办法的时候,逃就是最好的办法。”
混沌中,有个极好听的声音不断重复着。
阿羡如遭蛇咬般猛然睁眼,原本带着些微暖意的夕阳只余下炭火燃尽后的黯淡橘红,看来袭击方才是无意中睡着了,她定了定神,起身凭窗,本想将仅剩的余晖纳入眼帘,却在不经意间望见远处升腾的黑烟。
那个方向少有人家,更无大户,燃不起如此大的炊烟,何况黑烟直上云霄,可见火势之大。
那是费丹园子的方向————
阿羡霍然发力,桌上的小物件被扫了一地,青色的鞋尖于桌面一踏即起,翩翩然往后院落去,于消散的余晖中,像只双翼渐燃的蝶。
从羡归飞施展轻功奔过来不过片刻之间,阿羡急急的吐了一口气,觉得很荒唐,这条路她三年间走过无数次,从未使过轻功,西湖美景,烟柳画桥,有什么理由来去匆匆?但从地宫一事起,一切都开始变得不受控制,由不得她优哉游哉了。
青衣擦破夜色,转瞬间掠上墙头。
满眼都是呛人的浓烟,以锵然堂为中心的大火一路蔓延,冬日的干燥让漫天火光在梁上急速扩张,灼人的热浪带着飘飞的黑灰扑面而来,阿羡以袖掩口从廊下奔出,发肤在弹指间变的滚烫,任谁看一眼都知道,这里完了。
她在这一瞬间心念百转,却无一种办法可解眼前惨况,费丹的书画几乎都在锵然堂,如果现在冲进去……也许还能带出一些……
此念一起便在脑中不断盘桓,瞳孔中吞吐的火舌与梦中的鲜红重叠在一起,她下意识的连退两步,心脏在胸腔中剧烈跳动,脸色变的惨白。
有个声音哀哀的唤着,带着愤恨的哭腔,在烧的劈啪作响的火海中格外微弱。
一个伶仃身影手脚并用的爬了过来,他额前渗血,混着眼泪和尘土,在脸上花做一团,但那只小手牢牢牵住阿羡的裙角,如溺水之人抓住仅有的一截枯枝,在裙摆上抓出五个鲜红的指印:“……月娘偷画…她抢走了书房里的画!求你救救郎君的画吧……求你了!”
他有些看不清眼前的人到底是不是阿羡,但无论是谁都好,只要有人能救救那些书画,他都愿意诚心祈求。
阿羡蹲身将金枝半抱入怀,看着他哀求的模样,露出一个似哭似笑的神情:“月娘家……在哪?”
金枝低低的说了个地名,又絮絮的重复着一定要追回来之类的话语,阿羡举袖按住他头上的创口,那是受钝器重击所致,深可见骨,血不断的渗出,浸湿了袖角。
“郎君会不会生金枝的气…庭院还没扫…”金枝瞳中的神采渐失,神智不清的喃喃道。
阿羡轻轻抚了抚童子的头,染血的衣袖垂了下来。
“今日扫不完便明日再扫,明日不完还有后日,慢点……才好。”
梦呓般的低语在越演越烈的火势中戛然而止,怀中的人已什么都听不见了。
3.
从清波门出来向东数十里,有村名“栽霞”,多年前是个以种花闻名的小村落,当年常有风雅之士前来吟诗饮酒,留下不少佳作。但自从五年前有富商来此以高价收购名花,并在当地开设了酒楼和地下赌庄后,村民们就渐渐不再以培育新花为业,反倒游手好闲起来,吃酒赌钱便成了家常便饭,更有嗜赌者输尽身家,阖家老小卖作奴仆。几年间村民四散流离,富商也将酒楼等撤走,如今此处只是个破败荒村,余下的人家夜晚连灯都舍不得多点一盏。
月娘正在灶台上忙活,可惜破灶被塞的太满,她用火钳狠狠的往里按,恨不得再添一把柴好烧的更旺些。
真是晦气透顶。
她恨恨的拨着火,啐了一口。
眼见就是年关,主家却死了,她今日不过想拿几幅画卖几个钱,却被金枝那小娃儿狠命的阻拦,还要一个劲的嚷着要报官。情急之下她下了狠手,又仗着气头放了把火,反正费家也没了人,只要躲上一阵,说不定就算了事。
月娘从灶旁的竹筐里摸出一卷画轴,她大字不识更不懂画,接连看了几幅,都是大片的空白和随意涂抹的墨渍,月娘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大家都说主家画的好,可这些破玩意怎能卖钱?难道自己拿错了,这都是金枝涂的不成?
她心道早知该看清了再拿,懊恼的随手将这不值钱的玩意掷进火里,又不死心的去看另一幅。
门外突然响起了一阵敲门声,她有些不耐烦,又不知是哪个催债鬼!
“欠下的钱过阵子就还!老娘现如今没钱!”她不耐烦的嚷道,专心琢磨着手里的画。
门外并未响起意料中的骂骂咧咧,敲门声停了一阵,又响了起来。
月娘心里突然有点发毛,不知怎么的,想起平生不做亏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门这句老话。
但厉鬼也怕恶人,她捞起灶下的柴刀,大步走过去,一把将门拉开!
夜风挟裹着浓重的寒意掠面而过,月娘不禁打了个激灵,待她定睛看清敲门的人,顿时松了一口气,没好气的冷哼:“哟,羡娘子,你怎么来了?黑灯瞎火闷不吭声的是想吓死谁啊?”
敲门的人正是阿羡,只见她脸色极白,两手空空也没提灯,不知她怎能在黑漆漆的夜里摸到这荒村野地里来,月娘长的面白体壮,比阿羡高了足有一个头,虽然诧异,却毫无惧色。
门外的人无视那冷言冷语,平心静气的往月娘脸上瞧了一眼:“画呢?”
月娘闻言脖子一昂:“什么画?我哪知道什么画!”
她心知偷画杀人之事已被知晓,暗暗将握刀的手背到了身后。
阿羡声音放低了一些,轻轻的,似乎很温柔:“还我罢,话还好说。”
月娘心里发憷,面上却像烈火浇油般突然大骂起来:“你是什么东西!倒敢来问我要画,难怪三天两头往我家郎君这儿跑,老娘不揭穿你们就算了,凭地不要脸,也没见着这等狗————”
陡然一道乌光照面打来,那叫骂声随即被惨嚎替代,月娘尖叫着向后跌倒,脸颊上的鲜血如泉涌般顺流而下,阿羡振袖欺身,两指一下按在那支细长的乌棱镖之上:“若是费丹,说不定要用弹弓打你的嘴,我就不同了……”
月娘吓得魂飞魄散,只觉脸上的东西要被按穿颊骨刺入喉中,顿时一迭声嚎起来:“别,别呀!好娘子饶了我!画在厨房!”
见那袭青衣头也不回的掠身而去,月娘忍痛将脸上的乌棱镖拔出,忍不住又哎哟了几声,眼里露出恨极的神色。
阿羡自是无暇听那哀嚎,触目所见的情景让她彻底怔住,一股恶寒从脚底窜上背脊。
那些原本被主人珍之重之的画卷随意的摊在柴堆上,还有些在火中静静的燃烧着,就像最普通的一根柴或是一把杂草,悄无声息的化作飞灰。
她一路追来想过很多结果,最坏的不过是寻而未果流落山野,但从未想过,竟可以毁坏的如此轻易和彻底。
她陡然扑向灶台探手入火,猛地将那些残片抓了出来,袖风扬起的火星和飞灰落在衣上发上,灼烧出丝丝焦味。
残存发黄的宣纸在用力抓握后碎作一团团的灰烬,随着摊开的掌心缓缓飘扬而下,她用力喘了几口气后扶住灶台,胸口的窒息感更盛,灼伤至红肿的手指握的泛白。
月娘小心翼翼的靠近,她本要趁机逃走,又咽不下这口气,何况厨房里的人已僵在原地许久,极不对劲。这是个机会!她握紧柴刀,杀心顿起。
阿羡对此浑然不觉,她的目光从掌心移至火中,又滑到身旁的柴堆,那里尚有几件完好的卷轴,她拾起离得最近的一卷,握在手里感受它的质感,紧握了一阵才发觉这卷轴比其他的要小巧许多,不似费丹素日的喜好。
许是想确认它果真完好的事实,她匆匆的展开了卷轴。
三步之外有影子贴了上来,看画的人却似耳目俱失般毫无察觉。
阿羡目不转睛的凝视着画面,她已经感觉不到也不想去感觉任何了。
那是一幅本不可能出现的人物小像,有别于作画之人一贯豪迈潇洒的写意山水,小像笔意纤柔勾描细腻,画的是春日景致,画中女子立在庭中的玉兰树下垂首含笑,风拂青衣,娉娉袅袅。
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好似在哭——
“你不是……从不画人吗? ”
身后寒光乍起,当头砍下——
========================================================
补充说明(含吐槽):
1. 费丹扑街的时间是十二月二十一,下葬是十二月二十五,月娘杀人放火是十二月二十七。
2. 费丹是伤势未愈+过度耗损猝死的,(注:因为右手不可复原的损伤导致无法再画写意山水,若要活下去也只能以给人画造园林的图纸为生,此生追求已失又不免落入庸俗之中,所以懒得活了)在此之前已悄咪咪留下遗书,交代了一些事并说找个能看到西湖美景的山头随便埋埋就成。
3. 费丹一生只画山水,最后出现的这副画是他唯一的人像作品,既无题字也无落款,不知何时所画,也从没有向谁提起过。
4. 恭喜费丹达成了本企第一个撕卡PC的成就!!也恭喜自己达成了手撕挚友卡的成就!!(痛哭流涕)这都是交友不慎的后果,前车之鉴后车之师再想上我的车没门没窗缝也没有……(省略一万字吐槽),阿羡从这章开始彻底解锁,不知道还有没有人会想看这个画风变异的女子……总之,真的很谢谢看到这!!(合掌)
虚实两阵一起跑,我分身术潮强(不
成功化身流水账狂魔,互动的大家都没写到几句……不好意思响应,只好跪下…………
已经好久没插上板子了(呆滞
上接徐飞白【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上)http://elfartworld.com/works/105541/】
见徐朗二人都不言语,林鹰扬只道他们旧雨重逢不知从何开口,就也不再接话。方才见得徐飞白只靠内力便可为阿朗驱毒,使他恢复如初,林鹰扬悬着的心也落下了一半。
那日林鹰扬因身携阿朗配刀在八卦田被徐飞白救下,带回住所疗伤。修养期间,他曾向徐飞白问起当日八卦田是否还有别人。徐飞白回忆片刻,便告知林鹰扬除他之外未曾遇见旁人。几日相处,林鹰扬认定徐飞白不是说谎之人。既然出口处只有自己一人,那应当是连海生伤势不重,已经先行离开了。
思及至此,林鹰扬也心生懊恼。整日想着行侠仗义,结果做起事来却是这般德行,也不怨连海生负气,只能怪自己太过没用。
许是心里有愧,也是不肯承认失败,林鹰扬得知徐飞白准备去万贤山庄寻阿朗后,即使被其以有伤为由婉拒,仍执意要一同前来。今日水潭旁有幸一见高手过招,自己这伤号果然成了累赘。不过既然阿朗已无大碍,林鹰扬虽惭愧,也不再纠结于此。
半月前同行四人,如今已有三人平安,只有谢楠云还不知身在何方。
林鹰扬原本盘算着找到阿朗后再将谢楠云之事告知二人,如果可以便一起去寻她。但是现在情况不同,还有另一件事情,他想自己去探查清楚。
刚才在水潭前,徐大侠与一人遭遇,当时他虽在远处看不真切,却也隐约在那人后方见了几个熟悉的身影。
若那几人正如自己所料,此去就不宜和任何人同行。
下了决定,林鹰扬便拿出先前为阿朗准备的衣物伤药,细细叙述了自己上次离开地宫的经过后,借口说方才碰见个熟人,与徐朗二人就此告别,向两人相反方向去了。
自水潭前折返已过了半日有余,却毫无自己要找之人的踪迹。白兜了几个圈子的林鹰扬只得返回那处小门环绕的厅堂,想着继续往地宫深处探索。
大概是耽搁太久,此时厅堂四周小门紧闭,空旷无人,比半月前更添几分肃杀之气。
今日故地重游,难免回想起当时种种。虽然心情大有不同,林鹰扬却觉得若是重回那日,他的所做所为也并不会有何变化。
生来没有那种气魄,恐怕这辈子也做不了大侠。
不过此时实在不是思索反省的时候。林鹰扬在厅中四下徘徊,正愁着该去何处,就在一面石门上发现了同行时谢楠云曾经用过的记号。林鹰扬大喜,遂决定沿此路前行,先行找寻谢楠云。
经过一段与当初自己与连海生离开时相似的迷宫,不知寻了多久,昏暗处隐约见一女子倚在石壁旁休息,定神细视,正是谢楠云。
此时谢楠云已被困十数日,衣角沾灰,脸上脏污,左手臂活动也不太自然。见林鹰扬找来,她有些惊讶的站起身,脸上流露出喜悦的神色来。林鹰扬却是没想到谢楠云这般反应。他本以为被抛下的谢楠云理应有些怨气,谁想却看她喜形于色,心中更是愧疚。
谢楠云见他无恙,也不谈自己遭遇,开口便问起其他二人情况。得知连海生平安脱身,阿朗也和朋友结伴离开,谢楠云更是喜不自胜,仿佛身上的伤痛都在此时飞了去了。
面对如此的谢楠云,林鹰扬自感汗颜,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只得从随身携带的东西里掏出衣服干粮递给谢楠云。东西递了出去,才意识到这地宫实在没有女孩子换衣服的地方,难免有些尴尬。谢楠云却是没想到这层,随手将东西收入行囊。整理一番之后,两人便结伴继续探索。
短的我也好尴尬……
柿子在之前八卦田到底做了什么,我们有缘虚阵再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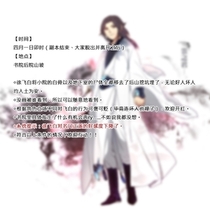



暗搓搓的来更新一下……打破月更BUFF……
这回画风剧变走的是神叨叨路线,主要是因为有个神叨叨的挚友(X)
从这一章开始终于慢慢解锁阿羡的个人线了!(筋疲力尽的摊成一团)
上接自己:http://elfartworld.com/works/105251/
==========================================================
十二月十五,西湖之畔。
冬夜飞雪寂寂,洋洋洒洒的将黑夜的寂寥渐渐掩盖,费丹的园子临近西湖,入冬后更是风寒水冷,阿羡拢了拢身上的兔毛斗篷,看了一眼不算太高的院墙,墙根下的雪已积了一层,月色下白茸茸的,很是松软的模样。
小桂提起灯笼照了照,有些嘟囔:“就这里了吧?费郎君伤的莫非是脑袋,好好的大门不让进害得我们……”
“有你啰嗦的功夫,早就进来了。”
不知何时已经坐在墙头的小藕打断了小桂的絮叨,伸出手来,阿羡搭上手,歪着头笑眯眯道:“小藕就是干脆。”
“也就这种小事能为娘子效劳,哪里敢当呢。”小藕平日里举止娴静,此时却干脆利落,手劲也出人意料的大,她轻松将阿羡拉上墙头,两人眨眼间便没了踪影。
园内,锵然堂。
今夜的金枝依旧睡的不太安稳,他揉了揉眼睛,在好不容易热起来的被窝里挣扎了一会儿,咬牙爬起来穿好衣服,摇摇晃晃的端着油灯走了出去。
他本有自己的房间,不用将就在冰冷透风的锵然堂,然而金枝心内的担忧却不允许自己回到离书房略远的下人房酣睡。
自从费丹从千金堂回来,便呆在书房甚少露面,金枝也曾从门缝里偷看过,只见满地废纸上尽是些繁复凌乱的线条,既不像山水也不似园林,与费丹平日所画大不相同。
但费丹不许他进去他便不敢进去,只能定时将饭菜与汤药放在门外,再痴痴的盼着郎君能吩咐些什么,可费丹却很少说话,送去的饭菜与汤药常常是热了又热,有需要便写了字条压在门下,似乎这世间的一切都已与他无关。
想必今夜书房的烛火依旧亮着,而自己依旧只能默默看着窗棂上映出的熟悉剪影,但即便如此,也足够金枝回到凉透的被窝中安心入睡。
堂前数盏灯笼被风吹的直晃,明亮与阴影在摇动中的交错不定。
金枝被晃得眯了眯眼睛,稚气的小脸上满是困惑。
“羡,羡娘子,你怎会在这里……”他本想问你怎么进来的,但困意还尚未散去的脑中一片混沌,只能呆呆盯着堂内站着的人。
阿羡正对着眼前高大的书架出神,这里满墙的书卷都坠着竹签,用小字仔细做了注释,看得出主人十分珍爱。她从前来时也曾翻看过几本,书里的字迹端秀,似是女子所抄。
寒风从半开的门外灌入,竹签互相敲出细碎的清响。
“听说你家郎君吩咐不许任何人进门探访,所以我从墙上进来的。”
雪夜的风确实有些冷,阿羡合拢双手呵了口热气,大大方方的解释。
这理所当然的答案让金枝更加困惑:“不,不是的,郎君的意思是……”
“好啦金枝,进都进来了,一起去看看你家郎君可好?”阿羡揉了揉冰凉的指尖,对此似乎有些不满,她细心的将手捂在斗篷里,熟门熟路的往书房走去。
金枝急忙跟上,连连摇头:“诶!羡娘子,郎君说过不见客的!”
从锵然堂到书房不算太远,以青石碎瓦铺成的小道于花草间蜿蜒,园中虽种了不少花树,却唯独不栽柳树,阿羡也曾笑问,这园子曾叫柳园,却偏偏不栽柳树,是让客人留下好还是不留的好?
那时的费丹是在观花还是在赏石?阿羡边走边想,也记不太清了,只记得他说:“什么柳园,也不知是哪一任主人取的,我的园子,没有名字才好,无柳自是不留了。”
这般有一搭没一搭的回想着,便到了书房,房内灯火烨烨,里头的人自然也未睡下。
金枝远远立住脚,屏息看着窗户上映着的人影,他不敢靠太近,生怕打搅了书房里的人。
阿羡走到门前,她步子很轻,在风雪声中几不可闻。
那剪影正自挥毫,只是惯用的右手的改成了左手,运笔间尤为滞涩,不复往日的行云流水。
然而挥毫之人专注如昔,就算只看影子,她也能想象到费丹那副风云变色也事不关己的表情。
那日——
“我倒是想去看看。据闻万贤山庄背山临水,高低有致。佳苑难得,官府一封,开启便不知何年了。”
听了女子兴致勃勃的描述,专注于笔下的书生眼神微动,难得露出了感兴趣的表情。
“不就在眼下?你要是真想去,喏,钱塘湖门外大理寺贴着募集告示呢。”
女子半开玩笑的一指,拍拍手将掌中的点心碎屑尽数喂了雀儿。
一句玩笑,竟至如斯。
阿羡叹了一声,她甚少叹气,只因叹气太多的人据说运气不会太好,所以她一叹即止,伸手往门上推去————
费丹的声音也是这时恰到好处的响起————
“阿羡?”费丹声音有些低哑,颇显倦意:“别进来。”
“你怎么知道是我的?”阿羡不由笑了起来,手扶住门板:“也许是金枝也说不定。”
“金枝才不会在我窗外叹气,何况不听主人言,半夜三更进园子这种事,别人做不出来。”房内费丹好像也笑了。
“费郎君当真知我也,”阿羡微微一笑:“那么,我可以进来吗?”
屋内沉默了半晌,见费丹未表可否,阿羡索性在门前石阶坐下,将斗篷能灌进风的地方一一掖好:“王子猷雪夜放舟访友,幸好是刚至门前就兴尽而归,否则吃了闭门羹,岂不是佳话变笑话?”
“从未见有人敢自比王子猷,丹更不敢与戴安道相提并论。”
阿羡笑眯眯托腮:“若他不服,便来找我,你怕什么?”
“羡娘子还是这般像雀儿,成日里叽叽喳喳的。”
“那你也还是画个不停。费郎君博闻广知,阿羡有几个问题想请教,”阿羡眨眨眼,她甚少不待人回答便自顾自的说下去:“我有位好友,许是听了我的玩笑话去了险地而受伤,如今他伤未好全又闭门谢客,我想知道,他最近还好吗?在做些什么?可我却见不着人。”
“好与不好又有什么分别,我自然还是画个不休。”
费丹放下笔,他画不下去了:“其实这事与你无关,何况此番行来,也非毫无获益。”
阿羡轻轻应了一声,她所坐之处正好能瞧见窗下的“映心湖”,那是以整石凿刻而成的小小盆池,只能容下寻常铜镜大小的一汪清水,月夜推窗而望,水中皎月沁人心湖,是此园的妙趣之一。
此时石上已积了一层薄雪,所幸水面尚未结冰,那轮娇小的月儿倒映在她双眸之中,潋滟生辉。
费丹的声音也渐渐清晰起来:“从前我喜画写意,只道是意在笔间,观画之人也无非是文人雅士,心中自有丘壑。可人人心中之念皆有不同,观者观以本心,未必是画者所想,在此之前,我竟从未想到过。”
夜风似乎变小了些,细雪被屋檐悄然挡在了数丈之外,好似飘飞的珍珠绡帐。
“玉皇山一行,丹方觉身临其境之人尚不能将心境道出十分之一二,又何况寥寥数笔?写意写的不过是画者自身的意,岂能苛求观者解之。”
他似乎不在意门外之人是否在听,又或是知道门外之人一定在听:“如今我只希望无论观画者是谁,都能如我所观,虽不知有无人可解我画中之意,也不知我这番领悟是否为正道,但我此时此刻,只想将这幅画完成。”
“要很久吗?”阿羡叹了今夜的第二声气。
“尚未可知。”
“闻道岂争朝夕,你……无所谓吗?”阿羡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浮生有尽而道无尽,人固有穷,何惜朝夕。”费丹的尾音有些飘忽,似乎有些怅然,又满怀热忱。
阿羡听罢,又叹了口气,起身拂了拂斗篷:“既是这样,那我便回去了。”
她当真说完便走,款款离去。
金枝原本听的云里雾里,突然回过神来,瞧一眼阿羡的背影,又瞧一眼房里,左右为难的开口:“郎君,那金枝……”
“去吧,好生送送羡娘子。”
费丹温声说完,重新拾起了画笔。
归家时风雪渐停,小藕小桂在前执灯引路,月照白雪的光亮耀人眉目,阿羡被晃的眨了眨眼,忍不住抬头张望,今晚的月色盈盈滟滟,似乎格外空灵,又似与每年的每一个十五之月并无不同。
这时的阿羡尚未知晓,这已是今年的最后一抹明净月色。
===============================================================
正文不够补充说明来凑,没啥用的说明随便看看
1.为什么阿羡三更半夜爬费丹家的墙费丹也没生气,因为他两是神经病之交……行为方式都有些特立独行,不那么看重男女之防。
2.阿羡的话中用了“王徽之(字子猷)乘兴访友戴逵(字安道)”的典故,出自《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3.“闻道岂争朝夕“这个出自《论语.里仁》——“朝闻道,夕死可矣”,阿羡只是拿它的表意反问费丹了,虽然费丹又用表意回答了。(只是剧情化用,就别辩证内在哲学问题了???)
4.费丹的行为难以理解也很正常,因为他就是个追求艺术的神经病(淡淡)。
5.费丹园子里的布置都是他自己的捣鼓的,阿羡从前看到有女子笔迹的书,是费丹唯一的姐姐(已夭折)所抄。
6.金枝,十岁,是费丹家的书童,这娃儿十分爱慕自家主子…所以费丹真是个害人不浅的家伙…(这种隐藏到地心的设定作为挚友就不客气的直说了) (隐藏在说明里的疯狂吐槽)
想狗的心最終敗給了想搞個大新聞的心,我又灰溜溜地回來繼續寫了(……
所以我就說徐青風是已經出現過的人物嘛你們不要不信(被打
以及回了娘家的鄭小姐表示自己的頭頂好像有點綠(×
為什麼我還是沒有開始副本的劇情,為什麼,我真想給自己兩刀……
↓
徐青風獨自一人站在空蕩蕩的院子中央。
已是二更天,花家小院自然是靜悄悄的,不論是花家家丁們的伙房還是為招親而準備的小廂房都已經滅了燈,只剩一盞蠟燭晃晃悠悠地點在前院大門旁,是給守夜的夥計準備的。
此刻徐青風所站的地方,也只剩一抹月光。
他手握著他的絹扇,仍舊是一副波瀾不驚的樣子,好像他這樣的人,從來就不會遇到什麼令他難堪或是動氣的事情,他永遠如水如潭,深不見底,不為任何事所動。
這夜,這月,這風,這扇,這人,徐青風都不需多做什麼,這幅畫面看起來就已足夠風雅。
可惜還是有人打亂了這風雅。
黑暗中,廂房處有扇窗子吱呀一聲打開了,隨後一個身影從中躥出,來到徐青風的面前。
來的人是百里成風。
徐青風笑了笑,打開自己手中的絹扇,也不看百里成風,只細細地在月光下欣賞起自己扇上的字來,漫不經心地開口道:“百里大俠,您就算是難以入睡想要出門透透氣,也不該突然闖到這院子中來,掃了我賞月的雅興啊。”
百里成風冷笑一聲,道:“賞月?從剛才開始你就死命地盯著我的屋子,你還有閒情賞月?”
百里成風平日里不動氣便有兩分威嚴,此刻的語氣中更是加上了些許怒氣,若是旁人早該被這氣勢所壓倒,戰戰兢兢地交代一切事情了。可徐青風卻連目光都沒轉向他,仍舊在月下看著他的扇子,仿佛永遠看不膩一般。他甚至還伸出指頭來,按在那扇上描摹這那筆跡,直到他用指頭滿滿走完了那些筆劃,他才幽幽地轉過身來對百里成風道:“本來指名要和對頭同住一屋,結果一開門卻發現遇見了自己的舊情人,我怕你一時又是生氣又是激動犯出點什麼錯來,我可不想三娘就這麼跟你跑了,當然要盯你緊一點。”
百里成風目光一凝。
有風夾著落葉吹過,一片葉子無意間落入百里成風和徐青風之間,正對上兩雙對視的眼睛。
一瞬之間,原本完整的葉子自中心開始,仿佛被兩把無形的劍砍開了一般,竟碎成了五塊,林林落落地灑在他們兩人之間。
好厲害的劍氣!
百里成風行走江湖多年,人送外號“鐵劍大俠”,除了使得一套凌厲的劍法之外,一身的內力也是不容小覷的,用劍氣震裂一片葉子自然不難。但仔細一看那裂成五塊的碎葉,除了從百里成風身上發出的一道劍氣之外,另外兩道劍氣的方向顯然是從徐青風身上發出來的。
難道他也有這樣驚人的內力?手拿絹扇,還有著一雙女人似的手,一襲白衣公子模樣的徐青風,難道也是個內功好手?而且從他的身上發出了兩道劍氣,難道在那一剎那,百里成風的動作竟然還不及他快?
百里成風顯然也有些吃驚。
但他很快就恢復了平靜,他低下頭看著地上的碎葉,道:“你實在不該用出全力的,這樣豈不是被我知道了底細。”
他這句話換來的是一陣笑聲。這笑聲不大,至多也只能讓他們二人聽見,但這笑聲很惱人,聽起來帶著一股濃濃的譏諷味。
這笑聲自然是徐青風發出來的,他打開絹扇擋住自己的半張臉,在扇后笑得癲狂,末了,他回應道:“你怎麼知道這就是我的全力?你早該知道,我做事情從來不用盡全力。”
百里成風心裡一沉,壓低聲音加重語氣,頗有些生氣地質問道:“宋澄誠,你究竟想做些什麼?”
徐青風,也就是真正的宋澄誠,聽了這話,倒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妥,他只是將扇子從面上拿開,緩緩地繞著百里成風踱了幾步,這才開口道:“我想做什麼?我不過是想要些東西罷了。”
“你要什麼?”百里成風問道。
只見宋澄誠的眼神忽然一凝,他身上的原本那種悠哉的感覺瞬間蕩然無存,剩下的是滿滿的殺意。他一個字一個字清楚地說道:“我要你的命,三娘的人。”
百里成風追問道:“是要她的人,還是要她的手?”
鳳三娘的手,那雙能泡出天下獨一無二好茶陳家茶的手。
宋澄誠啪地一聲收起了扇子,道:“有什麼差別嗎?得到了她的人,自然就得到了那雙手。”
“你休想得逞。”百里成風給出了他自己的警告。
然而宋澄誠卻像事不關己一般,悠悠然道:“你不信?不信的話你不妨來賭一賭,翠金樓上的賭局已經開了,這兒的事情忙完了,你不妨上哪兒跟我賭兩盤。”
說完這句話,他倒也真像自己所叫的青風那樣,如一縷清風般,一下就消失在了院子中,只留下一聲腳步聲,落在廂房走廊的拐角處。
百里成風只好走回自己的屋子。
但他忘記了,他原本是從窗子翻出去的,此刻卻從正門回來了,門板吱呀一聲,一開一合間倒已弄醒了原本睡著的鳳三娘,她從被窩中抬起頭來看著百里成風。
百里成風趕緊關上了那扇被他打開的窗,最後一點月光也被窗紗擋住,整個屋子又陷入了黑暗。
但百里成風知道鳳三娘沒有再睡過去,因為他在黑暗中看到了一雙還在閃亮的眼睛。
他歎了口氣問道:“你怎麼還不睡?”
此刻的鳳三娘倒不似白日里那麼有精力,她也不再和百里成風嗆氣,倒是坦白地答道:“枕頭太塌、床板太硬、被子太重、你有點吵。”
百里成風心裡一驚,怕她已聽見了他和宋澄誠的對話,但表面上還是裝作沒事一般繼續說道:“你在撫雲閣住慣了,以前的你不會這麼挑剔落腳的地方的。”
回應他的是鳳三娘的一個綿長的哈欠,之後才是她懶洋洋地回答:“那是因為宋澄誠有錢養我,你窮。”
百里成風緊追著她問道:“看來他待妳倒是很不錯,你有見過他嗎?”
“隔著珠簾見過兩次,沒看清樣子但應該是個小白臉,怎麼了?你突然問起他幹嘛?”
百里成風進一步地問道:“如果我說,他也來到花家這招親的小院了,你會不會相信?”
鳳三娘淺淺一笑,還帶著倦意地說道:“這不可能,翠金樓上有人花二十萬兩銀子跟他賭誰能用最快的時間趕到太原,他現在肯定還在路上。”
“他就這麼喜歡賭?”
“他平生沒別的愛好,就喜歡賭,而且他從未輸過,不然你覺得撫雲閣又怎麼能在短短五年間買斷全姑蘇的綢緞生意。”
“那些都是他賭來的?”
“對。”
“他真的從未輸過?”
“從未輸過。”
聽到這裡,百里成風竟然露出了一絲笑意,黑暗中鳳三娘雖看不見那笑容,但她卻從對方的語氣中聽出來了這笑意。
百里成風用一種雀躍興奮的語氣說道:“那他就等著在我手上輸掉他人生的第一盤賭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