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月二】论坛开放http://orzpen.com/moon/forum.php
========================
—【明月千山】—
南宋年间,围绕着江湖百家展开的开放型日常养老企,目前一期剧情进行中。
世界观基调可参考金古梁温大师作品,真实系无玄幻。
目前企划主线已更新完毕,进入自由投稿时间。
------
企划印象BGM:
http://y.baidu.com/song/173529?pst=player&fr;=altg_new3||-1

感謝G太太成全,希望和叔叔的互動不會太OOC……
以及我真的對古風完全懵逼,有bug的話請大家溫柔地指出……原諒我是一個文盲……
↓
姑蘇城中酒家客棧自然眾多,但有“鼎味絕”這樣氣派的酒家,卻著實不多。
左倚姑蘇河,右靠市井大街,自然是落在絕佳的地方,一樓長桌,二樓雅座,到了最上層的三樓,卻又是一條長桌,直直跨越了約莫有三個鋪位的長度,配套的則是十餘條的長板凳,好一副隨性瀟灑的做派,平白地將最好的位置佈置成最低賤的酒家模樣,尋遍整個姑蘇城,怕也不會有第二家了。
鳳三娘打撫云閣出來,轉身要進的便是這間“鼎味絕”。
可說來也怪,偏偏在這樣一個奇怪的店鋪前,站著一個跟這條街都不太相符的人。
一面大旗挑在一人高的棍頂,那旗倒是簡單得很,黑邊白底,上書“神算”兩個大字,可仔細一瞧,這旗子卻已是飽經風雨,舊色染在旗面上,縱是逃也逃不去。旗未想動,背旗的人像是在與鼎味絕的小二爭執著些什麼,惹得旗子在棍頂顛顛晃動著。
鳳三娘湊近了,卻聽那小二模樣的人道:“喝了酒自當要付酒錢,不付自然就是叫花子,誰又要你個瘋瘋癲癲的傢伙來算命抵債!勸你還是快些把錢交出來,可莫要小瞧我們‘鼎味絕’!”
而那背旗的人卻仿佛沒有聽見小二生氣的口氣一般,仍舊是晃晃悠悠,醉色滿面的樣子,左手捏起三指,神神叨叨地輕點著,隨後又頗有意思地點了點頭,似是真的受到什麼天上的指示一般。
鳳三娘從他後頭看去,倒真是有幾分可笑,她也不急著進酒家,就站在那人身後繼續看著。
店小二卻沒有鳳三娘這般好閒情,生意人自是惜時如命,他的聲音自喉嚨出來,就像是給人拿皮鞭在後頭趕出來似的,在高聲時尖利,沉到低處時卻化為沙啞:“趕緊的,酒錢拿來,你再要這樣裝神弄鬼想糊弄過去的話,可別怪我們對你不客氣了!”
那人還是一副無所畏懼的模樣,真當是把店小二的話當做耳旁風了。
店小二吃了一口悶氣,自然是不肯這麼輕易放過他,可就在這小二轉頭,想喊來店裡人時,鳳三娘聽見那人忽然開口道:“兄台,人常言人命天定,你可知人亦能改命?方才我正為你算天時,你卻好生擾我,害我一個手抖,這下,只怕你的命宮受擾,將有大變啊。”
他故意做出吃驚憂慮的聲音,惹得小二也變得緊張起來,喊人也顧不上了,倒是湊上前去,悄聲問道:“敢問……有何大變?”
那人笑笑,道“輕則失金,重則失紅。”
店小二果然一震,繼續問道:“不知還有什麼法子能救嗎?”
那人點點頭道:“自然是有的,只要兄台肯花些銀子替在下將那酒錢付清了,在下即刻為兄台改命。”
那小二自然不傻,此言一出便識破這又是那人的詭計,正要破口大罵,鳳三娘的身影卻從後頭晃了出來。
只見她輕輕地拍了拍那背旗男子的肩,轉頭對小二燦然一笑,道:“小二你莫要害怕,酒錢我自然會替他付的,那命格自然也是會替你改的,現在只求你快快進去,為我們尋一張三樓的板凳,再備二兩上好的女兒紅,我們好上去詳談。”說罷,還挑了挑那道利眉,又拿那雙暗藏鳳凰的眼睛對著小二眨巴了兩下。
這樣的鳳三娘,又有哪個人能夠拒絕呢?更何況一個小二,聽到有人喝酒便是笑容滿面的,他抬起腳剛要往內堂跑,卻被人叫住了。
“二兩怎夠,先將我這酒葫蘆滿上再說。”言罷,一只胖乎乎的酒葫蘆就飛進小二懷中,他轉頭一看,才發現又是那背旗男子開的口。
“唉喲,你這人,人家說兩句客套話你倒還當真了。”鳳三娘嗔笑起來,繼而轉頭又對著那小二道:“也罷,你就替他滿上吧,今個兒姑娘我也是要尋酒,索性就尋個痛快。”
聽了這句話,卻是換了一旁背旗的男子笑了起來,喃喃道:“姑娘?三娘你這年歲,又何苦還稱自己是姑娘呢。”
鳳三娘扭頭,衝著他狠狠地瞪了一眼。那背旗男子自當是以笑代答,這一言一笑之間,他們二人已來到了三樓。
長桌一張,直直向南邊橫去,而在這長桌上喝酒吃茶的人,亦是循了店家的規矩,散散呼呼地在長桌上坐著,乍一看去,倒頗有長街宴之感。
二人尋了個旁人較少的位置剛坐下,剛剛的小二便端來了二兩女兒紅,順帶將已灌得滿滿的酒葫蘆還與那男子。
此刻,男子已將挑在隨身木棍上的“神算”大旗放了下來,小二這才好好打量起這人來。
內著的白衣自是有些時日了,布料失了新買來時的硬挺感,柔柔地沉在一身青色外掛之下。那手腕用黑色布料纏了起來,本看不出膚色,可一看那面龐便明了得很,有些蒼白的臉上還掛著些許胡茬,嘴唇亦是失了些血色,但奇的是那雙眼睛!縱使整張臉看上去滄桑,那雙眼睛卻仍是閃亮,似是還藏著能置人於死地的力量。可那眼神,那本還銳利的眼神,卻在觸到小二手上的酒葫蘆時軟了下去,像是眸子已先飲過那酒一般,竟已開始泛出酒醉時的神色,綿軟無力,頗失神色。
鼎味絕一日接待酒客少說也有上千人,小二在這兒干了八年,自然是明了貪酒之人的神色,可他亦是覺得沒有人能像面前這人那樣,貪酒如是,僅僅看一眼便已幻想自己醉了。小二自是不愿再理,匆匆放下酒具,便離開了。
鳳三娘自然拿過那酒瓶,穩穩地倒了兩杯。放下酒瓶,舉起那小巧的酒杯道:“巫馬牧,許久未見,三娘自是先敬你一杯。”說罷,酒已滑過喉嚨,刷的一下下肚了。
巫馬牧接過另一杯酒,卻不急著飲下,倒回味著剛剛上樓時的玩笑,只見他轉著酒杯道:“三娘啊三娘,你若真還當自己是姑娘,可不該飲酒。”
鳳三娘一挑眉,道:“不喝酒?那我該喝些什麼?”
巫馬牧笑著道:“茶。自然是茶,閩中多產茶,你又為何不喝?我聽過人滴酒不沾,卻只見你一人滴茶不飲。”
鳳三娘道:“你自是知道我是閩中人,亦聽過閩中陳家茶的名號,一飲此茶,只怕其他的茶水,我從此是入不了口了。”
巫馬牧道:“茶是好茶,卻也是一口毒茶。”
鳳三娘的眉毛又挑起來了,她略帶嗔怒地問道:“何出此言?”
巫馬牧笑道:“一飲此茶,從此不再能飲天下其他的茶水,怎不算毒?要我說,天下再沒有比你陳家茶更毒的毒藥了。”說罷,將面前的酒一飲而盡。
鳳三娘皺皺眉,卻不似因巫馬牧的話而起,她的思緒隨著他的話飄遠了,離了姑蘇,度過萬重山,到了她的故所去了。可不知怎的,面前浮現出的卻不是陳家二老的面容,亦不是自家那可愛的小茶園的模樣,倒是鄭漾榕的臉,愈發清晰地出現在了她的腦中。
她歎了口氣道:“這陳家茶對旁人而言或許是世間最毒的毒藥,于我卻不是。”
巫馬牧笑笑,道:“他既已遠去,你又何必執著至此?”
他二人都略過最為重要的字句不談,只是淺淺擦過所言之物,但雙方卻都明了對方心底想說的話,可見這二人熟識頗久,互知心事。在這長桌上難免有不老實的耳朵,但他二人的這番談話,縱使被旁人聽了去,也是摸不著頭腦,期間的真諦倒真只有他們自己明了。
可他們躲著某個人的名字不提,長桌上卻是好嚼舌頭的人占了多數,總有幾聲高談,落入了他們的耳中。亦如此刻,在他二人位旁兩座的位置,有位著紫色外袍的公子便就著酒勁吼出了一句飯後的閒談。
“哼,什麼青年才俊,我看那百里成風就是個休妻的莽人懦夫!”
鳳三娘牙口一咬,眼睛早已瞪了起來,仿佛那人下一句話一出口,她就要沖去理論一般。
咔。
这天王家客栈开市早,客人却也来得早,两个小贩一前一后推门进来的时候,客栈的伙计张六才来得及把桌椅碗碟安置停当,有一段时间没修葺了的木门撞上担子,发出一个沉闷的声音。
王家客栈地处益州城外,虽然不是什么闹市之中的高楼大宿,但赶不上益州城闭门的旅人往往都投来此处歇脚过夜,倒也称得上生意兴隆。张六早见惯了这里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来来去去,上下一扫就吆喝着带两个小贩去了下房,那两人倒也不甚计较,痛痛快快给了钱放下担子,一个还跟张六家长里短的攀谈起来。
“咱两个是同乡,一路上相互照应着做点小生意……我这哥哥是卖药的,身上难免有点药味,所以不太乐意靠近别人,可不是故意看不起小二哥,还请小二哥多多担待……”
那卖茶的还在絮絮叨叨翻来覆去的说,卖药的迎上张六的视线,点头苦笑了一下。他的人和他的担子真的都散发出一股子药铺的气味。
“不打紧,这位大哥吃饭的时候坐偏些就行,咱们打开门做生意,味道冲了别的客人吃饭总是不太好。”
张六关上门的时候,那卖茶的还在点头哈腰地赔笑答应。
咔。
王义耷拉着眼皮看了一眼声音传来的方向,正见着两个横眉怒目的虬须大汉从门口进来。那两个大汉腰间各挎着一柄单刀,单刀无鞘,刀刃上却沾着些黄褐色的痕迹。身材粗短些的汉子肩上还挑着一个骯肮脏脏的布包,布包看上去又沉又坠,随着大汉的脚步时不时发出些硬物碰撞的声音。王义开这家客栈也已经有些年头了,他一看就知道这两个人身上有些麻烦事。他不想惹麻烦,而不惹麻烦的方法就是不看,一眼都不多看。所以他带这两个刀客去客房的路上也是低着眉眼的,这才没注意撞上迎面走过来的书生。书生的方巾和布衫都跟他手上的书一样有好些破洞了,但依然洗得相当干净,这一下被王义撞得书和人都摔在了地上,书生也只是爬起来一边拍打书和布衫一边小声说些“白丁无教……”之类的难懂词句,随即便匆匆走了开去。
“那是个住在下房的穷书生,落第了又不敢回乡,就在这儿赖着,帮人写写字算算账勉强糊口,成天只会念几句酸诗,也不懂规矩的,两位爷千万莫要见怪。”
两个刀客还没开口问,王义已经赶着解释了起来,那样子仿佛唯恐两人怪罪他撞了晦气。身材高大些的汉子摆了摆手,瞪了一眼书生走开的方向,粗声道:“他娘的,老子就看不惯这种认得几个字就眼高过天的鸟人,有什么了不起的!”
“有什么了不起的!”
粗短些的刀客像鹦鹉学舌一样随声应和道。
咔。
张王氏听见大门又轻又快地响了一声,急忙迎出去,门口是个年轻的公子正在帮一个客商模样的人搬行李,两人怎么看都像是认识了多年的好友。那客商体态微微发福,面上一层抹也抹不去的风尘之色,大概是过了好一段时间跋山涉水的生活了。他这样的客商,出手总是较阔绰些的,对这城外的小小客栈来说也是不多见的大主顾,但张王氏的眼睛没在他身上停留太长时间。他的旁边有这样一个人,谁都不会看他太久的。
跟他有说有笑的那个青年公子生得白净俊秀,走路又轻又有力,正是那种豪门贵家春风得意的公子哥儿们的走法。他看上去挺适合在青楼花街一类的地方跟漂亮姑娘们弹弹琴喝喝酒,可他身上偏又穿着长途奔波的人爱穿的那种黑斗篷。他帮那微胖的客商把行李全部搬进门来,转头就喊小二给他们两间上房,口气却还很有礼貌,一点都没有公子哥儿瞧不起人的架子。张王氏和伙计阿乙急忙上去帮两位客人拿东西,阿乙平时总爱板着个脸,跟那公子说话的时候竟也有些笑意。对着这么一个精力充沛又很讲礼貌的秀气年轻人,很少有人还能板着脸的。那公子起初还想帮张王氏两人搬行李,却被两人笑着拒绝了。别说是个讨人喜欢的客人,不管来了怎样的人,都没有让客人进了客栈还自己搬东西上楼的道理的。
“公子,您的行李都搬好了,您就住在上楼梯左手边最里头那间,跟您朋友紧挨着,要是有什么不满意,尽可以叫我们换的。”
阿乙说着,伸手想帮那公子把他一直背着的那个巨大包裹也搬上去,却一下扑了个空。那公子若无其事地把包裹甩到另一边,笑盈盈地点了点头。
“有劳小二哥了,这个不重的,我自己拿上去就行。——呃,你说我有朋友在这里?”
看着这年轻人一脸迷糊的样子,阿乙也有些困惑地挠了挠头。
“不就是刚刚跟您一起进来的那位大爷吗?公子怎么连跟自己一起来的人都忘了?”
年轻人愣了一下,失声笑了出来。
“啊,你说袁大哥啊。我们刚刚在大门口才认识的。”
王义、张六和王大力擦着手从后厨出来,正瞧见张王氏搂着账本笑得像朵花儿也似。王大力是这客栈的厨子,也是王义的表弟,却跟王义完全不一样,是个心里藏不住事的急脾气。三人之中也是他最先上前大声问:“嫂子,怎么笑得这么开心,莫不是捡到金元宝了?”
“你才捡到金元宝,成天脚不着地的,什么时候才能安定下来让我和你哥别再操心。”张王氏收起笑容瞪了王大力一眼,复又笑出了声。“你是没见着刚才投店的那公子,人家可阔啦,放下行囊就把钱全结清了,还多给不少辛苦费,我看他晚上这一顿就能赶得上下房那几个穷鬼住几天的钱。”
这话一说,几个人都禁不住笑了起来。不论是什么人,只要心里高兴就会笑,而钱总是让人高兴的。只是王义没笑多久,脸色就有些变了。他看着突然出现的那两个人,脸色变得像是刚吃了一截没去瓤的苦瓜。
“有钱人家的公子出来游山玩水,出手总是阔绰些的。”那两个刀客中高大些的满脸堆笑地这样说,只是他脸上横肉太多,堆起笑来反而更显可怖。“这样的阔朋友咱哥俩也想结交结交哩,他住在哪间房呀?”
“哪间房呀?”
矮壮些的那个也学着另一个满脸堆笑地问了一句,两个粗声粗气的大男人偏要挤着嗓子装出一副亲切模样,这场面本身就已经十分可笑了。但是伙计、厨子和掌柜夫妇都没有笑,他们非但没有笑,看着那两人拎在手里晃晃荡荡的钢刀,简直像是要哭出来了。
“他们绝对是那条道上的强人,若是惹他们一个不高兴了,我们绝对也要遭殃的。”
等那两个凶神恶煞的人走得看不见了,王义才敢窸窸窣窣地开口跟其它人这样说。一句话里用了两个绝对,也不知他是要说服别人还是要说服自己,反正其它人像是都被说服了,一个个都发出赞同的声音。
“就是,就是,而且那公子来的时候动静那么大,就算我们不说,他们也肯定能找出来的。”张王氏拼命点头表示同意丈夫的话,还多加了一条她觉得他们没对不起任何人的理由。说完了,她又闷闷不乐地吐了口气。
“只求他们别闹出人命。我们可还要开店的,何况那公子长得可俊哩。”
王义和张六在后院又忙活了些时候,忽然看见那穷酸书生从东厕的方向走过来。书生看见他们,还是那副不可一世的神气,却难得没有像躲避脏东西一样匆匆避开,而是迎面走过来,斜着眼打量了他们一下,冷笑道:“有法不循,可谓忠乎?贪谋私财,可谓礼乎?主人,这不忠不礼的事最好还是少做些,隔墙有耳,天网恢恢,吃了的不吐些出来,总要遭报应的。”
书生自顾自说完就走,那卖药的像是也刚解完手出来,看见书生急忙低着头闪在一边,书生却还是面露嫌弃之色,看也不看他便掩着口鼻加快了脚步。
“这……这天杀鬼打的穷酸,说什么乱七八糟的,小心我在你饭里搁沙子……”张六过了好一阵才回过神来,立刻尽职尽责地骂了一大通,随即又小心翼翼地望了王义一眼。
“掌柜的,您说这穷酸……该不会是看见我们后厨那东西了吧?”
“他成天说疯话,亏你也当真。”王义的声音听着比张六镇静些,却也有点犹犹疑疑的音色混在里头。“……你别管,也别声张,咱们明天就动手料理了那东西,我晚上再去看一眼厨房门锁没锁。”
不久到了晚市时分,王义便也重回大堂帮忙打些下手或是上酒上菜;他端着一盘熟牛肉回到大堂时,正好大堂里一张桌子上爆发出一阵响亮的笑声。
围坐在那桌的都是客栈的住客,卖茶的和卖药的并那个书生居然也坐在一处,倒让王义小小吃了一惊。坐在这桌人中间的是那下午投店的俊秀公子,这当儿他正跟同席人比划着说些什么,那巨大包裹不知怎么的又拿了下来,就放在他脚边。
“您说是吧,您说是吧?也不知这是家里大人谁给起的字,念着跟那听琴的短命樵夫一模一样,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自己的名……哎呀,我还没报过名字是吗?”
那公子边说边呷了口酒,朗声笑了起来。
“在下钟乐,黄钟大吕的钟,及时行乐的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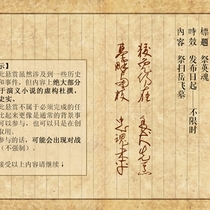
鳳三娘是個率性的女子。
但光光說她率性,是遠遠不足以形容出她的模樣的。人生本就是個大包袱,裡頭裝滿了互相矛盾的東西,誰也道不清自己身上背著的包裹里究竟藏了多少東西。
鳳三娘自然也不是個無趣的女人,因此旁人也都難以形容出她的模樣。
若單單看她那張臉,自然是叫人不易遺忘的。一雙眼睛雖不是柔情嬌媚的丹鳳,卻藏了鳳凰的模樣,眸子一轉,倒像是精氣神十足的鳳凰,剛從大火中重生而出,閃出一道利落乾淨的眼神,令人忘卻了她眼角暗藏的歲月的痕跡。接下來的鼻子,就這麼長在面龐中央,不高不矮,不大不小,不聳不塌,一個人有這樣一個鼻子是不容易的,世間俗人們的鼻子,不是太高就是太矮,叫人見了,總生出想要幫他們整整位置的念頭。再者,有的人生得但是好看,但那一隻鼻子,不是大如煙斗就是小如豆粒,面上失了平衡,看了也勾起人心裡反感的情緒。更不用提那些過聳和過塌的鼻子,前者看來不似漢人,後者看來就是個草包。因此,鳳三娘有這樣一個不高不矮,不大不小,不聳不塌的鼻子,是很難得的。再往下去,鳳三娘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就是她那一雙唇。
紅唇似火,倒不是沾染了胭脂粉飾的緣故,只因她本就生得一口豔麗的小嘴。那雙唇卻不似普通女子那般瘦弱淺薄,相反,豐滿的唇辦倒像熱切的邀請一般,招呼著每位碰面的旅人。在那誘人的下唇上,赫然顯出一顆黑痣,黑紅相襯,豔色不減反增,叫人不由得念起品嚐時候的香甜。鳳三娘因為著一口美麗的紅唇而出名,但她出名的原因不單單是因為著唇的模樣。
她不開口,輕含紅唇時美艷得每個人都愛她,可當她開了口,每個見到她的男人都恨不得掉頭就跑。
可他們還偏偏都跑不掉,只能憑著那雙唇張張合合,把他們從頭到尾數落上一遍。江東有醫名劉,見過鳳三娘那口紅唇后斷她氣血過熱,勸她調養,沒想反被鳳三娘連罵了一條長街,從醫德依始罵得劉大夫一愣一愣的,直等到夜色西沈, 鳳三娘趕著要喝酒才放過了他。
鳳三娘往江湖里一扎就是十來年,從無人問津到現在的人盡皆知,人們對她的稱呼也從早年的“翠嬌娥”變為了如今的“朱玉羅剎”,一綠一紅,倒是生生斬斷了鳳三娘的兩段日子。
鳳三娘是從百里成風成親之後,不再穿她最愛的翠色衣裳的。
一個女人,總得是有什麼緣由才能在江湖闖蕩十余年,抱著三十多歲的年紀還未成親。
除了為情所困之外,還有什麼能讓一個女人在一夜之間就變了模樣的?鳳三娘二九后便不再青衣,其中的酸澀怕也只有她一人才能說清道明。
晚風吹過撫雲閣,鳳三娘倚靠著最外的圍欄,想得卻是這等胡亂的往事。
她如今已是三十有三的女人了,見過的男人也有千千萬,她本不應該再為陳年舊情而感到心痛,她早已將自己的感情按在心底,盡管全天下人都知道她愛著百里成風,她就是不要再提,哪怕是一字一句,她都要對方謝罪。
可她今天又想起百里成風了。
她的手上正捏著一封短信,白紙黑字,只有瞎子才看不見上面寫了些什麼,也只有呆子才會不明白,這短短的一句話於鳳三娘而言,是多重的痛。
沒錯,那信上寫道,百里成風的妻子,閩中南音的掌門之女,鄭漾榕已被她的丈夫修書一封,由長安送回天興府了。
鳳三娘怔怔地看著那行字。
她還記得彼時她被百里成風迷得不行,甚至還大鬧了他的親宴,直到他明明白白地對她說,他這輩子只愛鄭漾榕一個人,不會為他人所動,也只愿與鄭漾榕一人白頭偕老,她才真正被打敗,乖乖地回了姑蘇,從此再不去長安,也不回閩中。
而現今這封信狠狠地摔了他們一耳光,不只是百里成風,鳳三娘覺得她和鄭漾榕也被狠狠地打了一巴掌,把她們都從美夢或謊話中打醒了,徒留一個火辣辣的巴掌印,令人難堪。
其實,鳳三娘本是不太信這信上所說的話的,人人都有眼睛,百里成風待鄭漾榕如何,人後她是不知道,但光從人前看,她是絕不信百里成風會休了鄭漾榕的。
他倒的確愛她,不論走到哪裡兩個人都如膠似漆,他也亦待她頗好,凡是鄭漾榕想要的,百里成風也都替她得到手。
只得慶幸鄭漾榕不是個刁鑽的女子,不然怕是有很多人會過得很難。有時候鳳三娘也會思索起這個問題,為什麼她和鄭漾榕長在同一個地方,心性脾氣卻差得這麼大呢?她火辣易怒,豪放無憂,鄭漾榕卻常常深鎖眉頭,把萬千的謹慎小心都收到了那小小的皺紋之中,叫人看了就不禁心疼。作個比方,她就是那曠野里的蘆葦,風怎麼闖她也都是奮力地搖晃,反抽風兒一個大嘴巴子,而鄭漾榕卻是空谷里的一朵幽蘭,碰見她,風都不敢大聲呼喊,只會收聲斂氣,從她身邊悄悄走過。
更多的時候,鳳三娘會懷疑鄭漾榕是否真的是閩中女人。
按她的印象,閩中很少像鄭漾榕那般沉靜無言的女子,至少在她離開那兒的時候,大多數人的家中還是女人掌權,一開口,中氣十足,一雙快手打得了麻將,也做得了家事。哪有像鄭漾榕那樣,輕聲柔氣,一看就是十指不沾陽春水的模樣。不過她似乎忘記了,在閩中,天興府南音本就是一個異類,夾雜在一堆又狠又粗的閩音之中,從琴瑟里呼出一曲悠揚樂聲。
就是這樣的一個鄭漾榕,就這樣被百里成風休了,任誰都會吃驚。鳳三娘自然比旁人更加驚訝,她是知道百里成風的性格的,她明白他是真的待鄭漾榕好,而如今這一紙休書,不僅休掉了鄭漾榕,也休掉了她對百里成風的信任。
但她的心中卻還在替他辯解。
她寧願相信百里成風是有什麼難言之隱,才不得不做出這些事的。或許是他遇上了些麻煩,不願牽扯上鄭漾榕,又或許他要去什麼遙遠的地方,不得不找個理由把鄭漾榕塞回天興府以保她的周全。鳳三娘兀自想了很多,想完後又搖了搖頭,這些假設太過蹩腳,她連自己都說服不了。
高樓束起來往薄雲,樹的尖頂留在眼底,撫雲閣本是個很美的地方,也是她留在姑蘇的“家”,可她此刻卻彷彿一刻都坐不下去了,她有些急躁地從欄邊起身,腰肢一扭,就往閣外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