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月二】论坛开放http://orzpen.com/moon/forum.php
========================
—【明月千山】—
南宋年间,围绕着江湖百家展开的开放型日常养老企,目前一期剧情进行中。
世界观基调可参考金古梁温大师作品,真实系无玄幻。
目前企划主线已更新完毕,进入自由投稿时间。
------
企划印象BGM:
http://y.baidu.com/song/173529?pst=player&fr;=altg_new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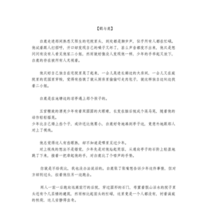
我覺得我寫著寫著就OOC了……不敢響應了,太太你看到了的話請看在我誠摯眼神的份上原諒我吧……
↓
鳳三娘本就是容易動氣的人。
有的時候,一個愛生氣的女人比一個不愛生氣的女人更受男人們的歡迎。
鳳三娘是一個受歡迎的女人。
因此當她有些生氣地瞪著鄰座的人時,不但沒有惹得對方生氣,反倒讓正在長 桌上高談闊論的男人覺得開心。
可鳳三娘不開心,十分地不開心。
這幾年來,“百里成風”這個名字就成了一種禁忌,但凡在她面前提起這個名字的人,少不得要挨她的一頓打。倒不是說她的功夫有多好,只是一般會在女人面前嚼舌頭的男人,多半也不會花多少時間在精進武學上,對付這些男人,鳳三娘還是很有自信的。
她的手本放在那長桌上,可聽到鄰桌的嬉笑時,她的手已經抬了起來。
那只纖纖玉手很快,快到鄰座那人都還未看清,手上的酒杯就已經飛了出去,跑到了他自己的頭頂。
鳳三娘能被“朱玉羅剎”絕不僅僅只是因為她的嘴毒,見識過的人都知道,她的手,也是可以很毒的。
那酒杯是被直直打上去的,此刻還是筆直向上飛著的,但只要再過那麼一會兒,等到杯子翻了個個兒,杯中的酒就必然要傾下,澆座上的人一頭酒水。鳳三娘打的就是這個主意,她不直接出手,倒是想要借他人杯中之酒去傷人,也不知是覺得不忍還是覺得不屑。
眼看著那酒杯就要翻倒,鳳三娘嘴角倒是提起了那麼一絲輕笑。她在笑什麼?那是快意的笑嗎?笑自己的計謀得逞,馬上就有個倒霉的傢伙要在這長桌上出醜了?或者是那笑是冷的,在笑自己雖然已經到了這個年歲,卻還是一聽見那個名字就如此激動?
沒有人知道。
鳳三娘自己也不知道。
可巫馬牧知道。
他不在意鳳三娘的笑是為何,他也不在意百里成風究竟如何,但是他知道這杯酒馬上就要惹出一些亂子了。
所以他出手了。
放在他膝上的木棍忽然飛出,這棍子來得快,停得也快,只見棍尖往空中一劃,隨即降了下來,直指鄰座的那位紫色外袍的公子。
棍上,穩穩地停著那杯酒。
鳳三娘白了巫馬牧一眼,微帶怒氣道:“我請你喝酒,你還向著他?”
巫馬牧還是那懶洋洋的模樣,道:“你們打架我不管,別浪費了好酒。”說罷,他將棍子往回一帶,一隻手收起棍子,另一隻手拿起那杯酒,一飲而盡。
而那位紫袍公子仿佛還未回過神來,他的酒杯是怎麼被人打飛的,又是怎麼落到那棍上的,他一概不知,剛剛他與對座高談闊論的氣勢突然就不知跑到哪兒去了,此刻他安安靜靜地坐在位子上,表情奇怪地看著巫馬牧和鳳三娘二人。
接話的倒是他對座的人,只見他大笑幾聲,轉而向巫馬牧抱拳道:“好棍法!”
巫馬牧卻只是將杯子丟了回去,似是對他絲毫不感興趣一般,轉過頭,端起了鳳三娘桌上的酒壺又給自己倒了一杯酒。
對方倒也不覺得尷尬,坦坦蕩蕩地繼續說道:“在下毛抗,先道聲謝謝了,不知朋友是何名姓?”
巫馬牧倒也不急著答話,一杯酒下肚,他才用棍子挑了挑那面舊旗,道:“我只是個算命的,和各位碰面也不過是偶然,又何必追究我名姓。”言下之意是不願說出自己的名字。
於是毛抗的目光又從他身上移到了鳳三娘身上。
鳳三娘眉毛一挑,道:“宋澄誠。”
這下毛抗的表情變得很難看了。
姑蘇城中見過宋澄誠的人不多,但沒聽說過他名姓的人卻是少之又少。年紀輕輕就已經將姑蘇城中所有布匹生意買斷了的撫雲閣閣主的名字,姑蘇城中的人想不知道都挺難。而總有好事者傳言他長相俊美,並且使得一手好扇,在江湖上也應有一兩分名氣。按常理來說,不論是誰吐出這個名字時,總要帶上三分敬意和艷羨的語氣。而此刻這個名字從鳳三娘的口中吐出,卻著是讓毛抗覺得刺耳。
他有些掛不住面子了。很顯然,儘管他對巫馬牧和鳳三娘和和氣氣,但這兩個人卻都不太願意理會他。
所以這下輪到他沉默不語了。
這回開口的卻是那位紫袍公子,他很是不滿地咳嗽了一聲,轉頭看著鳳三娘道:“在下董少平,在姑蘇住了二十多年了,還是第一次聽說大名鼎鼎的宋澄誠是位女子。”
鳳三娘的唇勾了勾,指著巫馬牧對著董少平道:“你信不信他是個算命的?”
董少平看著那“神算”旗道:“他這一身打扮再加那一面旗,我不得不信,總不會有人愛把自己打扮成算命先生出門喝酒的吧?”
鳳三娘道:“好。那你信不信我就是宋澄誠?”
董少平道:“不信。你是個女人,又怎麼會是宋澄誠呢?”
鳳三娘笑了,道:“我是不知道有沒有人喜歡把自己扮成算命先生出門喝酒,可我知道有一個人,特別喜歡把自己扮成女人出門喝酒。”
董少平問道:“總該不會是宋澄誠吧?”
鳳三娘笑著反問他道:“怎麼不是呢?我問你,在這姑蘇城中你見過宋澄誠幾次呢?”
董少平答:“一次都沒有見過。”
鳳三娘道:“這不就對了,你想,一個壟斷了布匹買賣的商人總是要出門談生意的吧?可至今都沒幾人見過宋澄誠的真面目,你覺得這是為什麼呢?”
董少平聽到這裡,聲音已經開始有些顫抖了,他有些不敢說下去:“因為……他扮成了女人?”
鳳三娘輕笑道:“還真是個傻小子,哪有讓女人去談生意的道理。”
董少平有些發愣,一時竟搭不上話來。
於是鳳三娘自顧自地接下去說道:“說你是傻小子倒還真不假,都能變成女人了,怎麼就不能再變成其他人呢。”
董少平木然。
“可你不是宋澄誠。”一旁的毛抗突然開口。鳳三娘猜他和董少平一定是結識了有些時日的朋友,不然怎麼總是在另一個人啞口無言的時候替對方出來擋刀呢。
她想到了這些,可她沒有再開口了,她只是坐在桌上,替自己倒了一杯酒當做回答。
於是毛抗繼續問道:“不知我們和兩位是否有過什麼過節?”
巫馬牧笑了,但他沒有答話。
答話的是鳳三娘。
“有。”她把這個字咬得很沉很重,像是一塊大石頭壓在她心上,逼她說出這個字的。她繼而說道:“你們提到了一個不該提的人。”
“百里成風?”
這是董少平的回答。話音剛落他就覺得臉上挨了一巴掌。雖然不疼,但響得令人難堪,他只覺得自己的左頰火辣辣地在燒著。
“鳳三娘?”毛抗問道。
“算你有點眼力勁兒。”鳳三娘笑道。
毛抗笑了,這回他笑得很放肆:“都說鳳三娘一往情深,這回我倒算見識到了。因為我們語不擇詞而生氣倒情有可原,不過,你可不該沖我們發脾氣!”
鳳三娘皺了皺眉,問道:“為何?”
毛抗答道:“有件事情,只怕你還不知道吧?”
鳳三娘更加奇怪了,她追問道:“什麼事情?”
“百里成風休了鄭漾榕是為了去娶那花家的小姐!”
這又是董少平的聲音,話音一落,他的右臉也挨上了一巴掌。這回的巴掌,倒是又響又重,疼得董少平忙捂起自己的右臉。
“你胡說!”鳳三娘張口罵道。
标题感谢玄学!
上接 http://elfartworld.com/works/94202/
补坑0.5/2
不知不觉又啰嗦了一堆,拆开减负_(:_」∠)_
丹丹的部分反应咨询过丹丹的亲娘,如有ooc,都是我的错(土下座)
※※※※※※※※※※※※※※※※※※※※※※※※※※※※※
柯行之瞟了一眼对面六人,扶着费丹倚石壁坐下。
自他与费丹落入洞穴已近日余,一路逆着洞内微弱难查的风向而行来到这处宽广的洞穴,不想竟被人堵了去路。
这六人皆是二、三十的模样,每人多少都带了点伤,手中兵刃轻微损伤,衣衫破损腌臜,颇有些狼狈,显是困在地宫不少时日。
为首的汉子年约三十许,面目甚为凶狠狡狯,正饶有兴致地打量着柯费二人。
那眼神,就像草原上盯着猎物的豺狼。
即便神思昏沉,费丹也不得不强打起精神。
狭路相逢,纵使他俩无意多生事端,对方自恃人多,甫相见就起了歹念。
若非之前跌得狠了,又伤了脚,以他的脚力和柯行之的身手,越过这些人扬长而去也未尝不可。
如今这拨人手握刀兵,渐成合围之势,正面冲突只在顷刻之间。
只是,他虽大致知晓柯行之武功高强,却也不知其以一敌六,胜算能有几何。
且一路行来,其余各处地面皆是泥土山石,唯有此处铺以厚实的黄沙。洞中空气相较别处的阴冷潮湿,也显得分外干爽。事出反常,此地亦不可久留。
“柯兄……”
“勿忧。”
费丹刚开口,柯行之便低声示意他放心。随即起身朝为首的汉子抱拳:“足下可是‘翻江蛟’曾平?”
“小子好眼力,认得你曾爷爷。”曾平颇为自得,其余五人也附和地笑起来。
“某受人之托,来寻王家大郎,请问他现在何处?”柯行之仍旧神色淡淡,混不在意他的无礼。
这曾平乃黑街中一混混小头目,“翻江蛟”是自号,讨厌他的人通常在背后称其为“浑水虫”。
这样的人,费丹不认识,柯行之本也不该认得。只不过此次受托入地宫寻人,郑曦认为找到一群人中的某几个人的几率,总比单单只寻一人的几率高些,花重金自闻尘阁买来与王大郎同行诸人的情报画像,临行前让柯行之记下,这才一照面就认了出来。
只是按当初的情报记录,出发时一行十三人,如今只剩六人,王家小子不在其中,怕是凶多吉少。
费丹倒是有些意外——没想到在这错综复杂的地下迷宫中,还能遇到柯行之所寻目标的相关人员。
能当上小头目的人,自然也有些小聪明。曾平见柯行之问得直接,也不推诿,只盯着柯行之手中宝刀,目光贪婪:
“小子就是这样求人的?”
柯行之顺着他的目光瞄了眼手中唐刀,颇为干脆地将之抛向曾平。
曾平接了刀,还不满足,又抬颌遥点柯行之腕间缠的夜明珠碎片。
“那个!”
“足下若告知王大郎下落,某自当奉上。”
柯行之仍旧面沉如水,岿然不动。
曾平“啧”了一声,随即装作欣赏宝刀的模样,向队伍边缘的一瘦小汉子使了个眼色。
那人会意,小心地没入火把光照不及的黑暗中。
“那小子不走运,进来没几天中了机关,死了。”
曾平状似漫不经心地回答,实则打量柯费二人的神色。见两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似乎并未察觉这边的异动,便接着说道,态度十分轻慢:
“也不知那短命鬼上辈子积了什么德,还有人来寻他。”
他摩挲着刀鞘上的宝石。
“王大家的斤两爷爷清楚得很,小子这么财大气粗,想必王家出得起的酬劳你也看不上。小子哪条路上的,划个道儿下来。 ”
柯行之微微皱眉,不答反问:“王大郎可有遗言或遗物留下?”
曾平心道这点子有些扎手,也不回答:
“不说也罢,让爷爷猜猜——听王大说过,他有个堂伯祖在千金堂供事,不会是那个姓郑的‘假娘子’请你来的吧?”
——待他用言语激这高个的出手,趁其不备擒住他的同伴作为要挟,接下来这两人就任他宰割了,就像之前落他手里的两拨人一样。
果不其然,对方眉头拧起,隐有怒意。
曾平见状暗喜,趁热打铁地将从王大那儿听来的流言变本加厉了一番。
“听说那‘假娘子’喜好男风,瞧你们俩一副小白脸的模样,莫不是那姓郑的相好?”
说得高兴,这伙人竟大笑起来,嘲弄之意随着污言秽语不绝于耳,丝毫不顾及柯行之愈发阴鹫的面色。
费丹在旁听得颇为恼火,一手摸向腰间挂的弹弓袋子,打算好好惩治一下这帮口出恶言的混账。却见身前蓝影一动,化作电光直击领头的曾平。
曾平虽暗自戒备,不料柯行之出手如电,丈余的距离竟如无物!刚想拔刀便被其扣住手腕,又是一折,剧痛之下刀便脱手,又回落回原主手中。
几乎在折断曾平手臂的同时,柯行之另一只手扣住他的下颌,“喀啦”一声捏得粉碎,又一掌似轻实重地拍向他的胸口。
曾平发出古怪的哀嚎,胸口凹陷着斜飞数丈,重重摔向石壁,随即跌落沙地。
同伙正要来救,柯行之已旋身。
火光中几道平行的斑斓轨迹划过,带鞘的唐刀击碎了最近一人的颈骨。
那人登时没了生息,手中火把滚落。
一时间火光摇曳,人影幢幢。
分不清谁是猎物,谁是猎人。
唐刀上的金饰宝石,在火光中熠熠生辉。
这光芒,在空气中留下数道简洁灵动的残影。
每一次残影的轨迹变化,就有一条人命消散。
翩若惊鸿,矫若游龙。
费丹怔然。
这是他初次见柯行之与人动手。
明明是一面倒的杀戮,只因几乎不曾见血,他竟然觉着——“打得还挺好看”?
他一定是饿疯了!
片刻,尘埃落定。
蓝光笼罩中的身影陡然一折,径向费丹身侧扑来。
※※※※※※※※※※※※※※※※※※※※※
Q&A;
Q:“假娘子”这个说法是怎么回事?
A:咳咳,可以理解为一个从小被家人宠坏又不学无术的小孩,对作为亲人长辈口中“别人家的孩子”的阿郑的羡慕嫉妒恨。
【阿郑:……这枪躺的有点远……】
Q:“郑熹”“好男风”这种流言又是怎么回事?
A:咳咳咳……因为师兄“弟”俩平时比较亲近,又都单身,好心人介绍亲事也全推了,于是……【世间总少不了各种八卦……
虽然两人都不care这种流言,但假如当着他们的面拿这事说另外一个……咳,结果之一大家也看到了……
【阿郑:……你真是我亲娘啊!】
Q:如果曾平只谋财不作死,柯叔会这么凶残吗?
A:不会。但他会黑吃黑(唐刀和夜明珠就是这么来的),然后扔下一帮被洗劫一空&被点了穴几个时辰不能动的混混,带丹丹扬长而去;)

我居然纯写文了。。。。啥也不说了先去切个腹。
错别字和病句请无视,答应我不要为难一个画手好吗(有脸说吗
----------------------------------------------------------------------------
1.
阮岑做了个梦。
梦中他被一条通体漆黑的巨大的蟒蛇缠绕,身体被紧紧箍住,骨头都发出悲鸣。蛇身冰凉而黏腻,坚硬的鳞片划过他的皮肤带出丝丝血痕。蟒蛇的头升起,悬停在他面前,吐出的信子带着浓重的血腥味拂过他的面颊。
只差一点。
阮岑的指尖已经触到刀柄的末端,但不管怎么用力也无法再向前一寸。只差一点就能拔出刀宰了这个畜生。阮岑表情扭曲,死死盯着蟒蛇大如灯盏的一对招子。
忽然那蛇笑了。
阮岑头皮一炸。蛇的笑声嘶哑又癫狂,又好像随时都会断气一样破风箱一般漏着气,听着说不出的诡谲。阮岑认得那笑声,他这辈子也不会忘记的笑声。
笑声戛然而止,蟒蛇的脸仿佛被打散的水波,慢慢汇聚成一张熟悉的脸。
那蛇一字一字地说:“我早说过,你逃不开的。”
然后阮岑惊醒了。
他背后出了一层冷汗,身上的疼痛和意识一起渐渐清晰起来,梦魇留下的恶心和厌恶如鲠在喉。
“阮大哥!你终于醒了!”一个惊喜的声音在耳边响起,阮岑转头看到库夏的脸。他被库夏扶着坐起,发现自己正在皇城司自己的卧室内。天色已晚,只有少年一个人守在床头。
“唐珏呢。”
库夏没想到阮岑开口头句话竟是问这个。他的笑容一下子僵住,好一会儿才像蚊子哼哼一样支支吾吾地道:“……让他跑了。”
阮岑猛地一把甩开库夏,少年趔趄几步坐在了地上,一时回不过神。他的阮大哥从来都是笑盈盈的,让人感到如沐春风,想要亲近。阮岑对他格外纵容,从未说过重话。即使他犯了错,阮岑也只会佯怒对他象征性的稍加惩戒。他从没有见过阮岑像现在这样的表情。那双以往总是弯出一个温柔的弧度的眼睛冷的结霜,仿佛在看什么碍眼的脏东西。库夏眼眶一下子红了,不知所措地向后退了些许。
忽然“哐”的一声响,门被谁粗鲁的踢开,打破了屋内凝固的气氛。
只见杜秋晏双手端着药跨进门内,后面跟着的越泽回身将门关好。望望床上那个,再看看地上这个,杜秋晏翻了个白眼,张嘴就喷:“你在床上睡了两天两夜,小夏也不眠不休的照顾了你两天两夜。谁知道你一睁眼就把起床气往人头上撒,阮大人好威风,区区长见识了!”
越泽一言不发的拉起库夏,发现他竟微微发抖。紧接着两人都被阮岑的惨叫引的望了过去。
“杜秋晏,你他妈想烫死我!?”阮岑端着药碗像端着烫手山芋,差点一把丢出去。
“难不成你还想区区吹凉了喂你吗?”杜秋晏早已经退开了好几步,省的药汤洒在自己身上。“反正你这个白眼狼也不知感恩,小夏你说是吧?”库夏忽然被点名,吓了一跳,抬眼见阮岑也看了过来,不禁一哆嗦。
阮岑打量库夏片刻,少年确实眼下发青,眼中都是血丝,看起来很久没有合过眼。长的那么人高马大,却被吓的一副战战兢兢快要哭出来的表情,着实可怜。他干咳了一声,放轻声音向库夏招了招手:“你过来。”
库夏鼓起勇气走到阮岑床边,单膝跪下,低头道:“都怪属下没有按阮指挥使的交代及时抓住唐珏,使计划功亏一篑。请您惩罚我吧。”
半天没说话的越泽也上前抱拳跪在库夏身旁:“属下失职,在地宫脱队,没有保护好阮指挥使。库夏因为从未见您受如此严重的伤,一时乱了阵脚,才让唐珏有机可乘。是属下的责任,请您责罚。”
“……”阮岑支起腿,颇为无奈 “我说这还没过年呢,在这儿跪一地我也不会给你们发压岁钱的。”
库夏闻言抬头,面前的阮岑眼中含着三分笑意,又变回了他熟悉的那个阮大哥。
“行了,你们先下去休息吧。别打扰大人说话。”阮岑挥手赶人。
杜秋晏也道:“别担心,好人不长命祸害遗千年,这厮一时半会死不了。”
于是库夏一步三回头地硬是被越泽拉了出去。
临安冬夜的风冷的刺骨,越泽将披风递给库夏时,发现他已经换了一副表情。库夏的眼窝比中原人都要深一些,月光打在他脸上在眼中投下一片阴影。他的神色中再没有像先前要被抛弃的孩子般的无助,而是近乎阴鸷地沉静。
“唐珏……”库夏喃喃道“……都是那个人的错。”
“阮伯渊,我从来没有发现你对找死如此有天赋!”屋内,杜秋晏变脸也如翻书快,怒不可遏地将药碗在地上摔的粉碎,气势汹汹好像接下来就要扑上来把床上坐着的人掐死。
阮岑从来没见过这位喜欢冷嘲热讽的公子哥这么失态地发飙,摸摸下巴想笑不敢笑:“我的错,是我托大了。秋晏先别着急……”
“不着急!?你知道姓唐的给你的身体里埋了什么吗?走脉针,等那根针到了你的心脉,华佗在世也救不回你……!等你一命呜呼了我再着急还来得及吗?”
“放心,我不会死的。”阮岑淡淡笑了笑,目光投向微弱的烛光。他又想起那个梦,那些曾经想操控他的人,想践踏他的人,想要他命的人,都已经被他杀死了。今后也不会有人可以妄图左右他的命运。
“我的命,只有我自己说了算。
2.
十二月初十。
清晨的薄雾未散,一个披着斗篷的白衣青年敲响了皇城司的大门。
两侧的侍卫仿佛没有看到他似得直视前方。半晌厚重的大门被从里面打开,开门的士兵扫了青年一眼,便一言不发的把他让了进去。
青年本想和领路的士兵客套两句,谁知抛出去的话皆是石城大海,没一个回响,也就不再言语,只时偶尔向周围打量。他们穿过长廊,一边的校场上数十身材魁梧的年轻军官正在操练武功,身手皆不同凡响。
忽闻一道凌厉的破风声,白衣青年挥手,掷出的暗器和射向他的箭在空中相撞,箭支被从中间切成两半,落在青年脚下。他抬头向箭射过来的方向望去,一个束着马尾的卷发少年持弓站在不远处的屋顶,居高临下的看着他,目光如同鹰隼。带路的士兵浑然不觉般自顾自的向前走,转眼间那少年又搭了两只箭拉满弓,对着青年放出。
青年抽出腰间的扇子,一边向引路人的方向退一边劈手击落箭支。随着箭支而来的还有从房顶跃下的少年,他飞身逼近了白衣青年,冷着脸二话不说拔刀就砍。白衣青年只好皱眉接招。奇怪的是不管是带路的,还是在附近练武的军官,都好像又聋又瞎,对这场打斗熟视无睹。
两人打了有三十几个回合,才听到一个懒洋洋的声音出来阻止。
“慢慢慢,小夏,叫你出来迎接唐公子,你怎么和他打起来了?”来者正是阮岑,身着一袭红色官服,倚在柱子上笑的神采飞扬,完全看不出和一个月前被抬回来出气多进气少的是同个人。
库夏闻言马上收了刀,规规矩矩地背手站到阮岑身后,再不看唐珏一眼。
“唐公子,别来无恙。这小子不懂事,喜欢和人切磋,没有恶意的,还请不要介意。”
切磋?刚才那副架势明明招招要命。唐珏不以为然,还是挑眉笑道:“无妨。”
阮岑一路有说有笑,带着唐珏来到一间客房。杜秋晏已经在里面坐着了,看到唐珏也不起身,只是微微点头算是打了个招呼。库夏关了门立在一边,板着脸好像一尊门神。
“那么事不宜迟,我这就给阮大人推针吧。”唐珏说着微微沉吟“只不过还要请这两位无关人等出去我才能开始。”
“无关人等?”杜秋晏眉毛纠结在一起,眼看就要发作。阮岑却按住他的肩膀,点头道:“唐门的绝学是不容其他人窥视,是我疏忽了,你们先出去吧。”
杜秋晏瞪了一眼阮岑,依言带着库夏离开。房内只留下阮岑和唐珏二人。见唐珏还没有动作,阮岑道:“唐公子还有什么要求?但说无妨。”
“正如阮大人所说,唐门绝学不容外人窥视。阮大人亦非唐门中人……在我为大人推针前,需要给你点穴闭气。大人没有意见吧?”虽是询问,唐珏却有恃无恐。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能有什么意见?”阮岑笑的无奈“唐公子,请吧。”
一炷香过后,阮岑被唐珏点穴唤醒。试着运气,阮岑没有发现异样,看来唐珏真的是要给他续命。
“那么,下月初十我还会在同一时间登门拜访,先告辞了。”
“唐公子不忙走,辛苦了你这么久,不如留下来吃个午饭吧。”阮岑嘴里这么说着,却刚睡醒般打着哈欠,一脸我就是和你客套一下你可千万别当真。
唐珏驻足眨了眨眼睛,干脆答道:“好啊。”
“啊嗷?”阮岑的呵欠打了一半走了调。他马上调整表情,好像自己真的很热情好客一般祭出招牌笑容“那再好不过。”
阮岑说要请客吃饭时虽然没有什么诚意,真招待起人来却是一点儿也不含糊。不一会儿客房的圆桌上就摆满了酒菜,虽然不见得是什么昂贵的菜肴,但都做的非常精致,别有一番风味。除了偶有仆人进来送菜,屋内还是只有他们两人,一时静的有些尴尬。
“我平日不是和弟兄们混在一处,就是和人出去应酬,这么安安静静的和人一桌吃饭倒有些不习惯了。”阮岑没话找话。
“唐门人多,每次吃饭也是很热闹的。”唐珏应道。虽然是他自己答应要留下吃饭,坐了半天,却并没有动筷子。
“每次请唐公子吃饭,唐公子都只坐着看。我倒不知原来唐公子是用眼睛吃饭的,光看就能看饱。”
"只要能吃饱,你管我用哪儿吃呢。”
阮岑算是明白了,这讨人嫌的家伙根本不是想吃饭,是在找麻烦呢。阮大人的脾气众所周知的好,最不怕人找麻烦。他不以为意地微笑,拍了拍手。不一会儿便有人推门而入,端上一个雪白的酒壶。
“不吃饭就陪我喝一杯吧,这是前些天别人送的葡萄酒,听说是从西域买回来的,很是难得。唐公子尝尝?”说着阮岑亲自为唐珏斟满了一杯,红色的酒液几乎要从白玉杯中溢出,鲜血般扎眼,散发出奇异的香甜味道。
唐珏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赞道:“好酒。”
阮岑总算满意了,坐下一边聊天,一边和唐珏推杯换盏,一派宾主尽欢。
然而唐珏看似喝的干脆,其实那酒一滴都没有入口,借着袖子的遮挡,全倒进了藏起来的小瓶里。
“嗯……也差不多是时候了。”阮岑半闭着眼微醺,撑着脸把玩着酒杯,忽然冒出了一句。
唐珏本想问是时候什么,忽然感到手脚发凉,整个人开始慢慢下沉,头脑发昏。他想站起来,却发现下盘无力,又跌坐回椅子上。再看阮岑,哪还有刚才要醉不醉的样子,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他,双眼不能更清明。
“你……”后半句还没说完,唐珏就彻底昏了过去。
3.
夜阑更深。
阮岑坐在离床不远的椅子上静静望着床上好像睡熟了的人。那人眉眼精致的有些凌厉,只有这个时候看上去才像卸下了防备,显得柔和很多。
阮岑至今为止见过许多形形色色的人,对忠厚老实的人他施以恩德,对有所求的人他给予他们想要的好处,对懦弱胆小的人他以其弱点牵制。顺应他的人他毫不吝啬的回报,和他对着干的人大都被送去见了阎王。
很久没有人让他觉得这么棘手。
然而不知为何他还是忍不住去探究,以至于他有那么一瞬变得不像自己,为此几乎命悬一线。
这不是什么好兆头。
想到这儿他的眼神沉了沉,但阴霾马上又被和往常一样的笑意冲散。
“醒了?”阮岑近乎温柔地开口。
唐珏从床上坐起来,默默检查了一下自己手脚有没有缺件后才抬起头:“阮大人这是玩哪出?”
“唐公子不胜酒力,小憩了片刻。”
“可那酒我一滴也没喝。”
“要是喝了,你现在也不会在这里。”
唐珏顿了顿:“熏香里下了迷药,酒里是解药?”
“不错,唐公子果然聪明。秋晏的迷香真是厉害,无色无味,连唐门都能放倒。”阮岑笑道,语气忽然多了几分伤感“我原以为和唐公子同生死共患难一番,已经是过命之交。没想到唐公子还是对我如此戒备,让我怎么放心把命交到你手上呢?”
“大人到底想做什么?”唐珏微微皱眉。
“我想还钱。”
“什么?”
“唐公子为了我用了极为珍贵的金风玉露,又耗费真气为我疗伤,那一百金不早日还给你,我寝食难安。”
“……”唐珏忽然感到不详“什么意思?”
“床头有镜子,唐公子照照便知。”阮岑微阖双眼,笑的意味深长。
唐珏狐疑地端起镜子看了半晌,身形一震,脸色突变,。
“我专门找了临安最好的工匠为你打造的,唐公子可还满意?”
唐珏扯开衣襟,只见自己脖子上戴着薄如蝉翼的金色的项圈,上面刻有细密精美的流云纹样,还镶嵌着数颗价值不菲的宝石,流光四溢。项圈的正中刻着一个狼纹,中间有一很小的“渊”字。
“这项圈工艺极为复杂,用的是自称鲁班传人柳老板特制的奈何锁,没有钥匙世上任谁也打不开。材料是极品玄铁,虽然轻薄,最锋利的刀也没有办法将其斩断,为了美观还特意镀了层金。加上上面的雕花和宝石,算下来花了我两百金……”阮岑若无其事翘着脚扳着指头吹嘘道“不过看着和唐公子这么相配的份上,多出来的算我的一份心意,便不用找了。”
阮岑又道:“唐公子既然握着我的小命,江湖险恶,我自然要保证唐公子周全。只是无奈公务繁忙,分身乏术。这项圈中间的刻印是我的私印,若唐公子在临安遇到什么麻烦,只要让城里的士兵看看这个印记,定有人会帮你解围。”
“……”唐珏盯着阮岑,虽然脸上没有表现出咬牙切齿,估计心里是被气狠了,一时竟无言以对。
“啊,差点忘了说。”阮岑才想起来似的一拍大腿,明快的笑容却沉了下去,摇曳的烛光映在他的眼睛里仿佛鬼影幢幢“……若是我有什么不测,戴着这项圈的人也会被认为是凶手,无论海角天涯都会被我的人击杀。唐公子切勿忘记。”
“这样一来,才是真的同生死,共患难。你说是吗?”
Q&A
1. 阮岑梦里看到的人是唐珏吗?
不是。是他的老相好(不是)。
2. 为什么唐珏让阮岑让闭气他就闭气,一点不反抗?
唐珏敢在皇城司杀人,出门就被剁了。而且要杀早杀了,也不会特意跑到皇城司。
3. 唐珏为什么会晕倒?
进门的时候熏香里有毒,到了一定时间才会发作。其实两个人毒中了毒。葡萄酒里面有解药,如果唐珏相信阮岑喝了酒就啥事儿没有直接回家了。人和人之间最重要的是信任啊。
4. 阮岑为什么要给唐珏戴项圈而不是戒指手环脚环?
戴别的地方万一对方是个贞烈男子一气之下把手啊脚啊的砍了怎么办。横竖头砍了会死,还是戴脖子上吧。
5. 阮大人给唐少戴项圈是出于啥心理?
报复?控制欲?
性命握在别人手里是阮岑的大忌,是最不能忍受的事情。为此甚至会做出鱼死网破的事情。别看他笑嘻嘻的其实也是非常窝火。


……三千字写了一个月我真是没脸见林小姐(/ω\)
反应有大体上问了问荔枝人但基本还是靠擅自揣测……林小姐实在太可爱了我力有未逮,希望并没有OOC得太多……
标题典出杜荀鹤《送友游吴越》。
上元夜,从唐时起便是个火树银花的不眠之夜。今年的元夕节天公不太作美,飘了点零星的雪点子,却丝毫没有扑灭都城百姓观灯玩乐的心情。宣德门前扎了三层楼高的鳌山,张挂各色各样新奇精巧的罗帛灯、羊皮灯、珠子灯、五色琉璃灯,俱皆妆饰华丽、巧夺天工,连官家亦登楼赏灯以示与民同乐。得不得瞻天颜尚在其次,内造的新样彩灯和贡灯总归是好看的。譬如新安这次的贡灯里有一种无骨灯,以绢囊贮粟为胎烧制琉璃灯笼,烧成之后倾去粟粒,整只灯笼浑然无骨,通体玲珑剔透如水晶球儿一般,引得游人竞相观看,排挤喧哗,十分热闹。
沈苑从摩肩接踵的人潮里左右张望了一下,盘算着是从吴山井巷还是都酒务巷折回家去能稍微宽松些。先前他送小妹芊仪过来跟已经出阁的妹妹萃音碰头,她们两姐妹感情好,原约了今天要一起看灯,姐妹俩一见面嘀嘀咕咕有说不完的话,他干脆就让芊仪跟着萃音到她家里过夜去,明儿一早再去妹夫家接她。
为了方便舞队往来,御街路心的杈子都给撤了下来,然而街上人潮攒动,有看灯的、看歌舞的、赶趁卖灯的、歌叫卖市食的,整条路上挤得满满当当,简直比平日设着杈子的时候还更难以通行。人一多,便难免有些奸猾无赖之徒混进来,觑着行人游乐不防时摸去些荷包钱袋、簪环首饰之类。也有更过分的,趁街市上拥挤,大人管顾不暇,便伺机诱拐孩童妇女去发卖。只为自己点滴私利,罔顾他人骨肉离散,最是可恨。
沈苑这会儿正跟在一队操持傀儡戏的舞者身后。那傀儡做得精巧,引来的观众甚多,一时教后面的人堵在路上几乎挪不动步子。他立在那里等了片刻,无意中便瞧见路边一个卖糕团的,正在跟人说话。
这情形本属寻常,然而那卖糕团的男人说话的神态却总让人觉得有些不像生意人,一面说着话一面眼神游移,频频往附近的暗巷里瞟,很有些鬼祟的味道。和他说话的人身量娇小,打扮像是个小少年的模样,这会儿刚巧偏着头对着这边的灯火,圆圆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细软的眉梢上似乎还残点黛色,怎么看都是谁家女眷,做了男装打扮方便出来玩耍的。元夕夜,都人都爱穿映衬月色的素白衣裳,她的衣着不算十分华丽,质料却一眼看得出来是极好的,还缘着细细的金边,明眼人一看便知是富贵人家的孩子,只是不晓得为何独一个人在此与人搭话,附近竟也没瞧见有家人仆从跟着。
这时候前面担着傀儡的杂耍人似乎表演了个什么特别精彩的花样,惹得周围的人群一阵轰然叫好,沈苑的注意力被引开了片刻,再回过头去看那女扮男装的小娘子时,也不知卖糕团的男人和她说了什么,便见她要跟着那男人往旁边人流稀疏的巷子里走进去。沈苑心里暗叫了一声不好,也来不及多想,几步挤过人群,径直上前一把拉住那位小娘子的手。
“妹妹,你怎么在这里?人这么多,走丢了可怎生是好?”
一面语气柔和地说,一面却不容分说地拉着她便往人多的地方走。他这一手来得突然,那两个人一下子都有些愣着没反应过来。沈苑微侧过身子遮住男人的视线,悄悄对那小娘子打了一个“嘘”的手势,小娘子仰头懵懵懂懂地看他一眼,也不晓得弄没弄清楚状况,配合倒是挺配合的,也没吭声。拐子回过神来的时候沈苑已经牵着她走出了好几步,待要喊已经喊不住,又不甘愿便就死心,仍吊在后面又跟了一小段,直到沈苑带着那位小娘子挤进热闹喧哗的人群中间,实在跟不住了方才肯罢休。
“……哥哥,我是认得你的吗?怎么我不记得了呀?”
之前一直并不吭声,乖乖牵了沈苑的手跟他走的小娘子这会儿突然开口,问的却是这句话。沈苑正偏头从眼角里觑那拐子还跟没跟着,闻言不禁失笑。
“你认不认得,自己记不住,怎么反倒来问我了?”
那小娘子却是一脸一本正经的认真模样。
“我们家里亲戚挺多的。也许我认识,但又忘记了,也是有的。”
眼见已经看不到方才那拐子的踪影,身边熙熙攘攘的人群又构成了天然的庇护,估摸着对方也不太可能再下手,沈苑便索性在路边停下脚步转过身来看着她。
小娘子身量约莫只到他下巴,需得稍稍仰着点头才能直视他,这会儿大大方方抬了头瞧他,瞳孔的颜色似乎要比寻常人稍浅淡一些,干净清澈得一眼能望得到底,神情一脉天真,全然是信赖的模样。也不知道谁家养出来这样一个玉雪一样干净的女孩子,竟然舍得没好好看牢。沈苑便半是提醒半是逗她地问了一句。
“你自己都不记得认不认识我,怎么就敢跟着我走。万一我是拐子呢?”
小娘子只略略露出些诧异的表情来,语气既不害怕也不惊慌,倒像是只提了个平常的疑问似的。
“咦?你是拐子吗?”
沈苑有些啼笑皆非,想了想还是只简短地答她。
“不,我不是。方才和你说话的那个才是呢。”
“诶?那个大哥哥是拐子吗?他说要拿澄沙团子给我呢。”
“那是哄你的。家里人没和你说过,莫和陌生人走到僻静的巷子里去么?”
她偏一偏头,露出点仔细回想的表情。
“好像是说过的……”
嘴上这么说着,脸上却不很当回事的样子,沈苑也不知该笑还是该叹气。
“年节里人多,小娘子这是与家人走散了么?”
她闻言这才哎呀一声,下意识回过头张望了一眼,可身后是挨挨挤挤的人潮,沈苑方才带着她又走出了相当一段距离,此刻回头自然是什么也瞧不见的。倒也没见她觉得慌,脸上的表情比起害怕更像只有些懊恼的样子,摸了摸头,不好意思地嘿嘿笑了一声。
“先前之义哥哥帮我去买兔子灯了,我跟大哥说想吃糖葫芦,大哥就让我和三哥哥还有小哥哥待在一起等他买回来。可是我头上戴的闹蛾儿叫人给碰掉了,三哥哥帮我去捡,小哥哥本来还在背后和我说话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走着走着就不见啦……”
她这一连串大哥哥小哥哥的说得人发晕,不过至少听得出来她不仅是与家里人一起出来看灯的,这家里的人口还着实不少。只是碰巧都走散了,这会儿恐怕家人亦都在焦急地找寻她吧。
“小娘子可还记得是在何处和家人失散的么?”
她想了一想。
“方才在卖饧糖的摊子那里,我还和小哥哥说话来着。后来,后来我瞧见旁边有一组走马灯,连起来是一整个故事,可好玩啦……”
她说着兴奋起来,已然忘了话头所在,比划着要跟沈苑描述那组灯有多么好看。沈苑方才也从那边经过,自然记得那组灯,可见她说得起劲,却也没忍心打断,只等她说到一段落才建议她折回先前与家人分散的地方等一等,兴许他们正在那附近找她也说不定。
御街自旧岁冬孟驾回就陆续有歌舞队列趁夜巡游,今晚是元夕的正日子,舞蹈和杂耍的团社更是各各拿出了看家本事。他们逆着人流慢慢往回走,正好跟行进中的舞队正面迎上,那小娘子禁不住瞧得入神,身量又小,几次都差点又埋进人群里走散了。沈苑喊了她几次没喊住,心下倒是有些明白她是怎么走丢的了,没奈何只好又伸手去牵她。她倒是一点也不抗拒,自觉把手递过去让他拉住,仿佛很是习惯的样子。
她的手又小又软,攥在手心里总觉得紧一分就要捏坏,可松一分却又怕拉不住。沈苑几乎便有些小心翼翼的意思,可看她一路走一路引颈顾盼的模样,又觉得不忍心太拘着她,只好略站得近了些,试图用肩膀替她挡开一些过分拥挤的人潮。
短短的一小段路,走回去的时候倒花了来时三五倍的时间,终于走到那组绘了神仙故事的走马灯跟前,见那小娘子还在频频回头张望鼓吹的舞队,沈苑不由得笑起来,摇了摇她的手提醒她。
“你瞧瞧,可是这里?”
她方才恋恋不舍似的回过头来,辨认了一下周围。
“嗯,大概就是在这里吧。刚才那位大哥哥就是在那边那盏鲤鱼灯边上找我说话的。”
顿了顿,似乎想起沈苑的话,却还是有些困惑的样子。
“那个大哥哥真的是拐子吗?”
沈苑一下子倒还真不知道该如何作答才好。
饧糖摊子边上堆着不少缠着大人买糖吃的孩子,他便也随手买了一份琥珀饧递过去。小娘子欢欢喜喜地接了,道谢的礼仪却周正,显然是好人家里教养过的。沈苑便含笑问她。
“说了这些时候倒还不曾问过,小娘子该如何称呼?”
她把琥珀饧含在嘴里,注意力却已经被不远处敲打铜铙的戏耍人吸引过去,像是漫不在意似地答他。
“嗯,我叫钰筝呀。”
沈苑怔了一怔,他本意只想问她的姓氏,并没想到她竟就这么大大方方把女孩儿家的闺名给抖了出来,正想说点什么,却见她踮起脚尖往街角的方向张望了一眼,然后雀跃地扬了扬手臂。
“大哥!我在这里。”
沈苑顺着她的视线看过去,正挤过人群快步走近来的青年看起来年纪要比她大上许多,瞧见她时明显松了口气,虽薄责了几句,语气里根本听不出什么严厉的意思,钰筝也就嘻嘻笑着答应了他两声,就从他袖子底下钻过去,跟他身后更年轻些的兄长们凑到一块儿去了。她长兄没奈何地叹口气,回身朝沈苑一揖,礼数端正地向他道谢,沈苑便微微笑着答礼。
“郎君客气了。”
他答道,抬眼去看他身后。围着钰筝的一对少年应该是双生子,从衣着到容貌几乎一模一样,她稍稍低了头让其中的一个把一只描金点朱的闹蛾儿插回她鬓边,身旁提着个精巧白兔灯笼的青年人和她说了句什么,惹得她要笑,又怕动静太大折了蛾子薄薄的翅膀,只能把嘴唇抿成一道弯弯的弧线,却连眼稍里都盛满笑意,仿佛颤一颤睫毛就要抖下来一点似的。
“我也是做兄长的,家里也有一个这般年岁的妹子。倘若她不慎和家人走散了,我自然也希望会有好心人看顾她的。”
街市上吵闹得很,人流拥挤得几乎站不住脚,并不是什么适合说话的地方。钰筝的长兄本还待多客套上几句,在人潮之中却也只能匆匆再致了谢,便护着弟妹们,半被人群携裹着往相反的方向离开。
一霎儿也不知道从哪里起了一阵风,吹得半空里纷纷扬扬就没停过的雪珠儿似乎更急了些似的,细细密密只往行人身上扑。
在彻底汇入人潮看不见之前,沈苑仍还瞧见了一次她的背影。娇娇小小的,牵着兄长的手心快活地说笑。有零星的雪点子落在她身上棉袄出锋的毛尖尖上,雪兔儿一般,分外可爱。
钰筝。
他突然忍不住想,也不知是哪两个字呢。
【注】
……我竟然忘了说一下开篇的灯品描述,以及一些零碎的元宵年节风俗,都来自于《武林旧事》中的记载。宋会玩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