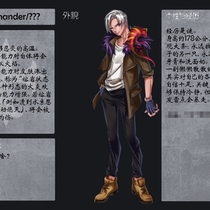


“我们什么时候回去?”
“两个小时以后。”
“你确定柯尔特会在那班船上等我?”
“我不知道,他是你的搭档。我只是这么被通知的。”
“嗯……”
“耐心点,这段路没什么事情可做,你可以休息一会儿。”
“可以吗?”
“可以,我不会超速的。”
1、
陶德转身挥了挥手,让箱型货车最外侧的两个人下来,把仍然沉睡着的“黑羊”拖到车厢的座位上,接着朝面前的人举起了枪。
那个人耸耸肩,轻轻吁了口气,微微眯起眼睛,以一种遗憾和近乎怜悯的眼神看着黑洞洞的枪口。
陶德皱起眉头,愠怒和受侮辱的感觉从胸膛里升腾起来,他的手指在扳机上轻轻跳动了一下,子弹像手电筒中射出的光线一样在空中划出一道轨迹,无声无息地射穿了那家伙的额头,血从小小的孔洞里渗出来,毫无破绽、高效、清洁、完美地夺去了敌人的性命。
——他站得这么近真是太愚蠢了,这家伙早该知道,就算是一公里之外我也能打碎他的脑袋……
一只手从一侧伸过来,把他的手臂压低,他看着那几根像坟墓中伸出来的枯骨一样的手指,猛然一惊,从想象中清醒过来。
“他不是敌人。”
雷蒙对他说。陶德悻悻地放低枪口,满怀敌意地瞪了一眼那个仍然在安静等待的“牧羊犬”。
“也不是朋友。”
“当然,不过‘组织’需要他,就像需要那个红发小子。”
“他给我们找了不少麻烦。”
“我希望他是一个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人。”
陶德抬头看着雷蒙的灰眼睛,接着马上扭过脸去,那眼神像剥开他的皮肤,把他的五脏六腑暴露在空气中一样令人毛骨悚然。还有那把大提琴,那低沉的呜咽简直比呼啸的幽灵还让人心烦意乱。
陶德认为,“物尽其用”一向是组织的主要宗旨,不管是“恩典”的所有者还是“第三种能力者”,只要能派上用场,“组织”不会吝惜财力和资源把他们吸收进来。虽然没有严格的约束,更谈不上什么忠诚心和信念,形形色色的人仍然能遵守这里潜藏的规则,并各司其职地聚合在一起,个中原因不外乎是他们不蠢,很快就能认识到强者支配弱者的铁则,在‘组织’里格外适合罢了。
雷蒙的职责是“评估”,他拥有一项很便利的能力,就是能够识别能力者所持有的恩典,以及它们的限制和强度。另外,“评估”的对象不仅包括“羊”,他甚至不用发动能力,只是观察、接触以及感受,就可以发现和测定“牧羊犬”。
——所以不得不服从这个装腔作势的混蛋。
陶德愤愤地推开雷蒙,向从“岛”上来的“牧羊犬”走去,他故意挡在那个人面前,然而对方完全无视了自己,只是垂下肩膀,无声无息,看似毫无敌意地从他身边走过去。操纵势能的“黑羊”姑且不论,来自“岛”上莫名其妙的“牧羊犬”,先是阻挠了他们的任务,接着把自己的同伴拱手奉上,为什么不当场杀了他,还要把他带去研究中心呢?
人质的消息是胆小怕事的约瑟夫带来的,他只想尽快和这件事撇清关系,回到自己舒服的小窝里去,吉赛尔那个蠢女人当然没什么主见,而最年长而富有经验的埃尔哈特又受到了不知从哪里来的威胁,甚至无法现身。这时雷蒙表示了意见,声称这家伙是不通过接触就可以稳定和控制“羊”的第三种能力者,作为研究对象非常有价值,况且他出示了弗罗恩地下机构的信息,已经展现了足够的诚意。他们应该带走这家伙,听听他有什么其他事情想说。
——这不对,该死,我们一定会走霉运的。
陶德打开车门,坐进驾驶舱,把牙齿咬得咯咯作响,猛地轰了一脚油门。
2、
车子在沿着高速公路延伸出去的小路上急速行驶,简单铺就的路面高低起伏,车身也随之忽上忽下。前面和后面都没有车辆,两侧只有黄色的枯草,视野中什么景致都没有,让人感到困乏无聊。
陶德用眼角余光打量着坐在车厢里的两个人。和他以前想象的不一样,“牧羊犬”和“黑羊”给人的印象和在岛外生活的普通人没什么不同,红发小子就像普普通通的同龄少年,而那个个子高一点的也不像是什么特别的角色,如果不是刚才那令人不快的眼神,几乎想象不到他和他们一样是能力者。
——还以为那个孤岛上的家伙们脑子都不正常呢。
陶德完全无法理解,正常人怎么能在那还不到几个街区大的地方过一辈子,他们一定会被洗脑,每天过着像钟表一样规律的集体生活,起床、晨祷、一起在四面透风的石头房子里吃寡淡的食物,一起发自内心地相信可笑的蠢话,毫无个性和隐私可言。
——而不像是这种……这种感觉。
陶德感到一阵焦躁。持有“恩典”的能力者更优秀、更强大,总有一天要摆脱桎梏,成为自由翱翔在天空中的群体,而限制和约束他们的人会像蛇蜕下来的皮一样被抛在身后,“组织”一直是这样告诉他们的。然而内心深处,他隐隐觉得,那只不过是给自己“生来不同”找的借口而已。
——他们……确切地说是“他”——现在醒着,手腕被铐在车厢座位后面的家伙。怎么能这么轻松地融入人群里,像常人一样活着,难道他意识不到,自从被检查出流着特殊的血液之后,就再也回不到原来的生活了吗?
——他在想什么,打算干什么,完全让人摸不着头脑,总之绝对不是想和他们站在一起。如果同为“牧羊犬”的老爷子在,大概能弄清楚吧。
“喂!”
吉赛尔突然尖叫起来。一辆卡车从对面驶来,陶德急忙向一侧猛打方向盘,同时放慢了车速,勉强从呼啸的铁皮车头前擦过。车身剧烈地摇晃了一下。
“能不能不要再分神了,我们这里能派上用场的人已经没剩几个了。”
雷蒙提高了声音。
——可恶,这群人明明只能依靠我的战斗能力,怎么还能这么理直气壮……
从后视镜里逐渐增大的影子瞬间中断了陶德的抱怨,他看见后面那辆黑色小轿车副驾驶座一侧的窗口伸出了黑色的细长物体,在阳光下面闪烁着反光。
3、
“我们真是在自找麻烦!能不能把这两个家伙扔下去!”
吉赛尔从副驾驶座挤过来,夺过方向盘,勉强控制住车子的方向。后面的人开枪了,子弹打在车厢后面的柏油路上,弹射出白色的烟尘。
陶德咂咂嘴,事情和预料的没什么两样,他从两个座位之间挤过去,开始捕捉对方的弹道轨迹,让高速移动的子弹向车身两侧飞去,接着他端起手枪,一次就击中了袭击者的手臂。
那个人哀嚎着缩回驾驶座,陶德又开始瞄准正低下身体,躲在方向盘后面勉强控制着车子的驾驶员。
——等等,那是……
车子仍在加速,而后面的车也紧咬不放,车窗外面传来气流的呼啸声,他看清了追上来车子里的几张面孔。
——那不是弗罗恩的人。
就在他意识到这一点时,车子剧烈地颠了一下,耳畔传来一声巨响,车窗前面有东西爆炸了,车玻璃完全被震碎,吉赛尔躲闪不及,车子几乎侧翻过去。
接着,几辆汽车挡住了道路,小货车拐了个急弯,沿着路肩一路颠簸,向一侧的草地轧过去。
黑色小轿车加速从右边贴上来,不断冲撞着货车,陶德看着满脸是血的吉赛尔,她伏在方向盘上毫无动静,车子仍然在向前,追逐他们的人已经近在咫尺,这些人似乎并不在意车上任何人是不是会受伤流血,只想把已经醒来,正被固定在座位上的红发“黑羊”带走。
奇怪的是,他们一直朝雷蒙射击,这家伙到底在干什么,究竟是谁更会惹麻烦。陶德诅咒着,试图一边躲避子弹一边举枪还击。
突然,他被一股力量推开,用手肘撑着地,恢复平衡的时候,发现岛上来的“牧羊犬”竟然已经挣脱了束缚。
“谢谢你们的顺风车,这算是小费。”
那个人的手肘像铡刀一样从肩膀上落下来,身体一侧传来一阵剧痛,脑袋简直要和身体分家,他仰面倒在地上,眼前金星四射。
合上眼睛的时候,他想起还有二十分钟车程的研究中心里,给小白鼠脱颈椎的景象。
3、
陶德恢复意识的时间比想象得来的早,岛上来的“牧羊犬”正在以车身为掩体和周围的人交火,远处有直升机正在接近,穿着武装防护服的人从四面八方跑来,有人正在给坐在车厢后面的“黑羊”解开束缚。
那是雷蒙,他楞了一下,随后明白了发生的事情。
弗罗恩的人不知从什么地方得到了线索,用“目标”作为诱饵接近了这里,他以为只有自己看破了这场骗局,却没想到如果不是与自己一起行动的同伴配合,事情根本不可能进行得这么顺利。来追他们的人其实是“组织”而不是“岛”,不是为了夺回俘虏,而是为了消灭叛徒,或者连他们也一起消灭,只带走他们马上要交出去的“黑羊”。
——原来我们才是被丢弃的垃圾,就像蛇褪去的皮……不,像被榨完汁水的柠檬一样,丢到地上任人践踏,只有他们认为“有用”的才有资格活下去。
——这和过去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某些人天生更重要,另外一些天生就该匍匐在地上呢?
他盯着那个看起来没什么教养的小子,朝他举起了枪。
如果发动恩典,子弹必然穿过座椅,打断他的脖子,击中车窗,打碎玻璃,再飞到窗外去。
——因为这是决定好的,这是‘我’决定好的事情。
4、
子弹顺着膛线翻滚着射出枪口,穿过空气,击中车窗,打碎玻璃,飞到窗外。
——离目标足足差了五十厘米。
陶德扭过脸,看着自己没有持枪的手臂,被一个和他自己一样衣衫整齐一丝不苟的男人牢牢按在地上。
男人稍微低着头,浅色的头发从前额两侧垂下,用平静无波,不带任何情绪的眼神盯着自己。
“没有时间了,只能对你们说一声对不起。我知道这种做法很糟,但这样是最快的。”
“你并不真心感到抱歉吧。”
“如果有别的途径,我会选其他办法,但假如再次遇到相同的情况,我还是会这么做。”
“我能明白。”
“喂……?!就这么走了吗?!”
“阿达西尔。”
“该死,我可是完全被蒙在鼓里啊!”
“阿达西尔。”
“不在这家伙脸上揍一拳的话……”
“阿达西尔。”
“不得不打断你们谈话,我该走了,希望你们一切顺利。”
“那么,也祝你好运。”
================================================
*全是NPC,都不好意思响应
*下回不乱搞了,突然深深体会到大片里空降地方基地的好处TUUUUUT
*前一篇接 http://elfartworld.com/works/87256/
*下一篇接 http://elfartworld.com/works/89020/
相关图片:
中华冠毛犬:http://pic.aigou.com/upload/shopping/2011/01/21/94931380.snap_m.jpg
阿富汗猎犬:http://news.sxxw.net/uploadfile/news/file/2007-8-22/20070822122330402.jpg
--------------------正文在下面♥-----------------
对于老六来说,莱伊比作中药的话,是三七。
不光是因为三七专治莱伊日常吐血和他三七分的头毛。
三七三七,三分客套,七分和善,十分虚伪。
这个人似乎已经虚伪到了就算直接把这个评语甩到他脸上,他也顶多就是笑着“哦”一声,连那面具壳子一样的笑容都不会出现一丝罅隙。
想到这儿,边刷着内部论坛边做着海报的勤劳小大夫不禁有点好奇,以这家伙的冰块儿一样的心肠,也不知道到底什么话才能让他觉得愤怒。
从第一次见到莱伊算起,到现在也有快两个多月快三个月了。说实话,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老六还是小小地惊艳了一把的。莱伊的皮相有种中性的清丽,偏偏还生的肩平背直腿挺长,长了副很爷们的骨架子。身高虽然差不了太多,但自己那有点儿溜的肩膀和上下一边长的小短腿,往他旁边一站顿时显得气场弱了一头。
那时老六刚回岛没多久,正被岛上炒鸡不便利不人性化的公共通信系统搞得焦头烂额。或许是岛上人本就不多,有权限随时接触外部网络的人更是两只手都数得过来。教廷里竟然连一部富余的岛内外两用智能机都找不着。申请了定制机以后被通知要十个工作日。按里洛尼亚跟宗主国意大利如出一辙的低下工作效率,说是10天,少说也得一个半月才能兑现,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
开业在即,老六急于联络药材进口事项,只能跑到离小院不远的这个市里图书馆机房上网。
弗罗恩的上机手续远不似外界的网吧或者资料室那么方便,每次都得去图书馆前台找管理员登记,预约使用时间,然后给随身的ID卡充权限,才能进前台后面那间一共没有几台dell老台机的小机房。权限都是单次的,出来就算上个厕所都要再登记一次,上个网搞得跟坐牢一样。
如果机房是牢房的话,莱伊大概就是门口的狱卒吧。或者看门犬更贴切一些?老六暗挫挫地想着犬化的莱伊,觉得这只笑脸面瘫的阿富汗还真是一点儿威慑力也没有。
拿狗来比自己的话,会是啥呢?苏牧?突然很在意的六子随手点开了岛内的内部聊天app,把签名改成了“大家说我比较像什么狗?”
几分钟以后一刷,底下多了好几条回复。
huck/ 中华田园犬 (……)
snug/ 古牧吧。(我有那么胖?)
赫西亚/……灵缇?(赫西亚你对我真好,这腿比阿富汗还长呢)
大主教/假装自己是中华田园犬的金毛。
老六怔了下,觉得卧槽不愧是主教,完全无法反驳,还有点儿小骄傲呢。金毛好歹也是最受欢迎犬种,还有种深藏不露的感觉嘿嘿。
正准备赞颂一下主教机智,这时候莱安发了一条:
/六六,我觉得你像中华冠毛犬诶!/
看着这个听着陌生的名字,他一脸问号地打开了google搜索。看着蹦出来那张照片先是一愣,然后趴在桌子上生生笑了五分钟,然后红着脸毅然决然地删掉了刚才那条状态。
你才是中华冠毛犬,你们还是松狮二哈牛头梗呢哼!已经完全忘了来机房目的的六六森森地怨念起门口那个祸首阿富汗起来。(莱伊在门口咳嗽了一阵,又默默吐了一口血。)
要说这么好看还温柔的人,就算体弱多病了点也应该是招人疼而不是讨厌才对。事实上莱伊的人缘也确实很好,不光有个蝴蝶犬一样头发加了特效,看起来飘乎乎的臭小子老来找他。貌似还有个死忠小粉丝常驻图书馆盯梢,每次老六去找莱伊“开房”的时候都能感觉到后脖梗子上刺刺的目光,一回头时不时还能看到书架子缝隙间露出充满怨念的粉色呆毛。
可莱伊对这些关心他的人的态度总是那么不远不近的。
有一回亚乌和莱安在讨论着一本小说,亚乌听了莱安的介绍很想看,莱安却忘了书的名字,俩小孩在书架边上走了一遍又一遍也没找到。那时候老六刚走到机房门口准备回家。无意间看到了莱伊悄悄地把自己手上那本看了一半的书阖了起来,摆在身边还书车上最显眼的位置。俩少年寻找无果,借了另外的书来了前台,一眼就看到了莱伊刚摆过去的那本。
“啊啊啊就是这个!我说怎么找不到,原来有人刚借过。”莱安指着书大声说到,然后被亚乌打了下头,“嘘!小声点。”少年一脸尴尬地左右看了看。
等少年们心满意足地借了“正巧发现”的小说开开心心地出了门。老六绕到前台,把ID卡甩到柜台里,一手撑着腮帮子看着莱伊登记。
“刚才我看到你放书了,直接叫他们过来拿不就好了。他俩不是跟你挺熟的吗。”
莱伊头都没抬,确认了下桌上电子钟的数字,抄录在一张几乎只有老六名字的表格上。
“我不知道他们要借,刚巧看完了而已。”说着有意无意地抬手掩住了面前刚刚从书中拿下来,刚刚写上了书名和页码的书签。
这人也太别扭了,老六想不通。
有病吧?
没过多久,他发现莱伊真的很‘有病’还病得不轻。
记得还是八月中旬,流火的天气。图书馆里虽然有空调,但不知怎的机房和前台这边的那台空调一直有问题。热得老六脱了短褂,只穿着个跨栏小背心,还把老糊后背的烦人发丝拿铅笔绕着在脑后歪歪扭扭地搞了个道士髻。
之前联系的中国那边的代理商老王头是师父的朋友,一直很好说话。最近他腰有点儿问题,住了医院,他二儿子王二暂时接手生意。这小年轻不知道情况,还有点轴,什么事都要反复说三遍才能明白,急的老六一脑门子汗。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越是着急的时候,越有人添堵。
正跟那二货解释第三遍关于那批三七的产地不对,不是汶山,是云南的文山。最后一个“山”字还没敲完,电脑“咔吧”一下热重启了,还卡在了开机画面一动不动。老六等了两分钟,决定还是召唤门口的莱伊进来帮忙看看。
大热的天,常年反着冷光的美青年却跟完全没感觉到一样,还穿着那身长衣长裤,脖子上裹了个大围脖,看得老六都觉得又热了几分。
“怎么了?”
“电脑自动重启完卡住了,关机没反应,再帮我开一台吧。”
“我看看。”莱伊走过去,站在六子后面,左手扶着椅子背,伸出右手跨过他耳畔,按上了桌上主机的关机键。本以为有新电脑用,没有让开地儿的老六被这突然拉近的距离吓了一跳。一阵没来由的紧张,弄得他头都不敢回。只是偷偷瞄着脸旁几缕闪着金属光泽的浅色长发,发梢还碰到了他光着的肩膀,扫得人心里直痒痒。
这几秒钟长得吓人。
老六感觉得他几个小时都没喘气儿。
“bi”的一声,屏幕一黑又重新亮起。看着莱伊把手伸向键盘,他往后一靠本想给腾个地方,忽略了两人之间的距离已经是极尽了,插着根筷子的脑袋一下子埋进了莱伊怀里。
吓了跳的老六赶忙回头想道歉,就见莱伊一口鲜血喷了他一头一脸。
六子整个人吓傻了,满脑子都是我勒个大槽这一头是要撞死人了我投好硬?赶紧抢救争取戴罪立功少判两年欸我救命金针没带身上怎么办。
还没等他的脑子过完这个超长的念头,‘重伤’的受害者却抢先开了口。
“抱歉有点没忍住……老毛病了。”莱伊低头看看满手的鲜血,脸色苍白,眼圈发黑,气息颤抖地说着。
这景象让老六突然觉得五脏六腑都随着他的气息一揪一揪的,拧着疼。
强行说服自己是医者本能作祟,病人在前应该尽职尽责,于是他一把抓住了莱伊还顺着往下淌血的手腕。
莱伊愣了下。
看到他吐血什么反应的人都有,皱眉头躲开的家人,面无表情地递纸巾的医生护士们,一下子哭出来的木星,他们的举动都很容易理解。这样突然拉住手是几个意思,莱伊被这个还算不上熟人的雀斑青年的举动和一脸认真纠结的表情给弄糊涂了。
“气血两虚,脾胃不和,心肺衰弱,肝胆气滞,肾有阴虚。除了肠子好像还没什么大问题,你这五脏六腑倒是坏得挺整齐。” 这个人能活到现在,真是不容易。这内脏明显有缺失,应该动过不少次手术,身体虚寒入骨,怪不得大热的天还穿这么多。
听着这番话,莱伊也隐约想起来对方似乎是刚从中国回来的医生。拉手原来是东方医术的“把脉诊断”?虽然青年说的话有些单词不大理解。但大体上的病情竟是说的分毫不差。他对之前只在书本上见过的中医顿时多了几分崇敬。
老六说完了诊断,没舍得放开那手感极佳的腕子。他偏头看了下还抓在自己手里那只白皙的长手,心想这人美手就是好看。就是都沾上了血,看着真心疼。突然灵机一动,一把将沾了血的小背心脱了下来,给自己胡乱抹了把脸,然后朝莱伊一递。
“凑合先擦一下吧,一会儿去洗手。”
看莱伊没有接过去的架势,老六心想糟糕自己真是傻了,那背心又是汗又是血的,还刚抹了把脸。自己糙人当惯了不觉得,人家看上去那么干净怎么用的下手。
莱伊这时其实没看到他伸过来的手。他是被青年背上身上扭曲着的几道巨大伤疤引走了注意力。不同于自己身上数次手术留下的蜈蚣一样长长的缝合痕迹。这个人的伤疤看起来更加狰狞,似乎是受过严重的外伤。有些伤口很容易想象到当时有多深可见骨,血肉模糊。
这个人,能活着也是不容易。
莱伊不着痕迹地收回眼神,拿起那件正要往回收的小背心。习惯性地温柔一笑,抬手拿背心擦了下嘴角的血迹。
“谢谢,抱歉弄脏了你的衣服。”
“没、没事。” 尴尬地他脸有点红。
刚想告诉他背心有点臭,擦手就好了。
啊,已经晚了o/////o。
那次之后,老六再去图书馆机房联系业务,总会拿上些配好的药丸。那天跟王老二买的一整批上好的云南三七几乎都用在了这些药丸里。
终于做完了海报的药房准老板撇了撇嘴,想起了前几天的争执。
哼,要知道他其实是这么别扭的人,当初就不该对他那么好。
心情有些莫名烦躁的六六不想那么快登记下机,主要是不想见登记的人。他顺手点开了桌面上存的那张长毛阿富汗的照片,开始拿鼠标给狗子画蓝围巾。
这时坐在前台的莱伊正默默看着电脑监控画面。最大的那个窗口中,扎着辫子的青年正一边涂着一只带围巾穿衬衫风衣的狗。
莱伊无奈地笑了下。
看来上次话说得太直接,他确实是生气了。
也罢,等他的药房正式开起来,应该也不会有那么多时间总是过来这里,对自己应该也就淡了吧。像我这种不知道还有多少日子的活死人,何必还要拖累人家。
莱伊自嘲地笑笑,关上电脑走到窗前。有点寂寞地看着对面那间已经挂上了绿色灯牌的小房子。
三七,主产自云南。《本草纲目》中称其可止血散血,亦主吐血衄血。曾是当年救下老六这条小命的主要功臣。给莱伊配着药,他总是忍不住回味起卧床不起的那段时光中每日服用的汤药。
散发着淡淡药香的苦涩味道。
只是等过这苦,回味时总会有一丝甜。




写个引子。
正常和异常的边界线一直是模糊的,或者说从未存在过。
符合人们认知的被称为正常,而跳出那个认知框架的被称为异常。但人类的认知实际上则小的可怜,如同井底之蛙,自以为是地框出一个边界,然后出版成书,口耳相传,然后对着更多的青蛙说道:“看,我们的世界就是这样的!”沾沾自喜却浑然不觉。
但这世界真的有边界吗。
以自己为中心,半径3公里以内是自己的活动范围,如果出了这里,那就可以称之为“今天做了件不一样的事情”,并且值得大书特书。但对于半径5公里,10公里,甚至100公里的人,这却连零头都算不上。
每个人都正常着,或者异常着。即便发生了改变,这份正常与异常的界限也在在与不在之间徘徊。如同在这个岛上,所有的“不正常者”都是这岛上再正常不过的一部分。
如果借此麻痹自己,忘掉所有不快的曾经,大概也就不是件困难的事了。
Frog and Frame
店里来了位不速之客。
之所以这么称呼,是因为Frey觉得自己认得他,但是却想不起对方的名字了。然而对方却明显认出了他,进门的时候拿着张纸条像是需要问路,本来Frey还想主动友好地凑上去招呼一下,刚露了个笑,对方对自己就马上露出了“你果然在这里”的表情。然后就拍着他的肩膀说真的是好久不见,然后像是常客一样熟络地往里走。Frey搜肠刮肚地思考了很久,觉得对方的语气和态度似乎有点熟悉,只是长相却和记忆里的截然不同。
“您是……Enzo?”
“对我就不要用敬语啦——怎么这么冷淡,连我都认不出了吗?”
“不,只是你变得似乎有点多一时没能认出来……要喝点什么?还是像以前一样,什么都不加的纯苦艾酒吗?”嘴上虽然还是询问着,手已经熟门熟路地申向了店里高级苦艾酒的瓶子。
“不,给我杯水就好,我戒酒了。”
“哦?你以前可是每晚上都到我店不喝得说不出话可是不回去的。”
“那是为了给你捧场,这都看不出来?”
Frey听到这打趣的话,笑了一下,但还是放下了一边的酒瓶,给他接了杯水,顺手还拿过一旁的暖壶加了点热水放在他面前。“胃不好就别喝凉的了。”
“……你居然记得。”
“当年直接喝到胃出血倒在我店里,我差点没吓死,怎么会不记得。”Frey点了根烟,上半身支在吧台的台子上,把刘海撩到了一边露出眼睛,支着脸看着Enzo——其实他并不知道对方现在到底是不是叫这个名字,但对方并没反驳他也就没再多问。“最近如何?老婆和女儿还好吗?”
“……她们都走了。”
Frey还没来得及道歉,就看到友人抬起了脸,对他有点无奈地笑着解释了下,“不是你想的那个意思,我老婆跟我离婚了,带着女儿走了,也没办法,毕竟我跟她感情也没那么深……所以只剩我一个人了。”
Enzo是和Frey在岛外认识的。
更准确一点说,是和当时还只是个酒吧最普通的小酒保的19岁的Frey认识的。起因很简单,付不起酒钱的穷酸客人,只点着最便宜的什么都不加的苦艾酒,一喝就是一个晚上,事后付不付得出酒钱都不知道。比起一旁指望着能来这里邂逅艳遇的暴发商户家的小姐和出来找乐子小费丰厚的富太太,这样的客人自然是没有人愿意来招待的,也就自然而然地被指派到了彼时还只是个新人酒保的Frey头上。然后就是几乎说得上有点俗气的“对谁都很好的年轻人遇见事业爱情双挫折的失意人通过亲切地交谈挽回了潜在的自杀者”这种台本——虽然对方并没有考虑过自杀这种事情,不过这么一来二去交谈的多了,于是就成了熟人。
在被酒馆发现自己是超能力者逃离后,辗转到了其它的地方,明明是仓皇离开的跟谁都没能来得及说,结果却在新落脚的地方,有天再次偶然碰见了他。对方应当听过传闻,也应该知道他是个异常者,只是对他始终一般无异,甚至连一句好奇的问话都没有,自顾自地跟他谈说自己又看上了哪个姑娘不知道能不能追得到,他的情敌是个有点啤酒肚的秃头男人诸如此类的话题。这份好意对那时的Frey弥足珍贵,他领了,也就试着开始与他真心相交起来。
——这是无关情欲金钱与地位,纯粹地不含任何杂质的朋友。
“你怎么会到这岛上来的?我没跟你联系过吧。”
“我要是说我打听到的,你会不会爱上我?”
Frey“嗤”地笑出声来,对着他极为缓慢地吐了口烟,白色的烟雾把两人相隔开来,一时彼此相看对方的面容都有些模糊。太阳不知不觉已经西沉,酒馆只开了一盏灯,夜色汹涌地涌入酒馆内,两个人的身形都被暗色牢牢地困在中间。
“要是Enzo我还真信,现在你是谁?”
“我的朋友,面对你,我永远只是Enzo。”
无言地沉默伴随着氤氲开来的烟草气息爬满酒馆内的每个角落,若不是突兀的一声开关声响,随之而来的光亮瞬间驱散了深黝的气氛,由对话引发的不安或许还会扩大。不过,现下因为这个意外并不需要再担心这个问题。
“我说你怎么不开灯……怎么有客人还黑着?”
Frey对着出现在微妙时机的同居人叹了口气,盯住Enzo的上半身收了回来。又对着Elvis招了招手,“这是我以前在岛外的朋友,Enzo。Enzo这是跟我现在住一起的……恋人,Elvis。”
注意到了那个停顿,Elvis愣了一下才对着恋人的友人伸出了手,虚虚地握了一下,很快就分开了。
“我是来这个岛上办事的。”
暂且名为Enzo的人这么说道,随后又补充说他现在给政府工作,只是作为政府派出的人员来视察一下这个岛,为了迎接15日的教皇的大驾光临。也不仅仅只有他一个人,不过他是之前看到政府的收容名单时偶然发现了他的名字,于是特意要了地址来看看他。
“毕竟你那时突然就消失了,很多人都很担心你啊,原来是被带到了这里。”
“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我现在也能有家自己的店了。”
“……你这样就满足了吗?”
Enzo找Frey要了烟,斜斜地叼在嘴里,却没点着,一味直直地看着Frey。Enzo的眼睛是绿色的,并非是如同宝石一般的绿色,更像是被爬满青苔的湖边石子。绵绵密密地包匝着核心,让人无法看穿,只能依靠他嘴里吐出的话语来揣度他真实的心绪。Frey曾经是读的懂的,然而现下他虽然读了出来,但无法明白对方眼里蕴藏的那份感情从何而来。
——一种近乎悲悯的眼神。
“你们,是超能力者,是高于我们这些普通人类的存在,你不应该就在这里度过你的一生。你跟我说过,你有愿望吧?你曾经想当个医生,可却被来自外界的指责和歧视流落至那种地方,如今也只是偏安一隅开个没什么人的酒馆,这——不是你想要的吧?”
“Enzo。”
Frey打断了他,嘴里的烟不知道何时已经被掐灭在了烟灰缸里,浅浅地笑了一下。如果此刻坐在一旁的Elvis能够看清,那种笑容他再熟悉不过。Frey无论何种感情几乎都会用笑来表达,或者该形容为用笑去掩饰。如果不是与他足够了解,几乎无法判断那中间细微的差别。只是现下Frey逆着光,刘海垂下来,刚好挡住他的侧脸,无从分辨。
“我作为Frey的这个个体,愿望从都至尾只有一个。虽然还没能被实现,但是我现下的生活却有可以将之实现的办法,所以我真的很满足。我知道你那算是在担心我,不过……我并不喜欢那些话,不要让我后悔对你讲过……曾经另一个人的故事。”
随着语句的结束,Frey稍稍抬起了头。
——看清楚了。
——那是难过的笑。
“……好吧。”对着友人几乎算的上是指责的语句,Enzo放松了身子,嘴里的烟没点着就被他丢进了吧台上的烟灰缸里。Frey突然有点记不清对方到底抽不抽烟了,之前给他烟,也只是从他衣服上缠着的烟草气息来判断的。一直自认为不错的记忆突然出现了一小块空白,某种说不出的违和感从心底缓缓地蔓延开来。
“没关系,你们不会这样下去太久的,一切都会改变的。”
“与其改变,不如一直这样下去,毕竟我无法判断改变会带来的后果。”
“……你这只是胆小而已。”
“或许吧,我是个恋旧的人。”
Frey唇边有着轻巧的笑意,一边若无其事地回答着他的话,一边目送着Enzo重新戴上帽子,穿上了放在一旁的制服外套。对方绿色眼睛里悲悯始终盛在眼睛里,但若是剥下那一层,似乎还有某种更深邃的东西——只是他却读不出来了。仅仅过了不过五年,Enzo无论是外貌还是内在,都变得他无从相认。不过仅凭相见就涌出的那份亲切感,无论如何都不会欺骗自己。
然而他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了,哪怕灵魂依旧相同,也不再是同一人。
“还是谢谢你,谢谢你一直记挂我,以及……再见。”
Enzo对他点了点头,说,我下次再来看你。
但Frey觉得,这位已经彻底陌生的友人,他应该不会再见了。
“你的愿望是什么?”
Enzo走后,方才彻底沦为听众的Elvis才终于开口。问题问的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虽然他并没有作答的意愿。不过对于Elvis这种过分了解自己的人,即使他扯开话题顾左右而言他,大概也会被很快直截了当地回到主题上来。
“我不想说,可以吗?”Frey拍了下恋人的脸,表明希望他能就此作罢。
“可我想知道。”
在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对彼此的界限一直小心翼翼。但他们被定下“恋人”这份关系后,他才意识到Elvis简直直率的可怕。这份直率一直是Frey没有的,所以大概也就一直向往。有欲求的东西无论如何都想得到,想要问的问题即使不回答也会一直问个没完。Elvis对于他“不想说”这句话一直有个误解——其实也不算是是误解,自己心底里也是这么希望的说不定。“不想说”仅仅代表在当下他不想说,但并不是“不能说”这种毫无转圜余地的回复。于是就会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再度挑起这个话题,直到他得到答案为止。对于这种无比率直的心机,即使擅长曲意迎合的Frey也实在无从下手,最终落败的大多还是自己。
“……即便说了,也不会改变任何事情的。”
“那就是说了也没关系的意思吧?”
对于这种带着对方主观意识的解读,Frey不置可否。不过看来若是拿不到答案,他应该不会就此作罢。考虑到最终的结果,他叹了口气,放弃了。刚准备开口的时候,却听到对方一句若有所思的话。
“你是只想这么普通地活下去吗?”
Frey笑了笑,摇了摇头。“一字之差。”
“我啊,只是想像普通人那样活着而已。”
他们看到报纸上大大的“刺杀教皇”的头条新闻,已经是一周后的事情了。虽然对于嫌犯的照片经过了处理,几乎无法辨认。但,他却能辨识出那份如同青苔一般的绿色。
真的,再也看不到了。
他笑了下,把报纸随手一揉,丢进了吧台下面的垃圾桶里,好像一切都没发生过一样。
笑容很浅,很浅,漫不经心地挂在脸上,似乎一撞即碎。
——即使青蛙爬到井边,想低头告诉同伴,也只会落得摔死的下场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