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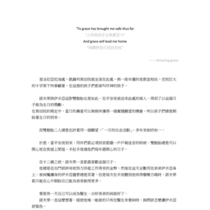
C1 牧羊犬(下)
门萨叩了三次。
他本该紧张,但不知怎的,心情格外平静。走廊里晌午过后的影子从天花板到壁角,密密实实盖住他,窗子投在墙上的阴影,酷似一架巨大十字。门萨漫不经心看了一会儿日影挪移,心里默数,直到门“嘭”地打开,一团稻草伸了出来。
“你来的好早。”“稻草”咕哝着,吸了吸鼻子。门萨把手里的纸袋递给他,他一把抓过来打开袋子嗅了嗅:“好香。”
“红丝绒杯糕和脱脂拿铁。”门萨告诉他。对方回过头,投来一个奇怪的眼神:“红丝绒杯糕?说真的?那不是女孩子吃的东西吗?”
他看上去并没有不高兴的样子,门萨只得把对这人实际上二十四小时离不开甜食的控诉吞下肚子,他无法想象,一个将芝士薯片和水果硬棒糖当饭吃的人怎么能有那样一口好牙齿。他随着罗可走进屋内那堆、被称为“垃圾”都算作过誉了的玩意儿里面,看着对方毫不在意地将袋子往床上一扔、抓着后背走去卫生间,一时竟有些无所适从。毕竟,承认这个事实吧,他不想坐到这里头任何一样东西上头。
“工作找得怎么样了?”卫生间里传来问话,门萨愣了一下,说:“东区的小牧场。我在那里帮工。”
“牧场?哦,哦,我知道那地方。很不错。”罗可大概正在刷牙,声音上像糊了一层生奶油般黏腻,“试着给自己找些事做,这很好,希望这种热情能保持下去。”
最后几个字说得又小又模糊,门萨只捕捉片缕,心想着还是别问的好。他环视四下,忍不住从地上捡起一个罐头瓶,又把桌边摇摇欲坠的几样包装纸收了起来。卫生间里的水响还在继续,罗可一时应该不会出来。意识到这一点以后,他又接着收拾起脚边地板上的一团狼藉,小心翼翼,不发出声响。当他就要动用扫帚的时候,罗可步出了卫生间。
门萨立刻停下动作,站得像童子军那么笔直。罗可奇怪地看了他一眼,似乎没发现四周有什么不对劲,来到桌边开始享用门萨带来的早餐。
“你来这里之前,在哪里住着?”
门萨把手里的汽水罐藏到身后:“蒙塔格。小地方,你大概没听说过。”
“是没有,不过那不奇怪,大部分地方我都没听说过。”罗可胡乱挥了挥手里的糕点,“我知道秘鲁,不过只在书上见过。你去过秘鲁吗?”
“没有。但我去过玻利维亚,和秘鲁离的很近,我想。”
“是吗?”罗可听上去有了些兴趣,但仍没从食物上抬头,“讲给我听听吧。”
门萨点点头,然而一时张口结舌,不知从何说起,他向来不擅长这种事情。“我……那是很久之前了,那里有很高的山崖,页岩,我远远见过那里的火山口。”他不动声色地将一叠泡面盒扫进垃圾袋里,“离开之前我去了一片盐沼,那里是……我无法形容。”
他回想起站在镜面般的湖水中时,天空倒映犹如脚踩在九霄云端,一切澄净无比,极度的蓝与皓白却狂浪般扑面而来,他几乎分不清人间与彼岸:“也许亲眼看看比听我说要更好。”
“如果我可以的话,就不会坐在这里啦。”罗可说。门萨这才想起羔羊皆禁止走出岛外的规定,便往他那里瞥了一眼:“我不是有意……”
“我知道。”
罗可喝了口咖啡,苦得皱起脸来:“这个真的是拿铁吗?”门萨看着他往杯子里大勺舀糖的动作,默默记下他偏好的糖量:“这么说你从没出过岛?”
“最远是朝西的海岸吧,我小时候常躲到那里捡贝壳玩。我还给自己做过一串风铃呢。”
“听起来挺有意思的。”
“有意思极了,有一次我被冲上岸的水母蛰了脚趾,肿起来至少三寸高!老天,我坐在那里哭了好久,直到黄昏才有人发现我,”罗可夸张的比了比自己的左脚,“现在那里还有疤呢。”
“他们让你一个人在外面玩?”
“嗯……可以说是我自愿的,毕竟我这么聪明又有趣,而那些小鬼都太蠢啦。”
饶是门萨也忍不住笑出了声:“这一点我深有体会。”
罗可大笑起来:“承认吧,你被我迷住咯。”
他又低头去咬蛋糕上的糖霜,从门萨的视角,能清晰看见他轮廓分明的侧颜。之前那被龙卷风袭击过似的金发此刻平滑的垂在他肩膀上。门萨咳嗽一声以制止自己胡思乱想,悄悄将一个空罐头捏扁,试图将思想集中在垃圾分类上面。
“好了,歇歇吧,”罗可突然从椅子上转过身来,门萨手里的瓶子顿时掉到地上,发出清脆一声响,“你真以为我没注意到你在做什么吗?过来,好好先生,跟我一起吃点东西。”
“我不饿。”
“我不管。”
门萨有些窘迫地站在原地,罗可看着他,一脸促狭笑意:“来啊,吃过早饭,我会和你一起收拾,我保证——毕竟这是我的房间。”
他伸出手来。门萨向他走了两步,突然意识到什么,怀疑地问:“你真的会和我一起收拾?”
“好吧,我不会,”罗可笑得更加灿烂,探过身来抓住他的手腕,将他拉向自己,“但我一定会好好监督你把工作完成。”
这人真是十足混蛋,门萨心想。
“我也知道你现在在想什么,亲爱的。”罗可说。
啊,该死。
对门萨来说,罗可仍是个未知数,不定性的谜。他们的每日会面活动在第四天不得不暂告段落,至少没之前那么频繁,原因是门萨的工作日益繁重,牧场乳牛的产奶期到来,他每天不得不负责运送十吨生牛奶到工厂进行处理。
罗可对此似乎没有什么异议,事实上,门萨没见他对什么东西有过异议,最多就是午饭的烤猪肉分量不够或者家中巧克力告罄一类的事情。门萨也不知道罗可平常都做些什么,他似乎没有特定的工作,游离在众人之外。岛上人不一定要工作以度日,但大多数人会选择找个活计来维持自己的忙碌,或者说,来真切感受自己仍然活在人世。他们与外界相隔太久太远,门萨直到来这里一年后也仍然怀念家乡郊外的广袤平原上太阳照射干草发出的香气,他也喜爱主城中蜿蜒曲折、似乎没有尽头的古老巷道,和夜晚入睡前家畜在围栏里悠长的叫声。
来到这里以后,那些就都是过去了。上一章节。门萨双眼所见的人们看上去都和善而快乐,满足于当下的一切,羊和犬都是些友好的人,教会则将一切管理得井井有条。当然,波动偶尔有之,比如几十天前,一次席卷全岛的“噩梦”。门萨不愿意多回忆那件事,尽管是它让自己遇到了罗可。
他后来向相熟的神父询问起那次事件,得到的答复无非模棱两可的羔羊暴走一类,他也并不特别在意。上午的礼拜堂里不过零星几人,彩绘玻璃闪烁着玫瑰色的光晕,门萨做了短暂祝祷,便匆匆离去。
罗可告诉他,最好的办法是不听,也不说。
“把你的狗鼻子放到别处去嗅吧。”他笑嘻嘻地说道。门萨无奈地叹了口气。他们两个现在越来越熟识,门萨也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给自己找了多大的麻烦。罗可有时候看上去明白的挺多,有时候又像个天真烂漫的小孩儿一样。
“你知道‘贡多拉’是什么东西吗?”
门萨停下手上翻书页的动作,“大概是威尼斯用作交通的一种小舟。”他不太确定地说道。对方点了点头,重又把目光凝着在面前的杂志上。
他看上去似乎充满着渴念,只是疏于表达。门萨收回了视线,然后就听罗可说:“我以为是一种烤饼还是什么的呢。”
哦,忘了他之前说过的那些。
羔羊不同于牧羊犬,有着另一套生活体系,他们大多带有独特的气质,令人能从人群中一眼分辨出来。主教说,这大抵归功于“器”的作用。
牧羊犬们大部分在岛外生活过或多或少的几年,直到通过验血才来到岛上。而绝大多数的羔羊出生于这座隔绝人世的海岛,从未碰触外界。门萨好奇罗可那种对什么都不太在意的性格是否就此养成,他知道自己不该有这种想法,罗可或许不需要自己多管闲事。他似乎把自己当做什么可爱的小动物来对待,也极少直呼他的名字。
一次门萨在沙发上玩填字游戏,抬头正看见罗可服药。他拿着一管猩红色的药剂,启开瓶盖,就那么直接灌进嘴里。有一点药水溢出了嘴角,顺着他上下滑动的喉结流下来。罗可把那些药用手背抹去,表情隐隐有种难耐的痛苦之意。
门萨看他喝药,想,那东西味道一定很坏。
这时罗可回过头看了他一眼,他才想起这家伙是能读心的。但罗可没说什么,只说,劳驾给我倒杯水来,门萨。
他鲜少这么叫他,门萨愣了愣,一时间竟不希望他能看透自己心中所思。有时他能看出这之下是怎样一种精心铸造的伪装,坦白来讲,以伦常和法规而束缚的令人不安的假象。罗可活在这套完美的体制中,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并不想就这么活着。
他去给罗可倒了水,对方从他手中接过水杯时,一如既往没有道谢。但门萨抓住他的手腕,说:“也许我们能成为搭档。”
罗可脸上的表情让他意识到自己是多么一时冲动,以及自己的话听上去有多么愚蠢。圣母啊,他们才认识不出两星期,他为自己的冒失懊悔不已。但罗可看着他,好一会儿,他的目光变得柔和起来。那比暮晚的天空的颜色还要瑰丽。
他将空了的水杯又塞进门萨手里:“为什么不呢?”
TBC


《龙与门门子》
门罗丨西幻PARO丨逗比向
罗可·没有姓是一条龙。
之所以要在“罗可”后面加一个“·”再加一个“没有姓”是因为罗可真的没有姓,但他是龙,名字后面假装有姓会显得他很帅气。
罗可的种族在拿大顶山脉盘踞了快有两千万年以上,罗可自己也已经有九千岁了。他在族群中不是最老的也不是最小的,不是最出名的也不是最没名气的,总之,就是不上不下的这么一个地位。
当然罗可有三个特点,这让他在族群中还有那么一点知名度。
第一个是他是一条金龙。
金龙很稀少。大部分龙的鳞甲都是黑色,好一点儿的有铁红和石灰色,再就是蓝龙。而金龙,两百万年出不了一条。
罗可的爹妈把这归咎于罗可妈妈怀罗可时吞了太多金所致,他们说她吞下的金块在高热的胃中熔化,最终为尚在腹中的罗可镀上一层璀璨的金甲。
这个说法罗曼蒂克极了。罗可喜欢。
当然这个颜色太特殊还是有一点不方便。比如罗可一下山偷羊吃,村里人认出来金龙金龙!漫山遍野地喊,最后传到族长耳朵里,一下子就听出来是罗可,把罗可的爹妈叫出来点名批评,扣一个月龙晶石。回去罗可就要挨打。
再或者隔壁破落户荒漠里的凤凰来屠山的时候,事情就比较麻烦。别的小龙“枯嚓”一下钻煤堆里了要不“刺棱”一下躲石头缝里,唯独罗可一身土豪金快闪出八星八箭了,目标贼大,老鸟儿们有什么大招都先往他身上放。还是挨打。
罗可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这么练出来的。
能吃。
天天挨打,龙的体型又天生巨大,没有足够能量根本扛不住。于是罗可从生下来以后,龙生主要目标就是吃。
吃牛羊吃鸡鸭,吃土吃房子,天上游的水里飞的,基本都让他吃了个遍,所过之处寸草不生。族里的龙都不敢轻易放他出山,造成的破坏能比那群老凤凰还严重。
但是,罗可从不吃人。
他喜欢人,觉得他们很有趣。看上去小小一只,一指头就能干倒,却可以建造房屋,铺设大路,修筑堤坝。
而且他们还会养很多很多的羊。罗可最喜欢吃羊。
然而罗可从没近距离接触过任何一个人。
他的第三个特点,或者不能叫做特点,污点还差不多。这个污点就是,他从没成功绑架过一位公主。
公主是一种雌性的人类,地位很高,罗可以为差不多是族长老婆这种阶级。
在龙的族群里,只有成功绑架一位公主,才能算作真正成龙,才能抢山头,打凤凰,每月收取龙晶石,走上龙生巅峰。
而罗可连大活人都没咋见过,更别说公主了。
罗可的爸爸妈妈很是捉急。他们不希望儿子变成啃老族。
特别是这只儿子还这么能吃,整个山头都不够他喝一壶的。
他们天天催着罗可去找公主,找公主,找到公主才能完成任务领点数。罗可耳朵起茧两百年。他不是不想做,也不是不能做,就是懒。
月黑风高的一个夜晚,罗可觅食回来,伸伸懒腰打打嗝,打算就这么睡下了。
然后他看到了月亮。
那天晚上的月亮不大,也不是很圆,甚至都不是特别亮堂,总之没有任何一种能人看了油然而生一种“人生大事就在此夜成真”的念头的特质。
但罗可一瞬间觉得,就是它了。
人生大事就在此夜成真。
他抖抖翅膀,往远方灯火通明的人间飞去。
罗可首先落脚的是一座城市。
他停在一座大楼顶上,往下张望着。下头黑黢黢的大道上,无数奇异的小盒子四处穿梭。罗可知道那个叫“汽车”,似乎不能吃的样子。他对不能吃的东西向来没什么兴趣,于是转移了目标去看街道上行走的人。他们看上去都脆弱而娇小,但又是那么有趣。
罗可想了想,把自己也变形成一个人的样子。
一开始很不成功,他一走下楼,就把好几个过路的行人吓得哭爹喊娘。他很是手忙脚乱了一会儿,有时候尾巴没缩回去,有时候眼睛没变形占了整张脸,最后好不容易看着正常了,就赶紧扎进拥挤的人潮中去。
他没什么目标,四处走走看看,所幸之前学过人类文字,招牌广告都能认个大概。一会儿“人兽保险”,一会儿“健康修脚”,不由感叹人类生活真是谜样丰富。
光看热闹也不管用,罗可没忘记自己的主要目的:找公主。路上拉了几个人问,别人都用“你他妈是傻逼吗”的眼神看他,搞得他很懵逼。走着走着有点累了,拐进一个小巷想休息会儿。正好看见巷子一排垃圾桶旁边有一个花花绿绿的招牌,上头几个花体字:美少女夜总会。
什么玩意儿。他又定睛一看,下头一排小字:水兵月公主、小兔公主等任君挑选。
公主。
哇哦。
踏破铁爪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罗可想,绑架公主根本没有他们说的那么难。
他高高兴兴的进了“美少女夜总会”。一进门酒味烟味呛得他一个响鼻,惊动了坐班妈妈桑。罗可惊恐地看着一个铁塔级别的女子朝这边直线移动,以为自己招惹巨怪了。
您是第一次来吧?长得真帅哦,想要什么样的女孩子,我这里都有哦。妈妈桑皮笑肉不笑,脂粉味儿熏得罗可想吐。他不动声色屏住呼吸,说,你们这里有什么水月饼公主吗,给我来一个。
妈妈桑的皮僵住了。
您说啥?
水——月——饼——公——主。罗可字正腔圆又念了一遍,生怕她听不清楚。妈妈桑看了他一会儿:你他娘的来砸场子的吧。
罗可没辙了。这人怎么都不会好好说话的。他决定使用邻居小黑教他的办法,从兜里掏出一堆金币,哗啦啦撒到妈妈桑面前。
他原来一直以为世界上不会有任何一种生物比龙更贪财了,现在看来还真有。妈妈桑笑得张牙舞爪,嚷嚷着贵客贵客,我们这儿可有的是最好的公主!现在就给您找来!说着往后头吼了一嗓子:水兵月给老娘过来。
罗可拒不接受进去就座,想着赶紧绑架赶紧完,老子还等着回去吃宵夜,站在门廊百无聊赖等着他的公主。左等右等,从帘子里出来一个人,黑发白肤,穿着水手服。
……罗可估摸着这人快他妈有两米了:“你你你就是水月饼公主吗?”
“我是门门子,”两米水手服听见他的称呼表情没有半点变化,“水兵月公主得香港脚,我来替他的班。”
“你也是公主吗?”
“这……”门门子不知如何作答,“大概……”
“那就行。”罗可放心了。心说这公主长得不错!大长腿,小白脸,回去给族长看肯定特有面子。他兴高采烈就现了原形,顺便挤塌了整个“美少女夜总会”还有旁边的“人兽保险”和“健康修脚”,在一片哭爹喊娘声中衔着门门子大摇大摆飞回去了。
罗可这一趟出去,见着了好多人类,花了金币,还绑架了公主,他觉得这一波不亏。回到窝里把门门子小心翼翼放下,对方已经快被叼得腰间盘突出了,一脸惊恐退到门口:“你是龙!”
“你这不废话吗,”罗可抬起后腿搔了搔耳朵,“今天你就待在这儿,明天跟我去族长家把任务交了就齐活了。”
“任务?什么任务?”
“绑架公主啊!我们不绑架公主不能成龙的,都是房祖名。”
门门子欲哭无泪:“我他妈不是公主!”
“骗龙!你不是那个什么水月饼公主!”
“水兵月公主得香港脚了,我替班的啊!”
“那我不管,你先帮我把任务清了。”罗可不耐烦了,鼻子里直往外喷热气,想了想,又加了一句:“你不帮我我就吃掉你。”
这一招是从邻居小红那儿学的,就结果看来是卓有成效,门门子·替得香港脚的水月饼公主上班·公主立马不吭声了,找了个地儿坐着。
罗可本来打算睡觉,又想到明天就要把这个公主交给族长,现在不好好看看就没机会了,于是腆着脸又蹭过来:“你站起来让我看看呗。”
“你看我干什么。”门门子无奈问道,但还是站了起来。罗可绕着他转了几圈,拱了拱那头奇怪的黑头发,瞅瞅他细长的胳膊,又低头看自己最中意的那双大长腿。
他一蹲下就要收腹,收腹就要吐气。
一吐气,门门子水手服的超短裙就整个掀起来了。
门门子:我了个大槽!
罗可:我了个大槽!
“你是公的!”
“一直都是啊!”
罗可震惊之余又看了看他的胸前,平坦如煎饼果子。这特么和说好的不一样啊。
少了两块,多出来一块。不知族长看见带把儿的公主会做何感想。
罗可有点愁。
他围着门门子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最后下定决心,说,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门门子表示我他妈都被绑票了您有屁快放。罗可是个诚实的boy,一五一十把自己想法说了。
门门子:……
罗可:……
门门子:我他妈就替个班你居然要割我鸡鸡!?
谈崩了。门门子坐到罗可大床上生气,罗可只好在地板上趴着,心想我这是招谁惹谁了。
迷迷糊糊捱到天亮,族长那头是不能去了,他只好跟门门子说,我送你回去吧。
门门子巴不得呢,也不顾自己腰间盘突出,爬进罗可嘴里。一人一龙开始往城市行进。还没出山口,一个霹雳打过来,差点轰掉罗可半边翅膀。
老凤凰们在上空哈哈大笑。罗可气得险些给嘴里的门门子截肢。他一路乌鲁乌鲁爆着粗口想冲上去暴打那群老不死的,结果寡不敌众又不能喷火,被揍得狼狈逃窜躲到半山腰一个石洞里。
他把门门子放下来,大吼:快!快用你的香港脚熏死他们!
得香港脚的不是我是水月饼!门门子几乎吐血。罗可浑身冒白烟儿,说,那你快跑!去告诉族长他们!
好!门门子立刻点头,跑了几步又折回来。那你怎么办?
我可是齐天大龙啊,我是不会死的!
门门子撒丫子往外跑。
等到族长他们赶到,罗可已经瘫在地上叫爸爸了。老凤凰们遇到真龙完全不是个儿,屁滚尿流飞走,罗可爸爸妈妈看着地上的儿子,又是心疼又是丢脸。
“你们别急着骂我,”等龙们都来到他身旁以后,罗可有气无力的说,“我绑架回来一位公主!”
龙群骚动了。罗可·没有姓居然成功绑架了一位公主!他们交头接耳看着门门子从一堆热乎乎的大尾巴大爪子中间钻出来,已经烧得光屁股了,来到罗可旁边,看他的伤口。
“这是门门子。”罗可为大家介绍。
门门子看着他,欲言又止。过了半晌,他说,我们好像还没有做过自我介绍。
罗可说,我叫罗可·没有姓。
门门子说,我叫门萨。
END
浓稠的黑暗之中,一簇豆粒大的火苗倏地亮了起来。
一支现代不常见的、陈旧而略发灰黄的羊脂蜡烛静静地燃烧着,昏黄的光芒让那秉烛的手显得愈发干枯瘦弱——那是只衰老的手,满是粗茧与色斑,活像只患了瘟病的禽类的爪。
身着旧式黑色套装的老人跪坐在瓷砖地面上,把那微弱的光明捧在胸前,虔诚地凝视着面前的墙壁。
颓败却一尘不染的壁纸之上,有一尊漆成苍白色的木质神像,以八根长钉从手腕和脚踝牢牢地钉死在墙壁上,呈现一种残酷的、殉难者的姿态;被灰暗的壁纸映衬着,显得愈发清高而圣洁。
烛光在老人的眼中蓬勃地跃动着,他呼吸急促、干瘪的胸膛因激动而微微颤抖,眼神似是带着种异样的狂热;让人恐怕那老迈的身躯就要承受不住激烈的情感,擅自爆裂或是燃烧起来了。
一滴温热的血滴落在瓷砖地面上,殷红刺目。那血珠从他的眼角溢出,一路划过老人瘦削的脸颊,留下触目惊心的泪痕;紧接着是二滴,第三滴——鲜血从他的眼角、口鼻、耳孔,从他每一根灰黄色头发的末端喷涌而出,顺着他的脸庞涓涓流下,像是数条欢快活泼的小河。几近腐败的松弛皮肤和着苍老的血肉从他脸上、胸口,从他浑身上下大片大片地剥落,在黑色的衣料上面挤成血肉模糊的一滩。他抬起手揉了揉眼睛,然后把两颗带着凹凸病斑的茶色眼球和大把枯萎的头发一起揉进口袋。
淡蓝色的眸子从那眼窝深处钻了出来——透着些许淡淡的、迷蒙的灰,让他瞳中的映像也蒙上了层稀薄的雾气,影影绰绰,像是他眼中的世界生来就带着种懵懂和迷茫——连羊脂烛火苗的光亮也显得有些晦暗不清。
随后是稚嫩的脸庞、细瘦的臂膀、年轻的脊梁——一个少年撑破了老人的身躯,从他破碎的躯干里生生挤了出来。
希尔•卡斯蒂安舔了舔嘴角,扬起血渍未干的小脸,散在肩头的浅灰色头发在烛光下泛着些微金属光泽;右颈后的头发被一种很烂的手法削得很短——像是个孩子气却有些出格的恶劣玩笑——露出纤细颈项上狰狞的古旧伤疤。
少年抖了抖尖尖的耳朵——那对耳朵在他产生记忆以前便被割得仅剩下半截儿,据说这样才能让“像他这种孩子”更好地聆听神的声音——从那件被血肉浸染得脏兮兮的裙子里爬出来,虔诚地趴伏在地面上,前胸紧贴着冰冷的地面。他白皙稚嫩的身体上满是破碎的皮肤血肉,像个刚刚破茧而出的新生幼儿。
他匍匐在神的脚下,低声咏诵着神圣的祷词。
神的偶像冷漠而威严地凝望着他光裸的背脊,审视着那被神圣真言簇拥着的、泣血之眼的神圣纹样。当他的母亲在洗礼仪式上,用圣水加持过的匕首将那些文字和图样一刀接一刀地、深深刻在他背上的时候,他一定疼得嚎啕大哭——他实在太小了,完全记不得那崇高的献祭,可那份疯狂却被完完整整地继承下来,像是那些神圣的单字真的被深深刻进了孩子幼小的骨骸。
“无上的神明,敬爱的父。”希尔直起身子坐在小腿上,提高声音说道,带着孩子特有的绵软,语气却肃穆得有些违和:“请您原谅——请您宽恕杰森先生,”他把那件盛着血肉的上衣拽到身边,两只遍布血渍的小手交握放在胸前——“他生活在您的庭院里;半年前他去到了您的庭院——是他把麦吉的白兔子带到您身边去的。虽然它在您的身边一定会过得更开心,不过麦吉找不到它,一定会非常、非常伤心的。可怜的麦吉。”希尔忧伤地说,深深地低下头,为了伤心的麦吉感到分外难过,又从心底里为那纯洁无暇的生灵终于得以去到神的身侧欣喜万分。“杰森先生让麦吉那么伤心,请您原谅他的罪。”他说,再一次深深地俯下身,亲吻着神脚下的地面。
在严格遵守的睡眠时间以前,希尔将换下的衣服顺着垃圾道丢进了地下的焚化炉;他熟练地把瓷砖地面擦了又擦,收拾得一尘不染——好像一刻钟前并没有哪个孩子在那里蜕去了一层苍老的人肉外衣。 他用冷水把自己从头到脚冲得干干净净,然后打着喷嚏缩进被子,读完了枕边书里几则没有插图的儿童故事。
然后,惯例性仪式般地,他捏着鼻子灌下了整整一杯温热的牛奶。饥饿感几乎立即消失了,牛乳特有的臭味让他深深作呕。孩子紧紧捂住嘴巴,感受着那些恶心的、浓稠的乳白色液体在胃里沸腾、翻涌着,然后蛮横地涌向涌向尾根——孩子尾椎骨末端的几个骨节猛地冲破了包裹着它的皮肤,不断伸长、生长——血肉和新生的皮肤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攀附上森白的、新生的骨骼——片刻熟悉的剧痛过后,希尔熟稔地把股间新生的牛尾拥进怀里,懒洋洋地打了个呵欠,伸手掐灭了蜡烛顶端跃动的火苗。
FIN.
------------------
其实算是设定,不过考虑之后觉得还是发在一章日常吧……
尝试着用文字描述希尔的角色纸,多少有些赘述……
码的时候还没看Q&A;,可能会有BUG……【忐忑
欢迎指点~XD
-----------------------
修复了BUG,没脸说……



扎哈尔推开眼前的文件,向后仰倒,半旧不新的皮质靠背椅吱纽一声响,稳稳地托住了那疲惫不堪的脊梁。白衣的研究员先生慢吞吞地活动着自己的肩膀,让堵塞的血管和经络重新畅通起来,然而除了酸麻胀痛以外,肩膀并没有用任何其他的感觉回应他。扎哈尔又向前弯曲上身,将肘弯撑在桌面上,取下了金丝边眼镜,拈着细细的眼镜腿儿,用手背蹭了蹭酸涩发热的眼皮以及鼻梁上眼镜架留下的浅痕。
他眯着那双浅灰色的眼睛,极力想看清楚待在桌子一角,压在一叠打印纸上的,放在这个糟糕的办公环境里仿佛清新脱俗的女王一般,安静又骄傲地占着它自己的小位置的那个盆栽。然而离开了眼镜,扎哈尔只能看见一团一团模糊不清的迷雾。
他于是起身,顺手扶了一把靠背椅,免得它发出剐蹭地板的刺耳声响,然后重新戴上眼镜——很好,他又能看清楚那叠打印纸上因为盆栽留下的细小沙土末了。
那是一盆秋海棠,一种亲切的,诚恳的植物。扎哈尔凑过去仔细看了看它那因为受到了温柔细心的照料而挺拔健康的枝叶,他那细细的眼镜链垂下来碰着了花叶,然后进行了一次深深的呼吸,把工作积压的疲劳以及压抑和着肺里的浊气一起吐了出来。
有点好笑,研究员先生此刻觉得重获新生了。
那盆花被他的呼吸吹动了花叶,如同被情人的耳语撩着而飞红了脸颊,叶片轻轻颤抖起来。
“你还真是有闲心啊。”同事端着咖啡杯路过,挂着同样熬夜工作之后的黑眼圈,疲惫不堪,白袍的衣袖看起来有一段时间没洗过了,沾上了灰黄的污渍,端着杯子的拇指和食指染着斑块状的蓝墨水。说完这话,他就当着扎哈尔的面,打了一个拖沓蔫吧,颇有大家风范的呵欠。
“我是在照料主的其他子民。”扎哈尔那同样因为疲劳而缺氧的脑袋里鬼使神差的冒出一句话,而他懒得思考,顺着本能把它说了出来。
他同事的反应告诉他,这句话让对方觉得听了个不太好笑的冷笑话,而他那短路的脑子显然不能很好的奔跑,让他机智的说点什么来破解这种局面,场面一时有点尴尬。扎哈尔皱起眉,因为想起了这句话的出处而烦躁地推了推眼镜,连夜工作的疲劳卷土重来,他觉得自己从柔软可爱的桌上女王那里掉落回了纸质的数字垃圾堆。
他用右手的食指和拇指以及虎口那一段位置撑住额头:“该死,这些数据让我脑子不好使了。”他作出恶声恶气的样子,冲他还傻站着想说点什么的同事发出低声威胁,“你还呆在这里干什么?!既然好不容易完成了工作,就快去睡你该死的觉!”
可能是扎哈尔的表情着实很可怕,也可能是突然感受到了来自床铺那神圣的召唤,那位同事撒腿就跑,矫健得像大森林里的一只野兔。
真希望他醒了之后记得洗洗外套。
扎哈尔揉着太阳穴,有气无力地看着发黄的白色衣角在门缝里被夹了一下,然后让主人粗暴地给一把扯了出去。
然而扎哈尔的思绪却不能伴着对方关门的声音一同静止,刚刚那简短的对话勾起了覆满尘埃的陈年旧事,如同被顽皮的孩童轻轻一吹便四处飘散的蒲公英,在这小小的室内到处碰壁,激荡起更大的波澜,最后终于起了漩涡,拽着他推着他挤着他,砰地一下将他撞进灰扑扑的记忆之河里。
银质的十字架在那位神父胸前一闪,玳瑁念珠互相碰撞,随着衣服布料的轻微摩挲声,这位生着一双绿眼睛的牧羊人直起身躯转过脸来,脱下那双满是泥土的园艺手套,然后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十四岁的扎哈尔望着他,几乎被对方眼角的泪痣和耳鬓的碎发吸引去了全部注意力。
他看着牧羊人安静地在身前交握双手,没有对十四岁的扎哈尔那浓重的黑眼圈以及憔悴悲伤的神色发出任何疑问,他只是微笑着冲扎哈尔点点头,祖母绿的眼睛如同春天化开的湖水,漾着令人平静的温柔波光:“你想走近点看看吗?”他后退一步,让扎哈尔站在自己原来的位置上,可以近距离的观察那几盆在上午九点钟的阳光下舒展身体的东方花卉,“这是秋海棠,是一种坚强的植物。”牧羊人那轻柔的细语声带着神奇的力量,使登岛后多日来夜不能寐的扎哈尔放松了紧绷的神经。
“远离故乡来到这里,虽然有些水土不服,却一直尽全力生长着。”
“是令人非常敬佩的,了不起的花。”
少年扎哈尔魔怔了一般直瞪着那朵花,觉得它在明亮的阳光下红的像火,刺痛了眼睛。
时隔多年,已经成为研究员和一名优秀的牧羊犬的扎哈尔·伊萨阿科维奇先生每每想起这事来都觉得很不可思议,对着一位素未谋面的陌生神父和几盆普普通通的东方花卉,因生活中接连遭遇变故而如同蜷缩起来的刺猬一般将自己封闭起来的少年人的自己,竟会在这样几句云淡风轻的闲谈中,失去自己那引以为傲的控制力,手足无措地任由大颗大颗的眼泪顺着脸颊滚落下去。
他的脑中一瞬间有很多跳动着的画面在晃来晃去,比如油罐车爆炸时冲天的火光和巨响,从头顶上飞过的零件碎片如同刀锋雨,压在车下怎么也拽不出来的父母的手,被血污所染红的视野,以及拉长了的警车鸣笛声,伴着闪烁不停的红蓝两色光,很多穿制服的人一拥而上,攒动的火光中,每个人的背影都漆黑一片,仿佛张牙舞爪的妖魔鬼怪。
所有的都在火焰疯狂攒动着,鲜红,赤红,,暗红——眼前看不见别的东西。
它们在肆意践踏十四岁的扎哈尔的幸福,并且耻笑他极其无能,毫无反抗之力。
十四岁的扎哈尔沐浴在夏末的阳光中,站在那位陌生的神父面前,梗着脖子,拼命咬着嘴唇,防止抽噎声从喉咙里倒溢出来。
神父从后面,将两只手覆上他的肩膀,把他转过来,让他远离那灼目的幻象火焰,然后将他拢进怀里,扎哈尔的头碰上了对方的胸口,听见神父的心脏在胸膛里沉稳地跳动着,如同一刻不息走动着的立式钟,而他自己的心脏则像只拼命挣扎着要飞走的小鸟,期期艾艾地鸣叫着。
离群的小雁,走失的驹子。
被人剪了翅膀塞进鸽笼,被人套上辔头关进马厩。
漆黑。
扎哈尔不断地,连续地,混乱地想起那些被自己拼命压在记忆深处,反复告诫遗忘的事情,他记得那些神父敲开了门,双手交叉在胸前,用他们那相似到仿佛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声音,以及可憎的悲天悯人的态度,散播福音一般对自己传达了无异于拘束令的通知。
“伊萨阿科维奇先生,您被主选中了。”
他也记得自己那虔诚的奶奶一瞬间露出的惊喜表情,以及随之而来的掩藏在眼底更深处的茫然无措。
“你们一定是搞错了。”他还记得自己故作镇定,挺直瘦弱的腰板,努力把书包拉到背后去,手还插在里面,紧紧握着一本不知道是什么科目的教科书,攥得死紧死紧,以至于手心的汗水弄软了书脊,“我是个刚搬来不久的外国人,我的父母在加油站爆炸中不幸遇难,我来这里投奔奶奶。”
他无法压抑自己紧张的情绪,机械地重复那从进入国境线以来就重复过许多次的话,那是他段时间内掌握最完美的一句里洛尼亚语。他如此熟练,倒背如流,语速再快也不会咬到舌头。
“神父们,我的梦想是做一名医生,我在新学校适应的很好,我很努力的学习,老师和同学都很好,我每周都会和奶奶一起去教堂,我已经能说很多里洛尼亚句子……”
然而神父们又用整齐一致的声音再次回答他,他们的长袍逆着光,细瘦的身影在夕阳下长的越来越长,一直爬过桌子,伸到扎哈尔脚边。
“您不用紧张,您是被主选中了,牧羊犬扎哈尔·伊萨阿科维奇。”
他们一起笑起来。
“恭喜您。”
银十字。
在逼近地面的一团火焰熊熊的太阳下,油罐车的碎片插进地里,生出了巨大的银十字,它们成片地破土而出,把寒冷的故国土地顶碎成渣土,簌簌落下来,十字上落着成群的乌鸦,它们呱噪地笑着,反复念叨着“恭喜”。
它们的身影被拖的那么长,就像是穿着黑袍的人一样。
——————-tb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