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间百器,皆具魂灵。
灵则缘起,来莫可抑。
悲乐喜怒,爱怨别离。
万相诸法,梦幻泡影。
==============================
渴望,思念,孤独,怨恨……这绝不是人类仅有的感情
抱有欲念被主人抛弃的器物,在春秋时分,化为付丧神。
而暗怀心愿的人类,也在寻求着某种际遇与改变。
人与器物的命运与缘分,无论善恶,在踏入这扇门时开始。
欢迎来到徒然堂,
今天的你,也在期待着什么?
企划完结
填坑小组:http://elfartworld.com/groups/1381/?p=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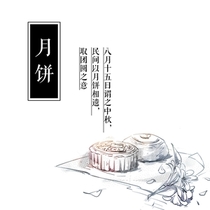





杏姐专场!!
写着写着就心疼起来。序章完结前的最后一张,稍微有点信息量,下一章收尾,点一些前面埋的伏线,会再死一个人。
我终于快写完了,叹气,还是要到3w字了……
让我再说一声:赵衔你这个辣鸡!!!
——————————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朱杏要寻那画中器魂说话,原还很顺利。
既要说话,便要灵器魂魄显出形来。她先略略打量过一回王家备下的屋子,果然与自己求的不差什么,窗上贴了青竹纹的冰砂纸,朱杏还倾身出去瞧过一回,隔着院墙再看不见那方小荷塘,回身把窗也闭紧,这才满意的点一点头。
她往日跟在母亲身边,行得多看得也多了,自然知道手上灵器的凶险——却也非是说就有能耐伤了她了,只她身边跟着昼间深夜两个,不说还只是个浊气缠身的灵器,便是来个老道些的狂百器,要伤她且还不能。
说着凶险,实是物器本身险得狠了,是清是浊俱在一念之间,半点受不得刺激。深夜同她说,也不必多费口舌,只将浊气都净去,自然也就好了,可朱杏咬咬唇,到底驳了他。
她心里头首先想的,是必不叫那画中灵害了王公子的性命去。器灵与人,在她瞧来实是同样的,灵器与狂百器,也说不得就有多少不同。
人有入了执疯魔一辈子的,器难道就不许一时蒙了头走岔了道?
且说这岔道,于旁人是蜀道崎岖难登天,说不得于事主便是清朗舒平锦绣团呢?
朱杏便总想着,不拘人或是器,总要听过对方的话音才好。这念头在她心中已久,有些个道理,她似是知道,又似不解,像是隔一层黄纸,细蒙蒙一层,却总也戳不开。
一时戳不开,也不打紧,总归这桩事归她做主,便由着自己的心思来安排。
将山水图往案上摊开来,灵物吃她一记大亏,缩着不肯出来,图面上便半点不露,清凌凌的墨意山水图配边上一只掐金点翠白瓷瓶,竟在这当口还显出了几分雅来。
朱杏先与山水图说话:“请姑娘出来一见,先前匆忙出手伤了姑娘,很该赔个不是。”
画儿静悄悄,只一味不回答。
深夜身后头一条尾巴摆了摆,叫朱杏拿眼止住。
接着便又自报家门,说了一些软和话,仍不得回应,那画灵早先叫常山来查看时,钻出画来唬了这官儿一跳,可换得朱家这个娇滴滴的小娘子,还未见便叫拿钗子掷了个对穿,晓得对方厉害,再不愿出头。
最后还是昼间轻笑一声,同深夜两个一左一右走到案前站住了。
他也不再提深夜说过的那些话,只道:“娘子,也想一想那王公子罢。”
此时磨得越多时间,那被困在画中的王公子可不是生机越薄。
他们家的娘子心善,事事想着留有余地,念着以理以德,可世道那里就这样容易,双全之法,那里可得。
昼间却也不点她,左右朱杏往后日子还长,先时不懂,何时碰着跟头,摔得痛了,也便懂了。
朱杏咬了唇,她的心是善的,决断却也极快。
她心里定了主意,便将皓白手腕一翻,掌中生出一朵白焰,只小小一朵,驱使了往山水图上引,奇的是火苗遇纸张却半点烧不坏,却扑朔冒了一缕黑灰轻烟,接着便响起尖利惨叫,见一点黑点自画中湖内翻涌,须臾湖水竟真个荡起波来,一墨色女子身姿自湖水里扑朔着翻滚上岸,惨叫一声弱过一声,黑色烟雾顺着画卷边沿一滚一滚溢出来,先是流淌一地,接着便渐渐凝成个韶华女子模样。
细长慢挑柳叶眉,紫阳清月翦水瞳。分明是二八年华的娇柔美人儿,面盘盈盈薄施粉黛,眉间贴得画钿,一双唇却不红润。
非但不红润,还微微泛着青乌,连着一双玉手伸出,也是死灰色。
那画中灵受得白焰灼烧,虽画烧不坏,那些浊气却与她相缠日久,极难分扯,烧着那些脏物,便同烧在她身也无两样,只觉烧得皮开肉绽,再忍耐不住,自画中扑腾出来。
她甫一落地,知道是眼前之人害她受苦,忍着焦灼便要扑将上去,昼间深夜两个那里能叫她再动弹,一边伸了一条臂膀,便将画灵死死按住,她再要挣扎,身上却已叫烧得没有力气,又那里能扭过那两个积年的活阎王,只赫赫地喘气,一双多情含泪桃花眼隐隐现着红光,牢牢钉在朱杏身上。
朱杏一言不发。
她是头一回这样近瞧着身缠浊气的器灵被灼烧的模样,收回那一小朵白焰,她面上不显,心头却说不出的五味陈杂。
决意的也是她,动手的也是她,这会子再说些心软不忍的话,只显得矫情。
朱杏也不品自家心里那些酸甜苦辣,努力正了面色,同画中灵说话。先问她王公子在何处,画灵不答,又问她为何如此行事,也不答,朱杏想了想,再问:
“可知自己姓甚名谁,家住何处?”
这一个问题,总算叫那只一味沉默的画灵变了神色。她先是颦眉,张口说“姓李,家住簪花巷子”,可说完自己却又恍惚起来,两弯柳眉狠狠拧起,眼中仿若含了秋水盈盈,泪珠子要掉不掉,声音讷讷:
“奴姓李,住簪花巷子,姓李,姓李,奴要寻三郎呀……奴要寻……”
她细细说个不住,本已叫烧掉些浊气,清醒许多,这一下竟又疯魔起来,手里衣袖也叫扯烂了,黑气猛然翻腾。
朱杏却狠下心,再不拖沓,也不惧那翻滚的黑烟,张口喝道:
“非也,你不姓李,也不住簪花巷子,李小姐早早去了,你却将将才生!抬头好好瞧瞧,你却还不醒么!”
一字一句落地有声,那画灵怔怔然一抬头,眼前陡然清明,正瞧见自己半身落在画纸外头,另半身犹在画中,心头猛地一窒,张了口,却再说不出话来。
朱杏斥过她一场,眼见她似是醒悟,语气便又不由软下来。
“你并非李家小姐。”她轻言轻语,话儿却不含糊,“你乃李小姐所藏画作,因受物主执念影响,生出一段神智来,你便是这画,画便是你。”
见画灵怔忡,目中红光消退,眼角眉梢戾气水色渐消,却露出几分茫然无助,像是出生婴孩一般懵懂起来,朱杏顿了一顿,叹了口气又道:
“去者已去,你因李小姐执念而生,却很不必将自己也困在这执念里。你既非是李家小姐,王公子如何便也与你无干系,放了他出来,不害得人命,自有你安身之处,往后如何过,全还在你一念间。”
画灵听她温声说话,本已有些听住了,神色越发缓和,只听到要将她那三郎放出,却抠了手抿了唇,不言不语。
她心里头且还懵懂,说话做事全只凭本能而动。先时一门心思以为自己是李家娇娥,一意寻心头藏着的那个三郎,拉了人的手,也不知是想着要将好儿郎一同带下水,还是要叫那好人拉了自己上岸。
画灵自醒来那日,便是长在水中的,她沉在塘底,一时烂泥烂草自面上的孔洞灌进来,有意哭喊,也只灌得一嗓子泥沼,可便是如此,痛苦得狠了,也只死不去,腕子叫水草缠着,抠断了指甲整个掀翻过来,也不流血,只日日肿胀窒息,却偏不死。
再之后她总算上得岸来,深恨这片湖水,却也离不了这片湖水,离得远了,整个身子再不成型,如一滩烂肉自骨架子上头扑朔朔往下落,叫水一泡,却又是还娇嫩红颜,只得泡在湖水中,支着身子立在岸边,浸在水中的身子一阵阵发冷,这时便又想起,她心头有个三郎,远看近看都是极好的儿郎,可他怎地就不拉她上来。
画灵既不识得自个儿是谁,也说不出这三郎是谁,想起那人仿若雾里看花水中观月,心头一阵阵的痛,又是苦又是涩又有甜,分不出滋味。
她生出来不过几年光景,头脑昏沉,不清不楚,直到山水图叫王公子得了去,日日观赏夜夜把玩,才头次出得纸面,自己却还浑然无觉,见着个儿郎,口里只会唤一声三郎,那里想王公子竟应了,自然认定了他,几日下来,叫王公子拉着她的手,一气扯进了画卷里。
此时听朱杏说她非是李家小姐,一声如雷轰然炸响在耳畔,将往昔镜花水月一时砸了个干净,兼之浊气损消,脑内清明,也晓得了自己原是那样来历,可叫她就这般放人,到底还是不肯的。
朱杏听她没声,也知并不这样容易,只她也没再闹起来,便已经算得是好兆头。当下连哄带劝,细细开导:
“我看那王公子,也未必便是你要寻之人,王家两年上一次京,等闲进不得李家大门,王公子要与李小姐有私,他却那里来得这样大能耐?家中行三的儿郎那样多,你若过不去心中那道关,此间事了,我便陪你去寻那人又如何?只你不害人,寻到了解消心结,谁也不拦着你去。”
画灵身上黑气愈消,懵懂的眉宇间又添出两分理性来,听朱杏说得恳切,竟好像也懂得了她讲的道理,虽仍是踌躇,却并不那样坚决了。
她忽地抬头,颤颤地拿眼去看朱杏的眼,盯住了她不松,蠕了蠕唇蹦出几个字来:
“与我、找、人,说、好了……?”
她声音轻脆脆的,透着叫朱杏再没想到的稚嫩,说是童音也似,同先前那把甜腻婉转的嗓音再不相同。
在场一人二器俱都明白过来,先且那娇腻甜音是李小姐的嗓子,这时这把清脆嗓音,才是属于这画中灵的。
朱杏止不住露出个甜甜笑脸来,伸出小指头停在画灵面前。
“说好了。我们拉钩。”
那画灵歪着头瞧了一会,也学着朱杏模样,伸出青白的小指头,冰冷的手指缠着朱杏的,一人一器却都不觉得凉,絮絮说起话来。
一个说:“找、到人,我不、害他、”
另一个就点头:“嗯,我陪你找。”
一个又说:“我就、想、问、问……为何不拉、我、我、主人、上去。”
另一个就道:“嗯,问问他,为何不拉你主人上来。”
一个停了停,犹犹豫豫还问:“这、回、必不叫、我、再、落水了罢……?”
朱杏心里裹着一股子热意,四肢百骸说不出的舒坦。吸了吸鼻子,用力点一点头。
“你且放心,必不叫你再落水的!”
画灵便抿了唇,面上现出几分活泼的笑影来,她伸手朝画卷中一捞,便见素手上多了一片衣袂,再一看,却是个年轻公子叫她捞在手里,形销骨立面色青白,却总还出气,是那王家公子无疑了。
那王公子看着狼狈,一出画卷,竟还有力气抬一抬眼皮,一眼便瞧见近在眼前的画灵,唬得牙关咯咯作响,也不知那里来的力气,竟将两手一挥,扭身瞧见旁边站着的朱杏,更是心生指望,不住挣扎起来。
一边挣扎,一边口中还骂:“兀你这鬼物——!巧言误我!救、救命——”
他几言讲得画灵面上先前那点子血色尽失,眸光点点摇曳不住,几乎拉不住他。王公子此时奋力一挣,人未能离得画灵之手,身子却是撞出去半边,晃得案台支撑不住,一边摆放的那只掐金点翠瓷瓶两下一摇,倾倒侧翻过来。
谁也不知瓶内竟装得大半的水,这一翻到,立时便浇在画灵人身并本体的山水图上,整张图都仿若淹在水里。
本已消退的黑雾顷刻间再起大盛,朱杏只听得一声痛苦尖啸并男子闷哼,骤起的狂风刮在她面上,眼前却黑风雾绕,一应全看不真切,只觉夹煞带怨,隐约听得女子啸中带哭,反复只念:“水、水、不落水、不要落水……”
她心中大急,一时也不知是否自己错觉,只觉又听见了那轻脆脆的声音泛着哭腔,朝她怯生生的求救,可耳里明明只有不成声调的异物嘶嚎,昼间深夜只将她护得牢牢的,怨气与浊气愈加浓重,又听得几声硬物断裂声,眼前声势猛地一收,只见一黑影破窗而去,朱杏却不知为何,把甩袖便要去追的深夜抬手拦了一拦。
她眼眶干涩,自己也说不出为何拦着,索性不提,越过昼间深夜两个,探身去看案台。
王公子无声无息的躺在案前地上,脖颈横扭着,背脊也弯了一折,脸色仍青白,脸上孔洞却溢出红来。
而置在案上的山水画,果然已没了踪影。



#怎么说呢……感觉还是很多bug 结局也很仓促……有空再改吧(应该不会有空#
“买定离手买定离手喽!”庄家大声吆喝着,剧烈摇晃着骰盅。赌桌边围满了赌客。一身酒气的赌徒额头上已满是汗珠,他死死地盯着庄家手里的骰盅,紧攥着拳头。
“开——!”庄家一把将骰盅定在桌上,“一二二,五点小!”人群发出一阵唏嘘声。赌徒看到点数,瞬间脸色煞白——他用最后借来的钱赌的是“大”。
几个伙计围上来,赌坊的收债人走近赌徒,嫌恶地用手在鼻子边摆了摆,略带怜悯的看着他道:“公子,你把我们借给你的钱都给输光了,古董家具能当的也都当得差不多了。若是还不上债……”
赌徒垂头扶着赌桌:“我再不济也还有一座宅子,你若能宽限我几日,我……”人群里却传出了讥笑声:“你说的如果是那座鬼屋的话,还不如把你这身衣服当了来钱快呢。”“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这话戳中了赌徒的痛处。“再给我一日我定会把钱还上,否则我任由你们处置!”他疲惫地一手贴着额头,另一手摩挲着腰间荷包里的物什,像被抽了骨头一般摇摇摆摆地朝门口走去。伙计们正想去拦,收债人却摆了摆手示意伙计们退下。
赌徒掀开当铺的门帘:“掌柜的……”
掌柜乜了一眼来人,打断他道:“今天又是来典押什么东西啊?”
“一枚铜骰。”
沿河的住家陆续做起了晚饭。炊烟在屋顶的檐角飘散,夕阳的余晖静静地洒在河面。这样一幕在寻常人眼里再平淡不过的景象却是六茕从未看到过的。屋檐下的燕巢,河底的水草,每家每户都贴着对联……与以前自己所处的地方和四季如春的徒然堂都不一样,一切都很新鲜。
不远处传来一阵小孩子嬉闹的声响。随后一个穿着厚棉袄的小男孩从巷子里窜出,举着一串糖葫芦边跑边笑。“阿妹,小玉姐姐,快……哎呀!”小男孩回头呼喊时结结实实地撞上了原本在一旁的六茕。他扶起小男孩,没注意到糖葫芦在宽大的袖子上留下了一片糖渍。
“可摔着了?”小男孩只当自己先前没看到这里有个人在这儿,不好意思的朝六茕做了个鬼脸后跑开了。
六茕也不在意,笑着走进了另一条巷子去别处闲逛。
在后头牵着邻家阿妹的谢喻听到一声小男孩的惊叫和陌生人的询问,心想莫不是邻家的小弟摔了跤。出巷口时却只看到已跑出老远的小弟一人了。
天色渐晚。今天本是元宵节,姑苏城里到处张灯结彩。往来行人络绎不绝,随处可见穿着白绫袄走云桥的妇人,正是一派热闹繁华的景象。谢喻慢悠悠地走在街上,怀里捧着包好的一小堆各式果子点心,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
难得能独自走动一会儿,谢喻并不想太早回去。于是拆了一包点心,一边吃一边顺着人群向庙会的方向走。街道两边的看街楼上悬着红灯笼,楼外的街上是卖糖画糖葫芦这类吃食的、卖布老虎泥人和面具的小玩意儿的、还有卖胭脂水粉和各类首饰的……各路小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谢喻饶有兴致地在每个小摊前驻足,打量着这些有趣的小玩意儿。
寺庙里有许多来进香的香客,门前也早早聚集起了围观舞狮的人群。一侧的大樟树也已挂上了许多绑有谜面的各式花灯,引来了许多想要个彩头的书生墨客驻足。谢喻嚼着点心游到此处,也被舞狮吸引了目光。无奈舞狮的观众和出入寺庙的香客太过拥挤,便想去一旁的灯谜会看个新鲜。
“……‘遇水则清,遇火则明’,该是一个‘登’字。‘翠竹掩映留僧处’是‘等’字。唔……”
正看得热闹时,谢喻却听到有人用不大的声音念着谜面,并未多琢磨便解出了谜底,还一连解了五六个。
循声望去,上下打量了下此人并不朴素的衣着。看起来倒像是个有点文采的公子哥,不过可惜这衣袖不知是在哪儿蹭脏了。
不过这人也是奇怪,不去与人争着答出谜底挣个彩头,只是默默地解答——
谢喻突发奇想:不如我替他搏了这些彩头,也不至于浪费了他的文采。便走上前去,“解”了几个还没人说过的谜面,得了几个小花灯。她心里乐开了花,想着也该向那人道个谢才是。
“这位公子,”谢喻走到那人旁边轻声喊道:“多谢你刚刚解的那些谜面啦,你要不要小花灯呀?”
那人听到后一句话才反应过来。低头看着身旁的小姑娘,摇了摇头,不解:“谜面是你解开的,何谈谢我。”
“我是偷偷记住了你念的才上去解的啦!”谢喻得意的笑着,对他说:“多亏了你我才能拿到这么漂亮的花灯呢,所以我还是要谢谢你!对了,请教公子大名?”
“我叫六茕……”
“原来是陆公子。”
“是‘六’。”
“柳公子?”
“是‘六’。”六茕不厌其烦的纠正。
“喔——‘六’公子,”谢喻拖长了音调,“要不这样,我带你去那边的摊子上转转,你看中什么小玩意儿就跟我说吧!就当是我给你的谢礼!”还没等六茕答应,谢喻便拉着六茕开始去街上的小摊到处转悠。
六茕被谢喻拉着看各种小摊,简直是眼花缭乱。但是带着他到处跑的这个小姑娘好像有用不完的活力,甚至每到一个摊位上都能跟老板聊上两句……不由得对她有些羡慕。
在谢喻跟一位卖小孩玩具的摊主聊天时,六茕发现了一个长得挺有趣的黄色布偶,就拿起来看了看。一旁的谢喻瞥到六茕的动作,偷偷地笑了,也拿起一个布偶问:“你喜欢这个啊?”
“啊?不是……这个是什么?”
“诶?!你竟然不知道吗?”谢喻很惊讶,“这只是个普通的布老虎啦。”
六茕似乎是有些害羞:“嗯……不过还挺可爱的,这个布偶。”
“那就这个吧!”谢喻向摊主结了账,把布老虎拿给六茕。“谢谢……”六茕欣喜地说道。
谢喻觉得有些好笑:“这是我给你的谢礼,你不用跟我说谢啊。”
玩具摊主用怪异的眼神看着谢喻:“小喻啊,这么晚了你该回家了吧,可别让家里人担心了。”
谢喻这才惊觉已经快戌时,回家肯定免不了要挨一顿臭骂。于是向六茕告了个罪后急急忙忙地跑回家了。
六茕看着这个有趣的姑娘渐渐远去的背影,心情十分愉快。独自逛到了一个人少的地方,抬头看了看散发着淡淡清辉的月亮。
“该回去了……”
拿出符纸用手一点,一道金光闪过——便无踪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