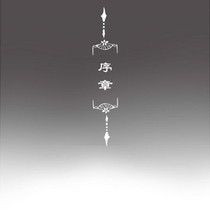世间百器,皆具魂灵。
灵则缘起,来莫可抑。
悲乐喜怒,爱怨别离。
万相诸法,梦幻泡影。
==============================
渴望,思念,孤独,怨恨……这绝不是人类仅有的感情
抱有欲念被主人抛弃的器物,在春秋时分,化为付丧神。
而暗怀心愿的人类,也在寻求着某种际遇与改变。
人与器物的命运与缘分,无论善恶,在踏入这扇门时开始。
欢迎来到徒然堂,
今天的你,也在期待着什么?
企划完结
填坑小组:http://elfartworld.com/groups/1381/?p=1
是雨天。
玉梢坐在亭子里歇脚的时候下的雨。与本晴空万里的天气忽然的就落下雨珠来,好在今天本来就没有什么预定,在亭子里坐着看雨也不失为一种消遣,绣球开的漂亮,只可惜估计这场雨过后就得蔫了。
土质过于湿润的话对于这种植物来说不是什么好事。
玉梢并不懂花草,只是看着那一团团的花朵在雨天里淋着多少有些可怜。
徒然堂四季如春,但并不代表不会下雨,这次的雨点还挺大的,突如其来所有人都没有准备,玉梢是运气好才躲进了这个亭子。
“啊呀,已经有人了吗?”雨滴搭在油纸伞上的声音逐渐靠近,最终停在了距离玉梢约几步远的地方,“是否介意?”
玉梢点了点头,那女子穿的华丽,裙摆倒是一点都没有湿掉,头上的装饰多到让玉梢想起了那些贵族,总是带着金色的钗画着有些夸张的妆容,手上拿着绣着精美纹样的团扇,不论到哪都是一股白粉的味道。
“你便是那新来的唐弓?”
阴雨天气总是人烟稀少的,好在温度不像是外界那样冰冷,多少不会因为一场雨就急剧降温。玉梢有些困,对方开口问自己是不是唐弓,迷迷糊糊间也就点了头。她早就已经不记得自己生于何年何月,更加不记得那是哪朝哪代,只是隐约记得战乱结束之后的样子。
“你可听说过盛唐之世。”
玉梢摇摇头,她醒了醒神,想着或许这人是来找自己叙旧的也说不定,只可惜自己没有什么能够给她说的。
“隋唐过度之快,只在几日之间。逼禅让便成国舅而后称帝,其后几代依旧战乱不止,盛唐不过是对比而言。”玉梢打了个哈欠,她知道的确实不多,前半确实是她曾经见证过的,后半是现今得知的事情。
那人没有再说话,似乎是在思考些什么的样子,雨倒是越下越大,打在砖瓦上的声音不绝于耳,比起那大珠小珠落玉盘的诗词更像是敲击在杨琴上的声音。
“你生于何时。”她问,而后又言,“或许我该叫你声姐姐。”
“我不记得了。”她吸了吸鼻子,“你出身贵族,不该与我姐妹相称,我于战场,你于宫廷。”
差别太大了,“叫我玉梢就好。”
前后恐怕只不过相差了几十年的时光,那也已经足够王超改头换面一番,玉梢不清楚自己被埋后的事情,只怕眼前这人是只知晓宫廷内的事情。
“我问你,你知道初期时有谁叛变被诛了九族?”玉梢突然想起这事来。转头便问,分明是正午时分,天上反倒是劈了雷下来。昏暗的景色,亮堂了一瞬,那人长着一双鸳鸯眼,看上去反倒是像只有些狡猾的猫。
“不知你说的是哪家。”她笑起来,一身华服此时此刻反倒是像沾了血,前朝几代人的努力和牺牲,不论是权力斗争还是保家卫国,自己的时代确实早已过去,自己的主人也早已死于这种毫无意义的事情,事到如今被问起有谁被砍了头,杀了家人,倒真的是答不上来,反倒是更想敲开这人的脑子看看里面究竟装了什么样的东西。
“哪家……”玉梢低下头去,要问起哪家,她还真不好回答,既不能答育有一双子女的,又不能说谋反的那家。
“再之前的事我不清楚,只是在我这代,死的人也不在少数,要是真的想知道,那也只有出了这姑苏城才有可能。”杨雨霖这么说着,更多的实际上是在劝诫和嘲讽,不论是谁,只要有些常识都不会这样问,又或者这人确实傻的可以。
“姑苏……”
玉梢似乎根本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若是真的有需要,可能真的会独自一人想办法离开姑苏去找自己想要知道的事情吧。
“你真的想出去?”
玉梢没有回答,似乎是还在思考的样子。
“总会有人愿意带你出去的,在那之前,不如好好享受。”杨雨霖顿了顿,“你也不像是贫苦人家的,除了骑射,可会歌舞?”
玉梢愣住了,雨还在下,只是比刚才小了许多,绣球的花瓣被打落了不少,树叶也落下来盖在了上头,要问自己是否会歌舞倒还真的回答不上来,她没有学过的可能,更不记得前主是不是精通这些。
拖了一会,最后还是摇了摇头表示否认。
“你要不要学?”
雨落春庭,一曲断肠。
如果现在有人匆匆路过院子,或许能透过雨帘,远远望见有谁在亭中起舞,一红一蓝,歌声不断。
没有什么过多的装饰,抬手之间也不带有金粉银沫,更没有莺莺燕燕花团锦簇。
不存在君王,更不存在观赏者。衣袂飞舞,似是流水,又带刚毅。
唯有一弓,一钗,一亭。
真要说起来,这两人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性,共同点或许也只有主人的离世,其缘由也只能总结为时事造人。
她们之间的关系就好像天平,以一种奇怪的重量保持着平衡,一方忘了所有,一方忘不掉所有,这个天平永远不会倾斜,但是这个天平也永远不会成立,命运是一种令人苦恼的东西,死亡并不会让事情变得好起来,永远只会变得更糟糕。为了权利,为了地位,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
谁死了都不能怨,但是有不得不怨。
谁都没有错,却也谁都有错。
杨雨霖怨,怨得成了灵,玉梢也一样,她只是怨得连自己的怨都已经忘了。现在又马不停蹄的,想要把这种情感找回来,在自己所能做到的最大范围内,在自己能够活动的最大范围内。
她们都保有着生前的样子,那不是自己的样子,而是自己主人的样子。如同她们那般,活着。
“你恨吗?”杨雨霖问着,朝前进了一步。
“我忘了。”玉梢答着,又朝后退了一步。
雨点打在好看的雕花栏杆上,最终放晴了。
“忘了也是好事。总不需要像我这样,总是怀恨在心。”
玉梢看了一眼杨雨霖,没有再朝后退。
“我想,我应该想起来。”
她最终,应该是选择向前进一步的人。自己呢?或许只能停在这里,又或者朝另一条路走。


杭城近来多了几家茶馆,好巧不巧,正和最先在此落户的赵氏茶馆只隔着两三条街。一时之间,茶博士也好,消遣用的果盘也罢,各位茶馆老板均是使尽浑身解数,想在杭城立下足来。
赵老板不慌不忙,心里的算盘打得响亮,临走前仔细叮嘱了茶馆的之前的乐师飞燕打点好茶馆,只因除了账房,只有她最熟悉茶馆的每日流通的钱两。
“去进一批松萝茶。”飞燕问起此行的目的时,赵老板答。飞燕了然地笑笑,前几日赵老板的友人来访,送的正是苏城的松萝茶。松萝茶冲泡开时飘荡出的气味,确实与茶馆平日喝的茶不同,比起众人最为推崇的天池茶,气味更纯而清。到底是多年茶客,赵老板很快便找好的货源,只等择日去一趟苏城做些商量。
赵老板走后,生意如常做着,在飞燕的打理下,没出什么纰漏。可这一商量,却饶是商量得半个多月都不见人影。屋漏偏逢连夜雨,很快,不知谁传出了“赵氏茶馆阴气盛,疑有恶鬼”。路过的人嘴上少不了闲话:本是向阳的地带,茶馆里却终日阴暗,不见一点阳光,更有人说,听说近来杭城有官家的人夜半自缢,死前喝的正是赵氏茶馆兜售的天池茶。
谣言不胫而走,添油加醋之后有了各种版本,小小茶馆很快成为众矢之的,光顾的也仅是几个不信鬼神之说的老茶客了。
而茶馆里的众人发挥着前所未有的默契,对此事只字不提。
鬼怪,鬼怪。安逸心中默念着,能和鬼怪有所牵扯的,无非他中秋之夜买下的那面对他毫无用处的青铜镜罢了。
“你有何愿望?”飞燕的声音。
“你有何愿望?”宝儿的声音。
“你有何愿望?”赵老板的声音。
鬼怪,意指某些非良善之辈,幻化出不同的声音,终日对他进行审问。他总想着有一天得毫不客气地质问回去,没有理由被一个不存在的愿望所困,不应该被虚无的歌声迷惑,于是他问道:“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镜子,日本国的女人,鬼怪,愿望,”这次是茶馆里评书人的声音,带点烘托气氛的起伏语调,好似终日身处疑团之中,“任由你想象。”
鬼怪擅长迷惑人心,众所周知的道理——安逸手里攥着那面青铜镜,他已在脑海里将它摔碎了无数遍,这种感觉,似乎他真的打碎了数面镜子,它照着他,他却不知道。
“不要故弄玄虚!”他数次加以警告,本着一丝物主该有的尊严。而人的尊严在谣言面前通常不堪一击,宝儿的哭闹和飞燕的勉力支撑终于使他发出了第二声质问,“鬼怪,你有何目的?”
“目的?目的总是很快转变,我没有具体目的,也没有最终目的。目的是终点。”它答,“我不会迎来终点。”
“你呢?你的目的是什么?”它又反问。
“我再说一遍,不要故弄玄虚!”感到被虚无的鬼怪作弄,他忍无可忍地打断,“目的?盘问愿望的另一种办法?那么我没有目的。”
“镜非悟具,乃迷具。”安逸想起了这么一句话,谁说的早已记不清了。对于结缘,他越发迷惑起来。
入秋的杭城渐渐有了寒意,饮茶的人数本该增多,而赵氏茶馆的生意却并没有丝毫起色。
“这首曲子弹完,就差不多了。”飞燕对安逸悄声道,茶馆里的其余小厮也开始收拾茶碗,发出叮当碰撞的脆响。
这时街边忽的挂起一阵大风,卷起了道上的秋叶,很快,在三两茶客的怨声中,雨声大了起来。
天色不知什么缘故,却是血红诡异,云层中间恰巧露出一个圆窟窿,好像一只明目张胆偷窥的眼。本准备避雨的茶客们见了,争先往外逃了出去,人对不寻常的东西做出的反应尤为迅速。最先抬脚的教书先生慌不择路,一把撞上了一伙准备入店的人,他抬起头一看,顿时吓得跌倒在地,这一身装束与打扮他是见过的——这是一伙刚来杭城不久的贼寇。
教书先生软着脚,扯着尖细的嗓音,颤颤巍巍道过歉后便落荒而逃。一同吃茶的几个见情况不对,神情慌张地牵扯着奔出店门。教书先生口风紧,唯恐招来祸患,便是对谁也没说那伙人的身份。人们只是本能的惧怕,惧怕血红的天象和不速之客。
可自从那日起,本是生意萧条的赵氏茶馆却门庭若市,茶客络绎不绝,同时官家自缢的缘由也有了新说法——平不了贼寇又帮其走私,东窗事发了。
而那伙人时常光顾茶馆,却都不是些正常的时候,几乎要到其余茶客散尽他们才出现,不要求奏曲,只要求闭门。对于这些古怪的要求,飞燕从来不拒绝,既不能,也无法。接连好几日,飞燕都交由安逸一些来历不明的东西,让他不论价钱,一定得典当出去。
“他们给的东西可以收,不能留。”飞燕最后一次给他的,是一块白玉,“如何东窗事发的?可不就是留了不该留的东西。”
闻言,安逸心中猜出了一二。这伙人是要他们帮忙办事,帮了忙便好处多多。可这些好处,将来倘若事态有变,可就全是些经过他们手的赃物了。思虑至此,安逸握着那块白玉的手出了些薄汗,双目失明使他无法看见来人的面相,而那伙人低哑的嗓音和闻所未闻的口音就像生了锈的镰刀一样划拉过他的耳朵——突然之间,他感觉有什么东西挠了他一下。
“鬼怪?”尽管安逸知道它的名字,一个拗口的东瀛名字,加贺见——会使用这个称呼的人寥寥无几。他倒是更愿意称它为“鬼怪”。
没有声响。
他感觉有什么东西反握住了自己的手,那东西伸出了细长的肢干,顺着他的手臂飞速窜上了脑袋。安逸心中一惊,还没来得及发出叫喊,有个声音忽然在他脑海之中亮了起来,像是骤然燃起的蜡烛。
“安逸,你有何愿望?”
一个小孩,有着模糊不清的脸,应该说,是他模糊不清的记忆。倒塌的家宅,在蜡烛的焰心。
“你有何愿望?”小孩张口了,问的是和鬼怪一样的问题。
他伸出手来,想掐断烛芯。
“你有何愿望?”火焰不依不饶地复燃了。
“是重见光明?还是重返过去?”
那火焰在他脸上炙烤,好像很快就能把它烤成那个孩子的模样,只剩一张模糊不清的脸。
“是重见光明,还是重返过去?”
太热了,太热了,烛泪垂了下来,有那么一瞬间,他知道了烛泪的颜色。
“你是谁?是东瀛女人?镜子?还是鬼怪?”他忍不住问道。
“你有何愿望?”
“没有这双眼睛,我所知道的东西就什么也不是了吗?”
“是重见光明?还是重返过去?”
“‘你’真正的声音是?本源是?器物是?灵魂是?目的?愿望?”
“安逸,你有何愿望?”
“我说过我没有愿望。”
“呼”一声,烛火不知被谁吹灭,簌簌声片刻之后才彻底断绝。
小孩沉默良久,又开口问道:“人没有愿望,何以称之为人?”
“那我便是野兽。”
“野兽尚有生存的欲念,你自己呢?什么都没有吗?”
“再问多少遍也一样,什么都——”
“那么你不是野兽,当然也不是人。你是什么?移动的人偶?”
小孩的脸从下巴开始,有了清晰的形状。这是什么?看?视线?是光?他用力眨了眨眼。
“凭什么移动?为何而移动?穿过了什么,取代了什么?什么填满了你穿过的空间?什么拉扯着你前进?”
孩子的脸愈发清晰起来,他知道自己已短暂地重新获得了双眼,可有些东西不是所有人都看得见,即使他们拥有双眼。
他眼见着孩子张开口,有什么呼之欲出,又消弭在黑暗里。
我是我。
我在这儿。
不是其他任何一个你见过的,和未见过的。愿望中的、坟地里的——你照见的其余人。
并非制作你的、并非你化形的。
独立而完整的,可被流动的空气与风填满的、在个体之中经历部分和完整交替操纵与翻来覆去死亡的容器——
“你有何愿望?”
“承认自己是一个容器。”
“是重见光明?还是重返过去?”
“双眼与静止并非不可或缺。”
“你有何愿望?”
“亲吻烛泪。”
“是重见光明?还是重返过去?”
“是走过一片田野,是田野的缺席者。”
他和小孩一块儿质问,一块儿回答。直到最后一个字眼蹦出了口,烛光平静温和地燃起,孩童时期的自己出现在眼前,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眼睛。
“是谁?”
“白玉葫芦,”它答,“看样子是从徒然堂里逃了出来。”
“不是你?”
“不是我,那难道不是你自己?”那鬼怪说,“白玉葫芦不提问,它只囚禁人。是你在发问,既是过去的你,也是现在的你。”
“那东西呢?白玉葫芦?上哪儿去了?”
“在你的眼睛里,化成一滩脓液了。”它平静地答,“却也没有死。”
“不,它不在我的眼睛里,”他听见自己怒不可遏地叫道,“你助它逃了!”
“做个人情,”它毫不遮掩,“白玉葫芦帮了我的忙。”
“什么忙?”
“它让我知道,你是什么。”
“你对人类做的事不怕徒然堂里的人知道?”
“我不拥有极深极强的执念,不曾杀害过人,我以我的办法了解人,或模仿,或提问,清净师不理会这样的事。”
“了解了人有什么用?你有什么目的?”
“我没有目的,目的是终点,我没有终点,”它说,“出于疑惑,因此我提问。我是谁?为什么化形?为什么映照他人?我是投影于其中的任何一个,是模仿的全部?是最开始的东瀛女人?还是注定戴着面具的九十九?”
“你要成为什么而自己却毫无自觉。”
“难道你还在梦里?难道你从未醒来?一切都是幻觉吗?”
“白玉葫芦又回来了?”安逸咬了咬牙,耳边有一丝风声略过。
“以前总是我捉弄它。现在,它见我仍有疑问,开心得很罢。”
天亮了,早市起了摊,叫卖声冲淡了萦绕于他们周身的荒凉气息。安逸心神稍弛,四处探寻,摸到了身旁冰凉的镜面,却被上面的裂纹割破了手。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