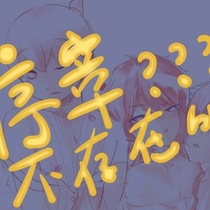世间百器,皆具魂灵。
灵则缘起,来莫可抑。
悲乐喜怒,爱怨别离。
万相诸法,梦幻泡影。
==============================
渴望,思念,孤独,怨恨……这绝不是人类仅有的感情
抱有欲念被主人抛弃的器物,在春秋时分,化为付丧神。
而暗怀心愿的人类,也在寻求着某种际遇与改变。
人与器物的命运与缘分,无论善恶,在踏入这扇门时开始。
欢迎来到徒然堂,
今天的你,也在期待着什么?
企划完结
填坑小组:http://elfartworld.com/groups/1381/?p=1




“玉指揽风风不住。茜纱窗昏。舟上摇波波不停,渡影重温。”玉梢拖长了尾调,唱着不知从哪听来的词句,仗着没人见得着自己,也就慢悠悠地晃过集市,找了家看上去就有些寒酸的茶馆。屋檐上滴着水珠,收起手上的油纸伞玉梢只听见雨滴声如同珍珠系数落地的声音,哗的一下全落在地面上。反弹起的那些晶莹剔透的圆点混杂着店面的倒影最终消失在骤雨之中。
将伞搁在桌边上,玉梢也不能指望店小二来问自己是不是要些茶点,自顾自的拿起已经凉了的茶壶往那白瓷青花的被子里倒。还未甄上半杯,那壶就空了。
玉梢也不在意,放下茶壶捧着没有温度的,甚至有些许凉意的杯子往肚里灌下一口茶。
寒意从口中一直线地路过背脊,浸满四肢,似是被埋入冰雪那般弥漫全身。
这天气,人来人往的谁都匆匆而过,又是下午时分,再过一个时辰恐怕是各家都要准备起晚饭来,店小二昏昏欲睡的,茶馆里清净得很,歌女早就已经回厢房歇着,为数不多的客人不是轻声细语地交谈诗词,就是独自坐在那和自己一样看人来人往。
“上元溪旁点荷烛,千盏承诺,怎奈雾锁红尘客。”玉梢没有再唱下去,雨声不歇,那几句词曲被淹没在雨滴和油纸伞之间不断的声响中。整个世界从那被漆红的门柱之间看去像是蒙了薄纱,行人在其中穿梭,用一把油纸伞挡开那料子匆匆前行。
怎奈雾锁红尘客,阴差阳错。
玉梢眯起眼睛,侧着头看那个姑娘。黑色的发梢滴着水,像是水晶的链子装饰着繁复清雅的发型,几片银杏样子的发卡也在闪闪发着亮,和树上长青的叶子那般泛着光,在雨水的打击中叮当作响。
她没有挡开那层薄雾,更没有匆匆而过,而是站在雨中等待那糖画师傅给她弄出个什么来。
可能是银杏。玉梢猜想着昏昏欲睡,思绪沉重地似乎是被什么软乎乎的被子压住了似得,无法挥去的像是被蜂蜜裹住了的粘稠感那般。
那姑娘转过身来了,手上拿着的是用糖浆画出的梅花,晶莹剔透,枝叶丰满,缀满了花苞。她也不急,慢悠悠地就走过来,玉梢一颤,对方似乎是看得见自己的样子,径直走来,也不避开人群,硬生生在伞花丛中劈开一条路。
那店小二听着有水溅开的声响便也醒过来,转头就看见那姑娘湿淋淋地坐在那。也是吓了一跳才想起来问问是不是要杯热茶。
两口热茶下肚,玉梢才尝出来这似乎是白茶。淡过头了,也亏得这店能营业到今天。
“你的主人呢?”
“无主。”玉梢答,手指抹了抹杯沿,看着里头的茶水泛起波澜,“名曰玉梢。”
“韩梅梅,道士。”
玉梢敲了敲桌面引来了那店员,梅梅配合地点上了一盆茶点,黄豆糕甜得恰到好处,咬一口再混着茶也算是一桩美事。
玉梢也不多说,捻起糕点往嘴里塞,她确实好事,但是又喜欢半途而废,毕竟活得太久,对新鲜事也只有一瞬间的兴趣了,多想想也毫无乐趣可言,也就成了今天这番有些麻木的样子。
“雨天还出来吗?”
“没人说过雨天不能出来。”油纸伞上的水珠已经形成了一摊水迹,缓慢地流向店外形成水迹,梅梅发丝上滴下来的水珠也一样在周围形成了一圈深色的印子,玉梢是担心这姑娘受凉,但是看着对方也丝毫都不在意的样子,便不去说些什么。
“你能看见我。”
“我能看见很多东西。”梅梅回答,撩起耳边垂下来的长发别到耳后,又给自己到了半杯茶水,“你呢,出来找什么。”
“这话可是暴露了你自己。”玉梢甩甩袖子,宽大的布料灌进风,这时倒也显得风流。
两人对坐对饮,也不是酒,但也有一句没一句地搭着话,从古至今谈论的东西从文化礼节到食物茶点,衣着样式到风流雅事。
“真的变了很多。”和她所知道的世界已经完全变了样子,自己心里所存在的那些稀松平常的东西已然成为了他人或唾弃或认为遥不可及的事物,就连那些平日里随处可见的住房今日也变为了古迹甚至不可寻的文字描述。
“朝代几经更变,你认识的东西已经不见了才是。”梅梅也无意嘲讽,只是实话实说,这些东西或许对于他人过于残酷,但是眼前这人倒是一点也不在意的样子,甚至兴致勃勃的想要了解各式各样的事情,一点也配不上那种清冷的气场。
“你也不像是刚才那样子。”玉梢点了点自己的发簪,“松了。”
梅梅闻言去扶自己头上的那些装饰,银杏的发簪有些落下来了,似乎是被湿了的发髻压塌的,她用力地往里头插了插,露出一截小臂,歪着头,收着下巴,眼角微微朝上,俨然一副美人图的样子。若是自己那时的被文人见着怕不是要夸赞一番肤如凝脂乌发如瀑才是。
“你在等人吗。”
“是啊。”
玉梢没有说下去,只怕这人在等的,是已经永远都不会回来的人,或者是已经回不来的人才是。
这世上有这种经历的人不少,但是也说不上有多少,至少就玉梢认识的人中,十有八九有着些不同常人的执着。
不过说来也是,自己本就是这样的一种存在,物以类聚,要是自己身边真的没有这样的人,那也说有些奇怪的,徒然堂的客人也好,器物也罢,那些冥器也好,清净师也罢,多多少少有自己的目的和愿望,不如说没有这种愿望的人实则少数。
“记得保暖。”玉梢沉下思绪,撑着脑袋去看那店门外的景色,裙角被打湿,水塘被搅乱,时不时听见有人抱怨秋风萧瑟凉意入骨,也听闻远处似乎是飘来琴声。
“老人已经到了要睡觉的时辰了吗。”
“不如你们小辈,总是那样神采奕奕不顾一切。年轻是好事。”
“长着一张少女的脸真能说得出口。”
互为独自一人的存在,伤痕累累,不知什么是人情世故更不了解毫无执着毫无牵挂的感受,只是增加着伤口,承受着周围人和自己的厌恶和视线。
血流不止痛苦万分,却依旧披着人皮长着人心混杂人群之中,孤独对于她们过于高贵,更多的,是无处安放的寂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