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うれし かなし
こひし にくし
想いは 万華鏡
さびし かなし
こひし にくし
絆は 蜃気楼
==============================
渴望,思念,孤独,怨恨……这绝不是人类仅有的感情
抱有欲念被主人抛弃的器物,在春秋时分,化为付丧神。
而暗怀心愿的人类,也在寻求着某种际遇与改变。
人与器物的命运与缘分,无论善恶,在踏入这扇门时开始。
欢迎来到徒然堂,
今天的你,也在期待着什么?
==============================
一期完结
小组http://elfartworld.com/groups/13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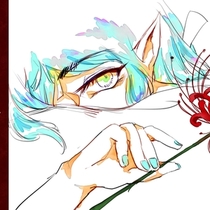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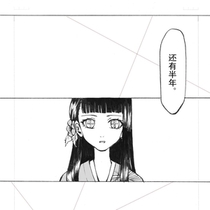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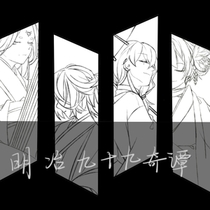
上接【http://elfartworld.com/works/139272/】
【這就又要打卡了……銜接用短章,文風文筆都次到爆炸,而且還短】
“付喪神?你接下來是不是要說自己討厭我,然後叫我把煙斗丟掉?我才不要嘞!”來幸原本就對對方不慎信賴,現在又加重了疑慮,“大哥哥,你要是坐夠了,就回去吧!”
對方露出好氣又好笑的神色來,這更叫來幸不舒服了。但為了不叫自己把情緒表現得太明顯,他給自己倒上一杯水。
“那倒是不會,我只是煙斗的付喪神。”閣樓的不速之客說道。
“唔……”來幸從身旁拿起來煙斗,仔細端詳了起來,“那我要是給煙斗添上煙草,你會不舒服嗎?”他說著用手指戳了戳煙嘴,再偷眼看著青年的反應,對方一臉平靜地看著自己。
“雖說我的身體也會因為煙草發燙,但因為煙斗本身就是做這種事情的,所以並不會覺得不舒服。”青年耐心解釋道。
“我該怎麼叫你呢……?”來幸又問,“叫你煙斗先生可以吧……?”叫煙斗聽起來有些生疏,單純叫先生也不太好,來幸便折中選擇了這個叫法。
“沒問題,反正我沒有名字。”自稱是煙斗付喪神的男人這麼說,“倒是你,竟然都不懷疑一下是不是真的付喪神嗎?”
“反正我這裡也沒什麼可偷的……”來幸說,隨即又想起煙斗本身的價格,他於是抱著裝古董的盒子緊緊不鬆手,接著又想起來一件事,“我可以給你取個名字?只有我能看見你?說起來,剛才村上夫人好像也沒看見你。”
“當然?”
“唔……那我想想吧,名字是很重要的。”
“隨便取個名字就好了……!又不是什麼名貴東西。”煙斗先生道。
“唔,不行,名字是很重要的。”來幸說道,“把外套脫下來吧,請您放在椅背上,我要睡覺啦?”來幸說著又攤開床鋪,把自己的古董盒子放在床頭,“對了……煙斗先生,我的名字是來幸。”
“嗯?是賴光的賴字嗎?”
“是未來的來和幸福的幸,幸福會到來的意思!好啦,我真的睡覺啦,晚安。”來幸說著脫下和服羽織和襯衣,給自己換上了寬鬆的睡衣,“煙斗先生,你要睡覺嗎?要睡覺的話就和我擠一擠吧!”他拍了拍身旁的床鋪,自己率先鑽了進去。
“不用,我不需要睡覺。”
“不許把煙斗拿走!”來幸嘟囔著,給對方騰出來位置,“晚安。”
“晚安。”來幸看到煙斗先生坐在桌前,好像獨自思考什麼似的。閣樓昏暗的燈光勾勒出成年男子背影的輪廓。叫他什麼呢,來幸想著,但比起那些,今天發生的事情實在太多了,他的頭一靠上枕頭,疲倦感便輕柔地灌溉過身軀。
算了,明天再想吧。他迷迷糊糊地告訴自己,墜入了夢鄉。
夢裡,他夢到煙斗變成了煙斗先生,然後又變成了一道鎖。他看到在津山的老家的大門被那把鎖牢牢地鎖上了。
逃走吧!那道鎖向他喊道。逃走吧!
隔天早上,他醒來後就忘掉了這件事,滿心想著又要去工廠工作了。煙斗先生已經不見蹤影,不知道是去哪兒了。果然是夢……啊!不對!來幸慌張地打開床頭裝著古董的盒子,看到煙斗還在裡面,忍不住鬆了口氣。他收拾了一番書桌上凌亂的文稿,把之前寫好的稿件裝進信封裡。再蓋上昨天忘了收拾的墨水瓶。
收拾好這些之後,他換上上工時穿的衣服,戴上帽子,正打算離開自己的小閣樓,卻看到黑髮青年站在閣樓門口,手裡端著熱騰騰的米飯。
“不吃早飯?”
“唔……是該吃。”來幸喃喃著,又坐下來,“我先吃一點……”
“慢慢吃吧。”煙斗先生將米飯端上書桌。久別故鄉,來幸還是第一次在東京被人服務。他有些不知所措地拿起筷子,扒拉起來米飯。
“對了,我要去投稿,”來幸想起來什麼似的,突然說道,“祝福我吧!”他吃完最後一口米飯,抱起自己裝著文稿的信封,慌忙地逃走了。
窗外,春季的綠意才初綻頭角。

“阿啾!”來幸搓了搓自己的鼻子,“感覺好冷啊。”他把被子裹得更緊了一些,愜意地窩在枕頭上看著煙斗先生在書桌前工作的背影。這個噴嚏也沒能破壞他今天在和煙斗先生散步回來的好心情,他吸著鼻涕,悄悄在心裡回憶今天所見的景象,好像等不及要將那片被燈光照亮的櫻花寫在稿紙上了。
“都說了要穿大衣,這不是感冒了。”煙斗先生的背影與書桌上的燈光融成一片。來幸瞇著眼睛,迷迷糊糊地向對方說話。
“不是穿了嗎!這肯定不是感冒,而是被人掛念了……”
“哦?這是被誰掛念了?你父母嗎?”煙斗先生在桌前活動了一番筋骨,甩甩他的手腕,“買點別的東西吃吧?老吃米飯可是會得腳氣病的。”
“說是那麼說,可是沒錢啊。對了,煙斗先生,你覺得愛戶嶺這個名字怎麼樣?”
“還不錯,挺好的。”
反應太冷淡了吧,說說喜不喜歡嘛。來幸失落地摸了摸枕頭的一角,有些埋怨起煙斗先生對這般重要事情的冷淡。這可是我想了很久的名字呢……
“真的?那我就這麼叫你啦。嶺先生、愛戶先生……adore!”他在最後大聲說出來他在那個名字裡面所埋藏的意義,期待起對方的反應。
煙斗先生——現在是愛戶嶺了,在桌子前抖了一下。
“小孩子……別亂說。你知道那個詞是什麼意思嘛?”
“當然知道啦,不僅知道,我還要告訴我的名字來幸可以念做英語的like。”來幸說完,又開始為自己在外國人面前班門弄斧自己那夾雜著日本方言口音的英語後悔。他側過身去,好避開煙斗先生的反應,“睡覺了睡覺了,晚安,嶺先生。”
“晚安。”
“嗯,晚安……”
“怎麼了?”
“睡不著……!”來幸又翻了個身,他看到嶺從桌前起來,走了過來。
“我來給你講睡前故事。躺過去一點。”
來幸乖乖給對方讓出來能坐的地方。嶺俯下身坐下,不知道在想些什麼,遲疑了頗久。
來幸催促道:“快講吧快講吧。”
“那是挺久以前的事情了……某個男人生來就有作為榜樣模仿的長兄,還是說算不上長兄呢?總之對方是個值得尊敬的人吧。這就是故事的開端。”愛戶嶺緩慢地說著,來幸看到嶺那雙溫柔的眼睛在煤油燈下閃爍著十勝石般的光芒。不知名的火燃燒起來了,來幸抬頭看向自己的書架,正好瞧到放在書架頂部、好好保存起來的煙斗。
“他被當做長兄的替代品,被人們冠上了長兄的名號,名跡流傳於世。自己做過的事情也好,自己沒做過的事情也好,全部都被賦予了長兄的人生才有的意義。貴族,商販,平民,農人,奴僕……”
“長兄現在在哪裡呢?”來幸插嘴道,期待地等著故事的後續。
“不是這樣的,他的心裡有一部分在那麼喊著。我是不同的,我應該是與那個人不一樣的……然而,並沒有任何人理解,甚至連他自己也沒法說出口。被人期待的感覺總要比不被人期待的好。他就這樣與人們維持著若即若離的關係……然後啊,某一天,叫著兄長的名字的人們請求男人道。”
來幸聽到了自己的胸口傳來砰砰的心跳,愛戶嶺輕淺的呼吸聲穿過厚重的棉被,送到他的胸口。他的眼睛透過愛戶嶺的話語,看到了那個年輕、被人們誤認為是兄長的男性。
被人當做他人的替代品,一定是很痛苦的事。
“‘你能為我們做一件小事嗎?’比起來請求,人們的語氣更像是在質問,‘如果是你的話,一定能更懂得如何討好權貴?如果是你的話,無論是怎樣的貴族婦人,都會忍不住瞧上一眼吧?如果是你的話,一定能很快地籌到足夠的錢吧?’……人們這麼說著,將他推上了高臺。”
“或許他曾經還說的上是討權貴喜歡,也或許他的樣子還算引人注目,但是只有那件事……只有金錢,他是確實做不到的。就這樣,他最終與人們失之交臂。意識到男人並非是兄長的人們,就這樣撤開了雙手……無論如何曾經努力去扮演他人,那個人最後還是沒有辦法討人喜歡。”
來幸看到嶺的雙眼被一團不定性的霧靜悄悄地凝結。而後,一種令人不安的瘙癢抓住了他的胸腔。自己並不了解愛戶嶺啊,他意識到這件事,感到自己之前的想法淺薄而愚不可及。對方不叫愛戶嶺的時候、對方不是自己的煙斗的時候、對方擺在貨架上的時候、對方擺在貨架之前的時候,這些全部都是松平來幸所不了解的。
“就這樣,他被遺忘在那裡,經歷漫長的等待。隨後,故事結束了。”愛戶嶺吸了口氣,揉了揉來幸的頭。力道很輕,但能感覺到對方的手指傳來的些微溫度。
付喪神也是有體溫的啊。來幸想。愛戶嶺沒再說話,只是為他掖上了棉被。
“嗯……”來幸想說點什麼,但他知道對方并不期待自己的話語,那股叫他覺得模糊而難以言說的感情,僅僅通過吞嚥的動過就能從舌尖上壓下去了。最終他鼓起勇氣,輕輕拉住對方的衣角。
“我可以要晚安吻嗎?煙斗先生?”他問。
“你幾歲了,小孩子一樣。”
“那麼,我可以給你一個晚安吻嗎?”來幸又問。
“請吧。”煙斗撩開了他額頭上的劉海。來幸象征性地、像母親對待自己那樣吻了嶺。
“我睡覺了,晚安。”來幸滿意地看到煙斗揉搓著頭髮,給自己捧起來自己的鼻子,“希望明天我的感冒就好了。”
感冒並沒有在第二天消失,反而更嚴重了。
來幸感到自己的喉嚨被一團什麼東西堵住了,一團病怏怏的氣還在向下走,頭腦也不怎麼清楚。狹小的房間在來幸看來就像燃燒來了一般扭曲,身體也是,無論是不是裹了被子,還是不停發冷。這種不適感催生出一種惰性,讓來幸不想起來。大概是發燒了吧。來幸想。
他很熟悉這種情況,每逢生病,最後都會發展成這樣的局面。雖然說不上什麼大問題,但父親就是以這作為來幸體弱多病的依據,不讓他出門。
不想起床……但還是要去打工。來幸想著,還是強迫自己起來穿好衣服。不工作的人沒飯吃。他提醒自己道。
“嶺,我出門了。”來幸向著在書桌前不知道在鼓搗什麼的嶺說道。
“你的嗓子怎麼啞了?”
“好像嚴重了一點。”來幸咳嗽了一聲,戴上自己唯一一頂帽子,“怎麼樣,戴得正嗎?看起來像不像紳士?”
“你先別去工廠了。”他聽到對方的腳步聲近了——一隻大手覆上他的額頭,付喪神的體溫傳達了過來,“你發燒了。”
“不行。好不容易找到了要我這種人也能賺錢的地方,不去工作怎麼行。”來幸嘟囔著,輕輕推開對方的手。腦子亂成一團,“我走了。不吃早飯去還來得及。”他給自己套上大衣,在地板微弱的傾軋聲中匆匆出了門。嶺原本想攔住他,卻被他躲開。
“真的別去了!”
來幸不知道為什麼有些窩火,或許是胸前那團叫人難受的霧氣讓他開始迷蒙了。他躲過嶺,快不下了樓梯。村上太太還在和家人吃早飯,並沒有注意到他。來幸就這樣上了街道。
路上的行人也變得不識相起來。來幸穿過擁擠的人群,但卻屢屢碰到陌生人的手背。七點的最後一班車算是勉強趕上,來幸和其他乘客擠在一起,等待火車慢悠悠地邁向洋火工廠。
像往常一樣,工廠的大門敞開著。製作洋火並不需要什麼技術,來這裡工作的工人多半像來幸一樣,沒有什麼長處。這份工作也收入低微,但比什麼都沒有要強一些。來幸回想起自己在逃出家門前曾經幻想的生活,雖然原本也曾預想過東京的生活會很苦悶,但多少對外界保持著一絲少年幻想。計劃總是高於現實所能帶來的境地。
他坐在桌前,包裝著火柴。工作單調又無趣,所有步驟只是像不停地向前滾動車輪一般運作。他擦拭了一會兒額頭上的汗,工廠很嘈雜,卻聽不到人聲。來幸在昏暗的燈光下分好火柴,他感到自己的頭腦緩緩下沉,如同浸泡在水中。
越來越冷了。
“怎麼沒精打采的?”來幸聽到身旁傳來了工頭的聲音。起初,他沒能明白過來對方是在和自己對話,直到成年的人手拍了拍他的肩膀,他才想起來。
“我不知道,可能就是狀態不好而已……”來幸聽到自己那有些刺耳的嘶啞聲音,唯恐對方識破了拙劣的謊言。
“感冒了,先回家去吧,明天好了再來。”
“可是工作……”
“我和他們說一下,不會扣你的。其他人能幫你做了你的份。”
來幸有些不知所措地接過這份好意。他支支吾吾地謝過了對方,帶上自己的隨身物品離開了工廠。不知為何,得到了對方的承諾讓他的腳步變得輕快了起來。現在還未到來幸平日下班的時間,街上冷冷清清,見不到什麼行人,只有出來買菜的家庭主婦在被樹蔭遮蔽的小道上閒聊。
回到村上夫婦的洋宅時,來幸想起他早上對煙斗先生生了悶氣。希望煙斗先生他不在意才好,要是他生氣了,就對他說抱歉。來幸這麼想著推開了洋宅的門。
愛戶嶺在樓梯上等著他。
“怎麼回來了?”
“在工廠裡叫人趕回來了……”來幸有些不好意思,他已經能想見對方笑起來的樣子。
但煙斗只是搖了搖頭:“我就說你這樣不行吧。”
來幸支支吾吾著上了閣樓。他脫下大衣和帽子,上了床。嶺叫他快點睡覺,自己則去樓下做了些什麼。身體還是很冷,但已經比早上時舒服不少。來幸裹著被子,迷迷糊糊地想到——煙斗先生是沒法被人看見的。隨後,他就在昏昏沉沉的知覺中睡了過去。
再次醒來時,愛戶嶺正坐在來幸身邊,讀著不知什麼報刊。閣樓的頂部傳來被雨水敲擊的一串聲響,嶺點了燈,讓室內還算明亮。
“燒已經退了不少,要喝水還是喝粥?”
“喝水。你會被別人看到的,想想一個水杯憑空移動向閣樓,那樣我就要被當成妖怪啦……”來幸嘟囔道,卻還是接過嶺遞來的水杯,小口喝了起來,“煙斗先生會生病嗎?”
“會吧?沒病過,所以我不知道。來,吃藥。”
來幸感到自己臉上燒成一片,他囫圇吞下嶺拿來的藥,靠坐在床上。他想象屋外的雨水打在屋瓦上,又跳起來,最後全都匯聚成涓涓河流,滲到地下去。
“好好躺著,買藥拿的是你的錢。”嶺又說道。
“那就好,不然我會愧疚的。”來幸聽從對方的指示,安靜地躺了下去。
“我也沒錢啊。”
“我知道啊,不是我在養你嘛!”
“好好,你厲害,你可厲害了。”嶺應付似的說道,來幸卻分明看到對方的嘴角掛著笑意,“快睡吧,吃了藥馬上就會想睡的。”
“我這不是在躺著呢嗎?嶺好像媽媽哦。”
“是嗎?應該是爸爸吧。”來幸聽到水杯被放下的聲音——然後是翻找書桌的聲響。
“不要爸爸。”來幸小聲說道,他拉上被子。閣樓的燈火還亮著,從書桌那邊傳來鋼筆莎莎的聲響。從閣樓狹窄的窗戶那兒,淌進來了半遮的月光。
“那我就當媽媽吧。睡吧,我就在旁邊。”
“嗯!”來幸窩在棉被裡,“晚安,我可以要晚安吻嗎?”
對方停頓了一下,來幸閉著眼,想到自己的要求或許太過分了點。他聽到自己的呼吸已經歸於平穩,身體也沒那麼冷了,到了明天,感冒或許就好了吧。他盡情享受著被對方照顧的這刻,直到感到額頭被對方蜻蜓點水吻了一下。
潮水般的暖意吞沒了意識。
“都多大人了還要晚安吻。”他聽到愛戶嶺這麼笑道。
*镜真名 出道准备!(假的)
*第三人视角(真的)
*假面舞会paro(真的)
我想我需要习惯这种舞会。
自诩高贵的人们在这里汇集,用大同小异的面具遮住自己的面容,也一并遮住了身而为人的廉耻心。虚荣敦促他们去猎杀更多拥有绚丽羽毛的禽类来满足他们的攀比比赛,那些尾羽晕染出不同的诡异的色彩,与酒杯晃出的光搭调至了一种极致。而掩在华丽羽衣之下的东西,我更加不愿去想。
我就像我的目光一样在这个臃肿的舞会中游荡着,等待着午夜的钟声敲响,将这些醺醺然的人们打回人性的原型。然后,我便看到了那个男孩。
那是在雄雉尾羽后面露出来的少年人清亮的眼睛。
他刚好处于那暧昧的阶段,他的身子在拔高,眉眼渐渐有了属于成年男子的味道。可当他转过眼来看着你——鹿一般的眼睛,湿润的,清澈的,漂亮的一双眼睛——你又会不由自主地对他心生怜爱。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小孩子。可他在人来人往的舞会中的表现堪称完美,一举一动都带着熟捻。
大概是哪家的少爷,带过来增长见识,同时也是一次扩展人脉的机会——孩子总有一天是要长大的。
我看着他悄悄支开跟着他的侍者,装作若无其事地向着另外一位侍者要了一杯酒。虽然在他喝下第一口后,他微妙的表情便暴露出了他的真实年龄,但那小孩子特有的小狡猾与小机灵还是很让我开怀。
他的言谈举止还处于那种多看几眼便能猜得一清二楚的程度,但足够让人想起自己年轻时做过的那些蠢事,并且对那些不可回头的岁月报以会心的一笑。
在我将要移开目光的时候,男孩做了一件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情。
他在邀舞之前摘下了他的面具。那再无遮掩的年轻脸庞便锋芒一样地露了出来,一瞬间让全场都瞩目。
我能在纷杂的眼神中辨别出不同的情感:惊愕,欣赏,戏谑,玩味,疑惑……这些视线如同无数直线,从不同的起点共同指向了一个中心。然则中心——他却相当自在。在邀舞对象将手放在他掌心的那一刻起,他就踏着节拍步入了舞池,兴致勃勃地参与进了舞会,享受着舞会的乐趣——真正的舞会的乐趣,而不是无所事事地拿着杯子,对着认识的人牵扯起嘴角的肌肉。
我被这样率性的行为所深深震撼了,他就这样表达着自己,这样直接又冒失,他究竟是怎么想的?
我终于没有忍住,在他一曲舞毕后走到了他的身边搭话。他回应的话无可挑剔,连用词都格外的令人神清气爽——那是一种恰到好处、点到即止的礼貌。那些曾经被谄媚包裹着的词语在他的言语里终于回归了本真,好像终于被雨水洗去油腻尘埃的草木。
“这是假面舞会,你怎么摘掉了面具?”我与他闲聊了几句,便再也按耐不住自己的好奇心。
“难受呀!”他的回答倒是和他脱面具的举动一样利落简单的。
“多戴戴不就习惯了。”他答得太过于干净迅速了,以至于在我反应过来之前,我的嘴巴就不自觉地说出了这样的话来。我吓了一大跳,却不知道怎么弥补。可这曾经是我最为厌恶的话了,旁观人给出的建议总是这样轻松的,我怎么就下意识地说出了这样常见的话?
他倒是不介怀的样子,歪着头问我:“先生在小时候便习惯这样的面具吗?”
说老实话,佩戴这样的面具跳起舞来并不好受。有时候汗水流淌在脸上,那些硬的材质便与它们一并粘在脸上,难受到令人窒息。
“总要习惯的呀……”我没有正面回答他。
“如果有人不想习惯呢?”他用小叉叉着水果。“有人”指的是谁也太显而易见了吧!
“那对舞会来说可是坏习惯……”轻松的话又滑出了我的嘴角,“坏习惯总要被丢掉的……”
他三两口吃完了剩下水果,摩拳擦掌地看上去像是想参与下一轮的舞蹈。
“可是‘这样’为什么就算是坏习惯了呢?”他看上去思考了一下,又在我说那些长篇大论之前打断了我。
“如果‘这样’是坏习惯的话,”他在转身的前一刻与我说,“那我还是不丢掉的好。”
“这……”我这是被一个小孩子说懵了吗?只好冲着他的背影说着,“总会丢掉的……”
“才不会丢掉的呢!”他回过身来,朝我做了一个鬼脸。这个在成年人的世界里一直彬彬有礼的男孩终于在我面前露出了一点属于小孩子的神情。
我在这样的神色前不禁失了神。我越为这神态闪现的光芒而震撼,便越对这样的神态心生向往,可与此同时,我的心里也越发惧怕起来。我太了解我失去了什么,就好像我对已逝的青春年华置之一笑一样,我对那些我所抛弃的、丢失的东西,也只会是缄口不言——就比如毫不畏惧地在精心伪饰自己的人群中摘下面具,将那些属于大人世界的东西用手远远地扔出去。
我难以不把我曾经经历过的套到小辈的身上去。这个孩子,他此刻所展现的东西愈耀眼、简单、干净,愈让人喜欢、怀念,便愈加让人对他往后可能会遗失这种光芒的未来感到遗憾。单单是想到这样的结局,我就已经变得麻木了起来。
一阵密集的爆响把我震了回来。我动了动长久捏着酒杯而僵硬的手指,看着重新闯入舞池中的少年。他此刻的舞姿已经不适用于“翩翩”之类的形容词了。那是踢踏舞。舞步和他的说话方式一样漂亮,带得整个舞会的气氛都变得欢快起来了。
哈!我算是知道那个鬼脸是怎么回事了,他绝对是和演奏舞会曲目的人说好了,要在成熟的悠扬之中插上一脚。
舞会中的人们面面相觑,这下就算面具遮着也能知道每个人的表情了。谁会想到假面舞会会有踢踏舞表演的一天?表演者的脚步呼应着曲调,毫无规则而充满着欢快,他摇晃着自己的上身,挥舞起来的手臂像是天鹅一样。
在这个充斥着禽类羽毛的地方,可能只有这个少年才能真正飞起来吧。
这样的孩子,就算失去了什么东西,也会奔跑着找回来吧。
在我所不习惯的假面舞会里,我戴着我的面具,看着舞池中唯一没有用面具遮挡面容、正发出欢快笑声的少年,默默地想着。
注:
明治时期踢踏舞尚未传入日本,写的时候觉得这种舞更适合表现人物性格便选用了,不妥之处望见谅。
=
麻木着失去的“我”与青春飞扬的镜家少子的对比。
镜真名大概是春夏交界时的孩子,和灿烂的阳光与清爽的风一样美好。
“愿你永远是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