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うれし かなし
こひし にくし
想いは 万華鏡
さびし かなし
こひし にくし
絆は 蜃気楼
==============================
渴望,思念,孤独,怨恨……这绝不是人类仅有的感情
抱有欲念被主人抛弃的器物,在春秋时分,化为付丧神。
而暗怀心愿的人类,也在寻求着某种际遇与改变。
人与器物的命运与缘分,无论善恶,在踏入这扇门时开始。
欢迎来到徒然堂,
今天的你,也在期待着什么?
==============================
一期完结
小组http://elfartworld.com/groups/13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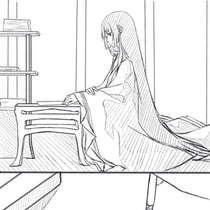
※是一个很失败的临时卡,截了前半剧情,大概还有在好好谈恋爱的6000字
※就算是出场很少的临时打卡我也要艾特阿式!!!!(有病啊
※终于和小一互动了一把!!!开心!!!
※卡文+摸鱼+论文导致没办法写到和黑崎老师的互动了所以先不响应,正式打卡会重新响应的对不起请让我保个命再说(土下座)
※其实黑崎老师是有出场的请猜一猜(不要玩
※wtf仔细一看我居然没有关联剧情,多次响应真的很抱歉!!!(被自己蠢死)
时间走过梅雨,走入六月。
平时从二楼望下去,院子里的樱树褪去了淡妆粉衣,徒然自碧。石榴花灼灼如火,紫丁香缀了满枝,还有更远处的常青枞树,近观远眺皆是行过立夏的明艳秀色。
只可惜今日天气不佳。云层厚重,悬悬欲坠。
纵然从云隙间渗出了些微光亮,也像是不溶于水的油渍,虚虚地透进来,不曾落下。
花叶黯淡了。如此光景不禁令人横生焦躁。
真黑静静地看着窗外的景色。她是决计不会感受到这些情绪的。于她而言,也不过是淡淡一句“要下雨了”。
要下雨了。
女性转过身去,面前门扉半掩。隔过一条幽静的走廊,对面的门正紧闭着。
若是凉子要出门的话……
思绪还未落地,青年的呵斥与少女的叫喊便突兀在廊下爆炸开来,紧接着,一抹倩影从隔壁摔门而出,急急冲下楼去。砰的一声,青年焦躁的面庞在真黑眼前一闪而过。
“凉子,你要去哪儿?!给我站住!!”
“用不着你管!!”
脚步声又急又重地滚落楼梯。
真黑遂提步上前,打开门来。恰在此时,隔壁房间的门也被再度打开。她心下一惊,忙收了半步。
青年从房内追出,视线掠过她,正常地穿了过去,并未投落在她身上。他刚跑出几步,却又停下了步伐,立于廊下,再没有任何追上去的迹象。
片刻,风推搡着被他焦急旋开的门扉,轻轻一响,缓缓合上。
他深深埋下头去,拳头重重砸在墙上,撞击发出的闷响迅速掩去了短暂而压抑的男声。
“……该死!”
爆炸随即停息,硝烟也同他的话语一起散尽。暗淡的沉默里,走廊尽头的窗外漫进了异常明亮的光。涨潮似的冲刷过地板,却始终无法触及他脚边。真黑注视着他,看他抬起头来,和少女相仿的眸里卷起了悲哀的浪。
——真黑。
忽听得少女的呼唤,真黑回过神来,和青年擦肩而过。
若是凉子要出门的话,得备把伞才是。
她如是心想。
少女径直走上街头。
起初是大步流星,每一步都狠狠地踩下去,脚底隐隐作痛。
“十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为什么会遭遇‘神隐’?你们为什么要隐瞒我?”
“……你不必知道。”
又不知不觉放慢了步速。
“我难道连知道过去的权利都没有了么?”
“凉子,我知道你长大了,但是有些事——”
终究停了下来。来往的过路人行色匆匆,几欲逃离头顶的雨兆。随后,脸颊感受到了第一滴清凉。似是无声的号令,点连作线,线再成面,天地顷刻灰茫一片。
熟悉的伞面阻隔了雨意。
她愣愣地转过头,看着真黑平静的面容,扯了扯嘴角,哑声道:
“……还好有你在。”
“那我究竟要多少岁才能知道?哥,总有一天我会去面对这些事的,难道你要等到那时候才肯告诉我真相吗?”
面对她咄咄逼人的质问,青年只是缓缓闭了闭眸。
“对,”他沉声答道,“如果真有这一天的话。”
雨脚如麻,打落花瓣几许,任其躺上泥土,化作花泥,消逝无踪。白光自天际掠过,翻涌的云层间,雷鸣滚滚。
“……够了。鹿又诚一,我讨厌你!!!”
开门声断了回忆。从门内出现的男人微微一怔。少女抿了抿唇,绞尽脑汁却挤不出话来,只好鞠了一躬,揪着衣摆低声说:“十文字先生,拜托您了,请让我……暂住几天吧。”
政纯瞥过持伞的真黑,敛了目光,抬手虚揽过少女的肩,将她接进屋去。
“不急,鹿又小姐,不妨先洗个澡,去去湿气吧。”
再碰上她恳求的眼神,男人也仅是淡淡一笑。
“房间很多,不必担心。万一着凉了可不好,我待会让夜半给你泡杯茶。”
“……谢谢,麻烦您了。”她再鞠一躬。
她永远也无法忘记,那时鹿又诚一露出的表情——像一只身负重伤的狼。鲜血汩汩从患处溢出,而他只顾呆滞地瞠目,回不过神来。
手握枪支的是她。
扣下扳机的也是她。
因此,鹿又凉子狼狈地逃走了。
◇
八百屋晓之助站在大门前。漆色有所剥落的墙壁上挂着一方略显年头的名牌,上镌“鹿又”二字。他挠挠头,伸手按过门铃。自身的紧张似乎通过指尖的按压传进了铃声里,隔着大门听来,闷响里还带着颤音。
他也不知道自己在紧张个什么劲儿,明明只是受人之托来取些东西。
门开了。晓之助几乎是在看见来人的第一秒便挺直了背脊。
而来人抬眼,微一瞠目,愣神片刻后竟叹了口气。晓之助困惑地眨眨眼,心说政纯先生不是在电话里说过他会来的么,怎么——又见屋内人摆了摆手,苦笑道:
“抱歉,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是来取凉子的衣物的吧?给。”
“……啊,嗯,谢谢您,鹿又先生。”
晓之助赶忙接过布包裹。
“这里面是一些轻便的夏衣,还有些给她的钱。”鹿又诚一再递过手中的信封,“这是给十文字先生的钱。请你帮我转告他,舍妹这几天,还得请他受累多关照关照。”
“好,没问题。”
晓之助又接过信封。
他本欲就此告别,却见诚一缄口不语,一直盯着他怀里的布包裹看,便探问出声:
“鹿又先生,请问您……没事吧?”
鹿又诚一忙回过神来,重重叹了口气,摇了摇头。
“没事。……凉子她,她……没着凉吧?她出去以后下了雨,要是——我忘了,她把伞拿走了。应该没有淋着雨,是不是?”
明明是极简单的问题,晓之助却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他捏着手里的布包裹,想起了临走前凉子无精打采的模样,缓缓点了点头。
“您不用担心。”
诚一揉了揉太阳穴,疲惫地叹道:
“……那就好。”
晓之助望着他。此时的鹿又诚一早已失了往日的光采。
晓之助印象里的这位兄长,即便在家也是温雅自制的姿态,头发打理整洁,衬衫熨烫妥帖。尽管在对待晓之助时态度会强硬起来,还眼含戒备和提防,但绝不会是现在这样——
这样憔悴狼狈的。
思及此,晓之助竟不知说什么才好。
“哥哥,哥哥,凉子姐回来了吗?我想和凉子姐玩翻花绳呀。”
这时,清脆的童音打断了思考。
小姑娘扒着诚一的裤腿,从他背后探出身来,努力仰头望着自己的哥哥,攒着眉头认真地问:“凉子姐为什么还不回来呢?快要吃晚饭了啊!”
诚一俯身抱起了杏子。低下头去时眼神仍是无奈,直起身来时便被笑意填满。
“凉子去朋友家玩了。”兄长温声回答,“过几天才会回来的。杏子忘了么?”
小女孩嘟着嘴,奶声奶气地说:“可我想她了嘛。”
“杏子乖,一会儿哥哥陪你玩。”宠溺地揉了揉杏子的小脑袋,诚一再度看向晓之助,“那就麻烦你了,八百屋君。”
晓之助愣了愣,无意识地张了张口,又作罢,紧了紧怀中的包裹,点点头。
“大哥哥再见呀!”杏子挥挥手。
这张缺了门牙的灿烂笑脸也终于驱散了徘徊在两个青年之间的沉重气氛。晓之助忍俊不禁,心中莫名的阴云随之散了些。
归途里,路旁的水洼碎了晚霞。
轻便的夏衣叠几叠,用布细心包上一层。晓之助反复掂量着包裹的重量,想起了离开鹿又家前,自己未曾付诸口中的话语。
——有什么我能帮忙的么?
答案或许是不言自明的。当他在走廊上再度碰见诚一挂念的少女时,心底竟蓦地生出了一片混沌不堪的沼泽。
“……谢谢您。”凉子紧紧抱着包裹,向他鞠了一躬,“真的谢谢您了,八百屋先生。”
“没事。鹿又先生他,十分担心您。”
“……嗯,我知道了。谢谢您。”
她垂眸低声道谢,然后转身欲走。
“——鹿又小姐!”
一时冲动喊出声来,却在她诧异的回眸中失了言语。一番挣扎后,晓之助只能认命地摆摆手,搪塞地笑,“……没事。”
于是,隔过凝翠欲滴的庭院,少女孑然的背影就这样渐行渐远。
——有什么我能帮忙的么?
——大概是……没有的吧。
那片名叫“无能为力”的沼泽旋即吞没了他。
◇
这天,十文字家的晚饭从惯常的菜品突然升格为寿喜烧。
对于这个决定,展颜者有七,欢呼者有二,叹气者有一。且不论振臂欢呼的阿式和作头疼状叹气的十文字政臣,当晓之助瞥见凉子——被绘梨佳指摘“女孩子就应该多穿穿不同款式的衣服”,然后强制换上了绘梨佳的洋服——之后,原本淡定的青年顿时像被扔进了寿喜烧的锅里,再咕嘟咕嘟几声就熟透了。
这下免不了被阿式和政纯一顿调侃,就连政臣也笑眼添上几句,最后,晓之助和凉子各顶一张大红脸入了座。
“唉,年轻可真好啊,你说是吧,政臣?”
“别把话头抛给我。绘梨佳,怎么不动筷子?”
“嗯——吃太多牛肉会不会胖……”
“鹿又,吃寿喜烧就是‘得牛肉者得天下’!你看这次牛肉这么高级,不多吃点可对不起家主啊!”
“好。可是式先生,浅原师傅他吃素呀……”
“我没事的。谢谢鹿又小姐关心。”
“咦,我刚才想吃什么来着……真黑,你知道我刚才想吃什么不?”
“……给。”
“哎呀,原来是魔芋,阿晓你真好!不过你怎么还红着脸——嗳,我错了,别抢我的牛肉!”
……
这顿丰盛的晚饭就在热闹如斯的气氛中圆满结束了。
如果不算上政纯突然抬头、以恍然大悟的语气说出的那一句“哎,我忘记一月今晚要晚些回来了,谁能给他留片肉?”的话。
夜幕茫茫,虫鸣此起彼伏。偌大的十文字宅邸里,住客们各怀心事。立于廊下望去,光暗几许。
下了楼梯,来到转角,庭院在眼前勾勒出模糊的影。白日里的红树绿柳、乱石清池,到了此刻也只剩轮廓,在走廊旁的石灯幽微的光萤中,或睡或醒。
突然,清晰传来的交谈声制止了他再前进——听上去是夜半和凉子。晓之助没有走出去,任由阴影落了满身。待夜半辞别后,他才回过神来。紧接着,方才还在和少女交谈的男声忽在耳边响起。
“……晓之助大人?”
青年“做贼心虚”地缩了缩肩,“抱歉……我不是有意偷听的。”本还想再说些什么,却见夜半眨眨眼,抬起手来,做出了一个“请”的手势。晓之助只好循着望去,恰巧和少女好奇的目光撞了个正着。
她朝他点点头,轻笑了笑。
石灯的光亮将她的身形描摹得越发单薄,仿佛坐在廊缘的只是一道虚影。
晓之助心下一动,向夜半微一颔首,然后大步走了过去。直到同她并肩坐下,他才猛地回过神来,慌忙想解释,又被她问得一怔。
“我哥哥他,有没有说什么?”
他打量着她的侧脸。
“鹿又先生他……很担心您,问我您离开家之后是不是淋了雨。呃,包裹里的钱也是他备的,抱歉,白天我忘记说了。”
“没事。我看见了。谢谢您。”
她垂下眼帘。
晓之助张了张口,旋即吞下了话语。
事实是,他既没有立场去询问这对兄妹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因何争吵,亦不知自己能帮上什么忙。
分明近在咫尺,却又远隔天涯。
虫鸣刺耳而聒噪。晓之助低下头去,看着自己屈起的十指,慢慢放弃了挣扎。
鹿又凉子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负罪感压得她几乎喘不过气来。
她料到会有冲突,可没想过会演变为争吵;她深知自己要冷静,记忆缺失带来的焦躁却远超她的想象,轻而易举便控制了她的情绪。
而此刻,她正坐在陌生的屋檐下,茫然、徒劳地悔恨着“如果当初”。
独属于这幢大宅子的喧闹蛰伏入夜了。虫子们欢呼高歌。石灯仍在挣扎。
她不愿就这样独自沉入夜色之中。
她不愿,可是,又有谁能——
身旁一阵轻响。凉子抬起头来,看见站起身来的晓之助挠挠脸,似乎很不适应地皱眉笑了笑。
“我在这儿估计打扰到您了吧,该传达的事我也说了,我就先回去了。鹿又小姐也早些睡,熬夜对身体不好。就这样,晚……”
“——别走!!!”
她抓住了他的手。
不属于自己的温度吓得少女又慌忙缩回手去。
“别,别走……啊,我是说,请不要离开,不,不对,应该是……”
凉子慌乱地组织着语言,在他震惊的注视中越发埋下头去,最后业已无法成声。
她有什么资格留住他?以什么立场留住他?凭什么、为什么、如何能留住他?
大脑混乱极了。凉子不知还能说些什么,更不敢抬头看他现在的表情。
须臾,近在耳际的男声小心翼翼地,敲了敲她的心门。
“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么?”
凉子错愕地抬起头来,撞进晓之助的眼里。
“能不能请您……再多呆一会儿,一会儿就好。”
他笑了。
“好。”
◇
那晚,她梦见了凌云阁。
周末的徒然堂总是会较往常热闹些的。陌生的面孔纷至沓来:娇俏的、婀娜的、娴静的女孩子们三两聚在桌旁,也不乏只身入座的男女,或是专心阅读,或是欣赏音乐。咖啡与红茶的香气在鼻间缭绕,凉子晃了晃脑袋,须臾,她听见了清越的女声。
“鹿又小姐,您的红茶。”
绘着花枝的茶杯清脆一响。
“谢谢。”凉子抬头笑,“周末这么多客人,您辛苦了。”
“谢谢,不过我也习惯了。热闹点儿也好,最近熟面孔越来越少了。”
微啜一口,凉子问:“会觉得寂寞么?”
“的确会有点,”虚方苦笑,“这两天七原小姐也不来了,歌丸也神出鬼没的,不知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七原。凉子眨眨眼。有些陌生的姓氏。
“哎呀,您瞧我,说这些太不礼貌了。”虚方轻拍脸颊,然后向凉子鞠躬笑道,“请慢用——真希望八百屋先生能快些来呢。”
“……嗳?”
话音刚落,长发女仆便巧笑瞥过凉子对面的空位,递了个意味深长的眼神,随即步伐轻快地离开,独留了悟的少女兀自闹了个红脸。
“……真黑,我总觉得最近大家老爱开我和八百屋先生之间的玩笑。”
凉子鼓着脸颊愤愤说。
乌发女性如烟现形,缓缓道:“凉子不喜欢么?”
少女背脊一僵,拨弄银匙的速度快了起来,“……也不是不喜欢……就是……这样会给八百屋先生添麻烦的。”
——他是那样好的人,昨晚不但留下来陪她,还耐心听她说了许多抱怨,丝毫没有流露厌烦之意。
有一些甚至不曾向爱子倾诉的烦恼,她也安心地一并说了出来。现在想来实在是有些不礼貌了。
可是,可是……他……他是那样好的人呀……
真黑笑了笑,不再说什么了,素手梳着小姑娘柔顺的长发。
日光穿透女性修长的身形,亲吻少女微红的面颊,轻柔得像是来自母亲的抚慰。
忽然,真黑的动作有所停顿。
凉子疑惑地抬脸瞅她,却见她目光若有所思地落在凉子对面的空位上。少女循着看去,又转回头:“真黑?那里……有什么吗?”
——空无一物,只有静了的阳光。
少时,本应无物的桌面上,倏地多出了纸笔,甚至还多了一小块砚台。凉子懵了,愕然看着面前的毛笔自行立起,跳进砚台里来回蹭了蹭,再跃上白纸,径自笔走游龙一番后,才重新躺了回去。接着,白纸也像有了生命,毫不费力地在桌面旋了一转,将那俏丽的字朝向手足无措的凉子。
【您好。】
这一幕真是有点怪力乱神了。少女拧着眉头,勉力从嘴里挤出了最真实的感想:
“您,您好……您这样,会被人围观的。”
纸再旋转,笔又跳起。
【没事的。我只想和您说说话。不过您似乎看不见我,故采取了这样鲁莽的方式。】
果真是“九十九”!
这样的情形她还是头一次遇见,这就是所谓的“无缘相见”吧?但这位付丧神此刻正坐在她面前呢,这能叫“无缘”么?凉子眨眨眼,收起满腹困惑,礼貌地笑看纸面。
“对不起,我似乎真的看不见您……不过,这种交谈方式好有趣,像传说中的‘笔友’似的。”
笔尖一顿。【“传说中的”?】
“啊……抱歉,我用词不太恰当。因为只听说过‘笔友’。”凉子摆摆手。她曾听哥哥说起过,他以前也有过“笔友”。凉子还央着他给自己看看信,但由于彼时尚小,识字不多,没能看懂太多。
用笔交谈、以信维系,多浪漫啊。少女不禁遐想。
毛笔又动了起来。中途有些微的停滞。凉子耐心地等待白纸转至她的正面。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们也来当笔友吧?不单是现在,以后您若是不介意的话,我可以给您写信的。】
少女心下微动。“那……那不会太麻烦您了么?”
【不会的。】
阳光忽如鱼,跃入砚台,在墨里溅出一朵光花来。清透的蜜浸入笔锋,一笔一划便皆柔似人的笑意。
凉子也笑了:“谢谢您。我是鹿又凉子,这边这位是和我结缘的‘九十九’,叫真黑。”
真黑闻言,朝座位上的女孩儿微颔首,又见女孩回以清丽的笑。
【一笔启上。不必那么拘谨,叫我‘小一’就行。】
她看着斜立的毛笔。的确有一股不可视的力量在支撑着它,但她看不见,这时便不免遗憾起来。然后她笑说:“好。那你也叫我‘凉子’吧。”
这时,门上的悬铃叮铃铃一阵清响,似是谁人兴奋而短促的祝福。凉子笑着抬眼,视线里突兀闯入了一角格格不入的黑。
于是,隔过茶香、音乐与人声,两人四目相对。
——那个人的苍蓝色眼眸里,像是住下了一整个冬天。
一笔启上的回复打断了她的出神。
【凉子也在等谁来么?】
少女一愣,脑海里悠悠浮出了晓之助的面庞,迅速红了脸,慌忙摆摆手,袖口在桌旁胡乱蹭过。
直立桌面的毛笔慢慢歪斜过笔身,像在代替主人表达疑惑。
凉子假意咳嗽两声,一叠声地说着“没事”,捧起了温热的茶杯。茶水刚送进口中,只见纸上又新添一行字:
【凉子有喜欢的人了?】
凉子“井喷”了。
“不,不是的,不是……”少女狼狈地喘了口气,“我——”
——不喜欢么?
“鹿又先生看上去很憔悴。杏子也在,她很想你。”
“……是我的错。本来不应该吵架的。是我没有做好心理准备,鲁莽地问那些事。从头到尾都是我的错……”
晓之助转过头来。幽微的灯火在他的眼眸里明亮如星。
“请别这么自责,鹿又小姐。”他缓缓说,“你们是血脉维系的家人。”
“可我,我伤害了哥哥……明知道不能说那些混账话的,可我……”
她埋下头去。年幼的诚一列举心理阴影前三位时的一本正经,长大后亲耳听见她说“我讨厌你”时的愕然神色,像是拧成一股的绳索,赫然勒住了她的喉咙,叫她喘不过气、说不了话、哭不出声。
——在等什么?
“鹿又小姐。……不好意思,失礼一下。”
话音是同动作一齐落下的。起初,小心翼翼抚上发丝的掌心带着不确定的颤抖。收到她茫然投来的目光,他微微笑了。
她不由鼻子一酸。他的笑容便模糊了,在视线中分不清,剩下一团团莫可名状的光晕。
二人没了交谈。唯余少女的低声啜泣,散入夜风里,再也寻不见了。
但那温暖而坚定的掌心确是真实的。那一刻,潮水般洗过心扉的声音亦是真实的。
这个心声来得如此措手不及,在所有慌乱与安心、配与不配的矛盾之中,让她想起了“为谁风露立中宵”,这样酸甜入骨的诗句来。
凉子自回忆中抽身,捧着茶杯,蹙眉轻笑道:
“要保密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