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罗大陆,圣别纪元后期。
血族女王莉莉安突然失踪,几乎同一时间爆发的怪奇疫病让人类数量逐年锐减,失去管控的血族加上疫病的席卷,让整个社会动荡不安。
将一切扭转的契机在于教会发现血族的血液竟是能治好疫病的良药。
从此,以血液为中心的利益旋涡将整个世界卷入了其中。
【创作交流群:6911995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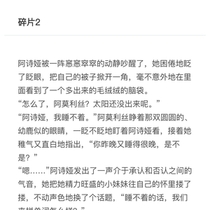


如果神是真正的神,而我的愿望成真,那么如今你一定会在哪里活着。只是我不知道你在哪里,所以无法给信封写上收信人的地址。
过去我认为自己无力,脆弱,甚至没有办法保护自己。但是在那样的厄境中,我们相遇,留下了回忆。不是猎人且并不健壮的我,依靠你教授给我的护身的方法,还有一些幸运,活到了现在。
是的,我活了下来,怀着一颗没有泯灭的心。过去在很多个瞬间,我都对这样的世界和无能为力的自己感到绝望,只觉得一切席卷而来,无情地带走了我珍视的人与物。但是,每当发现你还在为了保护谁而挺身而出时,我便意识到还不能放弃,倘若还活着,就应该努力到最后一刻。
我好像一直站在天平的中央。一边我想着我需要做点什么改变这个世界,哪怕是付出生命,我也要把我仅有的一切全盘付出,像飞蛾扇动翅膀投身到烈火中去,壮烈地燃烧自我;另一边我想着也许我只是该活下去,孱弱的能我活到现在已经非常不易,受过那么多的关照与帮助,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生命,受伤也好,残疾也好,变成血族也好,变成怪物也好,只有活下去这件事本身才是最重要的。
终于,直到现在,我能写信,能讲出这一切时,才意识到活着本身已经是一种巨大的意义。如果没有人活下来,谁会记得那些已经牺牲的人们呢?在见证者的目光下,与逆境对抗的战士们被定格在最为勇武的瞬间,变成永恒。而作为见证者活下来,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那一日的情景依旧会经常出现在我的梦里。我时常分不清哪些是真实的,而哪些是我的臆想。我意识到那也许就是我们的诀别,但我仍然许下了那样的愿望。活着终究是不是一件好事,特别是对于你来说如何,我至今没有答案。但就当作我自私,一时冲动,就算违背了你的意愿,也请原谅我。我希望你依旧活在某个地方,哪怕再也不会见面,我记忆中的你只停留到那一瞬间为止也没有关系。
我们的人生本来就像是两条短暂相交的线,但在我心中,好像只有交错之后的人生才有了色彩与意义。在那之前,我的人生游移不定,始终得不到心理上的满足。遇见你之后,我在你身上感受到了强大与平静,见证了你对真相锲而不舍的追逐(尽管真相让人如此沮丧),不曾放弃战斗的坚定意志。在我将要被真相带来的恐惧压垮时,又是你将我从深渊中拯救出来,让我踏出泥潭,迈向前方。我想我该活下去,是因为你对我如此期望。
圣女制度如今看来变成了一件荒唐之事,而圣女的血也不再有过去那样的功效,失去了意义。但是那是人们曾经试图抵抗过的证明,她们代表了在那个黑暗的时代人类极端疯狂的举措。褪去宗教的外衣,她们是当今人类的先驱。而随着一切的结束,剩下的圣女们也活了下来,也算是一件幸事。
在如今的时代,和平成为了常态,需要武力的地方更少了,大家正在试图建立新的秩序。但是过去的灾厄时代还未远去,还有一些人活在阴影里,但是一切正在变好。现在我找到了我的使命——那并不算是新的,但那是一种延续。大教堂虽然没有神父,也不举行宗教仪式了,但孤儿院和学校还是保留了下来,我在那里给一些孩子们教书。并且我还在书写,写一些过去其他的事情,也写一些给孩子们看的书。很多孩子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没有见识过那些灾难,我希望他们多多少少知道一些,记得一些。希望他们看到有增生的大人不要觉得他们丑陋,遇到害怕吸血鬼的人不要觉得他们古板,知道教会曾经做过的实验不要觉得他们愚蠢。人性是十分复杂的,扭曲的环境会催生扭曲的人性,但那仍然是属于人的部分,不应该被全盘否定。我想让他们知道,无论时代或出身,其实大多数人都十分类似。
爱尔莉丝还是和以前一样喜欢花花草草,涂涂画画。虽然年纪还很小,但是已经可以认一些字,自己读一些东西,就不像以前那样爱缠着我讲故事了。每当我又被噩梦困住,感到不安与动摇时,牵起她的手,就会重回平静。过去带给我们经验或阴霾,未来带给我们恐惧或希望。行走在这样的世界上,拥有珍视之物,才能拥有对抗一切的勇气。
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也许是在某些地图上没有名字的地方,又或者在更加遥远的其他岛屿或大陆呢?希望你无论身在何处,都能健康快乐。

无边的寒意,这是在意识回归之前便存在的感受。
上一次为寒冷所扰是何时的事情?她难得回忆起来,依稀在记忆深处,腹中空空的钝痛作为其孪生姊妹。饥寒勾结,恣意彻骨地侵蚀血肉凡躯,嘲弄无望的,草芥一般的生灵。
生命蜷缩着,如卵中未成的雏鸟,却觉得迷惘天地间,有人伸出手来,教她擦净一身贫穷烙下的印记,细腻温和因而价值不菲的丝织物交递过来,比雪花更轻地抚过肌肤:接着又问,你的愿景,是什么。
有窸窣细雪落在面前,落在发上,她感到前所未有的温暖和希冀,狂喜令人迫切地张口,寒风却趁机堵塞了全部的话语。
瑟莉安娜骤然睁开眼睛,从一片猩红炼狱中抬起头,破碎的花窗透露出天空的颜色,然而在一片铅灰中分辨不出究竟到了几时。
几近漆黑的深色血液已在身下积攒为一处血洼。她下意识去抚摸右肋下的溃烂圣痕,那里仍如几日前饮下黑血一般灼痛甚至更甚,变本加厉地为残躯提供过载的动能,仿佛第二颗心脏的搏动,催化着战逃反应。
这样的血液顺着阶梯向低处黏稠蠕动,不仅是她的,还有更多,顺势与其他鲜红的血液混成诡异的丝线,进而在大理石面上织作令人胆寒的锦缎。
尽管如此,周围四溢的血仍然提供了收回身体控制权的绝佳机会,浸透血液的义肢烫得能够灼伤人的皮肤。她拔出刺于身旁解脱多时躯壳的剑刃,拄着它借力从地上站起。双腿尚且脱力,她站得并不稳当,一只手握住她的右手,将立于大地上的实感传递过来。
伊莱……真叫人怀念。她说,用一种揶揄的口吻,见到你没事真好。
伊莱法缇的另一只手不自然地垂着,他当然有耐心等待自行恢复的时间,可他真的还有多余的血来痊愈吗?猩红的生命泉流顺着伊莱法缇的额角一刻不停地落下,经过为那只灾厄浸染的眼球,好像是这些血泪造就的那样,最后从无法再承载的眼眶边沿滚动下来。谁都清楚,这很难算得上无恙。他对瑟莉的话苦笑一下,是鲜少能在这张从容面庞上看到的局促。
教会猎人站稳脚跟,收回剑刃。比起和她一样方从血海深处醒来的异途旧友,她更关心在失去意识期间礼拜堂的战况。她踏上前方的阶梯,大教堂伟岸的穹顶却似乎于此时发出不堪重负的哀鸣声,紧接着是横梁崩裂的响动。石料黑色的间隙鼓动着,无数粘液不停歇地渗出,最终垂落过程中汇成巨大的触手状异物。地面上沉寂许久的黑色血液受到某种感召,如同吐信的巨蟒昂起头来,外部的天空不知何时已经血红,天地交融在混沌无序的血海中,仿佛亿万年的溶洞,等待漆黑无光的钟乳石和石笋弥合的刹那。
瑟莉安娜看见残月血族抬手,用法术企图驱散这至暗的恐怖,星光只闪烁了一下便消失在她眼前。她想做些什么,触手很快也温柔地吞噬了她的身体。
***
盛大的舞会。
无数枝形吊灯错落悬挂,点燃一圈,又一圈的烛火,像地面上踩着舞步回旋的客人,一圈,又一圈。
厅堂暖和得像一个不合时宜的春天,尽管瑟莉安娜不再那么渴求温度了。
这些人,参加舞会的人,全部看不清面庞,是因为覆着假面吗?她一个人坐在宴会四周的椅子上,用打量的目光观察着,思考着。
有人对她伸出手。黑色的手套,同样的假面,但她立刻认出这是父亲,于是欣然接受。
暗红色的布料流动起来,在旋转中轻快地离开地面,像水波,像一圈涟漪,像一场遥不可及的追逐。
没有边界的自由里,瑟莉安娜只感受到那位给予第二次生命的人,他的黑色缎面礼服揽住她的腰肢,他的耳语近在咫尺:
你的愿望?
——我的愿望吗,瑟莉安娜想,那实在是太多了。最初的时候,我想要不再受寒、不再饥饿。
然而她对着脑海中往昔的幻影说,我想离开你,我不需要你。
眼前的景象改变着,霎时有明媚的霞光照耀到瑟莉安娜的身上。这是圣伯拉礼拜堂后东侧连廊的倒数第三扇窗,几十年来从这里可以看见全圣都最美的日出。
身着修士黑袍的人牵住她手,他轻轻地问,
我爱,你的愿望是?
——在某刻我祈祷留住此时、留住我爱。瑟莉看着他,从模糊的五官上分离出清晰的思念。
于是她说,我想要的你都已经给予,我别无所求。
阳光迁移着,被吞没到廊柱之后,视线变得晦暗,但不久,圣伯拉的祷钟在耳畔响起来。立刻,血液逆流,回到不再残破的身体;武器收势,回到持有者的鞘内;星辰倒转,日与夜逆向而行。死亡、绝望,痛苦尽数收回魔盒之中;永生,安宁,乐园再一次回到人间。
逆光的神龛上传来比钟声更恢宏的声音,祂问:
你的愿望,是什么?
——在最后,我想要回到过去,回到属于我的伊甸去。
然而,只是想罢了。瑟莉安娜眯起眼睛,看着漆黑的,镀上一层金色光晕的神像,然后说,我没有愿望,我伟大的造物者,我没有。
我既不逆来顺受,更不强取豪夺。因此我绝不妥协,绝不扭曲。我赋予我存在的意义,哪怕连我自己也无比迷茫。
我的愚钝,正是我为人的本质。
***
神龛上的光消亡而去,等再一次能看清时,眼前只剩下圣堂那扇破碎的花窗。
神的肢体叹惋着离开了她。
瑟莉安娜感觉到眼角有什么东西,她眨了眨眼睛,深黑的血代替眼泪淌落,是凝视神祇的代价。不过,她没有心情再管自己了,她眼前赫然是一处正在蠕动的,难以言明真身的黑色胶状物。幽蓝的荧光沿着内部生成的脉络涌动,它轻微地律动,节律地呼吸着。
……伊莱,是你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