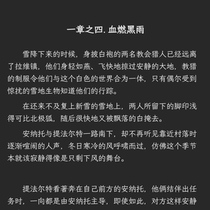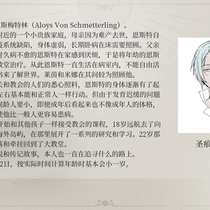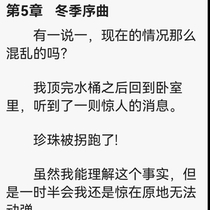欧罗大陆,圣别纪元后期。
血族女王莉莉安突然失踪,几乎同一时间爆发的怪奇疫病让人类数量逐年锐减,失去管控的血族加上疫病的席卷,让整个社会动荡不安。
将一切扭转的契机在于教会发现血族的血液竟是能治好疫病的良药。
从此,以血液为中心的利益旋涡将整个世界卷入了其中。
【创作交流群:691199519】




要是没有这声巨响,罗斯差不多都要忘记那两个家伙了。她发现上一次见到他们还是在十五号的晚上猎人们在城外据点的篝火旁边分晚餐,本来是这样的,但她和两个在血罐身上绑炸药的人渣吵了一顿后,事情就像枪管炸了膛一样混乱起来:莫名其妙之间猎人们就决定了“给湖骸炸他妈个大烟花!”。十五号就这样混乱又离奇地过去了,多少显得有些疯癫的狂欢结束之后,“炸他妈个大烟花”就像段群体的梦境一样悄然无踪,猎人们依旧照着原来的计划轮班守夜和巡逻,伤者仍然不分昼夜地被送到斯塔夫罗金医生这里。她跟着医生的指示在工会大厅里外来回穿梭,把能动弹的伤员交给运送伤员去城外森林安置点的猎人,不记得天是什么时候亮起来的,不记得中间自己见缝插针地打过几个盹,也不记得天色是什么时候又变暗了的——直到她获得了短暂的休息,从多姆神父那里讨到一块烘软了些的干面包打算补上午饭时,工会大厅斜对面一处应当空了的屋子里发出一声爆炸的巨响。
罗斯这才想起来,十五号的晚上之后她就再没见过洛多维科·里奇和亚伦·桑切斯,那两个为“炸他妈个大烟花”提供了绝大部分舆论气氛和技术助力的家伙。城里已经空了一大半,工会大厅附近的猎人大多是回来修整的,疲惫不堪地抬了头朝那爆炸声处望了望,都指望着别人过去瞧一眼,最终竟也只有罗斯一个立刻向那里冲过去。
她一边跑着,一边才后知后觉地想到:天杀的,这两个家伙真的在做炸药,我们真的要炸了纳塔城。
当她冲进了那间空屋子,又发觉自己对这两个家伙的担心很是不值当,当即把脑袋探出门外,朝往这儿看着的疲惫猎人们大喊:“别看了!没事儿!”。尽管被爆炸震得东倒西歪趴作一团,但两人都全须全尾,精神得很。洛多维科首先看见了她,跳起来大声说:“我们尊敬的提案发起人、我们的小老板来啦!噢,”他用大过了头的嗓音嚷嚷:“还带来了面包!天哪,我们俩多久没吃东西了?”他用手肘顶了顶正从地上爬起来的亚伦,独眼的年轻猎人晃了晃头,像是还没从爆炸的余波里回过神来。
罗斯低头看了看,面包在跑过来的路上已经被自己捏得变了形,松了手就倏倏往下掉渣子,她愤愤地踢了一脚“松鼠”洛多维科,“这是我的午饭!”
“你说什么?”洛多维科仍然用大过了头的嗓门说话,“我耳鸣!你刚刚说什么?”
而亚伦在他耳朵旁边大声回答他:“我们今天还没吃过饭!”
最后亚伦从包里找出了最后一张干净的纸,把面包垫在上面切成了三份,并礼貌过头地表示自己不怎么饿,主动选了中间被捏扁了的这段面包。他们盘坐在被炸得七零八落的屋子里,洛多维科耳鸣好了,便显摆似的向罗斯介绍刚刚炸出吓人巨响的东西:“我打赌给你三天你也猜不出,是白糖!嘿,这年月纳塔城里还能有白糖。那你猜猜这是怎么弄出来的?”
罗斯翻他白眼,往独眼的陌生猎人那里看去,这个叫亚伦·桑切斯的猎人说是雷涅的伙伴,常在西南那片活动,是以很少来纳塔城,罗斯自然也不认识他。年轻猎人发觉她的目光,挠了挠鼻子,说:“白糖能烧,在火药里配一份会炸得更远,熬成糖浆配进去效果更好,但是火候和配方得再调试……”
洛多维科听到被揭了谜底,顿时咋咋呼呼起来:“我们这已经差不多了,马上就能弄出够多的火药。”
罗斯早就习惯这“松鼠”的吵闹,索性也不理他,低头吃面包的时候正看到刚刚被垫在面包下面的纸是一封信,信封上不怎么好看的字迹写着“纳塔城玛格街二十八号,诺利亚先生收”。她觉得奇怪,也没有多想就说道:“纳塔城哪有玛格街?”
洛多维科也探过头来,问:“这是你的信?”
“我替人来送这封信,到了这里正好就遇上了湖骸。纳塔城没有玛格街的。”
“噢……”洛多维科这会儿的反应快得惊人,俨然一副见多识广的样子,“我猜猜,讨债的信?还是姑娘的信?”
亚伦仅剩的眼睛惊讶地看了他,答道:“姑娘的信。”
这下罗斯也明白了,用力撕咬了一口硬面包,说:“人渣,满嘴都是——”
“谎话。”
G夫人的声音像是从极高的地方落到他头顶上。他觉得寒冷,手指冻得发麻,冻得骨头发痛,全身的血都像凝固了。他应当已经不会被冻伤了,连过去手指上得冻疮留下的淤血块也消失了,但他还是会感觉到寒冷。后来亚伦·桑切斯的故事总是用一个谎言结尾:“最后天亮了”。实际上天没有亮,他从流淌着血横陈着死尸漆黑的矿道逃了出去,逃进了一个无月的漆黑夜晚。
亚伦·桑切斯出生在北方群山下的一个镇子,这镇子上的所有东西都是依托着它背靠的矿山存在的,这座山叫做达纳山,所以镇子就跟着被称作达纳。有很多事情都环环相扣,但亚伦并不知道,或者很久以后才知道其中的关联,比如说因为突然出现的死腐病和血药、突然变得疯狂的吸血鬼,外头出现了“猎人”这个行当;因为猎人兴起,需要许多武器,铜铁生意也连带着兴盛了,达纳山的矿上就需要更多工人;工头从南方招募来新的工人,南方来的工人就把死腐病也一并带来了达纳矿。不久之后死腐病就成了这里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得了疫病的矿工拼命地工作,期望自己在身体腐烂不能劳动前攒够买一份“良药”的钱,最后自然死在了这里,被抛进废弃矿坑里草草掩埋。人们总感觉死腐病是一种横加给所有人的灾祸,但后来想起来时,发现它其实也没有改变世界许多,死腐病出现前就有干旱和洪涝,有饥荒,在矿区就是矿难和塌方。亚伦没有感染上疫病,他遇到的是矿难,被困在坍塌的坑道里。所有人都死了,死亡本来是这里最寻常的事,得了病的矿工因为身体腐烂而死掉,健康的矿工因为事故而死掉,亚伦虽然因为一瓶被患病矿工偷藏着带下井道的血药而长出尖牙变成食人血的怪物,但未必没有机会苟延残喘下去,老矿工们喜欢对矿上的小孩讲这样的故事:一群矿工被困在坍塌井道里,等不来救援,开始互相残杀、同类相食,最后活下来的那个就会变成“鳄鱼”,变成一种嘴角裂开、牙齿尖锐、四肢干瘦但迅猛的怪物,那些废弃的坍塌的矿洞深处传出尖啸似的声音,就是饥饿“鳄鱼”的啸叫,它们仍然游荡在矿洞里,把落单的矿工当做食物拖走。矿工是很习惯亚伦这样的怪物存在的。
但一个老猎人为了这场血案来到了矿山,在这偏远矿山以外的地方,吸血鬼也划分出了许多派别,有杀人的,有中立的,也有通过血药治好了疫病却成了吸血鬼的,因此亚伦必须经历一次老猎人的审判,判决亚伦是否恶鬼,是否应当为矿井下死掉的人偿命。亚伦开始一遍遍地描述那里发生了什么,他作出了很多合乎情理的解释:偷藏了血药的伯尼病了很久,已经不能做重活,他害怕自己变成第一个被分食的猎物,因此用了药变成了吸血鬼,但他仍然很虚弱,他决定将被困者之中最年轻的亚伦也变成吸血鬼当做帮手;而亚伦逃跑了,他获得了超过人类的力量,于是从原本爬不上去的洞口逃了出来。老猎人未必完全相信他,但也没法从错综复杂的矿井里找到证据。G夫人——那瓶血液的来源,一名教会猎人,一个白肤冷面的女人,因为感应到了自己的血造就了一个新生吸血鬼而赶到这里——打断了老猎人的犹豫,她说:“把他交给我。”
G夫人的声音干涸嘶哑,像是很久很久都没有说过话了。她指了指脸颊上证明她身份的圣痕,说:“他的血来自我,我用教会猎人的名义为他担保。”
他藏身的洞窟外面仍然是看不见月亮的漆黑夜晚,老猎人空着手离开了,G夫人即将带他去往他一无所知的远方。他想说点什么,但G夫人走近他,铁钳般掐住了他的下颌。
“谎话。”
她冷冷地说道。
“我最想不到的是雷涅那样的人也会有搭档。”
到了十七号,城里终于不剩下多少伤员,重要物品也都陆续搬去了城外的临时据点,倒是像把纳塔城让给了湖骸似的,医生那里的活计少了,罗斯得空便帮着布置炸药的猎人从洛多维科和亚伦的小型军火厂里运送火药出来。她一进门,就听到停不下嘴的洛多维科·里奇大爷一边忙活着配火药,一边闲扯些雷涅的事,分明是打算把雷涅和亚伦的家底一并打探清楚,好在下次合适的机会占些便宜。
“你们是怎么搭上伙的?雷涅那样的家伙,”他比了个夸张的手势,“吃饭都恨不得一个人坐到天边去。”
这叫耗子女士也忍不住好奇了起来,她只抬了个头,就被洛多维科发现了,松鼠朝她挤了挤眼睛,招手示意她过去坐着一起听:“别急,休息会儿,等我这包做完了一起搬。”
独眼猎人正坐在屋子另一头小心翼翼地熬煮着什么东西,屋子里飘着一股隐约的甜味,想来锅里煮着他们说的白糖,回答说:“就是……那么样呗,我帮过他,他也帮过我,不知不觉就经常一起行动了。”
洛多维科显然不太满意这个回答,继续问他:“那怎么不见他在纳塔城也有搭档!你是西南那边来的?比昂人?”
“不是,是靠海湾那里的一个小镇子,那里没有工会,猎人很少的。”
“不对啊,你这是矿上的手艺,海湾那里哪有矿区?”
“我小时候在北方那里的矿上做工,达纳那里,出铜矿的。”亚伦手上边搅拌着锅里的东西边回答他,好像正自然地说着他真实的经历一般,“后来矿上闹疫病和吸血鬼,乱得很,我又遇到了矿难,被困在矿底下,困了好多天,幸好来了猎人。”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我也不知道地面上发生了什么,最后天亮了,我获救了,就跟着当了猎人,去了南方。”
“那你可走得真远。怎么样,会想回家乡吗?”
“那么你们呢?”亚伦突然反问,“你们都是纳塔人吧?”
洛多维科和罗斯不约而同地点了头,他就接着说:“你们要炸掉自己的家乡。”
“有什么不行吗?”洛多维科轻快地说,“城市不过是一堆石头和砖头,我的家乡已经被诸位同行搬去外面的森林里了,对吧,尊敬的猎人罗斯女士?”
“我们亲自炸掉,我们亲自重建,”一直坐听着他们说话的罗斯突然挺起身子,好像一个迷你版、完全不像斯塔夫罗金医生的斯塔夫罗金医生,“就该这样。”
洛多维科点了点头,刚好配好了一包火药,包装好交给了罗斯,又不知从哪摸出了一个三指见方的小油纸包,塞到了罗斯的另一只手里。“这叫职务之便。”他故弄玄虚地说。罗斯打开小包的一侧,看到里面装了浅浅一角白糖。那洛多维科已经转过脸,又孜孜不倦地继续打探:“你说西南那里没有工会?那有没有什么生意好做?我们现在也是过命的交情了,你可不能骗我……”
对不起,他说,对不起。
“骗子。”G夫人仍然这么说,“你根本没有在忏悔。”
她冰冷的手按在他的头顶,她说:“你杀了人,你不是被人变成吸血鬼的,是你抢了血药,是你杀了所有人。”
对不起,他说,我不想杀他们的,我流了很多血,我快要死了,那瓶药刚好在那里,我只是想活下去。
“你只是想活下去。”他听到G夫人的冷笑,“你只是想活下去,所以把他们都杀了,你只是想活下去,所以说谎也是可以的,做什么坏事都是可以的。”他放在地上的手被她踩在脚下,他听到骨头咯咯断裂的声音,却不再感觉疼痛了,骨头断了很快就会恢复,然后再被打断,大概时时都在疼痛中,反而就感觉不到痛。G夫人按在他头顶的手向下滑过他的右脸颊,自从他喝下西比迪亚的血、背后被打上圣痕烙印,他的右眼就看不见了,也不会再流泪了。她的手掐住他的下颌,逼迫他张开嘴,她说:“那么向你的‘朋友’说谎又是为什么呢?假装猎人是为什么呢?也只是为了活下去吗?”
他感到背后发凉,烙印在背后的圣痕却发烫,他好像听到烙铁在背后,皮肉滋滋作响的声音。对不起,他说。
“卑鄙的骗子。”她说。
十八号的清晨,天还没有完全亮起来。亚伦·桑切斯即将去炸毁一座他毫不熟悉的城市。寄给纳塔城东城区玛格街二十八号诺利亚先生的信还在他的背包里,猎人们正在将湖骸往陷阱里引诱过去,火焰将会吞没这座城的东城区,吞没破坏这里的怪物,也吞没他们要守护的街道,吞没真实存在的许多人的家乡故土,自然也会吞没那条不存在的玛格街,吞没虚假和谎言。
最后天亮了。
———End———
Q:为什么盖亚女士总是被称作G夫人呢?
A:因为小编总觉得喊盖亚夫人她会突然变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