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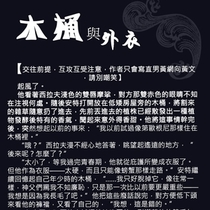
剩下的部分請看黑月的【http://elfartworld.com/works/95207/】
一
——將較大的一頭翻到領帶結下,穿過圓形的結後束緊,之後再做稍微調整,使領帶在衣襟前端正。只需要再做這幾步,就算是完成了儀容整頓。迷亭信樂——新原厚繼站在鏡前,食指輕輕擺弄領結。
這幾日異於以往的悶熱讓人想將襯衫快點脫下來,無奈舞會的侍者卻只能穿這樣的西裝,新原便只好趁著管事離開的時候偷偷提起黏在後頸上的衣領扇風。蒸得人頭腦發熱的烈陽暫且不提,不知從哪兒傳來的蟬鳴久久響徹,讓人更覺得悶熱;路邊的小兒穿著清涼,使人心中有種油然而生的燥氣,恨不能快些將衣服全部脫去,跳到河裡游泳。就這樣看來,還是和服要更好些——新原將頭髮梳向腦後,露出額頭,向鏡中模糊的人像做出謙卑的笑容。半晌,更衣室的門被敲響了,他也就放下整理儀容的事情,轉身開了門。
開門的是與他共事的女侍之一,對方名叫凜花,雖說是女侍,但真實身份卻是男人。只是那副容貌任誰看了都想象不出凜花是男兒身——且不提那雙金黃色的杏眼,少年的纖細與少女的青嫩之間早已模糊了界限,身上的侍女裝更加重了屬於女性的氣質,若不是眼神中還有些少年的銳氣,就算是迷亭也不會相信對方所說的“故事”的。
“怎麼了,凜花醬?”
“佐條先生說換好衣服的話就去大廳集合,讓我來通報下諸位。”凜花說著,又向更衣室裡一望——其他侍應生還在吃午膳,更衣室裡空空蕩蕩,髮膠和劣質香氛的氣味倒是沒少。凜花為這氣味皺了皺眉,但卻因素養而沒說什麼,迷亭便說道:
“這地方確實不好聞。”
“嗯……”凜花輕聲應和著。凜花身為女侍,所在的更衣室與男侍應和其他女侍都不同,雖說對對對方所在的更衣室有幾分好奇,但迷亭卻一直沒機會進去看看。
“因為有人每天不洗澡,卻還是噴香水……久而久之就成了這種味道。”迷亭說著,悄悄鬆開襯衫最上排的紐扣,“夏天這麼熱,卻還要穿成這樣,西服真是難以理解啊。”等他說完,凜花便點著頭,又小步離開了。迷亭便空著手到了大廳。在那裡,頭髮灰白的管事已經等候多時,正時不時看著手錶,間或眺望建築的四壁,仿佛在期待適應生們能從四面八方趕來集合似的。等老管家的視線與迷亭相聚,後者便慌忙將釦子又係上,此舉迎來對方不悅的目光,卻並未得到痛斥。
“新原,還記得我說過什麼嗎?”
“是?”迷亭收起笑臉來,等著對方一頓教訓。佐條站在他跟前,拍拍他的後頸,好讓他記起來告誡,卻得來困惑的表情。
“參加舞會的都是些尊貴的人物,你作為侍者太高了些。我再說一次,你一定記好,不能給人俯視他人的壓迫感。”管事說著,示意他將視線放低,“但背部的姿勢不可有氣無力,更不能顯得猥瑣,腰板還是要挺直。”
迷亭雖然覺得對方所說的自相矛盾,卻也照著做了一番,沒想到試了幾次,就聽到年邁的管事發出一聲歎息。
“就是將視線放低,也並非謙遜……你或許該做保安呢。罷了,你就維持那副笑臉,這總不至於招人討厭。”
“是。”迷亭莫名其妙聽著,隨後又加了句,“可我也不會什麼武道,只是空長個個子啊,要是我會,早些時候就說了。”
“……哪有這麼痛快地承認的,好了,請你幫我出去從報童那兒買個報紙,錢我會在舞會結束後再付給你,你有零錢吧?”佐條問道,迷亭便點頭答應,隨即便被年長者轟出了客廳。室外,暑氣更是灼熱得可怕,烈日曬得人頭腦發脹,水泥路面在炙烤下變得如同烙鐵一般,若是赤腳行走在上面,恐怕會留下燙傷。奇怪,幾日前好像還沒有這麼悶熱,或許是在雨季過後,太陽便開始不加遮掩地肆意襲擊行人與建築了吧。
迷亭注視著來往的行人,恨不得快點走到路旁的蔭庇下。但賣報的少年卻只站在稀疏的樹蔭旁,向人們吆喝著今天的頭條,內容不外乎是“松竹梅新劇目”又或“帝國對外戰爭”。這兩者之間,迷亭對前者興趣不大,後者更是毫無好感,買下報紙後,手上倒是多了遮陽用的傘和扇子,他便趁機在樹旁乘涼,好一會兒才回到建築。彼時,適應生們已經到齊。管事見迷亭拿著已經發皺的報紙,也並沒說什麼,只道了聲“謝謝”。這時,卻又聽到有人喊了一聲。
迷亭循著聲音源頭望去,才發現騷動的來源是個妖異侍應——對方的名字迷亭沒什麼印象,只知道那少女模樣的侍應生和方才叫自己出來的凜花一樣是男扮女裝。那妖異少年指著長桌,大聲說道:“桌子上有裂縫了喵。”
“這……”站在妖異身旁的另一位服務生露出面難的神色。舞會將在幾個小時後開始,無論是去別處借或是再請人送來都已經不夠時間,可這畢竟是名流的宴會,也不能繼續用表面上生了裂縫的桌子,會壞了主人的名聲。
佐條緩步走過去,俯下身檢查起桌子上的裂縫,過了會兒,又從桌子旁抬起頭來,向身邊的一名侍應說到:“沒什麼大事,長桌只是表面傷到,木材並沒有損壞。你去洗衣房裡拿過來那套鏽了金鳥的桌布,在賓客們來之前鋪上就好。”
被下了命令的那位侍應點著頭,忙小跑著離開。而裂縫的第一發現人似乎並沒為這事費多少心,只是隨口提提。那兩隻貓耳朵輕輕扇動著,不知其主人在想些什麼。迷亭邊饒有興趣地猜測著這位妖異少年的個性,邊幫著佐條和其他侍應清潔起生了裂縫的長桌。未等多長時間,佐條口中所說的“刺繡桌布”便被拿了過來。迷亭瞇起眼來,瞧瞧地注視起那意外的救星——從其充滿幾何圖形與花飾的圖案以及大正少有的做工中能看出,這物件是舶來品的,但那色調和針腳又能使人讀出工匠或曾試圖取悅過遙遠東方客人的痕跡。迷亭想著,攤開桌布,將其在長桌上鋪開,佐條和另兩個服務神各抻直桌布的一角,好使其平整。末了,佐條再放上裝了花束的花屏掩蓋凹陷的裂縫,事情就算大功告成。此時,離舞會開始的時間已經所剩無幾。侍者便在佐條的招呼下齊齊整整排成兩排,站在大廳兩側,等候著第一位到來的客人。
迷亭站在離門口最近的位置,午後帶著點熱氣的微風從敞開的大門處悄悄溜了進來,雖然還是讓人不舒服,但總比室外的烈日要好。他悄悄瞥了眼身旁的女侍,發現對方正是叫自己來大廳的凜花。
“凜花醬,凜花醬?”迷亭小聲叫著對方的名字,直到少年抬起一雙金色的杏目,這才停下來,“那個桌子上的裂縫是怎麼回事?”
“佐條先生也說了,是家具的表面有了裂縫。”女侍的目光毫不游移,筆直地注視著建築的入口,“不過那樣也太可惜了,完全可以說是人為的嘛……”
“此話怎講?”
“唔……有漆的木家具不能用水擦拭,日子久了會因此而壞掉……那裂縫看起來有點像因為泡了水而發脹導致的,所以我想大概不是因為用得太久才壞的……太可惜了!你想想看,那可是有漆的家具呀,真的買一個可是要花很多錢的,竟然就這麼因為這種保養方面的小事兒糟蹋了。”凜花輕聲說著,迷亭聽出對方或許精於此道,便出聲誇獎。凜花既不接受,也不做做樣子地否認,只是又問道:“對了,新原平日在自己的僱主家是做什麼的?”
“啊?我做的是家庭教師,專門幫著小少爺學點東西。”迷亭漫不經心地答著,“凜花醬呢?平時做些什麼?”
“我?我是游女哦。”
“……抱歉抱歉,之前那個說法是說謊,我其實是說落語的,只是因為缺錢而放不下面子,所以才謊稱自己是家庭教師。”迷亭再說道,“你有喜歡的東西嗎?”
“喜歡的東西——?我也不知道耶,只要是別人送的都會喜歡。”凜花答,少年的聲音聽不出是男性還是女性,加之打扮,甚至有些說不清是長相秀麗的少年扮作女裝,還是略有些英氣的少女了。
“‘別人送的禮物’這東西可不好送啊,凜花……!你平日在哪裡,我改日有時間找你喝酒好了。”凜花很快報上一個耳熟的名字,迷亭便記了下來,“除了別人送的東西以外呢,還有什麼喜歡的嗎?”見對方沉默了一會兒,迷亭也留給他思考的時間,隨後又說,“對了,你幾歲。”
“已經二十了。”女侍平靜地答著,迷亭原本想順著準備好的客套話,說他年輕,得到這回復卻不勉僵住了。
“那……豈不是只比我小……”
此時,第一對客人進了會廳,這話題也戛然而止,停在管事一聲歡迎裡了。
二
侍者穿行於人群,手中拿著裝盛了酒杯與甜點的托盤;衣著華麗的客人戴著假面,彼此間進行著必要的寒暄。不知何時起響起了舒緩的音樂,便有一對對的男女湧入舞池,在音樂聲下翩翩起舞。
與之相對,廚房內的人手正手忙腳亂、焦頭爛額。
迷亭匆忙地將已經空了的酒杯從托盤上取下,放入待清洗的餐具所在的水池,隨後又被叫去拿代替已經空了的餐盤的新菜餚。廚房裡一片撲面而來的熱氣,廚師赤紅著臉面對燒得發燙的鍋具,糕點師則在已經具備雛形的西式糕點上塗上均勻的花朵;來來往往的侍應生們拿著骯髒的餐具回來,又帶走剛完成的佳餚;洗碗婦兩隻已經被水泡得發脹發皺的手快速地在餐具上轉動。
“那邊那個,把白胡椒和砂糖也拿上。”
迷亭被人叫住,手上於是又多了東西。拿著一盞空了的器皿的女侍應幫他撐了下門,等他又回到不同於廚房的嘈雜地方時,迷亭才看清那侍女頭上的一對獸耳。
“是茗啊?謝謝!”他大聲向少女模樣的妖異說道,又轉過頭去,將廚師準備好的菜餚擺在鋪了餐桌桌布的宴席上,再附上對料理的簡介。之前廚房的廚師曾叫迷亭試嚐過一點,但西洋菜色卻無論如何都不合迷亭口味。主廚從試吃裡得不出中肯的評價,只好作罷。
“這是什麼?”有個遮了面的賓客問道。
“是煎鵝肝。”迷亭答,背起來主廚曾說過的話,“是著名的法○西菜,吃起來入口即化,您看這色澤,”雖說如此,看起來卻和普通動物內臟無異,“入口的時候,可以輕輕用刀叉將其塗抹在麵包上,就算是再普通的麵包,也會變得美味,”後者迷亭也不喜歡吃,“至於上面的青蔥色,那是蒜蓉,被主廚用特殊的方法烹調過,聞起來很馥郁,更將鵝肝本身的鮮美襯托了出來,”在熙熙攘攘人群的呼吸臭氣裡,哪聞得到那種味道——
“原來如此,是煎鵝肝啊,也好久沒有吃了。”戴著面具的客人說著,拾起一張餐盤,“請為我來兩份。”
“好嘞,請您稍等。”迷亭為對方盛上鵝肝,為使自己看起來不至於笨手笨腳、不慎思慮,又往碟子裡加了些調味品。
“還有,那鵝肝上面金黃色的東西是什麼?橘絲嗎?”客人又問。菜餚上,確實灑了些被切得極細的金色飾物,使得其整體看起來生色不少。
“是金箔。”迷亭又回憶起來主廚所說的話,便這麼答了。
賓客在面具下的臉雖然被遮住,面具兩隻孔裡的雙眼卻顯然充滿了嘲弄,他說:“你在說笑吧,那種東西怎麼可能吃得下去呢。這一定是抹了醬的橘絲,要不然就是蘿蔔絲。”
“哎呀,若是您說是抹了橘子醬的橘絲,那就是橘絲吧!我見識淺薄,也沒讀過多少書,亂說的,還望您多多品嚐。”迷亭向對方鞠了一躬。客人滿意於這回答,也就沒再多問,迷亭便離開了餐桌旁,又到廚房裡拿了喝飲料用的玻璃器皿,為客人分配酒水。再一看四周,竟然有不少自己認識的人——且不提達官顯貴,落語家或其他表演者中也有寥寥數人參加了舞會,甚至連花街的看門人也混雜在人群中,只是都帶著面具,自己身為侍者,不好去確認。也是這時,一位少女身材的客人走了過來。
迷亭原本覺得那身形很眼熟,看到對方身上屬於半妖的特征,便認出來了——面具上方遮掩不住的獨角乍一看還以為同樣是裝飾,仔細一瞧,卻是從本尊的額頭上生出的。至於打扮,和平日方便幹活的和服裝扮不同,是素雅卻仍能看出華貴的洋裝,淺茶色的長髮歪斜著扎成一束,從左耳上方垂了下來。
“紗織醬?”迷亭小聲確認著,對方聽到這稱呼後,微微愣著抬起頭。
“……迷亭先生?”半妖少女不確定地小聲問著,迷亭忙點點頭,“您怎麼在……”
“因為在花街和姐姐妹妹們玩太多,就沒錢啦!所以就過來打工!說來,方才還看到和花樓那位守門人相似極了的人呢!”迷亭笑嘻嘻地答道,又為兩人的身份顛倒而感到有趣,本想調侃幾句,但又覺得不大合適,便彎下腰來,仔細看紗織的雙眼,“怎樣?玩得開心嗎?”
“是的,很開心……稍稍有些口渴。”紗織答著,垂下眼簾。
“哎呀,好!失禮了失禮了,忘了工作的事情。來,這杯是為谷小姐特別調製的…那個啥可口調尾酒。”迷亭將在酒瓶旁準備的果汁甕提起,為酒杯注入各色的液體。說是雞尾酒,但不過是將不同的果汁混合在一起而已。各式果汁兌成石榴色的澄澈汁液,放在酒杯中,顯得和西洋酒無異。
“謝謝。”紗織接過酒杯抿了一口。
“如何?味道還不錯吧,這可是迷亭名產!好啦,紗織醬,祝你今晚玩得愉快。”迷亭向少女說著,對方點點頭,隨後便被舞伴帶走了。迷亭揮揮手,看到紗織嬌小的身材消失在舞池裡,才繼續關注起身旁的酒桌。這次,意料之中的客人卻來了,只是這人,迷亭並不想見。
彌助端著酒杯,挽著一位身材苗條的女性,走了過來。見到迷亭,先是停頓片刻,又叫那女伴去旁邊等著。等那名步伐優雅的女星走遠,彌助確定她聽不見後,便爆發出一陣大笑來。
“‘我勢必會參加舞會,不然就失信於你!’——我可沒想到你想的是這法子,笑死我了!”粗壯的男人拍了拍他的背,又大笑起來,“你可真是天生的笑匠!我還以為你要整什麼事情,等著你出糗,卻沒想到你自己先為自己出糗了!笑死我!”
迷亭聽著這話,也不反駁,卻講:“你那位女伴,不是從花樓找來的?”
“哪裡,”長相滑稽的男人在面具下的雙眼已成了兩道縫,語氣中不無一種自負,“那女子可是因為我的人格魅力,才隨我來的!”
“我看是彌助兄你想多了,您的人格魅力,比起您相貌的魅力來,還要更為遜色呀!”
若是平常,彌助早就大聲反駁了,但今晚他顯然是心情上佳,師弟說的話也並沒有引出怒火。那副寬大的、面具遮不住的面孔露出一副憨笑的神態:“那是你不知道事情的原委,我的女伴——她原是個潑婦呀,但你看,在我悉心教導下,是不是也已經變得端莊美麗,與華族富商家的小姐無異了?這可是我教導有方,無論你說什麼可都改不了這事實。”
“哦?這是怎麼回事,你說來聽聽?”
“哪有什麼怎麼回事,只是人必然會像鏡子一樣,反射出對方對待自己的態度,哪怕是潑辣的酒家女,被人像呵護富家小姐一樣對待,也會變得不同,僅此而已。我對那女子百般照顧,全無所圖,并彬彬有禮地待她,她便漸漸軟化下來。在交往過程中,我再教她怎樣做才顯得賢淑——來時我與認識的我的客人相談,對方還問起我是哪家的小姐呢!”
“原來如此,彌助兄,喝洋酒嗎?”迷亭雖這麼說,但手中的酒杯卻直接遞了過去。平日極少喝洋酒的彌助正在興頭上,並沒有推辭,而是一飲而盡。事畢,又大聲咂嘴道好酒好酒。
“真是爽快——要我說,人的個性就是會因為相處中他人的態度而變。俗語說人靠衣裝佛靠金裝,其實不是,人之所以能容光煥發,靠的是他人對待自己的態度。上好的衣服、姣好的容顏,都不過是使人對自己有好態度的‘誘因’罷了。”彌助靠在酒杯旁的肥厚嘴唇微微捲起,得意的面孔猶如得到秋刀魚的肥貓。
“哦?誘因?”
“是啊,是誘因——我並非因為生而有這副相貌而可笑,而是因為這副相貌被人奉為天生丑角,而因此我是丑角。”面相滑稽的男人這般講到,搖頭晃腦著高舉起空可見底,“我就叫你看看好了,彬彬有禮地對待潑婦,便能將對方變成淑女。反之,我也可以叫教育良好的紳士變成無賴漢,你且看著吧!”
“哈哈,不愧是彌助兄啊!不過你說的,我可是半點也不苟同。”迷亭信樂為師兄的空杯再蓄上瓊漿,後者被這反對的聲音驚得挑起海苔般的濃眉,“態度再怎麼說,也不過是個性的最表層而已,稱不上個性本身,若說是人格,那就更是無稽之談了。”
“怎麼,你又有什麼高見啦?”
“說不得是什麼高見——我問你,你能說這舞會上眾人所戴的面具作‘相貌’嗎?”迷亭微微向前傾去,注視起因酒水而面色赤紅的師兄的臉上泛起另一種紅色。
“——一派,胡言!”彌助大聲道,卻又不曾拿出理據反駁,只是音量險些惹來周圍賓客注意。過了半晌,他才抬起漲紅的臉,對師弟怒目而視:“態度又稱不上面具,倒不如說,你將這兩者做對比,也並不能證明我所說的是錯的。”
“哎呀,彌助兄,這可就不對,甚至有些過於幼稚了——你我都知個性看不見摸不著,卻能確切知曉其存在,這正如見樹枝搖擺便清楚有風一樣,是不是?”迷亭耐心說著,並為前來續杯的客人再續上酒水,“我眼前這位有些醉酒,我就和他對話以使他保持清醒。”他向那素不相識的客人說道,對方似乎有些理解過來的意思,便匆匆點點頭離開,“我們能高舉酒杯談論這事情,從一開始便是因為既不可以證明萬物之間即有聯繫與關係,亦不可能證明沒有呀。為這般事情動怒,或是壞了心情,都是蠢事——彌助兄,你是清楚你不可能說服我的,也了解我不能將你的思維變得與我一樣。事情一旦超過了善惡溫飽這般世人皆所需要的範疇,再上層的思想駁斥不過是語言的唇槍舌劍,是僅僅取決於是些微措辭的博弈。至於思想本身,因為以超出人類共有的範疇,是分不出勝負的。既然如此,何不高舉酒杯,痛快喝一場,各說各話、各講各事?”
“這……”彌助露出犯難的神色,接著又面色慍怒地瞪起了迷亭,這次,卻真再沒說什麼了。迷亭信樂拿起高腳杯來,徑自碰向彌助手中盛滿紅酒的杯子來。
“祝您萬事如意,身體健康。那話怎麼說來著——啊,是的——Cheers。”侍者打扮的青年便這般與客人對飲了起來,與他對談那人卻已放下酒杯,大步離去。並無多少人注意到這場鬧劇,卻能看到那青年侍者忽然被什麼事情吸引,向著舞池之後的某處望去。
“蒼海兄……?”
三
單憑身材便篤定奪去視線的人是蒼海,也未免有些太過自信。但那人垂在耳邊的髮絲、從假面下露出的雙眼以及演奏樂器時的動作,都與迷亭印象中的蒼海無異,只是對方穿著西式禮服的景象實在太過罕見,一時間讓人對自己的眼睛產生懷疑。不過,
“——也不是就不合適啊。”迷亭喃喃道,隔著人群,注視起蒼海的一舉一動。迷亭只聽過寄席的樂師彈奏三味線,不然便是藝妓為了祝酒而奏起的靡靡之音,那位看起來像蒼海的樂師手中的西洋樂器,別說是沒聽過其音色,就連見都沒見過——那木製的琴體比起迷亭所認知的琴要更具弧度,體型也更大,足有少年的高度;有別于木材的白色琴橋上繃緊了幾根纖細的琴弦,其正被樂師手中的琴弓牽引;也是此時,其他樂器的聲音弱了下去,迷亭才聽到那“洋三味線”發出的聲音來。
如果蒼海兄會彈奏樂器,演奏出的應當就是這樣的聲音吧。不知緣何,迷亭連秋葉蒼海懂音樂、或是舞台上的演奏者就是自己所認識的秋葉蒼海的證據都沒有,卻能如此肯定。正當他為那與蒼海有幾分神似的人發愣時,對方卻投射來了視線。
看到我了嗎?
迷亭在雙眼接觸到那人凜然目光的一瞬,便已經能確定那人便是萬川閣的老闆秋葉蒼海了。可對方的視線並未黏著太久,很快又轉向了別處。迷亭這才明白過來,對方不過是向台下的觀眾瞥上一眼罷了。
自己與那穿著西洋禮服的紳士、衣著臃腫華麗的貴婦、又或來去匆匆的侍者別無二致,不過都是秋葉蒼海視線裡一個小得不能再小的點罷了——可自己的視線,全部都被對方奪去了啊!這實屬不公!
迷亭想著,正想將手中托盤放下,視野內卻又闖入一個氣勢洶洶的高壯男人。迷亭彌助瞪著眼抓起師弟的前襟,瞪向對方。肥大鼻頭下的小鬍子劇烈地扇動,能從其主人的眼神裡感受到對方的怒氣。迷亭被師兄抓著襯衫,想將對方的手拍下去,卻沒料對方並未動怒,反而大笑了起來。
“我方才被你說得尋思不過來,又喝了一杯後,才意識過來你剛才所說的話漏洞百出,不過是為了堵我的嘴罷了。”
“哦?”迷亭拍了拍對方抓著自己前領的手指。可面相滑稽的落語家並未因此舉而鬆開手,反而抓得更緊。
彌助的臉上顯出幾許得意:“我仔細一想,嚯,全是漏洞。細想起來乍一聽聽起來極有道理,仔細想想,卻發現和你平常說得差不多,不過是些胡扯罷了,只是聽起來有些莫名其妙,頭一次聽聞會被唬住。除此以外,也沒什麼了不得。”
“彌助兄,要是您猜錯了,那豈不是更令您出糗了嗎。好呀,你竟然已經知道我所說的是詭辯,那就拿出自己的論據來,證明我是錯的吧。”迷亭笑著要為師兄斟酒,卻被對方一手推開。
“別再給我酒,我要想不清楚了……這莫非也是你胡話伎倆的一環?讓我醉酒、思維不清,這樣就不能再反駁你。”彌助抬起微醺的雙眼,面具已遮不住通紅的面頰,確實能看出他醉得厲害。得到這樣的回答,迷亭雖有些意外,卻又覺得有趣。
“哦?你是這麼想的嗎?”
“還能是別的不成?”
“倒也不無道理,就當做我是在履行侍者的職責好了。那麼,你就來講講你的高見吧,彌助兄。”
彌助深吸口氣,挺直了寬圓的胸膛,卻又憋不出什麼話來。
“喝太多了?”迷亭問到。
“……喝太多了。”
“倒沒什麼關係,我本來也沒有什麼期待。彌助兄,吃點心嗎?這裡的甜點師會做蜂蜜芥末大福呢——別那麼瞪著我啊,”迷亭道,“蜂蜜芥末有益身心,吃起來味道也很好,雖然名字嚇人了點,但別看這樣,那可是珍貴的西洋果實。”
彌助的雙眼緩緩瞪大了:“此話當真?”
“當然當真,你去廚房問問不就知道了?”
“不去,你肯定是要叫我出糗,才這麼講的。”彌助的臉上又生出狐疑,過了會兒又說道,“你給我拿一個來,不然空口無憑,我要怎麼相信?”
“好啊。”迷亭來了興致,旋即進了廚房,向廚房內的甜點師隨意要了一個圓形的西洋糕點,又回到舞池邊上。彌助分毫未動,看到迷亭來了,既不表現出翹首以盼,也不全然冷漠,只是隨意招招手,叫他快些過來。迷亭便把從廚師那兒拿回來的西洋糕點擺在他面前。
“這就是那個什麼蜂蜜芥末大福?”彌助挑眉道。
“正是。”迷亭將糕點捧起,向彌助展示其渾圓的形狀,“彌助兄,要不要嘗嘗看?”
“我看還是算了吧。”
“哎呀,那我就吃了。”迷亭說著,將東西放入嘴中,故意細細咀嚼,幾口後,又故弄玄虛地輕輕點頭,吃完之後,再輕輕咋舌,從手邊取來一杯紅酒,小口抿著,“美味,非常美味,彌助兄,你真不試試看?”他看向彌助的雙眼,便明白對方已經全然上鉤,對“蜂蜜芥末大福”充滿了期許。
“不要,那名字多怪呀。我是不會過去向廚房的侍者說的。”彌助雖這麼說著,眼神卻悄然瞥了眼空了的盤子,眉間又有幾分惱怒,這幅神情被迷亭盡收眼底。
“彌助兄,我去問問看人家,叫對方送過來,這總行吧?”迷亭說著,彌助雖掩著面具,但雙眼中卻能看出喜色來,似乎早已等著迷亭說這句話了,“您就在這裡等著,我馬上去叫人送過來。”他又進了廚房,隨意叫住個女侍者,“看到那邊那位先生沒?”
那年輕侍女點點頭,迷亭便有接著說道:“他剛剛要我點個奶油華夫餅,你送去吧,要是他說東西不對,那就說是送錯了、是舞會的特別試嚐品,如何?”見侍女又滿口答應,迷亭便向對方道謝,隨後拿著裝滿玻璃杯的托盤再出了廚房。這次,目的卻是舞池後的樂隊。音樂早已停了下來,四下是客人的交流聲,不少賓客已經離開會場。幾小時前繁盛的景象,如今也蕩然無存。桌席上的盤子空空蕩蕩,裡面裝著已經冷卻的殘羹剩飯。也就只剩下拿著甜點和酒水的侍者在四處走動了。
【風風的漫畫【http://elfartworld.com/works/96317/】的讀後感,完全我流的角度解讀……也還下國王遊戲,雖然葬花的是寶玉哥哥。我沒有買蟲×璃寬這個CP。買的是畫家璃寬(肺腑之言】
四處生了層輕而薄的白紗。結了星星點點的長草委身於秋末時節,多數已從濃綠轉成老朽的枯黃,萎靡於被行人獸類踏出的山路邊上;仍有少數挺立著,可這姿態卻也稱不上傲然,最多只能說是苟延殘喘罷了。山腰已無春夏時的喧鬧,候鳥在幾日前便遷向南方,樹梢上只剩留在山上過冬的小鳥——約莫是因為天氣越來越冷的干係,他們也不再鳴叫。
璃寬赤著腳,在結了霜的泥土上緩步前進。山腰的秋季要比別處來得更早,也去得更早。山腳下的農田還未踏入豐收的時節,山上卻已能見到凜冬所露的端倪。冬季的飲食或許會被天氣所影響,不過在山腳買賣蔬菜的集市便已經能保障每日的飽腹,因此璃寬也並不焦切。他的視野被蒙了層淺淺白練的山綠籠罩著,眼角余光中,天還未全亮,但已經能將一切看得清楚。從褐黑色土地中拔起的巨木並未遮蔽那點蒼白的日光,反而用自己稀疏交錯的影子將日光的存在展示得清楚。腳下的土地不知何時起已經被鬆軟的落葉覆蓋,給予人綿軟又安心的觸感。
他在那片蒼綠與焦黃交織的景象中行走,最終停在一點胭脂色前。
那說不上是什麼特殊的景象,僅僅是朵快要枯萎的野花,只是其鮮艷的紅色在被霜露覆蓋的山間脫穎而出。即使是幾個月前,山上也難以見到這顏色的花了,她更像是從夏季遺留下來的,固守著自己的色澤,可那種執念般的倔強到了現在,也要被帶走了。
“真漂亮呀。”璃寬喃喃著,俯下身去看那朵花,觸摸她柔軟發皺的裙擺。過了會兒,他生出將其採下的想法,便小心翼翼折斷她的莖。幾片花瓣不堪折曲,就落了下來,他也悉心地將那些殘花拾起,放在掌心內。
下葬的地方選在空曠的地方,旁臨山岩。不曾凝結的溪水潺潺而過。璃寬懷中放著枯萎的花朵,他蹲下去,徒手挖起濕潤的泥土,和服的袖擺沾到泥漿,卻被主人忽視了過去。他盡力挖著,不曾為指尖碰觸到堅硬的岩塊而吃痛,直到原本平坦的土地上出現了淺淺的小坑,雙手才好像突然恢復知覺似的痛了起來。他又看了眼因秋霜蔫枯的花朵,隨後溫柔地將其放進挖出的穴口,再掩埋。不過一會兒,地面上多出了微微起伏的小丘。他坐在那裡,仿佛能感受到小丘之下正在緩緩破殼的蟲卵,再過不久,蟲就會出來,吞吃那朵漂亮的花吧。
他在那朵花的墳墓前待了一會兒,隨後用耳朵去貼近平坦的地表,細細聽有別于地脈、水源、風聲的一種聲音,其蓬勃地在地面下攢動著。那聲音漸大,可最終又被水聲所掩蓋。
蟲醒了。蟲醒了呀。
它在地底吞吃著死物,蠕動、翻騰。萬物生長在其上,生養於蟲龐碩的巨軀,也將被其吞噬,化成蟲軀的一部分,埋葬於蟲。璃寬躺在土地上,感受著身上附著著泥土的蟲的生命,想象著花朵被蟲吃掉的模樣,微微闔上眼。



*总算是搞出来一篇……感觉已经到了懒癌末期【躺尸】。
*算是回上了少爷和老板的互动?以及希望没有把编辑先生写的ooc,如果真的那样了的话大概只能剖腹自尽了吧【思考】
*以及希望时间线没搞错……写的时候没网,太捉急了。
----------------------------------
距若江悠芙从家中夺门而出,已经过了数月有余。
路过万川阁的内院,看着已经郁郁葱葱的花草树木,她突然意识到了时间的飞逝。春天的花开的含蓄,一朵两朵的,像害羞的姑娘,总是遮遮掩掩。她的眼中只能看到模糊的景象,因此若不是走近,往往忘记了冬天已过。但是夏季不一样,到处都是绿色的叶丛,红黄的鲜花,一团团一簇簇,不用费力去找,也会自动的跳入眼中。大块大块的色团总是清晰直白,让她知道,那是百花盛开。
这个城镇,这个时节,让人感到无比舒适,以至于她都忘记了自己并非是本地人。
但是今天突然看到那显眼的颜色,意识到时间如白驹过隙,而自己,终究不属于这里……
“若江君?”
不待她多想,一声呼唤将她从伤感中拉扯回来。晃神中,手中一个哆嗦,托盘险些落下。“来了。”她应了一声,颇有些心悸。
“老板,茶和点心。”轻叩门扉,将门拉开一条缝隙,把装有绿茶和团子的托盘推了进去。雨烟袅袅的绿茶,旁边粉藕色的团子放在鲜嫩的竹叶上,作为下午茶点再适合不过了。她知道房间内有客人,没敢多留,起身就要关门离去。
“若江小姐,请留步。”
“石野编辑?”她转过身,仍旧跪坐着,看向了那熟悉的声音的来源。
坐在屋内的石野当间朝着他点了点头,算是见面的招呼。他是万川阁的常客了,虽然不是来买古董的顾客,但一个月总会来上三五趟,甚至更多。
他叹了口气,无奈道:“你偶尔也劝劝秋叶啊,不要让他总是拖稿了。你的插画都画得比他进度快了吧?”
“没有的事,”一旁的秋叶听着石野略带嘲讽的话语,淡然的拿起茶杯小啜了一口道:“她都是看完后才画的。”
“那若江小姐可比你效率多了,你倒是学习学习啊。”
“嘛……毕竟是年轻人,正常。”
“我不管什么借口,总之请务必按时交稿啊。不然我很为难的。”
“嗯……”
“所以今天能交稿吗?”
“似乎还差着点,若江君的插画也还没画吧。”
“嗯,嗯……”悠芙苦笑着听着他们的对话,被点名道姓后只能顺着老板的意思撒谎道。她平时除了整理店里的老物件、接待宾客、打扫卫生,闲暇时间便是拿着笔随手涂抹。她会提前向秋叶请教这次要写的内容,然后凭借自己的想象,提前便画好了出来。
“若江小姐你也……那不如趁着现在,秋叶先生这就去写吧!”
“若江君,我们的纸是不是已经不够用了?还有……”
“啊,有、有客人来了,我去看看。”从前厅突然传来的开门声躲不过若江悠芙的双耳,她像抓住救命稻草似的连忙起身致歉,慌慌忙忙的逃离了这个纷乱的战场。只留下秋叶和石野,再次就稿子展开了口舌之争。
--------------
若江一边缓步走着,一边整理着由于跪坐而褶皱的和服。她的和服并不是最传统的那种,而是改良版,相对方便美观。不是她不喜欢传统服饰,而是受个人限制,实在是不能自力更生的穿好。
“来了。”她推开从内院通往店内的门,随口应着以防客人着急。
古香古色的店内,一位先生正端详着摆在架子上的古董。她是根据身高和提醒判断这是位先生的,那身形看着有些熟悉,但无奈从未看清过他人的面孔,不听声音,无法辨人。
“咦,这不是前几天的……”对方闻言转过身,正好看到了推门而入的悠芙,却是惊呼出声。
“啊啊啊、咦?!花、送送、送花的…先生……?”对方刚刚出声,她就认出了来者。之前在街上慌忙的乱跑,因此撞倒了别人;无意中露出了已是白骨的左手,最后却是被安慰鼓舞了一番。当时慌张的不得了,道过谢后还没来得及询问对方的姓名,就为了掩盖自己的失态匆忙的跑走了。现在听到熟悉的声音,竟是又想起了那日对方为她系上的鲜花。
她分辨不出是什么品种,但感觉得到它的勃勃生机。悠芙喜欢它们,不仅仅因为是美丽的鲜花——她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觉,这花朵和她灿白的手骨真是相得益彰。因此,它还被系在左手腕上安静的吐露芬芳。
“是我,不过我的工作可不是送花工呢。说起来还没有自我介绍吧,”对方看着紧张到结巴的若江,露出了一个平和的微笑,道:“在下朝仓弥生,家里经营百货贸易。请问你是……”
对方的语速并不快,但是结结巴巴的悠芙还是没有能力插嘴进去;她的意思并非是送花工,而是“给我送花的先生”。——但是看到朝仓似乎并不在意自己小小的口误,她心中的石头也算是轻轻落了下来。
“若江……若江悠芙。”出于礼貌,报上了自己的姓名。
“太好了,终于知道若江小姐的名字了。那天你那样就跑走了,我还担心你会不会再撞到别人呢。”
“抱歉……那天、给朝仓先生,添麻烦了……”
“没有的事,我很高兴能认识你。”
“我、我也是……不不不对,是很荣幸……认识朝仓先生…”虽然明知看不起请对方的面孔和表情,但悠芙还是涨红着脸不敢抬头。低着头弯着腰,整个人都要蜷起来一般。
对方似乎轻笑了一声,随后道:“若江小姐不用这么紧张,不然怎么帮我介绍店里的东西呢。”
这话像一剂良药,一下子让悠芙镇定了不少。她大口的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双手叠放在起起伏伏的胸口,三次过后,终于恢复了平时的样子。
“抱歉,让您见笑了。”她说:“如您所见,我是这家名叫万川阁的古董店的店员,老板正在处理一些私人事情,所以暂时由我来招呼您。”
“请问您有什么看上的物件吗?”
朝仓看着一下子变得十分靠谱的店员悠芙,眼前一亮。他连忙转过身,看着刚才自己端详的那个古瓶。
“这只梨花瓶,可以让我看看吗?”
悠芙朝着对方的视线望了过去,她记得,那边的架子上摆放着两只同款瓷瓶。一只是梨花瓶,一只是桃花瓶。颜色相近,花样相似,而瓶身则一模一样。她一时有些迷茫,但是不好意思直接表明自己的眼疾,只好摸向了其中一只,边问道:“是这个吗?”
二分之一的几率,她祈祷着自己不会暴露。
“……是旁边那只,这个是桃花的。”
“呃……”
她还没握实的手连忙送了开来,就像是碰到了炽热的火炭一般,脸也变得通红。
“你,看不见吗?”突然,朝仓微微低下身子,看着紧紧盯着两个古瓶的若江。
“不、欸?怎么讲……”不知道为什么,她第一次羞于承认自己身体上的疾病。为此,她的脸颊也变得更红了,但是自己都搞不明白那原因是什么。
“这两只古瓶相似的很,只有上面的花种不一样。它们都不是稀罕的品种,但却极为相似,你作为店员更是不可能分辨不出上面的花纹。”他略微沉吟,继续道:“所以……”
悠芙听着对方的分析,一时呆住了。她咬着下嘴唇,沉默的点着头。
“抱歉……其实,只是看不清而已,并不会给客人们造成过多麻烦的。”
“若江小姐,我不是这个意思——”
“没事的!”
悠芙蓦地变大的声音传入朝仓的耳中,他一时竟怔住了。只能看着徐徐转身,缓缓抬头的悠芙,听着她轻柔得像羽毛一样的声音——
“没事的,朝仓先生。我和你们不一样,我从出生起,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世界。已经习惯了,”她说着说着,唇角竟微微上扬:“其实这样的世界,也很有魅力呢。”
这样吗……
“这样啊。”
人就如同一只蜗牛,胆小的蜗牛只会躲在壳里,一生一世背负着沉重的枷锁,需要安慰与抚摸,任凭别人如何激励却都不会改变那懦弱的看法;而勇敢坚强的蜗牛却不同,他们把沉重的壳当做是一种机遇,一种考验,他们会同它一起,走过一生一世……
“抱歉,是在下多事了呢。”他讪笑着,揉着自己梳理的整齐的头发。
“不、不会……呜…”
看着像被欺负了一般,随时都有可能哭出来的悠芙,朝仓弥生转过身,看着木架上的那两只古瓶道:“但是若江小姐,比起你的眼疾是否会给客人造成麻烦,我更担心是否对你的生活不便啊。”
“嗯、多多少少吧。所以……我会避免去热闹的地方。”
“那得错过了多少精彩,太可惜了。之前的舞会想来也是没参加吧?”
“啊……是的。不过我有听老板回来给我描述呢。去了的话,才是碍手碍脚呢。”
悠芙带着朝仓在店里走走停停,偶尔看到感兴趣的古董,朝仓会暂时打断当前的话题,悠芙也尽职尽责的进行描述。屋外阳光正好,金色的光芒从木窗打了进来,惹的无数细小的尘埃纷纷飞扬起来。
“在这里工作,很适合你呢。”
悠芙怔住了,她有些不解的歪着头。
“抱歉,看着若江小姐工作的样子,突然脑海中就这样想了。”
“谢谢……唔,朝仓先生又是做些什么的呢?”
“我?”他指着自己道:“我还算半个学生呢,但在帮忙家里打理朝仓百货店。”
“朝仓……百货?”悠芙喃喃自语着,努力的去回忆这座城市里某处的那家大型百货店。终于,她记起了那是一家大商店,车水马龙络绎不绝,是个热闹到让自己总是匆匆跑过门口的店铺。第一次路过的时候,穿着廉价木屐,改良和服,眼前一片朦胧的她,看着三两成群的人形,的的确确感受到了违和。左手狠狠地揪着宽大的袖子,她面红耳赤的跑开,从此便绕路而行了。
“咦?”朝仓放下了手中的香炉,转过头看着悠芙:“若江小姐没有去过吗?”
她点头,算是肯定。
“那里,太热闹了,不适合我呢。”
“这样啊,”朝仓弥生若有所思。
“那下次我带若江小姐去参观吧,”他说着,突然伸出手去,轻轻的牵起了悠芙变为了白骨的左手:“两个人拉着手,就不会害怕了吧?”
白皙又纤细的骨头上,系着的是熟悉的花朵,美艳不可方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