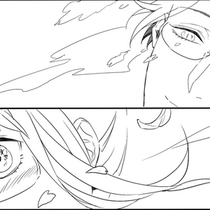長谷部+宗三,嫌惡組,no腐向,腐向評論也NG,謝謝合作。
attention!雖然連ヘイト創作的へ字都算不上(當社比)但是會出現刀劍之間認真地互黑,何でも許せる方向け
==========================================================
进入视野的第一样东西,是僧衣的下摆。
他在朦胧之中觉得有些奇怪。谁会把僧衣垫在刀架下面?难道是他被放在僧衣之上了吗?但如果是那样的话,视野中僧衣与自己的距离又有些微妙地遥远。
如果能靠近些看看那袭僧衣就好了。
这么想着,视野中的僧衣就真的急速接近了自己。
“……?”
最先感受到的,是某种难以言喻的沉重感。然后是离自己很近的地方发出了一声钝响,某种从未经历过的不快感觉从视野上方缓缓扩散开来。僧衣的格子纹填满了整个视野,他花了好一阵子才明白过来,似乎不是僧衣接近自己,而是自己掉了下去。他静静地留在那里,等着听到声音的某个下人来把自己放回去,但就在这样等待的时间里,让人烦躁的不快感也一直在主张自己的存在。
不知等了多久,不远的地方传来纸拉门被拉开的声音。有人大惊小怪地叫着他的名字,是一个高亢得有些奇怪的声音。大概是哪里的小姓吧,他忍耐着完全陌生的不快感,静静盯着格子纹的一点这样想道。
“我还想说为什么过了这么久都不见新刀出来……宗三左文字你这是做什么呀!你不会是被衣襬绊倒了吧!?”
开门进来的小姓咋咋呼呼地说着一些意义不明的话,却就是不把自己捡起来。宗三左文字恨恨地抬起头,看到的却根本不是什么小姓,而是一只长相愚蠢的狐狸。
——……抬起……头?
稍微开放了一些的视野边缘可以看到无力地投在地板上的白皙手腕,他想凑近一些看看清楚,那手腕却朝他的方向自己弯曲了过来。
他眨了两三次眼睛,试着让那条手臂朝右边移动,手臂就真的有些笨拙地朝右倒在了地上。
“啊——……我知道了,刀剑男士里偶尔也会有像你这样的呢,刚得到现世的身体结果不知道怎么用……你等一下,我去叫近侍过来好了!还有你一直这样趴在地上脖子不痛吗?”
痛?
虽然不太明白,不过宗三左文字也模模糊糊地察觉到那应该就是指正在折磨自己的陌生不快感。他笨拙地用两条手臂撑在地上勉强立起上半身,一个动作停了好几次才做完。
……近侍?
终于从名为疼痛的不快感中解脱之后,他才有空暇思考这个熟悉的单词。
这样啊,是要叫人来把我再放回刀架上啊。
虽然狐狸的话里还出现了好几个没听过的词语,不过那对宗三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笼中的鸟儿……就算对牢笼之外的东西发生了兴趣,又能怎么样呢。
狐狸像是完全没注意到宗三的负面思考,还在兴高采烈地啰嗦。
“对对,说到这个本丸的近侍是宗三你也认识的人呢,本丸里有认识的刀剑男士在你也会过得比较舒服吧!”
狐狸说了一个名字,是宗三完全没有印象的名字。谁让他历代的主人都喜欢搜集名刀呢,宗三左文字怎么可能记得住那些十把百把地排列在一起的刀的名字。
狐狸走后,宗三一个人在略显狭窄的和室里等待了一会儿,能够自由活动新得到的手足毕竟还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情,以至于和室的门再次被拉开的时候,他不禁感到有些不快。
“审神者有事不在,所以由我谨奉主命前来迎接。身体感觉怎么样了?”
与纸门之外的阳光一同洒下的是一个温和有礼的青年声音,听起来似乎是有那么一点耳熟,但果然还是记不起来。宗三懒洋洋地将视线投向声音的主人,依次进入视野的是金红两色的刀拵,西蛮教士风的服装,端正的脸庞和温和的笑容,……紫色的双眼。
“……啊,呀,是你啊……”
宗三抬起衣袖掩口而笑,而后第一次听到了自己发出的声音。
“下贱的无铭刀。”
宗三左文字是真的对压切长谷部这个名字毫无印象,不过不是因为不记得,而是因为不知道。在桶狭间的战场上第一次遇到那把刀的时候,他还没有名字。无论是开战的号角吹响的时候,还是义元的头颅滚落在尘土之中的时候,宗三左文字都没有被拔出来过一次。如果是新的主人……他怀着这样淡淡的期待被从义元的尸身上拔下来,还未习惯那个年轻人手掌的温度就被扔给了一旁的小姓。
“磨短。茎表里刻上……「织田尾张守信长」和「永禄三年五月十九日义元讨捕刻彼所持刀」,就这样吧。”
之后他几易其主,一再被刻上新的印记,然而只有最开始的那个年轻人漠不关心的声音,深深烙在他的记忆之中。
小姓恭敬地双手接过他的时候,他第一次感觉到了那道视线。
从那时起就被信长佩在身上,不知沐浴了多少鲜血的无铭刀,依然保持着温和的笑容,看着他的眼神却还是跟那时一模一样,充满了嘲讽与轻蔑。
“有力气说话的话,就表示已经可以自由活动身体了吧。站起来,无用的装饰品。”
说起来,无铭刀的名字的前半部分宗三好像还是有点印象的,毕竟他得到名字的时候,宗三和他姑且还是侍奉着同一个主人。他已经忘记了那天的天气是晴是雨,抑或那个茶屋主人到底犯了什么过错,依稀记得的只有信长静静起身时传到自己身上的震动,无铭刀出鞘的时候也没有声音,雪光般煌煌生辉的刀身朝下挥去的画面不知为何看起来缓慢异常,像是一个毫无真实感的白昼梦。
一瞬之后,刀身上溅满了鲜烈的红色。
如果宗三在那时就有人子的身体,他一定也是会蹙眉抬袖覆住口鼻的。信长空挥了一下无铭刀,甩去不断滴落的血珠,没有名字的付丧神面无表情地站在一边,满身淋漓的鲜血似乎没对他造成任何影响。比起无关紧要的茶屋主人,信长似乎对爱刀的锋利更为关心,当天之内无铭刀就被赋予了名字,短短的四文字,既无雅趣也看不出一点文才,这样的名字还不如干脆就一直无名算了,你不这么觉得吗?——宗三那天难得主动跟无铭刀说话,也许是他刚好心情不错,也许是他很久没有近距离看过那么大量的血了。无名的付丧神……现在应该叫压切了,压切的表情微尘未动,只是轻轻抬起眉毛做出了一个勉强可以算是困扰的表情。
“无论名字如何,身为刃物只要能斩……敌人就够了吧?”
宗三到现在也不知他那句话究竟是有心还是无意。
听说给了无铭刀后半部分名字的,是他的第二任主人。远征归来的宗三走到审神者的房间前,听见无铭刀对审神者抱怨信长将他赏赐给连直臣都不是的家伙,擅自抱怨完一通之后话锋一转又请求审神者称他“长谷部”而非“压切”,连三岁小儿都看得出的本心。宗三站在纸门之外一动不动地听着他们的对话,指尖感受不到一点温度,想必脸上的表情亦然。
当初是谁说的,有认识的刀在就会过得比较舒服?
互为钢身铁骨的时候尚且无法理解彼此,何况如今这副连自己都不甚理解的人类姿态。
莫名其妙的不快感从身体深处沸沸而起,宗三伫立在廊下的阴影中许久,终究还是没能拉开那扇薄薄的纸门。
转身离开的时候,似乎又感觉到了那道令人厌恶的视线,他猛然停下脚步,门里传出的依旧是无铭刀与审神者疏松平常的会话。
数日之后,他与无铭刀同队出征,途中却遭到了名为检非违使的乱入部队奇袭。混乱的战场之中,碰巧身处同一个地方的两人自然不得不并肩作战。数不清是第几个敌人倒伏在地上的时候宗三抽回刀身的动作慢了一瞬,视野的角落似乎有什么以惊人的速度朝着两人中间直冲过来。
传入耳中的是衣袂割裂的声音,映入眼中的是长谷部脸上的新鲜伤痕。
“……哈哈!”
长谷部发出的声音,比起笑声反倒更像是渗满狂气的战吼。敌方打刀胸前的伤口喷出大量鲜烈的红色,全身溅满血液的青年顺着抽刀的势头已经回身冲向新的敌人,与此同时的宗三左文字则是抬起衣袖掩住口鼻后退一步避开了飞溅的血沫,两人的动作流畅得没有分毫冗余,仿佛他们从四百多年前开始就一直重复了无数遍这样的动作。
前进的一步与后退的一步,两人之间一瞬空开的距离,一如那个狭小的茶屋中鞘內的他与那道雪光的距离,遥远得近乎绝望。
只是如今,异族的野兽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发出厌恶的咆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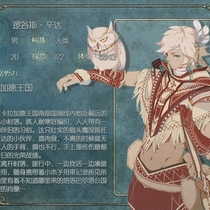

【算是很久以前寫的了(捂臉)】
“當秩序死去,人只不過是動物。
當秩序死去,動物們相互殘殺。
當秩序死去,動物們自相殘殺。”
序章 市集
他離開劇團已經很遠了,那過去曾經,現在依舊,將來還會是他生命中的一切。他又為什麼一直走了這麼遠?很痛,他有一次從鋼索上摔落,儘管有安全網,但還是流了很多很多血,也是這麼痛。
他該怎麼辦才好。
不可以,一個沙啞的聲音說,遙遠像迴聲一般但是又彷彿就在身邊。不可以,還不可以。
天氣很冷,他走進市集便不再前進,一方面他累了,另一方面再往前就開始靠近戰場和軍營,他不喜歡戰爭和戰爭所帶來的所有東西。市集似乎還未被這暴風觸碰,仍舊擁擠嘈雜,不過更多無奈和嘆息,士兵都沒了,那些原本四處巡視管理治安。
天色逐漸昏暗,他聽見有商家的老闆跑出店門一邊大喊小偷。
-- 荒 誕 之 市 --
第一章 秩序已死
他到處詢問,但看來似乎沒有店鋪原意在這種時刻僱用新的幫手,在他絕望的放棄後,他知道自己可能好一段時間都得住在街上。他不小心撞到一頭棕灰色的驢子,驢子回頭,喃喃自語著惡毒的字眼。
他看見一隻牛倒在路中央,胸膛被打開,裡面的東西散落一地。路過的都紛紛繞路而行。他記得在戲劇裡人們對死去的總是驚恐和悲傷,那麼血與死亡應該是是無比可怕的東西。
最後他落腳一處小巷,兩片屋頂遮蔽的窄小空間,堆放著一些廢棄的木板,他在那裡將包放下,包裡裝著他僅有的物品:一把小刀,一件上衣,十顆彩球,兩個銅板,一份劇本,一個針線包,一小盒快用完的顏料。他縮在牆角,頭靠在膝蓋上,很快便睡著。
此時巷口的邊緣兩隻喜鵲正好奇的對望。
第二章 兩隻喜鵲
“那是誰?”第一只眼睛這麼說。
“他有一個包。”第二只眼睛回答。
“是值錢的東西嗎?”
“不可能的。”
“他是從外面來的。”
“去告訴他們。”
“做掉他。”
“做掉他。”
竊竊私語,然後匆匆離去。
第三章 如幽靈般的
他在街上做街頭藝人,來來往往的都是他的觀眾,瞄一眼然後離去,偶爾有些停下腳步,很到一部分會慷慨的給予硬幣,一天下來收穫並不大,但他一點都不在乎,他只是覺得這不是一個討人喜愛的地方,也沒有令人喜愛的觀眾,看那些麻木呆滯的臉,拒絕一切快樂,那麼他的演出便毫無意義。
然後他就見那些長了尖角的山羊在群眾的最前方,手指間轉動的匕首映著他們深藍的眼,雙耳貼著頭顱被釘起。他差點漏接落下的一顆彩球,當他再試著尋找那些山羊時,他們已經離開了。
日復一日他們出現又消失。
地上逐漸開始出現積雪,他想他已經在這裡生活兩三個禮拜,但他不知道確切的時間,很久,他覺得,他應該換一個地方住了。於是他第二天找到一間廢棄的空房,原本可能是店鋪,有火燒過的痕跡,建築已經所剩無幾,滿地的木頭碎片和玻璃,他住在地下室的倉庫裡。
第四章 長角的魔鬼
半夜他被腳步聲驚醒,睜開眼睛的下一瞬間,那隻山羊——就在離他這麼近的地方,角頂在牆上,他能感覺到那些僵硬的羊毛刺痛他的臉頰。“你不准離開。”第一隻山羊說,用手摀住他的嘴,他用力掙扎卻一點用處也沒有,“你沒有地方可以去。”
“這裡是我們的地。”第二隻山羊說,一邊翻開他的包,儘管他已經藏起所有重要的東西,但山羊還是拿走所有的硬幣,“一切皆歸我們所有。”
“沒有人會幫你。”第三只山羊說,走到他的側邊,“因為這條街是地獄。”在第一只山羊閃開後他踩住他的脖子,“做好你的工作,我們明天還會再來。”他移開那隻腳,然後用力的踢了一下他的手臂。剛才呼吸被突然剝奪令他這時只能痛苦的咳嗽,從地上爬起來時,那些山羊已經不見。
他縮在角落,無法入睡。
第二天早上他沒有離開倉庫——一整天都沒有離開,都待在那幾乎無光的地方,睡睡醒醒,睡睡醒醒,他真希望劇團從未解散,那樣的話他就永遠不用停在這個街上。
他夢到他的舞台。
第二隻山羊拉著他的頭髮,湊近他的耳朵,“你違反命令,必須懲罰。”
很痛。他躺在地上,明天可能會很不舒服,他動動手和腿,還好,應該沒有骨頭斷掉。以前當他犯錯這樣的事也經常發生,團長說懲罰讓他變得更好,他可以知道自己犯錯的嚴重。團長總是正確的。
第五章 那聲音
那雙紅色的雙眼在黑暗中跳動閃爍如火光。
“你是誰?”他問。
“你是誰。”它回答。
第六章 屠夫魚
他在街上遊蕩,隨著天氣變冷街上也變得空曠。轉過一個轉角,他聞到一股難聞的氣味。
屠夫的店鋪就在這裡,那手執屠刀的魚穿著骯髒的圍裙,砧板也從未清洗過,污水流到大街上,匯聚在水溝邊。屠夫總為鄰居所厭惡,他們身上的惡臭和髒污似乎永遠洗不掉似的。
“你在看什麼?”屠夫不是很高興地說,刀尖嵌入木頭,他從動物身體裡將無用的都扯出來,刮掉所有鱗片,全部丟進一個鐵桶,然後將剩餘的與其他無頭的大魚一起掛在天花板的鉤子上。
蒼蠅在四周盤旋,爬在掛著的肉上,成群結隊。
“你在看什麼?”屠夫又再問了一遍,用更加不友善的語氣。他用圍裙的布擦擦手,轉身在後面的石頭上將刀磨的鋒利,再將第二條魚放在砧板上,那生物早已沒有動靜。
拿走他的刀。它在他耳邊低語。
他轉身走開,又聽見刀嵌入木頭的聲音,感到難過。
第七章 事情發生不需要原因
山羊每一天都出現,每一天每一天。而他什麼都沒有說,也沒有試圖掙扎,或許有一點點,一點點習慣了,玻璃碎片在身上劃出傷口,或拳腳留下的瘀傷,無論是什麼都沒關係。
他不明白自己哪裡做錯了,它們也從來不說是什麼。
它就在旁邊看著,依舊只是一團模糊的存在。它看起來跟他一樣疑惑,卻又充滿興趣。
“你為什麼不反抗?”它問。
“也許我做了讓他們不高興的事情。”他說。
“你沒有錯。”它從一個角落移到另外一個,“他們這樣做不需要理由,這是個那麼荒唐的地方。”
“你怎麼這麼確定?”
“因為他們是我的同類。”他聽見它咯咯地笑,“暴力,無理,惡……”
“惡?”他問,一邊擦掉從傷口滲出的血。
“你不知道嗎?”
他搖搖頭,可能曾經聽說過,從角色的口中,邪惡的!可憎的!卑鄙的!可是到怎麼樣才叫“邪惡的!可憎的!卑鄙的!”,他並了解,也沒有人教過他。
“惡是……”它沉默了一下,“我——而他們只擁有我的一小部分。”
“你會一直在這裡嗎?”
“我一直都在這裡。”
他給他一個安心的微笑,“謝謝。”他說。
第八章 審判一隻野兔
今日在這街上行走著的都反常地聚集在一個街口,喧鬧聲一片,他也跟著靠過去。
“看吶,這無恥的東西!”喜鵲大聲說道,他和另一隻喜鵲穿著由破布拼湊出來的軍隊式制服,背後站著四隻熊,兩隻手上握有木劍,兩隻正押著一只野兔,那兔子的手和頭都套進一個挖了三個洞的木板,全身赤裸,兩隻熊抓著他的手臂不讓他有機會逃跑。
“一個軍官的僕從!”另一隻喜鵲說,“天天在他的主人面前說著那些虛假的奉承的言語。”
“威脅來領之時卻轉頭向我們的王承,並諾獻出腹中狡猾的詭計。”
野兔前方有一個大坑,是他們連夜掀開地上的石板挖出來的,熊推著野兔向前一步。
“如此卑鄙之徒應當受審,並得到相應的刑罰!”
“這種時刻看他還能否向他的主人求援。”喜鵲嬉笑著讓開,其中一隻熊從地上提起一具穿了真正軍裝的屍體,已被破壞的面目全非,他將屍體扔進洞裡。罪犯嚇得一句話都說不出。
接著那隻熊在野兔身上倒滿了油,點起火把,他將火把觸在兔子身上,他便全身燃燒。他瘋狂的扭動身體,大聲尖叫。兩隻熊再將一桶桶從屠夫拿來的發臭的腐肉倒進坑里,觀看的路人紛紛摀住鼻子。抓著罪犯的兩隻這時放開手,用力一踢,那野兔就墜落到洞裡,再也出不來了。
過了一會,動物們紛紛離開,留下未被填上的大坑和滿空氣燃燒脂肪的氣味。
第九章 慶典前祭 上
最近一切變得格外活躍。
有什麼事要發生了,他想,這就像在新劇首演之前,劇團周圍會聚集很多人在旅館裡住上幾天,就會變得格外熱鬧。
他慢慢的走,要到一個人最多的地方,他小心的繞開被丟棄在地上一個動物的頭顱,有些已經開始長蟲,有些上頭的血還未乾。這幾天路面上有很多這樣的東西,躺在被砸壞的店鋪或住家門口的路中央。見到山羊,所有生物都要迴避,它們正瘋狂的破壞和奪取。
有什麼事要發生了。他聽見接口的鴨嘴獸對著水獺說。突然一直山羊從街角跳出來,割去了鴨嘴獸的頭,丟到他腳邊,另一隻山羊拖著水獺到巷子裡。山羊舉起拿著刀的手,不再是從前的匕首,早已換成樵夫的砍柴刀。他指著他,歪歪頭,接著回到巷子裡,不見踪影。
聲音咯咯地笑著,一整天。
第十章 慶典前祭 下
好幾日都沒有人再到地下室拜訪,他覺得送了一口氣,但又有些奇怪。
一隻手接住彩球,拋給另一隻手,機械式的變化花樣,那些觀眾也機械般的鼓掌。三隻山羊在街角,圍著一個彈琴的斑馬,不管那動物怎麼大叫或求饒他們都無動於衷——他們聽不見。第三隻山羊扭斷斑馬的手指,其他的山羊奪走斑馬所有的物品。
他移開視線,收起所有的東西,他想早一點回去,今天的雪下有點太大了,恐怕沒有多久又會開始在地上堆積。
他經過那個可憐的斑馬,轉入廢棄的建築,從梯子爬下去。
落地的一瞬間,好像踩到什麼東西,他看向地板,散落一地的紙片像雪從入口飄進來似的,他撿起一張。“:騙徒!滿口謊言的”
反复讀了好幾遍,才真正反應過來——劇本,他的劇本!
突然周圍只剩黑暗。
他微微睜開眼,後腦一陣劇痛,他感覺到自己在流血,但不知道哪裡,透過模糊的視線他看到那三隻山羊的身影,幾乎扭成一團,他們圍著一堆火,那火在他眼裡格外刺眼,他還看到他的包……不可以,他想爬起來,卻動不了。
山羊將他的東西一樣一樣丟進火堆。
全部都沒了,一切僅剩的意義。
他輕聲的哭泣。
然後它蹲在他前面,擋住了唯一的光源。
“要幫忙嗎?”它問。
第十一章 山羊之死
那雙手從他眼前拿開,之前的傷似乎沒什麼痛,但是他能感覺到握著的東西的冰冷。砍柴刀落下,卻沒有清脆的撞擊聲,只有一聲悶響。他看著自己的腳下,驚恐的往後退。
他們倒在地上——或者他們破碎的堆在地上,在那池紅色中冒著熱氣,空間中的鏽鐵味令人難以呼吸,第三隻山羊痛苦的拖著剩餘的身體往出口爬去,內臟在地上拖出長長的痕跡。
染滿血的手顫抖著。
它看他呆在原地許久,先前的得意逐漸消失,“沒關係,你只是害怕而已。”
“我以為——我以為你只是要他們離開……”他靠到牆壁上,“為什麼如此殘忍……”
“相信我。”它說, “不要質疑。”
他的聲音小到難以聽見,被自己恐懼的呼吸掩埋。
“或許……你從不應該出現……”
第十二章 一切惡
像風吹起陰影,它就這般出現黑暗中,從未如此清晰,一個巨大的身影,不穩定的閃爍著,長著枯枝般的角,它的嘴與其說是嘴,更像是臉上一個裂口,半身隱沒在暗中,隱約可見一條蛇的長尾。
身上所有傷口的痛同時回到他身上,令他頓時無法喘息。
“難道你忘記了嗎?”它幾乎心碎的咆哮,“難道你忘記他們怎麼傷害你?為何又要將我驅逐?我帶走一切痛一切恐懼和悲傷,這樣不是很好嗎?”它湊到他面前,氣息聞起來像灰燼,它張開手臂擁抱他,很溫暖,卻又很不真實。“收回你的決定,令我回去,我保護你,只要你相信。我一直在保護你,你不知道嗎?為何將我驅逐?”
它是那麼的難過。“對不起。”他小聲地說,手指輕輕觸碰它的手臂,它的確存在。
“沒關係,我可以原諒你,不管多少次。”聲音在他耳邊低語道,“你以會很少聽到我了,但你要知道我一直在這裡。”
他——它從梯子爬到樓上,現在是半夜,雪積了一層在地上,路上很安靜。他踩過地上的玻璃碎片和木屑,才想起來自己好像忘記穿鞋,在雪地上留下一串紅色的腳印——不過一點都沒有感覺。
他把手上最後一只山羊的首級丟到路中央。
第十三章 授予鹿首
喜鵲出現在他的門口,仍穿著拼湊出的軍裝。他握著砍柴刀,那兩隻喜鵲小心地退後幾步。
“你殺死了山羊。”第一只喜鵲說。
“你將代替他們。”第二只喜鵲說。
“我們的王要見你。”
“跟我們來。”
於是他跟隨喜鵲一直走,幾乎穿越了整個市集,走入居住區,最終進入一個很大的建築,看起來像是鎮長的房子或者宴會大廳,可是也同樣是廢棄的,四個人被吊在二樓的床邊,那一定是是鎮長和他的家庭。兩隻熊打開大門,裡面面很暗,只有大廳盡頭點了燈。他走上骯髒的地毯,兩邊在暗中閃爍的眼睛異常興奮,動物的叫聲充斥著整個空間。
獅子座在用紙板和木箱堆疊城的高座上,頭上戴了偽造的皇冠,四周圍了的蠟燭有的已經快燒盡。喜鵲站在他的兩旁,悄悄說了幾句話。
獅子站起,動物們便沒了聲音。
他走下來,手裡提著一顆鹿的頭顱,剜去了雙眼,縫上嘴巴,削去右角,流淌鮮血,他把頭放在他手上。
“我宣布!”獅子抬起雙臂,大聲讓所有在場的都聽的見,“你從此成為我們的一員。”瞬間群眾們高聲歡呼,為新加入的同伴。
多麼荒唐的一個地方。
他揚起嘴角,輕輕地笑了起來。
【最近寫的後續】
聲音從滿溢著腥味的地下室往上爬,一邊想著這個地方已不能再居住。它走過廢棄的房屋,踏在尖銳的木屑和器皿的碎片上,在木板並且雪地上留下另一串紅色的腳印。
半夜了,聲音抬頭,厚重的雲阻止所有光透到地上,不過對它來說都是一樣的。它慢慢走到路中央,朝左右望去能看見零星的動物首級,一半埋在雪裡,未來得及腐壞。
“躲藏在巷口街角的眼睛啊!我們的到來你們看得清楚,現在呢?是否還在暗處窺視?”它舉起手裡的東西,是一顆山羊的頭顱,底下仍牽掛著脊骨和連接臟器的管道,往空氣裡冒著熱氣,這已是他帶上來的第三個。“這街上遍布你們嬉鬧的證據,足跡一般橫跨整個街市。唉——這荒唐的地方!失了那些管理秩序的士兵,你們就同失了腦的身體,只會在原地亂轉,一無是處!一無是處!
“但這一切與我們又何干?我們不過是一個暫居此處的過路人,不曾與任何人談話也不曾惹怒任何人,就是當我們作空氣也毫不為過。然而——然而!你們非要夏索參與其中,將他逼至絕境——不過說到這裡我還得為此感謝你們,幫了我一個大忙!”聲音大笑,將頭顱仍在地上,與另外兩個堆成一堆,“既然如此就讓我——就讓我替他出演這一齣可笑戲,在這裡添上最後的裝飾——就當是作為晚到的招呼和感激的謝禮吧!還是你們仍嫌誠意過輕?!那就再讓他們來啊!若你們的領頭還有更大的能耐,就再讓他們來啊!無論多少!我都將全數返還!”
這時它突然轉頭,正好捕捉到一雙眼睛縮回黑暗之中。果然是在的,它朝那個方向憤怒地咆哮:“逃!逃!振起你們的翅膀!去通報給你們命令的那個人!告訴他,那個外來者願意做他——做你們的玩伴!你們既然要奉我的名行事,就要做好被本人取代的準備!”
聲音站在原地,它覺得此時應該會有潛逃的腳步聲,但是卻被雪隱蔽——沒關係,它對自己說,想像著那些東西慌亂地竄逃,回去自己的窩向領頭求助——不禁又笑出聲來,在空無一人的雪地裡站了許久才轉身,開始想今晚還能在哪裡過夜,雖然自己是不介意與死屍待在同一個空間裡,但是夏索不會喜歡。它有些訝異地發現路上的血腳印,顯示出來來回回走了三遍,低下頭思考了一會,想起來自己好像忘了穿鞋。
都是一樣的。它邊走邊揚起嘴角,一點感覺都沒有。
现存者:三个男人,三个女人。
铅笔划过纸面,这熟悉的声响让草仪森林觉得安心。
这声音的节奏频率,那些字迹的轻重缓和都在他的控制之下。
“按照一般演剧论发展的话,接下来的人物走向有这么几种。”
他好像给制片人或者剧作科的学生讲课一样,敲了敲桌面。
然而空荡的屋子里只有一片沉默回应。
1.遵守规则——随时间推移胜出or死亡
2.逃避发狂——不受控制的起爆剂可以推进剧情发展,但也会打乱节奏。
3.摸索&解密者——主角阵营往往在这个位置。
中途必有牺牲,最后也许能有人成功——尽管答案也许是更大的绝望。
他想到这个可能,一瞬间停下了笔。
“……”
寂静让他觉得自己的课程不是那么有意思,于是半开玩笑地提起了另外的可能。
“……嗯,一些作家也许会加入爱情要素。”
他很少带着自己的感情去评判他人的作品,但硬要说喜好的话,他并不喜欢现在的流行——不管什么世界观和剧情,总要加入爱情要素的这种风潮。
话从口出,他才发现自己从来没认真考虑过这种可能。
在这种谁都不能保证明天能够平安醒来的情况下,这种走向极端的感情萌生也并不奇怪。
人在面对无力对抗的存在时,最终只好把眼光重新投向自己。
“大爱救世界”——其实不过是即将消失的思考能力在拯救最后的一点自我。
“我果然还是很嫩啊……”
他觉得自己的字有些颤抖,于是放下笔,决定走出房间,呼吸些宽广空间的空气。
---------------
警察的尸体已经被清理得干干净净,就好像这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想起第一天这个大叔带领大家各自介绍,知道游戏规则后又四处奔走调查——然后莫名其妙的挂掉了。
“其实也不能算莫名其妙。”
他一边走一边继续自言自语,
“这个走向简直是必然——看起来最能解决问题的人一定会最先退场——不然剧作家就得和他斗智斗勇了。”
他嘟嘟囔囔着走到了庭院附近,那里有几张朴素的长椅。
它们似乎从来没有被人使用过——除了一张以外。
长发少女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那里,她听到脚步声,警觉地抬起头看了过来。
“啊……呃……不好意思打搅到你?”
草仪停下了脚步,条件反射般举起双手摆出投降的姿势,耸了耸肩。
身穿蓝色连衣裙的少女有点困惑地盯着他,但是看着对方有点可怜兮兮的样子,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不介意的话,稍微聊聊?”
然而男人得寸进尺,带着他标准的,略显疲惫又看来无害的笑容,
“我想咱们都需要散散心,三夏椿小姐。”
听到自己的名字,少女不自然地动了一下手指。
但是就像这个人说的一样,这种情况下他们彼此都需要倾听者——哪怕对方也许不怀好意。
只要小心点不多说就好了……
少女想着,移动了一下身体,给草仪让出一块地方。
草仪客气地点头示意,然后坐了下去。
长椅不是很宽。
他们的距离就像第一次约会的情人一样有点微妙。
草仪坐下的地方一半是材质本身的冰凉,一半带了点少女的余温,他有点尴尬但是装作平静,但还是不自然地摸了摸下巴。
“我叫草仪森林。……呃,虽然咱们自我介绍过,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他想不到什么话题,就再自我介绍了一下。
“我记得您。”
少女短短地回了话,但是不提自己的什么。
三夏椿,看起来教养很好的大小姐。
草仪有一搭没一搭地看向少女的方向,然而对方警戒心很强的样子,一直半低着头,掩藏着自己的表情。
“嗯……可惜这里似乎没有CD机什么的。”
他唐突地貌出这么一句。
“……?”
少女疑惑地抬起来看他。
“呃,我不知道你平时习惯怎么放松,”他看向面前的草坪和植物们,“我以前紧张失眠的时候就会听些音乐……或者广播。声音开得很小,基本不听内容,但是有些声响反而容易睡着。”
“嗯……”少女看了看他深深的黑眼圈,轻轻地附和了一声。
“虽然这么说,这里的床还是挺舒服的。如果能睡着的话……”
他又说了个只有自己才能笑的笑话,三夏椿眨眨眼,不知该怎么回应。
“说来有的人换了床就睡不着,你怎样?”
男人突然把视线从草坪收回,对上了三夏椿透亮的双眸,少女吓得立刻把脸转开,不自觉地握紧了双手。
“我,我没有什么挑剔的……”
不知是逞强还是怎样,少女硬生生地回答了这个没什么意义的问题。
“哈哈哈,那我应该向你学习。”
面前的少女看似比实际年龄还天真的反应让草仪忍不住笑了出来。
这个游戏也不知道是怎么选人的,每个人都个性有趣——
简直是最好的演员。
“……那就是说,这几天你都睡得很好咯?”
草仪把手搭在长椅的椅背上,有意无意地从空间上侵犯了少女的空间。
“……?!您什么意思……”
少女惊愕地看着他。
她不明白对方的真意,但‘夜晚’这个单词对他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刺激神经的一把利刃。
“别装了。害怕就表现出来。你其实很心慌吧。”
草仪凑近她,声音还是很轻,但是一字一句让少女感到彻头彻尾的冰冷。
“这种情况下,谁都会害怕吧!!”
少女没有想到自己会发出这么大的声音,但立刻,她对自己有失冷静的举动感到羞耻一样浅浅地吸了一口气,缩起了身体。
“……没错。”
草仪把视线粘在她就快哭出来的脸上,然后另一只手摁住了少女的肩膀。
“那就让我们互相安慰吧。”
他亲吻少女的额头,然后向下,吻住了她的嘴。
整个过程显得那么自然,简直像下午三点播出的电视剧——只要背景设定不是这个世界。
未知的体验让少女整个呆在那里,她感觉到男人的手滑向她的后背,然后顺着向下停在长裙的腰带上。
她已经无暇顾及,那仿佛一直要窥视到她灵魂深处的目光。
少女大叫起来,拼尽全力推开了对方就要压上来的身体,在草仪松手的一瞬,她连滚带爬地逃离开来,并没有注意到对方根本没有追上来的意图。
“唉……”
看着少女像受惊的小鹿一样慌乱逃走的身影,孱弱的青年又坐回长椅,调整了一个让他更舒服——看起来很慵懒的姿势。
“剧情起爆剂的角色需要体力啊……”
他歪歪嘴角,吐了自己的槽。
渐渐的,周围的世界在他看来已经是另外的景色。
没有摄影机,没有导演。
没有收视率的奴隶,没有蛆虫一样的偶像。
他是一切的起始,他是创造故事,指挥一切,随心所欲的王。
天气看起来一片晴朗,庭院看起来一片繁茂,世界和平。
他保持慵懒的坐姿,抬起头来。
然后慢慢伸开双手,拥抱看不见的太阳。
就像这个世界的神一样。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