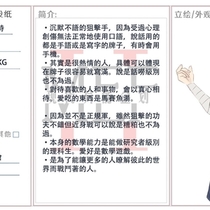魔法少女
我作為做夢者,視角似乎是電視鏡頭。
細節已經記不太清楚,只是覺得夢裡很震撼;雖然叫做魔法少女,但是實際上身為主角的九人team中有男性也有女性,每個角色都有自己的代表色,隊伍應該是五女四男的比例。設定似乎是靈魂特別明亮、能照亮他人靈魂的人就可以成為魔法少女。雖然這麼說,但是也有靈魂明亮但不是魔法少女的人。夢的反派是外形很噁心的人外組織。
一開始很平淡,九個人覺醒了力量後,決心去幫助他人,經歷的事件有高樓倒塌,救水災,等等。我發現半空中漂浮著一個只有我能看見的數字,似乎是代表每個人的點數,如果在戰鬥中點數為零就會死亡。
之後記得比較清晰了——用電視劇的角度來講,大概就是到了結局篇吧。英雄活動失敗了很多次,九個人在頹唐時站在廣場上。隊伍的Leader(♀,代表色橙色)被告知世界的侵略將會從商場開始,壞人將會一一掠奪她身邊的隊員。當商場的指針指向兩點的時候,這裡將會爆炸。
Leader被如此告知,便對著廣播說了一段冗長的嘴炮,得到了隊員的支持。唯有作為鏡頭的我明白,她的內心其實已經接近崩潰了。
之後果真如其所說,魔法少女一一被拐走,拐走的方式都和各自的黑歷史有關;藍色代表色的女性(在夢裡似乎叫班長,戴眼鏡)是被長相很像自己父親的大叔帶走;還有一些則記不清楚了。為了拯救被拐走的同伴,Leader和代表色是綠色的少年一起上了商場的頂樓。
被怪人蠱惑的路人開始攻擊起他們。明明是自己應該保護的人,他們卻還是下手了。就在這時身為反派的怪人站了出來,大肆宣揚起綠色代表色的少年的過去——那孩子小時候被人長期強姦過。
這時發狂的人群好像要將那孩子吞噬乾淨似的圍了上去,有人打罵,有人用語言攻擊,也有要脫褲子的……那樣的人群無異不正常。少年的臉露出絕望的表情,他的四肢已經被好幾個人固定住了,還時不時有人踩他的肚子。
我身為鏡頭,在人群中看到了他們曾經救助過的路人。反派似乎是意識到了我的視線,大笑著說道他們(路人)並不是被我們洗腦才會這麼做的,而是原本就有那樣的想法,我們把那種情緒引導出來罷了。你們以為身為正義者這樣就可以了嗎。
少年絕望之後(被玩壞)被怪人手下帶走,怪人的BOSS站在一旁摸著Leader的臉說道:“你最後的親族都已經被我們拉扯(確實是這個動詞,不懂夢裡的自己)下來,絕望吧。”
這時我眼前突然出現了九塊電子屏幕,上面播放的都是魔法少女成員的現狀。紫色那位似乎被什麼東西迷住了,藍色的班長和自己幻想中在一起,剩下的幾個已經記不清楚,依稀地記得青(♂)被人挖出來了眼睛,正躺在地板上。
綠色的少年在被路人圍攻的過程中已經被打得失去反抗能力,恍惚間,我似乎聽到有人在喊不要打他的臉,打得鼻青臉腫就沒有強姦的慾望了。
怪人說:“結束了吧。”
就在這時,一直身為鏡頭的我,不知為何說話了。
我問leader:“還要救那些孩子嗎?他們的靈魂點數已經快要歸零了哦。”
說完之後意識到自己的語氣和聲音是QB語氣,實際上造成這些悲劇的,可以說是因為我也不為過。
Leader只是站在那裡,並沒有回答。再仔細一看,她的靈魂點數已經是零了。
只是站在那裡死了,連倒下的過程都沒有,所以我沒有察覺到。
我突然意識到自己在少年被爆出小時候的黑歷史前,一直站在他肩頭上。直到他被撲倒以後覺得這個視角太危險,才跳到被人浪分隔開的Leader身邊去,看著Leader無用地向人群大喊。
七騎士
我是男性。夢的背景是末日,周圍的人類不是死了就是變成怪物。這時候身為男主的我和六位夥伴在城市裡開始了某項任務。感覺上似乎是仿照七美德,每個人都有一種神奇能力。但是除了七美德每個人又對應一種七宗罪。人設上似乎是我(黑髮少年)神秘的女角色,不良少年,眼鏡,賢惠的妹子,剩下的忘了。我們七個就在廢墟裡打打殺殺,直到進了一個百貨公司似的建築,驚奇地發現裡面的人都很正常,然後神秘的女角色就說要找找看【王】……於是我們就打算進去看看。
王是什麼,我們也不太清楚。
在百貨公司裡面和一個老頭鬥智鬥勇。他似乎是boss,結果這個時候從百貨公司的地底爆出什麼東西,建築塌陷,有夥伴死亡,怪物來了,不良少年第一個衝出去,直接被穿透全身,血濺得到處都是。眼睛男也死了。我拉著賢惠妹子的手,正要放大招,結果妹子就在我手邊被戳死了。重傷的我躺在廢墟上,身旁是神秘女,她看了我一眼。
她說要組織這一切不如從根源上停止這個災難。
夢開始了第二周目,我在災難開始前去尋找同伴。這一次解釋了一下,說我們七人的身份是騎士,存在的目的就是要保護王。但是實際上王是誰我們也不清楚,連神秘女都不清楚。
二周目的不良少年很中二,我就嘴炮教育他。同伴們因為我教育不良少年而圍了過來,不過這次不認識我了。(因為是第二周目)就在這時發生了地震,我對神秘女說道:“【那天】要近了,我們要開始【造王】。”
這個時候我突然發現自己的記憶不對,其實我是從未來穿越過來的,二周目才是一週目,真正的二周目裡我忘了什麼重要的事情,然後神秘女是我們未來人和過去人接應的。似乎未來人要避免【那個災難發生】但是他們也不知道王是什麼,只知道是災難的關鍵。
地震之後我對神秘女說那個要來了,必須要開始造王了,得要選出來的王是誰,後來在人群裡中選出了一個正太。但是根本沒用,災難還是開始了。
我們深入一個地下的巢穴,帶著極為拖油瓶的王進了怪物的老巢。
我問神秘女,你覺得這次能行嗎,神秘女說我們已經試過好幾次了嗎?我說嗯……進去以後突然意識到不對啊,但是來不及了。
看到巢穴中央的大蠕蟲,七個人下意識地跪了下來。
原來怪物才是王。第一週目裡,毀滅商場的大蠕蟲就是王。
最後的記憶是跪著的我在想:“也就是說人類必須要滅亡嗎。”
BL
記不清楚了,不過似乎是我做了個玩企劃的夢。夢裡的我畫風和現實不一樣,和我互動的那位我也不認識,雖然中間有些雜七雜八的事情,但是夢中的我寫的故事蠻有趣的,挺短的就順便記下來吧。
夢裡我兒子的設定是黑髮金眼,是個從小就被家暴,長大以後變成了喜歡用暴力的扭曲抖S角色的設定,他cp角色的設定是義弟,兩個人從小一起長大。已經記不清具體細節,但我兒子用溫柔的手段拉近對方的心,卻又輕易地踐踏,用暴力讓對方折服於自己。
相方屈服於這種暴力,整個人似乎早已失去了反抗的心,整個人都只是依賴我兒子而已。“已經離不開xx哥啦。”最後那孩子這麼說道。
依稀記得有張插圖是兩個孩子一起在河裡洗澡,兩人身上都是傷口;我兒子是被他父親打的,相方是被我兒子打的。
少年與房間
夢中的我是名女性。
我走在一個和式(或是中國式)的長廊上,右側是房間,每進一個房間,就會看到一段故事,那故事都在講同一位少年。最初的房間是少年身為邪教教主的爺爺在享用男色,少年只是靜靜地看著,之後爺爺被警察帶走……越往後走,少年的年齡就越大。
到了倒數第二個房間,我意識到少年即將赴去他死亡的地方。我百般阻攔,少年卻好像聽不到一般,年少輕狂地笑著離開了。
我走入最後一個房間。
房間內演起了木偶戲,這時不知從哪兒響起了歌聲。雖然聽不懂,我卻明白那唱的是少年,沙啞的歌聲好像在嘲笑我似的,一直持續著。
這時夢中的我流出了眼淚,說道:“那是我哥哥啊。”
Youtube動畫
我是以電腦前看動畫的觀眾這個視角開始夢的。夢到的動畫畫風是萌系,有點像美國動畫Adventure Time。
夢的一開始看到的角色是個小男孩,還有他姐姐,從對話裡面知道他們家很有錢,有個爸爸,看不見媽媽在哪裡,爸爸好像在睡覺,躺在床上,什麼話都沒說,只在小男孩說話的時候微弱地嗯了一聲。小男孩和姐姐開心地出門了,姐姐手上拿著一個斧子,走到陽光明媚的小區裡,和大家談話。
姐姐說要去買東西,小男孩就拉著姐姐的手一起去了。
兩個人很緊張地一直牽著手,在貨架之間,中途一直是Adventure time的畫風,作為觀眾的我剛剛開始想好無聊的時候,突然意識到商場裡面的其他客人要不是顏色奇形怪狀(像是紫色的人類)要不然就是臉變成了奇怪的樣子;看起來像臉從額頭中央往下裂開一個大口,中間是鋒利的牙齒,眼睛則被擠到了一邊。
他們就在貨架旁穿行,姐姐時不時拿斧子砍一下靠過來的人,小男孩拼命拿水拿物資,兩個人一起出了商場。回到家以後,我意識到他們家是那種在公寓樓裡面有兩層的複式。
兩人進了家門以後說“爸爸我們回來咯”。打開電腦,看到有錄像傳過來。是幾個月前在外太空的母親錄的,現在蔡傳過來。從母親的衣著來看,似乎是科研人員。
這個時候屏幕外的我作為觀眾聽到我的小夥伴說仔細看,這裡有伏筆。
母親講了一大堆話,我都沒太聽到重點,大致都是什麼你們還好嗎,我們的研究成果怎麼怎麼樣,到時候接你們來外太空啊,中間屏幕一晃看到了宇宙船的玻璃,然後鏡頭轉了轉,主要是介紹船裡面什麼什麼樣……然後母親突然說爸爸在看嗎,兩姐弟就舉起來電腦給他們爸爸看,調大音量,然後我才意識到哪兒不對,他們父親從被子裡面露出來的手是深紫色的。
他父親看著那個影像說話斷斷續續的,大致就是什麼我愛你,好想妳,之類的。電腦前的我吐槽了一下這個畫風我竟然能感受到虐,還有你剛才說的伏筆在哪兒,然後朋友給我開了個一分多的youtube視頻,重放了一下在外太空那段,然後我才看到玻璃上有個喪尸倒影,只有幾秒,要暫停才能看到。
之後視角就變了,變成政府在上空撒藥,結果那個藥是對有的患者有效,另外也有一些會發展得更厲害。
前幾個畫面都是被治愈者;其中一個是男人被治愈好,還有一個是小孩子被治好的。
最後一個是看環境是廁所裡,一個臉上嘴巴已經變了形的姑娘,跌跌撞撞進了廁所隔間,趴在馬桶上,廁所的隔板能隱約反光的,一瞬間視角變成了她的,然後她就說了幾句很絕望的話,背景音是廁所外面人們在歡呼,突然間動畫安靜下來,畫面上廁所隔板上她的臉慢慢扭曲成根本稱不上是人的狀態了。
我看到這兒心情複雜地關了電腦,轉頭看了眼我朋友,才意識到朋友的臉和動畫裡面那種臉上裂嘴的人是一樣的,只是是真人而已,但是我一點沒震驚。後來不知道做了什麼要拿手機自拍,拿著桿子拍了一張,我才意識到我也是,已經是……然後突然聽到有人說,幾年前的動畫片好看嗎?
至此就醒了。
子時過後一片寂靜,那是空最喜歡的時間,換上素黑色的衣服後,他就感到自己好像化成了夜的一部分,變成真正的無——他的身形隱藏於黑夜,呼吸則被風聲蓋過,就是這樣的環境,能使自己完全地冷靜下來,把最後一點屬於自己的“特點”剝去。
他輕巧地在房瓦上跳躍著,偶爾,那些東西會因自己的體重而發出清脆但微弱的聲響,他在奔跑時能看到貓兒在屋頂上休息。空無心逗弄他們,只在接近時小心地繞開,貓兒見到來人,便撒開爪子從房簷上跳了下去。凌晨時分的天色最為黑暗,除了星光月亮外什麼也看不見,子時以後就不見了燈火,腳下的住家一片寂靜,唯獨清風搖動著樹葉的聲音能聽得清楚。空享受著自己在高處時,梁上之風吹拂過臉龐的快感。他眺望過去,街上並無什麼人。
本當是如此的。
在數片房頂之間,站著個高大的男人,空看到那人腰間配著把刀,身上的衣服不甚整齊,做浪人打扮。想必是近些日子,從別的藩國來的吧。空一直不懂得浪人為何背井離鄉,從藩國那裡申請許可,對武士來說不是什麼難事,偏偏有些武士去做浪人,還要站起來反抗幕府——空并不是不懂其中緣由,只覺得那種事情是不該做的,幕府統轄日本以來,萬事太平,溫飽無憂,又能有什麼不滿?這麼想著,空就生出種自豪感來。
既然自己身為幕府的忍者,那就給浪人些苦頭吃吃好了。空這麼想著,便從房梁上跳了下來,忍鐮直直砍向對方的脖頸——
擋過來的,是道在月色之下閃爍的銀光,其後是清亮的聲響。空為自己雙手偏離了原本動作軌跡的鐮刀而吃驚,卻見對方後手又是一刀砍來,自己只得側身躲過。
被發現了。
空對自己的身手,可說是相當有自信,可眼下,他明白過來形勢處於劣勢,自己對對方擋下來了不說,更致命的是自己錯過了最佳的機會,所謂忍者這種戰鬥方式,第一擊若是沒能取下對方的首級,接下來就要難辦了。
正在懊惱間,對方攻了過來。
“你是誰。”那男人質問著,極快的劍舞在夜中如同銀色的閃光。空拿起短鐮來,一一將那些攻擊擋了下來,直至一擊來襲時,短鐮勾住了日本刀的刀身。
“很厲害嘛。”
空說著,露出一個笑來,對方卻並不驚慌,只一個挑刀,反倒是空手中的短鐮先飛了出去。
“你……”空看向對方的臉,雲間的月亮撩開了厚重的紗,讓他看清了對方的臉,那人生得很有男子氣概,卻又清秀,好像同時把硬朗和細緻的五官揉到了一塊,正當空注視著那人的臉時,他聽到有晨間的鳥叫了。
不好,天要亮了嗎。
若是剛剛他沒靠著月光看清我的臉還好,天亮了,就肯定會被看見了。如此一來,就只好離開。
“切。”這可算是落荒而逃了。空想著,又跳上了房簷,“改日再戰。”
說罷,他便順著房簷離開了,直到出了那擁擠聚落的邊緣,才在東面等著日出。可太陽並沒照常升起,按常理,天空應當要泛魚白色了。
“怎麼回事。”他嘀咕著,向著師傅和自己的住所走去了。
【因為相方的親娘沒有把佐為登錄ELF,所以就不響應啦;我個人很喜歡日本人的國民性、天主教徒、江戶時代的反天主教風潮三者重疊在一起時,所構成的那種壓抑至病態的美感。】
少年從飯館裡出來的時候,身上穿著紺青色的短和服,沾著油污的前襟並沒受到太多在意,短髮倒是梳理在腦後,整整齊齊。清川朗向對方招了招手。見到來人,少年墨色的眸子就亮了起來,即刻走過:“武士先生好啊,今天有新醃的小菜哦。”
“好。”清川朗答應著,將腰間的刀鬆開,便進了飯館。被喚作佐為的少年又一個轉身,即刻就進了嘈雜的人海,輕巧的身子好像浮在水上的河燈似的,一眼就能在周圍的人群裡看見;那副模樣不知為何,讓清川覺得少年有種獨特的美。
家附近的飯館,以親民的價格和美味的食物聞名鄰里,可以說是這附近最為熱鬧的場所也不為過。清川朗時常在這裡吃飯,幾次下來便認識了那少年——對方是飯館老闆的小兒子,時常出來幫著父母做事。佐為的年齡又與自己的幺弟相近,便被清川當做弟弟來對待。清川回想起初時見到少年,還覺得年紀頗小的孩子就在幫著家裡做事,是很了不得的;母親即使迫於生計,也不願放下武士家族的面子讓孩子去做學徒,硬是要家中的兩個弟弟去附近先生的私塾,直到最近,二弟才去學了木匠。
“久等啦。”少年捧著發亮的茶壺,將澄澈的茶水注入杯中,孱細的水流好像剛從泉眼而出。那雙比清川的手要稍小些,卻已做了不少粗活的手熟練地做著這一切,直至筒形的茶杯盈滿,對方才停了下來。清川捧起桌上的茶水,茶清得能看到杯底,卻帶著種漂亮圓滑的色澤,他啜飲一口。
佐為從短和服裡露出的纖細手腳撐著桌子,他踮著腳問道:“今天吃些什麼?”
清川朗笑了笑,答:“吃蕎麥麵吧。”
“好嘞好嘞。”佐為提起茶壺,又輕巧地離開了。清川朗注視著對方的背影,少年苗綠色的短髮之下,是從青色和服中露出來的一屆白皙脖頸,如同冬日新雪,卻又不知為何帶著難以言喻的情色——那種美是清川朗埋藏在心底的貪慾,是他默默渴求的慾情所迷戀的東西;其是凝固的、無雜質的水,卻又帶著令人浮想聯翩的混沌美感。只要在佐為身旁,那種情感就會開始沸騰。
不行啊,這可不行,他提醒著自己。和服裡冰冷的十字架貼著胸膛,時刻警醒著他。不可犯下那樣的罪,若是做了那樣的事,他必然會後悔的。
懷中的十字架越發沉重。他默默地壓抑著那感情,不應被這情慾所吞噬。他所喜歡的,只是少年那份純粹的感情,清澈與美本是同意。佐為的潔淨就是美到那種程度——一種清麗感,舉手投足間都讓人覺得純粹得不可思議。
那正是少年的美。
貪戀著那份清澈的自己,污濁不堪。
“久等啦。”盛著蕎麥麵的碗扣地一聲放上了桌子,清川朗才回過神來。等他再看向對方時,那孩子又離開了。清川埋頭吃起了蕎麥麵,好讓飽腹感將那種空虛驅走。吃完之後,說了聲再見,便又離開了飯館。清川握著腰上的刀,想著佐為的事,少年那張白皙的臉仿佛又浮現在自己面前了,他險些因此而撞上往來的小販。
江戶之城朝早的生命力已經開始活躍,街上往來的人群如池魚般或是方向性、或是無目的地走著。清川看到有個同僚與他隨性的少年一同從身旁走過,那少年臉上戴著青澀的笑,抱著他所侍奉的主人的刀。
——不一樣,自己和那些人不一樣。清川知道,同僚之中也有不少喜好美少年的人,但是清川朗明白,自己心中對佐為的那份感情,並不相同——他已說不清自己是為什麼而戀慕那少年的了,他愛那少年水般的明澈,對方又如同聖畫上的天使般純潔;他或許是以近乎宗教崇拜似的感情接近佐為也說不定呢,只有他自己清楚,他透過那少年的清澈,能使自己得到片刻的安寧。
起先,他只是把對方當做弟弟;但不一樣,那孩子不一樣啊。清川朗無法在兄弟身上釋放自己的私心,也不會起那樣的欲念,但是對那孩子,卻不知為何感受到了些什麼。這種心思使清川起了切腹自殺的心思,可戀慕之情卻如流水一般,從未斷過,反倒逐年上漲了。
其他關係好的武士若是知道他戀慕商人家的少年,多半會去嘲笑他吧。
他蹣跚著步子,好像是老人似的,向著自己家的住宅走去。父親死後,家產變賣一半去還了治病的債,如今只剩下一棟房子。他輕聲地走著,覺得自己越發沒了力氣,走廊上的地板被擦得泛白,妹妹養的白色貓兒見他來了,便遠遠地踏著步子離開了。他打開紙門,見到母親正正坐在廳堂中央,合著眼祈禱。女人早已失了年輕時的美麗,無論是臉龐還是雙手都已佈滿與年齡不符的溝壑,看起來比同齡人要老上十歲不止。那一動不動的姿態,會讓人有片刻產生她已死了的錯覺,只有眼皮些微的顫動才能讓人意識到她還活著。似乎是聽到有人來了,她才像是從墳墓裡爬出來的尸體似的,支起身子來。
“朗啊……你還記得你父親的表哥吧……”年邁的母親跪坐著,翻動著渾濁的眼白,早已失去了生氣的雙眼裡滿是淚水,“他死啦……”
“是。”清川答過話頭,為母親所說的點了點頭,“您在為他祈禱嗎。”
“是啊,是啊……孩子,你也一同來……”母親那雙沒什麼力氣的雙手好像要拽過他去似的,清川低下頭來,順著母親的意思做了。婦人方才還陰霾密佈的臉上看到這順從的舉動,露出一個苦笑來。清川從對方微弱的呼吸中嗅出病疫的味道,恐怕母親也已經時日不多了,只是遲遲不去看病,每日收著家中的聖母像發呆。
他不是不明白母親的苦心,所以瞞過了弟妹。
前院之葉,早已凋去了一半。
……
“那麼,請清川先生進來吧。”打扮得滑稽的侍從說著,視線卻是直指自己,似乎是在觀察自己的反應。
“是。”清川解下刀來,隨著對方一同走進了房間,房間的門口,放置著一個不大不小的木盒,“這是……?”他抬起頭來,看向那侍從,對方眼裡閃過一絲狡獪。
“啊,這是踏繪,清川先生出身長崎,所以未曾見過吧。這東西是用來測試來人是否是蠻人邪教的信徒的,看吧,若是踏上這東西,就可以證明自己並非幕府的敵人了。”那侍從說著,便踩了上去,以腳來回攆著突起的聖像浮雕。
“原來如此。”
清川朗撚起一個笑來,不卑不亢地走上前去,以穿著草鞋的腳踩上了踏繪之上、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受難者。




【一個腦內廢渣,大概是後世學者寫的論文】
從古至今,凡有文明的地方必然誕生出詩歌的文化,無論是否有文字將其記錄下來,詩歌多多少少都會被傳頌下來。本文講述的是身處世界極南的沉澤群島獨有的民歌文化。儘管沉澤使用象形文字,但卻不用這些文字記錄詩歌,其原因大概與象形文字難以朗誦有關;又因為島上能夠識字的人只有祭祀,這種記錄方法難以傳播,因此沉澤的民歌多數以傳唱的方式流傳至今。在長久的歲月中,詩歌被賦予了更多的意義。
沉澤的民歌主要以貼近群島之上的生活為主題展開,也有描述情愛乃至性的詩歌,同樣,狩獵時、耕作時、捕魚時也都有相應的歌曲。在沉澤諸島上祭典時也會有祭典所唱的歌,但筆者認為與信仰扯上的歌曲不可算作民歌,因此不在本文中贅述。
在沉澤的民歌中,有三者扮演著特殊的角色。其一是領歌者,或譯作雄伶,該職位通常由部族中出色的青壯年擔任。民歌對雄伶的意義,教育性質大於享受歌唱本身,以群體為歌者的合唱歌曲中,雄伶是第一個開口的人,似乎比起歌唱者,更像是青年領袖。
其二則是啞鼓,啞鼓的扮演者們在歌唱的過程中不能言語,或是以雙掌相擊作為節奏,或是重錘沉澤鼓,也有時是以樂器伴奏的形式將節奏傳遞給眾人。有啞鼓的情歌並不多見,除情歌外的其他種類則或多或少加入啞鼓。
其三包含沉澤文化中野蠻的一面,這一職務的名字叫嘶吼者,也譯作欺啼者,通常由被抓獲的俘虜來扮演,也有時是部落的叛徒。欺啼者的作用是這樣的:他們在歌唱隊伍的隊首,通常被捆綁得不能動彈,就在這時拿著長矛或其他武器的部族勇士們刺向欺啼者的身軀,并拖動著欺啼者繼續進行歌唱,知道該欺啼者因失血過多昏厥,不再發出哀嚎為止。不,與其說欺啼者是沉澤民歌的演唱者,倒不如說是樂器要更適合些。
摘錄少許經翻譯過的沉澤民歌,望諸位共賞。
無名船歌
[雄伶領唱]:啊——嘿呀[啞鼓拍掌]海的神今日給我們恩賜呀!
[眾人]:偉大的海神,至高的存在,我們的命根[一句至今未能譯出意義的咯哈][啞鼓拍掌]
[雄伶]:啊——海的神今日給我們福慧呀!
[眾人]:豐收的漁獲,掠來的俘虜,海呀,我們的至高神呀,謝謝你!謝謝你![啞鼓拍掌]
[雄伶]:海的神呀!我們該怎樣報答你!
[眾人]:教化那北方的愚者,凡信海的留,凡不信的則殺!啊!海!殘酷的海!美麗的海!我等至高的海啊![啞鼓猛地錘敲一陣]
這首船歌在實際演唱時,是以上所有句子不停重複,筆者便不再贅述。下一首則是描繪男女愛慾的歌,這首歌中並無多少沉澤的特色,筆者的意思是,歌中並無沉澤頗具特色的雄伶和欺啼,伴奏者雖然以鼓掌為樂器,卻也並不是不能言語的雄伶。
歌以相互愛慕的男女對唱展開。
採
[男]:正是時候!
[女]:春光正美![女歌者用雙手擊掌]啊,已到啦。
[男]:你可如花呀。
[女]:情郎,情郎。[男歌者拍掌]你的後背可曾如弓般彎?情郎!
[男]:啊,戀人,戀人,你的身子[缺失]
[女]:那便一同去採些花吧!哦!我的情郎!我正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