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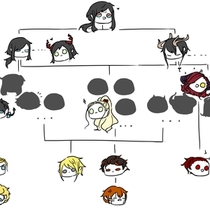
【隨便寫寫】
————————————————
【0年 舊神居】
他是承着期待出生的,至少所有人都這麼說,烏佐,維加爾,權座的利劍,這一代最接近父神的人,受眷顧的孩子必將成為未來的支柱。他還沒想好要如何回應這種期待,或者該如何告訴他們自己有多討厭戰鬥。
但是好像來不及了。
放眼望去只有血霧,就連遠方地形的變化也看不清楚,身上帶著太多傷,儘管不致命但是他清楚自己撐不了太久,爐芯已經不能再使用,空氣裡的毒氣早就讓自己喊不出聲,馬上其他的活動也會受到影響。他得回去,或者找到族人,誰都好,他需要安全的地方。
然而猩紅色的平原上只有他一個人。烏佐不記得自己曾經有一個人的時間,二十五年來他第一次——有什麼握住他鎖骨之間的那節氣管,突兀地讓他還以為自己受了內傷,心臟飛速地跳動,有哪裡在痛,可是是哪裡……
被落下了。
他輕喘著,呼出的白氣蒙了眼,此刻他只希望自己能控制自己,不行,心跳太快,會崩潰的……
寒意順著腿竄遍全身,不同於任何他受過的傷,猶如冰錐直接打穿骨頭,又同時被灼燒的侵蝕感包裹,他向下看,那雙染血的爪子嵌進肌肉深處,那瀕死的黃色雙眼和微笑他永遠無法忘記。一刻間左腿便失了力,他跌坐在地上,慌亂間將對方踢開,卻怎麼也沒有辦法將自己支撐起來。
望著逐漸被溶解的皮肉,烏佐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他見過很多了——腦中一片空白之間只能嘲笑自己大概會是有史以來最沒用最短命的劍。爐芯的鼓動逐漸變得紊亂,燃料不夠就會開始消耗自身,馬上左眼也會失明吧。然後他輕輕地笑起來,被厚重的空氣掐地窒息,父神給予的使命連一項都沒有完成。
烏佐握緊隨意拾起的金屬碎片,感受其觸碰下眼瞼柔軟的皮膚。
這是什麼玩笑……
下一個瞬間彷彿在他眼中定格。光芒之中她這麼降落,直接踢開他準備自盡的手,銀色的小刀反射出灰藍色的光芒,他看不到來者的臉,被她背上的戰斧擋住了。因見到同類的釋然和明知她會採何種麼急救措施的恐懼糾纏在一起,失去意識前她說什麼,他也不記得。
這究竟是什麼樣的玩笑——
是熟悉的味道和溫度。烏佐在腦中說道,好像在向自己確認自己並沒有作出錯的結論。他下意識地想要爬起來,可是身體沉重到不像是自己的,按著順序觸碰過爐芯集中的部位和末梢,看來並沒有壞死——本來打算因此鬆一口氣,從左腿上那隨著恢復意識而變得越發清晰的緊繃與劇痛感卻又將他帶回現實。他在中央,是重傷員療傷的區域。
“可以,還蠻快的。”面前的人眨眨眼。“我記得你是前些時候被派到五哨的新人?”
烏佐想要開口,卻發覺喉嚨乾澀到無法發聲,便只能點頭答應。
“被帶毒的空氣嗆到而已。”她說,一邊遞過水袋。“過幾天就會恢復,你很幸運,除了腿傷都不是永久的。”然後她拍了拍烏佐的額頭,“這種事情絕對不,能,有,第二次。我底下怎麼會有你這樣沒用的傢伙,誰訓練的?之後一定要全部從上到下懲罰一遍。”
“對不起,長官。”
“道歉有用嗎?”她歪過頭,毫不迴避地直接迎上他的視線,烏佐被這突然的轉變嚇了一跳。“嗯?道歉那些死去的人會回來嗎?你多殺一個敵人我們能減少多少損傷知道嗎?我的能力也有限,要不是看在劍更珍貴的份上,我能救回多少更優秀的戰士你知道嗎?”
烏佐最討厭的便是自己完全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而如今無論做什麼都已經太晚了,既不是樂師也不是弓箭手,缺乏機動性的劍,連談價值的資格都沒有。
他咬了咬下唇。“那還不如……”
接下來的句子未出口就被打斷,反應過來時已經感到溫熱的液體順著頸側往下流,呼吸也同時被截走。她的手掌可能都還不如他的手腕寬,卻穩如鐵鑄,仍舊歪著頭,原本平和的笑意早就消失無踪。“啊,啊——你倒是給我數,那種情況下去死能帶走多少影裔?嗯?給我數——”隨後她站起身,進一步將烏佐摁進身後的墊子。他沒有打算抵抗,領受上級的責罰本是理所當然,況且面前的人並沒有真正的殺意,只是異常憤怒,用盡了全力燃燒爐芯去治愈才不至於直接挑斷他脖子上的藍紋。“一個都數不出來對不對?因為你不能,要是真的覺得這是個好主意的話,在最開始,知道自己無法戰鬥的那一刻就會跑到前線自殺了吧。下次敢說這種話我把你扔進血池一輩子作下一代的養料,我的東戰場不需要你這種人。”
烏佐聽見周圍傳來試圖制止衝突的聲音,但是在人開始靠近的時候她已經將他放開,揮著手讓他們不要擔心,小心地拭掉他的血,轉身又坐在床沿。“真是浪費。”她輕聲道,一邊舔了舔指尖。“我捨棄自己的搭檔就為了救這麼個東西。”
“我……”
“你就沒必要覺得內疚了,就算我再厲害也救不回來——就是這樣。”面前的人嘆氣,回過頭依舊是不悅,或者說是一種慍怒和無奈之間的表情,“盾……最終也是會死的啊”
他不知道該怎麼理解,更不知道如何回應,但是能應約感覺到從網的另一端傳來的,那種無端的窒息感。
“你過幾天到主哨報到,我來帶你。”
烏佐愣了一下,抽痛令他暈眩。“可是……”
“還能動就給我去戰鬥。”她說,“被所有人保護著的我們只有一個責任,沒有選擇。”
維加爾,烏佐,好好記得了,從今天開始,但凡是同族的死,都是你的錯。
烏佐走在本部的塔樓裡面,聽著外頭植物生長又被掩埋的聲音。除非有特別重要的會議,他已經很少拜訪中央,東戰場的膠著不知道該被稱為困境還是穩定,可是無論他正在做什麼都不是什麼錯事——至少他們能把大部分精力放在更重要的西邊。
似乎也不是最理想的狀態……烏佐瞇起眼。如果他有餘力的話——總是這樣,如果他有餘力的話。他向幾個打招呼的年輕人點點頭,沒有說什麼,緩緩往橋的方向去,多少年下來發現作為司令唯一的好處便是無論何時展翅都會有人接應。
透明的光組成的薄翼從他背後展開,籠罩周身,一直垂落至地面,從什麼時候開始室內已經容納不下這雙翅膀,什麼時候開始他終於成為該成為的樣子。下一刻他落在另一端的橋尾,岩石鑿出的平台如同伸向天空迎接來者的手,直徑通往窪地裡封閉的圓形建築。
招呼。點頭應答。
沿著盤旋的樓梯向上,他總是覺得把重傷員和新生兒放在一起很可笑,又明白不得不這麼安置,腥味充斥著每個角落,卻帶來種莫名的安然,熟悉的氣味和溫度,最安全的地方。拖著自己爬到樓頂,一邊提醒自己為什麼越來越少到中央來——太多樓梯——雙開的黑色大門前站著他來到此處的目,正小心地闔上門盡可能不發出任何聲響。
普萊斯抬頭,看到烏佐時顯然有些詫異。
“能回去了嗎?”烏佐問,明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
“長官怎麼來了……”
“順路來看看而已。”不行,指尖靠近後頸時對方會閃避,已經成為反射動作了,畢竟從這人出生以來最重的傷大多來自自己,要是有人問起他會承認他還沒適應和盾合作,不過這些人的恢復速度對他來說一直都是可愛的驚喜,就是常常不知道是自己太寬容還是是他們本身特質所致……總之他得換個方式結算錯誤。他無視普萊斯的不情願,仍舊捏起他後頸的皮膚,後者是一點都不高興。“壞習慣給我改掉。”
“是。”
“裡面的人有沒有說什麼?”
“他們……大概不敢。”
烏佐笑。“乖孩子,幫我下樓然後跟我去西邊。那裡和其他地方不一樣,你準備下。”接著他放開手,普萊斯很自然地就站到左側讓他能將自己作為額外的支撐。烏佐已經太久沒有和任何人成對行動,自從原司令死後他就一直作為指揮在各個點穿梭,本職樂師的副手也不可能跟隨在身邊,都忘了這有多方便——若當初他不那麼果斷地拒絕配給的話一切或許是會更輕鬆點。
他揉揉普萊斯的後腦,後者僵了一秒又強迫自己放鬆下來,假裝什麼都沒發生。
【Uz:該死的垂直建築】
【Uz在中央話語權也是非常重的,不過他很少去,都讓副手代替了】
【uz的前輩很小只,就是被吐槽能一手拎起來的那種,把uz當作盾的替代撈了起來,強行讓他學會乾乾淨淨地作戰】
【uz給了amy他從前得到的命令,用他從前被訓練的方式訓練,只不過發現amy仗著血厚痛覺遲鈍脾氣倔犟對體罰接受度並不高,uz表示養孩子真難,好在a大部分時候是很乖】

【3497年】
厄洛伊最不喜歡聽到哭聲,特別是小孩子。他緩緩地放下手裡的杯子,酒館內有些熱,大概是自己又喝太多,意識開始變得渾濁。兩年前他以為自己再也不會喝酒,可最近不知怎麼的又把這些習慣拾了起來,每一次第二天醒來都很內疚,艾登討厭酒味。
這個名字在他胸口嗡鳴,明明就已經快一年了,他下定了決心要將那個城堡的一切拋諸腦後,但是隨著時間記憶並沒有如其他人說的那樣被沖淡,反而越發地容易侵占他的思緒——每一刻都在質問他做出的決定。
“介意我坐在這裡嗎?”來者說話的同時已經擅自在厄洛伊對面坐下,在室內仍舊戴著帽子,似乎是旅人,和他年紀差不多,斗篷上有許多磨損,身上卻什麼都沒有帶,要是這種人出現在首都必定會被重點盤查。那雙深黃色的眼睛正在打量他,沒有惡意,純粹的好奇。厄洛伊思索著是在哪裡見過類似的人。他接著指了指厄洛伊腰間的佩劍。“你是士兵?”
“傭兵。”
“你還好嗎?”
“我沒事。”
清晨的薄霧遮住前方的城門,細細的水珠漂浮於空中暈開晨光,隨著他前行的腳步沾染到他的披風上。還是這其實是在下雨?那他從出生起就熟悉的氣候,此時如冰霜刺痛他的喉嚨和嘴角新癒合的傷,拖慢他的步伐,明明帶著的行李並不多,卻異常沉重。他坐上馬車,坐在人群之中就如另一個普通市民,唯有角落裡穿著制服的人在偷偷打量他,想著在哪裡見過這張臉。
一扇扇城門敞開,一扇扇城門關上,相同的景色在視野中飛掠,融化在水汽背後。最後經過一段短暫的黑暗,城市突然變成開闊的平原,一望無際僅僅被連山坡都稱不上的隆起打擾,乾淨地彷彿瞇起眼就能辨認出遠處的海。
回家。這個忽如其來的意識讓厄洛伊心裡尤其不安,他想他從未把那個地方當作家,從小的記憶便只有浸了水的訓練場和無止境的動盪,或許也只有那些熟悉的臉能令他期待回去,在狹窄悶熱的營房裡相互戲弄玩笑的日子,穿上相同的制服並肩作戰……
啊,他們早就葬身身後的地牢裡了。
“要從我這裡買自由?你以為你值多少錢?就算按照一般侍衛的薪資也能在一個月之內還清,就算這樣也沒關係嗎?”王子這麼用手指戳着自己的胸口,淺淺的微笑僅停留於嘴角,眼裡並沒有多少情緒,“況且為我工作你就是叛國之罪,會被除去軍籍甚至放逐的。”
他想他答應便是因為那個曾經被他稱作“家”的城市已經沒有任何能迎接他的人,沒有了家和同伴,至少得保護住自己的諾言,要不然便真的什麼都不剩了。
後來想起來還真是可笑。
“我不能接受敵人的施恩。”
小王子的頭偏向一邊,滿臉的不解。
“最近很多僱傭兵呢,原本都是士兵……”旅人說,“你看起來也像個士兵。”
“以前是。”
“哦?被遣散?逃走?”
“辭職。”
“真好,士兵還能辭職,看來這個國家的王還不錯,可惜駕崩了。”
“一般吧。”他回答,嚐到嘴裡的鐵鏽味。
“來了。”面前的人回頭看向酒館深處,手臂抱著椅背,似乎在期待什麼表演開始,但是厄洛伊並沒有心情去管,周圍的客人發出疑惑的議論,伴隨著齒輪轉動的聲響,從動靜來看像是拍賣會。此時旅人又轉回來,對酒館裡發生的事情失去興趣,低下頭,喃喃自語。“無主的地上真是什麼都長得出來……”
厄洛伊沒有說話,人聲攪成一團。
馬車僅在城門外不遠處就停下準備返回,厄洛伊跳下車箱,和其他所有旅客一樣必須另尋前行的方法。他緩緩地朝東步行,希望到達森林之前能遇到有著相同目的地的車隊。邊境已經不在森林邊了,他從前的國家至今已經被奪去三分之二的領土,剩餘的再過不久也會被吞併——厄洛伊發現自己並沒有決心離開時那麼在乎這件事。為王而生,為王而戰——他低下頭讓斗篷帽簷的陰影遮蔽他的視線——什麼王?
耳邊傳來馬蹄聲,厄洛伊下意識地伸出右手去護著本該在那裡的人,卻只撈了個空。他停頓。
“你還在啊。”艾登在消失了幾週後看到他還有些詫異,仍舊是淺淺的微笑,這次帶了點疲憊,閃過他的視線的同時一邊撫平他上衣的褶皺。“制服很適合你。”然後他便沒有再說什麼,將自己關在房裡又是一周。
厄洛伊倏地扶著自己的額頭,酒精造成的暈眩和頭痛一起爬上耳後,手肘撐在桌上感受到木紋嵌入皮膚。
後來他詢問過才知道艾登因為公然挑戰國王被扔進了牢裡。後來他才知道那個小王子根本不是他在王座廳裡見到的那個高傲的王儲,都是做給欺凌者看的假象。也是後來他才知道艾登喜歡往危險的地方跑,遇事後喜歡一個人躲起來。
那個名字繼續在胸口嗡嗡作響,越來越大,自己彷彿是一個正在塌陷的深坑。
“喂,你真的沒事嗎?臉色很差啊。”旅人傾身,打量著厄洛伊,語氣裡充滿擔憂,隨手便把他面前的杯子拿走,他沒有阻止。
“我好像犯錯了……”他開口,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這麼說或者自己在說什麼。敵國的王儲,那只是個敵國的王儲,既麻煩又難以捉摸,動不動就亂跑,自己動作要是太用力還會受傷,受傷了還要躲起來……他就不該任自己習慣他的存在。“我把他一個人留在城堡裡。”
旅人眨了眨眼。“誰?”
鑲嵌了黃金和翡翠的深綠色大門在他面前矗立,同樣華貴的走廊已經許久沒有真正被使用的痕跡。手裡的酒壺差點翻覆,皺皺鼻子,空氣裡熱食和腐爛的氣味混雜令他反胃。裡面不斷傳來叫喚傭人的聲音,他不是負責侍奉的傭人,只是臨時被指派來送酒,侍從們害怕靠近這個地方,於是漸漸沒有人願意來了。他想他該敲門,可全身每一處都在阻止自己這麼做。
從小他就幻想自己長大後在王座前接過來自他的王的命令,或者領受他的王賜予的勳章,為了王而生的他也會他的王而戰,不該是這個樣子……
那十歲的孩子蹲在國王臥房的大門前哭泣,雙手痠到幾乎沒有知覺,不敢靠近,又不敢違抗命令。
可是他嚐到了鐵的味道。
“對不起。”艾登是這麼說的,小聲地幾乎聽不見,慌亂間只能重複同一句話,他想他從來沒有主動傷過人。“對不起……”
玉色的雙眼蒙了霧,呼吸也變得急促紊亂,在那之下卻一點對自己選擇的懷疑都沒有,無比堅定——就是這個時候厄洛伊知道無論如何艾登都會下手,決定,命令,然後執行,不過是時間的問題而已——戰爭中他遭遇過比這些都更危險的情景,甚至好幾次都差點丟了性命,他以為自己不會害怕任何事情了,即便如此他驚愕地發現自己會在那眼神前退縮。
此刻僅僅是一道傷口,但等到該他奉上生命的那一天,他不可能會有任何轉圜的餘地。
“他道歉了。”厄洛伊輕聲道,一邊去碰嘴角的傷疤,早已癒合,剩下一道褪色的痕跡。“每一次見面他都會道歉……”
都已經是定局了,為什麼還要不停道歉呢?
“是很重要的人嗎?”
“大概……大概很重要……是敵國的,但是……”他不知道。
旅人稍稍揚起下巴,讓眼睛能迎到燭光,偏灰的膚色給他一種異樣的氣質,但厄洛伊將其歸咎於自己正處於酒精的影響之下。他給厄洛伊一個充滿同情的微笑,彷彿他比任何人都能理解這種困境——就算厄洛伊什麼都沒有說清楚。那人挪到厄洛伊身邊,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後向後靠在椅背上。“反正這兩個國家遲早會變成一個……你也不是士兵了不是嗎?”
“為敵國賣命……”
“嘿。”旅人用力地踢了一腳厄洛伊的椅子,讓他嚇了一跳,瞬間也清醒許多。“想清楚啊,”那人說,這時語氣變得嚴厲,“搞清楚什麼是最重要的,一旦決定了就不要改變,聽懂沒?”
匕首在他嘴裡,因為對方眼裡的恐懼而不住顫抖,直到他伸手將其穩住。
酒館裡的吵雜逐漸沉澱下來,拍賣結束了,人們開始結算剛才的交易,只有齒輪積壓的聲音並沒有減弱的跡象。旅人迅速地瞄了一眼騷動的源頭,接著起身。
“再給你一個建議,厄洛伊,快點離開這個地方,不要被它抓住。”
他抬頭,不記得自己曾經告訴對方名字,可是旅人已經不見踪影,剩下擱置在桌上的錢幣和空杯子。
【用uris的方式寫eloy】
【iden會道歉因為他那是還沒有能力保護自己的東西,他其實不會隨便犧牲eloy,那是他第一次體會到信任的感覺,實在是太難得了】
【alor本來是準備要殺eloy的因為剛好遇到了嘛然後e不穩定就有可能讓sd出現】
【alor:兄弟我懂你,我可是花了幾千年才悟出這道理的呢】
【eloy到最後也沒有為敵國賣命,他效忠的對象只有iden這一個人而已】


【0年 舊神居】
已經是第幾天了?阿爾感覺到被後冰冷的岩壁,想開口,喉嚨卻異常乾澀,他幾天沒有說話了?啊……還有多少事情需要做,他有幾天沒有參與工作了,他不記得上一次見到艾米是什麼時候——不知道他現在做什麼?阿爾的手指骨劃過自己的前額,經過眼前,可是因為周遭的黑暗而並沒有帶來任何區別。
他知道自己在哪裡,光之裔西戰場前線的第三哨塔,他在這裡已經住了好一段時間——作為一名戰士而不是俘虜,艾米要回到戰場上,出於擔憂他正式地加入本該是“敵方”的陣營。
他沒辦法形容自己有多後悔做出這個決定。阿爾想自己能聞到那股苦澀的血腥味,一陣反胃,就算很清楚這小小的空間裡除了一張毯子以外什麼都沒有,光裔們給他獨立的空間,也不是特意為他的舒適著想,僅僅是因為他的存在讓他們不自在罷了。阿爾可以理解,他也樂意遠離其他人,太擁擠也太熱。
西南戰場那場惡戰標識著彷彿無盡的戰爭終於有結果,它們輸了,封印混沌的鑰匙回到領主手上,現在剩下的便只有將異族消滅而已。阿爾笑起來,異族,不就是自己嗎?
他深呼吸,還是如此苦澀刺鼻。
他想他殺太多自己的同類了。
門被打開,強光令他瞇起眼睛,苦澀中混進絲甜味,門口熟悉的身影遲疑一會才走進來。阿爾別開臉,他還沒想好要如何面對這個人。
艾米站到前面,身上顯然帶著新癒合的傷,他想起來前幾天應約感覺到的震動,大概便是那時留下的吧。艾米的臉上沒有表情,眼中盤踞著細薄的霧氣——外面在下雨嗎?阿爾知道他是累了,太累,連爐芯的顏色並不理想,似乎好久沒有好好休息……這種無節制地消耗,他不知道艾米是如何堅持下來的,明明就只是一枚盾,也沒有人要求他這麼盡力,這更不該是他做的事情……
艾米沒有說話,抬起手,手中黑色的物體指著阿爾的眉心,藏在布料下仍感覺到從那光滑的金屬表面上散發出危險的氣息,連空氣都能斬開。
“給你。”艾米輕聲道,不帶任何感情,“前幾天回收的,你之前說過需要換一把……”
“你居然記得。”
利刃仍然懸在空中。“你能先拿走嗎?不想用的話能跟上面申請更換,最近回收了不少。”
阿爾咬了咬嘴唇,握住那黑劍的前端,隔著包裝感覺裡面流淌的陌生力量,帶著另一端因為疲倦和被武器排斥的不適感在掌中鼓動。阿爾想不起來他在哪裡見過這武器,試圖努力地回憶即刻便覺得毫無意義。
“謝謝。”他只能這麼回答。
“我先去報告。”
“你這幾天都在哪裡?”
轉身到一半的艾米又頓住。“中央。”
“過來。”阿爾招他坐下。“一個人走回來的嗎?”
對方停了半晌才決定照做,點頭表示應答。
“這麼遠……下次可以直接叫我的。”阿爾邊說邊傾身,隨意地拉起艾米的手,搓揉著那些指節,為了爐芯他們的皮膚生得實在薄,脈搏清晰而快速,和第一次在邊界會面的時候一樣保持運作的狀態。“停。”他說。艾米困惑但是仍然服從,藍紋散發的異常溫度逐漸在他指尖消散,沒有打算過問,靜靜地望著他。在想什麼呢?如果是烏佐的話一定能瞬間就給出答案,那傢伙一定知道該如何阻止這種過激行為……直到失去了才發覺那段時間的安穩有多麼珍貴。
“可能……”
“這個地方不適合你。”
阿爾抬頭,“什麼?”
“去別的地方,也不要靠近血池,我們剛剛清掃過西邊的群島,你可以去那裡。”
“然後呢?你們清理過的地方還能住嗎?”
面前的人垂下眼。
“那你呢?你會去哪?”
他沉默,似乎在思考是否要回答,開口又收住,最後才決定說出來。“柯賽爾需要人。”
號角手,東戰場原副司令,恐怕是光裔僅剩的樂師。他一點都不會驚訝這樣的角色會首先失去在身邊保護的人,另一方面他必須承認米琳說得沒錯,光裔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艾米的確是唯一適合那個職位的人,或許當初重新接納他們就是為了這種時候。可那是最前線……而這人準備一句話不說接下指令,若剛才放他去報告,恐怕也就不會回來了。
要是自己盡了責任,也不會落到這種地步吧。
“況且你知道我走不了……”他又說,“你沒有翅膀,我不在你怎麼移動?”
“我可以用走的。”
“帶著那把斧子你走不了幾次的。”
“我這次就走回來了。”
“你準備每次都透支爐芯走回哨塔嗎?!”
阿爾的手指被扭開,他發覺自己還沒意識到時爪子已經在對方的手背上留下印記,不足以造成任何傷害,但顯然是讓對方不舒服了。艾米的表情沒有變化,也沒有生氣,只是認真地在將自己的手挪走罷了,僅此而已。
接著艾米緩緩地起身,跪起來才比阿爾高。阿爾有時會覺得光裔的體型小的可愛,有些他單手便能拎起來,此時被艾米稍稍俯視還很不習慣,有種異樣的壓迫感,彷彿道出的都是命令而不是請求。阿爾有些內疚地將利爪壓在腿下,不知道是否該道歉,想說卻怎麼都說不出口,曾經他也不覺得加入某個陣營會很困難,不覺得開始為了特定的誰而戰有什麼問題——有差別嗎?除了得和別人住在一起?——就是現在他也想不出有什麼理由讓自己擔憂。
但就是動不了啊,就連拿起武器的念頭都令他感到噁心。
“艾米,我不能成為一個稱職的劍……就不該帶你去上界的……”阿爾說,極力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平穩,他是還沒想好要如何面對這個人,幾乎比要他現在立刻去戰鬥更困難,或許他在期待著某種明確的指責,無論是什麼,都是他應得的,想重來也來不及了,祈禱對方會保持沉默然後再也不理自己就好,即便這樣一來他永遠無法原諒自己背棄過去的承諾……或許他只想一個人待著。
他們的關係不該是這個樣子。
“我想我騙了你,該怎麼辦……”
“我知道。”艾米輕聲道。
“什麼叫……什麼時候?”阿爾愣了下。“從開始就知道了是嗎?這不可能成功……”
“是的。”
“但你還是答應了。”
他點點頭。
“到底為什麼啊……”阿爾低下頭,再向前便靠在艾米的肩膀上,伸手環過他的腰背,沒有層疊的厚重皮革與金屬原來是那麼單薄,對方卻沒有因為多出的重量移動半點,陽光般安定的氣息彷彿可以遮蓋所有的不安,實際並不能。
落在他的後頸,幾乎全灰的視線猶如那日雨天,要是領主看到可能會笑吧,什麼都沒有變——什麼都沒有變。
“我就要出發了,想來也可以,但那裡不會給時間適應,你還是去別的地方比較好。”
“至少讓我送你過去。”
“沒關係。”
“我準備好就去找你。”
他感到更多東西落在他的脖子上,手指,下巴,鼻尖,呼吸,噓聲讓字句能夠沉入自己的意識深處,放緩語速讓自己能夠聽得清楚。“沒關係。”
阿爾將他又抱緊了些,他真希望能一直這麼做——在一個更輕鬆的氛圍之下,不需要擔心任何事情——可是艾米已經開站起來,輕易地就從他身邊脫開,其實一開始就是這麼容易,這人的力量總是比他記憶中的大許多,性格也總比印象中強硬……他總是在思索那些人是從哪裡找到“乖順”這個詞來形容艾米的。
什麼時候自己也開始理所當然地認為他是個乖順的人呢?
艾米最後拍拍阿爾,轉身走向門口。
“小心點。”
“知道了。”
“你要等我。”
艾米停頓。“是。”他回答。
門緩緩關上,沒有發出一絲聲響,留下阿爾坐在黑暗之中。
【alor沒過幾個月就跟過去了,而且再也不會走了】
【alor也是個樂師,不過因為戰斗方式的關係選擇換成近戰武器】
【他們差一點就走成了06/07的樣子,差一點點,就一點點,可是Alor比fe更專心點,amy比venn更果決一點,沒有上下級關係,沒有階級差,沒有對方也能好好地過生活,吵起來也不會造成災難性的衝突,反正有的是時間】
【但同時他們也不是會互助的一對,可以幫助對方忘記傷口卻無法療愈,畢竟他們之間關係的根基是為你好和沒關係】
【好無聊只想發發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