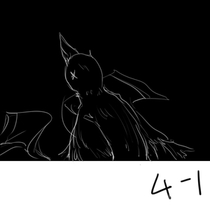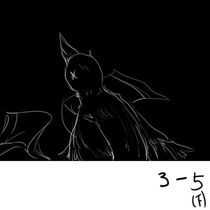十七,
剛開始還他會為了自己熟悉的空間被他人擾亂而惱怒,現在仔細思考一下,若要是忽然少了這麼個人,自己還能不能安穩入眠。埃圖瑪維以為忒勒斯不會回來了,下次再見會是在和商隊集合的地方,還想著到時候該怎麼打破這個僵局,他不常和人爭吵,事後那種隱隱的刺痛感和後悔讓他有些錯愕——原來是這樣的,說不定對這個人來說也是這樣的。
他沒有介意忒勒斯受僱於人,也不介意他們忽然給自己按上一個莫名的期許,如果自己真的是領主的血,這是託付給自己的地,那自己也只能接受並承受,如果那只是誤傳,那也不會影響自己也為這塊地方盡力。他介意的是自己答不出那個最簡單的問題。
想要什麼?從前他覺得只要安靜地在森林裡生活就足夠,現在他身邊多了許多人,他想要這些人想要的東西,多到無法將其理成一個明確答案。埃圖瑪維的手指還留有灰藍色的印記,順著忒勒斯手臂上的黑色紋路一路走到了他的手腕上,末端的菱形尖端下方的是脈搏,正指著身上的弱點。他想起來自己還沒有問過這些紋路代表什麼,將那十指握進掌中,就這麼隨意搓揉忒勒斯也沒有動靜,拋開酒醉,這人慢慢地也開始不會被自己所驚動,是太習慣有自己的存在。
不想要經過夜晚,也不想看到日出,所以才即便要裝也要這麼一直一直睡下去。
和商隊匯合的那一天意外的沒有下雨——事實上在襲擊那日之後雨變得溫順許多,他們說如果保持這樣多好,說不定今年也就不會淹水了。埃圖瑪維將行李搬上車廂,原本的大帳篷連著其他物件託給了氏族剩下的人,他們只準備帶著最簡單的裝備。忒勒斯在車隊裡亂晃,和其他的商人打招呼,小跑著跟人去別的車廂裡看新奇的東西。不花多少力氣就能和陌生人人稱兄道弟的能力總是讓埃圖瑪維有些羨慕。
“還行嗎?”萊門從車廂內探出頭,帶出一股煙味,底下隱約藏著種苦澀的香。“大人也願意隨行所有人都感到很安心。”
“為什麼?”埃圖瑪維沒有抬頭,繼續繫著繩索。“你為什麼走不過王的領地?那個箱子裡裝的是什麼?”
對方沉默了一會,爬到車廂邊緣,確認周圍沒有人才壓低聲音說道:“古物……也不算是,確切來說是人造物的殘骸。”
古物,與人交易,誘人墮落,他以前都覺得這些是警戒小孩子的故事,直到忒勒斯說都是真的——似人非人的東西,或許他早就發覺了。“你和古物交易了?”
“沒有。”他聽見鈴聲,對方已經跳下來到他身邊,伸了伸懶腰,上下看起來也不過十五的年紀,神態和語氣卻有著不符合外表的世故。第一次遇見埃圖瑪維就感覺到了這個人身上的違和感,然而只有這個人握有連醫者都不知道的信息。也就是同行而已,他對自己說,大不了半途退出,即便不清楚其他地方是否還有其他和他一樣的人存在,或者是否和這邊一樣對自己抱有敵意,就兩個人要隱藏踪跡旅行一點都不難。“但是我必須把貨物帶到東邊去,畢竟我的工作是為人尋找丟失的東西,這是委託的一部分。”
“會有危險嗎?”
“沒有,”萊門笑起來, “大人可是領主的兒子,古物迴避都來不及呢況且這一個僅僅是殘片。若想看的話也是不是不可以。小的要先告辭,有什麼需要儘管提。”
又是這種話。
埃圖瑪維伸手按住對方的肩膀,後者在突如其來的力道下有些緊繃。怕嗎?“你是怎麼知道這些的?”
“怎麼說呢——”他回過頭。“我和你逃亡的同伴不同,商人嘛,在大道上旅行什麼消息都能聽到。”
真是敷衍的搪塞。埃圖瑪維遲疑著放開手裡的人,雖然想要繼續質問但是又不想顯得太緊逼就輕聲道了句歉。後者用寬袖遮住臉,輕輕一鞠躬然後離開。
忒勒斯從背後跳過來皺了皺鼻子。“致幻鎮靜的香。”他說,“你沒有感覺?”
“沒有。”埃圖瑪維回頭想攬過忒勒斯,卻被對方閃過。這個人這種無意識的反應力一直都讓他很欣賞,像是動物的本能似的,可是在對戰的時候怎麼就會突然不會了呢。
忒勒斯嘟囔著埃圖瑪維這種體質真方便。
“那你還在這裡。”
“一點點無所謂。”藍眼的弓箭手說著便從口袋裡拿出一枚箭頭向埃圖瑪維炫耀,大概是剛剛從別的商人手裡買來的,整塊打磨的金黃色晶石和忒勒斯弓箭上鑲嵌的是同一種。“你看他們說用這個絕對不會碎,我剛剛試過了。”
“撿不回來怎麼辦?”
“會找到的,我不是才簽了一個專門找失物的雇主嗎?真不知道這弓原本的主人是怎麼……”忒勒斯說著思緒就飄走了。想到了什麼?“沒事。”說著就把箭頭塞進口袋裡。“要不要去河邊?”
他們在細雨中的河岸邊對練,享受難得的日光在皮膚上留下些許暖意,腳步掃起的碎草被風帶進流水中,在半清的水裡打轉然後消失。遠處地平線上壓著的厚重雲層預示著另一場暴雨,緩緩地向平原這一段爬來,他們會等暴雨結束再出行,他們總是在等雨。埃圖瑪維揮起武器,他手裡骨製的大刀事實上是個鈍器,想著這樣不用太擔心意外劃傷對方。那原本是他養父的東西,聽說是他獵殺的第一個獵物製成,想起這些瑣事他胸口忽然有些悶,長年來積壓在心底,此時此刻他或許找到了正確的情感。
埃圖瑪維第一次發覺他曾失去過一個無比重要的人。
忒勒斯踢開大刀,勾起腿就將其踩在了腳下,短刀向他刺來,埃圖瑪維立刻放開閃到側邊,前者沒有想到他會如此輕易丟棄武器,面對突如其來的失重便直接蹲下躲過試圖擒拿他的空手,掃過埃圖瑪維的腿打亂他的重心,順勢一撥將他摔倒在地。這人的動作在他換了大刀後就變得很收斂,轉向很迅捷,自然地在面對不同對手時採用不同的行為模式——這段時間下來他漸漸地開始明白那種細微的控制的區別,嘆息自己不足的全是經驗。
忒勒斯跨坐在他身上,刀隨手插在了埃圖瑪維耳邊的地裡,早就不是原本的那一把,記得沒錯是從襲擊小鎮的匪徒腰間搶來的,換過刀柄才看起來很新。他曾經指著上面歪斜刻著的花紋,說這把刀原本的主人應該很虔誠。即便不識字,也要把記憶中的教條刻在隨身之物上,他的口吻裡帶著些譏笑,大概自己連寫了什麼都不知道吧。
“分心。”忒勒斯有些不滿地哼道,用手掌根往他額頭上拍了兩下。“哪天遇到一個不怕蠻力的對手怎麼辦。”
“有那麼差嗎?”從坐在身上的人的表情看來也不至於如此,埃圖瑪維歪過頭,“嗯?”
“這樣下去沒有意義。”他輕聲道。“你變得太熟悉我的動作,這樣下去對你來說也不好。”
“沒關係。”
“我看到隊伍裡有拿長槍的人,你可以試試看,手長的人都特別難對付。”
“嗯。”
埃圖瑪維閉上眼,雨的氣味開始變重,隨之從天上低落幾些雨滴,正好落在他額間,半溫的水珠。身上的重量挪開了,他聽到草地上踩起的焦躁的小腳步。我已經沒有可以給你的東西了——他幾乎可以聽到那些囑咐背後的暗語,儼然是個習慣在被拒絕之前便甩手離開的人,忽然被拴在地上後在這裡不知所措的樣子。梅爾薩警告過他此時就要開始警戒這個人,她也曾經以為自己能成為系住這個人的繩。
“我的養父被襲擊是十幾年前的事情。”他說,對方沒有反應但是他知道他在聽著。“現在想起來我至今不知道他的名字,我們只有離開森林過一次,他不喜歡和人打交道。”
“他人好嗎?”
“我記不清楚了,大致是個既不嚴厲也不慈愛的人,從小就和他一起狩獵,即便跟不上也要硬走,要不然會被留在外頭。”
忒勒斯澀笑一聲,又坐回埃圖瑪維身邊,將臉埋在手臂裡。“跟老師很像。”
他伸手向天,擋住淋向臉的水珠,也擋住烏雲縫隙透出來的最後一絲明淨的陽光。我什麼都沒有感覺到,在聽到逃走的人被襲擊的時候也什麼都沒有感覺到,只是有一點生氣而已。
十八,
“只是生氣而已。”萊門輕輕掀開香爐的蓋子,吹了吹裡面悶燒著的東西,揚起一小簇青藍的煙塵仍是早上的那種味道,致幻鎮靜的香。“還真是,他的樣子。”
“誰?”
“領主。”年幼的商人笑得有些厭惡,“暴食的怪物。”
是因為是古物才敢這麼說的嗎?埃圖瑪維給裝備上油的動作緩了下來。“這是什麼?”
萊門抬頭,此時表情又有了一絲孩子的樣子。“擔心嗎?你的弓箭手也容易受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影響,這個對他來說反而是好東西,我可不想我價值十枚金幣的僱傭兵出事。怎麼,大人不喜歡這個味道我可以加點別的香草。”
“不用,你說沒問題就沒問題。”埃圖瑪維敷衍地答道。此時忒勒斯從上方推開車頂的小窗口,探出頭來。
“他們好像找到可以過夜的地方了。”
“下來吧。”
忒勒斯皺了皺眉頭,“不用,我不喜歡這個味道。”萊門暗笑著蓋上那個金色的小蓋子,忒勒斯卻不准備領情。“反正等一下要先去周邊確認安全,你一起?”
埃圖瑪維抬抬手指表示自己會去。車頂上的人給了那頭的人一個眼神,停頓下又開口。“你手上有武器嗎?”
“有。”萊門回答,從包袱地下摸出一把小小的彎刀,綴著玻璃珠的武器更像是一件飾品。“就只有這一把。”忒勒斯瞥了一眼就沒有多說什麼坐回原本的位置,也不知道只是想試探這人是否想要藏武器,還是作為保鏢必須確認雇主是否有基本的自保能力。
“給我看看。”埃圖瑪維輕聲道。年輕的商人沒多想也就將武器遞給了他——他去接的時候反而遲疑了,就這麼將身上唯一的刀遞給只認識不久的陌生人,他該不該責備這種毫無防備的行為,還是該提防這個人說謊的可能。掂在掌中的彎刀比外表看起來的輕,從玻璃珠看進去能發現裡面幾乎中空,刃也是玻璃而不是金屬。“不能戰鬥但是可以刺殺。”他小聲對自己說,不過和忒勒斯的弓不一樣,這顯然是屬於人的東西。
“裡面裝了毒,可以讓人麻痺的。”萊門似乎是看透了埃圖瑪維的掙扎,慢慢地對著燈就說起來。“我對戰鬥一無所知,這只是委託的其中一件。這把匕首來自海對面覆滅的王國,它的主人早就沒了——已經是徹徹底底的失物了。”
海的對面曾經有個王國。人類的第一個王國。起初一切都很順利,但是那裡的王漸漸變得傲慢,他們說或許他們從來都不需要神和教廷。領主沒有將背棄他的人抹滅,而僅僅是不再在乎他們的死活。也是因為這傲慢和與教廷的衝突不久後第一個王國瓦解了——有權勢的人擅自畫地為王,上面不遵守法律普通人也不再遵守法律,教條不再作數,這個國家就這麼自己從內部將自己蠶食殆盡。
“你是因為這個才渡海的?”
“故事都是聽別人說的,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自己在這裡。”萊門笑道,又指了指自己眼睛裡面那圈將他們區別開的黑斑。“這個,這代表我是在海對面出生的,領主給新生的一代打上的無神的印記。大概就如你所說是被家人帶著一起逃來的吧,在亞魯士王都淪陷的時候教廷剩下的祭司救出了一批人,可能就是跟著到這邊來的,不過他們也不在了。”
埃圖瑪維沉默,他想起小鎮遭到襲擊的那晚,那雙彷彿寫著掠奪和屠殺是理所應當的淺紫色眼睛,耳邊傳來自己告別那時隱約沒在背景裡的哭泣聲。
“如果你說的是真的,要是我成為王,這種事情也會發生。”他說。
對方聳聳肩。“或許會。或許不會。”
突然他們身下一震,馬車停了下來。忒勒斯再次打開車頂的小門,探出頭。“到了。”
埃圖瑪維下車,簡略環視周圍的環境,是在山腳斷崖處找個大的空洞駐腳了。抬頭看太陽還有一段時間才會完全落山,他和一小撥人進入洞穴探查是否有大型動物的踪跡。
這批商人帶著的全是稀有的貨物,所以僱傭的保鏢異常的多——異石,他依稀記得是這麼稱呼,帶著魔法的礦石,給忒勒斯的箭頭,和此時此刻領頭提著的無火無煙的燈都是用那種東西製作。這些人也有海對面來的,也有在小鎮上僱傭來補齊襲擊那天失去的人手的,混雜在一起自然地就分成了兩個小團體。一路上埃圖瑪維只是偶爾提醒這些人需要注意什麼樣的痕跡,需要在哪裡設下記號,在兩種口音的交談背後他覺得有些不自在,他從未與這麼複雜的團體結伴,更沒有忒勒斯那種自來熟的能力,讓他都有些後悔自己當初該以僱傭兵而不是客人的身份跟隨。
我在做什麼。
洞口傳來嬉笑打鬧的聲音,剛升起的火堆後面已經搭起帳篷,馬車被安放進洞穴乾燥的庇護之下,他聞到不知名香料的味道。
埃圖瑪維回過神意識到自己正在離開平原,離開他發誓守護的人和地。一股焦燥突然在心裡升起,在部族失去領導只能被迫寄人籬下,在所有人得想辦法從殘骸裡拾回正常生活的時候選擇離開,自己究竟在做什麼。
離開森林的厚重陰影後他第一次覺得自己能夠呼吸,拖著滿身的泥濘和雨水幾乎無法再向前——他跑了多久,在同樣的樹前打轉了幾次,小心翼翼地回過頭,背後的森林一如往常安靜,沉著的深綠色在雨中模糊猶如一堵高牆,似乎什麼都沒有發生過,異象只是他的臆想。
不,不要回去。他心底的本能仍然這麼高喊著,拽著他的腳步向前,讓他想起自己第一次獨自狩獵的那一天。那是陷阱,他現在是獵物,森林裡躲著他無法理解的東西。
埃圖瑪維又走了不知多久,根據星空大概能知道自己正往東走,空曠的平原上連能藏身的遮蔽都沒有,即便雙腿早已累得沒了知覺他也不敢就這麼歇下。
“你是哪裡來的!停在那裡!停下來!”
胸口的一陣刺痛,目光向下移看到火把微光下的指著自己的削尖的木棍。喝止他的人大概也沒有預想到來者會就這麼直直撞上武器,嚇得將木棍收了回去。青年舉起手裡的火把上下打量了一下埃圖瑪維。“喂,受傷了嗎?你沒事吧?“
埃圖瑪維想要開口卻似乎忘記該如何說話,發出的聲音令他感到驚訝,這和自己記憶中自己的聲音有些許差別。“我……”
對方此時已經走到他身邊,攤開雙手表示自己不是危險,那人身上有乾燥的木頭的味道。“會說話嗎?聽得懂我在說什麼嗎?”他問,“是不是被誰襲擊了?還是遇到野獸了?”
在混雜著疲憊,困惑和暈眩的噁心感之中埃圖瑪維只能搖頭。負責守夜的人讓他坐在火堆旁並給他了點水和食物。“族人們都睡了,我不能隨便讓陌生人靠近,況且我還得在這裡看著,你……就在這裡休息明天再說吧。”對方說著又歉疚地揉揉脖子,“剛剛真是抱歉,一般人看到武器都會自動退開的……”
“埃圖瑪維。”
“什麼?”
“我的名字叫做埃圖瑪維,是森林裡的獵人。”
他們似乎很輕易地就接納了他。
你若是願意為我們盡心盡責我們也會把你當作家人對待,你若與我們為敵就是與平原上所有氏族為敵,長老那微微顫抖卻有力的手指指著他的眉心,從前獨居的你可能還無法理解,互相依靠是在這個平原上生存的唯一辦法,但是你也要學著理解‘我們’和‘他們’的區別。
我們需要能自保的能力,能工作的雙手,也想要你對森林的了解。老人繼續說,但我們不是貪婪的人——獵人埃圖瑪維,你要什麼?
遠處隱約的有什麼在牽動他的思緒,那是一股溫暖卻危險的力量,卻同時對他來說如此熟悉,他站在木屋的門口聽到的便是這誘惑的低語,模糊的聲音緩緩匯聚成一隻無形手指向森林深處那扇通往無處的大門。
來我們這邊。
【沒的情人節】
【AT對家這個概念其實沒什麼感覺,生命貴重但是不具體,沒有感情全是責任】


閣樓如往常凌亂擁塞,雜物和衣服隨意散落快要看不見地板,唯一能呼吸的只有天窗之下的床位,連個床架都沒有,僅是個泛黃的床墊,是他從前租戶那裡繼承來的,也不知道在這之前還有多少人睡過這個地方。天窗由布遮住了,本來一直都沒有窗簾梭倫也沒有在意,但法倫提並不喜歡陽光直射。
“我出生的地方沒有光。”他曾經這麼說。“三千年多前第一次見到太陽,還沒習慣。”
此時他們點著燈在床腳的沙發邊翻著書,一半是他用來學習的食譜,一半是他朋友們丟在這裡的小畫冊。
他原先只打算用適當善意換幾個願望,能進牽上對的人就好,他這麼承諾自己,能跨進那門檻就好。可是他也慢慢感覺有這麼個室友似乎也不差,即便看不清這個古物到底在想什麼——有時候彷彿瞬間能看透他的心思,有時候和他解釋東西又是一臉一知半解的樣子。
梭倫用腳尖推推對方的小腿,後者翻過身望向自己,穿著長睡裙在高挑的骨架上倒顯得短。他也發現了法倫提其實並沒有性別——更確切來說他想要是什麼就能成為什麼,或許這就是自己剛開始會困惑的原因吧,不過這也僅僅是讓自己覺得新奇的小發現之一,看過這傢伙的真身後自己漸漸地不會被什麼新發現震驚到了。“你最近好像不太出門,平常想留你都找不到。”
“外面很危險。”
“古物有什麼能怕的。”
“這個世界有很多更可怕的東西。”法倫提只是說,“你覺得為什麼我們要躲起來交易。”
“是嗎……”
“你想要我走嗎?”
這一句話將梭倫嚇得支起身。“沒有!我只是覺得有點反常……”
法倫提笑起來,他懂,也只是在逗自己玩罷了。梭倫別開臉,“覺得外面危險的話就繼續待著吧。只要你不到處顯擺自己的能力,組裡挺歡迎你的,店長和鄰居也都以為你是我的新女友,有這樣的關係網要偽造身份也比較容易——我是說……如果你不介意的話……”他的語氣漸漸變小,不清楚自己在說什麼。他忽然覺得臉有點燙,也不知道是因為自己的失態還是因為此時此刻主動權被他人奪了去,讓他覺得自己像個極力隱瞞犯錯卻還是被大人發現的孩子。
影子晃過眼前籠罩著他,是法倫提從地上爬了起來,拍拍衣服,仍舊微笑著。這微笑究竟是在人間生活養成的習慣,還是這古物在盤算著什麼,此時一舉一動一個表情都多了些意圖——他懂,而且將自己看得明明白白,“想要嗎?”
前段時間他找不到祖父遺留的那枚金戒指,還以為遭小偷,那大概是他身上唯一真正有價值的物品了,到最近才將願望和代價這兩個概念聯繫在一起,“想要”這兩個字突然擁有許多重量,如果答應這次又會失去什麼。
“可以嗎?”
那銀灰色的身影慢慢跨上他坐著的沙發,破舊到變形的椅墊在重壓之下向下一沉。俯看他的瞳孔成豎直一道,髮尾掃過他的臉頰——這個他倒是慢慢能認得,是看到食物時的興奮。
“我是屬於繁星的古物。”法倫提捧起他的臉將他的視線牢牢定住,就在那雙雙色的眼睛裡面,古物低語著。“你的慾望就是我的慾望。”
他想要。他什麼都想要。
梭倫的手帶著遲疑環上對方的腰,怕是下一秒這軀殼就會散開,成為逃竄的黑影消失於角落,猶如方才隨口開的玩笑。溫度透過薄薄的棉布傳到身上,就和他從前接觸過的所有人同樣的溫度與觸感,帶著那夜後巷中開出的巨口那種微微濕潤的氣息。“你真的,很像人類。”
法倫提拍拍他的額頭,換回平時天真無害的語氣。“你也很像。”
【FLT業務能力極強】
【下界沒有光,是個像口內一樣濕軟的地方,他就在那裡住了不知道多久,剛開始真的見光死】
【這個打算做很傻的小甜寵,我覺得家裡相當缺這類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