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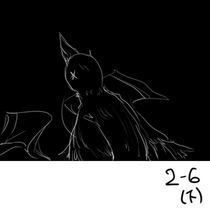

十一,
這是在邀請我嗎?對。
本來只是想要調侃埃圖瑪維的,沒有想到那傢伙還就這麼耿直地回答了。忒勒斯坐在河邊,不想要去人多的地方,不想遇到熟人,不想和人打交道。樹林裡孤立的小房子啊……好像也不錯,小時候他也會羨慕這種生活,自給自足,安逸而隨意,像他這種出生在人堆裡的孩子怎麼也沒辦法想像——他把手浸在河里,總有種錯覺要是就這麼浸著下一秒就能洗出血來。現在可以,他會說,那種幾個月都可以不需要開口說話的感覺,他不知道自己究竟更喜歡哪一種,總覺得無論是什麼形式的安逸都對自己來說過於奢侈。
無休止的水和雷擊打大地的聲音,忒勒斯往自己又縮了縮,他越發討厭這種天氣,早上麻痺感官晚上吵得難以入眠。但是輾轉間就會有什麼突然罩在他的耳上,那溫度他實在是太熟悉了。
他的老師從前常常說他天分很高但是意志薄弱,大抵就是這個意思。雨水重壓在肩背上,寒意包裹他彷彿能洗褪所有對他人的觸碰的記憶,友善的的惡意的,生的死的。他蜷起來,希望自己就這麼被打散,隨河流而去。
別淋雨,會生病的。別玩了。該走了。他幾乎能聽見有人說,幾個不同的話聲重疊在一起,變得似人非人。
他準備回去的時候已然是傍晚,小心地混在別人的營地之間打算抄近路,每一個對他來說都很像,只有規模有些許不同,他總是很疑惑梅爾薩如何遠遠就能識別別人來自哪一個氏族,不過想了想外面的人也沒法像他那樣辨別祭司之間的區別。忽然有個人影從巷弄裡低著頭匆匆竄出,忒勒斯輕跳閃過,心煩這個人怎麼回事之際視角邊緣掠過一絲光。他側身躲過襲擊者,看著刀刃從眼前掠過,趁空抓住對方反手用手臂勾住對方的脖子,奪過武器。“為什麼襲擊我?”忒勒斯頂了下對方的膝蓋後方。“三秒讓你回答。”
那個人吐出幾個無法辨認的破碎的字,被酒味給埋沒。他沒有理會,握緊自己的手腕,等著對方失去意識。
“不好意思,可以請你暫且放過我的人嗎?”
忒勒斯轉身,讓臂彎裡的人擋在自己和來者之間,“你派來的?”
來者慢慢地走近,完全沒有緊張的意思,攤開手表示沒有惡意。臉藏在斗篷之下他只知道是個高大的男性,說話也像是附近的人。“不,我們是從東邊來的,這傢伙一直都有癮,我已經警告過他了,別把錢都花在酒上,現在可好到處闖禍……”搶錢?忒勒斯皺皺眉頭,天底下哪一個搶錢要直接衝著對象的眼睛去,而且剛剛的動作對一個酒鬼來說也過於精準了——他後退後幾步,刀尖貼在手裡的人的皮膚上。
對方沉默了一會。“你……是個祭司嗎?在教條的執行者面前作案罪該萬死,我也沒有資格阻止,請裁決吧。”
無聊。忒勒斯鬆開手,往襲擊者的背後踢了一腳,對方踉蹌著逃走,他將小刀收起來。
斗篷下的人向他鞠躬致意。“謝謝。”他說。“我回去會好好教訓他的。如果方便的話跟我走一段吧?”忒勒斯沒有拒絕,他只是覺得這個人奇怪卻不知道怎麼形容,總有種很熟悉的氣息。
“你說你是東邊來的?那裡不是很危險嗎?”
“對,我和族人們住在東邊森林外圍的小聚落裡,附近越發危險,加上那個大火……”那人嘆了口氣,“東邊雖然和這裡不一樣,沒有淹水的危險,但是也沒有什麼好的地,森林很多,所有人都散居守著自己的小地盤,即便圍著祭壇建了個聚落但教廷大概是不知道那裡的祭司病逝,很久都沒有代替的人了,你應該也能想像,沒有約束的地方會變成什麼樣子。”
“教廷人手一直都很緊缺。”忒勒斯說。他知道有些祭司會被派去不同的地區,從沒有想過教廷在那個小懸崖以外有什麼影響力——至少在審廳被取消以後就沒有了。
“你呢?從教廷旅行來這裡有什麼特別的目的嗎?”
“沒有,老師讓我出來走走,我自己也沒有什麼目的。”
“是嗎?”身邊的人忽然聽起來很欣喜似的,將手搭在忒勒斯肩膀上,力道讓他反射性地有些抗拒。“要不然跟我去東邊吧,我們正好需要一個知道怎麼主持祭祀的人,有了教廷的監視那些掠奪者應該也會收斂一點吧。”
忒勒斯撥開那人的手臂,忍住沒有顯露出敵意,他一直都會被認作祭司,在某地方他都不敢在大道上走,可是顯然在這塊地上這個身份相當好用。“你都得到森林另一頭求資源了,我去能得到任何好處嗎?海那一端的天氣可比這裡好得多。”
“明明是從教廷來的居然不知道嗎?看來往那個方向的消息真的不太通啊……這樣說吧,這塊地馬上就有新的主人,而且是主上親自指派的人選,到時候一切都會慢慢變好的。說來聽聽,你想要什麼?”
這是什麼?新的預言嗎?面前看起來是個相當重視教條的人,那他該明白擅自杜撰預言是禁忌,為何要特地跟祭司說這種話……他故作思索,囁嚅了句,“我喜歡胸大的。”
那人又笑,因為尷尬而有些僵硬。“啊——還真的難到我了,雖然不能給,但是介紹道還是做得到的,如何?”
“可以是可以,反正我回去也得經過森林。”忒勒斯聳聳肩,“你們住哪?我得先和醫者說明一下才能去找你們……我還想先認識一下你的同伴,畢竟差點因為那個混蛋而瞎了呢。”
“當然,我會讓他親自向你賠罪。”那個人轉過身指向小鎮朝向內陸的方向,“我們明天就啟程,清晨在東邊那條路口碰面,到時候你要是決定不跟我們走我也不會強求。”
忒勒斯望著那個奇怪的人走遠——窒息感,對,和埃圖瑪維在一起時被無意識攥在手裡的窒息感。他甩甩身上的雨水,剛才的對話在腦海裡來回回放,有些懊惱自己竟什麼都沒搞明白,連對方所在的位置都沒能得到——主上親自指派的人選又是怎麼回事。好奇心催促著他跟上那人的腳步,可是理智卻阻止他繼續探查,直覺告訴他這個陌生人不是一般人,即便感受不到惡意,心裡那種不上不下遲遲卻沒有褪去。
“埃特。”夜晚忒勒斯望過自己的手臂和凌亂堆疊著的織布和皮草,面前的人側側身表示自己有在聽。我在街上遇到一個奇怪的人,那個人請我去東邊的祭壇,如果去的話說不定能找到那個集結盜賊的混蛋,只要一箭就好,然後我就回來,我們一起去旅行——他本想這麼說,可是話語卡在舌尖怎麼也道不出,知道埃圖瑪維絕對不會答應更不會放他走。對方等不到忒勒斯繼續說話便睜開眼睛,滿是詢問的意思。忒勒斯喉嚨一緊,“教我打獵吧。”
埃圖瑪維微笑,“雨太大了,等天氣好轉再說。”說完閉上眼又安靜下來。忒勒斯沒有接下去說,不想再打擾對方平穩的呼吸,靜靜看著那應約的牙白色輪廓。事實上他也沒有特別想要什麼東西,只要有食物和住所就好,跟著誰比較安全就跟著誰——他都是如此過來的。
你受過訓練?你能戰鬥?跟我們走吧,我們能提供食宿和陪伴——只要你為我們濺血。
說起來他不知道埃圖瑪維究竟想要什麼,他不需要保護,不需要借他人之手去達成什麼目標,就只是旅行有個導遊就願意搭上自己和族人的安全也未免過於牽強……他強迫自己也閉上眼不去多想,風雨背後又是那種似人非人的濁音。
十二,
忒勒斯敲完鐘便去和其他人會合,男男女女不到二十人,正圍著什麼議論著,有些認識的面容不在其中,說是去保護長者和小孩到外圍去躲險了。他遠處看到別的營地也開始敲警鐘,小鎮上異常明亮。
“怎麼回事?”
“有外人混進營地裡,正準備摸進大帳篷裡剛好被抓住。”
這時一個女孩撥開人群向他們走來,看起來是議論有了結果。“埃圖瑪維。小鎮不能被破壞,要不然誰也別想過冬,我們打算找其他部族的人一起去鎮上。能不能……”她頓了一下。“能不能請你幫忙跟榭利氏溝通,畢竟他們數量最多……”
“好。去告訴其他人,派一部分去抓捕入侵者,但是不要太分散。俘虜能抓多少是多少,全部集中在哨塔,他會跟你們去。我有種感覺這些人不只是來搶資源的,我想辦法去找他們的領頭。”其他人點頭表示同意,隨即便散開去和其他部族交涉。
“打算怎麼做?”忒勒斯把稍早搶來的那把小刀扔給埃圖瑪維,想起巷口的那個醉漢——他該說出來的,沒想到事態會惡化得如此快速。
“絞死。”埃圖瑪維輕聲答道。
他反應過來自己接到的是什麼命令,倏地回頭,埃圖瑪維臉上沒有表情,但他知道那眼底暗暗湧動的是怒氣,就和按著他的喉嚨質問自己的目的時一樣平靜的可怕,此時此刻看到的又是最初那個流著血追擊自己,殺伐決斷的獵人。
是嗎。急促的心跳之下忒勒斯發現自己揚起嘴角,也不知道是因為緊張還是興奮。他啟步跑著跟上其他人。
鎮上和忒勒斯預料中的同樣混亂,各種不同的人拿著器械揪成一團他根本分不清誰屬於誰,只能照著同行的人的指令行動,接下來的的過程就異常簡單,襲擊,壓制,捕獲,傳話。他一路穿過房屋街道,糧倉在哪個方向他不知道,只知道哨塔在前方。
“弓箭手……忒勒斯!”
忒勒斯收刀抬頭,在人群中看遠處到穿著祭司袍的醫者正在試圖將傷者扶到巷子裡。他深呼吸,拉開弓,緩緩地閉上一隻眼遮去周圍的喧鬧。巷子後方那個人影應著弓弦的顫動倒地,醫者嚇了一跳,直到忒勒斯抵達才大致明白發生什麼事情。“情況呢?”忒勒斯扯了一下醫者的手臂。
“是從鐵匠鋪附近開始的,他們先破壞了熔爐,在所有人都趕來滅火的時候開始襲擊人群。”她說,蹲下身去摸倒地的人的口袋,除了武器和幾個硬幣以外沒有任何可以表明身份的物品。“他們似乎在把人往外趕,目的不明確。至少祭壇周邊還是安全的,這些人還沒有瘋到攻擊教廷的地呢……”
熔爐,東邊。忒勒斯瞄一眼路口,都在往哨塔的方向跑,看來在外敵面前再陌生再互相嫌棄的一群人也能朝著相同的目標去——還真是簡單。“我們打算把抓到的人集中在哨塔,埃特有他的打算。我告訴他們傷員可以去祭壇沒問題吧?”
“可以。”醫者停頓,思考著。“哨塔嗎……那裡好像已經被佔領了,你的身體剛恢復沒多久,不要太冒險。”
忒勒斯沒有回答,將斗篷的帽子拉過頭頂。如果塔上也有弓箭手就麻煩了,得先去清空哨塔才可以,他對自己說,那個塔不大而且看起來很窄,安靜一點的話他可以輕易解決。
你不需要一個人擔心這種問題。
“可惡。”他低聲咒罵了聲便往無人的巷子裡跑去。
那石塊和木頭胡亂堆砌成的塔樓甚至不足教廷的藏書室高,卻已經是周圍最高的建築,連著朝東的圍欄,上面點著代表有襲擊者的火。他隨便找了個屋頂爬上去,瞇起眼試圖判斷守在那裡的究竟是己方還是敵人。
隱約間他似乎辨認出熟悉的身形,放箭,對面的人倒下時沒有多少動靜。
是稍早撞他的——果然這些人是算計好才來的。
忒勒斯快速放倒塔樓門口的兩個守衛,披上他們的斗篷摸進建築內部,一路想著自己身上的箭所剩不多——這把弓唯一的缺點就是耗箭。此時背後的門口傳來集結的人群的腳步聲,他沒有打算回頭去接應,爬上梯子趁塔里的人靠近想問他話之際將小刀埋進對方的喉嚨。他把那仍在掙扎著的身體往角落推去,順手抽走那人腰上的一柄乾淨的刀。
下一個——
火。火。
忒勒斯覺得自己彷彿回到那夜夜襲——事實上城鎮並沒有起火,他正站在塔頂端眺望那片由火把組成的光河,此時此刻他慶幸這裡有雨和那些泥瓦的屋頂。人能夠逃走的都逃走了,原本正在奮戰的也都慢慢準備撤退。
又一次。他所經過的道路終究會成為廢墟。
背後幾個族人剛剛到達,剩下的眾人守在塔下圍起一個圈。他們沒有多問他這個塔里發生過什麼,只是迅速和他交換了一些信息,轉身便去安置俘虜。
埃圖瑪維在哪裡?忒勒斯扶著塔頂的窗探出頭,瞇起眼睛想要辨認混亂中的面孔——應該不會太難才對,埃圖瑪維在這種時候應該是最亮眼的那個才對。他的目光掃過廣場。
那是什麼情況——
另一個人群停留在那片空地邊緣,火光的照耀下兩個對峙的影子,埃圖瑪維正緊握著大刀備戰,遲遲不敢向前,而對方……對方帶著相同蒼白的光暈,站姿很是從容——
找到了嗎?敵方的首領?他皺起眉頭。這個站位又是怎麼回事?決鬥?現在?埃特?困惑之餘他架起弓箭,拉滿弓,體力也差不多耗盡了。那傢伙哪裡來的自信能跟一個經驗豐富的人一對一決……從這個距離即便是這把弓估計也沒法造成太多傷害,但是只要能讓那些人分心哪怕一秒……
箭尖隨著那兩個影子來回搖擺,在他的手指間卻無比確信。埃圖瑪維不知道會不會生氣。
生氣便生氣吧,自己有任務在身,他必須得這麼做。
“咻。”
在忒勒斯腦海裡繪著對方被箭擊傷的畫面,直到他的後背因為用力過久而顫抖,回過神發現箭此時怎麼還在弦上。
一瞬間時間似乎暫停了,他動不了。有什麼慢慢攀上他的肩膀,溫潤如晴空和春日的陽光,笑聲在渾濁的空氣裡輕撫他的後頸,宛若銀鈴一般輕巧,彷彿從另一個世界傳來。
誰?誰還笑得出來?他咬緊牙不讓自己被影響,自己早該習慣了這種突如其來的打擾,就跟兩年前一樣……
佈著灰藍色紋路的手指輕輕搭在他的手背上,太小,太輕,帶著他完全無法理解的強大——他記起高燒中隱約看到的幻象,觸碰的瞬間幾乎將他灼傷,令他緊繃的身體退縮。
殺了他們。她說。
箭桿從忒勒斯手指間脫開,他尖銳的深吸氣將自己的驚恐壓回喉嚨末端。
【看TLS和三王互相敷衍(笑)三王不會想招TLS的啦這個人不確定性太高,只有ATM才會自信去撩好嗎】
【這個時候兩個人都沒法和三王正面剛,畢竟他比ATM早出生快要1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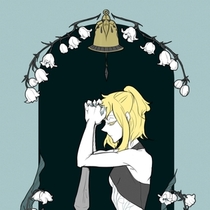
九,
若雨沒有太大的話,他們會早起洗漱,塞兩口昨日的乾麵包,巡邏,對打直到太陽升到當空,去提水,將衣服洗上,接下來剩下的時間便在鎮上閒晃。埃圖瑪維以為忒勒斯已經習以為常,但事實上每一次見到新東西這個人比自己還要好奇,他懷疑他可以的話會把所有能拿起來的東西摸一遍。
隨著雨變得越大持續得越長,他們的活動從街上移動到了祭壇裡面,那裡的醫者並沒有反對的意思,反而還很樂意教導他們讀寫。忒勒斯剛開始會在一旁安靜地聽,假裝自己也是從頭開始,在廢紙的背面畫小圖,不過經過幾次後人就消失了,埃圖瑪維沒有打算問他去哪裡,畢竟這個人一開始就是從這樣的環境逃走的。
我從來不是個很好的學生。他這麼說。所以他們把我扔到訓練場上。
你不介意嗎?
他聳聳肩。這是我唯一擅長的事情。
忒勒斯回到原本的樣子算是讓埃圖瑪維鬆了口氣——他從沒有這樣照顧過任何人,還以為有什麼地方犯了錯。他記得那日正午在河邊,忒勒斯緊緊拉著自己的手躺倒在草地上,將表情藏起來。在森林裡有十個人,他的聲音很小,我差點就死了。
他想那次經歷終究還是在這人身上留下了些什麼。
不久後埃圖瑪維自己去見過梅爾薩,後者被叫出來時還很驚訝的樣子,似乎本來就沒有抱有太大的期待。這個人比他印象中直爽很多,心裡沒有任何多餘的空間藏匿目的和情緒似的,他發現自己已經開始習慣不了這種簡單的交流。她隨手撈了幾個隨行,指示著他們去取些物品作為表示友好的贈禮,就埃圖瑪維所知這一行人都來自同一個家系,卻不是以家族的名義去交涉的。“不是所有人都同意,”她說,“可是畏畏縮縮的也不是辦法。”
他發現自己沒有什麼理由反對,或許就是因為如此他才答應幫這個忙。
厚重的幕簾隔絕了外面陰涼的空氣,他抖了抖身上的水珠,下意識捋了下上衣,深呼吸後才踩上那圓形的紅棕色地毯,面對對面一排面無表情的家長們他還是不禁會緊張——就算這些人他已經都熟識了,他總是會想起第一天自己也是被這樣圍著審訊——事實上他仍舊被審訊着,八雙眼睛,將他釘在原地。
“你怎麼比我還緊張?”
我還想繼續待在這裡。埃圖瑪維回答。
“獵人埃圖瑪維,陳述你的請求。”他們說。
“並不是我的請求,榭利氏族長女想和各位長老談話,我是來為她擔保的。”
“就憑你一個外人嗎?”
“你們讓我為忒勒斯擔保,為什麼不可以?”
“還不是因為你接連帶著危險的人……”
“聽著——”梅爾薩哼了聲,直起身就準備上前去對質。
“你聽著!”
他垂著眼,早就知道會得到這樣的場面,在他還給忒勒斯弓和劍的時候就已經有許多不滿的聲音,慢慢地長成尖牙咬回自己身上。他能夠明白這種謹慎,卻又怎麼也想不出有什麼事情值得讓幾些人代代將敵意傳承下去。獵人埃圖瑪維,他們這種時候會這麼稱呼他,他是屬於森林的獵戶,他們是來自平原的遊民——即便他們被相同的問題所侵擾,為同樣的目的掙扎。
“讓她說完。”他輕聲說道。
帳篷裡本來嘈雜的爭論突然安靜下來。周圍的人摒息,看著埃圖瑪維的手壓著腰間的獵刀,那淺綠色的雙眼暗沉如暴雨中的水霧,也沒有落在誰身上,就只是在腳邊徘徊,連梅爾薩也有些警戒地退開。等待在帳篷周圍負責以防意外發生的人開始躁動,緩緩地向中間挪步,卻沒有人敢上手——這些人多少都知道他能戰鬥,即便在這個小空間裡無法面對所有人他還是能造成無法估量的傷害。此時就只有坐在正中間長者傾身,緩緩招手讓他走近——真正的族長,也就是當初讓他留下來的人,那日也是這樣招手讓他靠近。他遲疑著,知道走過去的瞬間他就只會是個無理取鬧的小孩子。對方見了也沒有打算強求,手搭在座椅的扶手上面,“我們都很喜歡你,你也幫過我們不少忙,不過你來自森林,並不知道氏族間長年以來的恩怨。當然這不是你的錯,既然客人已經在這裡她的情願我們也會傾聽。”老人停頓,帶著種命令的意思。“但是,孩子,你如果一直都這麼越界的話我們也不得不考慮是否能讓你留下來。立刻把刀給我。”
埃圖瑪維沒有說什麼便解下腰帶連著獵刀一起踢到家長們的椅子腳邊,他當時承諾幫忙保護這個隊伍,傷害這裡的人是他最不想做的事情,可是同時他並不打算退讓——畏畏縮縮的也不是辦法。他稍稍側側頭,瞄過身邊的梅爾薩。“繼續。”他說。
她被這突如其來的動作嚇了一跳,半晌才反應過來,開口時多了份緊張。“東北那些靠打劫為生的混蛋不知道為什麼集結起來了,而且正在慢慢地掠奪我們的平原,現在還可以靠著地廣人稀避開那些傢伙,但要是哪天他們決定佔領這個鎮怎麼辦?你們打算逃嗎?逃走又如何?憑你們做得到自給自足嗎?”仍舊是沉寂,正是因為他們知道這些質問的答案,若要是能在平原上自己自足他們也沒有必要年年這樣追著資源遷徙。
“我們會找到辦法。”
“最好是。上次那場大火你們怎麼逃出來的?丟了多少人?十個?”
“八個。”
“那也沒有比較好啊。”梅爾薩歪過頭,“讓忒勒斯留下來也是因為誰也拿他沒辦法不是嗎?想著能收一個教廷的人做保鏢多好的事。好意思嗎?他才十七歲啊,雖然那傢伙完全不可信就是了……不過你們——除了在場的這幾個大概沒有自保的能力了吧。”
“確實如此。”老人回答,在周圍不贊同的目光之中沒有反駁和解釋的打算。“這就是你來的目的,試圖說服我們和你們結盟?你的父親同意這件事情?”他沒有等梅爾薩回答便露出笑容,就像平時那樣和善,“下次想要說服外人前先做到說服自己人再說,現在,請回吧。”
他們兩個被帶武器的人送出大帳篷,梅爾薩向著同伴搖搖頭,沒有多說什麼一起走出營地,最後她回頭給埃圖瑪維一個擁抱。他看著對方黯淡的神情,藏在長髮下幾乎強忍著不想表現出軟弱的樣子。“抱歉,還害你跟族人鬧僵了。我一直相信,即便那些家長們不願意面對事實也有聽到這些消息年輕的人會理解。我不喜歡這種氏族間惡性競爭的感覺,我只想要家人能過得上安穩的生活。”
“有需要的話我會盡力協助。”
“謝謝。”她離去前又停下腳步。“自己保重。”
十,
“就叫你不要跟那些人摻和在一起……”回過頭時忒勒斯已經從背後的車廂上跳下來,手正在箭袋裡數著有幾支箭,一時間埃圖瑪維都不知道這個人打算去找誰打架,茫然之餘只能伸手捏住他緊繃著的的手腕。
“別走。“他說。“不要做傻事。”
“做傻事的到底是誰……”忒勒斯低聲叨着,一臉不滿。“怎麼辦,會不會就這麼被趕出去?”
“我不知道。”
“你沒有別的地方可以回嗎?森林呢?話說你不是有個家人?”
“不在了。”
“為什麼?被殺了?知道是誰嗎?”
“我不知道,還沒有來得及去想是什麼我就把他埋葬了,我以為是野獸做的。”
“這樣……抱歉,好像問了不該問的問題……”
埃圖瑪維其實不太明白這種問題有哪裡不妥,這大概是某種祭司特有的說話習慣。他記得的並不多,那一天清晨迷迷糊糊地起來,木門半掩著,背後的燭火依然燒盡,平時會在那裡整備的人不在了,空氣裡瀰漫著他已經開始慢慢習慣了的動物的氣味。獵物要這樣處理,他的養父會在樹底下這樣對他說,去掉內臟,把皮剝下來可以賣掉,肉抹上鹽吸去水分來延長保存的時間,骨頭可以製成工具——但也就在那一刻他發現從未有人教他如何處理人,所以他在後院挖了個坑,那時候他的手和力氣都還那麼小。他記得要清理火爐,要去尋找食材,要把衣服洗乾淨,後來想想自己該感覺到些什麼才對,他想那個時候的自己還沒有真實理解到發生什麼事情,於是他給了旁邊的人一個沒有理由的微笑,“但是屋子還在,不知道到時候還能不能住人,到時候要不要先跟我去看一眼?”
忒勒斯愣住,別開臉壓低聲音模仿者埃圖瑪維的語氣。“這是在邀請我嗎?”
他丟開忒勒斯的手腕,隨意捋了下對方的後腦,“對。”忒勒斯忽然變得格外安靜,大概沒有預料到他會真的回應這個玩笑便不知道接下來該如何反應,敷衍地拍拍他的肩膀。我去走走,忒勒斯輕聲道,放心吧,我不會幹什麼。
埃圖瑪維這次沒有試圖挽留,歪著頭看著弓箭手小跑向帳篷的方向。他自己找了個木樁坐下,不想去思考剛剛自己在家長面前過分逾越的行為,忒勒斯是對的,自己才是做傻事的那個人。他一邊將小樹枝折成一節一節,聞到空氣裡的水汽,快日落又要下雨了。
他緩緩地漫步過營地的邊緣,看到水霧後面自己那張米白色的帳篷,周圍有忒勒斯的腳步——那個人走路非常輕,不仔細看很容易忽略,稍微掀開門簾的一角,如他所預料,弓箭和其他的裝備都被擱置在角落。埃圖瑪維會笑這樣做的意義何在,那日他不一樣空手走進危險之中。
他也應該笑,自己那份邀約到底是在期待什麼。他閉上眼就能回想起森林裡他從小就住著的那個木屋,每一個角落,每一扇門窗,周圍布下的每一個陷阱,屋裡石頭砌成的火爐,地下室儲存的各種皮革木材和工具,他的房間,門外院子裡簡陋卻整理的幹乾淨淨的小墓地。三個月並不算長,即便這般下雨,他想他還能靠自己修好那個曾經的住所,或者他大可直接和忒勒斯一起離開,過著去哪裡是哪裡的日子。
什麼都好……他立刻就揮去這種想法,自己發過誓,更不希望從小生活著的平原遭受侵擾——他早就默默決定了,如果要為了保護什麼而死,也會在這裡。
可是如今連敵人是誰都搞不清楚,若再次被驅逐,他還能做到什麼……
三個月前他被逐出森林。
埃圖瑪維從沒有和人提過,一方面是覺得別人並不會相信他說的話,一方面是不想在沒有搞清楚的情況下隨意散播恐慌。他記得醒來的時候看到窗外晃眼的白光,下意識用手擋住視線,還想著今天太陽為何如此明亮。穿上衣服,踏過空曠冰冷的走廊想著必須生火——自己很早以前已經接受了,試圖讓這個地方看起來有人居住,可是怎麼都無法將這裡弄回養父還在時的樣子——他停在門前,就和那日一樣,他突然感覺這樣的情境和過去相似的太過詭異,如果他此時打開門是否還會看到那具面目全非的身體……直覺告訴他不要進去,彷彿耳邊傳來的不是自己的心跳而是未知生物的低吼。於是他收起手,轉身走到前門邊,小心地提起裝著工具和武器的腰帶和斗篷。
走了可能就回不來了。他對自己說。
埃圖瑪維推開門,盡量不發出任何聲響,一瞬間眼前被亮光充滿,他瞇起眼睛,仍是一片雪白——下雪了?他想,這片地上鮮少下雪,更不要說是能夠覆蓋樹林還能過夜的大雪。他披上斗篷,讓視線有時間習慣光亮,他這才看清,不是森林的色彩被覆蓋,而是眼前的一切都缺失了色彩,從圍欄向外連同土地和樹幹,就只有樹梢縫隙透出的一抹灰藍和散佈在白色草叢裡的點點紅花。
這裡是哪裡,慌亂此時才開始爬上他的胸口,他所熟知的森林仍舊在這裡,所有的記號和路徑都在,可是他卻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埃圖瑪維撿起腳邊的斷枝向外扔去,樹枝劃過空氣落在白色的草地上,就那麼靜靜地躺著,並沒有被周遭感染的跡象。
到我這裡來。
他起步,不敢回頭去看是什麼在向他低語,只覺得並不會是個人類,他深吸氣踏出圍欄,迅速確認暫時不會有危險後便用最快的速度跑了起來。
埃圖瑪維用盡體力朝著平時出森林的捷徑前進,可是不知為何總是回到錯誤的地方,白色的異象猶如迷宮試圖將他困住,不知多久,他看到面前似乎有個開闊的空間——出口?他正想著還不能放鬆,穿過樹木時卻發現那不過是一個圓形的小空地。他踉蹌著差點跌倒在灌木裡,陽光和細雨之下空地中間矗立著一扇通往無處的破舊石門,他因為跟不上呼吸而無法思考,拖著身體繞到門後的花叢下希望能姑且藏身。
埃圖瑪維始終沒有看清楚究竟是什麼在追他,在那扇不知從何而來的石板門下,他閉上眼便沉睡過去。
半夜埃圖瑪維被身邊突如其來的動靜驚醒,睜開眼看到忒勒斯已經蹲在門簾邊,身上穿著裝備。“聽。”忒勒斯輕聲說,稍稍掀開了布的一角確定外面沒有危險。“好像有什麼不太對勁。”
埃圖瑪維沉下呼吸,寂夜中除了動物以外的確還有什麼東西在遠方轟鳴。人聲?他分辨不出來,但顯然忒勒斯認為這是威脅——這個人的視力和聽力一直都好的不可思議。“你去敲鐘。我去召集人手。”他翻身下床,“小心。”
忒勒斯沒有回答,已經帶著弓箭迅速溜進夜色裡。埃圖瑪維用最快的速度整備好,鐘聲響起,他跑出去,人們已經在開始在營地中央集結,因為睡夢中被吵醒而不滿,問著發生什麼事情和為什麼是那個人在敲鐘。
埃圖瑪維緩緩地步過因為疑惑躁動的人群,掃過一眼確認有誰在場。
我們遭襲擊了。他說。
【偽神:艹別宅了給我出去跑劇情】
【ATM:瘋狂直球】
【TLS:全世界不是要殺我就是要撩我,我覺得被針對了】
【接下來就是認親環節了(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