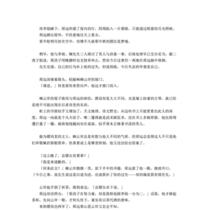【明月二】论坛开放http://orzpen.com/moon/forum.php
========================
—【明月千山】—
南宋年间,围绕着江湖百家展开的开放型日常养老企,目前一期剧情进行中。
世界观基调可参考金古梁温大师作品,真实系无玄幻。
目前企划主线已更新完毕,进入自由投稿时间。
------
企划印象BGM:
http://y.baidu.com/song/173529?pst=player&fr;=altg_new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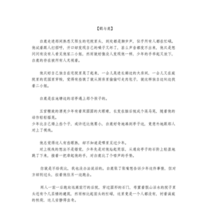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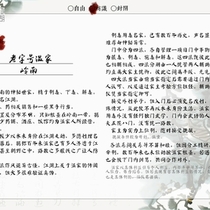
解谜来了,其实荔枝人的逻辑思维不好答应我如果有什么bug忽略它好吗(比心(揍死
第一人称注意!!
帖链接老是有乱码,于是其余略写的地方相关剧情见:http://elfartworld.com/works/106186/
========================================================
启
我杀过很多人。
因为自己,因为命令。
第一个是毒打我不成想要欺负我的“爹”,我知道他其实不是我爹,只是个想把我卖个好价钱的人牙子。(详见http://elfartworld.com/works/105462/)
当杀的人够多时,那就不是一条人命了,而只是个数字。
从被义父收养开始,我就明白,对于义父来说,我只是个好用的杀人工具。现在看来义父从不用疑人,连同我自己都不清楚的身世都查得清楚。姐姐找出的这封信,倒让我想起昔年我十九生辰时,义父告诉我,待我满二十时,让我去一个地方,有一个人需要我见见。可惜义父没有等到我满二十就命丧叛徒之手。没想到五年后,这件事竟然被我们重新翻出。
在潜入叶府之前,我想过很多种情况,却没有想到,我第一眼是见到一个和我面貌相似的人吊死在房梁上,我第一次见到自己的亲姐妹,竟是一具冰冷的尸身。
我最初只是想进叶府来看一看我的至亲血肉,和查找我被卖给人贩子的原因,可是现在我改了主意。
我刚刚将她的从白绫上放下时,她的身体已经冰冷僵硬。正在查看她同我十分相似的面孔时,却觉察到外头的雨声中传来一人窸窸窣窣的脚步声,此时要藏起尸体为时已晚,来人是什么身份我也能猜出八分。我迅速退到门边从腿上抽出匕首,在她踏进屋内关门的刹那被我从身后制住,并将匕首架到她的脖颈上低声威胁她不许出声。果如我所料是个丫鬟,我胁迫她走进卧房,她看到躺在地上的小姐时,身形顿时晃了晃倒了下去。
我瞧见她直接吓得晕厥过去,只能先把她放那里,四处查看小姐的房间。没想到却从写字用的几案上发现了她的绝笔信。叶小姐名叫叶采葑,字迹娟秀,通篇只说不愿受辱、不愿辱及家门,劝父亲珍重之类的话,却未说明到底所受何辱。见到再找不出什么,我只能先将这绝笔信收好,转头就拿了水泼到丫鬟的脸上。
她悠悠醒转的时候已是后半夜,雨也渐渐停歇。那丫鬟一睁眼瞧见我这个蒙面的黑衣人就想张口呼救,被我迅速捂住了她的嘴巴。
“老实些,不然现在就杀了你。”我放开她的嘴把刀子架回她的脖颈上。
她被吓得发抖,瞥到旁边小姐的尸身又开始不断掉眼泪。“是你杀了小姐?”她颤抖地质问我。
“是你家小姐自行了断。”
“你胡说!小姐过几日就要成亲了,如何会寻短见?”
“我胡不胡说,你自己瞧便是。”我把叶小姐的绝笔信丢给她,让她自行辨认。“这是不是你家小姐的字迹,你比我清楚。”
那丫鬟逐字逐句瞧完书信后,失魂落魄地跌坐在地上不知所措地流泪,嘴里念只叨着小姐。
我瞧她悲愤的样子,蹲下身问她:“你难道不想知道,你家小姐为什么出嫁前夕寻死吗?”
那丫鬟闻言含泪把我一瞪:“你想做什么?”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你家小姐寻死。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忙。”
“我凭什么相信你?”
“就凭这个。”我说着,摘下了蒙面。
当她瞧见我的脸孔时,充满恐惧的面孔露出惊讶之色。
“你究竟是谁?”她颤抖着问我。
“不会害你就是了。”我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我是谁?是季白萍,还是叶家的小姐?这个问题其实我回答不上来。
这名丫鬟名叫锦衾,是叶小姐,也就是我的亲姐姐的随身丫鬟。名字也是叶小姐起的,取自《葛生》中“角枕粲兮,锦衾烂兮。”
从她口中我得知了叶府内的情况,下人、管事、厨娘甚至叶老爷的情况,叶小姐是已去世的叶夫人的头一个孩子,自幼体弱多病,老爷只对那个败家少爷上心,对小姐毫无关心。管事姓林,媳妇就是管厨房的林嬷嬷,在叶府跟了叶老爷三十年有余,资历最老。
我将叶小姐的尸身放回床上,往她口里塞了定尸丹,虽身子已经僵硬,但可保短时间内尸身不朽。锦衾帮我换上了叶小姐的衣服,又照着叶小姐的样貌画好妆容,并教了我她平时的言行举止。正好因为叶小姐体弱,基本是足不出户,也省去了很多会被认出的麻烦。
从锦衾口中还得知叶老爷平日似乎不喜人多,整个叶府下人比较少,叶小姐只有她一个贴身伺候的丫鬟。从她的躲闪的眼神里我明白,她是不信我的。可是她宁愿答应我,也不愿意去找叶府的其他人,也足以瞧出这叶府的情况。不过,她信与不信,都不会影响到我最后要的结果,只会决定了她自己能活多久。——如若她生二心,我肯定先杀了她。
承
锦衾毕竟只是个不出府的丫鬟,对老爷的事情知之甚少。要想知道更多,还得出去走一趟。从白露那里得到叶大公子的生辰八字,还有一些关于叶公子的消息。这倒是让我明白了七八分,叶小姐的死,多半就是因为这叶公子。
我当夜回府后就细细询问她前几日小姐的行为举止是否怪异,锦衾只告诉我,小姐原本过年后身体好很多了,叶老爷才忙去和定亲的人家确定成亲的日子。但是自半月前似乎小姐的旧疾又开始复发,终日卧病在床大门不出。听得锦衾说了这些,我心里更清楚几分,叶小姐的病,只怕是心病。
次日的夜里我也依旧出门,这次却没有改头换面,而是就穿了一身叶小姐的打扮出去。
取那个花花大少的首级轻而易举,不过居然没想到这样的货色居然还会被别的人盯上。对方轻功极好,用暗器,夜色里我没瞧清此人样貌,而我也没有刻意遮掩我的模样和行踪,只带着人头让那个人在我身后,因为在别人看来,只是叶家小姐砍了叶公子的脑袋。虽说我总觉得,这个跟踪之人我不是第一次见面。
锦衾瞧见我带回的人头吓得魂飞魄散,可是事情已走到这一步,她虽害怕却也只得听我命令行事。我用另外一颗定尸丹放在头颅的口中,再将头颅藏入平日敞口罐内以纸封好后吊至房梁上。
倚香阁的事也是从白露处得知,这位叶大公子对一位铁琵琶的名角求而不得,看来为了确定最后一件事,还得去倚香阁一遭。这一遭却去的不虚,除了确定了叶公子的事情也能享耳福。(详见http://elfartworld.com/works/109063/)
事情既已确定,就等成亲之日了。
转
转眼就到了成亲的日子。(详见http://elfartworld.com/works/110970/)
晨起我便被一些这几日都未见到的丫鬟和喜娘围着开始梳妆打扮,我任凭她们梳洗打扮,对着镜子,我竟有些恍惚,虽是假扮的别人,我居然也有穿上嫁衣这一日。不过我不是很喜欢红色,红色只会让我想起血的颜色。
算着迎亲队伍的时间,我向锦衾使了个颜色。她将几个人都支出去,换上了我准备好的迷魂香后也借口有事关上房门出去,不一会还在屋内的几人已经中了迷香倒在地上。我将迷香熄灭,把叶小姐的绝笔信放回几案上,脱下外衫,将绳子绑在身上,把叶小姐上吊用的白绫和绳子一起绕过房梁。又取出叶公子的头颅,将他的毛发缠到我的右手。接下来只要把脖子伸进白绫里,踢倒了凳子就可以等人来发现尸体了。
从前我杀人时,也有的人因有特殊要求而下重金。所以假扮一具尸体对我来说不是难事。
叶小姐的尸体或许能给众人带来很大的冲击,而对叶老爷来说其实也没什么,叶小姐自缢只会让他觉得丢了面子,叶小姐手里的人头,才是最让他接受不能的。
因为有锦衾帮我里应外合,现场的人抬人的抬人,报官的报官,却毫无人敢去接近一具拎着人头的尸体,等到人都离开或者被锦衾支走后,我割断了绑在身上的绳索,将绳索整个抽掉后,把一直藏在被褥中的叶小姐的尸身取出,将嫁衣脱下给她穿上后,原样把她放回白绫上。
当完成这些事后,本应该杀了锦衾灭口,可是念她对我的姐姐如此忠心耿耿,而如没有她的帮忙,我在叶府这些事业不好做。
我只问她:“叶府如今也不是你在的地方了,你可否跟着我走,谋个其他营生?”
锦衾却笑笑摇头道:“奴婢的命是小姐给的,既你替我报了小姐的仇,我也还了你的恩情,如今我们也两清了。”说罢竟然转身一头撞死在桌角上。我看着她的鲜血溅满整个几案,只得帮她阖上双眼后离开叶府。
合
叶府的事情,一夜之间已经传开了。
我在街上随意找个早点摊都能把整个事情始末听个大概。
同姐姐道别之后,我又潜回了叶府,叶府此刻死气沉沉,众仆人们散的散,走的走。更别说是有不止一条人命的小姐闺房了。虽然已被官差过来查封,不过这点还难不倒我。
今夜是个晴朗夜,月虽不圆,但也够亮堂,还依稀瞧得见星辰。
我换回本来的衣服,慢条斯理地踱步到叶老爷的房门外。瞧见院内一个仆人都没有,只有一个端着药的管事爷要往屋里走。那位管事瞧见我站在门口,吓得手里一抖药碗跌落,我伸手接住他手里的药。拍拍他的肩,示意他放下盘子坐在旁边的石凳上。管事爷面色铁青,一直死死盯着我的脸看,显然他把我认成了死去的人。
“我是人,不是鬼。”见他坐下,我先告诉他,“不过,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嘴角带着笑意问他。
他只瞧我不答话。
“林管家,你也跟在老爷身边30年了吧?那么,你是知道的了?叶公子的生辰是七月初七呢,我的生辰也是七月初七呢。”
管事爷似是想起了什么,颤抖着抬起手指着我,嘴皮不住地打颤:“你你你你你……是你…………?”
“是我,想不到我居然会回来?”
“你……你……你你你……你回来……干什么……?”
“回来么,当然是看看,当年是谁——把我丢了的?”说到这里我抽出匕首在手里把玩着。
林管事颤抖得更厉害,急忙噗嗵一下跪到地上:“二小姐!!二小姐!!老爷……老爷不是不要你,是……是他有他的难处,所以才……”
“所以才用我换了你的当天刚出生的儿子?然后把我卖了?”
“您是老爷的亲骨肉,老爷,老爷怎么舍得卖了您呐,是……是把您寄养在别处……然后有天,那边来信说小姐被人牙子拐走了……”
“哦——难道不是叶老爷一瞧见我便想起难产的夫人和不是自己的亲生子所以郁结难解干脆送的远远的吗?”
林管事听到我说此处抖的更厉害,也不敢说更多。“因着我害死主母,而又因为夫人作嫁妆的产业不愿归还给莫家,所以无法再娶。所以都怪到我的头上罢了……可是,和我真的有关系吗?”
“如今,有没有关系,也不要紧了。反正叶蓁也死了,还是被我一刀砍下了他的头呢。”
我见他只跪在地上不答,也不再理他。端起托盘往叶老爷房间里去。
屋内富丽堂皇,叶老爷已经醒转过来。他瞧见我端着托盘进来,也同林管家一样,身躯一震,嘴巴上下不断张阖,半响吐出一句:“你是……苓儿……”
苓儿,这是我的名字吗?我冷眼睥着他,把药放到桌上。
“想知道,叶大公子怎么死的吗?”
他不答。
“被我砍死的,知道我为什么砍死他吗?”
“因为他知道自己身世以后,在叶小姐成亲前污了叶小姐的清白。”
“所以叶小姐自缢身亡了,在七天前。”
我自顾自地说完这些,不管此时的叶老爷是何等震惊的表情,只是当着他的面把一包鹤顶红倒进药碗里。又端到他的面前:递到他的手上。他只愣愣地接住,目光呆滞地对着我。
“该服药了,爹爹。”我温言道。这是我第一次叫我的生父,亦是最后一次。
所谓父亲,不过是留着相似血液的陌路人。我不想再多看这位叶老爷一眼,看着他喝完毒药就转身出门。回到门前,只瞧见林管事已经吊死在院里的树上。
甫一出叶府大门。就瞧见院墙墙沿下头停着白天接我的马车。上了车马车就动起来,七弯八转进入一处院落,两边有人引我下车。进入屋内只瞧见大姐斜斜的歪在贵妃榻上。似是在闭眼小憩,待过了半响,她才淡淡问道:“回来了?”
“嗯,回来了。”
从未有人知道叶家有过一位二小姐。
过去如此认为,现在如此认为。外人如此认为,叶家也如此认为。
我也如此认为。
===============================================
Q:白萍本应该叫什么?
A:叶采苓
Q:白萍和一个死尸睡那么多天不怕吗?
A:活的人都不怕还怕一个死人吗?by白萍
Q:砍头那天晚上那个跟踪的人到底是谁?
A:这个跟踪的人自己会说明的……!
Q:去倚香阁到底为了确定什么事?
A:确定叶公子干禽兽不如的事情到底是真的禽兽不如还是他知道内情。现在确定是他知道内情而有恃无恐。
Q:为什么白萍一定要先亲自假扮尸体?
A:造成完全密室,让人确定就是自杀。
Q:白萍杀他生父了吗?
A:她没有亲自动手,而是把真相告诉叶老爷以后逼他把毒药喝下自尽。
Q:和叶小姐定亲的新郎怎么办?
A:这不在她考虑的范围内。




“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
念了这两句诗的,是一个青年男子,一身霜色衣衫半新不旧,腰间斜佩长剑,望着眼前粼粼水波,正自出神。这诗是诗仙李太白传世名篇,六岁小童亦可诵得,然而当真来到镜湖、站到若耶溪畔,忽然这两句涌上口边,意趣与在书斋之中学得,自有不同。想李太白彼时虽不得意,乃有古来万事东流水之叹,然而这诗的气象胸襟,大开大合,毕竟不是凡人所有。
正自乱想时,他身侧一老仆弓弓身问道:“少爷,什么吩咐?”
青年回过神,摇头道:“并无甚吩咐,不过自言自语罢了。这若耶溪这般景致,我居上虞,几步之遥,却未曾得来过几次,实在可惜。以天下之大,不知更有多少秀美山川,只怕终生不得一见。”
那老仆身量不高,瘦骨嶙峋,肤色黝黑,头发斑白,一身短打扮。却与一般下人不同,听了青年人这话,也不凑趣,只听得未曾吩咐他,便呆着脸一声不答。青年人也不介意,真个当自言自语,又去看水光。
此刻是晌午时分,虽连日晴天,毕竟入了七月已不太热,这一主一仆,似富家子弟郊游玩耍,闲适得紧。青年人忽然脸色一滞,道:“胡叔,咱们这便走吧。”
说着信手丢给旁边艄公一块碎银子,快步走上早备在一旁等他二人的小舟。那胡叔仍是不答话,低着头跟在他后面上了舟。艄公得了银子,喜笑颜开,解了绳索,也跳上舟来,长长念一声:“走嘞——”,便要撑船。
胡叔忽道:“且住。”
艄公刚拿起篙竿,尚未沾水,抬头赔笑道:“客官还有什么吩咐?”想是那小块银子功劳,这艄公方才还爱答不理,此刻热情了许多,便是对胡叔也恭恭敬敬起来。
那青年人原本容色和善,眉眼间总带一丝盈盈笑意,此刻蹙了眉,轻轻跺跺脚道:“我说,开船。”
胡叔唤道:“少爷。”拿眼去看他。
青年人虽不愿转头,渐渐被看得不自在起来,终是叹了口气,道:“唉,是我的不是,胡叔莫怪。”转眼见艄公一脸怔忡不知所措,又微微一笑,安抚道:“船家不必慌,我们说几句话就走。”
此时方有一阵马蹄声由远而近,一骑奔了过来,至岸边方有一人滚鞍下马,向青年人行礼道:“可算追上少爷了。”
青年人此刻倒舒展了颜色,笑道:“章师父,何事劳得你老人家出马?我爹还是不放心么?”
那章师父是个苍头老人,看去筋骨却是硬朗,和那胡叔对视一眼,苦笑道:“少爷,老爷说了,请少爷回去。”
青年人没半分异色,仍是含笑道:“我不回去。”
那章师父似也料到,干笑两声,道:“少爷,有什么话,回去自可跟老爷当面谈,还请少爷别叫老章头为难。”
“我岂能叫章师父为难?”青年人忙道。这章师父是他拳脚启蒙师父,他向来以师礼待,此刻章师父这话很有几分倚老卖老的意思,他不能叫他不卖,却也不想买。一边思量,一边细声慢语答道:“只是这一趟,我非去不可,也非我去不可。烦章师父跟我爹说一声,我必将找……带那人一齐回去,请他老人家安心才是。”
那章师父一脸难色,道:“少爷有所不知,此事……此事老爷自然安排别人去,”青年人不肯明说何人何事,他也跟着含糊称呼,“倘若真是不得,老爷说了,他可亲自出马,断没有不成的道理,叫少爷不必担忧,还是先回去商量商量再说。”
青年人沉吟片刻,忽道:“章师父,你在我陆家,有三十年了吧?”
这话风马牛不相及,那章师父一脸莫名其妙,答道:“老章头自徽宗爷元年便在陆家服侍老爷,今年是……第四十三个年头了。”
青年人点头道:“我今年才十八。陆家的事,章师父知道的,是比我多的。”
那章师父小心翼翼地看了看他,答道:“不敢。”
青年人微笑道:“章师父不必紧张。章师父是个聪明人,胡叔也不是外人……我便明说了吧,阿爹为何唤我回去,姊……此事是如何起的,我约莫也知晓。章师父自然更是心中明镜一般。”
那章师父便拿眼去看胡叔。胡叔仍是低着头,呆着脸,一言不发。青年人道:“跟胡叔无关。章师父还不晓得胡叔?最是惜字如金,若一次跟我讲话多过十个字,我便可去上炷香了。”
章师父赔笑了两声,再开口却道:“老奴不明白少爷的意思。”
青年人不以为意,挥挥手道:“那也无妨。章师父只消跟我爹娘说:养育之恩深重,依明粉身不足报春晖片缕;姊姊也是爹娘亲骨肉,我亲姊姊,自我幼时一处长大,待我极是友爱。我陆家只这四口人,素来相亲相爱,一体同心,自当毫无嫌隙,亲密无间。当此乱世,更是如此。世道不太平,我不放心,一月……两月,最多三月之后,必然归还。”
章师父寻思半晌,方道:“好罢。说不得,老章头回去传这一段话。也请少爷务必小心为上。”
“多谢章师父挂心,依明自会多加小心。”
章师父拱了拱手,径自上马去了。青年人转回头,见那艄公呆呆站在一旁,望着他们。他心下多少省得,江南多水路,舟楫是常见,骑马却是难得,况且金人不断滋扰,马匹多为军用,百姓人家有匹马骑,着实并非易事。果然那艄公按捺不住,问道:“非是小的乱打听,只是适才听得,少爷莫不是陆家庄的大少爷?”
这话问得不伦不类,青年人笑起来,点头道:“正是,陆家子陆依明。”
艄公啧啧连声:“原来是上虞陆家!怪道怪道,也是小的愚笨,看少爷这气派,原该知道,这绍兴城内也没有哪个能有?便是知州老爷家的公子,也难得少爷这么……这么……”
陆依明听他胡吹大气地奉承,末了又卡壳,心下好笑,自不当真,正要开口叫他开船,一直默不作声的胡叔道:“这船,几钱?”
艄公发愣:“啊?”
胡叔索性抓起他手,拿过篙竿,又将一枚银锞子放在他手心,道:“这船,买了。”那银锞子少说有三两重,这条小舟不过几块木板钉钉,说值半吊钱都是抬举,决计是不亏。那艄公呆立那里,似乎转不过来弯,银锞子是立时攥住了,面上还是呆呆傻傻,张口结舌地瞅着胡叔。胡叔伸手示意他下船,那艄公又浑浑噩噩回到岸上,胡叔自行撑起篙竿,深入水底用力一点,小舟登时离岸丈许,向下游漂去。
陆依明默默看他施为,待船离岸,方道:“何不留那舟子撑船?倒要劳动胡叔亲力亲为。”
胡叔道:“吵。”
陆依明不禁一笑:“确实。”
胡叔又道:“不是好人。”
陆依明却是一怔:“呃?”
胡叔用脚点点船板,弯下腰揭开,上面是薄薄一层木板,下面露出真正船板,竟掏了一个大洞,又拿一块圆木板堵上。陆依明不是笨人,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走,登时皱起了眉:“这?”
胡叔点点头,重新把薄板盖上。陆依明思量片刻,道:“我水性也还过得去,家住还这么近,想必他也不敢害我。”
自朝廷南渡,北人也纷纷过江来,倘或是北人商客,不识水性,又在当地无亲无故,船行至中游,那艄公悄悄把这洞一扒开,再不会有人知晓有些人就此彻底消失,盘缠细软自是落到艄公手里。如此妥妥当当,确实不必害陆依明这等本地大户。这在江湖之上原是不值一提的常见戏码,但陆依明毕竟听闻不多,虽自我安慰一句,终究是有些寒心,又点头道:“是了,就是他不去害我,我们又何必跟歹人同船?兼且,当真太吵。”说到末一句,又笑起来。
胡叔仍没理他,自顾遮好船板,又去撑船。陆依明早惯了他寡言,自坐在舟尾看水,这日亦是天朗气清,水面映着日头,宛如撒了一江碎金,又都活过来跳跃攒动。陆依明心不在焉地看着,暗自等着胡叔开言。
船至中流,胡叔才问:“你怎知?”
陆依明故作不解,反问道:“我知什么?”
胡叔寂然良久,方道:“你晓得。”
陆依明看他半天,终于不再玩笑,轻轻叹口气,道:“唉,胡叔是看着我长大的,我瞧着就跟长辈也近似。只当预演罢,我还真不知异日如何跟阿爹禀明。”
这胡叔看去有五六十岁年纪,其实是老相,实际尚不及五十岁。他母亲是陆家现任家主、陆依明父亲的乳母,陆父幼时与他一起长大,亲如兄弟,是以胡叔在陆家确实地位超然,陆依明这话说出也并无不妥。而陆依明自幼便得胡叔照料,虽然胡叔寡言罕语,但待陆依明也是十足好,陆依明心里,有时比威严过头的父亲还要亲近三分。只是他酝酿半天,仍是不知如何开口。踟蹰着又叹口气,方道:
“先说姊姊吧。姊姊性子是不大好亲近,但人是最好的,素日也最守礼,我原本还奇怪,怎会突然留书出走呢?又是不解,又是忧心,而此事终究也不便太多人知晓,便禀明阿爹出门。也幸而胡叔肯随我出门,不然,我看爹娘再不能松这个口。”
原来陆依明长到十八岁,还是初次不随父母独自出远门,而这一出门,便是为了要寻他出走的姊姊。他陆家在绍兴府如何他不知道——观方才那艄公,也是有些名气——在上虞县城,也算得有头有脸的人家,陆依明虽不在意,并且觉得他姊姊约摸也不会在意,但一个未许人家的小娘子擅自跑出门,就算他们习武之家不比那些个读书人狷介,终究不甚好听,陆依明也很不愿有人议论他姊姊,是以方才有旁人在,他提起时都只说“那人”“那事”。
他又叹了口气:“刚出门时心急如焚,到处乱走,却也没撞到姊姊踪迹。而这时阿爹叫我回去,我也未曾多想,立时就要回去听阿爹安排,却刚好探听到姊姊是往临安府去了。我自然是要过去看看,却不料阿爹竟然拦我……我心下便有了猜疑,悄悄找素练姊姊——就是姊姊的贴身大丫头,胡叔兴许不熟,我知姊姊是很信重她的,向她问了当时姊姊离家情状,约摸八九不离十,晓得姊姊为何离家了。”
他看了看胡叔脸色,胡叔脸上还是毫无牵动,恍若不闻。他只得再叹口气,续道:“后来我跟娘说了出来,便不甚着急,是为有了缘由,我想姊姊的身手不比我差太多,虽然说不上高手,偶然遇上一两个小毛贼还伤不了她,运气若不是太差,或许还吃不了大亏,因此不再着紧,慢慢找来……唉,是了,这是托词,实是我也不知如何见她才是。而阿爹今日竟然请章师父直追到若耶溪边,我只有愈发笃定,姊姊必是无意中得知了,一时想不开,才跑了出去……最怕是,一时半刻,也不愿再见我。但她孤身女子,怎好留她一人在临安府乱闯,少不得要寻她回来才是,且此事既然由我起,也当由我结。我不听阿爹话回去,胡叔不会怪我吧?阿爹,唉,阿爹也不要怪我就好了。”
胡叔抬眼看他,道:“为这,不回?”
陆依明道:“自然是为这个,还能为什么?”
胡叔难得说了句颇长的话:“怕是,为你,一时半刻,不愿见老爷。”
陆依明一时间哑口无言,心中忽而飞过无数旧事,三两岁初次记事时,他阿爹,端方严肃的陆家老爷,在阿娘撮弄下笨拙地把他背到背上,玩“飞高高”,十年后偶然提起时阿爹的脸色黑如锅底,称绝无此事;四五岁时跌了一跤手臂骨折,一贯待下人温柔可亲的阿娘,罕见地大发雷霆,把当时跟随他的侍女们骂了个狗血淋头,还是他自己开口“替姊姊们求情”才算过;六岁时第一次见到自幼在峨眉修行的姊姊,那时比他高了一个头,拍着胸脯说姊姊回来了,再也没人能欺侮你,被阿娘一通教训女子怎可如此粗鲁;……还有便是,那之后一两个月,他无意中听到家下老仆交谈,突然得知的那桩事:起始他如何肯信,然而私下里悄悄探听,诸多印证,却只是越发凿实了。
一晃十二年,若是姊姊那位峨眉的师尊——那位不知有没有过百岁的苍云禅师看来,想必也只是白云苍狗不过转瞬,然而对陆依明而言,他活才不过是活了十八岁,十二年,已经是相当之长。他真心微笑起来,恳切答道:“虽是不知如何跟阿爹禀明,但我其实……六岁起就晓得啦:我并非爹娘亲生子,乃是阿爹拾来的弃婴。”
胡叔的面容终于略有松动,他面带疑惑,直直看着陆依明。陆依明柔声道:“只是那又如何?阿爹阿娘待我如何,我心里是知晓的;而阿爹阿娘不愿叫我知道,那我便不知道。唯有姊姊……”他最后又叹了一口气,道:“只望姊姊不要太生我气啊……”
胡叔早不再看他,背过身去撑船,留他在一边默默出神。然而这件事他早已想了无数遍,焉能此刻突然有了什么新鲜主意?到底只能苦笑摇摇头,问:“胡叔,咱们这走水路到临安府去,还需多久?”
“三个时辰。”
“如此近。”陆依明叹道,“我竟从未去过。”
只曾听闻,临安城如今是行在所在,鱼龙混杂,居行皆不易,不知姊姊这一个月辰光,是在何处渡过,又过得如何?
但愿相见不会太难。
——————————
介绍了一下小少爷身世。
感觉露了好多马脚……看到什么bug大概不是错觉(。
实在不擅长考据,无论历史人文水文地理,有任何舛错都欢迎指正,十分感谢;当然懒得说就当是架空放过去的也多谢宽容……or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