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月二】论坛开放http://orzpen.com/moon/forum.php
========================
—【明月千山】—
南宋年间,围绕着江湖百家展开的开放型日常养老企,目前一期剧情进行中。
世界观基调可参考金古梁温大师作品,真实系无玄幻。
目前企划主线已更新完毕,进入自由投稿时间。
------
企划印象BGM:
http://y.baidu.com/song/173529?pst=player&fr;=altg_new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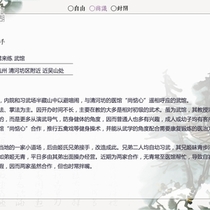

上接:http://elfartworld.com/works/185122/
====================================
前情回放: 田知甚对宝藏的来由进行了一系列的推测,发觉黄龙岛正是星罗宫旧址,而另一边,阿羡等人则依照总会的任务指示,找到了神秘的禁地入口……
====================================
田知甚一行人很快发现,有无证据已毫无意义,因为杀戮已然开始。
他们先是在树林里的撞见天罡斧徐广阳七零八落的尸体,很快又在山谷中发现两名身首异处的紫衣少年,而杀死他们的刀客,也因伤势过重,倒毙在三十步之外。
尽管死人不会说话,但任谁也看得出打斗激烈,而这些紫衣人无疑就是星罗宫的弟子。
卢泰本想掘坑掩埋尸体,以免被野兽啃食,但星罗宫已经开始狙杀分散行动的人,实在不应在此久耽,无奈之下,只得先堆了些石头掩盖,也强过曝尸荒野。
不久后,三人沿着河流来到一处巨大瀑布之下,田知甚眼尖的察觉到,水潭附近的地面留有不少脚印,潭边青石上沾的湿泥痕迹尚新,似乎有几人刚刚来过,卢泰则勇往直前,沿着泥痕于青石上借力纵入瀑布,才发觉其中别有洞天。
原来瀑布后的半山腰隐藏着一处洞穴,置身其中,只觉大小洞穴层叠相套,既互相通透又崎岖难辨,若不留神来路,只怕要兜上十来圈才能走进最里间的四个石室,石室清一色的空空荡荡,除了石桌石凳,唯有壁上凿刻的大片古篆字分外显眼。
田知甚等将山洞摸了个遍,再没有任何特别的发现,只好顺着垂在山壁间的铁链回到地面,走出一段距离后抬首仰望,但见瀑布状若阶梯,从十数丈高的山崖分流而下,于第二阶山石间迸出轻烟白絮,复又至第三阶冲激盘桓,最终在第四阶汇聚成数条玉龙,轰然泄入翠绿的深潭之中,泼溅出白光千点,又于风中化作云雾。
眼前是难得一见的四叠瀑布,又有凉风鼓袖,水气萦身,田知甚心道,若这里不是杀机四伏的黄龙岛,也算是人间奇景,不输于蓬莱十三景的“倾天银雨”。
一番折腾,已近黄昏,卢雁干脆捡柴生火,要烤一烤自带的冷炊饼,填饱叫嚣的肚子,卢泰忙不迭的削了根粗长树枝,自告奋勇的去水潭叉鱼,田知甚无事可忙,只得坐下帮着烤炊饼。
他先从怀里取出一把薄竹刀,在早已经冷透的炊饼上划出几道齐整的口子,接着串上剥去外皮的树枝,在火里翻了十来个转。待冷硬的饼面渐渐蓬松起来,又摸出一个油纸包,取出几个细竹筒,依次撒上调味料。
“你……怎么还带了这么多调味料?还有这刀……田公子平时都是这样吃炊饼的?”卢雁目瞪口呆的看着田知甚有条不紊的撒了好几种调味料,她本想用火烘热就行了!不知是不是饿了的缘故,只觉得原本普通的炊饼,居然散发出肉的香气,连微微鼓起的焦黄饼面也显得分外的诱人。
田知甚眼神专注得连刚才看石洞篆字时都不曾有过,语气却很轻松。“香料本来是烤鱼用的,用来烤炊饼应该也无妨,拿竹刀剖鱼片鱼,可减少铜铁腥气,要是有河鱼又有山鸡,可将鸡肉去骨剁茸,与调味料拌匀烤至五成熟,再塞入鱼腹上火慢烤。这是河鱼的烤法,若是海鱼……”
卢雁听的两眼放光,满心热切道,“既这样,等哥哥回来我们再抓只山鸡好不好!”
田知甚刚要应允,恰巧卢泰嘀嘀咕咕的回来,可惜却是空手而归,“怪事,老大的水潭怎么连小鱼小虾也不见一只?我看还是打野兔来得快。”
田知甚道,“瀑布冲击之力太大,鱼在浅水处如何禁受得住?不过方才见那水潭似是极深,潭深必有大鱼,卢兄尽管去打野物,我去去就回。”
说着他将插着炊饼的树枝塞给卢雁,嘱咐两人烤至两面微焦就可以吃,还不忘掰下一块饼做“鱼饵”,以他钓鱼的功夫,一小块鱼饵也足够了。
但他这一去却没有再回来。
卢泰和卢雁连抓了三只山鸡又放走两只,直等到月上树梢,再也按捺不住,举着火把到水潭边找人,可除却冷清的月色和隆隆水声,潭边没有任何人的踪迹。
卢雁忧愁的看着水面上被割裂的月色,又看了看卢泰,“田公子不会不辞而别的,他定是看到什么不寻常的事,悄悄跟了过去。”
卢泰点头,“要是碰上星罗宫的人那可不妙,我们先把火盖好再往林子那边找找。”
两人嘴上不说,心里却腾起不详的感觉,难道田知甚真的遇到了星罗宫的狙杀?可为什么他不发声示警,是来不及,还是由不得他发声?
田知甚确实来不及示警,确切来说,是压根没想过需要示警。
他在潭边寻了块石头坐下,将袖中藏着的银丝尽数解开,悠闲的将几根水草和鱼饵挂好后一扬手,将银丝勾远远的甩入水潭深处。
平日里,田知甚左右袖中都收着极长的银丝鱼钩,这些东西本就作钓鱼之用,这是他的一大乐趣,偶尔也可做武器使用,以银丝勾的坚韧,足以钓起寻常海鱼,所以田知甚以一种姜太公的心情,闭着眼睛听水声。
他回想着白天看过的石壁刻字,每间石室的墙壁上都有九十字,看起来像是诗句,刻字的人在如此隐蔽的地方留下篆字诗句,应当有其用意,可这些诗句无论横看竖看,甚至以藏头隔字等方法看,都没有太深的含义。
万贤地宫里也有类似的诗,这里的诗句会不会也是一种特殊的谜题?
夜色渐沉,银丝越放越少,连田知甚也觉得,这水潭未免深了一点。
就在这时,银丝“嘣”的一紧,田知甚霍然睁眼,手上已用起缓劲划圈,要耗一耗上钩大鱼的力气,谁料对面拉力愈盛,拼命往潭心猛坠,偏偏这口潭深的出奇,直到无线可放,对面竟力气不衰,僵持了足有一盏茶的功夫!
田知甚一面觉得好笑,一面也被激起了少年人的心气,难道这水潭里还能有龙王不成?
眼见线越崩越紧,只怕就要脱钩,他忽地将银丝在臂上狠绕几圈,一个翻身轻巧的贯入水中,心道既如此有力气,且让你拉着,看能游到几时?
他自恃水性极佳,又可在水下视物,一边收线一边任由自己被拉往潭底,奇怪的是大鱼不往水缓处逃,反倒猛地冲入瀑布,霎时间泡沫翻滚目不视物,上方的水流如有千钧之力压在身上,田知甚突觉手臂上拉力激增,紧接着头部狠撞在石上,脑中一昏,身不由己的被拖入黑暗。
田知甚很快醒来——
他撞昏不过片刻,下意识的在水里保持着闭气的状态,手臂上的拉力也还在,但四周一片黑暗,身体不断撞上的尖锐石头让他不得不清醒,也很快明白了大事不妙,四叠瀑布如此壮观,可见岛上水流丰富,潭底定是连通地下暗河,所以鱼可以顺着暗河水道来去自如,但他是人,即便水性再好,陷入情况不明的暗河很快就会气尽溺毙,他没有选择,必须回到潭底的入口!
田知甚立下决定,就在这时,狭窄的无法转身的水道突然一折,笔直向下漏去!
田知甚只觉得自己也是老天爷网中的鱼,不知被倾入哪家的鱼篓,一片漆黑中摔入更深的水域,接着被猛烈的水流冲过十来个弯,若非一身武功几乎要头破血流,最后狠狠的摔进了一个浅洼,而那条始作俑者早已不知在哪一段就被冲散了。
这里虽有空气,却依然暗无天日,田知甚听了一会儿,猜想这里应该是暗河深处的某个浅滩,他试着摸了摸身后的岩壁,湿漉漉的岩壁上全是大大小小的孔洞,勉强将手伸进其中较大的孔洞,发觉另一边竟是空的,不知对面有些什么。
田知甚一边瞎子摸象一边思考,这条暗河在水潭之下,水潭在山谷之中,黄龙岛位于东海,再深入下去将会通往何处?总不能是龙宫吧……
他自嘲的冷笑一声,心里怒骂星罗宫耗子投胎害人不浅,不但四处打洞,连老窝藏着也千百个洞眼子。火折子都在岸上,这里又没有其他照明之物,光凭摸怎能脱困?即便什么也不顾的大喊大叫,岸上的卢雁和卢泰恐怕也听不见。
突然,他耳朵一动,听到了几乎不可能出现的声音,尽管距离有些远,但隐约像是有人说话。
田知甚忍不住脱口而出,“谁在说话?”
自己的回声很快湮灭在一片水声之中,四周空寂黑暗,这种滋味实在不好受,即便是田知甚也觉得心底有些发毛,他不愿坐以待毙,立即拔出螳螂的刀,对着最大一个孔洞用力挖去!
这里的岩石出奇的脆,几轮挖削下来,原本人头大小的洞,扩成脸盆大小,田知甚再用力挖了几刀,终于觉得合适,收起刀扔了块碎石,听过落地声后,立即钻了出去。
田知甚落地时身法轻捷,几近无声,可他立即觉得不对,因为左边有微弱的风刀掩了过来,更要命的是,右、前、后也有微风以不同的角度挥来!像是黑暗中凭空生出铁打的网笼,要将他一举成擒!
他双膝一跪向后仰倒,左右的兵刃立即落空,紧接着一个鲤鱼打挺弹起身来,前扫胫,后蹬腿,只听前后两声闷哼,有人踉跄而退,田知甚堪堪脱身占据上风,忽闻“噼”的一声快逾闪电的锐响,脖子已被什么尖利带刺的兵刃扫中,痛楚让他身形一滞,就是这瞬间的缓慢,两柄剑已架上后颈,两人似不受黑暗影响,精准的出足踢向田知甚膝弯,“跪下!”
田知甚一足锁住来人一脚,一膝跪压一人足面,黑暗中顿时响起两声吃痛的吸气,但他自己也被剑锋压的几乎抬不起头来。伤口又麻又痒,田知甚仍不忘一哂,“奇也!星罗宫的耗子不但会打洞、会暗箭伤人,还说起人话来!”
只听有人咦了一声,一点幽青的荧光如蛇眼般浮近,两分没好气、五分没奈何、还带着三分固有的笑意开口——
“从来不知耗子会说人话,今日一听,果然好生稀罕哪?”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
可有可无的闲话:
四叠瀑布:《千里江山图》中有一处奇景,就是在现实中从未出现的四叠瀑布,有学者猜测,王希孟是参考了江西庐山的三叠瀑布,也有人认为王希孟是凭想象绘制的,不管怎么说,四叠瀑布也算《千里江山图》的一个地标吧,所以将它写进故事,融为黄龙岛上的瀑布,当年蔡京也许就是通过这个四叠瀑布,最后确认了宝藏点呢!(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相关剧情http://elfartworld.com/works/73951/
八卦嘛……从来都不嫌多的。
=======================================
八月十七
十五的月亮十六圆,舒舒服服过完中秋节,店里又忙碌了起来。
今日的行程阿羡可是打算好了,一早先到城门边陆大嫂的茶棚来碗热腾腾的甜豆花,送完货之后顺道可以往新街巷的花月楼用午饭,招牌甜点八宝酥酪自然是要吃的,如今天也凉了,再过阵子胡厨子该做蜜浮酥花了吧……
一边想着一边到了茶棚,刚踏进去,手脚麻利的老板娘就招呼 “羡娘子,今日进城送货啊?”“是啊,老板娘早,来一碗……”
“甜的是吧!蕊儿!快盛甜豆花来!”果然是熟客了,不用多说就知道阿羡的喜好,才眨眼的功夫,一个大眼睛小姑娘就稳当当的把一碗雪白豆腐花端了上来,端盘的正是老板娘年方七岁的小女儿陆蕊。
“蕊儿最近越发能干了,老板娘好福气啊。”阿羡赞道,却见小丫头闷声不吭又去了另一桌收拾碗碟。
老板娘有点不好意思的赔笑”羡娘子别见怪,蕊儿最近在和我赌气呢。”
阿羡吹了吹热气,勺了一口豆腐花,嗯……真是香甜嫩滑……
“这是怎么了?蕊儿一向很懂事的。”
“可不是吗,都怪上个月我带蕊儿在城门边放风筝,谁知半空中线突然断了,风筝卡在了城墙顶上……”
阿羡边吃边听故事“莫非是丢了风筝才赌气的?”
老板娘有些神秘的靠近了一点“要只是丢个风筝也罢了,偏偏那日蕊儿正哭的厉害时,来了一位郎君说要帮我们把风筝从城墙上拿下来,我正想着这怎么可能?那郎君突然嗖的飞上了城墙又嗖的跳了下来了,着实吓我一跳!等回过神来,人却不见了,也没能问个姓名道个谢……”老板娘又是比划又指着城墙“有那么高!”
阿羡顺着方向看了看不远处的城墙,平整坚固的高墙似乎并无可供攀爬的缝隙“哎呀呀,大概是江湖人士吧……说不定是哪位江湖大侠呢,蕊儿运气真好。”
老板娘笑了起来“羡娘子这么说,那肯定是大侠了,只是蕊儿从那天起就嚷着要学那窜上窜下的功夫,我说她做梦呢,她就赌气。娘子瞧瞧,好好的姑娘家想做什么大侠……”
“是女侠!”那边传来小姑娘气嘟嘟的童音。
“你看这……”老板娘好生无奈,阿羡莞尔,放下铜钱“老板娘不必太担心,小孩儿嘛……过阵子就忘记啦,告辞了。”
“娘子慢走啊,下回再来!”
“好的呀。”阿羡笑眯眯的往城门走去,这临安城真是日日都有新鲜事呢。
===========================================================
1.不知道宋朝有没有豆腐花…既然都有豆腐了那豆腐花也…?反正就是想吃嘛!但江南是叫豆腐花还是豆腐脑……吃甜的还是咸的?感觉写出了什么大BUG。
2.酥酪就是蒸牛奶,蜜浮酥花是借用了《武林旧事》里蜜浮酥捺花,古人取的名字念着绕口……冷天以酥油冷凝制成茉莉花状,浮于蜜中。应该挺好吃的!古代版奶盖蜜茶(大误)
3.为什么萝莉要做女侠?因为女侠和大侠更配呀XDDD
4.给某位唐/严/倪的少爷添了笔飞来桃花运,会被花椒门追杀吗大侠饶命……
本来是要写“吃我白金闪卡啦!”的中学生桌游paro,结果跑偏了。
这一篇就当做恭喜Lily春晚和大临安之恋(x)发行的贺礼好了。(谁会要这种东西了啦x)
大临安之恋记得要出收集套卡哦><
终于写明松书院相关了,全员酱油x!所以就不一一关联了。
(也写到了当初看到设定就很喜欢的不笑藏先生,然而现在找不到他的角色卡了不知道还在不在企划里……qwq)
感谢沈老板!
【大量捏他魔改注意】
====
一羽白鸽在屋檐下盘旋一圈,扑棱着翅膀停在窗台上咕咕着偏头朝里张望。正坐在厨房矮凳上清洗碗碟的布衣夫人站起来顺便在围裙上抹了抹手上的皂沫,解下了鸽子带着的竹筒。
“孩子他爹,明松书院寄信来啦!”
-
晚餐时父亲给自己斟上小酒,母亲则多做了几碟小菜。并不以术数见长的你也随着父亲的脚步进了明松书院的确是件令人兴奋的事儿。“或许是在占卜方面比较有天赋吧?她时不时会看看周易。”“说不定像我,喜欢祖国大好河山呢。”父亲作为一名曾带工维护运河的水文专长者,眼角的皱纹都笑深了几分,乐呵呵地咂摸一口酒,感叹一下真不愧是吴水窖的杰作。
-
我喜欢的是星象啊爹,你心里边想着边多扒了几口饭。
真想找个人看星星看月亮从天文历法谈到奇门遁甲。
-
“不过得加油,跟你爹我一样,要进天班。”父亲轻咳了一声做出深邃的样子,“班级可是按照算策成绩来的,入学就要进行测试,你要做好准备啊。”
母亲假装生气地道:“你也不是在黄班待过么,是谁总说术数不是一切来着?”
天班……这个名字便在父母打情骂俏之间印入了你的脑海。
-
到了要去上学的日子,该带的东西早已置办好了。学校在城郊的明松镇,信件中说独自前往的学生可到城门外集合乘牛车同去。你背上行囊,在家门口别过了父母便出了城门,果然看到不少和你一样的少年少女在两架牛车周围聊着天。
“请问……你也是去明松书院?”你向最近处的女孩子询问道。
“没错,我们同路。我叫黎里,很高兴认识你。”扎蓝色发带的姑娘露出俏皮的微笑点了点头,随后伸手指向一架牛车,“不介意的话,我们可以坐在一起哟~”
-
缓缓行驶的牛车上你跟黎里坐在了一起,刚开始时不时聊些有的没的。听黎里说自己是从外地一个人来明松念书的;又听她讲了不少自己四处游玩的趣事;再跟她不知道怎么引到了诗词的话题上,从“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背到“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再到“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就这样缠斗了几个回合你一句我一句,竟都离不开李青莲的诗。
-
“哇哦!你也喜欢李白吗?”
“…嗯。”
你当然能想到其他诗人,但就是被眼前这个黎里带进坑里去了。
-
找到了共同兴趣的你们又聊了好久,突然肚子有些明显地咕了一声。你当然不好意思承认自己饿了,黎里却是先从随身布包里掏出几个小方块递给你。
“喏,映柳轩的桂花糕。”
你把这个用纸包裹起来的小块儿仔细端详一番,上面画着小巧玲珑的桂花,还写着映柳轩的字样。这样精致的点心自己之前确实没有吃过。
“可好吃了,快尝尝!”
-
打开包装的时候一张卡片掉了出来。“这是……?”
“你还不知道吧?这是侠士卡。每块桂花糕里都会附赠一张侠士卡,上面写着他们的名字给人收集的。”黎里朝你凑了过来,“我收集了有三十多张了,银鱼卫都快要集齐了!”
你低头看了看手中的卡片,画像上是一个英俊的青年,眼神中流露出几分傲气的神色,身披黑袍头戴云纹高帽,一看便知是位官爷,旁边写有两字:“朱……翊?”
“啊!你抽到了朱翊吗!我有三张了!他是银鱼卫之一呢……可帅了,有二分之一白!”黎里的喜悦之情难以言表,你在她旁边都感觉要被带动着跳起来,却不好意思问朱翊是谁,只好小声道:“什么叫‘二分之一白’呀?”
“就是有半——个李白那么帅呢!”黎里一边比划着,一边无视你可能并看不懂她在比划什么而沉浸在粉色桃心的海洋里不能自拔。
原来黎里不光是喜欢李白,还是个超级迷妹呀!你清了清嗓子,开始想办法让黎里回魂。
“黎里?”
“你也吃一个桂花糕吧?”
“这张卡我可以留下吗?”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诶!你刚才叫我?”
-
牛车停在了明松书院里,一众新生下了牛车,先回宿舍收拾,之后便在大厅举行开学仪式。
校长是位精干的长者,须发皆白而精神矍铄。讲了些欢迎新生的话,又介绍了一下学校的课程,盯着校长有些累,你不禁将目光投向校长身后的先生们。
左手边是一位白发的男先生,年纪似乎并不大,定神一看衣衽却是反的。身旁放着一柄禅杖,一副闭目养神的模样,不过听说厉害的人能做到不需要看就了解周围事情的,看来这定是位特别的先生。其次是一位黑色短发的先生,一身黑边的白衣搭配平淡不惊的表情好似给你一种名门大宗的即视感,不时扫视一下场内学生。他身边是在场唯一的一位女先生,一色淡蓝衣裳褙子滚着深蓝镶边,头发两侧各有一簇花饰,面带微笑地望着大家。第四位是披绿衣的男先生,两鬓长长垂下,文人的气息在一举一动中都有流露着。
-
“下面公布根据算策成绩将各位新生分班的结果。”
-
听到分班的消息,你看见黎里一下子绷紧了身体。“你说会被分到哪个班呢……真希望是天班啊。”
“呃,说起来,四个班有什么区别吗?”
“好像没什么区别,不过因为术数的成绩不同,在其他科目上也会有些小区别吧?”
“我觉得自己可能也就是黄班的料……”黎里突然有点泄气似的,“上次去映柳轩买吃的都算错钱了QAQ”
“没关系的啦!”心想着自己也可能被分到黄班的你伸手拍了拍黎里的肩膀,“术数又不是一切嘛!”
老爹在家里突然平白无故地打了个喷嚏。
-
“别是黄班……别是黄班……”当你的名字被叫到的时候,你在心里一直默默念着这句话。
“——玄班! ”
在那一刻,世界仿佛安静了下来,这简直是难以置信的事情,就像以为勉强长到160的人突然听说自己实际身高165一样。
然后下一刻黎里拉住了你的手腕,两个少女一起为不是黄而松了一口气。
我们不要黄,要白!
嗯,要白。
-
在这之后江湖人称“水里针”的青年穆长水作为学生代表欢迎了新生并强调了河洛堪舆课程的重要性,接着由优秀毕业生代表发言,教师席旁边一个衣着朴素的青年站了起来微微一礼:“映柳轩沈庭芳幸会各位算友。”声音温软,文雅而清晰。
“你看你看,那位就是映柳轩的少东家呢!”黎里拽了拽的你的袖子,轻声说道。“买桂花糕的时候见过好几次的,却不知曾是这所书院的学生啊。”
那个美味的桂花糕就是他做的吗……真是个好人啊。你这样想着,丝毫没觉得自己逻辑不对。
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这样以后去买桂花糕就可以说是东家算友了。
不知道有没有优惠呢?
……
……
白洞,白色的明天在等着你们!
寄信回家的话可以使用谒者馆提供的信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