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月二】论坛开放http://orzpen.com/moon/forum.php
========================
—【明月千山】—
南宋年间,围绕着江湖百家展开的开放型日常养老企,目前一期剧情进行中。
世界观基调可参考金古梁温大师作品,真实系无玄幻。
目前企划主线已更新完毕,进入自由投稿时间。
------
企划印象BGM:
http://y.baidu.com/song/173529?pst=player&fr;=altg_new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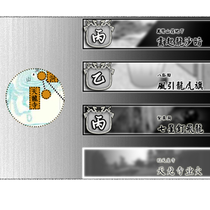
上接: http://elfartworld.com/works/8443216/
文中只一日,世上已一年,不管怎样先来一铲子!!
====================================
前请回放:阿羡与田知甚暂时和解,两人分别在即,不料阿羡却在池州城内遭遇袭击……
====================================
这日一早,阿羡就和田知甚渡江去接呼雷,才见着面,呼雷已抖擞腾越,一头拱向阿羡,鼻中嗤嗤喘气,热烈的鼻息几乎濡湿阿羡的衣裳,阿羡环抱马颈,手指慢慢理顺它的鬃毛,呼雷愈发瘦棱棱的,原先的鞍辔也不翼而飞,但她仍觉满心的庆幸欢喜。
反观茶棚掌柜惴惴不安,生怕田知甚卷土重来是为报复,小心的解释了马是他从别人手里买来的,其余一概不知,又殷勤的唤人雇船相送,恨不得将麻烦送出十里地。
船过江心时,阿羡笑问,“其实以田公子的本事,何需听掌柜的使唤?”
田知甚对此不以为意,“他不会武功。”
阿羡一时语塞,田知甚不欲以武功逼掌柜交出呼雷,自是他心地光明,自视甚高,不在乎被人占些便宜,不然还会有什么理由?倒是自己多此一问。
田知甚却提起另一件事,“呼雷没了鞍辔多有不便,不如等下船就进城添买,不过,恐怕比不上你从前那副。”
阿羡好奇的看着他,“田公子怎会记得呼雷原来的鞍?那是泷泷置办的,她素来喜爱华美之物。”
田知甚顿了一顿,移目于潇潇江水,阳光映照之下,江上波光粼粼,美如画卷。“那天钱塘江边,你们阵仗那么大,想不看见也难。”
撑船的舟子适时插话,这两天恰逢大墟,十里八乡的行商都会入城,正是最热闹的好时候。
糟了。
糟糕的不是眼前的死巷,而且身后的阵阵铃声连绵清脆,越来越近了。
阿羡回身站定,望向铃声的源头,只见来人肩挂褡裢,手撑铃杖,杖头虎铃摇动,看起来像个走街串巷的游方郎中。
“巷子走不通,先生还是回头的好。”
那郎中却不领情,只顾往里走,“外头人挤人有什么好?”
阿羡听他声音低沉,明明尚有距离,夹在铃声中依旧字字分明,不由警觉心起,抬指轻轻按在腰间藏着的韧风上,她本不用剑,何况韧风是师父所赐,她不想有什么闪失,手指在摩挲了两下又放开,大大方方的让开路。
“那么先生请吧。”
“小娘子不走,鄙人怎好走?小娘子不妨先请。”
郎中径直走来,恰好踏在阿羡让出的空隙前,巧妙的罩断三面退路,阿羡这才看清他的样子,只见他年不过四旬,颔下留着几缕稀疏的山羊须,身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面貌也说不上任何特点,仿佛随处可见,又随时会被忘记。裹头的发巾虽已旧的卷起毛边,却仍比衣服要好,因为左右两边的袖子居然是用不同的衣服缝补起来的,满身的落拓萧索,乍看貌似斯文,眼光浮动不止,言语听似客套,举动却完全相反。
阿羡微笑,“我忽然不想往前走,先生能让我回头吗?”
郎中双目上上下下打量着她,面上几乎没有表情,嘴里却嘻嘻一笑。
“小娘子要是急着归家,鄙人正好顺道送娘子回去,少说还能讨杯酒水。”
阿羡叹口气,退了一步,背后就是土墙,小巷过于狭窄,她又不能跃墙而去,实在没有逃跑的空隙。
“只怕我与先生不大顺道。”
郎中见她退让,似乎乐在其中,更加得寸进尺。
“怎能不顺?鄙人知情识趣,小娘子何必见外,你想怎么谢,我都生受了如何?”
巷子里的天无比狭长,高墙将阳光剖作阴阳两线,若此时有人自巷口望进来,便能看见明暗之间,两道淡影骤然交错——
郎中翻腕扣阿羡手臂,阿羡振臂解扣,两人在极窄的巷道里转瞬拆了三招,但对方轻功高明,如影随形,再次以小擒拿扣握阿羡左手,阿羡被他拉得一个趔趄,左手两指如蝎尾弹出,顺势飞削其双眼,同时右手猝起,曲指如角,急撞他颈上工尺穴!
她内力虽失,招式尤在,出招的时机拿捏极准,逼得郎中不得不放手躲闪,挥杖迎击,阿羡合掌夹杖,正要全力下压,郎中忽而倒踩步法,每一步恰如春云浮空,流水行地,腾挪转闪间不落痕迹,阿羡猝不及防被带出三步,架势已被拉歪,自从右足受伤后,她已无法像从前一样施展轻功,无从跟上对方的步法,郎中夺得先机,转步之间巧妙的绕至阿羡背后,以杖当剑,压在她颈侧,哈哈一笑。
“这下你还有什么招数?”
“也实在……没什么办法了。”阿羡满是无奈的答话时,右足足根自后蹴向郎中足踝,她身材纤小骨骼柔软,这等毫无征兆的暗袭多不胜数,郎中虽没被她踢中,但也颇觉头疼,就在其分神的一瞬,忽觉脸侧风急,他抬肘急挡,嘭的一声,惊险的架住一记过顶踢,阿羡刹那间拍开木杖,手握银簪,拧腰发力、如飞燕穿云,刺向郎中颈侧——
郎中大吃一惊,她竟还能反击!
噗的一声,银簪刺透一物,却绝非人体,原来郎中应变奇快,甩出褡裢时抽身猛退,令这一击无功。
阿羡眼见功亏一篑,再无可趁之机,忽然掉转簪尖,朝自己喉头刺去,这一连串动作只在交睫之间,郎中再度大骇,难道她要自尽!想也不想丢开木杖,劈手捉住阿羡的手,用力往回拉,同时开口——
哪知阿羡这一刺只是虚招,她一直紧握簪头的尾指微微一松,一蓬飞针嗖的打出。
这才是最后一招,离最开始的一招仅仅过了数十息而已。
“阿羡!”
松开手指的那刻,熟悉的声音犹如一道惊雷落在耳边,阿羡大惊失色,只来得及全力向前扑出,那一扑直接将人撞倒,自己也摔得生疼,她倒地后用手一撑竟没能起身,只能睁大眼睛望着对方,霎时间一切感知自身体中褪去,刻意被遗忘的过往决涌而出——
男人的五指拍在老仆脸上,断线的纸鸢栽进江中,如血的夕阳渗入江面,火舌烧穿了屋顶,舔痛了脸颊,烫得视线都模糊了……
“是我、我啊……”
背脊直接着地的郎中哎哟了几声,捂住后脑勺勉强爬起来,瞥见阿羡神情如同见鬼,又急忙挪过来,紧张的问道,“没事吧?摔着哪了?”
阿羡这才回过神来,怒气随着剧烈的心跳声冲出胸膛,“郑曦!你干什么?”
她满眼愠色的伸手自郑曦鬓边摘出一枚细针,脸色比自己中了飞针还要难看。
她习惯随身携带各种暗器,朝天阙也好,六棱镖也好,足底刃也好,明刀暗器与她而言并无分别。这银簪也是程放所授的精细机簧,能在一尺发出三枚细针伤人,只因杀伤距离太短,以前从未用过,没想到会用在郑曦身上,她只是不想落在任何人手里,却差点做了无可挽回的错事。
郑曦从未见过阿羡如此气恼,又瞧见那枚细针,一下子由惊转惧,后颈阵阵发凉,若非阿羡及时反应过来,自己少说也要被射瞎一目,玩笑开的太过了!
她不禁心虚起来,拈起阿羡的袖角扯扯。
“是我胡闹过头……真恼了?要不你揪我胡子罚我吧?粘的可牢,撕着可疼了。”
见阿羡不答,她挨到她身边,
“揪揪看嘛,要不我撕给你看……”
阿羡本来不愿理会,却禁不住耳边一迭声夸张的嚷痛,余光见郑曦当真毫不手软,左一绺胡子右一缕眉毛的撕了个干净,揭去乱七八糟的易容之物,变回熟悉模样,笑意慢慢涌到嘴边,忽而变作后怕,眼中不觉一热。
“除夕前夜的事……怎么不说?我差点又害了你。”
郑曦没料到阿羡想起这回事,笑道,“早忘了的事,还提来干什么?”
阿羡闻言牵了牵嘴角,眼中仍是雾濛濛的。“那时我一心只想扑灭火光……对不起。”
郑曦忽然明白,那夜阿羡出手攻击自己,原是为着灯笼的火光,她拼命想要扑灭的,根本不是那盏小小的灯笼,而是早已无可挽回的定局。
“你看——我现在不是好端端的?一只鼻子两只眼睛,胳膊腿不多也不少,放心,我又不是泥捏的,才没那么脆弱。”
郑曦笑眯眯的拍拍阿羡的肩膀,“倒是你,你怎么会在池州?看见时吓我一跳。”
“你呀……也不知谁吓谁一跳。”
阿羡掠了掠脸颊边散乱的发丝,没奈何的笑了笑,当日娇生惯养锦衣轻裘的郑曦,会扮成落拓寒微的江湖郎中,确实是件难以想象的事,她忍不住仔细端详,忽然发觉郑曦左眉尾多了道细长的血口子,原来飞针虽没有射中眼睛,却在擦过时划出一线伤口,不由大为皱眉,“还是受伤了。”
郑曦下意识伸手摸索,她现在手臂疼背也疼,全身都在抗议自己方才的恶作剧,其余的反倒感觉不大出来。“在哪呢?”
阿羡拍开郑曦的手,自怀里取出丝帕。
“别乱动,都流血了,幸好针上没淬毒,先擦一擦再敷药罢。”
郑曦好笑的看着她小心翼翼的神色,也不知到底谁才是大夫?她索性一动不动,懒洋洋的伸着脖子等,不经意瞥见阿羡的手指,脸色骤然一变,“别碰我!”
阿羡正要将丝帕按在伤口之上,陡然被郑曦一袖挥开,不禁满面诧异,顺着她的目光,看向自己的手。
刚才猝然扑倒,手上添了不少擦伤,虽然都是不起眼的细微伤口,却也沾染了不少尘土,是因为这个吗?想到这点,她滞在半空的手慢慢收了回去。
郑曦本想扯出一个惯用的笑脸含混过去,不料阿羡收回丝帕,仔细翻出内里最柔软干净的一角,隔着袖子推到她手里,“这就干净啦。”
郑曦闻言心神一震,阿羡见她动也不动,忍不住柔声催促。
“粘了灰留疤可怎么好,快擦擦呀。”
郑曦拿起丝帕,心里叹气,这人眼里压根看不见自己手上的伤口,倒是生怕别人脸上留下一丝疤痕,迟疑了一瞬,终不忍心相瞒。
“一点灰尘算得了什么?是我的血有毒,任是谁伤口沾上一点,轻则浑身麻痹,重则窒息而亡,你手上的口子虽小,我可不敢让你沾上。”
阿羡吃了一惊,立即想到厉害之处,“你中毒了?”
“不要紧的,我自幼就这样,师父还特意为我调配过血毒的解药,如今好着呐。”
郑曦安慰阿羡时眼神温煦,多年来掩埋在心底的东西,吐露时却是那么平淡,像三两蝴蝶,款款飞散。
听说有柯云调配解药,阿羡才稍稍放心,想了想才道,“难怪……流霜说的毒,原来是这么回事。”
郑曦正拿着丝帕擦脸,闻言竖起耳朵,“那丫头和你说什么了?成日间八哥鸟似的叽叽喳喳。”
“大家都记挂你。况且我能及时收到你的信和药,还多亏了你爹。”
郑曦眼中有光闪了闪,“我爹?”
阿羡的眼中上多了一丝狡黠,“急病暴毙之说我本就不信,又见飞雪流霜不在灵前举哀,偏偏郑叔父还烹茶相待,话里有话的谈了半日,我哪能辜负他的苦心?所以等到夜里,我和田公子一块进灵堂开棺,又找到飞雪流霜,才知道怎么回事。”
郑曦兴致勃勃的听着这两人在自己家胡闹的经过,又想到这一切居然是她那个向来被族中盛赞温文稳重的爹纵容的,故作惋惜的哎呀了一声。
“可惜我不在,竟白白错过好戏。”
两人相视一笑,霎时彼此为镜,照得澄澈通透,相见一如旧,故心终不移。
说笑一番后,阿羡捡回铃杖,见郑曦仍在整衣掸尘,忍不住将铃杖塞给她,帮忙拈去发巾上沾的草屑,就在这时,一股银光自背后缠住郑曦手臂,将人狠狠拽了出去!
来人悄无声息,一手已按上郑曦背后重穴,森然开口,“动手断手,动脚断脚,选吧!”
“田公子别伤她!”阿羡这时才来得及惊呼一声,急奔了过来。
田公子?
郑曦没好气的扭头一看,来人原本横眉冷目,在看清她的脸时顿时呆住,气焰从三十丈消作三丈,收了银丝,干巴巴的打招呼,“郑大夫……你好。”
郑曦微露浅笑,气度雍容的拂了拂衣袖,仿佛刚才被猛拽开七八步,用铃杖撑抵才没摔个狗啃泥的人不是自己。
“原来田公子也在啊。”
田知甚郁闷的想,什么叫也在?他向来眼尖,不但瞧见郑曦脸上有伤,还看出阿羡眼角微红,像是刚刚哭过,这情形怪异极了,但他自知理亏,只好老实道歉。
“刚才是我眼拙,以至于生出误会,还请郑大夫海涵。”
阿羡确认过郑曦未添新伤,笑着望向田知甚,“你怎么找来了?呼雷呢?”
田知甚将久等不见她回来,把呼雷寄在马行再来寻她的过程简略说过,又轻描淡写的的补充,“买马鞭何须那么久?所以我来看看。”
“早知还是不抄近道为好。”阿羡笑盈盈的转向郑曦,“都怪我耽搁太久,我想田公子不是有意的。再来,还有个顶要紧的人,阿曦定要去见一见,猜猜会是谁?”
“什么要紧的人?”郑曦听着阿羡用心良苦的引田知甚说清缘故,气也消了大半,瞄了一眼田知甚,心道这也是个憨包!伸手拉过阿羡,就往巷口走去。
“不是要见见吗?人在哪里?”
“就在城外,可你还没猜呀……”
阿羡被拉着走了几步,回头一笑,“田公子也一道回去吧,还得去接呼雷呢。”
田知甚大为诧异,固然因为郑曦毫不避嫌的拉着阿羡,亲昵之态远胜寻常,更因为他第一次见到阿羡展颜欢笑,那是一种不加掩饰,纯粹的愉悦心情。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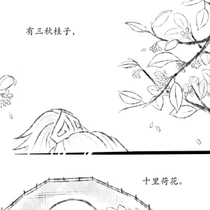



雷慈有一阵子没感觉到那灵巧的手指在自己脸上动作,便颤着睫毛悄悄睁开眼,偏偏那少女刚好就在这时转过身来。
“…我…”雷慈一时间竟觉得心下一乱,便是慌忙开口,却发现自己好像也不是真的想说话,这个「我」字后面该接什么他根本不知道,就也再说不出别的话来。明明也不是什么该心虚的事,他却像做错了事似的再次紧闭起眼。他这下闭眼特别用力,看起来就闭得格外紧,连眉头都微微皱上了。
少女瞧见他这副样子,不禁笑道:“我让你闭着眼睛只是怕你眨眼乱动,又不是怕你偷看,你干嘛跟做贼似的呀。”说罢,她笑着将一张蝉翼般的薄片覆到雷慈耳侧,寻着巧妙的角度贴上,雷慈的脸部轮廓便立刻产生了些许变化。少女此时说话的声音无比柔软,手上的动作和她望着雷慈的眼神也是同一般。她轻轻拍了下刚贴上的薄片,又说道:“你要是真的想看,就看吧,其实也碍不着我什么的。”
雷慈的睫毛又颤了颤,眼睛稍稍眯开条缝,他就这样看了那少女一会儿,便又再闭上了。只是这次他似是闭得十分轻松,两道浓黑的剑眉也就都跟着舒开了。
然后他的嘴角便出现了一个和少女眼神同样柔软的笑。
眼前这位娇美的少女是他所陌生的,无论他看得多久,看得多细,好像都没办法从她脸上找到一点自己熟悉的地方。要是他们两个在外头街上擦肩而过——不,哪怕一百次擦肩而过,他也不会察觉到一丁点不对劲的地方。
——至少半个时辰以前是这样的。
“你好呀。”身着墨绿色斗篷的少女冲着雷慈微笑道。
雷慈并不应她,只沉着脸将眼前这少女粗略打量了一番——她看起来不过十六七岁,圆润饱满的脸颊仿佛带着绒的蜜桃儿般充满青春活力。她娇小的下巴向里收着,头也微微垂着,两道弯弯细眉下却是有一双眼角稍稍向上飞起的漂亮眸子,似羞非羞地瞧着雷慈。
雷慈面上不动声色,扶着门的右手却已悄然垂下,向身体后收拢过去。
少女见他久久不应自己的话,眉头便渐渐皱了起来。她急急地吸了口气,像是有什么话想脱口而出,却又硬是咬牙给忍住了——她的牙也确是咬着的,皓齿轻咬着红唇的一角,看上去真是格外的不高兴。就那么一会儿功夫,她那双原本带着笑意的眸子也渐渐寒了下去。可要是说她那双眸子笑着的时候能勾着十人中的六七人的话,寒下去的时候却能有八九人了。少女眼中的寒意不但不会让人感到危险、不安,反而令人心升一股怜惜。只可惜即使十人中真有九人会为她的眼神所动,雷慈也是剩下来最不解风情的那一个。
“你怎么不理我呀?难道你…呀!”少女朱唇轻启,终于再次开口,她的人也作势向前倾去,像是想同雷慈更亲近些说话,可那温软的话语却是忽然被一声惊呼打断。她身形刚有动作,雷慈便猛地出手朝她颈侧袭去。那少女看着柔弱,身法却意外地灵敏,只一个侧身竟避开了去。雷慈一击未中,也并不意外——一个从未见过的陌生人,无人引荐,在这个时间出现在临水居…无论怎么想这少女都是来找麻烦的。而她既然敢直接找上自己,想必也不会是什么简单的角色,武功也不会太弱。雷慈对自己的武功还算是有几分把握,只是跟这些拳脚功夫相比,这女子身上还会不会藏有什么暗器毒烟之类的才是真的该小心的地方。雷慈见她避开自己一势,原本将要收回的手也忽然变了动作,朝着少女的肩头袭去。他出招的动作看起来即迅疾猛烈,变化却又快得让人躲闪不及。少女心里似也笃定他不会对自己下太重的手——一个来路不明又没有表现出杀意的人,留着活口总是比杀了要有用的,眼前的霹雳堂长子显然也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于是乎她也做好了硬吃下雷慈这一招的准备,可实际接触到时却发现他掌下只是轻轻一抚,甚至都没有什么感觉,可下一瞬少女便感到自己膝上一记针刺般的酸麻,双腿仿佛不受控制一般软了下去。她当即咬牙提气,身上动作却还是因此慢了半息。雷慈又怎会放过这个机会,旋即拧过她两条手臂扭到背后单手抓到一起。
他双眼紧紧盯着这少女,面上仍是毫无表情,少女却知道他仍在堤防着自己。可她现在是真的无法动弹,雷慈这看似满是空门的姿态竟让她找不到一处能下手反击或脱身的地方。她皱起眉狠狠瞪着雷慈,眼里羞愤和委屈好像要化出水来。雷慈自是不为这眼神所动,但一定要说的话他也并不是毫无感觉——这个少女是谁?她为什么到这儿来?为什么来找自己?她只身前来,会不会只是想要牵制住自己,真正的目的是为了霹雳堂?诸如此类的数个念头极快地在雷慈脑海里盘旋了一圈,但都被他轻轻挥了去。这里是临安,霹雳堂的大宅,天子脚下的江湖名家不是那么好动的,也是因为如此霹雳堂的守卫一直不算森严,即使同为临安名家的万贤山庄不久之前才出了那样的事霹雳堂也没有因此加强任何安保措施,在外人看来这也许确实是一种狂妄到无法理喻的自信表现,但雷慈自己清楚,这也只不过是一种消极应对的态度罢了。
或许现在看上去很好,但霹雳堂其实从来都不缺麻烦。
他雷慈自己也不缺。
可他已经习惯这种看似被动的状态了,即使这少女此刻真是来找她麻烦的,他也会先看看这麻烦是不是他能对付得了——如果对付得了,那麻烦也就不是麻烦了。
而如果真的不巧,他对付不了,那接下来的事就更不用他去费心了。
无论是死人还是没有选择的人都是不需要费心任何事的。
这倒是跟霹雳堂眼下的状况一般无二。
他想着这些,脑袋里却总有另外几个跟霹雳堂,跟「长公子雷慈」无关的问题也在不合时宜的出现着。
唐珏去哪里了?他怎么还没有来?这些事跟他有没有关系?…他会不会有危险?
还是说这一切其实都是那个看似无害的慕容峯曌在搞鬼?
雷慈想着这些的时候并没有分心眼前的事。他牢牢限着那少女的行动,思索着是该问些什么还是等这少女自己开口,却见这少女忽然笑了。
也就是她笑起来的这一瞬开始,她的眼神完全变了。里面的羞愤、委屈…全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得意。
“捉人倒是很熟练呐。你明知道我不擅近身相搏,还总这般欺负我,到底是不是故意的?”
雷慈愣住了。他怔怔地看着眼前的「少女」——她此刻说话时不仅口气和先前的娇柔温婉毫无关系,连声音都完全变了个人。
一个他认识的人。
雷慈紧皱起眉头,将这一天发生的事重新在脑中又过了一遍,忽然恍然大悟。他瞧着眼前的少女,还来不及松开手,嘴角就先翘了起来。
“唐珏?”
之后就变成现在这样了。
雷慈一边换上唐珏给他带来的衣服,一边仍用充满着疑问和好奇的目光打量着眼前的人——一个姑娘,看起来还是年纪很小的姑娘。他看看身上换好的衣服,又看着唐珏从提来的箱子里不断拿出些不知道装什么的什么的瓶瓶罐罐,和一些他根本不认得的稀奇古怪的东西,心下自然了然这些应该都是用于易容的工具了。只是唐珏自己已经装扮成了这样一个娇俏的女子,又会让他易容成什么模样呢?雷慈在心里想了好一会儿,终于忍不住开口问道:“你打算把我变成什么样?”
唐珏手上动作一顿,转过脸冲着雷慈眨了眨眼嫣然道:“你想我把你变成什么样?”
雷慈被他问得一愣,从方才接过唐珏带来的衣服起,他便认为唐珏应该早就想好了两人的装扮,不然这衣服莫非只是随便取的吗?他看着眼前连身姿体态都几乎完全变成另一个人的唐珏,又在心里摇了摇头。他原本只是好奇唐珏接下来的打算——其实仔细想来就算好奇也用不着问出来,只要安静等着任他安排便早晚也会知道结果——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没能把这句话给忍住。他话说出口的时候,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期待得到什么样的回答,无论唐珏告诉他「什么样」,他也许也再没有能接的话了。
反倒是唐珏现在这句不知是不是玩笑的反问让他凭空生出些期待和兴致来。
雷慈眼睛一亮,竟端详着唐珏易容后的眉目微笑道:“配得上这位姑娘的样。”
他这句话刚说出口,就觉得仿佛失了正经。面前的人就算外表是个少女,里头却毫无疑问仍是那个在江湖上颇有些地位的唐门少主,不出意外的话自己还会在不久后成为他的大舅子,说这样的玩笑话好像有点过了头。而且即使抛开这一层关系,只是把现在的「唐珏」当成一个真的陌生少女,自己似乎也不该说这般轻佻的话。
唐珏却似乎对这话里的「不妥」没有一点感觉。雷慈只见他轻轻笑了笑——他之前就发现唐珏在这种易容的「状态」下会完全变成另一个人,变成一个他正在「扮演」着的「角色」,变得完全不像他所认识的「唐珏」。这应该是唐门中人的习惯和他们引以为傲的本领之一吧,在想将「自己」完完全全地隐藏起来的时候便真的能够做到并做得很好。雷慈对江湖上关于唐门的一些传言也是耳熟能详,但现在才真正领教到这门功夫的厉害之处。
只是唐珏听见这话时的轻笑却不像是这个「少女」的角色,倒像是他认识的「唐珏」这个人。
可他认识的唐珏,却又会不会只是一个角色呢?这样一个小念头在雷慈脑海里一闪而过,他还来不及细想,唐珏便转过身来不知拿着什么东西抚上他的脸。鼻息间忽然迎来一丝脂粉香气,雷慈本能地想要向后避开唐珏的动作,耳畔却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
唐珏轻声说道:“别动,把眼睛闭上。”
他几乎想也不想地便立刻应声阖上了眼帘。一刹那间他仿佛也看见唐珏眼里有一丝惊讶的神情一闪而过。
只是当那微凉轻颤的指尖触到他的脸庞时,他就把什么都给忘了。
后来他也不知道是过了多久,估算着怕是也有近一个时辰了。一直到他感觉到唐珏已经替自己梳好了头发,过程中雷慈都没有再睁开过眼。
他觉得自己应该是有些防着唐珏的、或者说是有那么些必要得防着的。可就算对方在如此近的距离对自己几乎是「肆意妄为」了,他都还是没有什么动作。
也许今天的自己本来就不太对劲吧。从答应慕容峯曌的「比试」时就不太对。还是说更早一些?从自己去见师父的时候就不太对?
唐珏的手指在他脸上不住游走,有的时候轻一些,有的时候重一些;在有的地方只是轻点即过,另一些地方则会停留久一些。雷慈静静地感受着他的动作,试图从这些动作里去猜测唐珏将会把自己易容成如何的面目,却无论如何也没法在脑海里组合出一个恰当的形象。
在自己脸上活动的这双手偶尔带着一点点轻微的颤抖,从稍长的指尖传递过来——连这种地方都武装到了啊,雷慈心下默默佩服。他想着唐珏的手,纤细却有力的十指,平时看起来总是十分白净整洁。…今天呢?他突然发现自己好像想不起来。从脸上的触感来看,他的指甲似乎比平时要长一些、尖锐一些,是在易容成女性的时候也做了相应的调整吗?是不是也和一些姑娘家一般染了朱红呢?唐珏轻颤着的指尖扫过他鬓角碎发时雷慈被痒得微微一抖,他忽然想到这双手应该是一双多么危险的手——一双可能摸过无数暗器毒药的手,一双沾过不知道多少人的血的手。
他是不是应该害怕一下?
面前的这个人无疑也是危险的,可他就是防备不了,就是怕不起来。
想到这里他的心口忽然紧了一下,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在心里毫无预兆地翻腾起来,连带着他的气息都几乎要变得紊乱——所幸他还控制得住。雷慈皱着眉头暗中调整了内息,又缓缓地、尽量不动声色地深深吸了口气。
他猜这些动作都是瞒不过唐珏的。不过应该也不会影响唐珏手头上正在做的事。
雷慈忽然觉得喉咙也变得有些紧,像是有话想说,可他却明明不知道有什么话需要说。
兴许是坐得久了,渴了吧。
他抿了抿唇,是有些干了。于是他探出舌尖想将唇润一润。只是微红的舌尖才一出口又触电般的缩了回去,雷慈猛地睁开眼,烛火的光又刺得他只能把视线给偏开。
摇晃的火光里他看到唐珏抬在半空的手和刚才被他无意间舔到的指尖。
“…我…”雷慈觉得有些尴尬,他仍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但又觉得自己必须说什么。
“嘘。”唐珏却忽然迎上来,抬手轻轻覆住他的眼,教他又重新把眼睛给闭起来,“快好了,你再忍忍。”
——是他的声音,唐珏自己的声音。虽然比平日里柔和了不少,却不是那个「少女」的声音。
“…嗯。”雷慈点点头,使自己尽量平静下来。他感到在烛火的映照下自己脸上的一些什么药物正在慢慢将皮肤收紧,带来干燥感的同时又有微微地灼热。
戌时过了。雷慈听到临水居外传来打更的声音。
他感到一些汗珠从自己额角发迹缓缓渗出落下。是因为烛火吗?还是因为易容的关系?
在这个二月的晚上,他第一次发现原来冬日也可以如此燥热。
======拖稿的分割线======
……虽然填了一些但时间线完全没追上!!!汤勺每次的剧情后面都接着催稿真是让人压力山大啊!!O-<-<…
不过其实这篇也只是为了赶520纪念一下…成功就好wwwwww(。)
粘乎乎的相处太难写了!!!虽然赶上了但字数超少的就随、随便吃吃…
耻到我几乎不好意思发!(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ry
惯例好像没什么好解释的…这一段剧情从这里开始,会完全都是雷慈视角,所以他不知道唐珏在相同时间在想什么,只是他自己一直在胡思乱想ry
而虽然内心有2W字的戏,这个迟钝的直男还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仍然感谢看到这里的各位!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尽情地留言…(毕竟辣么乱…
以上!


上接http://elfartworld.com/works/106186/,为第三夜后的次日
过渡篇
感谢小秦提供灵感!如有OOC都是我的锅!
失眠产物,各种吊书袋出没,如有不对请勿深究(抱头)
“采苓采苓,首阳之巅。人之为言,苟亦无信……”叶小姐正手持一卷诗经念着,听得脚步声抬头瞧见是自己的丫鬟锦衾拿着绣棚进来。
“大小姐,是时候该用晚膳了。”说罢收好绣棚,又道:“您的身子刚好,前些日夜里下的雨寒气重,到今天还没散完。成亲的日子又快到了,您可注意着身子啊。”
叶小姐放下手里的书,摇头道:“哪有这么娇贵了呢,倒是快些传饭进来吧。”丫鬟点点头,出去不一会,就和一个仆妇拿着饭菜进来一样一样放好。
叶小姐向着仆妇行了礼,这位仆妇姓林,同叶府管事爷为夫妇,所以叶小姐对她也格外尊重。
“不知嬷嬷今日可曾见到父亲……”叶小姐刚问出这话,林嬷嬷却面露愁色,叹了口气说道:“老爷今儿个一大早便出去寻少爷去了。少爷也是,这么大个人,没点要当家人的样子。天天不是睡这个什么月楼,就又是那个什么香阁。再过几日就是小姐的大喜日子,现在却完全不成样子。唉……”
叶小姐不言,只暗暗和锦衾使个眼色。锦衾便一面接了东西,送了林嬷嬷一道出去。送走了林嬷嬷锦衾才回来关了门。
叶小姐也不忙着吃饭,只拿个调羹搅着汤问道:“林嬷嬷送走了?可还念叨什么?”
“左不过都是那几句。少爷不好,对不起老爷和去了的夫人之类的。唉,我听得都……”
叶小姐也没接她的话,只吩咐她说:“我的笔墨纸砚没了,晚膳后替我去趟少爷的房间拿些来,再拿两本东坡选集过来,反正少爷不在,也用不着这些东西了。”
锦衾听得这话后脸色变了变,忙应了下来。
月上柳梢头,正是倚香格迎来送往的时候。
可今夜倚香阁的名角之一铁琵琶秦何限却被人包了去。
秦何限正思索着是哪家官爷公子,却瞧见进来个陌生公子。一身的绫罗绸缎,手中一把白玉象牙扇,可见非富即贵。
秦何限照例行了礼,从小丫头处接过自己的琵琶。就瞧见这位公子挥退了一旁伺候的人。只留秦何限一人。
“公子好,敢问公子名讳?”
“姓李,单名一个皓字,”
“哪个皓?”
“清歌传皓齿,皓齿发清歌之皓。”
调弄着琵琶的秦何限抬了抬眼,指尾轻轻一拨琵琶,朱唇轻启,一缕轻音流出。如此唱完一整曲,除去唱前那轻轻一拨的琵琶声,整曲无一丝竹管乐相伴。饶是如此,也余音袅袅,不绝如缕。
伴着余音消失,沉寂片刻,才响起称赞。
“好歌喉,不过……”李皓一收扇子:“这‘铁琵琶’的称号却有些实不至名不归。”
“公子这是从何说起?”
“清唱固然悦耳动听,可这琵琶却不能让姑娘逃了去。”
秦何限却一笑:“清歌传皓齿,不是公子要听清歌吗?”
李皓闻言,斟满一杯向秦何限一敬,道:“清歌一曲倒金壶, 欲向东风先醉倒。敬姑娘一杯,换姑娘一曲琵琶罢。 ”
“李公子眼生得很,怕是头一次来这倚香阁呢。”秦何限眼波流转,“可形状瞧着却像是熟客呢。”
“秦录事聪慧,如何敢瞒?怪道叶兄极力向我举荐,没有叶兄,还没有这耳福呢。”
“叶公子?可是叶蓁叶大公子?”秦何限轻笑,朱唇上扬,“叶公子可有些日子没来了呢。”
“叶兄近日忙于家中大事,李某识得叶兄日子不长就常听叶兄提起姑娘,可见姑娘被叶兄念着呢。”
“蒲柳之姿承蒙公子错爱,不过叶大公子相识的要都是李公子这般琢玉郎样的人,那来多少个听曲也是不打紧的。”
“秦录事过誉了,李某若是‘常羡人间琢玉郎’,秦录事也当是‘天应乞与点酥娘’。”
秦何限笑起来:“李公子真是会说话。罢了罢了,允了公子这一遭罢。”说罢弹起琵琶。
李皓又满上酒盅,伴着酒听秦何限弹起琵琶。曲毕,李皓直接递上一盏酒盅:“素蛾今夜,故故随人,似斗婵娟。 铁琵琶,实至名归。”
秦何限笑接酒盏一饮而尽。
二人遂对饮起来,酒过三巡,只瞧见秦何限两靥飞起一抹红。李皓眼神也有些迷离, “醉脸春融。斜照江天一抹红,正如此状。”
“李公子醉了呢,可要歇息片刻?”说着要扶他躺到春凳上。李皓却摆摆手,自个斜倚到上头,半阖着眼念叨:“这点酒量,醉不了醉不了。上次同叶兄在弄月楼比酒,这点,也就够暖身罢了。”
“说起叶兄,他近日可忙的酒都没得喝了,所忙秦录事可知?他同胞姐姐好容易寻得户好人家,要嫁人了。”
“同胞姐姐?”秦何限往香炉中添加了些醒神的香料时一回头。
“有何不妥吗?别看叶兄平日里那个样子。对这唯一的姐姐倒还上心,不过……”
“公子怎的不说了?”
“不过若那是对胞姐的态度……又有些不似……倒像是……像是……男子对女子那般……”
秦何限坐到他旁边的圆凳上,眨眨眼:“像男女之情么?”
“正是正是,秦录事果然聪慧!”
“哪里担得起聪慧呢,瞧得多了,自然就看得清了。”
“哦?瞧得多?秦录事也瞧见什么了么?”
“哪有瞧到什么呢。毕竟是叶公子的家事。”
“秦录事有这等好酒量,叶兄在你这可喝的不少吧?他的酒量我是知道的,定是喝醉了,嘴边又没了把门的。嗨,他在哪处都这副模样。醉了就念叨自个爹娘不好。”
秦何限眉毛一动,“可不是呢,非说自个不是亲生的。”
“叶兄连这都说过了?待再见他可要好好打趣他一番了。”
秦何限笑道:“看来叶公子真是坏事传千里啊,谁都晓得虽说叶夫人当年就是生了他才去的,可当年也是叶夫人娘家产业大,叶家当年全靠夫人娘家支撑才有的今天。叶老爷如今还健在,胞姐虽说体弱可也定了亲事,又分不得家财呢。”
李皓虽半眯着眼同秦何限说话,可方才却暗暗紧了紧拳头。“正是此理。李某同秦录事心有戚戚焉。”说罢,李皓睁眼坐起。
秦何限瞧李皓眼神没了先前的迷离醉态,倒和刚来时的透亮眼神相仿。笑道:“公子酒醒的倒快呢。”
李皓接道:“亏得秦录事的好香,酒醒了大半,现下也该回府了,今夜得秦录事一曲,这趟也不算白来。往日若得空,定常来捧场。”说罢,没等秦何限行礼便转身离去。
秦何限也没送他,只低低哼唱道:“……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李皓听得此句,脚步一滞,又一步不停地走出倚香阁。
================================
本篇章诗句由苏东坡赞助提供(殴
《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
《菩萨蛮·绣帘高卷倾城出》
《南乡子十七首》
《减字木兰花·赠小鬟琵琶》
《诉衷情》
《采桑子·润州多景楼与孙巨源相遇》
================================
Q:这里的李皓是白萍吗?
A:是
Q:为什么白萍又双叒叕去逛青楼?
A:找秦姬问到的事情有限,且从秦姬那里得知叶公子是小秦的常客,她还有别的的事情需要得知。
Q:她演那么多是为了什么?
A:以东坡诗词刷好感,然后才能引出她想要问的关于叶家和叶公子的事情,她在小秦处确定的事情一共有两件。
Q:叶公子是谁?
A:上篇里被白萍一刀断头的那位。 因为脑袋被白萍带走了,所以叶公子现在的状态是失联
Q:为什么用如此迂回的办法?
A:叶小姐婚期将近,不能打草惊蛇。
Q:为什么最后李皓出门会脚步一停?
A:听到唱词内心有感,什么感以后说。
========================================================
荔枝人的话:写这个过渡篇的根本目的是借PC和NPC之口向看的大家说明一些无法直接插入文中描述的事情和线索【删除】以及再能撩个妹子逛次青楼【/删除】希望能让大家看明白_(Xз」∠)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