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番外
·西芙,唐草已交往设定,猫又的角色我还没来得及开总之先写了(……)
·这么一看起码也该是二年生时期了写这么早真的好吗——!
虽然位置在百慕大,也许是中国人不少的缘故学校的中秋气氛很浓厚,杂货店摆满了各种奇怪口味的月饼。
而西芙头疼于眼前的圆润,透亮,绿色健康无污染的食材。
绿豆。
作为一个把弟弟健康拉扯大的好姐姐,西芙甜点技术是绝对过关的。泡芙,松饼,提拉米苏……但是这个技能点绝对不包括传说中的天朝特色美食。
月饼。
“neko,月饼要怎么做呢?”
“吾怎么会知道,不如说都说了多少次吾是从日本来的妖怪把日本和中国混为一谈啊!”
渐渐开始习惯莫名其妙多出来的名字,变成普通猫型的猫又难得窝在契约者房里就得接受对方缺乏常识的提问,气得原本顺滑的毛皮炸起,挥爪子抓了西芙一口子。
“在我看起来长得都差不多啊。”啊唐草除外就是了,“诶neko想打架了吗,不行我得等一会在陪你哦。”西芙不甚在意地继续她前途渺茫的研究大业,而黑猫僵直了几秒觉得自己完全没有和这个笑眯眯的怪力女谈下去的欲望。
“吾还是不明白,那个家伙到底哪里好了。”
“neko没看过莎士比亚吧?”
“什么鬼。”
“不,不要以为我在恭维你;
你除了你的善良的精神之外,身无长物,我恭维了你又有什么好处呢?
为什么要向穷人恭维?
不,让蜜糖一样的嘴唇去吮舐愚妄的荣华,在有利可图的所在屈下他们生财有道的膝盖来吧。
听着,自从我能够辨别是非、察择贤愚以后,你就是我灵魂里选中的一个人。
因为你虽然经历一切的颠沛,却不曾受到一点伤害,命运的虐待与恩宠,你都是受之泰然;
能够把感情和理智调整得那么得当,命运不能把他玩弄于指掌之间,那样的人是有福的。
给我一个不为感情奴役的人,我愿意把他珍藏在我的心坎,我的灵魂的深处,正像我对你一样。”
不不不,西芙这种话你还是正儿八经让男孩子说好吗!!!!!
炫耀你看书看得多了不起吗死学霸!猫又被雷得发抖,妖怪服从强者也不代表它必须对和自己脑电波完全对不上频率的愚蠢人类扯淡。猫又保持自己高(zhuang)傲(bi)的身姿跳上窗台,临走前回头看了一眼看上去丝毫没有会有欲望的白痴契约者。
“总之你先搞熟了再说!”
唔,绿豆应该不能放进烤箱吧?
西芙只希望自己最后做出来的不是黑暗料理,将绿豆丢进煮沸的水中。
总觉得哪里不太对……
除去这个,月饼皮的制作方法简单太多,至少材料看起来都是似曾相识的东西。
总之艰难得做完了一个月饼,西芙勇敢的自己做自己的小白鼠尝试了一口觉得自己对唐草的爱真是感天动地。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what a sad story.(邓布利多摇头
唐草本人却对中秋节没有太多感想,毕竟中秋是个家人团聚的节日住宿学校不放假没人权啊!
不过过节也可以和女朋友约个会什么的。
【约会计划书要怎么写,急,在线等_(:з)∠)_】
楼主(花花草草):如题,明天就要中秋啦想和女朋友出去玩,求攻略。
沙发(LL大法好):抢沙发!中秋节约什么会,乱放闪光弹罚款哦。
板凳(到底有几个好妹妹):楼上有什么立场说这句话,举起火把。
地板(臂上能走马):诶亲爱的你想约会吗?做什么计划这种事我来就好了嘛233
4楼(堕落圣歌):虽然觉得哪里不对,但是瞎。
5楼(通天塔):虽然觉得哪里不对,但是瞎。
6楼(不是李白是lee white)虽然觉得哪里不对,但是瞎。
7楼(懒):强迫症哭,托塔李天王
8楼(叉叉克三):楼上果真对得起这个名字,求翻译。
9楼(LL大法好):应要求翻译:强迫症搞不懂到底是哪里不对要哭了,以及56楼的朋友你们听说过托塔李天王吗吗吗!!!
10楼(黄段子是世界的正义):画风不对啊这对兄弟!连这么透明的马甲都看不出来一定是天然呆(摇头.gif)
11楼(欧派万岁\(≧▽≦)/):虽然很想给楼上上的解释和楼上的吐槽点个赞,但我还是要说,你们歪楼了。重点难道不是约会计划吗?
12楼(通天塔):嫌弃一下楼上的名字,以及重点难道不是烧烧烧吗?
13楼(不是李白是lee white):嫌弃一下楼上上的名字,以及重点难道不是烧烧烧吗?
14楼(臂上能走马):瞩目了托塔李天王二连杀。以及大家不用想约会计划书啦我直接去约男朋友☆
脸上发烫的唐草想自己作哪门子死在学校论坛发贴,简直傻逼。
自我反省到一半感受到身后女朋友飞扑过来的力度。
我的腰——!!!
“亲爱的节日快乐☆”
“节日快乐,西芙。”他回过头看到女朋友和一样穿衣风格截然不同的绿色短旗袍……比起黄段子果然旗袍才是世界的正义……不对我在想什么啊?!
“我想了一下,约会怎么样都可以,我只要和唐草在一起就可以啦。”西芙打开便当盒,里面却不是月饼而是……绿豆粥。
“我记得你喜欢吃绿豆好不容易从杂货店换到了,可惜月饼试做失败。不过这个还挺好喝的。明年后年还有以后,我觉得总能学会的,然后来夸我吧。”女孩抱住恋人蹭了蹭,“因为我最喜欢唐草啦!”
啊他被西方人的直白打败了,不过这种话果然还是应该由男生说出口。
男孩回抱住对方,。
“现在的西芙就很值得夸奖,是最棒的女朋友。”
2010字
不耕,获;不菑,畬。则利有攸往?
——《易经·无妄》
很久很久以前,有这样一个地方。那里有无限广阔的沃土,有宛若大海的天幕,氤氲着清淡花香的空气,清澈见底的池塘……几乎一切自然的极致的美都被毫不吝啬地堆砌到了这里。
这里的人享受着不必劳作的生活。是的,他们不用劳动。每一年,沃土中就会长出作物,到了成熟季节,一望无际都是丰收。麦田中金黄的麦子低垂着头,在风中轻轻摇曳,掀起一阵金色浪涛;果园里翠绿的树叶中掩藏着造物主的无尽珍藏……而这所有的过程都不需要人们劳动,他们只要看着这块田,等待成熟,就可以了。
有一天,一个人无意中闯入了这里。他看到面前不可思议的景象,用看着神祗的眼神看着村民。他问:“为什么你们都那么勤奋地劳作呢?”那里的人很吃惊,反问:“劳作是什么?”
原来,这里的人早已不知道劳作是什么意思。他们无需干这种事情就可以年年享受丰收,这着实震惊了那个外来者。
“可是,你们又是怎么做到的呢?”外来者问。他的内心开始了动摇——是出去,还是留在这里?
“我们也不知道,从很久以前就是这样了。我们只管享受。”
安闲舒适,空气清新,天空如同包容了海洋那般湛蓝。这人间仙境依山傍水,自然之景美到了极致。
最重要的是,不必劳作便可享受丰收。
外来者当即表示希望留下来,与他们一同过这种生活。村民们回去讨论了一下,觉得多一个人也不会有什么压力——反正每年都不愁粮食。于是他们就接纳了那个外来者。
年复一年,外来者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太舒适了——他只能这么说。他每天都和村民们一同散步,聊天,或是和小孩们一同玩耍,或是独自看书,拨弄琴弦,在茫茫天地之间大发感慨,挥毫弄墨亦是闲情雅趣,但这里唯独不必劳作。他欣赏这里瑰丽的自然之景,和睦相处的邻里关系,还有这种可以坐享其成的安闲生活。
他沉浸在这里,他甚至有时候可以一天躺在床上不动弹,照样有吃的。这里的食物口感异常好,他甚至觉得自己不需要什么运动,光靠吃这些东西就可以维持身体的健康。
这真是一块宝地啊。
又是一年过去了,不知不觉间,他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十年。
“今年怎么没有作物长出来?”
这年春季的某天早上,他看见田野里没有丝毫动静。村民们都或扛或拎着耕作的工具,拿好了种子,走出家门去往田野和果林中进行劳作。他奇怪极了,这里一直是无需劳作的啊,为什么这群人都出去了?他也走出门,赶上一个走得比较慢的人。他问:“这里不是不需要……那个词怎么说来着?劳……劳……”
自己都已经忘了“劳作”这个词了。
“劳作啊,什么时候不需要了?”村民用奇怪的目光打量着他,像看怪物一样。“看衣服你是这里的人啊,难道你从来没有参与过劳动吗?”他鄙夷地扭过头,匆匆走了。他今天还要开垦一点荒地,自己家里尚剩有棉花的种子,但是已经没有闲置的地可以用于播种了。
外来者惊讶地呆在原地。难道一切都是梦境?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他可是在这里过了十年,十年不必劳作的生活,十年闲适的生活,十年笔墨风流的生活,十年幸福的生活。
他觉得头痛欲裂,突然疯了一般地奔跑起来。所到之处都是一片空白的沃土,纵横阡陌在过去犹若一个个丰收的符号,而此刻却只是荒芜。他奔跑,本能地、崩溃地、疯狂地奔跑,土地在视野中慢慢变得焦黑,开始龟裂,仿佛有残忍的烈焰灼烧,周围的鲜草开始枯萎,犹如在同一时刻被死神的镰刀收割而去。天空覆上了阴霾,太阳的光芒无法穿透云层。他恐惧地发现自己的皮肤开始皱缩,就像老人那样,皱纹就像刀刻的那样深深地嵌在他的皮肤上。
体力渐渐不支,他原本可以跑得更快更远。
他停下来,喘着粗气。前面有一汪水池,这在干裂如同刀刻的大地上就是珍宝一般的存在。他拖着疲惫的身躯,一点一点挪到池塘前,看着水中映出的自己。他竟然已老去,分明只是过了十年,却好像已经过了一生。他早已不是那个年轻人,他满脸皱纹,骨瘦如柴,仅剩的一点干枯的白发凌乱地被湿热的汗液黏在头皮上。他意识到自己已然老去,长期不从事劳作的身体无法支撑这种远距离的奔跑。
这都是真的吗?那十年,是真的仙境,还是魔鬼展现的虚伪的甜美?
他再一次感到头痛难忍,千万种不同的声音和言语涌流般汇集,几乎要炸裂他的大脑。紧紧捂着头,他瘫在地上。
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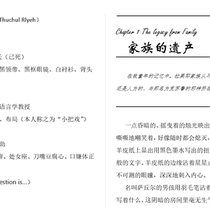
“人们一直认为,亚特兰蒂斯文明不过是柏拉图为解释他的理想国学说而虚构的一种文明,是对当时雅典社会的一种勉励……许多现代学者也曾去寻找这一文明,最后都无功而返。几种假说,分歧实在是太大……或许你们都搞错了一个方向,那就是研究亚特兰蒂斯文明,就要从亚特兰蒂斯文明的语言文字和本土遗稿中研究。
“今天,我将在《语言》杂志(注:美国一著名语言学学术期刊)上发表我这十年沉默以来的成果——《对亚特兰蒂斯文明语言的研究》。我相信,我对亚特兰蒂斯文明失落已久的语言的研究,将引发学术界一场‘亚特兰蒂斯狂潮’。”
穿着黑色西装的中年人微笑着点头,面对演讲台下“咔嚓咔嚓”不断亮起的闪光灯,深深鞠躬。约克•莱辛知道这一次学术发布会的意义何在——他将成为世界语言学界的泰斗级人物,为亚特兰蒂斯文明的研究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最后他会名留青史。
他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教授抱歉地看了看台下意欲采访的媒体,做了一个暂且离开的手势。约克慢慢走到一个角落,按下了接听键。
“你的学术发布会好像很成功的样子。”电话对面传来一个平静的男声,听着很年轻,不过二十三四岁。约克知道这是谁,“托你的福,非常成功。”他嘲笑道。
对面沉默了,过了一会儿说:“你应该知道那份研究成果对我来说的意义。那是我的父亲和母亲,甚至我的祖父外祖父,祖母外祖母,用一生去研究得出的成果。”
“但是你看,你又不需要名利——或者说墨尔本大学最年轻的教授这一职位已经为你博得了许多名声了,‘古代文字学的天才’。”约克耸耸肩膀——虽然他知道电话那头的人看不到他的动作,“但是我需要,毕竟世人都不会像你那般淡泊名利,是吧?所以呢,还不如给我——反正你研究的,你已经掌握咯,这些知识对你来说已经在脑子里了。”
电话对面传来一声冷笑,不知为什么这声冷笑竟让约克浑身颤抖起来,他感到了透骨的冰冷。这只是一个小屁孩的嘲笑,他在内心如此麻醉自己。
“拉莱耶家族的秘密研究成果被一个外人窃取并且公开发表,我想您应该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拉莱耶家族……
“那是什么狗屁家族,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约克回以一声冷笑。他偷偷瞄了一眼会场——这么多媒体记者都在,出席者也不乏学术界中“掌握发言权”的人物。一个二十三四岁的年轻人,难道要在大庭广众之下杀了自己?“暗杀可不是一个好主意,拉莱耶先生。”他低声警告。
电话对面的拉莱耶先生轻笑一声,开口道:“我从来没说过暗杀,先生,从来都没有。”
然后,约克听到了极疯狂的大笑声。这名教授神情一凛,“请回头看看您的会场,莱辛教授。”
炽热的气浪直扑到他脸上,一阵巨大的爆响在会场中心响起。约克感觉整个世界都剧烈地颤动起来,他往手机的麦克风处大吼:“你是什么时候……把炸药给放进来的?!”
“请用更加专业一点的词汇,亲爱的莱辛教授。”电话那头的声音很平静,仿佛是高中化学课上讲师用极其平淡的语气教授知识那样,“环三次甲基三硝胺(Cyclotrimethylenetrinitramine),一种无色结晶,明火、高温、震动、撞击、摩擦都可以使其燃烧……威力大概是TNT的1.5倍吧。我知道你化学肯定没学好,不过我也没学好,我只是……脑子比较好,都可以记住罢了。”
约克努力回忆着在哪里看到过无色晶体,突然他反应过来了。
“你这个会场地上怎么那么多玻璃碎屑?”他对一个戴着鸭舌帽的工作人员质问道。
工作人员鞠了一躬,始终没让自己的脸暴露在约克面前。他说:“昨天几个小孩子把外面的玻璃打碎了,估计是调皮。然后清扫的时候路过这个会展厅,撒了一点下来吧。”然后他匆匆走开,还不小心撞到了约克。约克皱了皱眉,也没多想。
又是一阵剧烈的爆炸,约克分明看到被炸得飞起的残肢断掌血肉模糊的样子,它们落在地上,不再具有那种叫做“生命”的东西。还幸存的人们疯了一般地哀嚎,拥挤着,躲避着,很快他们中就有人因为推搡而倒在地上,他们的肉体和地上那些原始制得的环三次甲基三硝胺晶体剧烈地摩擦,很快又是一阵明火窜起,爆炸的气浪将那一片的人都掀到一边,处于爆炸中心的就是被残忍地肢解了。
人们要逃,要活命,在死亡面前人类的求生欲望是那么明显,也是那么丑恶。约克亲眼看到一个男性记者为了躲避一次爆炸,竟是将身边原本可以活下来的女子扯住,用力拖进了爆炸中,自己则借着这力闪到一边。那女子发出的哭喊甚至还没传出来,火光就吞噬了她,而又心满意足地吐出她已经变得焦黑的肢体。
“他们都因为你而死,约克先生。”
约克不禁呕吐起来。
“在密闭条件下能够由点燃产生爆轰……我记得书上是这么说的。”那边的声音还是那么平静。
“你说我不要名利,我确实不需要那种东西,我如果想要名利,以我的智商,随便做一些什么都可以为我赢来名利。”约克仿佛能看到梳着大背头的青年优哉游哉点了点自己太阳穴的样子,冷汗从他的后颈沁出。
“但是这并不代表你可以窃取对我的家族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如果你这么做了,那么我想对你最重要的,超越名利的,应该是生命了吧……?”
约克惊慌失措地开始逃跑,他从演讲台上跑下来,用力推开人群。他不知道地上哪里会有那些结晶体,只能够赌一把。“你布局就为了杀我?!”他难以置信地对着手机大喊。电话对面的青年啧了两声,说道:“如果以你的智商这就构成一次布局了,那么你可以称之为布局吧……我只是用最简单的方法,抹消所有侵犯了我家族财产的人而已。”
“所有。”
这个疯子到底布置了多少这种炸药?约克觉得自己是无法猜出来的。若是能够有一个量化的指标,那就是“可以杀掉整个会场里的人”。
拥挤,实在是拥挤。一连几次爆炸让整个会场的人都挤在一块,你推我一把,我挤你一下,挣扎着,无限渴求地奔向出口。
他的西裤因为剧烈的摩擦燃烧起来。当约克才反应过来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的时候,爆炸又一次发生了。
以他为圆心的一次爆炸。
萨丘尔满意地听到电话对面传来了最后一次爆炸声,随即就恢复了未有来电时的忙音。他站起身,伸了一个懒腰,随后把杯中的咖啡一饮而尽。语言学家拿起桌上的那把手枪,检查了一下弹药的装填,稍稍想了想使用的方法,便娴熟地拉开了保险,把枪口对着自己的头颅。
突然,他那台已经关机的电脑上跳出来一个对话框。真奇怪,他已经很久没有连接过互联网——否则自己的一系列准备行为很容易从网上被找到。
他眯着眼放下手枪,凑近了电脑屏幕,轻声读出了对话框中的内容。
“想明白生命的意义吗?”
“想……真正的活着吗?”

确认一下现在的状况:我被锁在黑暗里。
一秒钟,更准确地说是半秒钟,最正确的说法是一瞬间一刹那之前,我还在做着非常平常的事,平常到每个身体健康行为正常的人每天都会做一次或几次的事。但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事,对生命体来说这应该仅次于——不,应该和进食跟繁衍同等重要的事。
刚才还在做着这么平常而重要的事的我,在下一个瞬间就被封锁在了黑暗之中。
这是完完全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以及完完全全连我自己呼吸的声音都被隐没掉的寂静。
我身上唯一能帮我照明的东西,只有一部手机,但它的电池已经快耗尽了,现在它只有我在触碰屏幕的时候才能发出一点微弱得如风中残烛一般的光芒。
在这片黑暗和寂静,不仅仅是我的视觉和听觉,好像就连我的方位感觉都被扰乱,我现在甚至无法确认自己是否还像黑暗来临之前那样站立着,而我所在的这个空间的重力是否还如我所熟悉的世界那样正常,这里的物理是否还在宏观上遵循着牛顿所总结出来的三个定律。
总之,就像现在这样什么都不做也毫无进展,我并不是无事可做或无事能做,我还可以用我的手机发出的弱光去探查或者感知一下我所在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环境。
我举起手机,用大拇指触碰了它的智能屏幕,把那上面所发射出来的光芒照向前方。
出现在前方的光晕中的,是我的手机。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只听滴滴两声,我的手机上发出的光芒终于被微风吹灭,被黑暗吞噬。
电池终于耗尽了,我再怎么频繁或者用力地触碰屏幕或者开机键也无济于事。
我周围的世界再一次陷入完全的黑暗和寂静,留给我的只有刚才我的手机所照射出来的那个神秘图像:我的手机的正面。
那究竟是否真的如我的眼睛所见是我所想的那个东西?
为何我能突然看到本应被我朝向前方的手机的正面?
我的视觉是否有因为那一小点尽管微弱却在这个情况下显得弥足珍贵的光亮的存在而产生了混乱?
在脑中思考并纠结了诸如此类多种多样的复杂问题之后,我终于意识到了,我所看到的东西,并不是什么手机的正面,准确地说并不完全是。
那东西是面镜子。
现在的我被锁在一个黑暗的空间或类空间中,而在我面前的东西——如果说这个地方不会随着不知是否还遵循着正常法则的时间的流逝而改变它的形态或结构的话——是面镜子。
黑暗,和镜子。
我不禁想到了那个古老的都市传说。
那个据说是血腥女王召唤仪式的传说。
根据传说,这个仪式的进行地点,必须符合两个条件:
1-在黑暗中;
2-在镜子前。
我的心跳骤然加速,呼吸也急促了起来。
至少现在不再寂静,但我并没有因此觉得安心。
冷静一点,这种都市传说肯定是骗人的,什么血腥女王,这是哪个打ICC打出毛病来了的家伙想出来的东西啊。
况且,就算它是真的好了,现在只不过是地点符合条件了而已,其它的条件要是没有备齐的话,仪式还是无法进行的。
其它的条件……我记得那个传说中还提到了仪式的时间。
那个时间是:半夜十二点整。
……现在是几点?
不不不,在现在这个异常的情况下时间还会正常流逝吗?
先姑且认为它会正常流逝和运转好了,那么现在是几点?
如果我的手机还能用的话,我就可以看看那上面的电子时钟了。
但是现在我的手机不能用了,不过我还记得,刚刚我有瞥到一眼那上面的时钟:
23:5X。
那个X是什么?!
因为我仅仅只是无意中瞥到了一眼,所以我没记住那个X具体是0到9中的哪一个数字。
不管是哪个数字,那个时间都离半夜十二点非常接近。
从那时候到现在过了多久?已经到了十二点了吗?还没到吗?还是已经过了?难道说在我现在打下这个问号的时候才是刚刚到十二点的时刻?!
不不不,冷静一点,都说了这种都市传说是骗人的。
就算它是真的好了,现在也只不过地点和时间(可能吧)符合条件而已,其它条件……
其它条件我不记得了。
因为当时觉得这不过是个无聊的传说,所以我根本没有用心去记。
没错,这只是个无聊的传说……
但要是我在无意中达成了那些条件呢?
比如说,我现在的姿势,我现在手的位置,我现在呼吸的频率和深度,我现在的心率……等等等等。
所以我应该调整呼吸和我的姿势?但要是本来就没有,但在我因为慌张而随便乱动的过程中达成了条件呢?
仔细想想,关于这个传说,我还记得些什么呢?
哪怕一星半点也好,这样我就可以尽量去避免了。
……
我记得好像这个仪式还需要咒语。
那是什么样的咒语?
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但好像是……
我以本人的名誉起誓,我愿意成为我的女王的仆从,我愿意为我的女王献上我的鲜血、我的肉体、我的灵魂、我的欲望。
为什么这种东西我偏偏记得这么清楚啊?!
虽然没有念出来,但我总觉在我心里默想这些东西就能产生和把它们念出来一样的效果。
别想了!别想了!
根本就没有什么女王!那种传说不过是骗人的东西!
但如果那是骗人的的话……这片黑暗又该怎么解释?
把我封锁在这里的这个黑暗,又是什么呢?
如果连这种东西都存在而且被我亲历过了,那血腥女王什么的……
不也很有可能真实存在……吗?
不不不!
我不由自主地挣扎起来。
虽然我看不到,但我的大脑确实发出了让我的身体开始挣扎的指令,而且我也能确实感到自己肢体的运动。
在挣扎中我好像碰到了不少东西,有的硬有的软,其中的一些像是被我碰掉了一般发出落地的声音,有的甚至还发出了破碎的声音。
那些是什么?
难道是……毒气瓶?或者其它更可怕的东西?
不,不要!
我不想死在这里!我不想就这么糊里糊涂不明不白的死去!
“救救我!”
我竭尽全力发生声音。
我祈祷着这股声音能穿透这片黑暗,传到外面有能力救我出去的人的耳朵里。
“救救我!快救救我!我快死了!”
我从未如此渴望过自己能活下去。
只有在死亡的威胁步步逼近的时候,人类才会有这种想法。
“救救我!”
刷!
就在我用尽我全身的力量让我的声带以最大幅度振动的时候,黑暗消失了。
就如它突然降临将我封锁一样,它突然消失了。
我的呼救得到了回应。
现在我的置身于一个明亮的白色空间内。
这里的天花板、墙壁和地板都是白色的,神圣得没有一丝污垢的白色。
而刚刚在我前面的那面镜子,也正常地映照我从恐惧中解脱出来的欣喜的脸。
我得救了。
“我得救了!”
虽然不知道是谁把我用什么方法救出来的,但总之我终于得救了。
“我得救了!!!”
“吵什么!半夜在厕所里遇到停电就吓成这怂样了吗?!”
门外——我所在的这个房间里有扇门——传来一个女人怒吼的声音。
……
半夜在厕所里遇到停电……
原来是这样的事啊……
话说,好像有点不对劲。
我明明是单独一个人住在单人公寓的啊。
外面那个人,是谁?

胆小鬼连幸福都害怕,碰到棉花都会受伤。
我一直,听不懂这句话。
“……一分钟!”
光电风暴的杂音消失,我和丹越过暂时不再蔓延的绿色,听到唐宵他们在搏斗中破碎的声音。
身体只是稍微有些发疼,四肢的活动也并不迟缓。连魔力的运转都不成问题。
但我知道,身体的状况不像表现出来的那么好。
从内到外的,在崩溃——
我的身体素质在队友们当中算是很弱的,说不定还比不上生存于社会暗面的亚历山大。开启了基因锁之后,能恢复行动力真是万幸。
……崩溃了之后会发生什么呢?
……失去了行动力之后我会怎么样呢?
……身体破碎之后我会怎么样呢?
答案呼之欲出,就隐藏在薄薄的不透明帷幔后面,仿佛我伸出手就能触碰一般。
但是我不知道。无论如何都不知道。不管怎样都无法知道。别说看到,就连感觉到都不可能——
想到这一点,我就焦躁的连呼吸都要停滞了一般。
生而为人。
“小心!”
被丹拍了一下,我从因为虚弱而混乱的思绪中挣脱,看着唐宵如同利刃般切开前方的藤蔓,向仿佛燃烧在藤蔓中一般的红色果子伸出手。
“……!”
那位没有说过几句话,有着可爱名字的男孩被触手穿过心脏,扯进绿色的汪洋之中。我条件反射的运转起魔法,让风刃切开一点他身边的藤蔓。
“别犯傻,那孩子已经死了!”
唐宵大声冲我喊道,他被藤蔓擦伤了左手,不得不向后退去。我还在纠结唐宵的意思,有什么东西从左边那一大团绿色藤蔓中挣脱,以匪夷所思的动作回避着攻击,并粗暴的止住腹部的血——
基因锁!
“亚历山大!”
喻谅手中的枪发出爆响,子弹击中追击俄罗斯男人的藤蔓。唐宵终于扯下那几个红色的果子,身上的衣服有些破烂。
“好,这下子我们……该死!”
他另一只手的骨刃剧烈颤抖了一下,恍惚间我看到,那是什么绿色的东西打在了上面。
“它们暴走了!”
不需要他的提示,我们就明白了现在的情况。藤蔓狂暴的挥动起来,如同蛇妖的头发,带着恶毒到极点的獠牙——
把总裁先生和黑发的赏金猎人,卷了进去。
“……阿莫!”
反应最快的是丹和喻谅,没等紧接着反应过来的我击碎藤蔓,向他们冲去的时候,总裁先生就被疯狂的藤蔓挤成了一堆碎末。
……那一定很痛。
而且,变成那么一滩东西的总裁先生也很难用手拉回来呢……
我偏过视线,和莫炔对视了。
莫炔的眼神锋利如同刀刃,却一直藏着蜷缩在角落的孤狼般的戒备。但这戒备与我无关,与丹无关,与喻谅无关,与在场的队员无关,与海洋队员们都无关——
我再也不想,和同伴永远分开了。
——我再也不想,又失去一个容身之处了!
“阿莫!”
我有些沙哑的喊道,火焰形成的锋利刀刃切碎周围的藤蔓,丹和喻谅打断支援的绿色,向那位赏金猎人伸出手。
仿佛某座冰山融化一般,他笑了。
子弹击中藤蔓产生的光电炸开,男人动作凌厉,没有平时训练有素的凶狠,取而代之的是野兽般诡异而精准的直觉——
藤蔓被他躲开,甚至被他的小诡计耍的难以前进。他抓住喻谅的手,我们四个向门跑去,唐宵为我们和地上喘息着的亚历山大抵挡怪物。
“撑住,撑住!撑到下一个房间!”
副作用已经发作,顾不得亚历山大的痛感的丹扶起他,几乎是拖着一般带着他前行。最后一扇门被猛地关上,我们几个瘫坐在地上,而莫炔剧烈的抽搐起来。
我刚看见喻谅把他抱到身边,在我身后的唐宵默默用手捂住我的眼睛。
“不可以看。”
他说。
--------------
“22,20,23。”
我用纽扣在地上划着。一旦开始计算大脑就有些发疼,只好用笔算代替心算,尽量减少负担。
“从现在看的话……”
我小声地说,喉咙发干的感觉非常难受。
“改变位置后的同种坐标轴之和,如果是一个比较大的数的话……即使是安全房间也可能有危险。”
“能确定大概是多大吗?”
喻谅问道,我闭上眼睛,回忆起之前遇到的房间。
“我不大确定……可能是50或者60以上吧。”
“那就视作45。”唐宵大致恢复了体力,他先站起身来。已经简单包扎过伤口的亚历山大和莫炔吃力的站起身,看上去使不出什么劲。
“只要比45大我们就不进房间,那么,我们……乐乐?”
门被打开的声音传来,熟悉的人出现在另一边。乐行身着白衣,稍有些吃惊的张了张嘴。
“……你们都没事吗?”
他问。唐宵似乎回到了之前的状态,向他露出安心的笑容。
“没事。乐乐这身衣服是……?”
声音没有落地,我的耳边就传来一阵风声。
丹的手,抓住向我刺来的骨刃。
“……带着大家!”
丹咬着牙冲我简短的说着,声音因为用力过度而变形,带着蛇吐信一般的嘶嘶声。我还没有明白现场的状况,呆滞地看着试图收回骨刃的千岛——不知何时潜伏到旁边,身着白衣的千岛。
唐宵的反应比任何人都快,他一拳把白衣的乐行击回边上的房间,然后跳了进去。丹则顶着千岛,同样进了另一个房间——
声音被钢门隔断,我们几个迅速跳了起来,检查其他房间的数字。
“这边,是……”
喻谅没有受严重的伤,他的动作比我们要快的多。等他报出数字的时候,勉强自己在脑内迅速计算完毕的我,还没有来得及发出警告。
“……!”
庞大的蛇尾从那边一卷,喻谅被它扯了进去。莫炔发出吓人的吼声,冲到房门之前。但是很容易转开的门把手却被卡住了一般,根本就无法转动。
我们只能呆在原处,听着三个房间内的搏斗声。幻书悬浮在我的身边,随时准备放出支援的魔法——但是毫无意义。
呆在这里不动的我们,又有什么东西会袭击呢?
……我又能,做些什么?
莫炔一拳砸在墙壁上,鲜血从纹路中慢慢渗下来。我从没见过他这么不冷静的样子。亚历山大阴沉的靠着墙站在门边,手持几乎没剩下子弹的手枪。
搏斗声渐渐平息。丹离开的房门的把手开始旋转,我凑到那边去,但却把手只转动了一半,就停了下来。
喻谅的房间发出一声闷响,我和莫炔同时旋开两个房门,走了进去。
“……丹丹!”
房间里是吓人的血腥味,我看到角落是一堆看上去像是镜像人千岛的东西,整个被肢解掉,应该已经失去了行动力——接着我才看到,丹躺在门边的地面上,身上都是伤口和骨片,鲜血渗了一地。
她在抽搐。我慌乱的从洞口钻过,衣服都有些扯开。看到这边情况的亚历山大敲了敲墙壁,闷声提醒我。
“缺氧。不快点处理的话情况会很糟糕。会人工呼吸吗?”
他说。我不知道这样下去会让丹变成什么样,不过如果这样做能让她舒服一点的话……
……并不是,什么很难的事。
我不断地眨着眼睛,把挡住视线的白发稍微撩到耳后……然后下定了决心。
“失、失礼了……”
---------------------
六个人重新聚在一起的时候,状况都不大好。
唐宵喘着气靠在墙边,独自忍受着基因锁后遗症的痛苦,除此之外,他的脸上似乎还带着难以言表的愤怒和悲哀。喻谅伤痕累累,所幸也挺过了后遗症……丹的身上到处残留着不完整的镜像人千岛,被切开的伤口也一直向外渗着血。莫炔和亚历山大重伤,我的伤势算是最轻,但大脑痛得连计算都要无法进行了。
“……”
这么一会之后,唐宵稍微吸了一口气。
“……我们,去渡桥吧。”
喻谅露出一个虚弱的笑容。
“六个人爬过去?”
正如他所言。
我们慢慢在房间之间挪动着,慢慢计算着数字。接下来的路途出人意料的平静,互相搀扶着的我们,终于到达了渡桥,打开了它后面的房间。
大家相视而笑,穿过那扇门的白光。
但却进入一片黑暗。
“……?!”
重新适应亮度之后,我注意到自己被装置牢牢固定在了地上。说实话,我的魔力已经见底,连吟诵咒文的体力都不知道有没有了。队友们,不在身边。
平淡的男声响起。
“What's your name?”
我摇晃了一下自己的脑袋。
“……Eve.”回答。
“Do you believe in god?”男声接着问道,然后补充了一句,“Yes or No.”
我……相信神吗?
身为人间失格的我……相信神吗?
胆小鬼连幸福都害怕,碰到棉花都会受伤。
我一直,不明白这句话。
我从来就不懂得隐藏,即使是在意识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之后。班级里的宠物死了?死是什么?同学死了?死是什么?祖母死了?死是什么?
问我,为什么和同学坠楼的尸体说话?
……尸体是什么?
我的记忆中模模糊糊的有这些名词,但是总在别人说到时才记起。即使记起,我也不知道它的意思。
我从来就不懂得隐藏。不像那位叶藏,不像那位幸福的胆小鬼,不像那位……好孩子。
所以我,一直独自一人。
一直一直,思考着什么是活着。
“你……不难过吗?”
父亲这么问道,我则不明所以,眯着眼睛躲避着过量的灯光。
“为什么?”
“因为有人死了啊。”
“死是什么?”
他沉默了很久,注视着我没有色素而显得鲜红的眼睛。
“……伊芙。”
“怎么了?”
“你知道什么是活着吗?”
我摇头。毫不犹豫,斩冰截雪一般清脆地回答。
“不知道。”
他把手放到我的头上,一言不发。那里能传来手的温度,但却让我感觉冰冷如铁。
于是我退了学,呆在图书馆的角落,翻动着发黄的书页,人少时就整理无序的书目。望着人群在街道上穿梭,如同我是——不存在的幽灵。
如同那只应当被剃刀毫不犹豫削去的,没有温度,无法碰触,不能交流的幽灵。
既然如此,又有什么可以害怕?
既然如此……又怎么会受伤呢?
“Yes.”
我小声回答,机器放开了我,黑色的门打开。
然后我露出狡猾的笑容。也许那是在队友面前也不会露出的……仅此一次的微笑。
“Because……I'm God.”
如果这世界上,真的有神明的话——
——那就应该,是幽灵一样的我了。
我站起身,走进黑暗的房间中打开的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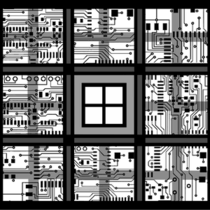
“857,Clear。”
“674,736,Clear。”
计算完毕,靴子测试安全。大家依次钻了过去,七岛扶着几乎没法走路的我穿过洞口,门在我们后面关上。
寂静。
“看来是安全的。”
喻谅松了口气。但是七岛和白星却皱着眉头捂住了鼻子。
“……好臭。”瑟特克嘀咕道,我们看向周围,在狭小的房间的角落里——有一大团肉块。
“什么东西?”我歪了歪头,林鸮凑到那团肉块旁边,仔细观察着。
“是蟒蛇没错,不过这种品种……”
他低声念叨着什么,唐宵也凑了过去。
“你认得?”
“……一般的种类倒是了解,但是这种我可从来没有听过啊。至于这一块——”
林鸮毫不在意的研究起这一大团尸体边上的另一小块,用脚尖拨弄了一下。
“——理所当然是蝙蝠的。”
“这么大的蝙蝠?”亚德撇了撇嘴。
“没错。能啃人脑袋的那种蝙蝠。”
你的表情看上去可不像你的语气那么冷静啊。不过,这么危险的东西,突然起来攻击我们怎么办?
“它们不会攻击我们吗?”
我问道。新人们向我投来奇怪的目光,已经经历过一部恐怖片的大家则扶住了额头。咦、咦?这是干嘛?
“嗯……它们,已经失去行动能力了。”
唐宵斟酌了一下词句,拍了拍我的头。虽然我还有很多问题,不过看现在的气氛,还是忍到回主神空间再问吧……
“这个大家伙的身体部件能做武器,要试试吗?”
林鸮露出了笑容。嗯,是那种死宅看到新游戏发售的时候会露出的笑容。
“动手吧。”唐宵耸了耸肩,“我最讨厌枪了。”
接下来的情况大致就是,巨蟒的尸块被分开,骨骼被做成了不少武器。因为现场的惨烈程度不亚于凡尔登战役,如果写出来的话这篇文章要漫画化就困难了,所以暂且不表。
“有点短。”
白星把手枪交给七岛,然后向下挥舞着白色的骨刃,切割空气的声音呼呼作响。
“不可能那么长的,就别抱怨了。”林鸮把蟒蛇的蛇牙递给唐宵,后者正在用兑换的秘籍里记载的不知名的技术,用蝙蝠尸体给蛇牙淬毒——大概是用来当暗器。
明明只是蝙蝠尸体啊。到底怎么做到的?
好奇心要暴走了!
千岛熟练的挥舞着肋骨做成的忍刀,又把脊椎切成的薄片收在身上。嗯……一下子恢复了很多战力呢。
肋骨做成的匕首被分发给所有人,瑟特克和亚德拿到了多数。这两个人似乎很会用这种武器,正把它们收在合适的地方。
“……这边就不用了。”
莫炔如此说道,林鸮看着拿着手枪的他和亚历山大,了然的点了点头。做好的一把把武器被大家收在身上各式各样的地方,总觉得有点像哪里的恐怖分子集团。
“糖糖,能帮我拿下那个吗?”
唐宵正试图从做好的骨刃里找到接近唐刀的武器,他从旁边拿出一根只有上半部分的肋骨递给了我。
炼金术师的笔记悬浮在我身边。
《妖精之书》,是炼金术师帕拉切尔苏斯所撰,记载着操纵四大精灵法术的幻书。我所用出的魔法,很多都是借助它来完成的。闲话不提,这本书用出四大元素的魔法的本质是操纵元素精灵,换句话说——
——让元素聚集在一起,要比发出元素攻击简单的多。
我念诵着拉丁文书写的文字,用手抚过那只有一半的肋骨。风之元素不断聚集。
因为解开基因锁后使用过那样的魔法,控制力大幅上升的我用元素做出锋利的武器不是什么困难的事。问题就在于,除了幻书持有者以外的人是抓不住它,反而会被它所伤的。用弹匣做刀柄也行不通,根据《妖精之书》里的神秘学知识,金属通常对魔法有排斥性,让元素附着在上面很难——换句话说,只要有合适的刀柄的话,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我手上不可能有秘银。那种轻巧又坚固的亲魔金属我曾在主神空间的兑换中看到过,比一般铁锭稍大一点的一块秘银锭,就需要10000奖励点。
怪物的骨骼。
我手中拿着的,正是最优良的导体之一。
除此之外则是,怪物的血液。无论在哪部神秘学著作中,血液都是仪式或法术的重要素材……而这些幻书上记载的文字则确确实实的证明了这一点。顺带一提……女孩子「那个」的血液是最好的材料之一,因为它本身具有「周期」的神秘性。
再怎么好用我也不用。
我脸红着摇了摇头,把四处乱飘的思维重新集中到眼前。
风之利刃从刀柄开始延伸,无形的凶器很快成型。维持这点魔法,我还是做得到的。
“……看不到,要小心。”
我小声的说着,然后递过刀柄,唐宵有些吃惊的接过它。
“风王结界?”林鸮在精准的时机发来吐槽。别玩梗啦!
玩梗的是你。他的眼神好像这么说道。
大家把武器收好没多久,立方体就开始震动起来。虚弱状态的我根本没法靠自己站稳,只能紧紧的抓住七岛的手臂。
“又移动了?”喻谅把自己的匕首和眼镜扶正,震动很快平息下来。
紧接着,是机械运动的巨响。
奇怪的藤蔓,从C门涌了过来。
“触手怪。我是第一次看到真的!”
我出声道,喻谅则做出了上一次我们在林中小屋的悬崖底部见到尼斯湖水怪的时候,一模一样的吐槽。
“在这之前谁看过真的啊?!我们跑好吗?!”
海洋队员们,拔腿就跑。
“Clear!这边!”
林鸮刚才就在检查周围房间的序号,他在D门前面冲我们喊。无形的利刃划过空气,唐宵迅速的斩断朝这边涌来的藤蔓,如同暴风。
“伊芙!”
七岛向我伸出手,我则勉强起自己的身体,抓住她的手成功过了房门。队员们不断跟上,唐宵则一剑斩断最后一根触手,随手转了个刀花,以难以捕捉的速度跟上了我们。
“墙上有字!”林鸮大声念着“Everything according to its kind……又是圣经!”
“别管那个,快去看序号!”唐宵一掌打到跟过来的触手上,后者爆成了一堆粉末,“我们没时间了!”
“没有屏幕,不需要回答。”莫炔确认了周围和手表的情况,林鸮以根本看不出是胖子的速度,旋开一个个房门计算数字。
“不能用火烧它们吗——?”白星干脆利落的斩断向我们这边伸来的藤蔓,我应声召唤出火球,向藤蔓扔了过去。
“没用、没用!那藤蔓上有东西……是防火的!”
唐宵挥舞风之利刃的速度越来越快,几乎看不见他手的运动——即使被没收了所有道具,他的身体素质也是我们之中最可怕的。
现在的他——仿佛在发泄着什么一般,挥砍着冲过来的藤蔓。
恐怖的让人不敢接近。
“738……Clear!还是D门!”
我们随着林鸮的喊声通过D门,最后一位的唐宵迅速的关上房门,终于暂时把藤蔓与我们隔离了开来。
“……我想爆粗口,这鬼地方到底怎么了?不是说好没有质数乘方就是安全吗?那个藤蔓是怎么回事啊?改剧情也就算了,尊重原作好吗?就算你是主神你能放出触手怪但我又不是魔法少女?啊?不对……千岛呢?”
林鸮缓解恐惧的吐槽声突然暂停。我默默点起房间的人数。
“她也消失了。”
亚历山大用有些沉闷的声音说出大家都知道的某件事,气氛再次陷入沉默。存在感几乎丧失的张德帅和总裁先生默默的靠在一起,一言不发。
还会消失多少人?
“我们先去其它房间吧……该死!”
还没等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大概是唐宵的残影就从我身边闪过。侧身,扭腰,接着出拳——
砰!
人形的怪物被击飞到墙壁上,倒了下去。
……好厉害!
“这些家伙到底从哪里出现的,这里只有这么大!”
丧尸。
腐烂的人型们从各式各样的地方出现,嘴巴不正常的大张着,连喉咙深处都是密密麻麻的牙齿,让我有点心里发毛。它们的双手大到诡异的地步,仿佛能把人类的头直接包住提起一般。
队员们默默聚集到房间中间,五六只丧尸从旁边围了上来,没有一点死者应有的迟钝。而被唐宵打到墙上的那只丧尸慢慢的爬了起来,似乎毫发无伤。
“再生。”
我提醒道。总计七只丧尸发出怪异的吼叫声,嘴里密集的牙齿有规律的扭动着。唐宵在我们身边以肉眼难以捕捉的速度掠过,一个个击飞了向我们扑来的丧尸。
在狭小的空间里,即使是唐宵也难以完成这件事,但是——
内力强化。
无形的能量奔涌到他的四肢,移动和出拳间,短时间内被强化的身体素质展示的淋漓尽致。
“伊芙,用火!”
甚至不需要他的提醒,我就已经念诵起火焰的咒文。唐宵发出和他的形象不符合的咆哮声,再次击飞了复活的丧尸。他不敢使用别在腰间的风之利刃,如果这些丧尸有感染性,而血液又溅到我们身上的话——
就糟糕了。
“……伊芙!”
内力强化的作用消失,唐宵无法再次击退七只同时扑来的丧尸,队员们拿起手中的武器。
丧尸,再也无法过来了。
我面色苍白的驱动着幻书,让火焰之环绕着我们旋转。那火环如同对我们的一个圈注,把人从怪物中分离开来。恐惧光与热的怪物晕头转向的后退,然后靠到了墙边。
为什么总有一种邓布利多和哈利从阴尸湖里逃脱的既视感?我会从天文塔坠下,就像邓布利多那样吗?
身体有点虚弱,我的眼前仿佛也闪着不祥的绿光。
丧尸的身上燃烧起火焰,瘆人的嘶吼声中,不死的怪物终于化为了灰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