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gm:米津玄师——loser http://music.163.com/song/512359195?userid=114958610
那匹狼最终还是输给了看不到的敌人。
那是灰色的残影,嗤笑着在他眼前晃动着。
枪声响起的瞬间,麻生宙希枝的本能被迅速唤醒了。他扯住身边的浅羽真白,让她躲到自己的身后,他这面对危机时比常人多一分的敏锐使得浅羽伤的并不算重,但他自己却被子弹剥夺了一部分行动力。麻生吃痛地啧了下嘴,侧过身扭头看向子弹出现的方向,他不能让伤口映入自己的眼睛,只得拉着浅羽一起蹲了下来。
和他们一起来的还有法华津伊御,葵五月和之后出声搭话的千言一。看到法华津从眼前走过,麻生向前挪动了一点抓住了他的手臂。“喂,还不清楚情况别过去。”
“别管我。”
麻生沉默了几秒,抓着法华津的手加强了力道,“勇敢和鲁莽可是两回事,说难听点,有赴死的觉悟和不要命也是两回事。”他压低了声音,“而且,我不想因为你的鲁莽而给自己添麻烦。”他这带着威胁的话语里参杂了一点不愿明说的私心,麻生说这话时低着头,故意没有让法华津注意到他略微扭曲的表情,那是回忆起过去灰暗的一角时,内心软弱的某处表露出来的证明。见状法华津没有再轻举妄动,但是千言和葵却不听劝阻地向着暗室走去。麻生腿部的伤口开裂了,他倒吸了口凉气,身边的浅羽真白拿出绷带帮他包了扎。
“谢谢。”
“不,倒不如说应该是我来道谢才对。谢谢你,麻生同学。”
“你也照顾下自己吧,浅羽。”
话音刚落,再次响起来的枪声告诉麻生他不愿意见到的事态还是发生了。跟着赶来的几个人一起进入密室后,他发现还不仅仅是这样。
奥古斯都·泰兰特,成为了新的死者。
狼嘶吼着。它看不到自己的敌人,它只知道他们在前方发出了嘲讽的声音,镣铐再一次束缚了以为自己已经挣脱了他们的狼,它的皮毛被划破了,被血液浸湿的部分长出了石蒜的花朵。
狼仍在挣扎着。
——在他看到千言和葵倒在地上的身影时,那些灰色的碎片一涌而出,占据了麻生的视网膜。他不自觉的喊着葵的名字缓慢地走到她身边,确认对方没有大碍后,他着实地松了一口气。他的拳头捶向了地面,响声并不大,但足以淹没他那句咬着嘴唇说的“可恶”。他站起身,把手机的光照向奥古斯特的尸体又收了回来。眼前的景象和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混在了一起,麻生走到暗室的角落里,扯住自己的额发,试图把那些东西从脑子里揪出去。
这种束手无策的感觉真是最糟糕了。他想。
祭狩御灯到达暗室的时候,看到麻生宙希枝闭着眼睛靠在墙壁上短暂的休息着。他的脸色比平时要苍白些。听到声音麻生立刻睁开眼睛,他脱口而出一句,“你没事吗?”很快他便反应过来已经没有再听到枪声,低下了头,“别在意。”
“我没事哦,脸色不太好呢,要不要先去休息下?”
“我去洗把脸就好了。”他笑着耸耸肩(在祭狩御看来那是勉强的笑容),走过祭狩御身边他伸出手,故意把那灰色的额发揉的有些凌乱,这是他用来转换心情的方法,同时也是一个迟来的回报。祭狩御梳理了几下自己的头发,没有多说什么,他看向了麻生腿部的绷带,开口问道,“麻酱你受伤了?”
“没事,永生帮我处理过了。我马上回来。”说着麻生把双手放在口袋里,离开了暗室。
他打开水龙头,将脸和头发都置于水流之下,冰冷的水流刺激了面部,这份刺激顺着神经传递到了大脑,赶走那些纷乱的东西。麻生并不适合复杂的思考,他只觉得头很疼,然后他抬起头,看着镜子里自己的脸。那副灰暗的表情让他越发觉得不悦,关上水龙头,他扯了扯脸颊,告诉大脑现在不是想那些事情的时候。
那些灰色的东西还是没有放过他,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麻生与绯乃华岁儿擦肩而过。和服的一角在眼前掠过,一时的头脑发热操纵了麻生,他伸出手抓住绯乃华的手腕。“别过去,万一—”
少女被牵制着向后退了一步,同时剩余的凉意刺激了麻生的大脑,他立刻松开手,向绯乃华道了歉,“抱歉,注意安全。”绯乃华抬起头瞥了他一眼,便没有再看麻生的眼睛,略带阴沉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不用您提醒我,我也会去安静的地方渡过裁判前这段躁动的时间。“一滴水滴顺着麻生的头发落到了绯乃华的袖子上,她抬起袖子看了一眼,“阁下还是找块手巾将仪容整理干净吧,任水滴破坏了现场可不好。”接着她便向麻生点头示意,只留下了远去的背影。
麻生回过头又看了少女一眼,“也不用你提醒我。”他小声说着,脱下皮衣简单的揩了揩头发和面部,抬起脸,他的表情里混入了一丝阴冷。
回到暗室后,麻生一言不发的开始了调查,他没开手电,借着围着尸体的一群人(其中也有祭狩御)的灯光勉强看清了暗室的一角,却不慎撞到了人。是雨宫明,受到冲撞力的雨宫身形有些不稳,麻生扯住了他的胳膊让少年能够站定。雨宫抬高眼帘,迎上麻生鲜少的无表情的脸。
“抱歉,我没看路。”
“没事,你还好吗?”
“不好。”麻生垂下头,坦率的承认了自己精神不太对劲的事实,接着他立刻转移了注意力,“我的事无所谓啦,调查要紧。”他打开手机照亮,看到祭狩御从尸体旁边走了过来,两只手里都握着什么东西。祭狩御摊开手心,两只手里各放着一颗糖。接着手机的光,麻生可以看到分别是绿色和黄色包装纸。
“薄荷味和柠檬味的,选一颗?”
“薄荷的。”
祭狩御将绿色的那颗塞在了麻生手里,之后便把黄色的那颗拆开包装吃掉了。麻生有些纳闷的看着他,祭狩御给的糖都是比较刺激性的味道,目的也许是让他恢复精神。得到这样的结论,麻生把薄荷的糖吃了下去(虽然并没有产生多大刺激),把糖纸收到了衣服里。
“麻酱在这里会晕晕乎乎的吧?要不要去其他地方?”
“不看尸体大概就没事,我在这里有人问我问题也方便些吧。”说着麻生对祭狩御点点头,开始在整个暗室里调查起来,祭狩御跟在他的身后。奥古斯都的尸体正对暗室的门,身旁和周围不远处都有血,麻生匆匆地确认了下没有拖动的痕迹,便立刻转移注意,将手机光照向了暗室中央,注意到了什么的祭狩御拍了拍他的肩膀。
“哪里是不是有桌椅啊?”
“是,怎么了?”
“麻酱不觉得那桌椅的风格和这个屋子风格不太符合吗?”闻言麻生向着桌椅的位置走进,的确如祭狩御所说,暗室中央和桌椅和整个空间的气氛不太相近,可能从其他地方搬来的。手机抬高一点,麻生的注意力被一旁的展柜吸引了,他开口叫住了正巧在附近调查的雨宫。
“雨宫君,你之前来过这里吗。”
“嗯。”
“我记得我和葵交谈的时候,听到暗室里传来一声类似玻璃被打破的声音。感觉像是打碎了展柜的玻璃。”
“啊,说起来,这个展柜里之前是有东西的。”
“是被谁拿走了吗?”
听到靠近的脚步声,麻生转过身,看到了脸上带着些无辜神情的幸美澄,“……啊那个,是我拿走了。”并不是过多询问的时机,听到幸美的话麻生想着。他没太在意地继续看着展柜,展柜的玻璃并没有破损的迹象。
“...现在就不问你为什么了,修复玻璃的大概是VON吧。”
“是的,听到我砸碎玻璃的声音它就立马冲进来了……还有什么问题吗?”
“那个东西,现在在哪儿呢?”说完幸美摊开手,一块有明显裂纹的红宝石躺在他的手心,对此麻生并不是特别感兴趣,一旁的雨宫则是露出了难以理解的表情,麻生听到雨宫说“没我什么事我就先离开了。”向他挥了挥手,接着转头看向幸美“收好吧。”
“没有其他问题了吗?”
“没了。”麻生弯下身准备观察地面,听到幸美的问话稍微抬高身体,“那我可以问问麻生君吗?”
“……听说你好像是第一现场发现者……总之是比较早到达现场的,当时发生了枪击?”
“对,和法华津君他们一起来的,然后突然被枪击了。”他指着腿上的绷带,“严格来说我之后才进来这里的,最早进来的是千言和葵。”
“嗯,他们两个等到学裁时自然会有大家来问他们……麻生君看起来好说话一点……我就不寒暄太多了,我想问,当时你们进入的时候是否注意到子弹的方向?”幸美的提问听上去难度极高,麻生苦笑了一下,保持着弯腰的姿势实在是不舒服,于是他直起身来,“这种事我也是第一次遇到,我也没有能看清子弹的视力,不过,当时我是正面对着暗室,受伤的部位是腿正面这里,枪声听着是从暗室发出的。”
“暗室和大厅中央吗……好的,谢谢解答。”幸美说完便一个人陷入了思索,麻生再次低下头,观察地面的时候一个细小的点刺痛了眼睛,虽然光线并不充足,他仍能看清那个颜色是什么。
“唔。”
身后传来祭狩御的声音,“麻酱,怎么了?”,说着少年凑到了他身边。
“那个应该是血...能麻烦你帮我看一下吗,灯君。另外,手借我。”
“好呀,麻酱果然还是去休息一下?逞强可不是好习惯。”麻生借着祭狩御的手站起来,“谢了,不用,还不至于难受到想吐。”
“我看看哦,这里有两个弹痕呢,子弹都在里面周围有一点血。”
“这里是千言他们倒下的地方,血可能是他们的吧。...奥古斯都的尸体前面好像也,有血?”
祭狩御点了点头,用一如既往嬉皮笑脸的表情向麻生打趣道,“麻酱你,虽然一副丢了魂的样子,但意外的记得很清楚呢。”
麻生别过脸捂住了嘴,“...少啰嗦。等等,这么说来,墙那里好像也有弹痕。”,麻生走到墙壁附近用手电筒照亮,在靠近门洞的位置找到了一处弹痕,麻生摸了摸口袋,从皮衣的里侧摸出了随身携带的一把螺丝刀,将子弹从弹痕中取了出来。麻生看着那颗被压扁的子弹,又瞥了眼奥古斯都尸体的方向。他对雨宫挥了挥手,把自己的手机递给了他,“雨宫君。你能帮我去照一下左轮的照片吗,主要是枪口的部分。”
“哈?“雨宫看了眼他手上的子弹,“哦哦,ok。”
麻生闭上眼,试图去寻找一个方法,最后他小声说着”禁书目录“,如他所愿,子弹原本的形状出现在了脑海里。他接过雨宫递过来的手机,对比着左轮的枪口,说道,
“大概能对上,射击我们的恐怕就是这把枪,但还需要知道枪的子弹数目。”
狼叹息着伏在地面上,它想要寻求一个可以反击的时机。于是它紧紧盯着前方的影子,渴望着将其咬杀,撕碎,但它明白,首先它要挣脱锁链。
从暗室出来,麻生特意地没有与祭狩御一起行动,他知道自己仍旧不够清醒,现在的他需要一个安静去处来驱逐纷乱。接着他遇到了奥蕾莉亚,他庆幸自己没有再次撞到人(撞到这么娇小的少女实在是不太好),奥蕾莉亚拿着一条毛巾递给麻生,“啊…麻生同学,伤口还好吗…用这个来包扎一下吧。”
麻生有点局促的看着那双黄色眼睛,“我没事了,但可以用它擦擦脸吗。”
“辛苦了…对不起没帮上忙…”
麻生摇了摇头,“不,奥蕾莉亚,这与你无关,给自己徒增责任感会很累的。…说起来,你来找我是有事要问吗?”
“嗯…听大家说千言同学是之后才和麻生同学你们会合的,你有注意他是从哪个方向来的吗?”奥蕾莉亚低着头,有点怯生生地说着。麻生配合着她稍微下蹲了一点。“我们是在进了展列之间之后才听到她的声音的,那个时候他应该在我们后面,所以没注意到,抱歉。”
“啊没事的!那个还有…好像响起了几次枪声,麻生同学有注意到响声响起的顺序吗,是连续不断的吗?…以及嗯,子弹的高度?”清晰明确的问话让麻生一时有些招架不住,他捂住头想了一会儿才答道,“…子弹声一共是三次,一声,五声,两声。应该都是连续的声音,高度我就实在看不太出来了。”
“啊…居然有这么多次枪声的吗,…说起来,千言同学和五月同学都在暗示倒下了呢,他们是进暗室之前就有受伤吗?”如果那样的话我就不用面对那样一幕了吧,麻生暗自思忖着,摇了摇头,“看上去没有。感觉那个时候他们还挺灵活的。”
“原来如此…真是太危险了…麻生同学也要小心一点!”
他蹲下身,拍了拍奥蕾莉亚的头,“我没事,已经不用担心了。”
狼想着,我一定要扯断锁链。于是狼开始了前进,向着它咬杀的东西前进,有更多的血液和花朵在它身上浮现,而狼只是一味的前进着。它知道,自己有一个渴望到达的终点,那不仅仅是撕碎灰色的影子。
麻生宙希枝看着奥蕾莉亚的背影,在原地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离去。
他知道,他并不想再输的一败涂地。
于是,化作狼的少年开始了反抗。
End
*需要声明的部分:
1.关于受伤,因为在剧情沟通时出现了一些小问题所以真白其实也是受伤了的,但因为被麻生拉开了所以伤的比麻生轻一点。给各位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难很抱歉。
2.依旧是搜查部分很多为个人推理,请以实际提取的言弹为准。
*关于这篇里麻生的心态和态度:首先要向暴君道歉,这个人怎么说呢,并不是个一心为别人着想的大好人,在他心里还是自己的生命大于他人的。只是不喜欢看别人不珍惜生命。所以根源还是自私吧,对不起(跪下
心态的部分,这里有个很微妙的需要区别的概念,麻生的心态更接近于“面对这种情况束手无策很不爽”而不是“因为没拦住人而自责”,这里怎么表达清楚我还想了蛮久的ry
*关于绯乃华:这一段要在日常补充,这俩人咋说呢,有点麻生单方面结的梁子(
*关于狼:因为暂时不能透露麻生心态的真相,所以用了比较抽象的描述,三章会说清楚的!总之每个名词都是比喻(
*另外,取出来的子弹之后又被麻生暴力推回去了((
虽然响应很多但基本都很水,对不起各位(跪下,由于中之人粗心大意导致线索没有表示全造成了多次修改响应,非常抱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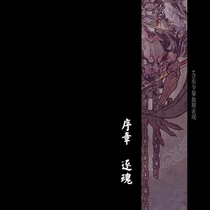
低血糖?
我心里这么想着,用规范的姿势,像照顾平时上课时所用的医疗模拟人一样将五月放平卧倒,但视线在触及五月的面部的时候却感觉哪里不对劲。
心头闪过一丝不祥的预感,我一把抓起五月的手,腕部却丝毫没有属于生者的起伏。
“……葵?”
我感觉自己的心脏一阵紧缩,仿佛全身的血液在一瞬间带着体温都流空了一般。有些木然的、我无视了身体上的疼痛仍旧熟练的按照着平日练习的急救训练行动着。
俯下身将耳朵贴近对方的心口——没有心跳,用手指撑起对方的眼皮观察——瞳孔扩散,耳部没有明显外伤,口鼻处没有一丝气息。
“怎么可能,她没有呼吸了。”
我喃喃自语。
心源性猝死?非心源性猝死?会和之前提到的耳部出血有关联吗?
“……大脑收到了严重的损伤……”
我还在怔愣中,隐隐听到周围有人说出了判断结果,是通过魔法判断出来的吧。
对,有魔法,只要离开裁判场,拿到手术工具,有万能巧手跟禁书目录的帮助就能救回她了,她才刚刚失去意识,来得及。
“平等院玄真,快救人,把我跟葵五月送出去!”
平等院坐在椅子上,手放在那只滑稽可笑的猫身上,纹丝不动,只是抬起眼睛看着我,眼睛里还是那股不知是悲是讽的情绪。
“没有用的,这个人已经完全死亡了。”
死亡了。
冷汗从下巴滑落到地板上,随着轻微不可闻的“啪嗒”声砸出一小圈水痕,我低下头看向自己的手,再看向平躺在地上的五月,明明她刚才还在裁判场上说话,她的皮肤甚至还比我的指尖暖上几分,却告诉我她已经死亡了。
“灯,你的脸色很差,吃点药?”
熟悉的声音唤回了我有些朦胧的意识,我打了一个冷噤,才意识到自己浑身已经被冷汗浸透,胸口的绞痛在提醒我宙希枝说的没错,如果我现在照照镜子,恐怕真的是一副快死了的模样。
我从随身的药瓶里取出药片含下。
“宙希枝,我原本可以救她的。”
我含着药片,没有拿出我一贯的笑容,模糊不清的对着他说话。
“我知道。”
“如果我再聪明一点,再重视一点……”
“我知道。”
他抱住我,像是叹息一样重复着这三个字。
我看不见他的表情,只有带着些颤抖的声音传到我耳中。
与前两个人不同,她是第一个完整的在我面前步向“死亡”的人。
如果我能够在赶到暗房的时候就意识到广播的异常,强行要求检查当时冲进现场的千言一跟葵五月的情况的话,说不定能在五月死亡之前将她抢救回来。
但是我没做到,即使学会了魔法,我也与之前毫无差别。
“超凡人级”这个称号冠在我头上真的是一点都没有错。
如果在场的是妈妈或者是母亲的话,一定不会让她就这样死去的吧。


梭子蟹组海员paro
立志做夜空中最亮的一颗星(不
順便推一下BGM:KOKIA-白雪
你们本不会听到这个故事的,但我还是执意要讲给你们听。之后你们就会知道,如果我想给一个人讲故事的话,那个人是绝对无法拒绝的。但与其说我即将要讲的是一个故事,倒不如说是一个人。
是一个有关于那名叫罗密欧的男人的故事。
时间是星镇节刚过去后的那个周末,我又坐上了出岛的船。其实倒也不是为了要去什么地方,关键的问题,正如我一开始就提到的那般,是罗密欧。
彼时的他在“绿洲号”上当水手,高高大大的个子,直直的眉毛和深深的眼眶,乍看之下显得十分凶恶,我也曾把他当作是个凶神恶煞的家伙,直到某次出船前,我看到他蹲在船舱阴影下沙地上,拎着个亮黄色的星胶桶时,我便笑着凑过去跟他搭话。
“你在这干嘛呀?”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竖起手指凑到嘴边示意我安静。
低下头,我才发现他那幼稚的星胶桶里,装着的是大大小小的沙蟹。
眼看着又有一只壮硕的沙蟹马上就要被他捉住,我忽然动起了坏念头,冲他大喊道:“喂!你是在捉螃蟹吗!”
果不其然,原本就要到手的沙蟹听到我的声音,噌地一声收起钳子,溜溜地躲入了石缝中。
他回头看着我,一对眼睛仍个先前一般,他生气时也顶着一张凶气十足的脸,等到后来我更了解他时,我才知道他压根没在生气。
他的确没在生气,他回头也不过是为了看我一眼。我走到他身边,在他右边蹲了下来,姿势和他一模一样,那傻气的星胶桶就在我脚边不远处。
“这些不是螃蟹,是沙蟹。”
过了半晌他忽然开口答道。
“这种事情无所谓吧,”我耸了耸肩,“你为什么要抓牠们?拿来吃吗?”
“不,我养牠们。”他严肃地说道。
不知怎地,我对于这个回答感到一股没由来的恨意。
于是我站起身来,一脚踢翻了面前的星胶桶。
沙蟹们举着自己小小的钳子,欢呼般在沙地上留下小点的脚印,向着象征着自由幸福的石缝飞奔而去。
如果说这个时候罗密欧显露出哪怕那么一丝的怒意,我想之后的故事恐怕都会连篇改写,等你下一次再听到有关他的故事时,只怕讲述者早已不再是我,今后的故事也都与我无关了。
但他没有生气。认识他十年甚至是更久之后,我不禁怀疑起他究竟是不是永远不会生气,当然前提是,你不要动他的宝贝哈特。
哈特是他养的一只梭子蟹。住在他精心准备的玻璃水缸中,每天他都会把自己的海鲜意面吃得只剩鱿鱼圈,然后把那些鱿鱼圈带回底层船舱,他自己的卧室里,用剪子细心地剪成小段,一点点地喂给哈特吃。
三年前我实在忍受不了他对于哈特的钟情,正当我烧好一大锅水,顺便放下身段切了一菜板的大白菜,用着捞勺往那大玻璃缸里捞哈特的时候,原本说着去码头市场买活鱼的罗密欧竟然两手空空地闯进门来,一把将他心爱的哈特从我罪恶的捞勺下抢救了出来。
两个月之后,哈特死了。
我发誓我什么也没做,只是哈特死后,我试着问过罗密欧要怎么处理尸体,他瞥了一眼静静沉在缸底的哈特,起身烧了一锅水。
他做的梭子蟹炖白菜的味道的确很好。
当然这一切都是后话,当我踢倒他的星胶桶之后,他只是起身捡起了它。不远处传来登船的号声,他转头向我伸出一只沾了沙土的手。
皮箱被他放置在头顶的置物架上,船身摇晃,然后突突地向着离岛的方向开去。
我走出客舱,他正在船头收着麻绳,脚下,透明船体涌现出海面的颜色。星星在波浪间闪烁,这些埋在海水中的宝石只在夜里才闪闪发光,仿佛要依靠那光芒来诉说一段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我靠在甲板的围栏上,低头看着这些星星。
它们是否知晓故事呢?是否会像我对你们那般,将我今后的故事娓娓道来呢?
星星们不说话,我只有叹息。
在更深一点的夜里,罗密欧跟我说了一个故事,一个他从古老的书上看到的,有关他名字的童话。
听罢,我凝视着他的眼睛,说道:“这本可以是个好故事的,可你的声音干巴巴的,糟蹋了这个故事。”
他不置可否。
对于他这种态度,我一向不喜欢。
我有块宝石,被我用红绳串成项链,挂在胸前。说实话那不过是码头集市上二十星石买来的地摊货,但我骗他说这是我母亲留给我的遗物。平日我装作很宝贝它的模样,但每当他的回答让我不甚满意的时候,我就会揪下这项链,发狠地将它丢进茫茫的海水里。
他总是会替我拾回来。夜里,沉在海中的星星很明亮,整片海底清清楚楚地印在他眼中。当他回来的时候,身上总是沾满了星屑,粘在他的衬衣上闪出微弱的光芒。
后来我试探性地问他是否知道那串项链只不过是地摊货,他还是保持着一成不变的低沉声音回答:
“我从不相信你会把宝石堂而皇之地戴出来。”
他这句话说的不完全对,我也是戴过真宝石的人,当然付款的人是罗密欧,我的确从不把花自己钱的宝贝戴出门。
他似乎执意要漂泊在海上,我倒也无所谓,遇见他的前两年我是到哪儿都无所谓的,后来便是跟着他去哪儿都无所谓,这种转变微妙而难以言喻,我也不清楚我为何会做这样的决定。
他和我讲的童话里,决定一直都不是件重要的事情。为什么王子会爱上公主,公主又为什么愿意和王子在夜里私奔,逃向一个一无所有的未来,这些问题从来不会有解答。不论我再听多少这样的故事,也没有一个能解答我的疑惑。
所有的童话里,这些都不过是一瞬间的事。公主可以在见到王子金发的那一刻就爱上王子,尽管她曾见过无数这样的金发,其中还不乏发质尚佳者,但她就是对那王子倾心。
毫无逻辑。
所以当我看到罗密欧第三十三次带着一身星屑和海水从船檐爬上甲板时,我看到那些奇奇怪怪的光芒停留在他身上,看到他那因久未停船而变长的金发被胡乱拨到一边时,我忽然发现自己的眼睛在那该眨眼的瞬间停住了。
这不是一个好预感。
当那沾了水的项链递到我面前时,我迟疑着是否要去接,停顿过两个星刻,他将那湿漉漉的家伙直接套进了我的脖子。
回想当时,我竟然没有当场发飙,这个故事一定有那个地方不正常。
我绝不相信自己竟然会老老实实地接受了一串湿漉漉的项链。
我和老套的童话故事一般,在半路卡壳了。我侧过脸去看他,他却已经拍掉身上的星屑,走回他的岗位了。
童话故事总是戛然而止,我讨厌这样。非常地讨厌,结尾在幸福生活的简单概括之后忽然就停滞了,没有眼泪没有嘶吼,没有痛苦和无眠的夜晚,仿佛所有生活的终点就是那撒满花瓣的婚礼会场。
我讨厌这样。
在嫁给罗密欧的第二年,我从他那该死的船上逃了出去。
我承认我受不了他对于他的宝贝哈特的奇怪执着,我一想起那只梭子蟹就恨不得把它放进大锅里痛快地煮了,或许还配上一些配菜,叫来一些朋友,凑成一桌吃一顿痛快的火锅。
这样想了之后,我突然意识到的问题并不是自己没有办法真正煮了哈特,而是自己并没有朋友。
我似乎只有过一个朋友,后来就成了要与我共度一生的人。
我划着小船奋力靠近岸边,那岸上灯火一片,又是一年星镇节,人们在岸上载歌载舞。
我忽然感受到自己被黑暗包围,这是罗密欧给我讲述的那些童话故事里不曾有过的。那些骄傲的公主会不会也有那么一刻觉得自己被世界所抛弃了?她们会不会在想要痛哭的时候,忽然找不到王子的肩膀?
我不知道。
所以我只能放下桨,看着对岸人声鼎沸,回头,罗密欧的大船沉默地停在我身后。
星星在我身边闪烁,忽明忽暗,一些吞下了星星的透明水母浮在海面上,一抖一抖地在跳着奇怪的舞蹈。
最终我还是划去了岸边。在集市的篝火中我似乎看到了当初那个卖给我廉价宝石的商贩,那是个长着白头发的老人,在火光中跟随人群蹦跳,开心得仿佛回到了童年。
我忽然发现,如果自己的故事里缺了罗密欧的时候,叙述就开始变得平淡乏味。
我只得承认这点,或许当年纪一点点变大,不论你我都必须放下架子去承认一些事物。然后我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追上了罗密欧的大船,一登上甲板迎来的就是哈特的死讯,当天的晚饭就是我盼望已久的梭子蟹炖白菜锅。
我喜欢这种奇妙而不可预测的生活,这让我的故事听起来象是一个童话。
罗密欧的故事或许听来更不像一个童话,他先是个水手,然后在第五十四次替我捡回项链时,他告诉我这条船其实是他爸爸名下的。
这烂俗的发展。
于是当天晚上他又帮我捡了三次项链,他捡一次我扔一次,直至天色大亮,日光照耀下他再看不清海底。
从此他再没有替我捡过项链,那二十星石的便宜货正奢侈地躺在这片充满星光的海中,悄然伪装成贵妇雪白脖颈上的宝石,诱骗着下一个傻瓜去替某个姑娘拾回它。
我想这个故事应当告一段落了,这颗星星上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甚至连最条理不清的童话都不愿在此发生。
但它毕竟是一颗拥有罗密欧的星星,因此它闪耀的光远远超过我眼中其他的星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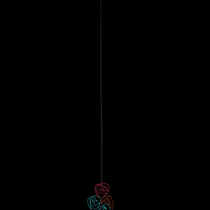


◎字数:大概2k
◎看起来响应了一群人,其实全程只有四个人在讲话。
Chapter .00
蓝德尔带着一本《从现代咒语看古代魔文》坐进了空荡荡的车厢,他的同伴还没有上车。
稍早的时候,蓝德尔托运了行李,在那里他与克劳提茨打了个照面,没有过多的交流,只是点头示意。至于菲尼克斯和兰斯,目前他还没有见到他们。
蓝德尔静心在车厢内等待,他翻开这本昨天刚出版的新书,第一页写着作者:艾利奥特·威尔斯。
这个名字是从同为拉文克劳学院的鹤鸣学长那里听说的,似乎是他曾经的室友,在校期间总是痴醉于古老的魔文。甚至于他在宿舍有一个专门的书架,上面塞满了他自己在各种旧书店淘到的古老书籍。最终,研究魔文成为了他的工作,算是梦想成真。
他记得那是假期开始的前几天,在图书馆寻找与古代魔文相关的书籍时,他巧遇了鹤鸣。
“如果你想学习古代魔文,那我十分推荐你去阅读一下艾利奥特·威尔斯的古代魔文学论文。”
鹤鸣带着温和的笑容提议道,“他在学校的时候就总是研究这些,我想图书馆的档案室里就能找到,你可以在馆内翻阅,但不能借走。”
之后他确实阅读了艾利奥特的论文,那是一篇关于古代魔文历史演变过程的文章,写的十分严谨且含有大量的实例而不仅仅是猜测。甚至有一部分举例中他描述了如何解读运用楔形文字改写的魔文,也就是说这位在校生曾经凭自己的调查与研究破译了一部分人类最古老的文字。蓝德尔也借此对魔文有了诸多全新的理解。
后来蓝德尔试着打探这位毕业生的消息,得知他的第一本书即将在8月下旬时出版,他当然在第一时间购入。
蓝德尔阅读完前言的时候,克劳提茨已经带着一些零食坐在他的对面。兰斯和菲尼克斯还没有来,车厢在的过道充斥着新生的自我介绍与高年级们过完假期后的寒虚问暖。无论是蓝德尔或是克劳提茨,这都是不必要的过程,毕竟与大部分学生不同的是,他们四个人几乎整个假期都在一起,且每年都是如此。
“你见到菲尼克斯他们了吗?”
蓝德尔接过克劳提茨递来的南瓜汁,随意地开口。
“大概快来了吧。”
克劳提茨看了看时间,“我想昨晚我们离开后,他们又玩了很久。”
“我想也是。如果有噼啪爆炸牌大赛,他们绝对会包揽前二。”
蓝德尔说得煞有其事。天知道昨晚的狂欢最后变成了什么,他们四个原先只是普通的在玩巫师与地下城,后来不知道是因为谁先提了一句,兰斯与菲尼克斯便较上了劲,他们以一个学期的黄油啤酒为赌注开始噼啪爆炸牌的比拼。而蓝德尔和克劳提茨为了不被波及,便默契又狡猾地找了个借口先一步撤退。
“希望他们不要睡过头。”
克劳提茨拆开一包薯片放进嘴里,蓝德尔听了也没有回答,重新埋头于阅读。车厢内只剩下咀嚼薯片的声音,显然,他们看起来都并非真的在担心他们的青梅竹马是否会迟到。
最终在蓝德尔阅读到第五页的时候车厢被打开,一绿一红的身影走进来。而当他们看到菲尼克斯一脸得意洋洋时,他们立刻明白兰斯将负责菲尼克斯整个学期的黄油啤酒。
四人聚首的不稍一会儿后,蓝德尔的学长瑞克·戴斯蒙德便举着一本《量子场论》快乐地找了过来,但遗憾的是就在他准备踏入车厢门时,菲尼克斯那像是要杀人的绿眼睛已经直直地瞪了过去。接受到这刺骨地凝视,瑞克立刻知趣地打着哈哈在门口尴尬地转了一圈离开了。
“哼哼,麻瓜的破烂……真是不可理喻。”
菲尼克斯直到瑞克消失在他的视野中才转过头来,他不满地发出抱怨,语气中充满了不屑,“我真是服了。他可是一个纯血。真不明白,他怎么会如此痴迷那种东西?还有你,蓝德尔,你也一样。我劝你最好离他远一点,麻瓜的知识?那就像曼德拉草的叫声一样恶心。”
“但我却不这么认为。”
蓝德尔早就习惯了菲尼克斯的这种偏激的态度,他用轻松的心情去回答他,“戴斯蒙德知道麻瓜科学里有什么是正确的,他试着将那些也作用在魔法上。这是一个大胆的想法,而且如果成功,将会是物理学上的……”
他开始他的长篇大论之前,菲尼克斯立刻打断他的话:“麻瓜没有正确的东西。蓝德尔,你的脑袋里难道长得都是南瓜吗?麻瓜的理论全是错的,所以那些泥巴种来学魔法,而不是去学什么物理。”
“但是算术占卜中就有运用到几何学,图形对算术占卜起到重大的运用,而如果我们能了解几何学,那么这门课程也同样会得到很大的进步。你会看得更透彻。”
“我不需要看得多透彻,我只需要在O.W.L考试中这门课程能得到E及以上。”
“……菲尼克斯,麻瓜界有一句俗语。”
蓝德尔看着菲尼克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果你痛恨麻瓜的东西,就更应该去了解它们。”
然后他们的对话到此为止,气氛变得有一丝尴尬。当他们提到麻瓜物品的时候,气氛总是会变得尴尬,这是近几年四人,或者说蓝德尔与菲尼克斯之间的小矛盾。所幸的是,他们都从未真的因为麻瓜物品而对对方有什么意见。在这方面,他们一向分的很清楚,针对的是事物,而绝非人。他们永远不可能为了无聊的事情发生争吵,对此四人都心知肚明。
“说起来,来的路上我见到了莱茵,我看到他的猫差点被他的弟弟丢出窗外。”
兰斯不经意地打破尴尬,菲尼克斯挑了挑眉毛,他们是一起上车的,这说明他也目睹了那场可怕的谋杀,
“利昂真的很讨厌猫,他领着小家伙的后颈还要戴着手套。”
“可怜的小家伙,我希望你的室友没有真的那么做。”
克劳提茨看向菲尼克斯,利昂·赫克斯利是他的室友,而正巧,他的胞胎兄弟莱茵·赫克斯利又是兰斯的室友。
“当然没有。那只是个恐吓。他讨厌一切有毛的动物。我的灰烬也从不去招惹他,但他哥哥的小短腿,真不知道那只小毛球是怎么想的?它竟然胆敢在利昂的校服上打滚,落下一身的白毛。”
“至于莱茵,他喊着猫是无辜的,冲上去想要抢回来,鉴于利昂不是真的要扔,所以事情简单的解决了。”
兰斯边说边拆开一盒巧克力蛙时,那只深褐色的青蛙跳了出来,被克劳提茨迅速地抓在手里,又一脸嫌恶地丢进兰斯嘴里,后者不雅地咀嚼着手掌大的巧克力蛙向克劳提茨道谢。
“那只曼赤肯看起来分明挺乖巧,却总想着要向其他的猫示威,没想到这会儿连人也不放过。”
为自己沾上巧克力的手施展清洁一新后,克劳提茨看了看腕表,“喔,是时候发车了。”
指针落在11点整的时候,果然火车的汽笛响起,车厢开始晃动起来——终于,霍格沃茨特快列车今年也出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