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之计在于晨。
微风轻拂,唤醒浅眠的生灵。白色的毛团抖动耳朵,踏出栖身的三角体,循着空中气味跨越众多障碍,轻巧地落在餐桌上。厨房中,以鲣鱼、干贝熬制的粥散发诱人香气,早早起床的饲主正将粥舀入碗中,配以喜爱的渍物。味增汤则取用最简单的豆腐,撒上些许香葱,另有一碟高汤蛋卷,便是一顿丰盛的早餐。当然,还有猫先生最爱的猫粮。
堀江昶入学御凉亭学园已有一个多月。一个月的时间足够他适应新环境,形成新的生活习惯。自从国三视力骤减,告别道场,堀江昶便将清晨社团训练的时间改为晨跑,早早离开家中,归家用餐时,父亲也已经出门。只是,如今的公寓高楼不比京都町家,晨跑再归家的习惯显然过于繁琐。短暂的思忖后,堀江昶只得改变作息。先在家用过早餐,和猫先生一同出门,在御凉亭公园散步当作晨练,再由后门入校。动线清晰明了。
今日也不例外。
在楼下便利店买过一份鲜牛乳,一人一猫步入公园。如雪的樱花早已凋谢,唯有大片绿荫遮挡初夏的阳光。裹在冬季制服下的皮肤表层有些微热,少年不知不觉偏向树荫行走,不经意扫过一旁漾着微波的湖。
夏日的水,从没有什么好的回忆。
少年蓦地停住脚,跟随的幼猫轻叫一声,绯红的瞳看向少年,疑惑地摇动尾巴。少年遥望那池水波,轻轻开口:“我们离水远些吧。”猫先生没有追究,只是踏着优雅的步伐,跟随人类彻底躲入树影之中。
“嗯……还是不对。”异色瞳的教师点点头,手中红笔旋转一圈,在空中划出一道饱满的弧线,准确点在了堀江昶的笔记本上。一旁的少年也仿佛被笔尖点住,本就笔直的脊背又挺了挺。
歌利老师交叠的双腿向前伸直,带动身体前倾更加靠近学生。淡色发辫随着他摇摆,停滞的笔尖再次开始滑动,将少年思路出现偏差的位置一一勾画出来,分别进行讲解。少年听得认真,平放膝头的手指不知不觉跟随老师一笔一动,描摹出同样的公式。
放课后无人的教室,年轻的教师与同样年轻的学生,这样的一对一教学已经不是第一次。
堀江昶还记得歌利老师初次踏入一年A班,长外套衣摆飘摇,衬得人更小,却又有种莫名的气场。全班同学都在这种交错的观感中暂时性失语,愈发寂静的教室中,年轻的教师在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开始授课,短短几句却将大家的注意力牢牢抓住。
高中的知识较国中更为复杂,歌利老师的讲解却是浅显易懂,理解起来并不困难。并且,歌利老师总是从大家已有的知识引出新的知识点,协助建立完整的知识体系,形成关联。各方面而言,歌利老师都是一名优秀的教师。
正因如此,堀江昶才会更加愧疚。拥有如此优秀的教师,仍无法顺利掌握课业,问题只会出在他身上。事实上,早在国中、甚至更早些,堀江昶便发现他于理科毫无天赋。无法顺利掌握全部课业的他是残次品,这一事实,他也早已接受。
不过,歌利老师并没有放弃这样的他。在某个午后,堀江昶前往办公室请教课上未能理解之处时,解惑完毕的老师询问他,若是时间允许,要不要进行一对一的单独指导。
堀江昶不是第一次前往办公室询问,歌利老师也不是第一个为他答疑之人。只是那一刻,歌利老师与以往的老师们清晰的剥离开来。没有在解惑后推开笔记本,没有笑着感慨:“其实你不笨,只是没有你哥哥聪明。”
不仅歌利老师,御凉亭的每一位老师,都不曾这般说过。
“堀江?”少年回过神,老师清澈的双眼正看着他,歪着头,颇为不解。堀江昶收敛心神,道歉:“非常抱歉,有点走神。”
“唔。”浅色发辫摆动,少年身形的教师回头看了看笔记本,思索片刻,点点头,再次看向堀江昶,“今天就先到这里吧。”
“诶?”很快,少年便反应过来。歌利老师误认为他的分心是由于知识过多,暂时无法吸收所导致。错误,却温柔。
“我先告辞了……今天真的十分抱歉。”行至教室门前,少年转身行礼,再度道歉。
“嗯……回去路上小心。”老师摆摆手,低下头继续收拾东西。
歌利老师恐怕无法理解他为何总是道歉,甚至很多时候连他自己都不清楚为什么,可以肯定的是,他确实心存歉意。
究竟是何时养成的习惯,早已记不清了。
“哥哥,这道题我不太懂,可以麻烦你吗?”
“嗯,我看看。”温柔的兄长,只需扫一眼题目便能轻易解出,“这道题不难,只要把这个公式代入,再这样。”和父亲一样有力的手指握住他的手,带着他在课本上写下过程,“看,这样就可以了。”
“谢谢哥哥……那,这道题呢?”
“我看看……嗯?”兄长意外地看着他,“这道题和刚才那道思路一样啊。阿昶不会吗?”
“不……”未出口的话语消失在喉间,少年低下头,“抱歉。”
“阿昶不必道歉的,是我没讲明白。来,我们再来一遍。”兄长摆摆手,再次握住他的手,握紧他的笔。
兄长不会错。错的人,是他。
从回忆的泥淖拔足而出,堀江昶这才意识到,不知不觉间他竟走到了运动场。正值部活,球场中都有部员挥洒汗水,指导教师在旁点拨,恰是青春华章。
堀江昶在铁丝网外驻足,凝视那些奋力练习的身影。他喜欢人们努力的模样,虽然付出不一定有所收获,但不努力一定什么也不会拥有。他不是哥哥,没有那样的天赋,能够做的唯有努力、努力、再努力。期盼着或许有那么一天,他的付出能够有所收获。
每当他自我质疑,怀疑是否真的会有那一天来临时,就会看看他人努力的模样,激励自我。有这么多人都在努力,如果他就此停下脚步,还能得到什么呢。
心底似乎涌上一些力量,堀江昶轻拍双颊,一定要振作起来。正准备迈动双腿回家时,耳朵似乎捕捉到了奇怪的响动。
是水声。
没什么可奇怪的,网球场相邻便是泳池。然而若他没有记错,御凉亭并没有游泳部。准确的说,是早已废部。那么,如今的水声又是因谁而起呢?
初夏傍晚的一时兴起,堀江昶转变了前行的方向。
走得愈近,声音愈清晰。
水面漾起阵阵涟漪,水雾翻腾,一道身影拔然而起。水珠顺着肌理滚落,洇出一道道漂亮的肌肉线条,每一根汗毛都泛着淡金色泽。即便以男性的眼光看,这也是一具优美的躯体。他划水来到泳池边沿,摘下泳帽的刹那,短发折射光辉,耀眼夺目。沿梯子攀上岸,突然毫无预兆地回过头来。
被那双眼凝视,堀江昶这才意识到,他盯着对方看得时间似乎长了些。未待他思量好如何开口,对方已爽朗一笑:“你也是来游泳的?”他拎着泳帽泳镜走近,亲切友好。堀江昶下意识摇头:“不……算是路过吧。”虽说是好奇游泳之人,特意路过。
少年点点头,本该结束的话题却没有中断:“要不要加入游泳社?”
……
…………
………………?
“游泳社?”堀江昶一时愣怔。暂且不提前后话题的关联度,仔细翻阅记忆相簿,他确实没有在社团招新时见到这一社团。
“御凉亭的游泳社似乎作废了,我正准备重建。”少年适时道。
原来如此。堀江昶了然。只是解除这一疑惑,下一个问题又蹦了出来。他几乎是无法遏制的,开始计算重建社团需要的精力、人力、物力。最重要的是,需要个人魅力。抬头看向眼前人,对方似乎对他的沉默毫不在意,四目相对,再度粲然一笑,露出一口白牙。
似乎有这个基础。堀江昶沉默,脑海不期然闪过一抹身影。
与他不同,夺目,耀眼,璀璀生辉。
远比他更适合“昶”的名字,远比他更能担起这个名字所背负的期望。
“你会游泳吗?”或许是他沉默太久,对面的人终于再度开口,鲜艳的眸有波光层层漾开。
“会。”堀江昶下意识答道。
“有加入社团吗?”“文学社。”
“没有运动社?”“没有。”
“太好了,加入游泳社吧!”“……嗯?”总觉得哪里不太对。
不过不能这样了。堀江昶闭眼,甩去心头那抹不断浮动的身影,定心后再度开口:“请问现在社团有几个人?”没记错的话,社团要有五名成员才能成立。
对方的回答也极为爽快:“算上我已经有两个了!”换言之,除了他只有一人?望着那阳光下仿佛闪闪发亮的人,堀江昶对他那积极向上的心态敬佩不已。
“如果你加入就有三个人了。”上扬的声调彰显了对方的好心情。难道因为在泳池相遇,才让他如此执着?
堀江昶百思不得其解。
“即便我加入,也还有两个人才能成立。请问你有人选吗?”“嗯?没有。”“部室呢?”“在这附近。”白发人指了指不远处的独栋建筑,“不过我去看过,基本都废了,必须彻底扫除才行。”“……”“啊我邀请了指导老师哦!有指导老师!”
一言以蔽之,百废待兴。
堀江昶叹息,扶稳镜框,直视那双发亮的眼:“请问,这样的条件下,你有什么自信能够重建游泳社?”部室荒废,人员不齐,没有人脉,没有资金。看不见光明的未来,唯有沉重的现实。
那人轻松一笑,扛在肩上的担子化为轻烟飞散。他面向泳池,展开双臂:“因为我们有这——么大的泳池啊!”波光粼粼,面向阳光的少年却比太阳更加夺目,令周围的一切黯然失色。
他回过头,眼眸璀璨:“这可是本市最大的校园泳池!只是看着就令人澎湃不已!心潮涌动想要扎进去游个痛快啊!怎么可能没人来嘛。”
他的声音过于轻松,语调过于雀跃,以至于仅仅是旁观者的堀江昶也不禁染上几分雀跃,或许……重建一个社团,真的没有他想象中那样困难。
“要不要一起游泳?”少年转过身,挥动手中的泳具。
“我……试试看。”堀江昶轻抿嘴唇,即便心动,他也还有另一个问题。“请问,这里有多余的泳裤吗?”
“嗯?不清楚诶。去体育馆找体育老师借嘛!”“不,那个……size……”“肯定有学生泳裤的!”爽朗的声音盖过堀江昶微弱的疑问,霎时间,心头那抹犹豫也被一扫而空。总之,先去借泳裤吧。
堀江昶不会游泳。他的时间大多贡献给了学习,贡献给了他永远学不懂的理科,为了追上兄长的脚步,为了不辜负父亲的期待。
“阿昶,这个假期部里组织去海边,一起来吧?”国中某个假日前夕,兄长这样说道。
“弓道部吗?不要因为贪玩耽误训练,学习也不能落下。”父亲先他一步道。兄长笑答:“您放心,去海边可不仅是为了玩乐,训练计划早已安排妥当,部里的大家都很期待呢。阿昶也很用功,训练和学业都不会落下的。对吧,阿昶?”
“……嗯。我不会耽误训练的,请您放心。”面对兄长的笑容,父亲的训诫,堀江昶怎么也说不出,他根本不会游泳。
兄长没有特别学习过,看那笑容,想必早已掌握了这一技能。部长和部员们想必也从未怀疑兄长是否会游泳。
他是兄长的弟弟,是血脉相连的亲属。必须要会才可以。必须掌握这些技能,才能不愧为兄长的弟弟。同为兄弟,兄长会,他不可能不会。
必须掌握才可以。
学校泳池率先否决,太过显眼一定会被同学发现,被兄长知晓进而指导,他不希望任何人得知此事,不希望被任何人发现。不远处倒是有一家健身馆附带泳池,但是父亲经常去。离家不远,也有被邻居发现的可能。顾虑太多,堀江昶只得在周末借口锻炼,搭电车前往远处的游泳馆。紧赶慢赶,总算在弓道部活动来临前勉强掌握。
部长精挑细选,竟选出了一片游人不多,风景秀丽之处。抵达当日,在旅馆放好行李,一行人便吵嚷着前往海滩。兄长在前方被大家簇拥,堀江昶放慢脚步,落在后面欣赏风景。他不似兄长,总能游刃有余处理好人际。相比众星拱月般的追捧,他更愿独自一人,至少清静。
然而生活总有那么些不如意。
看着那些手捧梳妆用品围绕他的少女如狼似虎的眼神,堀江昶几次深呼吸,总算按捺住逃离的冲动,乖乖闭眼任由那些人倒腾他的长发,替他装进泳帽。
而待这一切完毕,没了为他梳理长发的乐趣,少女们很快散开,继续簇拥至兄长身畔。
堀江昶松了口气。部长与年长的部员们陆续下水,岸上余下的人越来越少。他不想引人瞩目,也只得下了水。海水与泳池的水终归不同,适应一番后,与人群保持距离独自划水也有一些乐趣。
只可惜,世事难料。
一秒前还在寻找欣赏海面倒影最佳高度的堀江昶想不到后一秒就会被沙滩排球砸到头,更想不到就在他失去平衡的刹那,腿部一阵抽搐。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他一头扎进海里时,抽筋了。
浅海水面下并没有纪录片中深海的幽深可怖,然而当水流从面部灌入体内,大脑的空茫与内心的恐惧仍令他惊慌失措。越想挣扎,越是动弹不得。偏偏五感格外清晰。他能听到不远处部员们的嬉笑,感受到同学取排球时水流的推动,甚至看到海水折射的他的倒影。
但这不是海面,那恐怕不是倒影,而是他的幻觉。
感知时间变得艰难,他不确定过去了多久,也不知道他到底向海面下扎了多深,只有大脑在最初的慌乱后,逐渐空茫一片。
若是那时,没有人撞上他,偏巧让他借此稳住身体,若是那人没有意识到他腿部抽筋,扶他上了岸,等到兄长和其他人发现,他或许早已消失不见。
彻底消失。
待大家玩得尽兴,上岸却发现他长发尽湿,正用毛巾擦拭时,面对兄长和同伴们的疑惑,堀江昶只是平静道:“不小心散开了。”
那之后,他再没下过水。
向体育老师道过谢,换好泳裤的堀江昶与少年再度来到泳池旁。剪了短发果然轻松,戴泳帽不再艰难。在岸上充分活动过身体,堀江昶下了水。
皮肤接触微凉水面激起一片战栗,全身泡入后反而好了许多。堀江昶直视前方,深呼吸后匀速吐出,戴上泳镜。
目之所及湛蓝清亮,与那一年的海面略有不同,却又在眼前交替闪现。蹬水的刹那,刺痛感从腿部传来。
心理作用而已。堀江昶自我安慰,集中精神,稳住呼吸。不远处却传来清亮的嗓音:“姿势不错嘛!唔,细节处还有发展空间,不过会游已经很棒了!怎么样,这么大的泳池游起来是不是很爽?加入游泳社吧!”
眼前的阴影不知何时开始消散,清亮的蓝再度出现。浸泡在水中,心情都轻松不少。
堀江昶游了一个来回,回到岸边时,少年正等在一旁,待他上岸便冲了过来,竖起拇指:“同学,要不要加入游泳社,尽情享受本市最大的校园泳池!”
堀江昶后退一步。不知是不是没戴眼镜,视线模糊的缘故,他竟然看到闪亮的星星不断从对方身上迸射,背景是耀眼的光芒。
一定是用眼过度。堀江昶双眼微眯试图聚焦,对着视野中白得发亮的人形道:“那个……请问你是……?”过了这么久,他居然忘记问对方姓名!
“啊,忘记自我介绍了!”少年也是恍然大悟,摸了摸头发,“山崎仁,一年C班!怎么样,要不要加入游泳社?”
“一年A班,堀江昶。”虽然现在的衣着有些失礼,堀江昶还是行礼道,“若是初学者的我也可以……就请让我加入游泳社吧。”
“当然可以!是个人就行!”山崎君非常开心,虽然说的话有些奇怪。
被那份活力感染,堀江昶不禁笑了起来。国中末,由于视力缘故彻底告别道场,而现在,或许他可以换一种方式继续锻炼。
只可惜猫先生不喜欢水。
着装整齐与山崎君告别,看到御凉亭公园门前翘首等待他的猫咪时,堀江昶不禁如此想。
“猫先生,今晚洗澡好吗?”“喵——”“不好啊……那我们换一天。”
——————
八月份的五月章orz感谢不嫌弃让我写的老师和同学……!响应打扰了!
果然工作才是督促码字的利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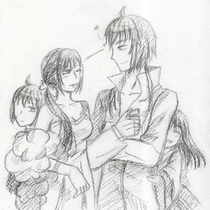
法官宣读判决时法庭里响起了几声稀疏的掌声,更多人没有做出反应——受到指名在周六上午出席法庭参加无甚紧要的案件审理对于大部分人是不那么情愿的事,陪审团们陆续沉默起身离开座位。真是运气最差的一天,两周前我也以为事情已经是最糟了,费尔南多不无自嘲地低声自语。
那时他将身体陷进沙发椅靠背,神情专注地看面前的屏幕反复播放一段前后长约三分钟的录像。不甚清晰的影像前半分钟完全是静止与杂音,夜色里白色外墙的三层建筑毫无变化,连门前的梧桐枝叶也不曾被风吹动,只有右上角显示时间的数字持续跳跃。第三十五秒视频中传来了年轻男人的笑声,随后一楼最左侧房间的窗户打开了。一个,两个,三个年轻男人大声吵闹撑起窗台跳到外面,最后的男人有着引人注目的长发,炫技般只用单手抓住窗棂,结果重心不稳跌回房间里。一瞬间录像中听得到令人心悸的异样巨响,而盖过它的男人们的笑声更令人不快一些。三人说笑着走到摄像头正下方,仔细分辨还能听清楚对话里的下流笑话。长发男人伸出手理了理头发,效果不佳的胶片摄影机依旧忠实地记录了那一刻他露出的脸和左臂的奇怪纹身。从男人出现在镜头下方看得到五官到伸出左手整理刘海之间几秒的场景被单独打印出来,此刻正和几份另外的文书一同摆在费尔南多面前的橡木桌面上。我可能还是该把头发扎起来,说不定好看一点,他盯着资料思绪游离地想。
“……洛佩斯先生。”
费尔南多努力将视线从屏幕撕开。办公桌对面的中年女性单手轻叩桌面,另一只手抬起钢笔抵在金丝眼镜镜脚。坐在她旁边的男性校监每隔几分钟就会神经质地举起一只手在面前痉挛般左右摆来摆去,像是想要把他与费尔南多共同呼吸过的空气也从面前赶开。费尔南多没那么热爱他读的金融学,比起学业更喜欢把时间花在爵士乐和交友上,因此对学校状况知之甚少。在这个下午之前费尔南多一次也没有留意过校长的长相,甚至记不清她的全名,就像他读了两年还不知道琴房对面的教学楼外安装了摄像头一样。
“对于你上周六带无业游民闯入学校琴房并且造成了破坏这件事,还有什么要解释吗。”
费尔南多扯了扯嘴角。是乐队,最后他订正。
费尔南多所在的乐队的组建者与核心是二十七岁的吉他手兼主唱,瘦削的金发男人原本学习古典乐,今年春天辞去了小学音乐教师一职,现在每天在破陋街区的出租公寓里填词谱曲,只靠此前的微薄积蓄维持生计。乐队的发展遭遇了很多问题,技术是一方面,例如四个月过去主唱终于在上周学会了如何顺利地在一小节之内弹奏两个和弦,场地则是另一方面。最初他们在主唱家中排练时门被推开了,住在对面的年轻情侣神情恍惚地端着啤酒走进房间与他们干杯,随后口齿不清地坐在地上自顾自拍手伴唱,他们离开后几个小时屋内还弥散着挥之不去的大麻气味;另一个晚上他们找了僻静的河沿排练,在桥洞露宿的流浪汉追打他们跑出去半英里远。“要是下次再来鬼叫打扰我睡觉,老子就要把这东西插进你们的屁股里。”蓬头垢面的老人挥舞手中球棒用尖细的嗓音朝他们的背影喊着。费尔南多没用太久就想起了校庆时见过一次、罕有人问迹的钢琴房。
他拿着校长推过的打印清单离开了办公室。列表很长,详尽地写着费尔南多违法校规的具体条目、音乐教室被损坏的物品和校方要求得到的赔偿,页尾是手写的最后缴付罚金期限。那行字的墨水还没有干。时间是一周后,费尔南多先生,校长扶了扶眼镜做最后宣言,无法按时交齐的话将对您退学处理。费尔南多觉得清单中诸如地毯磨损和墙纸刮花之类的事项完全是一向对琴房疏于管理的校方趁机讹诈,然而最醒目也最没有争议的一项——甚至索求金额的数字比上下都长出几位——是费尔南多从窗台跌落时击中的三角钢琴,甚至早在事发当晚他就已经意识到自己对那乐器造成了何等损坏。
费尔南多不知道要从哪里凑齐这笔钱,他与朋友们从衣柜底层抽出冬季大衣逐一翻找口袋把摸到的每个美分堆放在一起,总数停留在请求款项的三分之一。他沿街敲开每家商户的门询问是否招聘工资日结的临时工,收效甚微,甚至不需要使用什么数学知识就能算出微薄的薪酬无法在一周之内攒足差额。第四天的下午他一无所获推开家门,扑面而来令人生理性剧烈头痛的呛鼻腐烂臭味,费尔南多一瞬间警惕地回想木工斧放置的地点想要抓它防身。电视的声音盖过了费尔南多的问询,喊过几次后他坐在地毯上的十四岁弟弟才终于把音量调小从《芝麻街》移开视线。男孩打湿的头发外面层层叠叠地裹着塑料布,费尔南多朝他打量了几次,醒悟到那就是气味的源头。
“大家都笑我的卷发太娘娘腔了,我想把头发弄直。”弟弟解释,“哥,别告诉妈妈。”
是氨水,费尔南多想,读中学时他在化学实验里用过一次。老师是个姓李比希的严苛古板德国男人,因为日益推后的发际线被一部分学生起了外号叫圆底烧瓶。他在最热的夏天里也坚持穿长袖衬衫打好领带上课,讲话时语调毫无起伏,更有志于科学的那部分同学会评价李比希讲解清晰,费尔南多则每节课从头到尾都全力与困意战斗——作战失败的次数比起成功要更多一些,而在他的课上打磕睡会换来短则五分钟长则整节课的罚站。溶液酸碱性的那节实验课是在周五,途中他试着把半试管的指示剂直接倒进装有一升碱液的试剂瓶里,疑惑为什么玻璃瓶中液体没能像刚才的演示一样变成鲜艳粉红色想要再加更多时,身后嘴角轻微抽动的李比希老师提起他的衣领,将他丢出了实验室门外。第二周李比希没有出现,对于这件事校方没有做出解释,而学生们最初的分歧只存在于德裔教师猝死的原因究竟是心脏病还是脑溢血或是交通事故。半个月过去终于有细心人发现了德国人的消息,法庭的判决印在本地日报的中缝里,白纸铅字无需置疑:贾森•李比希,男,中学教师,在自家地下室制毒被判决。公告简练扼要,学生们一片愕然,没有人能顺利把阴郁的化学教师与制毒者联系到一起——得知他做这种事却也难说意外。费尔南多回想和他的中学同学们传看报纸的下午,海洛因大概可以卖很多钱吧。
他推开窗户,夏日的热度与邻居割草机的发动机噪音一起涌进房间。身后没得到回应的弟弟站起身跟在后面,还在继续要费尔南多答应不要把自己拉直头发的事情告诉妈妈。
“不用我告诉她,妈回来自己会看到的,你完了。”
弟弟陷入了迟来的慌乱之中。
附近三个街区的居民都宣称那天夜里听到了安德森家传来的尖叫声。城市在八月十七日再次发生了一起盗窃未遂案,午夜三点安德森家的小女儿从梦中醒来,口渴异常,穿着睡衣走到客厅喝水,与正在那里翻找书柜寻觅财物的陌生年轻男人视线相交。下一秒女孩发出了足以让聋子也有所警觉的大喊。缝线的医生说女孩运气不差,入侵者试图逃跑时挥舞餐椅与镇纸造成的伤口再偏几英寸就会击中动脉。窃贼证据确凿人赃并获,连作案动机都不需要花太多时间调查,法院只花了一周多就给出了判决结果。费尔南多•洛佩斯,20岁,以盗窃、非法入侵、人身伤害三项罪名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去往监狱路上的狱警之一是个健谈的年轻人(对于心情不佳的费尔南多来说有些过于健谈了),看起来没比费尔南多大几岁,来回翻看费尔南多的判决书和庭审记录追问细节。费尔南多没有说必要回答之外的话,也努力维持着不做出什么表情。他坚定地相信现下境遇只是诸多运气不佳的堆叠,而自己终究和“那些”犯罪者是不一样的,甚至只要那天晚上离开琴房时自己更小心一点后来的一切就不会发生。最终那名狱警耸了耸肩。
“够倒霉的。你这样的人被送来戴维尔监狱。”
另外两名的狱警不无斥责地看了看他,想来是认为身为警察他对囚犯讲得太多了。那之后车厢重回安静之中,费尔南多胡乱想着此前扫过几眼的社会新闻里提及的减刑案例。他一言不发地被狱警押送下车走向监狱大门,自认这种沉默可以维护住一些什么——无论它是否真的能够做到,费尔南多的微小努力也还是不可避免地终结于目光扫到视线尽头监狱走廊里突然停下脚步的中年囚犯一刻。
“怎么是你。”
如果费尔南多刚才还有所迟疑的话,另一端率先开口的的囚犯也已经扫清了他的全部疑虑。他嘴角扯动,最终无法抑制地放声大笑起来,见多识广的狱警也难以预料到面前的情况,此前善谈的年轻人更是再次翻看起费尔南多的资料确认新送来的囚犯的确没有患上任何精神疾病——虽然未加确诊的隐疾在入狱的巨大冲击下突然发作也合情合理。几秒过去经验更丰富的警员终于有所行动,上前责令费尔南多让他收敛一点。中年囚犯说出口的名字被狱警的呵责与费尔南多神经质的大笑共同淹没,因而没有传达到任何人耳中。
“费尔南多•洛佩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