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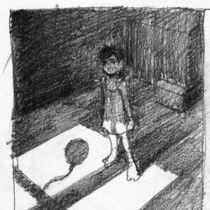

☆事到如今还在赏花,察觉到死亡的气息
☆在此郑重感谢十文字 政臣先生(
养虺成蛇。
松井家的一楼是以皮薄馅厚得恰到好处而远近闻名的铜锣烧店铺,其休业的时间并不固定,全看前一天的营业额扣除琐碎款项后结余的份还能换回多少米面与豆馅。等到个子不大的布袋瘪瘪躺倒在地上、活像只猫咪懒成一滩,店主人就会从尚带余温的铁板前走开,关上朝街的前门,接着整整供人歇息的桌椅和井井有条的碗柜,最后上到二楼去。
“你在的吧?”“是的。那什么,今天天气很好,我本打算趁这机会晒晒被子、做个扫除什么的,结果——”说话的人拖长了尾音,最终还是选择省去细节直奔主题,由这副口舌吐露而出的这般言语实在是重复了太多遍,以至于浓浓歉意拉扯坠地的字音复又高高弹起,反倒染了些轻描淡写的意味,“非常抱歉,主人。”
人类青年绕过衣物、箱盒,以及所有者都不记得从何而来的杂物所构成的一地狼藉走到坦荡荡大开的窗户边上,确认完这间屋子里唯一一条被褥现在只是一动不动地横陈在于后街更后疯长的灌木枝叶之间,他转过身,但又并没有执着于在这六叠的空间里找到什么人。
“我说过你时刻都得让我看见。”“啊。”“我也说过不要乱动屋里的东西。”“你说过。”年轻人现出身形的同时向侧走了一步以保证自己确实出现在对方的视野里,多此一举的因牵动相应的果,他因此踩上什么东西,白瓷质地的物件干干脆脆地碎成几截,甚至猜不出本来样貌,“……我很抱歉。”“去把掉下去的被子拿回来,这边我来理。”“好。”
鹤见时江逃也似地蹿下楼梯,还差点在最后一阶上绊倒,他推开屋子的后门走出去,阳光劈头盖脸地轧下来刺透身躯,它们不曾给他造成过任何伤口,也不曾给予他过任何温暖。
自从护身符的付丧神离开徒然堂以来,就没少给松井没有名字先生添麻烦。他累计已摔碎俩盘子仨杯子一个豁口的茶壶盖子,绊倒过鼓囊囊的红豆白费过半斤面粉,现在又折腾得好好的房间乱得和进了贼似的一片混乱,事到如今,要说自己的初衷只是想为了主人做点事,也只会显得像个拙劣蹩脚的借口罢了。
“你。”青年将手撑在窗框上居高临下地喊,狭窄院子里傻愣愣站着的年轻人循声仰首,这般视角下,后者金色的眼瞳藏在圆框眼镜后、比往常看上去更加模糊不清,“被子,是够不到吗?”“呃,不,抱歉,我走神了。”“等会我要去趟集市。”“知道了。”
松井消失在窗口,两秒后窗户也关上了,时江没有余裕继续胡思乱想,他拉扯过勉强也能算是好好摊开来晒过的被子抱在怀里,边顺手拣走背侧粘着的几把枯枝败叶,边快步往回赶。
既然有缘同住一个屋檐下,房客和房主总需要在各个方面达成共识才能开展和谐生活的共同建设,松井与鹤见在落笔成文的契约之外又做了许多口头约定,其中就有这么一条:付丧神只要通报去处就能自由行动,而人类要出门的时候,他就得时时刻刻带着护身符。
“我知道这绝不是个好提议,可你带着我肯定比不带好。”时江讲述过往经历的时候虽是好好地看着他正与之对话的对象,却也巧妙地避免直视对方探寻的目光,“上一个把御守落在屋里就出门给人上课去的教师先生被人烧掉了半个书房,另半个也给烟熏得过了头,花费数年收集了几排的手抄古书一本都留不下来。你肯定也不想遇到如此飞来横祸。”
话音落地之前,些许的窘迫便匆匆地追上他,实际上,这场灾难完全可以追因溯果,不必复杂的推理就能得出结论——[一切都是由他招引而来]的缘故。
听来足够荒谬,但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厄运这般虚无缥缈的概念,在名为鹤见时江的同为虚无缥缈的存在在场的前提下,是可以具体量化的,这些既有方向又有大小的箭矢指向他,让他的世界、与他有所联系的他人的世界一并笼罩在自己庞大的阴影下——这一点在与他结缘的人类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雨水落地会向低处流走汇入江河,江河上涨便会吞噬岸堤、甚至形成洪流,而最接近江河的人自然而然就会被江河卷走,就是与之相似的道理。
难道不会觉得把付丧神的意识与本体剥离,又把付丧神的躯体与本体联结,如此行径是造物主过于恶趣味的安排吗?既然赐予他一副无法与他人长久相处的身躯,又为什么要许诺他向往与他人相伴的心灵?而他自己,他作为一个独立意识所拥有的理性,又为什么要纵容强烈似执念的愿望如同蛇咬般侵蚀内心,导致他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地犯下错误?
青年并没有看穿时江这会儿格外复杂的心思,或者也可以说他并不在意,松井只追问了一个细节,就爽快地将这算得上冒犯的要求答应了下来。
于是亲爱的倾听者们便可得知,等到多余的麻烦以及顺势开展的真正扫除终于告一段落、两人终于可以出门的时候,时间已经有些晚了,想要在这个点儿的集市买便宜新鲜的食材怕是很困难。松井没有说什么,时江也开不了口,只在对方身后三步左右的位置亦步亦趋地跟着,他们离开后街,经过前街,房屋与房屋之间拦起一片焦黑的土地,其中一些木质结构的建筑残骸已经和数日前撞毁于此处的车辆一起被拉走了,一些仍没有,它们无言地伫立在原处,供人辨识一场席卷了此地的无妄之灾。
“你是不是说过,那天早上你来过这里?”走在前面的人突然问道,把跟在后面的结结实实地吓了一跳,“我领你回来那天。”“是的。”九十九一边回答着,一边在脑内搜刮记忆,“我想应该是的,先前听说河畔有几株樱花有了花苞,所以那天早上就趁没什么人的时候从店里出来,想要去找来着,后来的事你也知道了。”“你喜欢樱花吗?”“不知道。”这次时江给出的答复简单而干脆,“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喜欢没有亲眼见过的东西。”
松井看向他,年轻人笔直地站在午后倾斜的日光之中,脸上不带什么表情地回望过来,他的容貌姿态分明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并非人类的异物感却陡然膨胀,给人以一种仿佛是什么完全无法理解的生物披着人偶、或是别的什么徒有其表的东西在与自己对视一般的错觉——也只是转瞬即逝的错觉罢了,再者,论说躯壳内所存的内容,松井拥有的未必就比鹤见多。
“那要去赏樱吗?也快到时节了。”沉默了一会儿,青年开口说道,没成想得到一个反对的答复:“不了吧,人会很多的。”“那正好可以卖铜锣烧。”“不不不,我的意思是人多的地方容易出事,特别是小偷扒手之类,还是别去——”“你难道就不想看看樱花吗?不是说从来没看过吗?花期很短的,错过了可就看不到了。”“……你就不觉得用这样的说法劝说别人十分狡猾吗?”“什么?”
“没什么。”九十九撇撇嘴,该说的都说了,说服不了你算我输还不成吗,“就如你所愿吧,我的主人。”
“那就这样说定了。”
日子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九十九所能记住的第一个四月,松井如约将他带来了上野公园,也正如他自己所预料的那样,热气腾腾又物美价廉的甜食是前来赏花野餐的人们的心仪之选,不一会儿小推车前就人满为患。付丧神这会儿是帮不上什么忙的,当然也可以说,就算他想帮忙也只会让自己的主人忙上加忙,于是青年就打发他四处逛逛,赏赏花,最好能挑一个僻静又没什么人的地方占上一席,也不算白来这一遭。
这也算是物尽其用的一种了,时江十分擅长找那种没什么人的偏僻角落,这是几分天赋与丰富经验的积累互相结合所能得到的最好的结果。不知觉之中嚣嚣的人声便被喳喳的鸟声所替代,他顺着不成路的泥土小径寻到了所谓[理想的场所]。
御守是在秋分的时候化的形,他见过漫山遍野的蹡蹡红叶,见过铺天盖地的皑皑霜雪,但确实没有见过如此之多的花,它们颜色浅淡如云絮,瓣片柔软如绒羽,粉粉白白,赏心悦目。美丽的事物会对一个人,或者将范围算得更宽泛些:一个灵魂,起到多大的影响呢?时江站在盘根错节的古老樱树下,步伐挪不动分毫,直到眼球因接触空气太久而刺痛难耐、甚至涌出泪水,他这才慌慌张张地低头抬手擦拭,接着看着自己袖口洇湿的痕迹哑然失笑。他认为有必要总结一下刚才的感受与体验,不过在这之前他听到脚步声,来人好像肩上担负奖章一般身姿挺拔——可能有点太挺拔了,他不得不伸手拨开挡在面前的枝叶才能自由前行。
“失礼了,我还以为这个地方没有别人找得到。”不知为何有些面熟的陌生人也在树前停下,他朝着时江的方向开口道,后者愣了愣、露出奇怪的神情:“……那个,是在向我搭话吗?”“对。”“哎呀,这可不好办了。”“不用介意,我也只是顺路过来看看,席位已经在别的地方设好了,你随意就好。”“啊,恩,十分感谢。”虽说并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你喜欢樱花吗?”“是的。”时江回答,他马上就将普通人能够看见他时都会发生些什么事的思考抛到脑后,像是正等着谁来问他这个问题一样夸张地眉飞色舞起来,“非常喜欢,非常、非常喜欢!先生!这大概是至今为止我最喜爱的事物了!自然也好,神明也罢,究竟是如何才会想得到创作出这样梦幻的风景呢?而且,而且啊,比起欣赏到它们,我更开心的是我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出‘我喜欢樱花’这句话啊,先生!不是从书上、不是从插图,而是亲眼见到它们!为它们天然的美所彻底折服!这多不可思议!”
当然他真正想表达的远不止这些,还有很多难以解释清楚的细微情绪于胸腔中一并炸裂开来,这是一个行走了数月的生命所能承受的对于这存在了数不尽的岁月的世界的感动,这是无法和已经生活了数十年的生命分享的感动,他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安静了下来。
“咳咳,抱歉,说了些奇怪的话。”“没关系,我明白你确实很喜欢樱花了。”男人礼貌地点了点头,这让时江更加窘迫,他尴尬地想要转移话题:“那个……虽然很突然,请问你喜欢甜食吗?”“喜欢。”“那么,作为如此良辰美景的酬谢,请让我介绍一家铜锣烧做得很好吃的店给你吧?”年轻人抬手邀请后者同行,“今天店主人也到了这里来……啊,当xin——”
他出声得太迟了,想要警告的对象快上九十九两秒,踩上青苔脚下一滑、一头撞上粗壮的树干之后花瓣兜头淋下,将整个人染得粉粉白白,很是春日风情。
……希望他之后吃上铜锣烧时不会被烫到嘴吧。时江真心实意地如此祈祷。

☆小江这次大概是没力气掐死我了,良心并不会痛
☆借用了一下虚方姐!大胆地响应一下!
明知故犯。
他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头顶上的天空依然是蓝色,太阳没有变成两个,世间的一切也都在井然有序地依照着某种不可视、不可闻、不可触、唯可贸然揣度的法则运作着,仿佛只有他这一个故障的齿轮脱落下来,在长达四十五天的坠落中看见一个幻境。
即是说,可能其实不存在一位不顾御守的劝阻、把呼唤灾厄的物件买下来的松井先生,从没有摔碎的碗碟,没有掉下楼去的棉被和漫天的樱云。付丧神向来对自己——不论是记忆力还是任何别的东西——是抱有过少的自信的,加上这莫名其妙的打击来得是如此突然又绝情,因此他开不了口,他无论如何都无法理直气壮地对着眼前这位将他从徒然堂带出、现在却又询问着他是谁的人类青年开口,说出:我们明明是认识的。
“你没事吗?”松井虽然也是一头雾水,但看见年轻人动摇到这般地步,脸色一会儿白一会儿青好像随时都会倒下,反而担心起对方来,“我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
“也许有吧,我不知道,我已经搞不清楚了。”时江最终这样说,他苦笑着,瞧着甚至有那么点泫然欲泣的意思,“我现在唯一可以确认的事情,就是我现在无处可去了这一点吧。”
他当然不会灰溜溜地回到店里,躺在柜架上等待什么[下一个机会]了,他可以向着天上那些从未护佑过他的神明发誓只有这件事他不会再做。痛楚对于名为鹤见时江的九十九而言是难以去忍耐、难以去承受的,不论是这副虚构的躯体为模仿人类生存而形成的生理上的痛觉,还是一次又一次地失败过后于心底产生的撕心裂肺的痛苦,全都让他备受折磨。他害怕,而一个懦弱的灵魂惧怕疼痛也算是理所当然,这并不是什么稀奇事。
“……你无处可去的话,要不要先留在我这?”
青年沉默了一会儿,侧过身,做出了一个邀请的手势。这幢占地六叠、高有两层的旧式木屋的主人,就是这样又一次将不速之客迎进了家门。
就松井而言,他并不会主动关注别人的私事,然而这位暂住者不愿言明的东西似乎有点太多了。年轻人只报上了自己的名姓,虽是穿着华丽,但却身无分文;他好像懂得很多事,能够写字算账,又常对许多寻常物件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兴趣。于是青年就猜测对方可能是从哪里的大户人家跑出来的少爷,毕竟这小伙儿往好听了说是不擅长做家务事,往不好听了讲就是笨手笨脚,还有点娇嫩。如此结论是三十二秒前得出来的,时江自告奋勇说要帮忙洗洗盘子,接着就在主人家眼皮子底下摔了一个,手心还给陶瓷的碎片划了一道见血的口子。
“很抱歉又摔坏了你的东西,松井先生,但我真没事。”如果他的眼眶没有红,这话听上去还挺有说服力,“反正没伤着……伤得很深,过几天就好了。”“还是处理一下吧。”
松井练过武,觉得自己也算皮糙肉厚,这点小伤不在话下。时江就不一样了,他拉着他往二楼走想找东西包扎伤口的时候,年轻人分外乖巧地跟在后面,什么话都没有说,大概是真的很痛。想着这些,他也就自然而然地忘了对方奇怪的说法、忘了橱柜里奇怪的空缺,忘了这两者之间的简单联想。他本就不是会为这种程度的异常就要追根究底的人。
而对于时江来说,他就算是做不了什么好事、也从来都是个会为主人多做考虑的付丧神,即使被冲击性的事实打击过度,花点时间总归能够重新振作,毕竟两人之间的缘分并没有终结,九十九可以肯定这一点(当然,为了这个[肯定],他偷偷跑回过两条街开外的古董铺专门确认过)。他算不上聪明,也不那么愚笨,几番推敲后总算是明白了对方态度改变的原因——松井忘记了一切与付丧神有关的事。他这是误把他当做了与他一样的人类。
这就不难解释很多事。鹤见心想。比如他现在拉着自己想要找东西包扎包扎,就是因为他忘记了自己就算受伤,只要没有损害到桃纹的御守,再可怖的伤口也能在几日内完全痊愈。
九十九切实地拥有着五感,但他们不会因此产生生理上的需求,单就这一点来讲就已经与人类大相径庭,更不用提人形与本体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又会产生怎样神奇的作用。因此“被视为人类”的体验是十分难得的,时江不可避免地注意到松井的话变多了,这个人不再是礼貌且疏离地与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再是只在他犯下错误时才开口、与他进行着最低限度的交流,不再是、不再是用着和中学教师,和行脚商,和护士,和大学生——用着和其他契约者一样的目光看着他,把他钉死在他从未想要拥有的一切上,让他举步维艰。
瞧,他当真是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呀!自己并不作为他的同族存在于世的事实,源源不断的麻烦皆有来由的真相,还有自己分明就是在卑鄙地蚕食着他的平稳的生活,等等等等,一切的一切,他全都不知道、全都不知道啊……
“时江。”付丧神还不习惯听到别人喊自己的名字,他停下胡思乱想、万分迷茫地望过去,松井便耐心地又问了一遍:“还疼吗?”
他现在终于意识到自己这是沉默太久了,于是赶紧摇了摇头,视线隔着玻璃的镜片顺势落到手掌心细细缠绕的绷带上,粗糙织物的尾端是蝴蝶结拉扯过度后失败的模样。他想告诉他说已经不疼了,喉头却被尚未成形的呜咽声生生哽住,吐不出哪怕一个字来。
这之后的第七天的早晨,即是说鹤见住下来的第十三天兼第五十八天的早晨,年轻人和屋主人说自己等会儿要出门。于是松井把人送到玄关,他就是在这在这儿眼疾手快地扶住平地上也能摔倒的房客。青年看看惊魂未定的小伙子,估算了一下时间,最终还是改了主意、陪他一起走上后街。
五月的街道和四月时并没什么太大的不同,就算连续几日的阴雨停歇了留下一片鼠灰色的沉闷天空,空气也仍旧是湿漉漉的,它将行人与行人之间习惯性的沉默渲染得更加抽象。这次先开口的是时江,他以一种事先准备了答案因而期望他人问询的心境把另一个问题抛给同行者:“你不问问我去哪吗?”
松井则是这样回答的,他的语气一向平平淡淡,此时甚至还有些缺少感情:“你要去哪里都是你的自由,没有告诉我的必要,就算你要离开这里回家去或者哪里都——”“我说过我是无处可去的。”他少见地以略显强硬的语气打断他的话,“除了你这里,我没有任何可以‘回去’的‘家’,我不会对你说谎话,松井先生,所以请不要——”鹤见仿佛被人掐住脖子一般突兀地停下来,“……抱歉,我太激动了。”“没事,我不在意。”
青年伸手,时江的个子比他还高些,所以他轻轻地拍了拍他的后背,这时候他们已经到了路口,他要离开,他也该回去开店了,只是年轻人那副焦急的模样触动到了什么,让他有种难以忘怀的复杂感受。他可能是知道他想说什么的,也可能不知道,他无法确定。
“路上小心。”松井顿了顿,补了一句,“早些回来。”
他猜测这句话是说得对了,因为小伙子总算笑起来、回了声好。
至于付丧神打算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毕竟失忆不是正常现象,既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表现出痊愈的征兆,那么前去咨询专业人士之类的简单事务,就算是他也不至于做不好。
“欢迎光临。”蕪木虚方听到铃铛响,她从椅子上站起身,发现来的是位有些面熟的客人,“哎呀,您是——”“我是那枚招来厄运的御守,蕪木小姐,去年秋分化的形。”付丧神礼貌地点点头,“先前来得匆忙,没有和你打招呼,还请原谅我的失礼……不过这次来访也还是因为我的主人的异常情况,他仍然没有好转。”“那确实很奇怪,狂鲤已经被打倒了,造成的影响也就应该消失了。他的症状是什么?”“失忆,他忘了和九十九有关的一切。”“你是说,他也忘了你吗?”“是的。”鹤见默不作声地移开视线望向窗外,“虽说如此,他也并没有抛弃我,只是把我当做普通人类收留了下来。”“那还好,这样说不定还好办些。”
现任咖啡馆管理人的前·清净屋看出付丧神的疑惑,她如此解释道:“他还能够看见你,那你只要告诉他他忘掉的事情就好了,九十九能够唤醒被狂鲤蛊惑的人,你肯定也可以。”
“只要告诉他,他就能想起来,是吗?”年轻人重复了一遍,“这么简单就可以?肯定还需要别的吧?毕竟,对,我的主人的情况有点不同,他受到的影响比较严重不是吗?不然怎么会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如果真的这么简单就能解决的话,我也不用烦恼那么久了呀?”
“可是你并没有尝试过这个方法吧?”虚方不由得因为对方奇怪的反应而疑惑起来了,“不如说,都过了这么久,为什么你没有试着告诉他——”
时江没能听完这句话,仿佛是将眼球内部的水分瞬间蒸发殆尽一般的剧烈疼痛毫无征兆地灼烧起神经,他哀嚎着倒在地上、鼻梁上架着的眼镜也不知道掉到了哪里去,他挣扎着滚动、尔后瑟缩成一团不受控制地震颤起来,而没有了任何阻碍,手指便毫无顾忌又神经质地狠狠抓挠眼周,指甲在脸颊上划出道道伤口,他这是下意识地想要将痛苦的源头从身体上挖出来以结束这可怕的折磨啊!然而勉强保留下的蛛丝般的理性又勉力拉扯着神智去阻止躯体实践自残的行径,他没有余裕去思考,只有期求这一切能够结束的念头残留在脑海——
也确实结束了,如潮水般席卷而来的痛楚在长达千万年的数秒后也终于如潮水般猛然退去,九十九喘息着扶着墙壁站起来,他不知道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被他吓到的虚方这会儿正为他匆忙奔找着店里的修缮师。年轻人摇摇晃晃地拾起豁了口的物件挪到店门口,他的眼睛不好使了、什么都看不清,所有的所有的一切都在歪曲的视野黏黏糊糊地溶解着混杂在一起,整个世界之中只有松井的声音依旧清晰。
他对他过说早些回来,所以他这就要回去了。
青年注意到自己的房客自从出过一次门之后就有些不对劲,时江开始经常用想要说什么的眼神看着自己,但出口询问的话也只会得到沉默的摇头作为回应,此外,他偶尔会看着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发呆,还会伸出手去,做出抓住什么东西再松开的动作。会不会是回来路上摔到了头?松井如此推测,而这个想法在看到对方豁口的眼镜之后变得更加坚定了。
“你找到它了。”他指指对方手里的遗失物,“这不是都坏了吗,要不要去换一副?”“还能戴,就不用了吧。”“不会妨碍到看东西吗?”“………………能妨碍到就好了……”“什么?”“没什么。”年轻人从房间角落的位置站起身来,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的时候,他就会待在那里,“那个,虽然很突然,不过今天能让我帮忙洗碗吗?”
考虑到上次答应这个请求的时候发生了流血事件,松井本来是想要拒绝的,可时江说这话时的神情是那样认真、甚至带点孤注一掷的意味,他也就只好先一步将绷带准备好以防万一。只是出乎他的意料,搞不好也出乎小伙子本人的意料的是,他这次什么都没摔坏,八个盘子,三个碗,两个杯子,什么都没摔坏,全都完完整整、干干净净地排列在壁橱里。
想做的话不还是做得到的吗!松井对时江这次的完美表现十分满意,他侧过头想要再说些什么、或者夸夸他,可当他看到年轻人脸上的表情的时候,这些话就讲不出来了。
……也不至于开心到哭出来吧……他轻轻拍了拍他的背,不禁这样想到。
鹤见时江知道只要他不开口,松井就会继续将他当做人类来看待,不会将九十九的概念回想起来;他知道这之后后院更后位置的灌木会无故地枯萎,常青的树木会惨遭雷劈;他知道只要他想,他就不会再摔碎任何东西;他知道他看到的是什么、抓在手中的又是什么。
【我其实什么都知道。】他听见自己这样说,即使他并没有开口,【我就是因为知道,所以才会这样做的。】
付丧神一觉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五月二十五日的傍晚,他披挂着屋主人借给他的毛毯从榻榻米上爬起来,看见自己的结缘者正坐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用他再熟悉不过的目光看着他。
“……九十九也会做梦吗?”
松井平静地提问,而被询问者以微笑作答。
他看着摆在自己面前的碗筷和饭食,露出了万分不解的神情:“请问这个是?”“我看你一直没有吃东西。”这么说着,松井在他对面的位置坐下来,“虽然只是粗茶淡饭,但应该也能填饱肚子。我的手艺还是不错的。”“可是我——”“恩?”“啊,不,没什么。”
他没有进食的必要,他并不是依靠食物存活于世上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包括松井,所以他从没有得到过一个机会去尝试所有人类都会尝试的吃东西这件事,好在他已经千百遍地看过别人重复这个过程,所以他能够顺利地拿起筷子、搛起一筷子的菜肴送进嘴里、咀嚼、吞咽,而不使眼前的人的心中升起疑虑。
他确实这样做了,然后狠狠呛住,止不住地咳嗽直到喉咙里泛起腥甜的味道。他向松井摆摆手,示意自己并无大碍,等到能够正常说话了,他耐不住激动地开口,他记得人类在遇到这样的状况时应该给出怎样的感想:“好吃……!”
“好吃你就多吃些,就是吃慢点,不要再呛着了,饭的话锅里还有,你放心吃。”
他看见松井微微地笑了笑,在此之前他从未见他这样笑过,他开始希望时间能够停留在这一刻。
丝线于此刻扭成第二个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