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罗大陆,圣别纪元后期。
血族女王莉莉安突然失踪,几乎同一时间爆发的怪奇疫病让人类数量逐年锐减,失去管控的血族加上疫病的席卷,让整个社会动荡不安。
将一切扭转的契机在于教会发现血族的血液竟是能治好疫病的良药。
从此,以血液为中心的利益旋涡将整个世界卷入了其中。
【创作交流群:691199519】
“无论憧憬真挚与否/怜悯的缘由存在与否/沉谜底于心”
---
少女睁开眼睛,自己正躺在床上。周围光线昏暗,窗帘都被拉着,但她看得清。身上不痛,伤口也找不到了,她想,自己一定是被那位大人救了。
她下床,走到窗前,想掀开帘子看一眼外面,看看自己在哪。“别动。”黑暗中传来低沉的男声,她的手停在半空。年迈的血族点燃了一枝蜡烛,火光下她看到那袭白袍。
.
Iris接受自己成为血族这一事实,并没花多少时间。“如果实在还晒太阳,就去做教会猎人。我不拦你。”那位大人在纸上写下手迹。Iris 捡了摇头。”没关系。反正.... …我本来也不太能接触阳光呢。”
那位大人看向被蒙住的窗户。太阳落下了。“那么,从今天起我便会教导你。”他写,“你喜欢鸢尾花吗?”
“还可以啦。怎么了?”
年迈的血族放下笔,示意Iris跟上他。他打开门,在灿烂的星空下,Iris 看到他的宅邸门前生长着大片大片深蓝色的鸢尾花。
“以后这就是你的名字。”
Iris接过他递来的种子,在蓝色的花海中种下一株黑色的鸢尾。
.
血色的枝蔓疯狂生长,Iris灵活的躲过冲她袭来的尖锐枝条。那位大人站在花园对面, 不动如山。他的法术停顿了一 瞬,因为他看到Iris 突然消失了。待他反应过来空气中混杂着他子嗣的血味时,Iris 己站在他身后。“我赢了。Lris有点得意地说,“你的法术现在可对付不了我喽。”“少用你的雾气。”血族拿出了纸笔,在上面写,“你晕睡过去的时间里没人知道会发生什么。”Lris很不高兴地看了他一眼。“猎人的话刚才那一下就死透了,况且对手是你啊,真是的,你也不夸夸我哦.....”
那位大人轻轻点了点头。“回房间吧。”他把羊皮纸递给Iris。“估计你得睡到明天下午。”
.
Iris对过去的记忆几乎截止于此。再之后,她只有一些模糊的印象。白色的影子,黑色的房间、一首很熟悉却怎么也记不起歌词的童谣、很多血,以及纠缠许久的头痛。她想不起那位大人怎么消失了,也不记得自己遇到了什么。那个看不清的身影从此以后每天出现在她的梦中。
.
赦罪演武结束的那一晚Iris终于看清了梦中人。那人的胸口别着一朵深蓝色的鸢尾花。Iris突然想起,自己已经很久没回过那座宅邸了。那位大人神秘失踪,宅邸自然归她所有。她顺着小路走回那里。花园里蓝色的鸢尾早以因缺水枯萎,只有黑色的那一朵仍倔强地绽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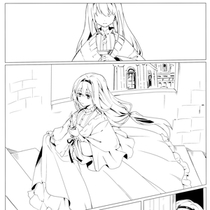







无边的寒意,这是在意识回归之前便存在的感受。
上一次为寒冷所扰是何时的事情?她难得回忆起来,依稀在记忆深处,腹中空空的钝痛作为其孪生姊妹。饥寒勾结,恣意彻骨地侵蚀血肉凡躯,嘲弄无望的,草芥一般的生灵。
生命蜷缩着,如卵中未成的雏鸟,却觉得迷惘天地间,有人伸出手来,教她擦净一身贫穷烙下的印记,细腻温和因而价值不菲的丝织物交递过来,比雪花更轻地抚过肌肤:接着又问,你的愿景,是什么。
有窸窣细雪落在面前,落在发上,她感到前所未有的温暖和希冀,狂喜令人迫切地张口,寒风却趁机堵塞了全部的话语。
瑟莉安娜骤然睁开眼睛,从一片猩红炼狱中抬起头,破碎的花窗透露出天空的颜色,然而在一片铅灰中分辨不出究竟到了几时。
几近漆黑的深色血液已在身下积攒为一处血洼。她下意识去抚摸右肋下的溃烂圣痕,那里仍如几日前饮下黑血一般灼痛甚至更甚,变本加厉地为残躯提供过载的动能,仿佛第二颗心脏的搏动,催化着战逃反应。
这样的血液顺着阶梯向低处黏稠蠕动,不仅是她的,还有更多,顺势与其他鲜红的血液混成诡异的丝线,进而在大理石面上织作令人胆寒的锦缎。
尽管如此,周围四溢的血仍然提供了收回身体控制权的绝佳机会,浸透血液的义肢烫得能够灼伤人的皮肤。她拔出刺于身旁解脱多时躯壳的剑刃,拄着它借力从地上站起。双腿尚且脱力,她站得并不稳当,一只手握住她的右手,将立于大地上的实感传递过来。
伊莱……真叫人怀念。她说,用一种揶揄的口吻,见到你没事真好。
伊莱法缇的另一只手不自然地垂着,他当然有耐心等待自行恢复的时间,可他真的还有多余的血来痊愈吗?猩红的生命泉流顺着伊莱法缇的额角一刻不停地落下,经过为那只灾厄浸染的眼球,好像是这些血泪造就的那样,最后从无法再承载的眼眶边沿滚动下来。谁都清楚,这很难算得上无恙。他对瑟莉的话苦笑一下,是鲜少能在这张从容面庞上看到的局促。
教会猎人站稳脚跟,收回剑刃。比起和她一样方从血海深处醒来的异途旧友,她更关心在失去意识期间礼拜堂的战况。她踏上前方的阶梯,大教堂伟岸的穹顶却似乎于此时发出不堪重负的哀鸣声,紧接着是横梁崩裂的响动。石料黑色的间隙鼓动着,无数粘液不停歇地渗出,最终垂落过程中汇成巨大的触手状异物。地面上沉寂许久的黑色血液受到某种感召,如同吐信的巨蟒昂起头来,外部的天空不知何时已经血红,天地交融在混沌无序的血海中,仿佛亿万年的溶洞,等待漆黑无光的钟乳石和石笋弥合的刹那。
瑟莉安娜看见残月血族抬手,用法术企图驱散这至暗的恐怖,星光只闪烁了一下便消失在她眼前。她想做些什么,触手很快也温柔地吞噬了她的身体。
***
盛大的舞会。
无数枝形吊灯错落悬挂,点燃一圈,又一圈的烛火,像地面上踩着舞步回旋的客人,一圈,又一圈。
厅堂暖和得像一个不合时宜的春天,尽管瑟莉安娜不再那么渴求温度了。
这些人,参加舞会的人,全部看不清面庞,是因为覆着假面吗?她一个人坐在宴会四周的椅子上,用打量的目光观察着,思考着。
有人对她伸出手。黑色的手套,同样的假面,但她立刻认出这是父亲,于是欣然接受。
暗红色的布料流动起来,在旋转中轻快地离开地面,像水波,像一圈涟漪,像一场遥不可及的追逐。
没有边界的自由里,瑟莉安娜只感受到那位给予第二次生命的人,他的黑色缎面礼服揽住她的腰肢,他的耳语近在咫尺:
你的愿望?
——我的愿望吗,瑟莉安娜想,那实在是太多了。最初的时候,我想要不再受寒、不再饥饿。
然而她对着脑海中往昔的幻影说,我想离开你,我不需要你。
眼前的景象改变着,霎时有明媚的霞光照耀到瑟莉安娜的身上。这是圣伯拉礼拜堂后东侧连廊的倒数第三扇窗,几十年来从这里可以看见全圣都最美的日出。
身着修士黑袍的人牵住她手,他轻轻地问,
我爱,你的愿望是?
——在某刻我祈祷留住此时、留住我爱。瑟莉看着他,从模糊的五官上分离出清晰的思念。
于是她说,我想要的你都已经给予,我别无所求。
阳光迁移着,被吞没到廊柱之后,视线变得晦暗,但不久,圣伯拉的祷钟在耳畔响起来。立刻,血液逆流,回到不再残破的身体;武器收势,回到持有者的鞘内;星辰倒转,日与夜逆向而行。死亡、绝望,痛苦尽数收回魔盒之中;永生,安宁,乐园再一次回到人间。
逆光的神龛上传来比钟声更恢宏的声音,祂问:
你的愿望,是什么?
——在最后,我想要回到过去,回到属于我的伊甸去。
然而,只是想罢了。瑟莉安娜眯起眼睛,看着漆黑的,镀上一层金色光晕的神像,然后说,我没有愿望,我伟大的造物者,我没有。
我既不逆来顺受,更不强取豪夺。因此我绝不妥协,绝不扭曲。我赋予我存在的意义,哪怕连我自己也无比迷茫。
我的愚钝,正是我为人的本质。
***
神龛上的光消亡而去,等再一次能看清时,眼前只剩下圣堂那扇破碎的花窗。
神的肢体叹惋着离开了她。
瑟莉安娜感觉到眼角有什么东西,她眨了眨眼睛,深黑的血代替眼泪淌落,是凝视神祇的代价。不过,她没有心情再管自己了,她眼前赫然是一处正在蠕动的,难以言明真身的黑色胶状物。幽蓝的荧光沿着内部生成的脉络涌动,它轻微地律动,节律地呼吸着。
……伊莱,是你吗?
他感到寒冷,或许是因为血液正在从他的右臂上缓缓流出,但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右臂为什么要被剖开任由鲜红的液体缓慢地从他的静脉中流出。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流了多少血。
他的脑袋昏昏沉沉,沉重的眼皮仿佛随时都要再次合上,在他失去意识前白色短发的女人出现在他的视野中,她蓝色的双眼中惊讶一闪而过,“你醒了?”但她并没有停下手上的动作,“干嘛要醒过来,再睡一会儿吧。”
她手上的针头在灯光下反射出森冷的光,她另一手滑动调节器上的滑轮,红色的液体快速从滴斗里顺着软管从针头流出,她关上调节器将针头先粘在自己的手背上,而后抓住他的左臂翻转露出臂弯内侧,用止血带绑紧上臂。她从盘子上拿过镊子从棕色的小瓶子里夹出一团被碘酒浸湿的棉花,棉团上的碘酒涂过他小臂上端的一处地方,最后她取下针头斜着对准血管。他看着针头刺破自己的皮肤进入自己的体内但却毫无感觉,当调节器再次被松开输液器开始运作将这液体输送进他的体内。
“奈杰尔,好孩子,闭上眼睛吧,”女人冰冷的手掌抚过他的脸颊,眼中是他看不懂的笑意,“当你再次醒来之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奈杰尔·戈林闭上了眼睛。
——————
“听说你最近弄到了什么有意思的东西。”
她抬起头看向身旁,但是对方赤色的眼眸只停留在楼下往来的行人上,就好像这只是一句无心的闲聊,“你指什么?”
“还能是什么,”卡拉转过身后背靠在二楼阳台围栏上,她迎上凯蒂的目光,“比如一些坊间谣传的偏方?”
“看不出来你还是属狗的呢。”
“过奖,所以你把那个嗜血怎么了?”
凯蒂挑了挑眉,“抱歉,看来狗可不如你,光用闻的就知道对方是哪个血族。”
“只是恰好对这个味道很熟悉罢了。”卡拉耸了耸肩,她抱起双臂视线移向了地砖上的一条缝隙。
“好吧,其实我不知道那个倒霉蛋是谁。一个工会猎人带着金发的小丫头头也不回地跑了……”
对方没忍住的一声轻笑打断了她的回忆,凯蒂不满地皱起眉头,“我知道你仇人很多见不得血族好,至少对同僚有点儿礼貌行不?”
卡拉轻咳一声重新端正神色,“抱歉抱歉,您继续。”
“……我讲到哪了?”
“金发小丫头。”
“哦,他们走了之后屋子里就剩下一半血族一半肉馅,我就随便拾掇了一点儿。”
“一点儿?”
“怎么了嘛,我又没有给那个血族补刀,这点儿保命钱都不给吗。”
“所以?你要那个干什么,教会又不是没有别的血,还是说你想换换口味?”卡拉皱起眉头像是吞下了一只虫子似的,她浑身打了个寒颤,“能不能吃点好的。”
凯蒂白了她一眼,“谁要喝那个,先留着嘛,从工会那借个血罐,没准以后就用上……”
“凯蒂小姐!”
少女充满活力的声音响起,她们一同望向楼下,金发碧眼的女孩笑着朝她们挥了挥手而后小跑着进了楼。但是凯蒂却抬腿踩上栏杆,卡拉听见她咋了下舌。
“她是来找你的。”
“我不在。”现在她两条腿都迈上了栏杆。
“她都看到你了。”
“那她看错了!”凯蒂朝卡拉抛了个飞吻,虽然对方躲过去了但是凯蒂并不在意,“帮个忙,给你带小礼物。”她从阳台上一跃而下。
——————
奈杰尔·戈林醒了,他坐在手术台上看着自己微微颤抖的双手仍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凯蒂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告诉他这个好消息了。
“恭喜你,戈林,”她拍了拍手,“告诉你个好消息,你的疫病已经治好了。”
那双绿色的眼眸中的迷茫渐渐散去,狂乱的欣喜迅速充斥其中,“真……真的吗?我……痊愈了?”他的手放在胸前,看起来仍然对这个消息感到难以置信,但是凯蒂真正想告诉他的不是这个。
“还有一个好消息。”
“什么?”
“你变成血族了。”
笑容凝固在他的脸上随后一点点地被打碎,凯蒂满意地看着他的眼神从感激欣喜变成恐慌,“血……族?但是,为什么,英格丽说你的方法是不会变成血族的!”
“那当然是因为我骗了她啊,”凯蒂无所谓地耸耸肩,脸上的笑容丝毫未变,她走到奈杰尔身旁伸出手轻柔的将他的鬓发拢到耳后,“傻孩子,疫病根本没有什么良药以外的治疗方法。”
“你明明知道她很信任你!”
“啊,对,所以我才这么告诉她的。我知道她崇拜我,她是个好女孩,热情,正直,善良,”她突然抓住奈杰尔的头发让他抬起头同她对视,“但是我不喜欢。不知道这下能不能让她不要再来我的面前碍我的眼。”
她的手腕被奈杰尔抓住,看来她抓痛他了,疼痛和愤怒使奈杰尔皱起眉头,“你,你疯了——”
“或许吧,不过我觉得你现在先管管你自己比较好,”她将他拖下手术台,他的身体摔在地上,奈杰尔的痛呼和器械被打翻的声音一同响起,凯蒂走过去拉开一扇窗帘,阳光毫无遮挡的照射在新生的血族身上,他发出尖叫声立刻向后挪进阴影中离开灼痛了他的光线。奈杰尔惊魂未定地看向自己的手臂,被灼伤的皮肤开始快速愈合,“瞧,你现在根本没办法离开这里。”
奈杰尔咬紧牙,但是泪水仍然止不住地从他的眼眶里滚落,“你到底想要我们怎么办?”
“你的话等太阳落山就可以走了,至于阿忒利亚,我倒是很期待她会怎么做,是坚持信念把你杀掉,还是违反原则给你开个特例呢,每一种情况我都很乐意看到,”她伸手想要拍拍奈杰尔的脸但是奈杰尔先打掉了她的手,她只是笑着站起身重新拉上窗帘,“你也很想知道她怎么做吧?等待你们的见面吧,戈林。”
她离开这间治疗室将无助的奈杰尔独自留在了门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