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罗大陆,圣别纪元后期。
血族女王莉莉安突然失踪,几乎同一时间爆发的怪奇疫病让人类数量逐年锐减,失去管控的血族加上疫病的席卷,让整个社会动荡不安。
将一切扭转的契机在于教会发现血族的血液竟是能治好疫病的良药。
从此,以血液为中心的利益旋涡将整个世界卷入了其中。
【创作交流群:691199519】


前文:
1-2节 http://elfartworld.com/works/9215613/
猎兵队设定:
http://elfartworld.com/works/9212961/
http://elfartworld.com/works/9212962/
3、
米迦勒做梦了。
梦中的他变得矮小而年幼,正仓惶地站在主母的卧房门口。他认得这个场景,那是自主母发病以来,阿密特第一次被允许重新见到自己的母亲。
他本以为自己已经记忆不清,许许多多的细节却在梦中复现:初春的温度宜人,阳光灿烂,主母卧房附近的空气里却弥漫着脓血和草药的味道。
曾经坚若磐石的女人如今垮塌在一张躺椅上,穿着最为轻薄的衣裙,生怕摩擦到她浑身溢出脓血的疮口。阿密特的父亲正小心翼翼地为她梳头,分股编好她日渐稀疏的红色长发,不断柔声诉说:今天的天气很好,索拉里娅,我们的小儿子来看你了。
男人一边说着,一边将新鲜采摘的花朵插入她的发辫当中。而躺椅上两眼无神的女人仿佛对一切都无所察觉,既感受不到自己其中一个丈夫的细致照顾,也看不见在门口凝望着自己的小儿子。
当缓慢而细致的洗漱与梳妆完毕,阿密特的父亲才站起身来,走到自己的儿子身边。
“阿密特,”他轻如耳语地说到,声音里仿佛有无尽的疲惫,“向她告别吧。”
死腐病是不治之症,特别对于这个偏远而原始的沿海聚落来说。他们没有知识,也没有资源,能够为他们的主母求得一份良药。除了那些他们遍尝不灵的偏方,以及虚无缥缈的传说。在一切努力之后,只有绝望的苦涩作为余味留下。
主母正渐渐化作一团血肉脓疮。只有极少数人被允许进出那间不祥的屋宇。而每日小心翼翼地剔去死肉,再小心地把嚼碎的牛膝草敷在她浑身疮口上,照顾主母垂死肉体的人正是阿密特的父亲。
阿密特很久没有和他的父亲单独相处过了。在照顾主母期间,父亲自己也急速地滑向衰老。如今他不再有任何精力与阿密特谈起过往他会耐心诉说的话题:海洋,狩猎,未来,星空。现在他只会隔几天匆匆回家,看一眼阿密特是否还如常自己照顾着自己,很快便会返回主母身边。
阿密特无法责怪父亲将一切心力投注在了他最爱的人身上——哪怕那并不是自己。阿密特同样爱着主母,但他与父亲所经历的绝望并不相同,也无法比较。没有一个家人能替代另一个家人。
姐姐们挑起了家族的大梁,她们默认主母的病已无可挽回,行将死去。而阿密特也默默计数着日子,独自学习生活和狩猎的技巧,维护着父亲和自己的小屋状况——现在更像是他一个人的屋子。他知道有一天父亲会回到自己身边,但在那一日,阿密特的父亲将永失所爱。
而那一日似乎提早来临了。
“醒醒,队长。”一个年轻的声音打断了梦境。米迦勒眨了眨眼,才意识到自己倚着身边的铁柩睡着了。
八匹马拉动的庞大篷车摇晃着前行,沉重的军备和铁柩那冰冷钢铁的气息包裹着他。猎兵队正在开赴纳塔城的途中,路途漫长,他们只能轮流在行进中休息。他吩咐过新兵一入夜就唤醒自己,现在那个少年正局促地望着自己,似乎不知在这种状况下开口是否合适。
“报告行进进度。”米迦勒简单地要求。
“我们已经经过了圣伯拉大教堂,还有半天左右到达目的地,”少年流利地回答。
猎兵在外执行任务时会遵守静默令。除被指定为代表的领队猎兵以外,其他猎兵不得在任务中开口。禁绝交流,也就禁绝了泄密。但现在他们尚未到达战区,也没有同行者,换言之静默令的确尚未生效。
“你做得很好,现在上来休息吧。”
米迦勒和新兵交换了位置。教会的地盘恐怕是最后的安全区,所以他才抓紧睡了一觉。接下来的路程越是接近纳塔城,他们就越有可能提前遭遇敌人——无论是血族还是湖骸,但猎兵队并不打算与之纠缠。
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
“猎兵队会前往纳塔城支援猎人工会,减少他们的损失,”数日前,米迦勒唤醒了铁柩,向圣人们报告自己的计划。米迦勒站在一地钢铁棺椁的中央,作为唯一的活人,进行着这场墓地中的会议。
“目前有两名武库先知正在纳塔城与猎人工会进行交流,奎洛罗与乌烈,二人都拒绝了召回。我们将在当地与他们汇合。”
作为猎兵队内地位极高的战争铁匠,武库先知拥有许多特权。他们也是猎兵队最“外向”的人,还会和猎人工会定期进行开源技术交流。如果乌烈和奎洛罗判断留守纳塔城从长远来看对猎兵队更有必要,那么他们就可以这么做。
“你打算带多少人去?”乌瑟尔的回声隆隆作响。那并不是棺材之中濒死的肉体真正开了口,而是发声器读取了他想说的话,“在我们还活着的时代,湖骸不曾出现,它的危险性无法被评估。”
“三支猎杀小队,以及5名做好准备的新兵。”
“猎兵队的支援只会是杯水车薪,”安达里士提醒到,“我们亦不可能全力投入。”
“这是自然,”米迦勒平静地回答,“大部分兵力和所有的铁柩圣人都将留守小教堂。”
“你应该清楚自己能做到什么吧?”
“是的,我们无法拯救纳塔城,” 米迦勒的语气一成不变,仿佛已经看到了血流成河的明日,并坦然接受了破城的命运,“我们只能尽力减少猎人工会的损失。”
如此,铁柩圣人们同意了他的行动计划。起码是大多数。
“我会与你们同行。”其中一具铁柩从自己的墓穴中起身,伴随着隆隆声响,巨大的钢铁之躯抬起了自己身前那块那刻有生平碑文的纪录石板,轻若无物地放在了一旁。
“让武库先知们准备好燃料。”
“如果您不信任我,可以直接提出,乌瑟尔队长,” 小山般的阴影笼罩着他,米迦勒现在得仰头和前辈交谈, “支援计划可以被修正,但圣人不应当离开小教堂。”
猎兵队的历任队长都无法轻易获得安息。猎兵队长重在伤或衰弱后,才会被装入由武库先知们改装过的铁棺材中,以武库先知们打造机械身躯为自己的肢体延伸,继续进行作战。
是他们曾经发动的围猎招致了血族酷烈的报复与永恒的仇恨,那么哪怕病重伤残,他们也必须继续守护小教堂。这些前任队长被束缚在活棺材中做成战争机器的唯一理由,就是保护猎兵队的最后据点。除此之外,他们理应获得安详的休眠,留守备战。
“你说得一点也没错,小子,但这是我个人意愿,”乌瑟尔坚持道,“备好燃料,还有我的机枪。”
情报来得很快,他们出发得也很及时,但湖骸的蚕食速度同样惊人。他们在路上就收到了纳塔关卡的猎人们已经溃散的消息,同样遭殃的还有斯奎尔农场。
“我们没法救全部人,”米迦勒并未改变先前计划好的路线,“继续前进。”
米迦勒心中并非如他表现出来的一样淡定。他只从书卷与情报中了解过纳塔城,而从未亲自去过。那是一座人口众多的大城,理应有属于自己的城防卫队,或受到附近教会武装力量的保护。但一路上越来越多的信号表示,离开的人远比前来护卫它的人更多。
湖骸虽尚未侵入城内,形势已经一片混乱。每一天,都有更多的人选择涌向出城的道路。大多数人只能徒步,过于幼小的孩子和老人坐在马背或是缓慢行驶的篷车中,携带着一点点家当,顺着细雪飘摇的道路离开,如同一条缓缓流动的苦难之河。而骑马的猎兵们沉默地逆着人流而上,走进这座将死之城。
当猎兵队到达纳塔城内部时,任何理想化的军事条例都已不复存在,或说根本就从未存在过。米迦勒连着见了几波自称是本地城防的代表,终于认清了一个事实:纳塔城根本没有统一防线。
这里只有一个个各自为战的小型据点。没有人能在一夜之间统合整个纳塔城的阵线,每一小队猎人、教会支援或是像猎兵队一样前来的力量之间都彼此独立,他们甚至没有一致的信号旗语。
猎兵队还有许许多多的准备工作要做,构筑自己的纵深防线,围绕猎人工会的主要工坊建立射杀带——这是两名武库先知强烈要求的。工会中留守的多数猎人将会围绕他们的血库作战,因为那是他们来之不易的战利品。但乌烈认为工坊的毁坏和高级工匠的牺牲将导致一部分猎具生产技术永久性失传,它们比血罐更为重要。米迦勒尊重了先知们的意见。
奎洛罗忙着指挥新兵就地取材制作一些小型工事。他还给米迦勒引荐了几波工会猎人——此后他们将在同一个区域驻防。米迦勒记住了几个面孔和名字。但在外人看来,静默令下的猎兵队显然是一群诡异的怪人,唯一会开口说话的米迦勒也是惜字如金。其他人很难分清猎兵们的职级,不知道他们守卫的马车里藏着什么大宝贝不愿意公开。显然,谁也不打算听谁的,只能说是互相混了个脸熟。
城内被抛弃的空屋比比皆是,不再受到照顾的牲畜茫然地在围栏中等待着不会再来的食水。湖骸来得如此之快,以至于饥荒与暴动甚至没能在战争到来前先行。这座城市将获得一个利落的死亡。但对于那些留下来并不幸将要活得更久的人来说,瘟疫与饥饿迟早会撵上他们。
留下的人正绝望地企图自救。少数人是不愿离开,更多人则是没有抛弃一切离开此地的能力。纳塔城本地的所有老人、妇女和儿童已经都加入了城防队列。他们在城外挖掘出一道道填入燃料的壕沟,企图延缓湖骸的前进速度。
本地民兵连队请求猎兵的指挥与混编。但那尽是一些拿着陈年猎枪的老年人,他们中许多甚至已经有了残疾或是视听障碍。在许多年前,他们或许也曾有过作战经验,但绝不是面对湖骸这种怪物。
米迦勒起先拒绝这些平民加入猎兵队的战线,但最后还是妥协于将他们安排成后勤的一部分,给予他们光荣的……运输任务。他们每一个都老得可以当猎兵们的祖父母,米迦勒不知如何向他们下达除了撤退以外的命令。
那些从纳塔关卡溃散回撤的猎人情况也十分糟糕。他们的面庞死气沉沉,肢体乌黑不堪,像是从黑色的沼泽中爬出,每一个都颧骨高耸,眼白泛青,许多人原本细心保养的外衣与软甲已经破损得完全看不出原本的样子。出于对先行接敌部队的敬意,米迦勒示意猎兵队为他们让道。那些归来的猎人像幽灵一般穿过了猎兵的队伍,仿佛从从未真正看到过任何人,眼中不再倒影出任何事物。
这些猎人遭遇了什么——新兵瞪大了眼睛,看着那些失魂落魄归来的猎人,不安地用手势比划出自己的疑问——他们好像丢了魂一样。
“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了。”米迦勒望着他们的背影,幽灵的队列穿过了一排排空置的屋宇,消融在这座即将化作血肉熔炉的城邦中。
“做好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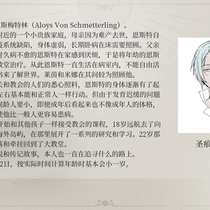
- 在这样一个企划迎来结局的时刻,我终于写完了序章……
- 赦罪演武的对手是没有详细设定的背景板猎人。
- 含有部分个人解读与私设,如有冲突请以企划方为准。
她在梦中穿越一处灌木,树枝划破了裙摆,锋利的叶片也割伤了肌肤。血还来不及落下,就被已经愈合的皮堵在里面,可她依旧只是一心一意地拨开枝叶,想要到达对面的地方。
好像有什么人在那里等着自己,她无端确信,却只在小片空地上遇见了篝火的余灰。
总觉得自己忘记了重要的事,也总觉得自己忘记了重要的人,可是在清醒时,就连自己已经忘记了这件事都忘记了,正如烧灼过后的灰烬由指缝间滑落,滑落,然后飘散在水面上,激不起一点涟漪。浸透了水,就深深地沉下去。
她望向水面。真是一张陌生的脸。
不是图省事的编发,而是精心打理的长卷;不是耐脏的长服,而是华丽的衣裙。最陌生的还属那双眼睛,那种笑起来的方式也不知道它来自于哪里。记忆空空如也,只余碎裂的回声。
陌生的女人回望着她,随后便被破开水面的手搅碎倒影。冰冷的水从镜面下回握她,从深深的潭水中捧起某物,递至她的面前。
她打开日记,纸页上只有晕成一片的蓝。
现实与梦境罕有不同,对萨曼莎而言,两者的概念同样模糊。她在现实里经历梦境,也在梦境中搅碎真实。
从有记忆以来,自己就一直生活在教堂中,可这样的记忆也格外朦胧。取得了血液就食用,取得了任务就实行,有可以安置的地方就闭上眼睛。只是这样而已。但如果只是这样,和徘徊的游魂也没有什么区别。
沐浴在夕阳的余晖中,她事不关己地想着,为什么自己还没有去死呢?一定是还有什么事情没能做完吧。但自己已经不记得了。
是这样吧,也只能这样解释了。她想着,否则就没有办法解释了,为什么已经变成了尸体却还是一个劲地想要行走,要被人杀死的时候还要杀死人。她靠在中庭角落的石墙上,阖着眼,感到温暖却日益稀薄的柔光一寸一寸地滑落下去。因为秋天到了。这样朦朦胧胧的念头一闪而过,再睁开眼时就已经入夜了。萨曼莎大人,一张担忧的脸停留在面前,是教堂里的修女。她叫什么名字?她在记忆里搜获一空。
萨曼莎大人。修女摇晃着她,已经入夜了,您不去参加赦罪演武吗?
对啊,差点就忘了。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以至于很多人对她迟到这件事都显得十分能够容忍。踏入第二礼拜堂时刚好有人喊出她的名字,她于是顺从地踏入武场。
可能是已经忘记了太多,她缺乏战斗技巧,只是无视一切,前往对方身边。既然会动,那就把能动的地方折断就好。如果不方便折断,那么直接捏碎也常常有效。
骨血碾碎于指间,每当这么做的时候,她都觉得自己碾碎的不单单是血肉。那是记得自己形状的骨骼和记得自己位置的血肉,是某种完整的、有了形体的、不会丢失和错乱的记忆。
好羡慕,我也想要。她伸出手,使劲地将它们握在手心。骨骼与血肉彼此交错,一瞬间粘稠不已,在她的手心里马上就混杂模糊,只是如同燃烧的蜡,不断地滴落在地。
萨曼莎猛地收回漂浮的神志,将被她抓住脖颈提起的男人丢了出去。与此同时,代表她胜利的裁判声从上方传来。
我还能战斗!男人挣扎着站起来,凭什么算她获胜?他就要拔出原本位于腰侧的刀,却看到刀柄留在吸血鬼的手上。
不可重伤。吸血鬼仿佛第一次记起这场比武的规则般缓缓念道,金属在她指缝间发出令人牙酸的呻吟,随后扭曲着掉落在地面上。
如果你是敌人,刚刚我就捏碎那里了。
——萨曼莎。
吸血鬼荡入梦境。
无比柔和的声音,呼唤她名字的方式却像在模仿不解其意的语言。每个音节都发声完美,呼唤者却不懂得它们所拼凑的含义。
——来。
萨曼莎睁开眼,发现自己竟身处森林。
就像是故乡。比任何一次都更真实,也比任何一次都更虚幻。树木与树木相依,在阴影中同彼此窃窃私语,描述着不被任何人梦到过,也不被任何人记住的梦。
所有死去的树木都在这里。所有曾生长过、不曾生长过的,还有仅仅在梦中才存在过的树木,所有死去的树木都在这里。它们和她一样,都是已经死去的东西。
——来。
那黑暗之中的东西呼唤道,窸窸窣窣的碎响交汇在一起。
——告诉我们,你的问题。
我能问些什么?在森林的尸骨中,萨曼莎忽而感到自己的思维清晰得就像针。你想要从一个记忆都不复存在的人那里得到什么疑问?
彼此相连的尸体摇动起来,它们一个接一个地向她俯视,穿透了她在死去之后仍然活动着的躯壳,将同样已经死去的目光深深刺入早已干涸破碎的深潭。
许久之后,它们开口。
——……你在找什么。
——你在找一个人。
声音逐渐确切,最终归为最初的声音。
——你在寻找你忘记的愿望。
我忘记的愿望……是什么?
树木颤抖起来,尸体在狂啸中摇动。
——一个问题!只有……一个!
它们叫喊,古老的森林在她面前轰然关闭。
萨曼莎睁开眼,从未感受过的清晰鸿沟划在梦境与现实之间。天花板的空白上夹杂着班迹,一如她被污染的梦。
胃中烧灼似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