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罗大陆,圣别纪元后期。
血族女王莉莉安突然失踪,几乎同一时间爆发的怪奇疫病让人类数量逐年锐减,失去管控的血族加上疫病的席卷,让整个社会动荡不安。
将一切扭转的契机在于教会发现血族的血液竟是能治好疫病的良药。
从此,以血液为中心的利益旋涡将整个世界卷入了其中。
【创作交流群:6911995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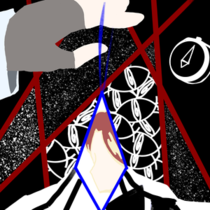







0.
如何穿搭,向来是一个十分难解决的问题。
就连血族也会为这种问题困扰。
“我的小宝石,明晚就是舞会了,该穿什么呢?”
时钟已经指到了六点,衣柜里原本挂得整齐的衣物被翻得乱七八糟,泽菲洛斯揪出一件看上去就有点年头的绸缎礼服在穿衣镜前比了比,又迅速给挂了回去,并对着自己的宠物蛇抛出了这个难题。
红色的大蛇歪着头,望向自己一筹莫展的主人。
【半个月前定做的那套衣服?】
“爆单了,加了钱也没赶制出来,听说我前面还有……”他叹了口气,掰着手指头数,“1、2、3……好吧,总之舞会的消息一出,全城的裁缝都要忙疯了!”
【吃了他!吃了他!】蛇摇晃着尾巴,兴奋地发出嘶嘶的声音。
“现在来不及了,等舞会结束再说吧。”泽菲洛斯把另一件带拉夫领的老旧衣服塞回了衣柜,“拖欠的时间就让他用命补。”
【之前那套有乱乱花边的衣服呢?】
“上次月下宴的时候被撕破,”回忆起上次自己衣服的惨状,嗜血血族不由得伸手摸了一下自己的肩膀,“早丢掉了。”
【你下次去就应该什么都不穿!】
……
泽菲洛斯瞪大眼睛看着自己的爱宠,一时间在思索是不是饲养时出了什么差错。而蛇则是理直气壮地看着他,吐着猩红的信子,似乎还在为了自己“很棒”的建议而沾沾自喜。
好吧,好吧。泽菲洛斯无奈地挑了挑眉,又转身再去翻找着自己的衣柜,把那一件件过于复古的款式挂到最里面。早年,刚从穷困潦倒与被死亡威胁的生活中逃脱时,他曾经沉迷于追一些所谓的“潮流”,在穿搭服饰上花下重金。但现在,那种蓬勃的消费欲早就被几百年的岁月磨光……
要不回头把这些压箱底旧衣服卖给文物商算了。
忽然,宅邸大门上的感应魔法被触发,与此同时,一阵礼貌的敲门声传来。斯佩妮从主人的脚边离开,向大门的方向游去。不一会儿,这条红色的大蛇就拖着一个看起来很沉的大盒子游了回来。
【没人,只有盒子。】她游到泽菲洛斯脚边,用头顶了顶那个大盒子。
泽菲洛斯顺手摸了一把她头上的小硬角,目光落到这个“不速之客”身上。这是一个沉甸甸的礼物盒,上面绑着缎带蝴蝶结,还夹着一张卡片,上面泛着淡淡的香水味道。
请在舞会时穿上吧——卡片上这么写道。
————————————————————
1.
秋日的夜,已经略显凉意。在晚风的爱抚下,大片大片的百合花如同银白色的浪,簇拥着当中被赋予“百合花”之名的广场。
月晖倾泻,一层淡淡的银色光辉铺洒在广场上,也为那些身着华服、脸覆面具的人们带来一丝属于月的神秘与诱惑。
今晚,人类与血族将共同分享这片月色。
当踏入这片热闹的广场时,泽菲洛斯下意识地伸手托了托单眼镜,但摸到的却是十分陌生的触感——带有蛇花纹的假面遮住了他的半张脸。
虽然假面舞会上,所有参与者都要戴上一副遮挡真容的伪装,但凭借血族对气味的辨识——与紧密血脉的感应,他还是轻而易举地在层层叠叠的伪装下嗅到了熟悉面孔的味道。
星月交辉下,少年铂金色的头发映着淡淡的光泽,他身着款式简洁修身的舞服,正在与身边的人交谈,而就在泽菲洛斯的目光投向他的一瞬间,他也侧过头来,回望过去。
视线隔着潮水般的人群相汇。
那视线对泽菲洛斯而言,就像是阳光一般无法触及,仅仅相碰就要将他燃尽成灰。他迅速地甩开目光,用手扶着面具没入人群之中。
落荒而逃。
血族没有心跳,若他还是百年前的人类之身,恐怕心已经要跳得从喉咙里蹿出来了吧。确定已经离西雷很远后,泽菲洛斯才缓缓地长舒一口气。他整理了一下领口的花边,将那张小小的卡片从口袋里翻出来。
“是26号啊……”他轻轻地念出那张标着数字的小卡片,抬起头来向广场的人群望去。
会是同族还是人类呢?
他偏爱惊喜。
……
而惊喜总是姗姗来迟。
当舞曲被奏响,柔顺如绸缎的乐声回荡在百合花广场上空时,这场假面舞会也徐徐拉开帷幕。在皎洁的月华下,戴着假面的人们成双成对地起舞,他们跳起优雅流畅的舞步,如同百合花丛飞过的一对对蝴蝶。而泽菲洛斯则是迈着轻快的步伐,灵巧地从五色斑斓的蝶群中穿梭而过,寻找着由神指引而来的人。
就在第一支乐曲落下最后一个音符时,绚丽的蝶群扇落翅膀,一个娇小的白色影子跃进舞池,这是个栗色发上还沾有树叶的女孩,她眨着大眼睛,好奇地向舞池里张望。与她一同进来的,还有另一个黑红色的身影。
黑色的圆礼帽上有着设计成蛛网的装饰,红色的薄纱遮住了面庞。身着黑与红交织的礼服长裙,那身材纤细的少年不像是加入舞会的蝶,反而像是前来狩猎的蛛。
他捏起手中的卡片,目光向周围望去。
26号。
“敬这月色,想必您就是我今夜的舞伴。”泽菲洛斯缓步走来,向这同族的少年行礼,将卡片摊在掌心里递给他看。
那少年的视线在两张数字相同的卡片上游走了片刻,一双天蓝色的眼睛直视起自己面前的男人。
“感谢命运的指引,今夜能与您一同起舞,是我的荣幸。”泽菲洛斯向他伸出手来。此时,他看着面前的同族,忽然觉得气味有些许的熟悉。
与此同时,一阵秋夜细风吹动百合花丛,音符也从淡淡的花香中萌发,顺着风跳跃在广场上空。第二支乐曲较之前轻快许多。
泽菲洛斯伸出去的那只手,被这金发少年猛然拽住。即使是透过面纱也能看到,在乐曲奏响的同时,那双蓝色的眼睛里好似闪起星光。
“看,鸟儿在森林中飞翔,花朵也为它绽放!”少年欢快地笑起来,拽着泽菲洛斯的手,将他拖进舞池中,“来跳舞吧,跳舞吧!”
伴着轻快的乐曲声,金发的少年随着音乐节奏而迈开舞步,他伸展着自己柔韧的肢体,月光在红色的衣裙上流动,那犹如蛛网般的裙摆扬起了风的弧度,高跟鞋点在染成银白色的地砖上,就像轻掠过月下湖面,激荡起了一层层水波。
是在夜中跳跃的火。
泽菲洛斯牵着自己舞伴的手,随着他的舞步而跃动,耳边的风声与音乐混在一起,将世界都隔绝在外。对泽菲洛斯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他从未想过自己的舞步也可以迈得这么轻盈,就像是两只穿梭在林中飞鸟,从广场的一端飞舞到另一端。
“哈哈,好开心!像飞!”
轻纱随风飘起,露出藏在下面的年轻脸庞,少年的眸子望向前方,畅快地放声大笑,一阵天籁般的歌声从他的喉咙中迸发而出,随着他旋转不停地舞步在夜空中摇曳。那纵情的旋律无比绝妙。被那从心底流露出的乐章缭绕,泽菲洛斯一瞬间有些失神,脚下顿时乱了一步。
就在他打了个趔趄,眼看就要摔倒时,手腕上传来的拉力将他拽了回来。他今夜的舞伴哼着轻快的曲调,牵着他旋转一圈后,稳稳地落下舞步。
“是我疏忽了,”泽菲洛斯抱歉地笑了笑,“您的歌声太过于美妙,让我听入迷了。”
金发少年歪着头,冲他咧嘴笑了一下,又哼起了一支柔和的曲子。
舞曲还在继续,他们的舞步也并未就此停歇。而刚听到前几个音符,泽菲洛斯立刻反应过来:“是《星夜下的帕蒂塔》的序曲?啊,今夜确实繁星闪烁,如此优雅……”
“你听过?”
“是啊,”说起这个,泽菲洛斯顿时提起了兴趣,“毕竟是那位家喻户晓的音乐家罗伦兹的曲子,当年《落日之底》公演时,真是一票难求呢。”
当说出那个名字时,他忽然觉得对方的手握得紧了一分。那双天蓝色眸子中,满盛着欣喜。
泽菲洛斯想起了什么。
“说起来……我确实见过您,不、不……”泽菲洛斯看着自己面前的少年,眉毛微微扬起,“是听过歌声。虽然风格过于迥异,但应当是您,在某个月下宴时……”
他努力地回忆着那夜偶然飘过的歌声,与似曾相识的气息,而舞伴的步子却逐渐加快。虽然没有回答,但看得出来,这少年的心情比刚才更加快乐,他一边哼着歌,一边拉着泽菲洛斯在舞池中翩然旋转。
就在这时,泽菲洛斯瞥见那个站在广场一边的熟悉人影。
即使穿着与平日简朴装束不同的礼服,用黑色丝带将双眼半遮起来,但也能一眼就看得出来身份。那个站在一旁望向舞池的人,就是自己唯一的人类朋友——莱尔德医生。
奇怪,他怎么一个人光顾着品酒?
“那边有一只落单的人类,不如我们……”泽菲洛斯起了个话头,目光移向莱尔德医生。而他的舞伴也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冲他咧嘴一笑。
“这位先生,一个人多无聊,来跳舞啊!”
“来吧,来吧!”
两个人在瞬间达成一致,一人牵住莱尔德的一只手,将毫无防备的人类拉下舞池。
“哇啊?!”无辜的医生慌忙倒腾着脚步,但还是被这两个坏家伙拉到了舞池中央,牵着手跳起了欢快的圆圈舞。
……
在嬉闹与欢歌中,这支轻快的舞曲蹦出最后几个高亢的音符,鸟儿振翅向夜空飞去。莱尔德医生被拉下舞池后,显然十分受欢迎,在这支曲子结束后又受到了其他人的邀请。虽然在这假面舞会中,人类与血族模糊了界限,但那甘甜的血香味可不会骗人……
至少、至少不会出现死亡。
目送着友人离开并默默祝他好运,泽菲洛斯缓下步子,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领。
“真是个愉快的夜晚,”他对今夜的舞伴礼貌地笑笑,“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讨论音乐,啊……如果您不介意交换姓名的话,我的名字是泽菲洛斯。”他轻轻地念出自己的名字。
那金发的少年没有立刻回答,只是看着他。在那一刻,泽菲洛斯有种自己被审视的感觉,甚至已经打好对方被自己冒犯的设想。
“抱歉……是我太唐突……”
“李文诺克斯。”
少年说出了自己的名字,还未等泽菲洛斯回答,他便扬了扬手,转身向广场的人群中走去。
“下次一起玩吧。”
那抹红色向月光下的银池跃动而去,瞬间没入舞会川流不息的人群中。
——————————————————
2.
又一支舞曲奏起。
这是一支舒缓优美的曲子,描绘着秋日湖边娴静的景色。而泽菲洛斯已经离开舞池,缓步在广场边走着。
他在找一个人。
可能是在执勤?那个人并不喜欢跳舞,也对这项优雅的交际活动没有任何兴趣,但环顾四周,穿着教会猎人制服执勤的人中,并没有那个人的身影。
真是有些失望,嗜血血族这么想着。如果碰到的话,他真的很想试试在对方执勤的时候来点意外的举动,在那张面无表情的脸上看到点出乎意料的神色……就像几百年前那样。想到这里,他情不自禁地舔了舔嘴唇。
戏弄正直又寡言的人,相当有趣。
就在寻找自己的目标时,他又在舞池外看到了熟人。
“晚上好,奥斯顿先生。”
面容掩盖在羽毛假面之下,那身着华贵礼服的亚麻色头发的绅士正在望向舞池,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字,便回过头来。
“泽菲?”看到老友冲自己快步走来,克劳伦斯·奥斯顿的脸上顿时显露出欣喜的神色,“我就知道,你肯定不会错过舞会的,我的老朋友!我们有多久没见了?”
“上次诺瓦利斯给你新的曲子时,我想。”泽菲洛斯摊开手,咧嘴笑起来,“哈哈哈!这么说来,他又拖够了十年?”
故意提起这件事,他满意地看着朋友的表情逐渐变得痛苦。
“没关系,毕竟我们的时间还多着呢,”他善解人意地拍了拍老友的肩膀,“还有下一个十年……加油啊,催稿的奥斯顿先生!”
“说起来,我刚才看见西雷了。”就像是回击似的,克劳伦斯直了直身子,侧目看着掩饰不住恶趣味的嗜血血族。而他也满意地看到对方的笑容在言语片刻间被冻住。
“嗯,”泽菲洛斯收敛起脸上笑容,目光向一旁撇去,“我看见了。”
“……”克劳伦斯张了张嘴,欲言又止,终于还是叹了口气。
“奥斯顿先生,我觉得……”泽菲洛斯伸手摸了摸自己脸上的假面,声音越来越低,“已经几百年了……可能我做得有点过火。”
“哦?”古老血族不由得扬起眉毛,“这么说……”
“毕竟他是我的……”泽菲洛斯只觉得自己的舌头有些打结,可他始终还是不想吐出那两个字,“你也知道。总之,我有点后悔,我们之间不应该是这样的。”
“唉!”克劳伦斯紧锁的眉头终于舒展开,他就像是忍耐了许久,终于长舒一口气,“天啊,你早就该这么想!这可是个天大的好消息!那么,你打算什么时候跟他和好?”
好友表现得比自己还要积极,泽菲洛斯一瞬间有些慌神,他只是说出一个想法,并没有马上就要付之于行动啊!
“我、我想……可能就是最近吧?”他挠了挠下巴。
“宜早不宜迟,”古老血族的脸上浮现出欣慰的笑容,面前这个傻孩子终于开了窍,“尽快吧!这不管对我还是乐团都是好事!”
泽菲洛斯恍然意识到,自己和西雷的事情大概已经困扰这位乐团管理者三位数的年份了,他顿时有些尴尬,只好连声答应:“会的,我会的,那我先走了!”
话音未落,他就飞也似地从奥斯顿的面前逃离。
刚刚萌生的想法就在瞬间落地成为一项计划,泽菲洛斯觉得自己的脑子可能又要为这件事“加班加点”了。
————————————————————
3.
最终,他在广场外的角落找到了目标。
在舞池之外,教会还贴心地为人类宾客准备了餐饮,衬着刺绣桌布的长桌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丰盛的食物与饮品,除了盘子里那些用糖霜画着可爱图案的小点心,还有各色的派与蛋糕,以及……
正在撕咬鸡腿肉的长毛大猫抖了抖胡须,警觉地向身后投去目光。当嗅到那个令它讨厌的味道时,它立刻弓起背,橘色的被毛炸起来,发出威吓的哈声。
“我说你跑哪去了,还以为你在执勤,”泽菲洛斯走到黑发的青年身后,双臂环抱在胸前,不自觉地扬了扬眉,“原来是在这公款喂猫啊?”
戴着眼罩的黑发青年并没有立刻回答他,只是伸手将自己的猫揽进怀里,轻拍了拍它的身子,安抚着情绪。
“你在找我?”待猫恢复了平静,教会猎人才缓缓地转过头来,回答嗜血血族的问话,“我请假了。”
“为了跳舞请假?”
“格拉特尼说想换口味,”拉斯特抚摸着大猫柔软的毛发,他虽然时常面无表情还寡言,但对待这只猫简直充满了一种无声的宠溺,“我就带它来了。”
“好吧,好吧,真是个好理由。”泽菲洛斯走到长桌边,目光向桌上的食物扫了一眼,“总之,我非常期待明晚的演武。”
他微笑着向拉斯特望去。但那笑容之下,潜藏的却是压抑了几百年的某种情绪,或者说,是检验自己曾经杰作的期望。
“我也很期待与你交手。”完全没有意识到对方话语中潜藏的东西,拉斯特点了点头,又伸手挠了挠猫的下巴。
“那么,明晚再见。”
……
拉斯特目送泽菲洛斯离开,当他再向长桌望去时,发现其中一盘小羊排已经不翼而飞。
————————————————————————
4.
把打包回来的小羊排喂给宠物蛇之后,泽菲洛斯将那套神秘的舞会礼服小心收好。
结果,经过今夜的舞会后,疑问还是没有解开。
所以衣服到底是谁送的?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