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罗大陆,圣别纪元后期。
血族女王莉莉安突然失踪,几乎同一时间爆发的怪奇疫病让人类数量逐年锐减,失去管控的血族加上疫病的席卷,让整个社会动荡不安。
将一切扭转的契机在于教会发现血族的血液竟是能治好疫病的良药。
从此,以血液为中心的利益旋涡将整个世界卷入了其中。
【创作交流群:691199519】
“需要我的帮助吗?”
雷涅听见了一个陌生的声音。由于同行的居民很多,脚步声杂乱,他并没有发现多了人。他回过头,发现一个穿着黑色斗篷的男孩在他身后,个头不高身板也瘦,年纪看起来也就成年前后。哪儿来的孩子?也许是新加入的工会的猎人吧。“你怎么一个人在这种地方?你这样的小鬼在外面晃荡是容易出事的。”
男孩面不改色地回答:“我正在找人……正好要回工会,能让我顺路一起过去吗?正好也许能帮到你。”
你能帮到我什么?不捣乱就差不多了。在雷涅眼中,这个男孩看起来毫无战斗的能力可言,也没有带什么明显的武器,只提着一个手提箱,很难想象他以什么心态讲出这段话。但好在他态度还不错,即使内心生疑,雷涅也以默认作为应答,继续背着伤员向前走了。男孩走到了行列的最末,扶住了一位腿脚不便的老人,帮助她赶上队伍,走到了没有过于脱节的位置。“谢谢你,年轻人……”老人的声音在寒风中响起,又迅速地消散,四周又只剩下踩在雪地中的脚步声。
这段路已经往返多次,雷涅已经很熟悉了,所以行进的速度越来越快——当然他也心急,拖得越久越容易遇到袭击,以至于忘记了还有走不快的人在。这个小子倒是细心发现了这个。不过他认为这件事没什么大不了的,就算这个男孩没有急着过来,也会有队伍后方其他人发现的,所以这件事并不算“帮忙”,顶多算“凑巧”。想到这里,他又回头看了一眼,发现那个男孩已经在队伍靠中的位置了,除了扶着老人,旁边还跟着一个只有半人高的小女孩。那个女孩和父母走散,到刚刚为止还在哭,而现在看到了有个年纪不大的人,脸上已经露出了笑容,而男孩也正冲着她温和地笑。
雷涅的疑心更重了。无论如何,这个男孩的气质看起来根本不像猎人,但看起来也不像一般平民,有些说不出的特别。猎人的直觉告诉他,这家伙肯定不是吸血鬼,而且不会是坏人,但他的心头仍缠绕着疑虑,还有更多的不自在。他挪动了一下肩上背着的人,又忍不住回过头,去看那男孩到底什么来头。男孩的头发和雪的颜色接近,肤色也有些苍白,脸颊被冻出玫瑰色。他走路的步子算不上太稳,也许是因为行李箱有些重量。无论如何,雷涅都认为男孩的身体状况绝对不能算十分健康那类,这不禁让他更担心起来。而这种思考又让自己有些分心,分心则会影响他对四周状况的判断,导致他的焦虑进一步提升。
寒风呼啸着吹在每个人的脸上。异样的感受让原本轻车熟路的护送变得难熬,路程好像也变长了。
男孩突然走到了自己的身边:“先生,我认为该休息一下了。”
“为什么?”雷涅低头去看。他十分不习惯有人指使自己,何况还是个看起来未成年的小子。
“我觉得大家有点累了,我还想检查一下您的伤口。”这时雷涅才发现男孩的嘴唇是比较淡的粉色,看起来似乎有些贫血。
“我的伤口?”
“您的左肩在流血,而且还背着伤员,负重会对伤口持续施加压力,不利于伤口的愈合。”
“就这点血,还不如给储血器流得多。”
“不只是流血,不愈合的话还会提升感染的风险,再加上冬天伤口愈合的速度本来就更慢……”
“够了,”雷涅打断他絮絮的声音,“你到底是来帮忙还是来找茬的?我不需要这种影响效率的提议。”
“先生,我是不希望您的伤口影响到之后的工作,您不应该如此短视。”
“短视?你不仅怀疑我的身体状况,还怀疑我的决策?”雷涅皱起眉头,音量也提高了一倍,“你究竟是什么人,哪里来的勇气质疑一个老猎人?”
“我……”男孩仅仅说出了一个字,就卡住了。他将目光移向一侧,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好吧,我尊重您的判断。继续前进吧。”
说完,男孩转身回到了队伍里。雷涅看着他的背影,怒火未平,加上尚且还不知道他是什么人,胸中又多了一份郁结。
冬季的白昼过于短暂,天空开始转暗,气温进一步下降。即使没有到完全天黑,这样的时间也已经影响了视野和判断,开阔的道路顿时变得昏暗不明,险象丛生,大家行进的步伐也变得更慢。雷涅心想,无论如何都要在天黑前把这批人送到安全的地方。他计算着距离和时间,决定加快速度——他向身后的男孩喊:“小子,你看住最末尾,不要让人掉队。”没走一会儿,他就听见后面男孩的喊声:“先生,老人和小孩跟不上。”
“别叫我先生了,我叫雷涅。”雷涅回头看,果真老人和孩子已经到了队伍的最末尾,而其他人也显得非常疲惫。他心中愤愤地咒骂了几声,又看了看迅速变暗的天际,回答:“临时休息一下。”当然此刻他的心中并不觉得是采纳了男孩的意见,而是因为他耽误了行程而不得不停下。
一行人挤进了一间破屋,生了个火。一位妇女拿蔬菜和调味料煮了点暖和的汤,分给大家吃,雷涅当然没有接受,而男孩也说不要。
雷涅坐在门口的位置,时刻警惕屋外的动静——这里如果冲进来一个湖骸,造成的后果可不是开玩笑的。正在他侧耳倾听的时候,男孩提着箱子来到了他的面前:“雷涅先生,让我看看您的伤口。”
“……医疗物资这么紧缺,还是给需要的人吧。”
“队伍里那位伤员我已经看过了,他失血比较严重,需要休息,但是伤口本身已经止血了。”男孩一边说,一边打开了手提箱——里面装着绷带,药瓶,注射器和一些他叫不出名字的玩意,“我先给您的伤口做一点简单的处理,至少不能就这样裸露在外面流血。”
“……你是什么人?是斯塔夫罗金医生的人吗?”
“斯塔夫罗金是谁?”男孩开口问着,手里却没有停下。
雷涅深深地皱起眉头,低声问:“你居然不知道医生的名字?”
男孩悄悄看了一眼雷涅的表情,把一些药水涂在了棉花上:“抱歉,雷涅先生,我本无意欺骗你,但我不是猎人。”
“你是谁?”
“我来自大教堂,过来查看纳塔城的情况,并且在寻找几位有恩于我的猎人。”
“大……教堂?”
说到这里,男孩才放下手中的东西。他解开了斗篷,还有领口的扣子,仰起头露出了脖子——上面有一列十字形的烙印。“我是一名神父。也许您认得这个。”
雷涅仍停留在惊愕中,而年轻的神父已经回到了手头上的工作——他拿着涂上药水的棉花,伏在雷涅的肩头,把伤口上的分泌物和一些杂质给擦掉,又擦干净了伤口边缘的血迹和污渍。也许因为他戴着眼镜,雷涅感觉他擦得非常认真。雷涅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刚才的种种疑虑瞬间就有了答案,但此刻他已经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思索片刻,他趁着年轻神父去拿绷带的时候说:“这些东西都很珍贵,还是留给其他人吧。”
“在我眼里普通人和猎人都是人类,也没什么差别。”神父把绷带一圈圈地缠在雷涅的伤口上,“绷带本身不是什么要紧东西,拿普通的布煮沸消毒也可以替代,您不用担心。”
处理好了之后,神父又把东西一件件收拾好,合上了手提箱。雷涅看着神父脖子上的圣痕,仍然感到了不真实感:“你看起来像个孩子……”
“虽然成为神父的时间不长,但我不久就要 22 岁了。”神父扣好了上衣,又重新披上了斗篷,“抱歉,忘记自我介绍。我叫做恩斯特。”
“恩斯特、神父……”
“没关系,叫我恩斯特就好。”
雷涅改变了想法。不过与其说是改变了想法,不如说是被迫这么做。重新启程时,他让恩斯特站在了队伍的最前方,还让他举着火把——他害怕这位年轻神父出事,打算让他保持在自己的视线里。神父自然照做了,还牵着那个不愿意离开他的小女孩。火光照亮了两个瘦小的身影。而队尾则安排了几个年轻人,他们有脚力,也能看着队伍中的人。雷涅背着伤员,走在队伍的中间,警惕地观察着四周。以保证无论哪里有动静,他都能迅速地照顾到,还能保护肩上的伤员。
这样的安排,雷涅自认为合理。只是他没把握,湖骸会不会有视力,把举着火把的人当作攻击目标。他甚至想去征求一下恩斯特的意见——但是时机已经错过了,已经这样继续上路了。包扎过的伤口好受了一些,但也仅限于此。浓郁的黑暗调动了更多不安的情绪,连月亮也躲在云后,不愿赏脸多借一份光来。
在队伍的最前端,举着火把的恩斯特也四处张望着,时不时也回头看看。火光下,恩斯特的神情中有藏不住的忧虑,雷涅也知道这黑暗着实令人害怕。他忍不住开始祈祷——他很久没有这么做了。他不知道这有没有效果,但也想不出更合适的办法——他希望神能保佑这个瘦小的神父。
霎时间,一阵猛烈的寒风吹过,吹得所有人都不得不停下了脚步。雷涅站稳了步子,只见眼前的火把被风吹熄了,一瞬间眼前陷入了绝对的黑暗。他想喊神父的名字,而开口却发现声音被风压盖住,无法传达。风吹开了云,一轮皎洁的月亮显现其间,将清冷的光芒无私地洒在林间步道上。然而光照亮了人,也照亮了人身边的黑色怪物。
“当心!!”雷涅大喊着,已经来不及赶过去。他看见月光下,神父敏捷地将火把挥向怪物的“头部”,又不知道从哪里迅速地抽出了一把小刀,砍下了一只伸向他的“触手”。这一切都发生得很快,但又很漫长,神父银色的发丝闪耀着和雪一样的白,而刀尖的反光更像是寒冰一样凛冽。他没有想到这个后生确实能战斗——看到他手提箱里的东西时,他彻底信了这是一个医生。
然而接下来的一切更拥挤地发生在了一瞬——小女孩开始尖叫,恩斯特试图去保护小女孩,更多的触手同时从几个方向向两人袭来。恩斯特似乎迟疑了,他最终选择了保护那个小女孩,将自己的后背朝向湖骸。多么危险无谋的举动,怪物的触手可以轻松穿刺这两个孩子瘦小的身体。雷涅已经没有任何时间和心情去咒骂,他举起自己的镰刀将远处的触手砍落,近处的则用身体挡住。触手打在雷涅肩上的盔甲上,发出令人不悦的金属声,同时从怪物黑暗的内部也传来刺耳的尖啸,好像在宣泄不满。
平民们骚动,尖叫,迅速地逃走,而恩斯特也很快地将小女孩推开。“雷涅先生……”
“快走。”雷涅一句话也来不及多说。他高举着镰刀,趁着湖骸还在叫唤时多斩断了几节,黑色的不明物体混着残肢散落在雪地上。恩斯特似乎也明白了在真正的战士面前自己也毫无用途,便也护着其他人退下了。没有后顾之忧的雷涅开始了战斗,他瞬间感到镰刀变轻了,湖骸的叫声好像也变远了。这滩可怜的怪物,爬到这里来也就是为了受死,他想。怪物无意识的攻击和无意义的哀嚎都不是老练猎人的对手,除了稍有些不讲道理,那毫无智能的行动远不及狡猾的吸血鬼或会呼吸的怪物。他看得清湖骸所有的意图——它试图再生,接上残枝,又或者看上了自己的某个部位而攻击。他一一化解这些行为,怪物的巨体被削减得越来越少,哼唱着的美妙的歌曲也变成了气若游丝的呻吟。当雷涅把镰刀的刀尖刺入湖骸中心时,湖骸的身体开始激烈地抖动,而顺着弯曲的刀尖,钩出来的一个已经看不清脸的头颅,后面还跟着一节断了一半的脊髓。湖骸剩下的躯体也不再动了,叫声也停止了,一切归于寂静。一阵风吹来,在四散的残骸上盖了一层薄薄的雪。
雷涅回过神来,才发现这场战斗更像是一场凌虐。当然,这也是他想要的。他必须活下去,因此要杀死每个猎物——不留给他们“复仇”的余地。他平缓着呼吸,重新感受到月光,黑暗,寒风,和腰侧被血浸湿的地方,已经变得冰冷。他回头去看其他人:平民们小心翼翼地走近,好像松了口气;而神父走在最前面,一直在走到自己的跟前。“你受伤了……”他的声音颤抖,语调也不平静,“是我害得你受伤了。”
雷涅不知道自己的伤是哪个瞬间弄上的,但他猜测也许恩斯特看到了。他挥动了下自己举着镰刀的手:“别担心,不碍事。”
“不……我看见刚刚血溅出来了……”恩斯特的表情中的沮丧仅仅在月光下也清晰可见。
“说不定是湖骸呢。”雷涅一心只想赶快上路。
“让我看看吧。拜托了。”恩斯特抬头看着雷涅的眼睛,那目光实在是让人很难拒绝。
雷涅叹了口气,向四周喊道:“那大家也休整一下吧,看看有没有少了人或者少了行李。”
这次检查伤口和刚才完全不同。恩斯特的手一直在颤抖,若不是能看见他的脸,还以为他在抽泣。此刻的恩斯特已经没有最开始时那样有神采,眼里已经看不到光芒。
“如果要是伤到内脏,可是很难办的。”神父轻声说。
“没那么重,真伤到内脏我也是有感觉的。”
“我是说万一。”恩斯特终于清理好了伤口附近的黑色污渍,“放轻松,平缓呼吸,不要激动。您一直在流血。”
“我倒是想平静,但身体好像还不太听使唤。”
恩斯特将绷带按在伤口上,想尽办法试图止血,但血一直止不住,绷带不停地被血浸透,他不得不继续换新的。他焦急地用手背去抹额头上的汗,却也把血抹在了额头和头发上,而且毫不自知。
雷涅看着恩斯特手忙脚乱的模样,只想告诉他自己没事,但也想不出有什么话比起流血的伤口有说服力。“你认识露提亚吗?”
被冷不丁这么一问,恩斯特突然抬起头。他只愣了一下,随后流畅地回答:“她是教会的圣女,是个安静的小姑娘。我和她聊过一些……她不能说话,只能用纸笔交流。”
这一刻,雷涅才彻底相信恩斯特的身份,他自己也才终于放下心来。“那个小姑娘是我送去教会的……但成为圣女,是她自己的命运。”
“很多圣女都是教会收留的孤儿……毕竟没有人牵挂的人,才能被推上这个位置……”
雷涅觉得“被推上这个位置”的说法有些古怪,但也说不出理由。“你看,血止住了。”他开口提醒。
恩斯特重新低头检查伤口,发现血不再外渗。“太好了!”他喜出望外地把绷带缠实了。
收拾好东西后,两个人一同站了起来。恩斯特的个头只到雷涅的肩膀过一点,就这么并排站着,雷涅更能感受到他只是个孩子。但这个年纪的人能做到的事情,他好像也做得差不多了。这么想也不坏。剩下的交给时间就好。
接下来的一小段路,在恩斯特的嘱咐下,雷涅用没有负伤的一侧抬着伤员,而另一侧则交给了一名青年。火把被重新点燃,恩斯特小心翼翼地举着它走在前方,没有让它再次熄灭。最终,他们到达了破败的,但亮着灯火的地方——猎人的家园。平民被接走,而伤员和本不属于这里的神父,则送往医生的面前。
医生自然不认识神父,但好像也不太在乎他是谁。“你能做些什么?”
“斯塔夫罗金医生,我能完成最基础的伤口处理,包括创面清理、消毒、止血、包扎、换药,还可以独立完成皮下或者静脉注射。一些简单的病情判断,以及安抚病人的工作我也可以做到。”
“那你跟我来。”医生将恩斯特带到安置伤员的区域。离开前,恩斯特回头看了雷涅一眼,就好像是之前在队伍前方时回望的一瞥。那眼神好像是想要说些什么,但最终也只停留在一瞬间的眼神交汇,更多的表情和言语都未留下。
但唯一能肯定的是,日后唠叨自己的人就这样又多了一个。
————————————————————————————————————————
剧情简介:教会来的牧师(读作医疗兵)来了,去纳塔城找教官和学长,被雷师傅一把子抓走,之后一直都是工会一名默默耕耘的男护士。
斗胆写了雷师傅视角,但想写的全没写出来!支棱不起来!就当先打了个照面!
后面的故事请看医生(你不可不看!不可不看!! )这段剧情正好接下篇开头
http://elfartworld.com/works/9230093/
http://elfartworld.com/works/92300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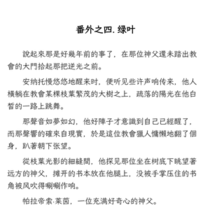
教会名下福利设施众多,最开始只是简单的福利院,收了些落魄至极的鳏寡孤独。后来逐渐分流,将儿童单独拎出,老人另设住所。又与医院机构合作,病重者可直接来到教堂准备后事。从平房一步一步到如今地院栋,教会所绘已不再是信仰之想象,所聚为信仰的力量。
塞勒涅的年纪比不上这些楼栋。她初进教会时,整日坐在忏悔室帮助开导。不过半年便开始处理文书,数着人头,贴点标签。渐渐地,也许是她家中从商所带来的敏感,慢慢地帮忙负责物资,教会内要举办地大小活动,大家都会来问问她的意见。好像她不是一个修女,而是场外援助的参谋。
参谋休息的时候,会朝着教会正门的方向,吹吹风,远眺一番。那里有大理石的拱门,周边灌木修葺整齐,信徒沿着道路,头顶阳光,或望或踌躇,前往教堂内祈祷。有徒步者,也有从马车下来的贵人。风起树林细簌,顺着脸颊撩起鬓发,塞勒涅叹气,今天吹的是南风啊。
秋末时节是没风的,空空使得枝叶返尘,嘈杂坠地,仿佛还是夏日的喧嚣模样。没有风,塞勒涅也就不会望着正南的教会拱门。参谋修女最近异常忙碌。越冬的衣物应该准备上了,还有预备的柴火,以防万一还得储备足够的粮食。养老院那边,需将去年的衣服取出,清洗干净各个分发。除了每人换厚被,还应准备多余的被褥,冬天可不方便晒洗床铺。何况冬天是老人的一道坎,屋内备好充足的木炭,提前准备墓地也不算多余。至于儿童那边,就要准备好药膏,避免冻伤烧伤。
笔记本上她写得顺畅,这些注意事项之后会传达给各位人员。接下来她查阅了教会的库存,向玛歌修女申请预算并外出。
纳塔城还是那副热闹样子,塞勒涅顺手拜访了独居的父亲。曾经的商人也在做过冬的准备,收拾了行李,打算去南方的温暖老家过冬。道别时父亲给予女儿一个轻飘飘的吻,“我会先去看看你的母亲,再回老家一趟。”,“替我向她问好。”塞勒涅轻巧眨眼
女儿已不是十年前活泼的模样了,似乎在母亲患病后,她的话少了很多,不再是当年蹦蹦跳跳的小麻雀了。如今成为了修女,一家人聚少离多,一些交流只能委托各地的猎人传送信件。这样的现状,让他思虑以后是否有团圆。不知春天能否还会到纳塔城居住,父亲有着犹豫,却依旧承诺“春天了我们再见面。”
“嗯,到时候我们一起去踏青吧,正好放放风筝。”
扑朔的北风立刻来了。不过是一场雨的功夫,气温骤降。夜晚的养老院,咳嗽声此起彼伏,虽然门窗捂得严实,可总觉得寒冷。屋内并无寒气侵袭,可对于老人,生命也已是寒冬。他们的生活已如冬季的草地,铺上了皑皑的雪,万里不见生机。一望枯燥,二望迷茫,三闭目,已无所可看。陪伴者所能做的,不过是在飘渺的白雪中堆起雪人,让他们怀念春天罢了。
教会加大了人员投入,夜晚分两班执勤。塞勒涅能力出众,足不沾地,接连照顾了几天,实在是没空回家。好不容易抽空回家,推开门,信件堆积在门垫上,乱糟糟的。她先挂好披肩与外套,再环抱起那堆纸片,尽量小心地落在茶几上。拂去沙发上浅浅的灰尘,弯腰取出信刀,塞勒涅侧躺下,一脚架在沙发扶手上,慢悠悠划开信件。
大写字母瘦长得夸张,连笔勉强能认清,好像又激动,又想写得尽量漂亮。M先生字如其人,做到了真正的见字如面。信件内容不过是一些提议,从未逾距,只提自己,不谈他人。M先生的造句有种撇脚的合理,话题从工作到琐事所见,语气从生硬到自在。塞勒涅翻个身,趴在沙发上,两条腿来回晃荡,琢磨M先生的心意。似乎被雇佣者的身份拘束,或者是他个人的社交风格,无论如何,他的话都带着拮据与克制,时不时提出一句“我可以帮您……”云云,仿佛他们之间的交往止步于此。最后一封信提到他不日就要启程前往斯奎尔农场,天气寒冷,需自行保重。信末“想必您这几日忙碌,若有空闲还需歇息,切忌劳累染病。期盼与您再见面。”
字迹诚恳用力,一转前几封的飘逸,末尾署名留了长长的墨点。不知他在犹豫何事。
她起身,抽出纸笔,本想在书桌前回复。思虑片刻,却先往壁炉里加了柴火,找了柔软的毯子,大剌剌拖拉椅子。柴火噼啪作响,火光跳跃,室温逐渐升高,焚烧的木香与疲惫一同涌上。塞勒涅卸力躺靠,头往左侧歪去,信纸压住毛毯,落笔时纸张向下凹陷。
问候语信手拈来,纸张沙沙作响,却戛然而止。
塞勒涅脸贴笔身,思考片刻,忍不住苦笑:坏了,她也犹豫了。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直到十二月,教会的工作才算稳定,教会人员终于能够熟练应对各种突发状况和日常工作。再也不会被人叫住,“塞勒涅修女,食堂有情况!”没人知道那情况是抽经,或者中风?每日工作就像抽签,难以预料,惊喜连连。
至于塞勒涅所受到的信赖,不过是有着好记性:每一种突发情况她都记得如何应对,即使她手法并非顶尖。最初她也没有经验,呆呆听从安排。如今成了指导者,处境不狼狈,心情很疲惫。
大家能够自觉工作,而非寻求指导,她也就清闲些了,取出了新购置的兔毛大披风,每晚在教会的澡堂享受一番,回家过夜。可瞬间风向突变,最开始是教会猎人被派遣,只一天就离去了一大半。第二天依旧有人离去,一问原因:铃兰内海突生湖骸,顺河流而上,向着纳塔城而来。
作为一个团结的集体,教会众人不需要公示,消息一传十十传百,病人也惶惶终日。这不是什么大事,修女们弯下腰,轻声细语,教会的猎人个个身怀绝技,英勇异常,湖骸以前从未有过,只是本次来势汹汹,众人以讹传讹罢了。安心吧——您……还能见到春天呢——
安慰声不绝于耳,语调悠长,乍一听恰像呵骗。塞勒涅瞅见这光景,咬咬唇,抱着物什从絮语一侧走过。她尽量放轻脚步,不打扰这片美梦。作为艾诺姆家的独女,且不提父亲餐桌上嘀咕的小心眼,她自己见过的自私自利者都不少。事实是这样,面对危险,有人作壁上观,有人铤而走险,鲜少有人现身而出,与其报希望于他人,她更着眼于当下。
父亲按照约定,通知到达农场的信件昨夜送到。落款12月5日,今天则是10日。不知中间五天的时差,父亲是否向南启程,至少目前来看,他和母亲都很安全。
要是他们有什么意外,估计又要花一笔钱,雇佣猎人去保护他们。既然父母没事,那么接下来就是物资,塞勒涅思忖,一步一步行至仓库门口。刚好她要取干净衣物,干脆检查一下仓库。
仓库有好几间,都存放了足够的生活物资。其中一扇门半掩,塞勒涅加重了脚步,靴跟敲打木地板,疾行到门口,驻足,先是叩门三声,再推开——这间存有医疗物资的仓库里面藏着几位修士。
昏暗的仓库照明不足,修士们举着灯,维持着躬身的姿势。他们的影子长长拖在身后,门外的自然光打断了他们的活动。后知后觉般,修士们望向往日的参谋修女,缓慢地直起身。
真像群老鼠,塞勒涅想,嘴上却说的敞亮“有谁受伤了吗?”
他们面面相觑,终于站直了,恢复了人样“没……没有……”
“嗯?没有?”塞勒涅目光落在他们脚边的包裹,皮笑肉不笑,“依我看,是你们病了。病的不轻。”
“逃出去?逃到哪里能安全?手无缚鸡之力的你们,估计都没有体会过长途跋涉吧?在路上遇到湖骸指望着好心人保护吗?”
“现在所有的教会猎人都外出了,即使还有留在此处的,不日也将出发。任何使用马车的申请都会被驳回,纳塔城的车夫肯定抓住机会狠狠宰你们一笔,你们只能用自己的小短腿上路了!”
“湖骸向着纳塔城来,那么必须突破关卡。在纳塔城彻底失守后教会才会被攻击。这是最糟糕的情况,但是相应的,湖骸的力量大不如从前。”
“是选择去更危险的地方冒险,为了你们所谓的安全,还是说留在教会,亲手给湖骸最后一击。孰轻孰重,你们自己估量。”
塞勒涅气势汹汹,面前的几位怔住了,一时之间没有动作。
看来应该更强硬些,她再添把火,“把东西放归原位……在我的视线里,建议您谨言慎行。”
她头也不回地走了,快步赶往厨房,又逮着几个收拾了干粮的修女,严厉说辞一番。之后不再关注去向。真正决心离开的人是留不住的,反而会洗清其迷惘。塞勒涅怕的是这群半吊子,想走又不敢走的半吊子,扰乱了民心。倘若教会真的不安全了……她可不能任由这群人抢走自己囤积的物资。
隔天,雪纷纷扬扬的下。门窗捂得严实,人聚集的地方更有人味儿,人言也传的快。昨天话题还小心翼翼讨论着塞勒涅修女,今天都疑惑着“圣女珍珠出逃了,我早上看见通缉令,吓了一跳!”
是否吓了一跳尚未可知,倒是质疑的视线明晃晃冲着塞勒涅的脊背来了。瞧瞧,圣女都逃了!教堂一点都不安全!昔日的问候没了,塞勒涅懒得和愚人计较,把闲谈的用笑容赶回岗位。留在原地,表情不情不愿的呢,那就去感受大自然的馈赠——去扫雪吧?希望北风能吹醒他。阿门。
她在人群中快步疾行,十来分钟就把整栋屋子来回走了一遍,整顿了秩序、找到了人、自作主张把仓库和厨房锁了。不能更乱,必须控制住局面。塞勒涅低头看着钥匙,抱歉,玛歌修女,我并不想越位行事的。
没时间了。要做的事堆积如山。她深吸一口气,该安排人员了。
昨天下午塞勒涅临时找了几位年长的修女修士们,讨论了接收难民的事务。晚上在家依照印象列了名单。要留几位手脚麻利的在养老院,维持日常事宜,并逐步减少老人们的活动,减少意外的可能性;把那群说闲言碎语的安排去接受难民,尤其是她亲自逮着的,去见见教会外的腥风血雨;关于圣女出逃一事,也得临时想一个解决办法。禁足与看守必不可免,但是如何从本就紧张的人手中抽调几位,又是难题。
塞勒涅依次讲了自己的计划,将名单递给最年长的修女。在他们浏览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应当去询问圣女是否有救助难民的意愿。如果有的话,想必在场的圣女能够安抚难民。这样同时与圣女进行救助工作的人可以监视圣女。而救助组轮换休息时,可以直接去陪伴圣女,完成任务。”
这个草案得到了大家的初步认可,随后他们进行了合理的修改,又完善了具体的实行细节。除了圣女的活动,还决定调动孤儿院中有一定能力的孩子……非常时机,实在是没有办法。
策划卓有功效,教会收纳了大量的流民,更奇妙的是,塞勒涅反而不如以前忙碌。工作已经固定,每人各司其责,不劳她每日奔走了。原先还有说风凉话的闲杂人员,应是被繁重的活计堵住了嘴,低头任劳任怨。象征教会的白袍行走于人群,递上保暖的衣物,安抚受伤的心灵。参谋修女立在一旁,纵览全局。
医务室的呻吟比夜晚的养老院更瘆人,抛却了一切逃出来的纳塔市民,并不像老人一样等待痛苦的结束,而是奋力于泥沼中挣扎。按照教会的分拣程序,只有重伤的难民才会躺在医务室,这也是此处哀嚎不断的原因。
塞勒涅从一排排病床中走过,目不斜视。医生半伏于病人之上,井井有条,或叹气或蹙眉。而所有白袍之中有一位离病人极近,手触胸口,却无医生应有之稳定。塞勒涅叹口气,快步走去。
走得近了,才能听清那床病人的呓语。他的嗓音干哑,气若游丝,也许是在描述纳塔城的惨状。而守着的姑娘,圣女艾薇,尽全力倾听他的求助。
塞勒涅低着眉,敲了敲床尾,再慢慢走近。艾薇感受到震动,回头确认来人,又附身倾听,一手贴胸,一手贴喉。男人的声音几不可闻了,但艾薇不放弃,尝试性的问:“水?是要喝水吗?”
依旧是含糊的回应,艾薇点点头,掠过塞勒涅。修女则顶替了她的位置,右手熟练伸至病人后颈,轻轻抬起一定高度。左手迅速移动,把枕头垫在腰下。在伸进缝隙,手掌张开,两手发力,托起病人上身,顺势坐于床沿。用右臂抵住脊椎,右手托住后脑勺,就这样维持一定的斜度,再腾出左手,调整一下被子。
凑得近了才能仔细观察病人:后背虚汗,发低烧,轻微脱水症状,嘴角水泡燎了一层,异味也散的差不多。还算乐观,看来过段时间就能搬出去,塞勒涅想着,望向小跑过来的艾薇,这样细微的求助声,也只有圣女能听到了。
“水,水来了。”艾薇焦急赶来,手上直接拿了个水壶,走得近了,慢下脚步倒了半杯水。修女配合她,手腕内扣,将病人的头微往前倾。因为这番移动,病人才勉强睁眼,半喝半吸。喝下去一杯,他本能舔舔嘴唇,抬眼看向水壶。艾薇读懂了,急切回应他,又倒了满大杯水,正要再喂给病人,却被塞勒涅制止。
修女伸出空闲的左手,挡在水杯与病人之间,微微摇头。下一秒她看向圣女,对着水杯勾勾手指,艾薇不明所以,只能乖乖递去。塞勒涅慢慢喂了半杯水,就止住动作,对着病人呢喃细语。她放下水杯,取走垫在腰下的枕头,缓缓让病人躺下,整理被角,轻手轻脚离开了。
【回去吧。已经到休息的时间了。】她面带微笑,结束手语后自然拿过水壶,留在艾薇身后半步,不远不近。
放好物件,温水洗手,擦拭干净,塞勒涅为艾薇裹上披风,领着艾薇从僻静的小道回房。
这条小道距离混乱的救助地很远,两侧没有建筑物遮挡,因而在寒冬腊月人迹罕至。她们向着教堂主体走去,喧闹的苦痛声越发远去,将一切苦难与哭号抛在背后。厚重的靴落在石砖之上,震耳欲聋,融于万籁。
艾薇突然停下,回头看一眼随行的修女,又望向灰蒙的天。半晌,憋出一句“我想去看看忒弥斯……可以吗?”
塞勒涅走到她的正面,【如你所愿】。之后仅仅站在原地,静静陪着艾薇。
这几日的天空总阴沉,灰色是天地间仅存唯一的色彩。仿佛停滞了时空,甚至乎死寂。除了呼啸的风警告凛冬的可怕,再无他言。寒意侵袭,连同思绪也被冻结,冰冷、麻木。广阔间的渺小,藐小却安于此,被无垠所掩埋。
往昔纷至沓来。过去的四年塞勒涅忙于工作。理论上而言,教会的修士修女皆可以接触圣女。但除非一些必要的场合,塞勒涅不主动与圣女们接触。反正,她是这样想的,大家都想要帮助圣女,那么也不缺我这一个了。别人费尽心机想与圣女接触,她保持距离礼貌行礼。
再想想她刚入教会,17岁过半,算来四年有余。巧的是,艾薇也是四年前被选中。她们当时都被扔进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一个想要证明自己,另一个不想成为累赘。纵然她们交谈不多,相处时公事公办,但塞勒涅一直看得清楚:有一位活泼的圣女会蹙着眉学习读写,更重要的是,她会用令人怀念切利口音向每一位神职人员打招呼。
来到纳塔的路十分崎岖,在马车上的颠簸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塞勒涅怀念自己的少年时代,也许是记忆美化了当初的争吵,又或许是纳塔城实在是……严寒刺骨。
切利才不会这么冷,切利一直都很暖和。夏季树木葱葱郁郁,从阳台远望时,一层层绿盖住街道。它们长得如此繁茂,倒不知是树还是花——恣意向上的、自由伸展的——不同的时节有不同的色彩,变化细小,异彩纷呈。冬天只是落雨,把秋意洗刷干净。风还是柔和的,睁开眼能看见迁徙的候鸟。父亲告诉她,因为切利靠海,温暖的南风带来了水汽,才会使这座城市如此宜人。父亲还会刮刮她的鼻子,“又冷啦?这一点都不冷。没事,等南风吹了,春天到了,给你买新衣服!”
她想念父亲的手,想念母亲沏的茶。湖骸是什么才不重要,圣女出逃与我何关?过去的塞勒涅一定会这样自暴自弃,可任何反抗在压倒性的现实面前都无济于事。慢慢的,她逐渐学会把控资源,将有利的一切牵扯至身边,为自己开创一切。
四年。四年间长成了一位稳重的修女,也塑造了一名真诚的圣女。塞勒涅见艾薇,如见过去的自己。忒弥斯的献祭、湖骸的爆发、珍珠的逃亡,让一个小女孩短时间内经历这些是否过于残忍?
不说她前路何方。但自己的四年中,有她为自己解乡愁。无心之举已帮了塞勒涅许多,而作为修女,只能以此刻的纵容作为回报。
她伸出手,隔着兜帽摸了摸艾薇的头。女孩缓缓扭头,怔愣地看她,眼神呆滞。北风将17岁的迷惘蹂躏,崩破如风中摇曳之火。
要将这火护住呵。为她挡半点风。
塞勒涅开始手语,同时回忆被自己抛弃已久的家乡口音。切利人说话不怎么用鼻音,也少翘舌。她磕磕巴巴地还原记忆中的一切,即使艾薇无法察觉这点区别。
【如果不是你在那里的话,想必那个病人会被忽视。只有你才能帮助他。因为你感受得到。你听见了。】
左手四指合拢,大拇指伸直,微侧头放于耳后。这是【听】。
“都到春天了,我要去放风筝!”
“出门净沾一身灰!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你了……”
“这有什么不好的?在屋子里闷这么久,是该出去吹吹风哩!”



小镇里的生活虽然平淡充实却仍有诸多不便,对于我这种上了年纪的老太婆更是如此,亲爱的哈莉,我想这也是你决心离开这里的原因。你向往着纳塔城漂亮的街道和便利的商店,教堂的尖顶托起了你的梦。最近镇上来了一个要去纳塔城的男孩,他说自己正在给病弱的姐姐找一处安心休养的地方,他的姐姐确实病的不像样,我看这女孩才不过二十岁左右却瘦得皮包骨,可怜的孩子,耷拉着眼睛,瘪着嘴一副活不长的样子,这怎么行!我招呼他们在家里吃饭她也吃得不多,我告诉他们实在不行就在这里住下,但是他们谢绝了我的好意。他们决心离开的样子让我想到你。你在城里孤身一人,孩子们,我这个年逾古稀的老太婆帮不上你们任何忙,但至少能帮你们相互扶持,于是我写了一封信交给他们告诉他们如果有需要可以带着这封信去找你。他们最后也离开了这里。
——————
“你还在看那封信?”
拖车里面的瘦弱猎人靠在拖车边缘,那双绿色的眼眸里是些许的好奇,她黑色的短发被风吹得有些乱,但她并没有抬起手压着乱飘的刘海儿。
弗林特坐在马拖车的车尾,耷拉在外面的小腿因为颠簸的乡路摇晃着,“没什么大不了的。”他的视线重新回到信上,信纸被重新折好塞回信封妥善地放进口袋,写了这封信的老人家——人们都叫她珍奶奶,告诉他们可以拿着这封信去找她在纳塔城的孙女。在她的描述中她的孙女哈莉是个活泼开朗,热情友善的女孩儿。而且很有孝心,她的梦想就是带着珍奶奶一起在纳塔城过好日子,为此她在纳塔城努力工作,每个月都会寄生活费和信回来,但是这个月女孩却杳无音信。
“我们会去找那个女孩吧?”
弗林特微微侧头,那双眼睛在对上他的视线后又马上低垂下去,她本就黝黑的皮肤因为躲避光线更模糊了她的面容,这个一副短命鬼样子的女人名叫罗斯,这次的任务里他们伪装成一对兄妹行动,任务很顺利,他们现在正要打道回府。
“你想去?”他问道。
“呃,至少我们吃了人家一顿饭……不是吗?”她句尾的语调小心的上翘。
“你说得对,至少跑个腿的时间我们还是有的。”
他身后再没响起女人的说话声,但是他听到气体被吹出,像是女人松了口气,接着衣服布料相互摩擦和木板被挤压的声音响起,应该是罗斯换了个姿势。这辆板车实在算不上舒服,对于罗斯这个身娇体弱的来说更是如此。在马蹄声和木轮碾过碎石的声音中这辆拖车路过一望无尽的田野和牧场,围栏里的羊们听到声音好奇地抬起头看向他们,一只老母鸡带着鸡崽儿们停在路边等他们过去,小鸡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在母鸡身旁不停地乱窜大叫,而纳塔城的城门仍在遥远的另一边。
或许等到了地方要先找个地方让他的同伴稍微歇一会儿。
——————
尽管弗林特年纪尚小,罗斯也不得不承认这个男孩甚至远比一些大人靠谱得多。等他们回到纳塔城已临近半夜,他反复地确认罗斯是否需要再休息一会儿,虽然路途漫长颠簸,但不用长时间地行走已经让罗斯能得以歇息,她现在只是有点腰酸背痛。在她的再三保证下弗林特才停止追问,即使他绿色的双眼仍不时投来怀疑的目光。
“我想我们最好先看看哈莉住在哪,这样明天还可以节省一点时间。”弗林特从口袋里拿出信封,牛皮纸信封上整齐的写着哈莉的地址。
那是个离城中心不算近的地方,借着路灯和还算优秀的视力罗斯将信封上的字收入眼底,当然,这也意味着离他们现在的位置很近,“离我们只隔了两条街。”
“看来我们很快就能休息了。”
这个男孩仍然对她的孱弱念念不忘,虽然这是罗斯本人也无法辩驳的事实,但是面对一个男孩她至少还是想展现一点成年人——虽然可能差了一点——成年人的底气。
“不着急,我们快走吧!”
或许是她的积极有点突然,弗林特微微睁大眼睛过了一两秒才想起回答她,“啊,好啊,走吧。”
城郊的房子虽然看起来有点老旧但房租却够便宜,有不少猎人也会选择在这样的地方租个安身之所。这里实在有些偏僻,暗淡的月光下熄了灯的房屋们紧闭房门静默地等待他们走到街道的尽头,月亮已经升到了最高的地方,银色的光透过房门微微打开的缝隙照亮了屋内地板的纹路,哈莉的房子如同对他们咧开嘴邀请他们进入其中的怪物。
“弗林特……”
“去窗户那里。”弗林特已经拿出镰刀,月亮在刀刃上投下冰冷的光,罗斯点点头取下背在后背的枪猫着腰缓慢地挪动步伐到房子的窗底,找到合适的狙击位置后她朝弗林特做了个手势。男孩收回目光到眼前的门上朝着房子的大门走去。
现在有两种可能,一种,入侵者是人类,一起再简单不过的盗窃抢劫或其他的乱七八糟的案件。这是最好的情况,毕竟人类尚且在他们能轻松解决的范畴内,但如果是第二种情况……罗斯小心地探出头透过玻璃查看窗户内的情况,漆黑的屋内入侵者的身影大半潜藏在阴影中,罗斯只能隐约辨认出一个娇小的轮廓,而在从窗户投在地板的月光中有着深棕色长发的女孩满是血污的脸庞清晰可见,她的头被一只有些小巧的手捧着,身体不自觉的抽搐着,上翻的眼睛颤动了一会儿转向了罗斯,在入侵者看不到的地方她苍白的嘴唇颤抖着张开。
快、走。
她的瞳孔忽的扩散开,颤抖和抽搐也停止了,现在她睁大的眼珠只是无神的对着她再也看不到的猎人和眼前的一切。
该死,真的是血族!可是弗林特已经推开了房门,现在罗斯终于在门被推开的声音中看到了入侵者的模样,就像是童话故事中会用各种甜美的伪装蒙骗可怜人的怪物,任谁都会想不到这样一个有着水灵灵大眼睛的女孩会是吃人的血族。
她看起来就像是养尊处优的贵族小姐,有些卷曲的亚麻色长发顺滑地披在肩上,回头望向来者的绿色双眸无辜而纯洁犹如一双透明的宝石,她的皮肤白皙细腻像是最光滑精美的瓷器,如果忽略她嘴唇周围的血迹的话。
“没想到这位小姐这么晚还有客人,”那声音也和浸过蜜糖似的,罗斯不得不时刻提醒自己她刚吃过人。她松开捧着尸体的手,尸体的头撞在地板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她的身高比弗林特略矮一些,这让她看上去更像个漂亮的洋娃娃,她的视线向下挪过一些,似乎注意到来者不善,“我想你应该不是她的弟弟什么的吧?”
弗林特没有说话,从罗斯的角度也看不到他的身影,如果那血族没有行动说明弗林特也没有做出任何动作。
这会儿就连风都没有,罗斯只能听见自己的胸腔里心脏剧烈撞击肋骨的声音,即使她努力不让自己发出夸张的喘息声她的心跳声也越来越大,她甚至开始担心那个血族会不会因为这心跳声而发现自己。好在木板的嘎吱声打破了这份宁静。
弗林特的身影走在从门口铺进地板的月光上,他一步步地走近地上的尸体直到与那女孩擦肩而过,他最后停在哈莉身旁缓缓屈膝小心地半跪在地上从怀里拿出珍奶奶的信放在她手边,他尚显稚嫩却布满伤痕的手掌抚过哈莉的额前合上了她的双眸。当他抬起头时迎上了罗斯的目光,但他只是又垂下眼睛站起身。
另一边的女孩儿已经擦干净了嘴,她将手帕收进口袋里,歪着头看似天真地问道:“你在和她道别吗?”但是弗林特仍旧一言不发,从罗斯的位置她看见女孩挑起一边眉毛,“你不想说话吗?我刚吃完饭,倒想和人说说话呢。”
“不,”弗林特终于开口,“我只是在想你的血值多少钱。”
话音刚落他向前跨出一步越过尸体猛地挥出手里的镰刀,但血族轻巧的后退躲开了他的攻击,她抓破自己的手掌,流出的血液扭曲变形,变成了一柄几乎能砍下一个成年人的斧头。
“你应该不介意淑女也用上武器吧?”当斧子撞在弗林特刚才站着的地方时地板发出了巨大的断裂声,罗斯趁机从外面捅开了窗户锁支起窗户将枪口架在木框上瞄准血族,她的手指在扳机上抬起落下却迟迟找不到扣下的时机。
尽管武器的差距让弗林特一时落入下风但他却并未退缩,终于在血族挥空斧头的一瞬间他从腰包里拿出锤子瞄准血族的后脑砸下,铁块砸在头骨上让女孩发出了一声尖叫,但这却没能彻底打倒她,在血族的恢复力下这对她没能造成什么实质性伤害。
“好疼啊!”她抓住弗林特的手臂迅速逼近对方用额头用力撞在弗林特的脸上,当他们分开时血液从弗林特的鼻子里流出淌进他的嘴里,他甩甩头,吐掉嘴里的血,但身体仍在趔趄。血族再次举起手里的斧头,而罗斯也终于找到时机,枪响过后血族纤细的手腕上几乎漏了一个洞,手里的斧子瞬间失去形状洒在地面上变回一摊血水。而她还来不及尖叫就被弗林特扳住肩膀,两个人的脑门撞在一起发出“咚”的一声闷响。
最后他们几乎同时倒在地上。
“弗林特!”顾不上血族还有没有余力罗斯抬起窗户便翻进室内到弗林特身边检查他的情况,好在他只是晕过去了。而那个血族也没有再起来,但是她还没来得及松口气门口的月光突然间被挡住。她急忙再次抓起枪对准门口的不速之客。
月光下他的金色短发泛着些许银光,地板被踏过的声音每一声都让罗斯颤抖得更加厉害,弗林特不省人事,她可没那个信心能独自应对得了这个一看就不好对付的血族。
但对方走过来后只是将手放在她的枪杆上,她的猎枪被轻轻按下,“不要逞强了,猎人,”他的声音几乎带着这里的空气都在震动,“我们都不想接下来的局面变麻烦,各退一步如何?”
当他转身蹲下抱起地上的女孩时他嘴角的伤疤映入罗斯的眼帘。
——————
光透过他的眼睑给黑暗晕染了些许暖色,他睁开眼睛,陌生的天花板上阳光照亮了这一切,弗林特眨眨眼睛,他本想起身但眩晕阻止了他。
“你醒了?我觉得你暂时不要起来比较好,”罗斯正在床的另一边的书桌前写着什么,她快速地收回了视线,她的脸庞在日光下清晰无比,“虽然我觉得你现在应该也起不来。”
于是他索性放弃了挣扎,至少他们现在都还活着,“这里是哈莉家?”他问道。
“嗯,我花了点力气把你搬上来,我觉得你应该有点儿脑震荡,但不严重,等会儿你应该就能活动了。”
“你吗?”
“至少我是个成年人。”她语气坚定,似乎打定主意要重申自己是年长的那个。
“那个血族呢?”
“呃,她……后来被另一个血族带走了,但是那个血族居然没动手,我们真是撞大运了。”
你真是撞大运了,他似乎总是能听到对自己运气的评价,弗林特便只是从鼻子里发出闷声闷气的鼻音,他的鼻子也疼得厉害,“那你现在在干什么?”
“我,我想模仿哈莉的笔迹给珍奶奶写一封回信。”
“你好像从离开那个镇子开始就对珍奶奶很上心。”
笔尖与纸面摩擦的声音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罗斯才开始说话,“弗林特,或许我只比你多活了一些年月,但是……”她嗫嚅了一会儿继续说道,“珍奶奶和我说‘你要好好活着’,不是为了利用我或是随便的同情心,弗林特,我想好好活着,我也希望她能好好活着……”
好好活着,他想起老人家语重心长的叮嘱,好像他们也是她的亲人,老人苍老得如同树皮但却十分温暖的手握住他的手,抚过他的短发,拍过罗斯的肩膀。即使他们或许再也不会相见。
“拿给我看看。”
“哦,好!”
“……我觉得正常人应该不会给自己的奶奶寄一份跟医疗报告似的平安信。”
“对不起,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写……”
“我感觉我好多了,我来告诉你怎么写。”
“谢谢你,弗林特!”
阳光平静地洒在一楼的地板上,照亮了女孩的身体,她躺在地面上,脸上的血污已被擦净,双手交叠放在胸前,下面压着那封寄给她的信。
——————
可是,亲爱的哈莉,人要如何才能收到一封再也收不到的信?不过我还是收到了这份奇迹,两个傻孩子,我虽然年老但并不至于两眼昏花。但是我还是非常感谢他们,他们在信里让我好好活着,他们告诉我,我一定会等到我们相见的那天。哈莉,你要知道,活着,并不只是靠我们自己呼吸进食得到存活的养分,让我们真正存活于世的是爱。爱和被爱,这种力量让渺小的我们在这个伟大的世界上留下痕迹,这才是我们生活的真谛。夜已经深了,如果我能抵达那教堂上的梦会不会看到你的身影?晚安,哈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