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罗大陆,圣别纪元后期。
血族女王莉莉安突然失踪,几乎同一时间爆发的怪奇疫病让人类数量逐年锐减,失去管控的血族加上疫病的席卷,让整个社会动荡不安。
将一切扭转的契机在于教会发现血族的血液竟是能治好疫病的良药。
从此,以血液为中心的利益旋涡将整个世界卷入了其中。
【创作交流群:6911995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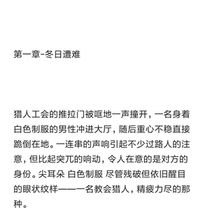






我们的目标是——搞事!【x
雷师傅视角请走这边:http://elfartworld.com/works/9215858/
==========================================
露缇娅的16岁生日,正好是舞会的第二天。
这些为了将自己献给神明而终日苦修的少女,一年中唯有生日当天,能得到些许的自由。
只要不是太过任性的愿望,她们的请求在这一天多会得到许可。
尽管每一个生日都意味着少女们离献祭之日又进了一步,但她们还是会尽可能去享受这特别的日子。
至少至今为止的每一年,露缇娅都是这样做的。
可是现在,她却有些犹豫了。
按照早早就定下的计划,雷涅今天会在城下町等着露缇娅,陪她度过这个生日。
曾经,是雷涅从吸血鬼的魔窟中将她救出。尽管他们并未同行很长时间,但她从未忘记这个不苟言笑的恩人。
所以雷涅也是唯一一个会收到露缇娅寄出的信的人。
作为一个猎人,他并无法经常抽出时间来见这个无依无靠的少女。就算说是给露缇娅过生日,今年也是头一遭。
所以露缇娅一直很期待今天的到来。
可偏偏在昨晚的舞会上,她感觉到了阿沙尔的存在。
不仅如此,当她匆匆逃回大教堂,才发现自己竟然在慌乱中弄丢了耳坠。
这么一来,就算阿沙尔出现在附近,她也无从得知了。
对阿沙尔的畏惧,和想要与雷涅共度这个生日的心情在心头纠缠,让露缇娅烦恼不已。
就在这时,一只手突然捏住了露缇娅的脸颊。
露缇娅吓了一跳,一抬头才看到蓟草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眼前。
今天负责担任她的护卫,却比她还要娇小几分的银发教会猎人指了指大门的方向。
“你在烦恼什么呢,小丫头?咱们该出发了。”
根据蓟草的嘴唇运作,露缇娅读出了她的意思。
她揉了揉刚被捏过的地方,叹了一口气。思考片刻才在本子上快速写道:“有很多来参加祭典的血族,我有点怕……”
关于阿沙尔的事,她并未和别人提起过,甚至都没有告诉过雷涅那个吸血鬼还活着的事。
“你怕什么,有我在呢!”蓟草看起来对露缇娅的担忧有些不满,“而且不光是血族,也有很多教会猎人和猎人在场,我倒想看看哪个家伙敢在这里造次。”
也对,就算是阿沙尔,应该也不敢在教会猎人的大本营门口闹事吧?
而且,我也得去把坠子找回来才行。
想到这里,一个身影突然浮现在露缇娅的脑海里。
昨晚的那个人,会不会捡到了我的耳坠呢?
======================================
露缇娅在蓟草的陪伴下来到大教堂门口时,雷涅已经等在那里了,露西娅嬷嬷正有些严厉地跟他说着什么。
嬷嬷大概又在数落雷涅的战斗方式太鲁莽了吧?
看到雷涅为难的样子,露缇娅的面部神经总算没那么紧绷了。
“哦,她来了。”看见露缇娅,雷涅简直像是见到了救星,大步走了过来,“好久不见,你有好好吃饭吗?”
“真是没情调,你对女孩子就没别的可说了吗。”露西娅嬷嬷用力拍了雷涅一把,“小蓟,这家伙要是没照看好露露,就让他吃点苦头,别客气。”
蓟草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似乎在说“交给我吧”。
还在揉搓被嬷嬷拍了一巴掌的胳膊的雷涅看了看那两人,长叹了一口气。
这次,露缇娅终于忍不住笑了出来。
“嗯,这个表情才比较适合过生日的小丫头。”
蓟草点了点头,和露西娅嬷嬷打了个招呼就推着雷涅和露缇娅向外面走去。
百合花广场上依旧人头攒动。
昨晚的舞会带来的兴奋劲还未褪去,今晚又有赦罪演武这种大型活动,也难怪这里的气氛还是那么热烈。
要想在这里找一个小小的耳坠无异于大海捞针,不过听说了这事的蓟草拍着胸脯把这差事揽了过去,让露缇娅享受难得的外出就好。
知道她也是为了给自己和雷涅留出空间,露缇娅也就接受了她的好意。
“那么,我们从那边开始逛吧。”雷涅看起来倒是没想太多,指了指路边的一溜摊贩,“毕竟是生日,也该给你买个礼物什么的。”
露缇娅慌忙摆手,表示自己并不需要什么礼物,雷涅这次态度却很坚决。
“别跟我客气了。”他拉着少女就向那些路边摊走去,“不过我不懂你们女孩子的喜好,看中什么我来付钱就好。”
看这架势,如果自己不挑个什么东西,雷涅是不会轻易放过自己了。
露缇娅有些无奈,又有些开心地打量了一下眼前的小摊。
就挑个看上去便宜点的小东西吧。
======================================
对平时没大有机会外出的少女来说,购物似乎并不是她想象中那么简单的事。
而且随便挑些便宜的小玩意儿,雷涅好像又不同意,结果逛了半天,他们还是没买到能令双方都满意的礼物。
眼看着太阳都渐渐西沉,两人暂时回到了百合花广场,找了个角落打算先休息一下。
雷涅正在一边嘀咕着什么,露缇娅读不出他的话,但大概能猜到他还在纠结送给自己的礼物。
明明只要像这样度过普通的一天,对我来说就已经是很好的礼物了。
可惜对不大识字的雷涅,露缇娅并无法顺利将这份心情传达过去。
要不要等小蓟回来以后,请她代我告诉雷涅呢?
也不知道小蓟有没有找到我的耳坠……
露缇娅正在胡思乱想,突然察觉有人正在向这边走来。
为了观看晚上的赦罪演武,人流已经开始向圣伯拉大教堂移动了,所以那个向着相反方向前进的身影格外显眼。
当然,那可以说完全挡住了那人上半身的巨大花束,才是他惹眼的最主要因素。
被这一大束花遮挡,露缇娅看不到来人是什么样子,只能勉强判断出对方还没有自己高。
可不知为何,看着这花束慢慢靠近,露缇娅总有种不安的感觉。
仿佛那些美丽的鲜花中,隐藏着什么令人寒毛直竖的危险。
这么说来,我好像见过这种花……
那不是在圣伯拉大教堂附近常看到的花,而是某种存留在记忆深处,来自遥远的过去的印象。
那好像是……经常和“他”一起出现的花。
露缇娅的身体顿时紧绷起来,不由自主地伸出颤抖的手,抓住了坐在一旁的雷涅。
那是阿沙尔每次拜访我家时都会带来送我的花!
“露露,怎么了?”
雷涅察觉了她的不对劲。
是阿沙尔!我们得离开这里!
露缇娅拼命比划着,可雷涅并没有看懂她的意思。
但至少,他看出露缇娅在害怕着什么。
就在这时,那个接近的脚步停下了。
花束微微倾斜,露出了一张有些熟悉,却感觉似是而非的脸。
“露露,我来接你了。”
出现在露缇娅和雷涅眼前的竟然是一个小孩子,但他尖尖的耳朵证明他毫无疑问是个血族。
而且那张脸,就算看上去比记忆里的年轻了很多,也仍能看出那时不时在噩梦中骚扰露缇娅的“他”的影子。
这个人绝对就是阿沙尔!可他为什么变小了这么多?
露缇娅有些混乱,但至少她还没有忘记要警惕眼前的“怪物”。
雷涅!他是阿沙尔!
她试图用肢体语言警告雷涅,可惜自己也清楚这实在没什么用。
但至少,她成功把紧张的情绪传达出去了。
“露露,你先离开。”
雷涅自然早就认出这个“小孩”是个血族,虽然这两天的百合花广场上并不缺少血族的身影,但他从阿沙尔靠近时就已经绷紧了身体,随时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状况。
只不过雷涅今天是来替露缇娅庆祝生日的,他并没有带着平时狩猎时用的各种装备。
露缇娅确实很想就这么扭头逃走,可她也很担心雷涅的安危。
“你还在等什么!快走!”
见她迟迟不肯离去,雷涅的声音少有的高亢了起来。被他的吼声吸引,广场上的人们纷纷扭头看了过来。
“你……”就在这时,阿沙尔眯起了眼睛,他的视线第一次离开了露缇娅,转而投射向了雷涅,“我说怎么有点眼熟。原来是你啊,窃贼。”
就连不懂战斗的露缇娅都能感受到,阿沙尔释放出了冰冷的杀意。
她浑身一颤,刚想拉着雷涅一起逃走,却眼见着他冲了出去。
雷涅一边扑向阿沙尔,还一边扭头对露缇娅喊着什么。尽管听不到他的声音,但露缇娅很清楚,他一定是在催促自己离开。
“你又要阻挠我了吗!愚蠢的人类,当年被你偷袭得手,该不会让你以为自己比我还强吧!”
阿沙尔毫不示弱,尽管他的身形只剩曾经的一多半,却游刃有余地接下了雷涅浑身的一击。
没等周围的人有所反应,阿沙尔已经反手把高大的猎人扔了出去。雷涅的身体落进了不远处的货车,带来一阵巨响。
广场上的人们这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纷纷尖叫着四散逃开。露缇娅却像是被定在了原地,愣愣地看着刚把雷涅丢出去的阿沙尔又转身向自己走来。
阿沙尔刚张开嘴想说什么,一道巨大的影子从他身后窜了出来。
身上已经添了几处擦伤的雷涅又冲了上来,这次竟把阿沙尔矮小的身体撞飞了出去。
“走!露露!”
他一边怒吼,一边向阿沙尔落地的方向追了出去,看来是想尽可能让阿沙尔远离露缇娅。
不行!这么下去雷涅一定会被阿沙尔给……!
露缇娅知道就算自己追上去也帮不上什么忙,但怎么也做不到把雷涅自己丢在这里。
她想要去找雷涅,但正试图逃向大教堂的人却化为一股巨浪,推挤着少女纤弱的身躯,让她根本无法前进一步。
露缇娅徒劳地与人流对抗,惊慌失措的人们却压根没发现这个想逆流而上的少女,互相推挤的身体不断撞在她的身上。
当又一次被慌乱的人流冲撞,露缇娅脚下一个不稳,整个人都向后倒了下去。
她忍不住闭上了眼,等待即将到来的冲击,一只手却恰在此时牢牢抓住了她徒然伸向天空的手臂,随后紧紧把她护在了怀里。
露缇娅惊魂未定地睁开眼,一时间却只看到一片炫目的金黄。
在落日的余晖都即将散尽,深沉的黑暗开始支配大地的这一刻,那金色却如同初升的太阳般耀眼。
后半部分:http://elfartworld.com/works/9214815/


以赛亚不愿靠近火焰,温暖是它的诱饵,火光是它的长线,它是不知饥饱的野兽,伺机缠绕而上,狂热地吞食一切,直到它自身也化为灰烬。
——————
神父的祷告声已然响起,他朝着那声音用尽全力奔跑,即使半路上撞到了什么人也来不及停下,他把咒骂和抱怨全部丢到身后,耳中此刻只有对圣女成年的宣告以及对上天的请求,或许这就是圣女能够听到的声音吧。
好在祷告仪式结束前他抵达了他的目的地,这里距离成年仪式的地点仅一墙之隔,这是他提前很久寻找并挑选的地方,既可以让他的伤眼也看到仪式,也不会轻易被别人发现。他曾下定决心一定要来看这次的成年仪式——她的成年仪式。
他并不知道那名圣女的名字,只知道她即将成年。她柔软温暖的手掌将他从地上扶起,轻轻拍掉他身上的尘土,他想要问她是谁,但她只是微笑着指着自己的耳朵摇了摇头,他这才知道这个人是圣女。她的耳朵从进入教会的那一刻起注定只能用来聆听神的教诲。
“你受伤了?”她半跪在他身前仔细看着他的膝盖,她从帽檐露出的些许红发,细密的睫毛在她低垂的蓝色眼眸上投下阴影宛若深不见底的海洋,当她抬起头时他好像从海底潜入天空,“疼吗?”她问道。
他摇了摇头。
但他的手仍旧被温暖包围,圣女站起身握住他的手,“我带你去医务室。”他本想拒绝,不知是不是她的手太过温暖他仍旧任由自己被带了过去。
碘酒涂抹伤口的滋味并不好受,但他早已习惯,因此他只是皱了皱眉。“好孩子,”圣女从口袋里拿出一块糖果剥了糖纸塞进他嘴里,看来她以为他在忍耐疼痛,“这是一位修女偷偷给我的,好吃吗?”
他点点头悄悄低下头,不知道他的红发有没有挡住他发红的脸颊和耳朵,“那就好。”圣女的裙摆从他前方飘然到他的身侧,床垫被挤压的声音从他的身旁传来,糖纸被展开,硬糖与牙齿碰撞,圣女含混不清的声音响起。
“好甜哦。”
好甜。他想。
后来他得知那位红发的圣女即将成年,她将在成年仪式上接受所有人的祝福,如果可以的话,他也想为她送上祝福,即使只能远远地看上一眼。
木箱被垫在他的脚下,他踮起脚将手撑在墙上,跪伏在地的人群,诵读祷告的神父,等待的修女,还有——躺在花棺里的她。透过墙壁上的缝隙他看见她闭着眼睛,洁白的花朵映衬着她的红发,她带着一如往常的微笑,像是在等待一个充满希望与光明的未来。如果这时她睁开眼睛是不是就会看到我?
“感谢神,我们为您献上女儿,将她迎接罢!”
修女结束了等待,她拿起斧头走向躺在花棺里的少女,但他还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接着太阳反射在高高举起的斧子上当它落下时那光芒被染红,他倒吸一口气下意识地捂住嘴,她一声不发,他也无法替她发声,蔓延的血色点燃了他看到的一切。
直到那颗头颅从花棺里滚落那双眼睛都没有看到他。
——————
“叶片锁,”恩凯特拿起挂在绑住大门的锁链上的大锁仔细端详着锁孔,“不难开。”
“要多久?”英格丽诗·阿忒利亚刚离开不久,并且随时有可能发现这只是个引她离开的诱饵。她的威胁性远比藏在她家的血族要高,如果可以的话以赛亚并不想和她两败俱伤耽误彼此时间。
“除非阿忒利亚一秒飞回来,”恩凯特安慰地拍拍他的手臂,“放心。”他从后腰的皮革腰包里拿出细长的开锁工具微微弯腰像是用钥匙开锁一样去对付那铁锁,以赛亚则在他身旁帮他望风。
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进行得很顺利,虚假的委托准确地传到了阿忒利亚的耳朵里,她也如他们预料地前往去会见从一开始就不存在的委托人,而且她家的门锁对于恩凯特来说也形同虚设,他们接下来只需要进入这栋房子找到目标,最后谁都不会发现什么,只有一个血族悄悄地消失。但不知为何隐约的不安在以赛亚的心头挥之不去。太阳已经西斜,天空下的一切都染上了燃烧般的血色,犹如这片日光逝去前无声的哀嚎。他想起恩凯特曾同他说过的被圣女的血杀死的血族的样子,他们宛若从内部升起一团无形的火焰,在痛苦地挣扎片刻后变成了一缕飞灰。
就如同放任不管的火焰会吞噬一切,在它尚未燎原前将火星掐灭是最稳妥的。当啷一声,沉重的铁锁掉在地上,以赛亚决定速战速决。
英格丽诗·阿忒利亚的房子里安安静静,厚实的窗帘将屋子里遮的严严实实,光线在外面挣扎着想要进来却无能为力只能在厚实的布料外沉闷的打了个转,使得房间里昏暗十分,他们放缓脚步彼此照应拿着武器随时应对潜藏在这栋房子里的危险。他们走遍这里的每一个房间却一无所获。
“或许会有地下室。”教会的猎人没有理由蒙骗他们,以赛亚俯下身用指节轻叩地板,从下面传来微弱的回响,顺着这声音他找到楼梯下面,楼梯狭窄的阴影中地板上的缝隙正在等待他们将这扇门拉开。他冲着恩凯特点点头,退到一边架起弓,等待恩凯特拉开地板上的活板门。门被小心翼翼地拉开,什么都没发生,看来这扇门没有被做什么手脚。
“有人。”他看见从地下室深处传出的微弱光线。
“我先下去。”恩凯特一手拿着武器另一手把住地板边缘灵活地转身下进地下室,他的大半身子都探了下去,这个地下室不算高,他很快跳下梯子走进了地下室里面。
他等在上面,放缓呼吸仔细聆听着里面的动静,面对这么狭窄的空间他的视力和射术起不到任何作用,只能等待同伴的信号。另一个男人的声音模糊地响起,他说话的声音很小,以赛亚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但是很快恩凯特的声音响了起来,“快走!这个疯子——”
火焰和气浪冲出小小的活板门,他没来得及听清后半句话过来身体便先一步做出反应,手臂挡住他的面部他的身体后仰摔倒在地,当那地下室的入口再次出现在他面前时活板门已不翼而飞,被炸开的入口周围落满了地板碎屑,白色的烟雾从里面升起。
“恩凯特!!”他毫不犹豫地起身跳进地下室,在浓厚的烟雾中一个人影隐约可见,是他们的目标,在他的眼中他无所遁形,他迅速挽弓拉箭,箭矢在烟雾里像是划破幕布的刀刃,当男人的痛呼响起那身影应声而倒。
中了。
“恩凯特!”他再次呼唤道,“你还活着吗?!”
“咳!我没事!”在这间地下室的另一边传出桌椅倒地的声音,恩凯特挣扎着从废墟里站起身,他甩甩头咳嗽几声,“就是有点儿耳鸣!”他大声说道。
看来在爆炸前他及时找到了掩体,以赛亚松了口气。现在该去看看那血族了。
烟雾渐渐散去,地下室里只剩下一些没有熄灭的火焰,当他走到那倒在地上的血族面前时他们彼此都失去了所有的掩护。他弯下腰抓住他的胳膊将他拽起来,因为扯到了受伤的肩膀血族发出一声呻吟,但他并没有求饶,而是皱紧眉头用他那双绿色的眼眸瞪着眼前的猎人。
“还挺有精神,”血族脸上的烧伤渐渐愈合,看来刚才他是想拼个你死我活趁机逃走,“这是阿忒利亚教给你的?”
但他只是看着他似乎想要透过眼罩看到那双他无法看见的双眸,忽然他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
“没有人教我,连英格丽也不知道,”他低下头,像是低声哭诉的提琴般的声音从他的喉咙里发出,“用你们的话说……这是怪物的证明。”他闭上眼睛,“让我化为灰烬吧。”
以赛亚松开手,被圣水麻痹的血族摔在地上,他从后腰抽出匕首,毫无疑问,这个血族在等待火焰将他焚烧,就像等待死亡的圣女。
“好。”
他要点燃这火焰吗?
就在他高举的匕首即将挥下时从他的身后传来地板坍塌的巨响,一柄巨斧劈开烟雾,“你们两个,把我耍的团团转,闯进我的房子,伤了我的人,”英格丽诗·阿忒利亚踏过没有熄灭的火焰向他们走来,恩凯特举着手里的长刀在她身前缓缓后退,她像一头发怒的老虎向他们逼近,“好大的胆子。”
以赛亚仍不愿意靠近火焰,但有时他不得不投入那火焰。
“要我和你道歉吗?”他微微抬起下巴转身用匕首指向英格丽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