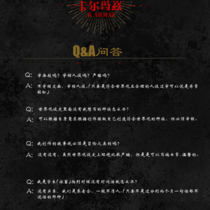我的记忆,曾经开始在纯白的病床,自出生起,我好像就很令人担心,不能触碰的东西多到可以列出一个长的吓人的清单,而这一切,都是他们在期望我不要变成一一个“魔女”。没有他们的指挥,我几乎不会做任何事,我不喜欢仆从们细碎的交流声,更喜欢穿过发梢的风和盘旋的飞鸟,我不需要耗费心力去探寻他们都语言,也就不必揣测从来没出现在我生命之中的“感情”。
庭院里的渡鸦,靠近我的猫咪,这些都很快离开了我的世界,为数不多残存的记忆里,父亲抱着我,疯狂的祈求上天不要让我变成丑恶的魔女,不惜让我住进高高的塔楼里,希望我离天空更近一点,好像这样,他这个与众不同的信仰神明的紫罗兰人就能得到神的救赎。
可是.我确实令他失望了,七岁时的我手中出现了一柄纯金的天平,我第一次使用它,均衡了高高的,高到隔绝了一切的高塔,和低低的包容了一切却没包容下我的大地。
当父亲用厌恶的眼神看着我迈出那扇与地面持平的窗户,赤着脚来到他面前时,那柄金色的天平被狠狠的拍到一边,我看见他拿出了武器,对准了,我的心脏。
很快,切都发生的非常匆忙,心脏的刺痛,另一位魔女的到来,紫罗兰的骑士冲进了庄园,他们都在谈论着我,像是某种物品样, 我被作为一个优秀的工 具,在他们的决定下,会在魔女会和帝国之间永远徘徊这一切都来自于我的天平,它拥有均衡一切的能力,而第二次使用它,我就被迫均衡了我的生死。
那位紫罗兰的骑士压我会死,代价是他的破剑,那位女巫压我能活,代价是她修剪下来的头发。
在父亲的描述里,女巫都可怖又丑陋,从不关心除了她们自身以外的任何事物,但我没有什么扭曲的肢体,也没有什么癫狂的想法,只是等候他杀死我,就像四岁时他杀死我的知更鸟一样,这一切就像这场荒唐的仲裁,我从中获得了并不完美的永生。
天平没有倾倒,指针稳稳的定在了中间,但我没有死去,只是心脏停止了跳动,又过了一小会儿,心脏再次跳了起来,而我的眼前又变成了一片黑暗。
她只是看了我一眼,将魔女会的地址刻在了我手中攥着的羽毛笔里,径直离开,那位骑士没有丝毫不甘的扭头,迅速寻求可以协助他抓捕并杀死我的同事。
我不喜欢魔女,不喜欢紫罗兰,不喜欢人类当然,我由衷的不喜欢我自己。
无论过去.... .我依然可以回想起,那时当骑兵赶到,中间围着一个穿着医者服饰的人,七岁的我在庆幸自己,没能获得自由。
实验,记录,只要我配合,关于魔女的头钉,“均衡”的实质,我曾度希望, 我死在下一次研究的手术台上。
后来,他们再也无法从我身上得到些什么了,于是,他们想起了我的天平。
他们选择允许我行走在大街上,以黛尔小姐”,一位在紫罗兰帝国新晋贵族出生的人类女孩儿的身份自由出入紫罗兰,于是我在魔女会建起一座高塔,用以怀念我屈指可数的童年。
他们将我安置在距离仲裁庭不远的地方,登霍尔这个城市总是散发着艺术的气息,每当仲裁庭开审难以处理的案子,我就会受到要求,隔着一层木板,双手穿过孔洞,接下双方带来的价值,放置在我的天平之上。
无数人紧紧盯着不停摇晃的标码,最后的偏向往往指引着“正义”,均衡的正义。
他们并不会,或者并不介意我的能力所带来的均衡,只是需要一个名正言顺的,获得场名声上的胜利。
我听过仲裁庭外的吟游诗人叫我“贪婪的特弥斯”因为出现在仲裁庭上的那个天平和那双手,摧毁了很多普通人的希望。
不光紫罗兰不欢迎我,身居高位的大魔女们看我的眼神,也好像在看某种奇异的材料,她们也利用着我的均衡之力,比仲裁庭更熟练,均衡药效,均衡伤势,我却只是需要我的高塔,在那里我才会发自内心的感到安全。
我的天平歪倒向一边,是偏向沉重的,价值高昂的,而后轻轻的,价值稀少的会在天平归正的一刻获得他们无法注意到的补偿。
我总有被发现的一天,就算我只露出了一双手和一个天平。
当有人小心的向我询问“黛尔小姐,您的双手是如何保养的?简直和....审判庭内那双“贪婪的特弥斯”一模一样。
我知道,我的自由,要戛然而止了。
不过,我反倒比那些看守我的紫罗兰人更加从容,因为不喜欢自由,独自一人站在大街.....我会觉得我像个异类,来来往往的人并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我自己。
我叫贝纶丝黛尔,均衡之魔女,“ 贪婪的特弥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