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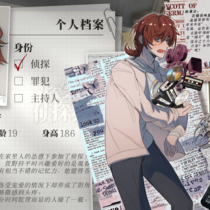




DVD读碟
阚秋来将一盘砂糖橘搁在袁启面前,橘梗上未摘去的叶子边缘卷曲着,有些蔫巴。袁启并未在意,竖起戴着手套的手说:“哦!谢谢!”
阚秋来点点头,拽了条干净的毛巾对着理发椅劈头盖脸一顿摔打,将这多年的老伙计拍干净后才把袁启的行李放上去。
让客人的东西粘上碎头发是不太好的。阚秋来这么想着,忽然意识到了什么,于是直起身拍打衣服。又有些不甚明显的头发在空气里飘飘悠悠缓慢下落,他抬起眼皮说道:“你先歇着……尝尝橘子?”
事发突然,当时阚秋来优哉游哉地看着剥太多橘子而发黄的手,正痛定思痛不能再食砂糖橘时,忽然一道身影走来,振了振背着的行李,用抱歉又落落大方的语气对他说了几句话。阚秋来完全记不清对方说的原话是什么,只感觉自己像穿越进了都市男频小说,第一章就遇到一位想在自己家借宿的陌生女人。
这放在任何一本男频小说里都是鲜辣的开头,阚秋来看过几本,高中时期还肖想过,可如今真碰到这种事情,他只觉得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甚至称得上狼狈。
“唉……”阚秋来叹了口气,一边急匆匆地走着一边抹掉围挡上干了的泡沫,大脑里计划着如何最快收拾屋子。
作为一个勤快的单身汉,虽然平日里经常打扫卫生,不至于让大环境非常难堪,但日常起居中还是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些生活赋予的杂乱。
让客人看见家里乱糟糟的样子是很没面子的事。他在小时候就领会过,要是屋子没收拾好就带小伙伴来家里玩,是要被老爹拍脖颈子数落的。
同时作为东道主,慷慨善良也是必须表露出来的一部分,招待客人必须尽自己所能办到最好。总不能让客人吃不饱穿不暖憋一肚子火受一肚子气走吧,客人回头就在网上开帖子怒喷几十楼“你这什么破屋子我家狗窝都比你这强!狗吃的都比你好!”
简直丢了小寒村……不,简直丢了整个东百的脸。
阚秋来提溜着一小袋黄豆,摆正镜子前的大宝sod蜜,又加快脚步在冬屋粮食屋和理发店之间来回奔走收拾东西。
他抓了抓头发,有些没来由的忧愁。且不说这套老黄瓜刷绿漆式的房子如何,光是自己这幅埋汰样,就指不定让对方见笑了。
“不用这么费心的。”大概是见他忙忙碌碌有些不忍,袁启笑着开口道。
阚秋来在她面前站住,搓了搓干燥发冷的手,问道:“明天早饭是豆浆油条配小米粥,可以不?”
袁启一愣,心想大概是可以买到的东西,遂点头称好。
阚秋来也点点头,去角落里捣鼓了一会儿,拿出一根把手样式的玩意儿。袁启问这是什么,阚秋来说是石磨的把手,磨豆浆要用。
袁启心说好家伙,大城市的手磨咖啡与吉事果对标小寒村的手磨豆浆与现炸油条,好有情怀的做法。
阚秋来背过身皱着眉头,他倒不是故意用石磨好卖弄自己的肱二头肌……只是自己之前图省钱,没买豆浆机,后果就是现在只能用最原始的方法手磨豆浆,甚是后悔。
阚师傅捋起袖子刚准备火力全开磨豆浆时,村口的喇叭又响了起来,老喇叭刺啦刺啦的电流声和调试声异常尖锐刺耳,他卯足的劲如被针扎爆的气球般散了个干净。
“今天事挺多啊……”阚秋来嘀咕一句。
喇叭播报的是一则通知,叫村里所有男人都去村长家开会,具体因什么事情开会则说的模棱两可,和喇叭的音质一样含糊。
“我出去一趟,马上就回来。”阚秋来放下袖子拉起衣领准备出门,又想了想,把空调遥控器和电视遥控器塞给袁启,示意她可以随意使用。
“好,”袁启挥手,又说,“很远吗,要不要我开车带你去?”
“不用,不算远。”阚秋来出了门,下意识往附近张望,没看到有什么摩托车。
方才折腾石磨时他俩有一搭没一搭地唠嗑,袁启表示自己有一辆不错的越野摩托,大概是出于不能白吃白住的心理,她提议明天白天两个人坐摩托兜风,阚秋来答应了。
在广东打拼时他向往过一台好摩托车,通勤便利的同时还很拉风,毕竟谁年轻的时候没幻想过自己开着一辆哈雷一骑绝尘,超吊。
回村后他只开过谁家二手的三轮车,刹车还不好使,带人上个坡都颤颤巍巍的,阚秋来费老大劲还是差点翻沟里。
他扬了扬眉头,有些期待袁启拥有的那辆好摩托,如果能坐着兜风也算是圆了自己年轻时的念想。
脚步声单调的在村路上响着,路灯明亮的光在道路中央映出大团大团霜白的地面。
开完会顺路提一桶油回去吧,要炸油条的。阚秋来叼着烟想,火机的火光一闪而灭。
冬日里的风总是刺骨的,刮在人身上像往肉里钉了钢钉,黑夜更黑了些,灯光更加刺目,将人的影子浓缩成很小一粒。
阚秋来停下奔跑的动作,浑身冷汗,僵硬地站在路灯下,燃了一半的烟从嘴里掉落。
“……?”他的脑海里席卷起无数狂乱又陌生的记忆碎片,如灰暗的蝗虫群一般漫天飞舞,肆意吞噬侵占过往的记忆。那些或许珍贵或许平淡的记忆在蝗灾里零落成稀稀拉拉的麦穗,又湮灭成烟灰似的东西。风声,烟灰,无声的虫群轰鸣和无形的碎裂沙石将他裹挟淹没。
那些蝗虫般的……不是他的记忆,不……也不是记忆……为什么会出现在他的脑子里。
阚秋来瞳孔震颤,他不理解当前的状况,但是心里腾起一股莫名的恶心和愤怒。
人的一生应该是一台数码相机,只记录自身看过的风景,可他现在才发现,自己是一台该死的老式DVD,只会读一盘祖传老碟。如今这盘光碟播完了正面,有一只手未经允许替自己翻到了背面。
也许早就该把这盘光碟翻到背面,这样一切不合理的现象都变得合理起来,一切谜团都有了解释。
“我是……我要…………要……”
见鬼,他要做什么来着,他完全不记得了。他现在满脑子都是曾经和自己交媾过的女人……真见鬼了,像什么欲求不满小头控制大头的咸湿男。
无数层叠的虹色幻影一会儿交合一会儿分离,一个是他的身影,另一个属于女性,两具身影下荡漾起温暖潮湿的虹色水波,在幻想中的自己逐渐分裂成丝线逼近幻想中的白色短发女人时,阚秋来伸出两只手,用力拍在自己脸上。
啪!
非常响亮。
阚秋来的瞳孔稳住了,大脑也清醒片刻,他像溺水的人抓住了岸上的缆绳,猛的抬起头探出水面,深吸一口冰冷的空气让自己冷静下来。
许久,他看着头顶的路灯,看着那惨白的灯泡直到眼花才低下头。
阚秋来尚未意识到,那蝗虫般侵略的东西不是记忆,而是生物的本能……能撕扯良知粉碎理智的原始本能。
他忽然想起来了,自己是从村长家走出来的,想必是开过会了,正在往家的方向走。他又点燃一支烟,浑不在意地继续往前走,不记得自己要买油这件事。
再次见到袁启时,阚秋来觉得心脏上似乎趴着一只毒蜘蛛,那蜘蛛慢悠悠地爬遍整个心脏,忽然伸出一条后腿开始踢毛,纷飞的毒毛落在心脏上很快就发炎过敏,起了细小的水泡,又疼又痒。
他抓了抓胸口,有些微妙的不自在。
“你不坐下?”他扶着另一个没有掸过碎发的椅子问。
“……不用了。”袁启从容地叼着一根烟,眯了眯眼睛。她觉得阚秋来有些不对劲,但是具体哪里不对劲她很难描述出来,需要再观察一会儿。
“噢。”除了忘记买油,他似乎也忘了拿毛巾拍椅子这一步骤,忘了让碎发沾到客人是不好的。
“明天貌似会更冷,开摩托兜风要不改天?”袁启摁灭烟头,突然说。
“噢,好,”阚秋来没有觉得失落,甚至没来由的有些欣喜,“不兜风正好……”
他怔住了,为什么会欣喜呢?他不该觉得欣喜的。
“……不对,我去做饭给你吃。”他甩甩头,站起来准备忙碌,路过水泥桌时发现一盆黄豆和装好的石磨。
阚秋来这才想起自己原本是要磨豆浆的。
“明天早饭是豆浆面饼和棒碴粥。”他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