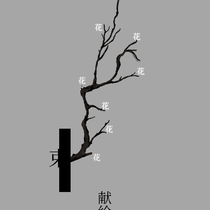窗外的街道不断向后退去,我闭眼瘫在房车沙发上,大脑像是被用力攥住一样胀得生疼。“下午再补个觉。”凌晓端着刚冲好的咖啡放到我面前的桌子上,“上半夜被梦妖叫起来要开饮料喝,下半夜被茶杯缠着要玩小游戏,你也是真行。”
“唔呃......吵到你们了不好意思。”我捧起杯子,轻吹去面上徘徊的水雾,热气从鼻腔涌入冲散了一部分困意,“谢谢啦。”
初入格林角,时光在这里失去了意义,上个路口陈设的还是雕琢细腻的古典美学人体,下条街道就变换成了一排肆意挥洒才华的抽象画作,不禁好奇继续向前会有什么全新的艺术。房车并不能进入市内,月茧在郊区找了个停车位,从驾驶座上跳下来:“我看地图上从这里往市区走很快就到购物长廊了!街上的人穿着都好有意思,我想去那里逛逛买点新衣服。森语还好吗?”
双手掩面深吸一口气,我放下咖啡杯扶着桌子站起,默认了一同出行的邀请。
阳光透过巨大玻璃拱顶洒在宽敞明亮的长廊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檀木香与海盐香,交织出一种独特的浪漫艺术气息,我们的休闲服在衣着风雅的人流街景中显得格格不入。“你不是在金砂镇买了新衣服吗?”凌晓走前面侧头看向身后的月茧。
“那哪能一样!这里可是大都市!”月茧显然不太习惯在人群中特立独行,拉低了自己的谜拟Q兜帽遮住半边脸。
我没有参与他们的讨论,为数不多的精力只够用来保持身体还在前进,月茧适时搂住我的腰部防止撞到他人。
一缕熟悉飘渺的香气勾起了我的兴趣,甜蜜像是成熟的热带水果,又参杂着淡雅的清新草木气息,宛若一位身着翩翩连衣裙正在热情待客的少女。“沙漠玫瑰?比我了解味道浓郁好多。”我招呼伙伴暂时停下脚步寻找香味的来源。
“哎呀,客人识货,”身旁蹲着的一位大叔腾一下站起,把贴得近的凌晓和月茧都吓了一跳。淡绿的围裙袋子里露出来铲子和园艺剪,他抹去手里小水壶流出来的水,“这是新进的改良品种,和大马士革玫瑰杂交后花色和香味都更上一层。我这里可是这一片最丰富的植物店,进来肯定会有你们喜欢的。”
不知什么沙地植物的根茎歪歪斜斜爬满了整面土黄色的墙,上面挂着“沙漠绿洲”四个手写古体字,看起来很有仙境之门的意味。我碰了碰月茧寻求意见,毕竟是她先提出想来这一片买衣服。月茧点点头拉上我的手往店里走:“逛街嘛,一起看看,正好房车里少个盆栽装饰。”
店主大叔所言非虚,帮忙看店的藤藤蛇正挥舞着双手欢迎,随着开门的风铃声响起,完全是踏入了全新的绿色宇宙,连屋顶上都垂下不少枝条招展,各色花香充斥整个空间,也是让我脑中的浓雾驱散了不少。“看,这排都是龙舌兰,耐活。”店主从阶梯展台上随便搬起一盆就足有半个人高,“狐尾龙舌兰,叶片宽大喜好阳光,刚听你们说房车旅行,这个再合适不过。”
“哦!这个开花就是那种一长条毛绒绒花序像麦穗一样垂下来的,挺有意思的。”我回忆着书上看过的内容,“感谢介绍啦,我们再看看——这个是什么?”我指向凌晓正在仔细看的矮小盆栽,叶片呈现出独特的星芒状,边缘带有淡淡的蓝色光泽,在阳光下闪烁着微光。
“那个叫沙地星,如果没有及时浇水的话,这玩意怕是能把根钻破我这砖地。”店长一边说一边拎着小壶快步上前补了些水份。
月茧单手举着一盆开了花的仙人球凑过来:“森语你看!这个好可爱,买来放在我们桌子上吧。”
这个仙人球不同于行驶在沙漠中看到的那些大仙人掌锋芒毕露,圆滚滚的身材上密布着没有攻击性的软刺,鲜艳的花朵让我不禁想到导游那热情似火的红发。店主突然从我们之间窜出来:“沙漠绒!花开的可漂亮了,你们赶上了好时候啊,来买一盆吧!”
“哦,啊,好,好的。”我熟练地从已经社恐慌乱到木僵的月茧手中接过沙漠绒盆栽,交给店主去打包。凌晓此时也从店门口附近端着盆栽进来,根茎肥大如酒瓶,粉嫩的花与圆润的叶好似分家了般各自长在不同枝干上:“这个也一并买了吧,就是刚刚你闻到的沙漠玫瑰,我查了下这玩意闻着味道能助眠。”
“就算助眠也解决不了被叫醒的问题啦......”我轻抚后背安抚着月茧,跟老板招呼道,“帮忙把这两盆都打包好!我们晚些时候回来拿,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