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头卡未完成 哈哈哈…………
————————
那门明明就没有上锁,又时常开一条通风的小缝,可缝中透出的黑暗却仿佛那片暗无天色的沉默森林,四处都缠绕着吓人的荆棘,连门把上都带着可怖的刺。因为体质的原因他很少受过什么骇人的伤,但这扇门他不再敢靠近半步。总是稀里糊涂地走到门的附近,又稀里糊涂的往回走,不踏入其中的原因换了又换,直到与理由的界限愈来的模糊,他方才释然,所谓血浓于水的说法,其含义建立于确定的事实之上,而他,越来理解便越感无力。
这时他反而恍惚了一下,意识就像被回忆的碎片刺伤,在伤口的空隙中互相挤压彼此,而后如波涛般翻滚奔涌。从来都不会得到结果的敲门,不再被回应的呼唤,甚至包括一只被吊在门口活生生饿死的兔子,这一切早就不言而喻,只不过也被一度忽视:他幼时所面对的与世隔绝的门里,从那日起就已经只剩下魔女一人了。
……说到底,那位将妻子跟女儿放在首位的父亲,还有那位认为世界就理应由上位种族来领导的母亲,他们的想法无一例外,亦不难揣测。遵循他们的意志所做出的选择,其对错,其悔恨,事到如今都没有再思考的意义。
他又忍不住咳嗽了几下,舌尖不自觉地压迫着咽,再自喉间舔到些锈味,最后情不自禁地呕出些卡在气管的血。
与咽下肥美的草食动物的感受不一样,也跟咽到小碎骨一类的异物的感受不一样。他再度失力地倚着墙,胸膛频繁地起伏,带出就像逃离的小动物一样紊乱的呼吸和心跳,拼命地,拼命地被激发原始的本能。从脸颊一侧滑落,最后滴在他衣领边缘的液体,混合了大部分的受之欺诈的血,还有少量的满含情绪的泪。
“......”
“你这笨蛋。”
房间外有什么轰然倒下,伴其的枪响亦不绝于耳。而他还听到了,似乎在哪儿听过的,怀念、熟悉的少女的声音。他还没有反应过来,在失去的视野那边,冰凉的右手就忽然感受到了温度。
“……白痴。”
那因恐惧引出的轻微颤抖,通过这双比他小一些的手传达到了本还有些恍惚的心里最深处,伴着轻声的细语一并,叫他猛然地惊醒,更是条件反射地抬头,全然不顾额上与右眼的血。
尽管现在还只能看见些模糊的轮廓,但于那顶过大的魔女帽之下,灰尘与擦伤的异物攀附在娇小的脸庞上,刺眼得就像一束不合时宜的光。
“你要死了吗?” 面前的那位魔女用着跟之前那句话一样,没带什么情绪的声音问道。握着他的双手,不知怎么的也在问出话后逐渐平静了下来。
他情不自禁地眯起余下的那只眼,张嘴动了动,没能出声。
“……”魔女顿了顿,紧紧握住他的双手又用力了些,“但我还不想死。”
“奥、萝……”
“别说话啊,蠢货。”
“……”
“……”
短暂的沉默间,魔女的帽檐低低地垂下,其下形成的阴影,将她本来不会有什么的面部表情遮住。她似乎在擦拭自己额上的汗水,过长的袖口中伸出了小小的手。
之后的几个呼吸,她明显发出了些不成调的音节,又仿佛沉重的深呼吸与咳嗽声的同时,与其混在一起的鼻音,带来叫人呼之欲出的,如同颜料般扩散开来的渲染。
而他有限的,模糊的视野里,仅能在她抬头后辨认出其侧脸上新添的少许痕迹。但这些不完整的信息已足以让他被灰烬沾染的眼角又开始变得湿润,然后淌过几条擦伤的伤口,最终彻底转为了扎在脸上、心上,还有意识上的阵阵刺痛。
“……我有办法,处理你的,那只眼。”她有些断断续续地,一边调整着自己说话的语调,一边伸出手,盖在了他刚刚被魔法流弹击中的右眼上。
魔女的另一只手轻轻地按在自己心口上,语调恢复到之前那样平静又冷淡的调子,她继续道:“条件是,你要成为我的使魔。”
尽管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就像面对寻常交易一样的,利益对等的事物。语气却更接近于陈述,也完全没有给他回话的空间。
“然后,带我逃出这里,普拉维斯。”她用跟小时候一样,仍然很稚嫩的嗓音高声命令道,其音色愈是接近末尾就愈来显得复杂。他听到房屋支架崩塌,听到野兽的咆哮与对应的枪响,甚至还听见了那只刺猬濒死的悲鸣,可在他面前蹲下的,就只有从记忆中消失很久的魔女一人了。
普拉维斯喘着急促的气,疼痛不过是组成混乱的一环,他昏沉得甚至没能对重获光明的这瞬间做出反应,然后在他仅仅发出一些嘶哑的喉音、组成不成器的调的时候,终于被一句话惊醒:
“因为我还不想死……所以啊、你也不许死在这里,白痴哥哥——!!”
被染红的手撑住布满木碎屑与灰尘的地,他拼命地,用尽全力地站起身来。
无论如同梦境与否,由回忆组成的幻觉在他眼前聚拢又散开,手里的温度,额上的湿润,还有眼角的痕迹,一切,都再次变得熟悉。
他猛地惊醒了过来,从稍微有些湿润的地上起了身,也不管自己的手背干净与否,两三下就把眼角的泪痕擦尽。
……哈啊。对了,这是那个时候的梦……
按照奥萝拉的被动的生存法则,即使被人类袭击再被人类所救,对能够区分不同人类的气味的他来说也都是截然不同的个体。但无论如何,为了避免麻烦以及尽快跟奥萝拉汇合,他亦从救他的人类手里逃了出来。
然后兴许是与奥萝拉失散的影响,在看见那轮红色的圆月升起的时候,他一度失去了意识,陷入刚刚的那种清晰得过头的“梦境”里面。但是视觉似乎更偏向于奥萝拉的那一边……何况能够按正确顺序区分那三种骂法的也只有奥萝拉本人。也就是说这是奥萝拉的梦,也不难想象是这只与奥萝拉互相交换的眼带来的影响。
而且、原本属于妹妹的那只眼不知怎么的,从刚刚开始就一直传来刺痛。
尽管多年来妹妹的说法都是向凶手“复仇”,但刚刚共同感知过“那时”的梦之后,他恍然醒悟了。奥萝拉作为生存意义对待的“复仇”,也许只不过是停留在表面上的浮萍。毕竟她很了解人类与人类之间的不同,正因为受到母亲的影响才更加对人类“一视同仁”。作为“不纯粹”的激进派的魔女,单纯地、强制地让自己继承着母亲那“纯粹”的思想……也就是说她并不想复仇?但她毫无疑问没有放弃推进这件事,哪怕到现在也毫无进展。又或许她只是害怕再次失去…所以在走散后,作为双生子的彼此察觉到了对方的梦。
现在的奥萝拉究竟在做什么呢。……不,在做什么都没关系。
他理不清自己被圆月所影响得躁动一片的思绪,但那种直觉始终挥之不去。于是他拍了拍自己身上的灰尘,向着“本能”的方向迈出步伐,踩着泥土与石子飞奔了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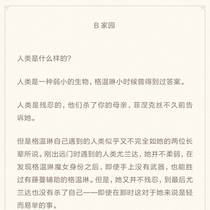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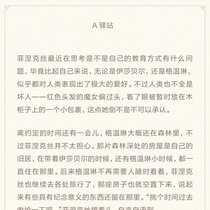





*注:有大片剧情与威尔斯剧情重复
*注:有大片剧情与威尔斯剧情重复
*注:有大片剧情与威尔斯剧情重复
当又有新的遗失了器官的魔女尸体出现在公会的停尸房里时,他就觉得事态发展很奇怪,隐隐有不好的预感在心底提醒着他还有更不可掌的事要发生。
虽然他本人很希望能有更多时间留在公会里研究“魔法”、“魔女”和“诅咒”,但再三的考虑后,他还是决定和威尔斯一起出任务:危险的外勤工作申请一位随队医疗兵来保障战斗后的第一时间进行治疗本就是合情合理的。如此也有机会见到活着的魔女,这可是比看古书记载更珍贵的情报资料。
那之后,仿佛就是要验证他心里的不安似的,魔女藏匿能力的失效、指魔针指引着猎魔人们几乎没日没夜的追捕。终于在11月13日那天,所有人聚集在了一起,进入了大魔女的“梦境”。
入梦后杰森并未察觉异常,周围发生的一切都真实的可怖,也或许这就是将要发生的。
被卷入事件中心的不是杰森,是他的好友威尔斯。
梦里这个不要命的家伙赶到森林,简单商议后,留体力不支的杰森在后缓步跟随队伍,威尔斯则直接带着杰夫冲向目标。
根据指魔针的指示,杰森尽全力在后追着,跑的上气不接下气的,但紧赶慢赶还是来晚了。
杰夫倒在地上昏迷过去,枪遗落在身旁的树根处;威尔斯腹部被打了个对穿,倒在血泊里。远处还有人,管家站着静候着他的魔女主任给另一位受伤的魔女接手,注意到有人靠近,警戒的将目光转移过来。
那一刹杰森感觉被冷水浇注了全身,羸弱的医疗兵自然不是魔女和使魔的对手,哪怕他们中的一人有负伤。杰森高度戒备起来,好在魔女放过了自己,默许他带走杰夫和威尔斯。一直到回到公会、抢救回威尔斯,杰森才后知后觉的发现手还颤。
作为见证过无数病痛和死亡的医疗部一员,杰森本该早早习惯这一切,但这一切发生在发小身上时,看着眼睁睁看着相熟之人心率降低的那刻,那种对生命流逝的无能为力和面直面对死亡的恐惧席卷而来,让他联想到自己的未解的诅咒,一点点接近、等待死亡降临……这种感觉实在太糟糕了!
“贵安,诸位梦者们。我是魔女之祖莉莉丝。”
恍惚之际,所有人回到了梦开始的地方,一个陌生的女声来自面前那个稚嫩的少女,却散发着不容人质疑的态度,向人们叙述当前发生的一切。
还好只是个梦,一切都还来得及阻止。
杰森有些侥幸,但目前看来,他们都还无法冲“梦”里醒来,他思索着大魔女说最后的话,似乎是在人们预警。
来到病房,威尔斯还没有醒。
杰森想到那时威尔斯得知事情真相后简直要杀人的神情,杰森完全有理由相信他接下来会做出什么失去理智的冲动的行为,以及可能的后果,索性直接直接迷晕将威尔斯带回公会,只是事发突然施法的力度没能掌握好……
关门,杰森看了看病床上昏迷的人,那双眼和平时一样闭着,要不是他现在的状态是自己一手所致,这样看就像在装睡。目光移留在了床边那张空荡荡的椅子,他记得在上一个梦里,有一个新人女孩一直守护在这张床边静候床上人醒来——从威尔斯被送入手术室开始、到转入重症病房为止,她一直跟随在一旁,红肿还泛着水光的双眼暴露了她已经在没人的地方哭过了几次。
得知一切是梦后,杰森就没有在公会再看到这个女孩。
他听威尔斯提过她的名字好像是叫兰卡·莫尔斯,很早以前就认识还托朋友照顾。而那一刻杰森从她的表现和反应察觉到一种不同寻常的感情。至少不是威尔斯说的那样只是普通的认识关系。
杰森在那张椅子上坐下,虽然魔法剂量大了写,但算算时间也应该差不多了。难得在梦里才能有这样安逸空闲的时间——尽管这都是虚假的。他翻开书静静的阅读着、等着那人醒,这本还是他申请出这次任务前,拉斐尔推荐给他的,他还没看完。
如他所料一般,不过十几分钟的时间威尔斯就醒了。只是没想到对方二话不说、直接从床上惊坐起身,吓了杰森一大跳,然后双手托住头仿佛在承受极大的痛苦。
“醒了?”话出口,杰森也知道这是明知故问,但床上的人只是微微侧了侧头,不说话。
稍微想了想便明白了,这人是因为睡了太久后、刚醒来动作幅度太大,大脑一时间供血不足而引起的眩晕。
另外还有自己魔法残留……
真是不让人省心的家伙。
想明白了的杰森也有些不好意思,叹了口气,凝聚魔力,手覆盖在威尔斯额前方慢慢催动魔法,帮他驱散了残留的恶心、眩晕感。在看到对方脸色恢复后准备收手时,却被威尔斯一把抓住了手腕,力气之大完全不像一个刚睡醒的人!
“杰森·史蒂文森!你为什么阻止我?”
威尔斯愤愤的道。
虽然猜到会是这样的发展,但杰森还是觉得自己的好心被当作驴肝肺了。看到威尔斯使劲眯着眼睛想看清事物的样子,还是忍不住叹息着递过去他的眼镜。
威尔斯直接接过戴上,然后,重新发问:“你为什么拦我?”
为什么拦?这人已经濒死过一次了,果然是没有把那个预言当一回事!不考虑生死,满脑子就只有消灭魔女!
杰森揉着发疼的手腕,有些没好气:“不然呢?放任你再去寻死?”
“这不是寻死。”
“一个想寻短见的人没资格这么说。”
“都是些陈年旧事,也与你无关!”
这话说的杰森有些恼怒。
当年他们相识还是因为威尔斯想不开寻短见才被家里送到教堂,还是修女妈妈和自己照顾的他!活到现在这个年纪了居然还一点都不懂珍惜生命,每每谈论到关乎自身生命问题时这人就是一副“死了也无所谓”的模样。
杰森是爱惜生命的人,他不认为有人明知会死还往枪口上撞,而眼前这个男人却一而再、再而三,总是不管不顾的冲向最危险的地方,然后遍体鳞伤的回来!
杰森抿着嘴、微微蹙眉。
“别忘了是谁负责治疗照顾的你,请不要给我们增加不必要的工作量。”
“那么我也希望你清楚,你这么做妨碍到我的工作了!”
混账东西!
“威尔斯·本!你知不知道当时再继续下去,你离死就只差一步?没人知道再来一次的下场会是什么!!当时什么情况我不信你不明白!”
你难道就那么想死吗!!
一股脑把气话全都吐出来,让杰森舒坦了不少,但心里的怒火还没有消失。
他是威尔斯的搭档,他讨厌这个人,特别是当他每次出任务都特别积极的样子。别人看来或许觉得他是出于对魔女母亲的仇恨和身的正义感而做的猎魔人,但只有少数真正了解的人才知道,猎杀魔女,只是他希望能在战斗中找到自己的葬身之地罢了。
果然,威尔斯对此的态度很淡,甚至还笑了,仿佛他们正在谈论人是不认识的路人而不是自己,接话时语气里的温度和感情也低了几分,平淡的有些冷。
“你知道我不在乎的。即便我真的死了,你也不需要为别人的生死负责。史蒂文森,不论你上个梦里看到什么,那只是个梦罢了。”
杰森听完,只觉得举起了拳头重重的打出去,结果只挥中空气,怒气全都憋回心里不说,还平添了郁闷。
“也有真实的,比如我们现在在梦里吵架。”
杰森觉得自己真的是没脾气了,闭目靠在椅背上,话说出口都显得有气无力。
“毫无意义的争吵。”威尔斯过来拍了拍对面人的肩膀,转而去取自己在床头柜上的衣服。“我们得找找醒来的办法。你要是还想有话,把这些话留到外面再说吧。”
杰森看着准备离开的背影,思索要不要开口。他直觉觉得,如果再放任威尔斯去,这个不要命的家伙不知道还会做成什么危险行为。
“我知道你不想听,但是本。”杰森还是在威尔斯开门之际叫住了他。每当有一个生命逝去总有人会为他伤心难过。例如你的叔父……和兰卡。”
威尔斯果然停下动作,迟疑回头望杰森:“兰卡怎么了?”
“她很在意你。”杰森想了想,补充道:“不是对前辈的在意,是对爱慕敬仰的对象的在意。我不确定,那孩子应该是对你有好感。”
杰森没说的那么具体,他觉得威尔斯自己能体会。
然而威尔斯的答复让杰森又刷新了对他认知。
“你想多了,我和兰卡相识时间比你久,我想我还算了解她。换成如果是马修,她也会同样伤心的。”
杰森只有回以威尔斯一记白眼,隐约见听到对方小声说很久没到女孩了,也就开口提醒:“兰卡最近没来公会。”
下一刻,重重的开关门声响起。空荡荡的病房里留下杰森一人。
真是自说自话到了极点……
没有心情再去做其他事情了,杰森觉得有点头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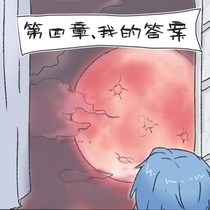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完全在写少女恋爱……这可是凝津啊?!
*
*字数:2642
*
菈弥亚陷在恐惧里。
鸟儿不歌唱,虫儿不耳语,白天未受它们呼唤却依旧换走黑夜。今天的云朵是灰白色,天空的蓝像是要被稀释掉一样寡淡。
她从床上坐起,先摸摸胸口——心脏还在跳,然后捏捏指尖、确认了无论哪个关节都没有祖安破皮肤的细线,最后,她赤着脚踩在地上,扶着墙面慢吞吞地走了几步。
菈弥亚的双腿带动她的身体。它们因没能甩开梦魇而愧疚得直打颤,踩在地上时十分地绵软,就好像是踏在了软乎乎的棉花里。她不得不非常小心,甚至刚挪出房间就觉得该停下来休息会儿。
狗就是这时候来的。
菈弥亚从未见过这样的犬种。它像是一把弓或一头小鹿,每跑一步,象牙白的腰腹都优美地伸展着,将它修长的足送得更远。它似乎是专程来寻她,在临近她时放缓了速度。
哒、哒、哒、
哒。
它垂下头停在她身侧,长长的吻蹭上她的指尖。细鞭子一样的尾轻微晃着,是友好的姿态。
它也像来自梦里的生灵。
菈弥亚轻轻屏住气,感受到手指被绵长有力的呼吸吹拂,犬的鼻头湿润,生命如海边潮汐盈余,随着它轻轻碰气,菈弥亚浮在半空的灵魂也重归身躯。
“活的……是你赶跑了它们吗?”
——铃声引魂找到归途,而犬吠会将其驱逐。
她的双脚总算松懈下来,半跪半坐在这乖巧优雅的犬身边,将脸孔埋在它短短的被毛里。它穿着件衣服,菈弥亚小心地不弄皱它。可她的眼泪落下去,还是将它弄湿了。
犬不安地偏过头看她。她的眼还流着泪,声音里有无法阻止的鼻音,可她的语调是轻快的,一如往常:“你是谁家的小狗?你真漂亮。”
犬退开两步,菈弥亚看清了那件衣服,突然有点儿不好意思,“原来你是布鲁斯舞者的狗……”
啊呀,她哭湿了他的衣服。
“你知不知道他到底叫什么?”她和这条犬说更多的话,好像它能帮忙转告似的,“你看,我现在叫他布鲁斯舞者,因为他的节奏是这样的。”
她踮着脚尖,搂着不存在的舞伴跳了两个八拍的慢四,犬专心地看着她,细细的尾巴左右摆动。菈弥亚追着它问,“是他吧,是他吧?”
犬原地转了两圈,应景地吠。它的动作轻灵,也像一名舞者。
菈弥亚又想起它不在的夜半。她亲一亲它薄薄的耳朵,“你要是能告诉我他叫什么就好啦。昨天的那些魂灵已死,不能再记住生前的事情……我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就没法帮忙送他们走。”
——可“断眉”究竟叫什么名字呢?
*
“——还没记起来。”当事人说。
他看起来并不困扰或焦虑,“我们认识的每个人都有名字,哪怕是我这样已经彻底忘却了过去的人,也有了属于自己的新名。”
“那您记得您的狗叫什么名字吗?它没戴铭牌。”
“我没有相关的印象……说是我的狗也不特别确切,老实说,我也是这两天才遇到这条狗。它很亲近我,所以我姑且让它穿我的外套,以免它被捉去炖了。”
“它又没多少肉,”菈弥亚本想向断眉请求让它晚上睡在自己的房间里,一听这话也顾不上了,“让它留在安全的地方吧,它到处跑呢!”
她真喜欢那条纤细的犬啊!它又乖顺又聪明,甚至能给自己洗澡……她从没见过这样的狗。
“我也不是没想过这么做,”断眉看了看菈弥亚,她正露出哀求的眼神,他局促地摘下眼镜用衣摆擦了擦,“虽然我实在记不得了,可也许它确实是我之前养的狗,我能想起它是条惠比特犬,需要大量运动——这也是我放它出来活动的原因。”
“是的。它有非常漂亮的体型,步伐又稳又轻巧,适合……”
“——适合跳布鲁斯是吗?就像我会更适合‘布鲁斯舞者’的名字——你想要那么叫我吗?虽然我可能并不会跳舞。”
啊呀!这可不得了!菈弥亚捂住嘴“滕”地退了一小步:“我、我说出来了?”
“你没有说出来,是狗告诉我的。”断眉笑着戴回眼镜,站到她面前邀请,“菈弥亚,不介意的话,请问可以教我跳慢四步吗?”
这也像是梦里才会发生的事,她的布鲁斯舞者真的会是舞者了!
菈弥亚面对美梦从不患得患失,她快乐地抓住他的手,“那我就来教您吧!您记得慢一点儿的旋律吗?”
于是断眉哼出她口琴奏出过的旋律。是她最喜欢的两句,珊雅常常对着她唱。
“我那亲爱的姑娘啊,快快来到我身旁……”
她还想接着唱下去,然而她的舞者停下了,问,“菈弥亚,这种节奏对吗?我们该怎么开始?”
“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吧,我来跳男步,”菈弥亚停下歌唱,一只手虚虚地按在他的腰间。那里的肌肉立即就绷紧了。
“您好像很不习惯肢体接触呢!是和性别有关还是对谁都这样呢?”
“我似乎不太擅长应付异性,不过这些东西总要习惯的,我们继续,菈弥亚……接下来该怎么样?”
菈弥亚用行动回答他。她迈出一步,脚尖抵着对方、迫使他退后一步。舞者该当是舞者,他很快地就跟上了,哪怕菈弥亚临时加了转身的动作,他好像也能从她手臂的发力里头猜到,毫不费力地跟上她。
于是菈弥亚又想,他很适合观赏型的竞技运动类项目,比如花样滑冰。
“您喜欢自己现在的外形和着装吗?”她问。
舞者的指尖在她肩膀轻轻地叩了两下,就像她思考时会去绕两圈自己的黑发。
“我认为是的。”他说。
菈弥亚很快就不用引导他了,他加入一些力量,隐隐地要占据舞步的主动权。
“您会不会格斗或者开枪呢?这里似乎很危险……”她又问。这两者对于她而言都不是太过遥远的事情,虽然不像呼吸、吃饭那么频繁,可在她待过的某些地方,这两者出现的频率甚至比珊雅在当地演出的频次还高。
但对于舞者来说好像并不是那么回事。他紧张地握紧了菈弥亚的手,原本放松了的身体也像被拧紧了发条的木偶,再次变得僵硬了。
“我对打架毫无兴趣,也不会对人开枪。但好歹,我是个成年男性,和大家一起行动应该没有太大问题,不必担心我。”
天!他可比她要担心得多……说不定他长那么大从来都还没打过架呢。菈弥亚在心里偷偷批评自己,决定同他一起承担他的慌张,“你要是什么时候觉得难过,能不能告诉我呢?”
“比起悲伤的记忆,我更想和你分享快乐的时刻。”
“有高兴的事你当然会告诉我啦,”菈弥亚理所当然地讲,因为她也会分享停在荷叶上的蜻蜓、生长在水洼里的彩虹。
可让人难过的事呢?跳舞的时候摔倒了、在树上睡着翻了下来……如果难过的时候没有人在,那些让人难过的事就会和太阳一起隐没在夜晚,不再会被看见了。
菈弥亚盯着他的眼睛,踮起脚去凑近他:“你难过和高兴的事,我都想知道。”
映在她双眼的青年往后仰,“好,好,我答应你……怎么这么盯着我,我脸上沾了什么吗?”
“动物生病的时候会装作没事,日本人也一样,经常很真诚地说假话……我在看你有没有骗我。”
青年好像屏住了呼吸,就像早上的她。
他真可爱!
菈弥亚笑起来。她轻轻地拥抱他,然后退回到让他能自在呼吸的距离。
“相信你了!布鲁斯还有很多种舞步,我慢慢地教给你。”
每天、每天。她会来教,也会来问,会用她自己的眼睛来观察。即使不知名姓、不识过去、她一直拉着他的手,总能摸索出她的舞者是走在怎么样的道路上。
=======================================
下节预告
随着探索的深入,这片建筑的全貌逐渐展现。
也许是因为吊桥效应,菈弥亚与“断眉”的感情迅速升温。但随着“断眉”逐渐回忆起失忆前的事,他的身份、立场也变得暧昧不清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