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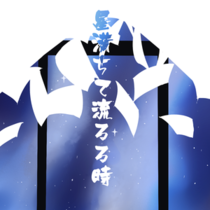








“这怎么回事儿?!”
耳边响起陌生人惊怒地喊声,帕王摘下头戴式VR设备,眯着眼稍微适应了一下光线。
苏兹·克劳福德正坐在不远处的休息区,一手握着冰激凌,一手紧捏着勺子,用力到指尖发白。她转身背对着帕王,肩膀微微地抖动着,从两人魔术上的联结里,帕王能感受到苏兹正压抑着惊天动地的大笑声。
在服装设计师的身旁,同为红组的御主基兰则是完全不同的状态——他双手抱胸,一张脸完全掩盖在一头蓬乱卷曲的亚麻色长发中,鸡啄米似的一下一下点着。游戏厅里播放着震天响的音乐,纷繁的灯光乱舞,来寻欢作乐的人们时不时爆发出巨大的欢呼声。在这种环境里,不仅睡着了,而且睡得无比香甜,这本身也算是奇事一桩。
更何况,自己的从者正在进行一场从者级别的争斗。
帕王将视线转向对面,另一个VR体验平台上,刚刚与自己对战的从者不见身影,倒是他身后的垃圾桶不知为何翻倒在地,杯装饮料和食物餐盒撒了一地,正留出一个人形的空档。价格不菲的头戴设备就这样惨兮兮地躺在这一地的残羹冷炊上,恐怕这就是工作人员怒火的由来。
“你们有谁看到刚刚那个梳辫子的男人了吗?”见没人应答,那人又朝着苏兹的方向,又问了一遍。
苏兹不着痕迹地踢了一下基兰的椅子腿:“醒一醒,他去哪里了?”梦会周公的魔术师被惊醒,差点从椅子上弹起来:“什么什么,怎么了!!”
当听到大家都在寻找自己从者时,基兰抬起了手:“他啊……他在……”话音未落,一阵无形的力量拉住了他指向背后手指,拎着它生生转了半个圈。
“他往那边去了。”苏兹顺着基兰手指的方向,朝着一旁的安全出口面无表情道。
工作人员转头看向帕王,红组的Saber立刻与御主指向同一个方向,务必真诚地回答:“我刚刚和他联机,突然就断开连接了,摘了头盔我看到那扇门动了一下。”
有理有据令人信服!苏兹在心里给帕王比了个小蓝手,基兰还没搞清状况,只是被阿芮寇妮缠着,只能跟着点了点头。
体验馆的人最后狐疑地打量了一圈三人,终于追进了安全通道。
见人走远,苏兹收回礼装,偏头瞧了瞧基兰身后的空气,问道:“Lancer在你身后?”
基兰有些无奈地点了点头,向自己不知为何不愿现出实体的英灵问道:“您这又是唱的哪出啊……”
“回避的时候用力过猛,栽进垃圾桶里了吧?”帕王也走下体验台,落座前还不忘把座椅朝远离Lancer的方向挪去,“这么老远都能闻到味儿。”
“现在的圣杯真是随便,什么都能召唤出来。以为好歹都是个人形,没想到连犬科都能回应召唤,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基兰语气毫无起伏地复述完英灵的念话,立刻指向背后,撇清关系,“他说的,不是我。”
还维持着实体的英灵从容不迫地挖了一勺御主的冰激凌:“可以啊,有机会咱们真刀真枪的打一架,差着几个世纪,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一代不如一代。”
“行了!”苏兹戳了戳不知何时出现的使魔,制止口水战无意义地升级,“先回去和其他组碰一下,我有事要说。”
她拎起手包,像是迫不及待地要赴一场邀约,翘着嘴角对两人说道:“稍安勿躁,机会很快就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