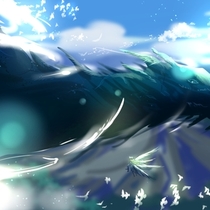*共4100多字
*标题想表达的其实是希望大家珍惜眼前人(不
*我先滑跪给姜可老师磕头了!!!!!!没时间打磨得更细致,非常对不起!!!!!
*我恨调班,我恨。
—————————————————————————————
1.
一年过去,渡边凉司总算习惯了“大正”这一新年号,亦习惯了他作为军官的新身份。
两年前他应征入伍,凭借优秀的身体素质和头脑,以及出色的运筹帷幄的能力,他拔得头筹,于半年前获得了军官一职。本就出身平凡的他自然成了父母口中的骄傲,邻里议论的名人。除去部队训练和应酬,余下的时间他都陪伴在父母左右孝敬二老,日子过得平淡且幸福。
不过,他总觉得少了什么。
究竟是缺了什么呢?凉司扪心自问,却又说不上来。这烦恼一直在他心尖乱挠,弄得他心痒痒。
直到七月中旬的某日,一户人家搬进了他家隔壁的空屋。
凉司走在被夕晖染成橙红色的坡道上,远远就瞄见父母同新邻居聊得眉飞色舞,他不自觉地笑笑,脑中组织起寒暄语。
一抹灵动的蓝色突然闯进他的视野。
邻家门前的垂帘被一位少女撩开,脸上绽着灿烂的笑颜。她身着蓝底印花袴裙,小跳到她那略显憔悴的母亲身边,垂在身后的麻花辫跟着跃动两下,扎在头上的黄色蝴蝶结与她琥珀色的双瞳相衬相映,显得分外醒目。
少女向他的父母微鞠一躬。她起身的瞬间,二人对上视线。
凉司呆在原地站直身子,少女则眨了眨琥珀色的双眼,错愕的神情转而变成甜美的微笑。
喔喔,凉司,你回来了啊。两鬓斑白的老人招呼他。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来打个招呼。
……我叫渡边凉司,请多指教。他僵硬地行礼,适才想到的寒暄语被忘得一干二净。
“我是黎悦,还请你多多关照咯,渡边哥!”
黎悦俏皮地吐舌,开始上下打量他。凉司只是木木地站着。
毕竟对他来说,心脏仿佛要跳出胸膛的事还是头一遭。
2.
鹅黄色灯光照亮了打扫得干净整洁的店面。一张檀木方桌配上两到四把椅子,数对桌椅组合将其分为大大小小的私人空间。三两幅油画挂在墙上作为装饰,女仆的问好、绅士们的聊天、唱片机播放的唢呐声共同织成店内的背景音。
有别于坐在对面愉快地哼着小曲的黎悦,渡边凉司是第一次来什么洋风咖啡店。他拿起茶杯抿了一口,旋即皱皱眉——比起红茶,他更爱喝大麦茶。
“让您久等了!这是您点的两份小蛋糕。”
女仆将盘子端上桌,优雅地欠身离开。黎悦眼睛一亮,合掌说了一声“我开动了”便切下一小块蛋糕送入嘴中。
“唔、好好次——!”黎悦托着脸颊赞叹着。她正要切下第二块,却瞄见凉司还没拿起刀叉。
“怎么了渡边哥,你不吃么?”她咬着叉子微微歪头,眨了眨琥珀色的双瞳。
“这是?甜点吗?”凉司端详着盘子里的三角形食物。边缘被切得十分平整,白色层或许是奶油,淡黄色的大概是蛋糕?最顶上缀着一颗草莓,看起来很讨少女们的欢心。
黎悦用力点点头:“嗯!好像是最近流行起来的蛋糕,不光长得很可爱,味道也很不错呢!”
凉司看看盘中的蛋糕,又看了看正捧着脸,洋溢着幸福的黎悦。他垂眸片刻,把自己的盘子推到黎悦面前。
“我这块也给你吧。”
——既然你这么喜欢的话,他在心里默默补充道。
“哎?真的吗?!”黎悦的语气有些激动,“渡边哥真的愿意让给我吗?”
“当然。”
或许是被少女愈发灿烂的笑容感染,凉司也禁不住嘴角上扬:“慢慢吃,不着急。”看着黎悦尽兴地享受甜点,凉司再度拿起茶杯。偶尔喝次红茶也不错,他如是想。
3.
“……渡边哥,觉得今天的默剧,好看么?”
黎悦低着头,眼角微红地询问道。渡边凉司本要把脱下的外套披在少女身上,现在他愣了一下,提着外套的手停在半空中。
“……是很深刻的故事。”半晌,他回答着,两手落在黎悦肩上。
“人家觉得好难过啊!”黎悦攥住外套,吸了吸鼻子,“他们好不容易才在一起的,却因为战争生死两隔……”她嘟起嘴,踹了一下脚边的小石子。石子顺势滚下斜坡,咕咚一声掉入河中。二人相对无言,萧瑟的秋风卷起落叶,西落的残阳如血,二人的影子被拉得很长。
“……这种事太悲伤了。”黎悦喃喃自语。忽然她激灵一下,转过头慌张地看着凉司:“啊、我不是说渡边哥不好,只是——”
一只大手落在黎悦的脑袋上,轻轻揉揉:“我不会离开的。”凉司对上那双仍然有些红肿的琥珀色眼眸,顿了顿接着说:“……哪怕要上战场,我也会回来。”
“真的吗?”她看着他,双颊微微鼓起。
“真的。”他坚定地点点头。
“那,”她又吸了吸鼻子,伸出右手,“渡边哥和我拉勾。”
“好。”他勾住她的小指。
“谢谢你渡边哥,今天玩得很开心!”黎悦把外套折好交给凉司,一如既往的笑容回到她脸上,“明天见咯!”她挥挥手,转身撩起门前的布帘。
“等等,黎悦。”凉司手捧外套,喊住正要进屋的少女。迎上她略显疑惑的神情,他微微一笑:“叫凉司哥就行了。”
“还有,明天见。”
4.
除夕夜0点,昭示新年到来的钟声在寺庙内回响,人们此起彼伏地欢呼。
“新年快乐,黎悦。”“凉司哥也新年快乐!”
青年与少女相视一笑,随后凉司握住黎悦的手腕,挤进参拜的队列中。轮到二人许愿时,黎悦忍不住偷瞄凉司,再合上双眼。
希望今年和凉司哥在一起的时间能更多一些……!她心中默念。
“黎悦许了什么愿望?”在返程的蒸汽机车上,凉司微笑着如是问道。
“是、秘、密、喔!”黎悦挤挤眼睛,举着食指摇晃两下,“而且一旦说出来了,愿望也就不会被实现了嘛!”
凉司回过头,看着依然灯火通明的街道:“说的也是……”
“那就希望我们的愿望都能实现吧。”
不知为何,黎悦从凉司的语气中听出不一样的味道。她正要回头观察他的神情,蒸汽机车却停了下来。而渡边凉司扔下一句“该下车了”便拉住她的胳膊,头也不回地往车门走。
黎悦不解地歪头,想要问些什么却也只能跟着他的步伐一路到家。连告别语也是“晚安”和“新年快乐”,不是“明天见”。
难道有什么见不到的理由吗?黎悦目送凉司走进隔壁的房屋,呼出的白气消失在空气里。
5.
黎悦的预感是正确的。
次日,她敲响了渡边家的门,甜甜地问道凉司哥在不在呀,得到的却是老人家温柔地抚摸她的脑袋。
凉司的话,一大早就回部队里去了。老人答道。
哎?为什么?黎悦诧异地眨眨眼,这几天应该还是新年休假吧?
好像是部队里来了紧急通知,老妇人补充。
这、这样啊,那也没办法……黎悦有些失落,她向两位老人告别,径自回到自己家中。
啪!她用力甩上自己的房门,往床上一横,开始盯着天花板发呆。
原来昨晚抽到的凶签是这个意思吗……她嘀咕着。
那之后黎悦也几度前去渡边家拜访,但得到的几乎都是一样的回答。新年假期都如此,更别提开春返工了。最幸运的时候她在睡前看见回家的渡边凉司,于是她拉开窗向他挥挥手。青年闻声抬起头,冲她挤出一个微笑,挥了挥手后一脸疲惫地走进隔壁屋。除此之外,她几乎见不到他的人影。
这也包括她生日那天。3月2日当晚,她的母亲在场,渡边夫妇在场,同龄朋友也在场,唯独渡边凉司缺席。在大家的祝福声中,她礼貌地笑着回答谢谢,心里却唯独想听他亲口祝福她,并亲手送上他挑选的礼物。然而少女的幻想如同泡沫般一碰即碎,她不得不接受渡边夫妇代为祝福和礼物盒。
神仿佛开玩笑似的,反向实现了她的愿望。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神大人要恶作剧也得有个限度哇!
黎悦抱着枕头躺在床上,烦闷地双腿蹬床。
唉,再烦恼也无济于事,睡吧。
不过,神貌似没那么坏心眼。很快,她等来了小小的转机。
四月底的某天,渡边夫妇喊住正要去上学的黎悦,并告诉她凉司今晚会在XX公园等她。黎悦听罢禁不住嘴角上扬,向夫妇俩道谢后,她走在街上脚步轻盈,难得地哼起小曲。
放学后她拎起早已收拾完的提包,下了车便向XX公园冲去。她远远地看见等在门口的青年,向他大力挥手:凉司哥,这里这里!
青年还是同四个月前一样微笑着,只是他的眼睛下方出现了黑眼圈。黎悦跑到他身边挽住他的胳膊:我们走吧!
嗯。渡边凉司点了点头。
然而,等到二人找了棵树坐下,黎悦反倒愣了神。明明有如山一般多的话想告诉他,见到本人的瞬间全都烟消云散。
“…喂,我说,凉司哥——”
身旁人从刚才起就沉默到现在,她轻唤他的名字,回过头却发现青年不知何时倚着树干紧闭双眼。黎悦凑近了些,对方均匀的呼吸声传进她的耳中,唇边还带着一抹浅浅的笑。
是这段时间太累了吧……黎悦为他盖上薄毯,摘下他的军帽,再为他打理好凌乱的刘海。踟蹰一会后,她俯身轻吻他的额头。
“晚安,做个好梦。”
6.
夏天来了。街上又响起了聒噪的蝉鸣,行人们纷纷换上了夏装。黎悦记得一年前自己搬来的时候是夏季,第一次和渡边凉司去洋风咖啡店也在这个季节。
她掰着指头算了算,喔,好像有半年没和凉司哥一起出门了。
——四月底的那次不算!哪有约了别人自己却累到睡着的理!下次见到凉司哥要好好抱怨一下!
黎悦嘟着嘴,闷头饮下最后一口汽水,弹珠在瓶中发出咔啦的声响。她把摊开的作业本推到一边,整个人趴到桌上。
……也不知道凉司哥什么时候再有时间……
黎悦发出深深的叹息,不经意地抬起头,下一秒她琥珀色的瞳孔变得瞠圆。
她噌地站起,椅子啪地倒地,空空的弹珠汽水瓶在桌上咕噜噜地滚了几下。黎悦三步并两步跑下楼梯,踩着小皮鞋撩起布帘,一句“凉司哥”哽在喉间呼之欲出——
她看见青年攥着一张红纸,他的手微微颤抖,眉头紧锁。
她知道那是什么。十年前她的父亲因那页红纸而一去不返。
渡边凉司闻声回过头,心脏漏跳一拍。他后退一步,声音有些颤抖:……黎悦,这是……
黎悦咬住嘴唇,难闻的铁锈味在她口中弥漫开来。她垂着头,用袖子抹了抹脸,再红着眼角,向渡边凉司伸出小拇指。
“凉司哥,我们之前约好了。”
“……嗯。”
青年勾住了少女的小指。
大正三年八月,大//日//本//帝//国正式向德//意//志//帝//国宣战。
7.
自那之后过去了四年有余。黎悦已经习惯了学校与家两点一线的生活,周末同友人出门时也不再被问到关于“邻家的军官哥哥”的问题。她嬉笑着切下一块蛋糕送入嘴中,和那时是一样的味道,但又感觉哪里不对。绅士们激烈讨论着捷报频传的前线,又说他们就快回来了。
黎悦叠好信纸塞进信封,再小心翼翼地封上口子。五六封信件的发件人都赫然写着“渡边凉司”,但大约一年前开始就没再收到了。
凉司哥是忙着和敌人作战吧!反正马上就能见到了!黎悦把信件塞到枕头下面,拉下顶灯开关。
军队凯旋归来的当日,她被友人拉去码头迎接。冰冷的海风拍打在她的脸上,黎悦禁不住裹紧了自己。从船上下来的军人们个个灰头土脸,其中还有不少挨冻的、中弹的伤员,没了当年意气风发的模样。
黎悦听见周围窃窃私语,但她并不在意这个。
等到军人们悉数下船,人群散去,友人拍拍她的肩膀,她才怅然若失地扭过头看着友人。
凉司哥呢……?她颤颤巍巍地问。
友人被她问懵了,摇摇头说不知道呀。
她一把推开友人,用有生以来最快的速度赶回家——
——那里仅剩一只木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