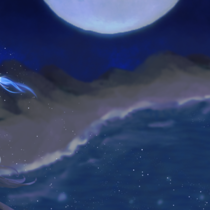













“您好,欢迎光临。Mommy!来客人了。”身材娇小的女仆打扮少女看了一眼来客便没精打采道,丝毫没有挪动一下屁股的意思。
洛浦西蒂也没什么意见,径直走向了银白色头发的女人,“找到您这里可真不容易,你这里可以接受我的委托吗?”
女人看了看洛浦西蒂,脸上的表情不咸不淡:“报酬?”
“啊,有的!”洛浦西蒂从披风里面掏出了一个刻着魔纹的罐子,“我在旅行途中收集的,希望支付得了,您看看?”
女人看了看罐子,伸手摸了摸,心下了然:“足够了,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洛浦西蒂搓了搓手,粉白的脸染上了一点红晕,“那……现在你看方便吗?话说老板怎么称呼。”
“墨尔波墨涅,梅拉,走了,带上行礼。客人你的船坐三人应该是足够的吧。”墨尔波墨涅起身,招呼上一边闷闷不乐的小姑娘。
“Mommy!这个客人没有给我报酬!她闻上去难吃极了!”小姑娘气鼓鼓的向墨尔波墨涅申诉,不过抗议无效,洛浦西蒂给的报酬墨尔波墨涅非常满意,这一趟看来是必走无疑了。
“客人,海上有什么在特别吸引你的东西吗?”梅拉很好奇这个钻空子到来的客人,她看上去很弱,出海对她来说算不上明智之举。
“嗯?哦哦,你问我,吸引我的东西……吗?”洛浦西蒂思索着,金色的眼睛里面起了雾,“美景,传说……或者是冒险本身都在吸引着我,更何况我的生命要是太过平淡,总感觉对不起我的母亲呢。”
“嗯……又菜又爱玩的客人。”梅拉不知道从哪里找到了小本子记录了下来,“洛浦西蒂,总感觉这不会是我们唯一的一次合作。”
墨尔波墨涅走了过来搓了搓梅拉的头,将她蓬松的头发搞的乱七八糟,“客人的报酬我很满意,有需要的话下次也可以找我。”
船只渐行渐远,已经看不到来时的路,洛浦西蒂跪坐在甲板上,朝着海上张望,她期待着,但是风平浪静。
“已经很远了,客人。再远就没法保证你的安全了,出了易灵间的我和普通堕天使的能力差不多。”墨尔波墨涅看着手里的光球朝着洛浦西蒂说到。
洛浦西蒂则是有些失望地回应道:“啊,那我们回程吧。”
飘渺的歌声顺着雾气飘到了船周,墨尔波墨涅和梅拉如临大敌,洛浦西蒂却是失了智般站了起来,三两下爬上了围栏。
“是你吗?是你吗?”洛浦西蒂向着迷雾伸出手去,墨尔波墨涅和梅拉心都提到了嗓子眼,雾气却轻轻柔柔地接住了洛浦西蒂,把她推回了船上。
返程时的路上,洛浦西蒂一直吹着她的口琴,调子简单极了,梅拉听了两遍就能跟着哼哼。
雾气一直围在船的周边,直到大陆的轮廓出现在了墨尔波墨涅的眼中。
雾气散去,洛浦西蒂停下了吹奏。
晶莹的拟态眼泪打湿了斗篷。
洛浦西蒂轻快地跳下船,脸上已经看不到眼泪的踪迹,她笑着向着墨尔波墨涅和梅拉挥挥手,“愉快的旅途,感谢二位的陪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