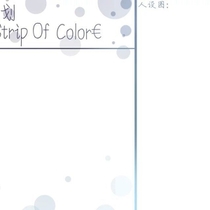----2471字----
瑞贝利安盯着自己的旁边的队长,表情非常认真。
“那个叫菲什么扎什么德是谁啊?”
如果说这名战士在加入瓦尔哈拉之前就态度恶劣地挑衅了队员的行为本身让队员们对他有所排斥的话,他擅自加入队伍之后的反复捣乱和不配合就让其他人不打算和他分享信息。他虽然和他们一起被传送到这座塔里,但事实上他一点关于塔,关于战争,关于任务的信息都不知道。尽管瑞贝利安可以说他关心的只是如何熊成一个熊孩子该有的样子,但是在队友频繁提起菲尔札·裘德的名字的时候,他还是觉得必须知道这个人是谁不可。
这么想了,所以就这么问了,但是奥列格也是一脸茫然地看回他。
“那个叫菲什么扎什么德的人……咦这人是谁啊?”
重复了一下瑞贝利安的问句,奥列格露出了尴尬的表情,偷偷扭头看了旁边的阿伦德尔。半精灵露出来难以置信的表情,而旁边的卡利亚估计已经开始后悔最初和他们一起出来执行暗杀任务了吧。
“他是邻国的将军,也是我们的暗杀对象。”阿伦德尔苦笑着给自己的队长讲解,此时他余光感觉到其他几位队员也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他觉得这群人里记得最初暗杀任务的人只有自己和卡利亚了。
“咳咳,所以继续去探索第三层吧。”奥列格尴尬地干咳两声,推着阿伦德尔向某个房间走去,还不忘回头招呼一声不打算走的卡利亚:“我们要走咯,千万别掉队啊。”
突然被点名,卡利亚露出一个遗憾的笑容,摇了摇头:“我把这位小哥带去一楼,你们继续寻找菲尔札·裘德吧。”
毕竟这个任务是安排给他们这群人的,卡利亚只要尽了引路人和监督人的本分就好。阿伦德尔这么想着,某种无奈之上的情绪又在袭击鼻腔。接下这个任务的人,并不是现在的瓦尔哈拉的全部队员。
想起永远脱队的两名队员,就会陷入混乱状态——这是阿伦德尔近期的情况。
刚加入队伍的时候,他几乎算是个无神论者,自由并且独立。他带着对自己能力的信任和遗都赠送的谨慎被传送到无名之城,然后就折服于“第五季”的光辉和神圣,女神保佑,他随后又在高等精灵面前打碎自己之前所有的骄傲,回到童年时期被歧视折磨的那副样子。但那时又出现了温柔的画面:队友的无条件信任,高等精灵捉摸不定的关心,以及两名同是半精灵的少女的陪伴和支持。自信与自卑,这些要素构成了第一次的混乱。他觉得自己要克服这些混乱了,因为在瓦尔哈拉小队内,他对自己的信任又一次逐步构建起来。然而温柔画面易碎易消散,最该被好好保护的少女成了法师塔的猎物。回眸时刻录在脑内的尖叫和血光至今仍然在阿伦德尔的梦境中盘旋,把他脑海里的正面的积极的部分击得粉碎。这种情况在瑞贝利安加入之后变得更加严重。对死的恐惧和对队友之死的自责,这是第二次混乱。
若不是有奥列格和suzette的存在,他可能要混乱到崩溃了吧。
此时奥列格推着他往前走的脚步停了。
“你要暂时脱队吗?辛苦啦!”奥列格无限有活力的对卡利亚说,而对方在瑞贝利安的“卡利亚叔叔再见”声里转过身,朝奥列格挥挥手。和他一起走下去的那名士兵本来低着头,突然想到了什么,朝着瓦尔哈拉的众人喊着:
“魔法!菲尔扎·裘德大人说瓦伦找到了魔法,他说这里有魔法——”
“魔法……”诸位冒险者几乎同时把玩起这个词来。
这种力量一直是库瑞比克世界居民所忌惮和追寻的,是天赋的产物,也是强大的代名词。这种力量只属于法师,或者暮刃,只要一出现就会被追捧和膜拜。瓦尔哈拉小队没有法师,但是他们有暮刃,而在那名不常说话的高等精灵身畔流动的就是魔法的力量。Suzette听了这话没什么表现,她注意到队员看过来的视线,也只是皱皱眉头不说话。在瑞贝利安闹起来吸引走队友的目光时,suzette轻轻吁了口气。
“接下来,继续探索吧”送走了卡利亚,奥列格第三次发出这种指令。现在在他们眼前的是三楼的六个房间,从左往右数,逐个编号,奥列格又转了一圈。
在楼梯左边的是一号房间,之前那些植物就往一号房间躲过去,所以冒险者们毫无分歧地选择往与之相对的六号房间跑。
推开古旧厚重的门,一阵灰尘让冒险者们忍不住打起喷嚏。这个房间积满灰尘,而灰尘掩盖下也不过是普通的储物间。并排的几个柜子,桌子,以及摆在桌子上的刀叉、停住不走的钟表之类的稀奇古怪的小玩意都一股脑儿地放在这里,阿伦德尔觉得如果自己有一个这样的小房间的话,也会懒得打扫任由它们招灰尘的。他觉得这座法师塔和想象里的法师塔不太一样,到现在为止那些堆到屋顶的魔法书,复杂的龙语手稿和魔法道具都没有出现,反而是厨房和储物间一个接一个。
此时瑞贝利安已经冲进房间里一个一个摸着房间里的东西。他完全不管灰尘,抓起几件桌子上好玩的东西就扔进口袋。受到他这番动作的影响,其余几名队员也走得更近,阿伦德尔打开柜子,想找一些书籍和笔迹,但是柜子里也摆着刀叉等物品。
“这位法师挺喜欢宴请宾客的,他积攒了这么多刀叉啊!”奥列格踮起脚看清了柜子里的东西,发出惊叹的声音。随后他做了让阿伦德尔吓了一跳的事情:侏儒收集了一大堆刀叉丢进包裹里,一边收集一边还在说“作为武器”。旁边的蓝也拉着川途走过来,他和队长不一样,他只收集小刀。
这种无聊的资源回收工作让瑞贝利安很快失去了兴趣,他在裤子上擦了擦手掌灰尘,环视一周,发现其他队员已经进入搜刮的扫尾阶段。他迫不及待地朝第五号房间冲去——
比起六号房间,五号房间显然更有价值。阿伦德尔走进去的时候,感觉自己之前的所有疲劳都是有价值的。这个房间似乎是书房,几个巨大的书柜上堆满了书籍,但是有一些已经散落出来,还有一些书被摊开扔在桌子上,好像被谁翻找过。但这些痕迹已经非常古老,翻开的书页上都满是灰尘。阿伦德尔靠近一本被摊开的书,弯下腰吹掉上面的灰尘,使纸张内容显露出来,发现上面都是龙语的笔记。可惜他不会龙语,所以他有些失落地放弃这些书,去看地上一本附带插图的书,女神保佑,那是用通用语写的。此时川途也靠近这本书,先是弯腰看,随后直接蹲下。
这本书的这一页画着悲荒之神萨玛菲。
“这是什么?”奥列格也注意到这本书,看清楚插图之后倒吸一口冷气。逝去的神祗总能让人想起过往的战斗和雄厚悲壮的史诗。但是他站起来之后,发现更加可怕的事情已经发生了——瑞贝利安没有在这间房里。
不管有多不喜欢,这名战士都是他的队员,奥列格脑子里已经出现了数百种可怕的影像,他身体颤抖了一下,冲了出去。
-----------
非常伤心



再次回到地城时,银隼的旧成员只剩迪赛鲁和奥诺二人,虽然在神明的指引下,同样损失惨重的秘风队与银隼合并为秘隼,不过冒险者这生死无常的生活依然让迪赛鲁嗟叹不已。奥诺成为了这只队伍的新队长,据她说这次他们是回到了银隼最初进入这个地城的地方。在弦月的指引下,本应该朝着左后的方向,然而其他人却开始吵吵闹闹不愿听从神的指引,作为牧师,这群人的言论实在刺耳,被神选召者却违背神的旨意,但想起上次冒险的伤亡率,迪赛鲁又什么也说不出来,最终,在大家投票后,还是决定跟随弦月的引导。
巨大的石球堵在去路之上,奥诺给大家讲着上次差点被这玩意砸死,而不知死活的吟游诗人突然不动声色的给石球来了一脚,看着颤巍巍地晃动的石球,迪赛鲁吓得赶紧找了些石头垫在下面,免得石球滚动起来出事。不过虽然石球看起来没有危险,但也完完全全挡住了弦月的指引,在队友们尝试了各种方法也没法通过后,队长提议走另外一边,虽然迪赛鲁对这种违背神意的行动老大不愿意,然而他也没有解决的办法,只能在心里嘟囔着怎么进了这样一个队伍磨磨蹭蹭的跟在队伍后面。
另一边的房间里似乎都是些古代物品,黑德爱尔各种侦测陷阱也没有任何发现,因为都是些没什么价值的东西,大家也就快步离开,来到一个有着各式精美器具的房间,迪赛鲁听前队长说过这个,上面有过鬼魂,他正想提醒队里的几个手欠的家伙,话才出口帕克就已经两眼放光的拿起俩瓶子,看他样子本来大概是想当战利品带走,听到迪赛鲁的提醒后,不但没放手,反而嘴里念念有词的召唤起幽灵来。大概是里面的幽灵已经被消灭了,这次什么也没发生。被帕克的行为气得不轻得迪赛鲁现在已经放弃了,有个什么都好奇的吟游诗人大概几条命都不够,迪赛鲁悄悄下定决心,等会一定要捏个治疗在手里,真有情况一定只给自己!
*WPS计字5042
*卡了一周的boss战……
*自从回家每天都在被gank……
*下一次川途回家
14.
它们跳舞,它们在月下旋转,它们的泪水流下,便是那溪的源泉。
--------------------------------------
“大家振作!顶住!保护叙泽特发动魔法!!”奥列格大喊,他清亮的声音像是浊水中的一道清流。
蓝的眼前还在一阵阵地发白。
火花在耳边爆裂炸响,植物摩擦的声音像是哭伤了的喉咙,人们在大喊,侏儒在尖叫。
他大脑里回荡着笑声和影子,思维仿佛呆滞,只知道一支支将自己手中的箭发射出去,把那些恼人的绿色生物钉死在墙壁上,光洁无缝的白色石墙被箭支扎得千疮百孔。
手边的箭用完了。
少年机械性地伸手向背后箭筒,想要去拿下一把,却摸了个空——
箭用光了。
而植物挣脱了箭支的禁锢向他扑来,被挣脱或腐蚀断裂的箭杆散落一地。
他向后跳跃,藤蔓抽打在他面前的地面上,留下一道被粘液腐蚀成焦黄的痕迹。另一枝藤蔓正待向已经躲闪不及的少年头上落下,一只手斜刺里伸出来将他拉到一边:“这里!”
男孩的手心是温软的,手指却比蓝不间断地放箭而导致脱力颤抖的手要有力得多。
藤蔓带着粘液擦着他的肩膀过去,斗篷上瞬间出现被烧灼的黑色印记,散发着刺鼻酸味的灰烬掉落之后露出下面棕色的皮衣和蓝色的皮肤。
他下意识地拔出腰间匕首,随时准备给这堆狂舞乱动的植物来上一刀。
而另一侧的高等精灵则是到了咒语吟唱的最后关头,她身周的火星已经凝聚成了火球,植物脚下的地面也开始发热泛红,绿色的恶魔们开始躁动,似乎感到了危险的临近,愈发狂乱地挥舞起枝条来,而叙泽特的声音也从开始的喃喃自语变成了高呼出声。
她的声音仿佛响彻塔上的天空,从那朱唇中吐出的字眼已经不是咒语,那是号令,是召唤,一瞬间这绝美的高等精灵仿佛有着引领天下的气势——
“天地疾风,地底不息之火,以吾之名,唤汝而来,呼之红莲,为吾之剑,于此燃尽世间一切不敬不净不静之徒,流星火陨!”
——一息间的静默。
而后,天空陨落。
火红的流星从虚空中诞生,裹挟着灼人的空气扑向粘滑的藤蔓,瞬间燃起的大火照亮了整个四层小厅,植物在火中发出难听的啸叫,它们根系所生长的地方变成了流动的火池,。
火焰之间仿佛有什么在咆哮嘶吼,绿色的枝条被灼成难看的焦黑色,一行人似乎听到了枝蔓间缠绕的号哭和尖叫,像是挣破了牢笼的斗兽向他们扑来,而后穿过他们的身体远去,离开这座塔,离开这个世界。
烈火燃过,大部分植物化作恶臭的灰烬,“漆黑之月”的碎片也掉落在地,整座塔都轻微的抖动起来,似乎是楼下的大门打开了。
“可以歇一下了么……?”看着植物留下的遗骸,阿伦德尔声音里似乎有点喘。
“先不要轻举妄动。”叙泽特脸色发白地站在那里,似乎在使用了这么一个高阶法术之后有些脱力,却也看不出什么不对的地方。
蓝则是尽快从四周搜罗回还可以使用的箭,以防还有什么出人意料的战斗。
安静的环境保持了不到一分钟,遗骸中就悉悉索索的有什么在响动,吓得几人一瞬间都做好了战斗准备。
然后一个黑色的……人形,只能称为人形的东西从里面站了起来。
人形甩了甩头,跺了跺脚,又抹了一把脸,破口大骂。
“妈的,老子要被烤熟了!”
听到熟悉声音的几人一瞬间放松了下来,瑞贝利安的声音从未让他们这样庆幸,然而几人脑子里同时抑制不住的还有一种“居然没把他烧死真可惜”的想法。
瑞贝利安狼狈不堪地从灰烬里爬出来,其他几人离得这一身恶臭的熊货远远的不提,再次做好了防御准备的一行人谨慎地收好碎片,准备撤退——他们已经不愿在这塔里多待一分钟。
“走吧。”阿伦德尔声音里带着深重的疲累,听起来并不是身体的累,而是失望和无力造成的沙哑。叙泽特和奥列格没有作声,算是默认了。
转身,白色的楼梯依然发着淡淡的光,和他们上来时如出一辙。
“你们……走不掉了。”
有人在他们背后这样说。
15.
他们向光芒奔跑,无论是真实或是伪装,那人守护这光芒的源头。
------------------------------------------
尚未燃尽的藤蔓开始缓慢地蠕动,掉落,露出那具原本惨惨然躺在其中的白骨。
然后那白骨在惊疑不定的几人面前站起,关节相撞喀喀作响,像是被一个拙劣的艺人指挥的劣质人偶,以一种被悬吊而起的诡异姿势歪歪斜斜地浮在那里,除此以外安静得和一具普通的白骨没有什么区别。
然后它站直了。
就像突然被电流击中一样,这白骨从诡异扭曲的姿态变成一种有自我意识的人类才可能做出的正立动作。
这还不是全部,它站直之后开始以一种奇异的频率抖动,或者说振动。一颗暗红的心脏随着振动渐渐诞生于它原本无生命的枯槁胸腔,被青色的血管围绕,却并不跳动——继而是肺,气管、肝脏,枯白色的骨上也凭空出现鲜红的肌肉、粉色的筋腱和脂肪,最后一层皮肤将这些全部包裹。
死而复生的男人睁开眼睛,全身肌肉依旧虬结,黑发依然像没修剪过的树朝着天空张牙舞爪,只是那双原本凌厉的瞳孔中已经完全浑浊,没有一丝生人的气息。
——真实的复生人。
对于复生人的传说蓝也早有耳闻,只是未曾想到会有一天与这种存在面对面地对峙。面前的菲尔扎·裘德从表面上看仍然是那个盛气凌人、手按在剑柄上扬言要杀掉他们的人,然而从本质上已经完全不同了——他甚至已经不能被称为“人”,只能被称为“生物”,或者更加差劲一点,“工具”。
“那是……什么东西……”阿伦德尔看着仿佛从腐烂状态回复的男人,震惊到表情连大脑的停滞都表现了出来。
然而那一路添乱到底的战士却不这么认为,他正跳着脚大喊,说的话是种奇怪的方言,蓝似乎在哪里听过然而还是听不太懂,似乎掺杂着“好帅”“帅爆了”一类的词语。
——帅爆了你也去当那具白骨好不好呀。
男人浑浊的眼珠开始左右转动,渐渐被红色的血丝充满。他活动了下脖子,嘴角以一种奇怪的弧度咧开,发出奇异而狂乱的笑声。
“多亏你们……”他笑着,声音与在塔下时的洪亮刺耳不同,是一种浑浊和阴沉,和他那死人的眼珠一样令人不适。
“多亏你们……打败了那些家伙,现在……”
他狂笑,鹅般的笑声在狭窄的塔内回荡,刺激着瓦尔哈拉众人已经备受摧残的神经,叙泽特已经皱着眉揉起了额角。
“……现在,这座塔已经归我所有了……!”
塔在男人的声音中震动,浑浊的人声里不知何时掺入了另一个尖厉恼人的音调,像是鹦鹉从喉管里挤出的声音。
阿伦德尔的手停在琴弦上,迟迟无法奏响破咒曲的第一个音:“这是……法术吗?”
他话音还未落,一本书从通往五楼的狭窄楼梯上飞下,书页在风中哗啦啦地响着,一具白骨——说是白骨似乎有些不确切,因为这白骨给人的感觉比裘德的那具有血有肉的身体还有生命力,然而它又确实是具货真价实的白骨——那具白骨继续用那鹦鹉般的音调叫喊:“正是因为那些讨厌的植物!才没法让我的力量渗透这里!”
“难道不是谁打败了这些鬼东西这塔归谁吗?”阿伦少年一脸不可思议,拿着乐器的动作几乎把曼陀铃砸出去,“本质上这塔已经是叙泽特的东西了吧?”
“你难道就是……所谓的死灵法师么!”蓝已经是本能反应一样地拉开弓,脑中转的却是过去听过的那些少得可怜的对于死灵法师的传言。
“你是死灵法师吗!”瑞贝利安抡起了那已经被植物腐蚀出了一块块黑色的大剑,看起来也是威风凛凛,然而接下来的话却立刻暴露了智商:“不过死灵法师是啥?”
白骨并不回答他们的话,只是发出刺耳的尖笑,和裘德毫无美感的鹅叫声一起在塔内回荡。
“你们真是帮了大忙了,年轻人!”
白骨无肉无皮的脸上本应该看不出表情,然而这一瞬间,所有的人都觉得它在笑。
“死亡的力量将灌注这里——!”
白骨带着它特有的尖厉笑声扑上了菲尔扎·裘德的身体,一瞬间令人不适的绿光猛地在众人眼前爆炸,书在污浊的光芒中升上半空,书页间仿佛飞驰而过的凄惨呼叫似乎在哪里听过,又好像不是应该在这活人的世界出现的声音。
“能……撤退么……。”
蓝清楚地听到自己吞咽唾液的声音,心脏的跳动冲击着少年的鼓膜,他听到自己的声音细如蚊鸣,手虽然本能地张弓搭箭,身体却在不自觉地发抖。
“我可不愿意背对着这种玩意。”
阿伦德尔似乎同样对这种东西没有好感,然而他握紧了手中的曼陀铃,破咒曲铿锵的旋律开始在他指间流淌。
这是少年生命中,第一个与非生命针锋相对的时刻。
他并不知道,此生中是否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这种经历,然而他唯一知道的,是现在他必须直面这他未知的恐惧,即使这恐惧将会令他再也没有第二次三次的机会去面对。
16.
孤灯一盏曳于晚风,璀璨花树燃尽此夜。
--------------------------------------------------
破咒曲似乎并没有起到它应该起到的作用。这个家伙——暂且称它为“白骨裘德”——白骨裘德所使用的法术似乎与几人熟知的那些法师所用的并不完全相似,所以破咒曲无法通过影响它的精神而打断法术。
奥列格清亮舒缓的安魂曲似乎对这东西反倒是起了作用,它发动那些魔法的速度明显变慢了,还有机会让川途从不知哪个角落出来对着它乒乒乓乓一顿刺砍。
蓝稳定了下自己的手,瞄准这一脸狞笑的法师那颗惹眼的脑袋放出一箭。
没有射偏,箭尾在空气中划出完美的轨迹,然后……
被偏转了。
铁质的箭支掉在地上,叮的一声。
完全愣住的少年表示无法理解目前发生了什么,他看看自己的手和弓,又看了眼那支落在远处的箭,脚似乎被钉在地上无法动弹,而泛着恶心绿色的魔法脉冲像是要报复他的射击一样朝他的喉咙袭来。
……这就是命?
这也许也是惩罚吧,惩罚自己的无能,惩罚自己没能救下那两个无辜的女孩。
“你找死呀!”
男孩的声音在他耳边叫喊,像是平地里炸响了一个滚雷。
天旋地转间他的脸已经被按在地上——说是按其实并不准确,他是由于背后的人将他死死压在地上才无法起身,然而这种压力也仅仅存在了一瞬间,川途的短暂的惊叫和他背后的力道一同消失,少年一手撑地翻身而起,看到川途靠在墙边,黑色的血正从他支撑在地上的那只胳膊下蜿蜒而出,像条恶毒的蛇。
“你谁都保护不了,更别说什么可笑的报仇,你这小杂种……”
半蛇人丑陋的脸又出现在少年眼前,它手中的刀横在少年脖子上,被磨得极薄的刀刃将少年蓝色的皮肤切割出一道黑色的血痕,那张吐着信子的大嘴几乎占据了脸上一半的位置,它血红的小眼睛盯着少年灰色的瞳孔,用话语嘲笑着少年的血统和决意。
“为你那没用的父亲报仇?蛇鼠……”
它的话说了一半,说不下去了。
灰黑色的脑袋就这样在少年面前掉了下去,腥臭的血溅了蓝一脸。
“你没事吧?去我家洗个脸么?”
金发的少年攀着一根绳子挂在他面前,左手匕首上的血污还在滴落。
那是半卓尔与换生灵第一次的相见,之后他们的生命仿佛被相互捆绑,不再分离。
蓝的喉咙干渴,并不是水分不足,只是他不知这一次是不是真的会面临他一直不敢想像的东西。
男孩的手臂终于没了力气,顺着白墙滑下,背后的伤口正在缓缓地腐烂,看起来再持续个把钟头就能到见骨的地步。少年三步并作两步将他揽住放在墙边。
手上似乎有什么滑腻的液体,他很清楚那是川途背后的血。
川途睁眼,虽然仍然蹙着眉头,靛蓝的眸子里却是平静无波。
“白骨身边……有防护层,我的飞刀无法进入,”他说话有点吃力,似乎是由于会扯到背后的伤口,“他会用白骨做的短剑和奇怪的火焰……防御,那种火焰,让我……恐惧。”
“你别动了。”蓝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他不敢看川途的眼睛,虽然嘴里说着恐惧这个词,那双眼睛里面却没有丝毫动摇和恐惧,男孩此时拥有的沉静已经不仅是超越了他孩子般的外表,更是超越了他的年龄——一个二十岁的大男孩应该是拥有无尽的激情,而不是这种老者一样有些沉闷无情的冷静。
“计算……。”川途重新闭上眼睛,似乎在忍耐伤口的疼痛。
再次拿起弓的少年灰色的眼睛中仿佛点燃了火,一支支铁箭以奇异的角度和他自己都无法想象的力道突破那道原本让他无计可施的可恶屏障,铁质箭头嵌进肉里的声音在他听来是最悦耳的音乐,已经超过了队内两位吟游诗人的歌声和演奏。
“你们还挺有本事的啊!”仍然是双重声,菲尔扎·裘德的嘴虽然在动,这声音却仿佛直接传进了在场的所有人脑中。
黑色的火焰原本仅仅围绕着书本和男人旋转,如今却分为几道向着他们扑来,如同乌鸦的羽翼,带着恐惧——“死”的恐惧。
发现破咒曲无效的阿伦德尔果断放弃,开始演奏不知什么时候学会的军乐,这曲子被这音乐天赋相当优秀的半精灵改编后提神效果出奇的好,甚至超过了那种“提振士气”的传统音乐。
箭再次发射一空。
——但是这次已经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少年这样告诉自己,使用起自己并不擅长的战斗方式,左手紧握川途的匕首,右手拿着自己的短刀,开始向着白骨裘德高速奔跑。另一边的瑞贝利安和叙泽特早已和这法师战成一团,瑞贝利安手中的大剑挥舞得如同旋风,而高傲的精灵则是在战士的剑和旁边的地面上来回移动,手中长剑上电光闪动,不时带起一泼黑色的血花。
他们都是不知何为恐惧的人。
抑或说,在他们的世界里,恐惧这个词原本就毫无意义。
他高高跃起,怒吼出声,面具被火焰和他自身带起的气流掀掉,白色的犬齿大概是第一次暴露在嘴唇之外,两把武器交互地或削或砍,一次次刺在这已经不能被称为人类的人身上,鲜血喷溅在他的脸上,一如他十六岁的那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