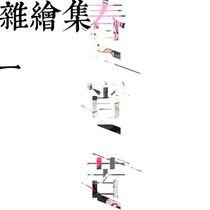阿比斯对于自己的童年的记忆,或许在别人眼里只有悲惨两个字吧。
他的记忆里父母永远都是那副痴狂到极致的模样,因为信仰着不存在的东西而什么都看不见,听不见,发霉的墙纸也好还是爬满了老鼠的厨房也好,他们都熟视无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那本书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在自己的家里呢,阿比斯自己或许也不记得,但是他似乎还保留着躺在了婴儿摇篮里看着空无衣物发黄的天花板的记忆,那个时候他便怎么哭泣都无法换来父母的注视,直到最后他停止了哭泣。
漆黑的衣柜里是他藏着孩童秘密的地方,里面有着他还算柔软的毛毯——尽管是线头已经开始脱落、毛绒开始结团的布料,也还有着短短的只能勉强点几次的蜡烛,还有一包受潮了只剩下两根火柴的火柴盒。那是他的全部记忆所在。
阿比斯还有一枚小小的眼镜,是三角形的,也只有一边它在太阳底下能当做火柴,把枯枝燃烧,烧出缕缕青烟,它也能隔着阿比斯的眼睛,当做了放大镜,把人的心放大,看到他们心里的愿望、欲望。阿比斯戴着眼镜站在镜子前,他怎么看都看不见自己,他想如果这个世界上会有和自己一样的人存在的话,会在自己的心里看到什么呢?
“——,我们终究会有一天会在主的身边获得新生,成为真正的幸福的一家人。”
——、是阿比斯曾经的名字,他看着母亲一张一合的嘴,却记不起这几个字的音节是如何发音的,那是他最后一天作为那个名字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然后是他看不见的味道从那个家里唯一仅剩完好的铁盆里冒出来,他被母亲抱在怀里,但是那不是他所了解的母亲的怀抱,不应该是如此紧缚的,不应该是如此恐惧的,终于在母亲的眼睛闭上前,他挣脱了这个怀抱逃离了这个充满不安味道的房间。
漆黑的衣柜,下午的阳光从衣柜门缝里透进来,就像是一道白色的划痕,他伸手去摸只能摸到粗糙的木质触感。屋子里是前所未有的安静,阿比斯张了张嘴,喊出了第一声母亲,第一声父亲,可是屋子里安静得很,阿比斯看到了底下那本书如同恶魔一般爬上了二楼的楼梯,它走过了每一房间,钻进每一个角落,弥漫在空气的每一个间隙中。它抓住了阿比斯。
他想,母亲,我不想去主的身边,母亲,我不想获得新生,母亲,我不想和母亲成为真正的幸福的一家人。
阿比斯有的时候会分不清记忆,他好像记得很多人来过自己家里做客,但是他们最后都没有离开,但是他好像也记得自己家里从来没有来过客人,只有成夜成日跪在壁炉前的父母。他在衣柜里睡了一觉,屋子里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偌大的屋子只剩下他了,他可以在楼梯上跑来跑去,可以在床垫上蹦蹦跳,虽然那张老旧的床垫永远都会有弹簧膈着他的屁股。
他趴在窗边看着走过的小孩子一天天变成自己不认识的人,然后跑到了镜子前,他比着自己的身高在镜子框上用火柴的木梗抵着头轻轻划了一下,他看着重重叠叠的划痕,想自己什么时候才可以长高呢?最后他偷偷地在那些重叠的划痕上面一点点的位置轻轻又划了一下,才满意地扔掉了木梗。
就像刚刚说的一样,书是恶魔,它抓住了阿比斯,阿比斯只能被它牵着乱跑,但是更多时候他会更想睡一觉,醒来的时候就能回到自己家里了。阿比斯捡起那本书抱在怀里,跨过了来家里做客却不知道为什么躺下了的客人,他想,客人们可真是喜欢自己家啊,连睡觉都要来自己家里睡吗。
书、不是把客人们弄睡着的罪魁祸首,客人们的心才是。
阿比斯这是从一开始就看得到的,他看得到愿望,看得到客人们的笑容,看得到父母…——哪怕他脱多少次眼镜都一样,他从一开始就看得到,父母称之为恩赐,阿比斯愿意称之为:
“诅咒。”
“诅咒?你不是什么诅咒,人类的丑恶才是真正害死他们的东西,诅咒这种东西从一开始不也是由人类的嫉妒心、欲望而生,和你没关系。”
那是最后一个走进阿比斯家里客人说的话,他石榴一样的眼睛只剩下一只,明明是浑身黑色的衣服,却总是穿着一件白色的长长外套,戴着阿比斯也有的眼镜,但是他有两个镜片!真让人羡慕!阿比斯也想要两个镜片的眼镜,因为他看不见这个客人的心,他想说不定两个镜片,两个眼睛一起看就能看到了,两个镜片!真羡慕!
“克拉伦斯,我是克拉伦斯·古斯塔夫。”
阿比斯蹲在地上捡那些七彩的糖豆,那是苦苦但是甜甜的味道,他想起了很久很久以前,久到他忘记了又记起来又忘记的程度,邻居家的那个穿着粉红色裙子的女孩子,总是会偷偷塞一个黑色的面包给他,那就是记忆的味道,苦涩的甜。
“没有了。”
阿比斯蹲在黑色的皮鞋旁边捡起最后一颗糖豆,抬起头的时候他才看到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出了家门,长得快要可以把他淹没了一样的黄绿色荒草,已经不见了的秋千,树枝上残留的绳子都被时间湮灭。就连向前一步,阿比斯也不知道会走向哪里,会掉进哪里。他只能后退,想要退回到那个漆黑的衣柜里,想要找回那条脱线的毯子,想要回到那个粉红色裙子的姐姐身边。
“我可以再给你买。”
男人开口了,他看了一眼阿比斯踩在褐色泥土里的脚丫。
“——还有鞋子。”
“两包。”
毫不客气的小孩子,还会讨价还价。阿比斯举着三个手指,克拉伦斯也没有拆穿他,只是说了一句嗯两包。
克拉伦斯带着阿比斯坐在夕阳的泰晤士河边,大腿上放着用两包巧克力豆两个巧克力雪糕和一对小皮鞋换回来的书本。夕阳像撒了一层金片在河上,金灿灿的,建筑行人汽车街道都在一片金色中,他们也当然在这片金色中。
“喂,你记得多少吗,你的记忆之类的。”
阿比斯吧唧了两下嘴,舔掉化掉开始淌下来的巧克力雪糕,那是一个快要他的脸高的甜筒,两个饼干棒被他拿在手像是勺子一样一下一下挑着雪糕吃,克拉伦斯伸手扶住不住向前歪、拿不住甜筒小孩的手。
“——你别掉了,掉了我不给你买新的。”
“嗯——”
阿比斯点点头,他还是继续用那根饼干棒挑着雪糕。克拉伦斯微不可见地叹了口气,终于放弃了似地松开了手。
“刚刚问你的,你还记得吗。”
阿比斯舔着饼干棒上的雪糕嗯了很长一段时间,舔着的饼干棒都被口水被弄得潮潮软软的。
“不记得了!”
那可是真话,因为那个甜筒才是阿比斯真正的记忆开始、——至少他本人就是这样认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