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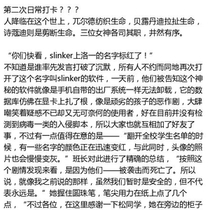



(字数5136)
神从远古而来,撕破了虚空,创造了世界,孕育了生命。
仁慈的神啊,它将特殊的财富赐予世间万物同时划分了三六九等,受到了所有生物的崇敬与朝拜。
位于中层的生物们,他们享受着生活,没有获得最好的但是他们现在所拥有的足够让他们领略到人生的美好。
他们感恩着神,并且充满狂热地信仰者它。
丰收的果实压弯了树枝,不远处的几个箩筐里也早已经堆满,在树荫下歇息的人们扇着风聊着天,嘴上说着对这么多果实脸上却满是笑容。面包房里的蛋糕刚刚出炉,街上便满是馥郁甜蜜的香气,儿童们趴着橱窗前一边对着可口的点心流口水一边央求着父母,而他们的父母也会笑着说些无伤大雅的抱怨话然后掏出钱包满足孩子的心愿。
富饶与幸福是他们的生活常态,空气里弥漫着只有乌托邦才存在的欢声笑语。
居于上层的生物们,他们俯瞰着世界,尽享玫瑰色的人生。甚至毫不夸张地说,从他们诞生之初,他们便拥有了一切。
金钱与地位,权利与能力。他们都有。
他们住在金碧辉煌的宫殿中,镶满钻石的座椅不过是他们众多家居中不起眼的一个;品尝着山珍与海味,手边是只有他们才能够享有的佳酿;出行时大批家臣前呼后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将一些稀有魔兽作为拉着装饰艳丽的车的工具也是十分普遍。
他们无忧无虑。唯一需要烦恼的,也不过是如何排除异己,将自己推上更高的宝座,获取更加广阔的资源,接受更多人的仰视。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贵族。
生来便高于众生,仅仅低于创世神的,贵族。
处于下层的生物们,他们遭受着最不公平的事情。他们身处地狱,努力地向着上方的光明伸出手也不过是将自己从最低层拉到上一层,在绝望过后堕入更深的黑暗之中。
这里空无一物,但却充斥着贫穷、奴役,苦难以及毁灭。
为了在这个被填塞了无限畸形恶意的世界中生存,他们挣扎着,苟且偷生着。
他们在垃圾堆里翻找着能够下咽的食物,即使已经发霉变馊;他们抱着膝盖蜷缩在桥洞底下,希望能够顺利度过寒冷的日子;贵族将他们视作被踩在脚底肆意践踏的蝼蚁,平民对他们视而不见甚至像躲避瘟疫一样地远离他们。
于是他们开始远离众人,待在阴暗的角落里独自发霉。
阿扎赛尔星,这是一个属于恶魔的星球。
恶魔这个种族,向来是都靠实力说话,因此「弱肉强食」这种丛林法则也就成为了这个星球最基本的生存之道。
当然平民无法打败贵族。
贵族之所以为贵族,多少是和血统有关的。红龙与其带领的七位君主的直系后裔和支脉旁系,凡是沾亲带故的基本无一例外的成为了贵族,在他们的血脉里流淌着来自祖先的绝对力量,不容侵犯。
贵族们有着各自的领地,领地的大小是按照强弱来划分。但是不管战斗力的差距,他们对胜利的野心是同样的。他们总是互相猜忌,然后纷纷拔出自己的武器,不断建立战场开始武装割据。
一场战争终有胜负,成王败寇,胜者为王。输者即使再不甘心也只能归入赢家的麾下,祈祷着期待着那位赢家的下一场失败。
深渊恶魔,一个远离战争的种族。
他们是在地狱深处和扭曲夹缝中诞生的魔物。
生于黑暗,活于黑暗。因此在整个城市——包括大大小小的领地——外的那片阴暗的森林就成了他们生存的不二去处。
尽管常年隐居但依然有其他的贵族对他们的实力与地位有所忌惮,终于在一个雷电交加的深夜,七恶魔的直系后裔们联合了血族以及他们的旁系们将深渊恶魔们一网打尽。
象是群居动物,但是再多的象也敌不过几个联合起来的鬓狗部落,更何况带领他们是狮子。
在破晓的时候,持续了一整晚的厮杀声消失了,而森林深处的哥特式建筑沾满了血。
深渊恶魔,族灭。
直到正午,阳光照进了这个被黑暗笼罩的区域,一个小孩子从深渊恶魔们生活的宫殿中出来。
他满手血迹,再抬头的时候看见了比以前更加灿烂的阳光。
然后他面无表情地朝森林的边缘走去。
伊恩第一次见到塔纳托斯是在他七岁的时候。
当时他刚买好一堆生活用品准备回家,走过转角就被一个小孩撞上。低头看时才发现小孩长得很漂亮,红色的瞳孔中掺杂着一些紫色,给人说不清的魅惑感。
看起来就不是什么好货。伊恩面无表情地绕过他——然后就被拉住了衣角。
再低头发现对方一副快哭出来的样子,小孩指指后面追来的两个彪形大汉,表情楚楚可怜,然后眼泪就吧嗒吧嗒往下掉。
年幼的伊恩当时并没有了解到世间的险恶。他把东西塞到小孩怀里后往角落里推,散步一样地路过那两个男人,如他所料地被揪住问有没有看到一个魅魔。
原来是魅魔啊,我说怎么长这么好看。伊恩心里这么想着然后指了指右边。“那儿。”
目送那两个被骗的离开,伊恩转头却发现那个小孩不见了踪影。思考了一下就翻上墙头,站在上面找小孩的身影,再跳下墙头的时候已经站在了小孩的面前。
小孩似乎是被突然出现的人给吓了一跳,手里的东西掉了一地。伊恩将地上的东西捡起来单手抱在怀里,另一只手揪着小孩的衣领往自己家的方向拖。
伊恩的家里空荡荡的,除了一张床一套桌椅就是堆在墙角的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反正这里就他一个人住。
伊恩将东西放到墙角堆好,双手抱胸坐在椅子上,微微抬头看着自觉坐到桌子上还来回晃着腿的小孩。
“你叫什么名字?”一片沉默中,伊恩首先开口。
小孩歪歪脑袋。没有说话。
伊恩想了一下,小心翼翼地开口,生怕一不小心就触到了对方的雷点:“你……是不是不会说话?”
小孩看看他,还是不说话。
伊恩叹了口气。得,这下看来是捡了个哑巴回家。站起身,顺手揉揉面前那看起来发质还不错的脑袋,抬头看着灰突突的天花板,说道:“既然你不出声,那我就叫你塔纳吧。塔纳托斯。”
再低头时就对上一双闪闪发亮的红瞳,小孩——现在该叫塔纳托斯了——用力点点头,脸上灿烂的笑容让伊恩想到了偶尔才会见到太阳,还是亮度最高的那种。
当伊恩第五天醒来看见塔纳托斯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小孩是打算长期定居在这里了。伊恩有些发愁地挠挠头,原本的鸡窝头变得更乱。
看来要多接些委托了不然养不活两个人。还有要不要给小孩子多买点吃的呢……伊恩盘腿坐在床上沉思,直到感觉有人在拉自己的头发才想起来都已经到吃午饭的时间了。
伊恩抬头直直地对上塔纳托斯的红瞳,神情严肃:“塔纳,天下没有白吃的晚餐——午餐也是,既然我都提供住处给你了,那么你也要付出相应的劳动力。”
塔纳托斯歪歪头,不懂伊恩在说什么,眸子里满是疑惑。
“那么——”伊恩指向厨房,“我们的午餐就拜托你来做了,用来支付你住在我这里的费用。”
塔纳托斯眨眨眼,点点头,走向那个自从伊恩住进来就没怎么用过的厨房。
伊恩再次躺回床上,翘起二郎腿,盯着天花板发呆,耳朵边是久违的从厨房里传来的乒乒乓乓声。人生真美——
“咚!” “咔嚓!” “咣!”
还没感叹完人生的美好就各种有奇怪的声音不断发出,伊恩听得心惊肉跳。
过了好一会儿终于消停了,伊恩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听见了一声惊天巨响,立刻从床上爬起来冲到厨房门口。
白色的墙壁已经变黑了,厨房用具被扔得到处都是,锅子里的是一团黑色的不明物体,而罪魁祸首站在狼藉现场的正中央,睁着一双大眼睛无辜地看着他。
是你让我做饭但是我做不好我也没办法嘛。伊恩感觉塔纳托斯的脸上就写着这一行字。
“……”伊恩一时语塞,只能认命地开始收拾残局。
厨房的爆炸导致午饭时间的推迟,等到两个人正式吃上饭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还是伊恩重新外出去买的。
吃饭的时候伊恩把自己碗里的肉时不时地夹到塔纳托斯碗里,嘴里念叨着“小孩子要多吃肉吃菜才能长得高”之类的。
塔纳托斯一言不发,将伊恩给的肉一块不落的统统消灭掉后擦擦油腻的嘴,突然开口说了第一句话,不过是两个字两个字往外蹦,语调也有点奇怪:“谢谢、款待。”
伊恩还没从“塔纳托斯会说话”这一个惊人的事实中回过神,就被对方的下一句话震在原地。
塔纳托斯:“对了,我、七岁、来着。”
伊恩:“……”把我刚刚给你肉还回来!!!
一起生活久了,伊恩在做些什么塔纳托斯也很清楚。
于是八岁那年,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傍晚,准备出门的伊恩被人拉住了衣角。伊恩当然知道塔纳托斯在想什么,看那像在讨骨头的小狗一样的眼神就知道了。
伊恩拒绝:“不行,这个是工作,不能带别人。”
塔纳托斯也没说什么,就继续盯着伊恩看,偶尔眨眨眼带出点泪花,轻晃伊恩的衣角,一副泫然欲泣的样子,浑身上下都在传达“你不带我去我就哭给你看”的意思。
伊恩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好少年不能就这样轻易屈服于对方。他将小孩的手指掰开后刚踏出半步就又被拉了回来,低头就看见塔纳托斯用比刚刚更可怜的眼神看着他。
你以为这样我就会听你的吗?你以为我会吃这套吗?伊恩在心中不屑地想着,然后牵起了塔纳托斯比他小一号的左手,把雨伞塞给塔纳托斯。
是的,我吃这套。伊恩有些绝望地想着。该说不愧是魅魔吗?在引诱人这方面真有一套啊。
伊恩一边撑伞,一边将自己意志不坚定的锅扔给了塔纳托斯。
被包裹在巨大雨幕中的夜晚尤其适合做杀人掠货这类事情。
按照委托人提供的地址来到一座宫殿前,伊恩看着眼前的华美建筑摇头叹息:“真是可惜了这么好看的房子了啊。”
塔纳托斯不解。
伊恩解释道:“你想啊,一栋建筑的价值在于有人使用有人观赏吧。这宫殿的主人过会儿就要死了,没有人想到回收它,不然就是把宫殿推了重新再造。”
塔纳托斯也说什么,只是点点头。
“好了!”伊恩伸个懒腰,缓缓拔出别在侧腰的刀。“开始干活吧。”
伊恩将刀插进目标人物的心脏后慢慢拔出,看没有任何血流出才满意地笑了起来。
一直没吭声的塔纳托斯终于忍不住开口:“就不能、一刀、砍头、吗?这样、好、麻烦。”
“那样太血腥了,对你影响不好。”伊恩想都不想直接反驳,然后才反应过来。“你终于又说话了?”
塔纳托斯没理对方的错误重点:“可是、你、带我、来这、的时候,就、已经、对我、影响、不好、了。”
伊恩:“……”不是你要来的吗!
夏天的时候伊恩习惯去河边洗澡。
在森林里的那条河流是伊恩发现的,平时也没什么人伊恩于是很放心大胆地把那里当做天然浴场。也同样把塔纳托斯带去了那里。
河水清澈得能倒映出人影,在阳光下波光粼粼,河底随意铺排的鹅卵石很光滑,水草顺着河水流向在晃动,偶尔有几条小鱼飞速游过。
伊恩将手放到水里乱搅一通然后漾起一道道波纹。他转头对着不远处因为第一次来所以好奇地四处张望的塔纳托斯喊道:“塔纳快过来!水很凉快的!”
塔纳托斯转过头,脸上还有浅浅的兴奋的红晕,他点点头,然后朝伊恩这里跑来。
“噗通”一声,伊恩很快就脱光了衣服跳进河里,水花溅了岸上人一身。还没来得及将衣服都脱下的塔纳托斯翻了个白眼,别过脸继续手里的动作,也不理水里那人的道歉。
塔纳托斯动作也很利落,三两下就脱光进了河里,然后就背对着伊恩开始洗澡。
“塔纳……”伊恩转过头似乎是想和塔纳托斯说些什么,刚转过头就发现了对方背上的印记。
印记很深,似乎是烧红的铁烙上去的,至于花纹……
伊恩想起来这个花纹是什么了。他将洗到一半的塔纳托斯从河里拉出来,不顾自己就先给对方套上衣服,末了还紧张地环顾四周,好像是在防备什么。
塔纳托斯一头雾水。他在伊恩穿好衣服才开口:“刚刚,怎么了吗?”
伊恩无奈地一口气,他就知道这家伙什么都不知道。
他警惕地看看四周,然后压低声音:“那个啊,你在遇到我之前是奴隶吧?”
“……是的,你看不起奴隶?”不同于平时的轻快,塔纳托斯的声音难得有些低沉,还有些难过。
“不是啊。这个花纹是奴隶的标志,如果在这种地方——”伊恩比划了一个范围,“被发现了的话,是会被立刻抓回去的。”
“……”
“所以啊,你要注意点啊。虽然我很厉害,但是人多了我也不一定打得过啊。”伊恩有些苦恼地抓抓头发。
“……嗯。”塔纳托斯几不可闻地应了一声。
“好了好了。回去吧,反正现在没事。以后注意点,我也会帮你注意点的!”伊恩拍拍对方的肩后率先往前走,没有听见还待在原地的塔纳托斯说的话。
“我来教你写字吧!”伊恩拿着不知道从哪里翻出来的写字本和笔对塔纳托斯说道。
“啊……?”塔纳托斯有些懵。这个人竟然会写字?
“别看我这样,我可是认识很多字啊,日常什么的肯定没问题的。”伊恩自顾自地搬了两张椅子——其中一张是在塔纳托斯来后新买的——到桌子边,坐下后拍拍另一个朝塔纳托斯招呼。“快过来!”
塔纳托斯依言走去坐下,然后伊恩就开始了自己的教学。
“我啊,以前被人收养过一段时间。”伊恩撑着下巴看着认真写字的塔纳托斯突然说道。
塔纳托斯有些猝不及防,笔顿了一下,然后拖长音回到:“诶——”
“大概是我五岁的时候吧,家族被灭门。但是我被我父亲藏了起来,那个地方好像还是父亲自己弄的,也没什么人知道。反正就只有我一个人活下来了。”伊恩低头看着手里的笔出神,“说实话,我不太恨杀了我族人的人,可能还有点感谢他们也说不定?因为直到他们死了之后我才能光明正大地出现在这里,也没有会对我指指点点,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而不是局限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他抬起头直视塔纳托斯的红色瞳孔,他在对方的眼睛看见了自己,面无表情但却有着解脱了的快感。一字一顿地说道:“我现在很自由。”
塔纳托斯放下笔,开口:“那就继续自由下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