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论要求:随意
——————————————
温室
普拉尔用滴管小心地将营养液滴入一排试管。试管里,是嫩绿色的橡胶草幼苗,在恒温恒湿的培育箱里,长得整齐划一。他记录下数据:温度、湿度、生长刻度。
完成之后,他走到旁边的温室。这里的橡胶草已经移栽到特制的营养土里,植株挺拔,叶片舒展,比传统土地里生长的苗株显得更加规整。
这里是第七区农业科研站。几个月前,还有穿着制服的人来参观,拍着他的肩膀说,这项高产橡胶草的研究,是为前线后勤供给的重要保障。普拉尔当时只是点点头。他知道自己在做一件正确的事。
外面的世界不太平,他是知道的。但在混凝土和强化玻璃构成的科研站里,他能听到的,只有循环系统低沉的嗡嗡声。
————————————
戴维是被征调的。通知下得急,他只能匆匆收拾东西。
“我得走了,”戴维看着普拉尔,脸上有些无奈,“去农场。这里……你多保重。”
普拉尔“嗯”了一声。他想说点什么,最后只是憋出一句,“你也保重。”
戴维笑了笑,没再说什么,转身走了。气密门在他身后合上,发出轻微的嘶声。
普拉尔站在原地,过了一会儿,才重新拿起记录本。他心想,外面怎么样,是外面的事。他只要管好这些橡胶草,做好自己的研究,其他的,跟他没什么关系。
——————————————
但事情还是一件件的发生了。
先是他的助手被调走了,说是去了一个战地急救培训,那边更缺人。普拉尔没说什么,一个人做两个人的活,只是每天在温室里待的时间更长了。
接着,是进口的营养液断供了。仓库的人送来一批本地合成的替代品,效果差了很多。橡胶草的叶片不再像以前那样油亮,生长速度也有些慢了。普拉尔试着调整光照周期,但效果有限。他看着那些叶片,心里有些烦躁,但更多的是无奈。他告诉自己,克服困难,做好眼前的事。
真正的麻烦来自冬天。站里接到了能源管制的通知,他们这些非核心研究项目被划为次级保障,夜间的供暖被切断了。
第一夜温度骤降,普拉尔几乎没睡。温室里的寒气透过衣服渗进来。他担心幼苗受冻,找来了几个旧式的电热管,勉强接在应急电源上。电热管发出暗红色的光,带来一些暖意,但也让空气变得干燥。他守在旁边,看着温度计上艰难爬升的刻度。
他不知道应急电源能支撑多久,但他没有别的选择。
白天,还有短暂的日照。夜里,就靠着这几根电热管勉强维持。他眼圈总是黑的,但他心里憋着一股劲,仿佛只要还能维持一天,他的研究就有价值。况且,外面就算炮火连天,也打不到他的科研站里来。他是这么相信的。
他偶尔会收到家里的信。内容越来越简单。最近的一次只是说,“我们还好,别担心。”
——————————
关闭的通知来得毫无预兆。
那天下午,站里的负责人来找他,递给他一份文件。没有解释,没有缓冲,只是一纸冷冰冰的通知:因战略形势变化,科研站即日起无限期关闭。
负责人拍了拍他的肩膀,叹了口气,也走了。
普拉尔拿着那张纸,在桌子前坐了很久。然后,他站起身,走进温室。
供暖供电已经关闭两天了。温室里的温度早已和外面一样低,呵出的气凝成白雾,久久不散。那些他精心照料的橡胶草,失去了恒温环境的庇护,正在不可逆转地走向死亡。最先表现出迹象的是最娇嫩的顶芽和新生叶片,它们已经发黑、腐烂。原本挺拔的植株支撑不住,开始东倒西歪地伏在枯萎的藤蔓上。大部分老叶也卷曲起来,边缘呈现出被冻伤后的黑褐色。他伸手摸了摸土壤,冰冷的,僵硬的,和那些植株一样,失去了所有活力。
他走到电热管旁,金属外壳早已冰凉。
那天晚上,他收到了一封信。是家里发来的。信很短,告诉他,老家那边局势恶化,城里进行了疏散,他们跟着车队去了西边的安置点,让他自己保重。
信纸从他指间滑落,飘到地上。
他突然明白了。
战争不需要真的打到你的门口。它只需要让你在乎的东西在你眼前慢慢死去,再用远方亲人的流离失所告诉你无处可逃。它一步步地逼近,压缩你的空间,摧毁你的凭依,这个过程,和你的个人意愿毫无关系。
他以为自己在为一个有价值的未来努力,其实他只是在一个即将被淹没的孤岛上,小心翼翼地堆着沙堡。
他回到冰冷的温室里站了一夜。
几天后的清晨,他回到科研站外。主建筑的门紧闭着,温室的观察窗后面,是一片死寂的、冻毙的灰褐色。
他穿着一身略显宽大的粗布军装,抱着钢盔。他的左臂上,套着一个崭新的白色臂章,上面印着一个鲜红的十字。
他拉紧了肩上的背带,沉默地转过身,走向远处那片扬着尘土的广场。那里,几辆卡车正发动着引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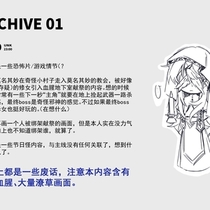
作者:江橼
评论:随意
这是一个发生在二十多年前的故事,年夜饭上吃过这么多瓜,自家亲戚的瓜少有。
就比如说这个,在辈份上属于我爷爷奶奶的两位的巨瓜。
且说,当年的爷爷——接下来请称呼他为J警官——是一名威风凛凛的刑警,具体啥档次不清楚,只知道当年出事的时候正在查一个跟地皮有关的大案。奶奶——又称W女士——当年刚从部队转业,在户籍口找了个容易给人行便利的岗位混资历。
很正常的配置,很符合俺家传统。
J警官手上的案子是市区重案,那时候各地都在埋头搞发展,上头要指标,下头的人就只能出歪招,这不就歪出事儿了。
一块要建商场的地给批了住宅,两头都拿了钱,中间商却失踪了,国土局的局长差点在办公室里悬梁自尽,最后因为没房梁老实被抓。但任凭审问,都问不出一点儿消息。
就在J警官快把市区所有地痞流氓都抓干净的时候,事故发生了。
W女士下班后,从单位走到车上的功夫,一辆桑塔纳飞速冲过,将W女士撞飞,血溅当场。
人群惊呼,刚有车没几年的老百姓哪见过这阵仗,红的白的撒一地,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但那时候的救护车跑的还没J警官的拖鞋快,赶到现场后,同医护人员把老婆抬上车斗,一脚油门直冲医院。
进急诊室,J警官签了所有能签的字,然后让同事看着,自己冲回局里。
年轻的汪老板那时候还叫汪狗,不过是某个大人物手下混的比较得脸的小弟。他的老大其实没有参与过地皮案,汪狗被抓到这里的原因,纯粹是他倒霉。
两家开发商在地皮上械斗的时候,他蹲城墙脚下嗑瓜子看戏,顺手给人两块板砖,就进来了。即便不讯问,过了今天,明儿一早也就放出去了。
“听说,你要结婚了。”J警官站在铁笼子外面,笼子里很多人,但只有汪狗对这句话有反应。
“你对得起自己这身皮?”混的人大多都不喜欢官方,有怕的,有恶的,汪狗更多的是恨。他其实已经不年轻了,三十岁的年纪,父母在老家地里刨食吃,自己混这么多年女朋友都不答应结婚,就因为他没房子。
这时候房子不是说买就买的,有钱是一份,有名是另一份,大多都是单位住房分配名额然后花钱买的模式。
汪狗有钱,他女朋友其实也有名,只可惜这个名额被户籍口卡了,转给了别人。
说来也巧,当年那套房子,正是转给了我家。我爹妈正好准备结婚,单位有房子的名额,W女士就行了个方便,把最后一个顶楼的名额给了我母上大人。
J警官知道,户籍口赚钱的门路他很清楚。
“帮我找个人。”他把汪狗放出来,带到门口的无花果树下,递给他一根烟,“房子和钱,二选一。”
汪狗不屑,“宿舍楼的房子你们不都卖光了吗。还有空的给我啊?”
“公安局宿舍住不住?”他和W女士可是名下一人一套的,一套老宿舍而已,这代价他很乐意接受。
不得不说,汪狗确实心动了。他也很清楚,自己其实混不了多少年了,跟老大这么久,都没混出个名堂,再加上女朋友那边的压力,他其实考虑过很多次换个活计。
而现在,出现在他面前的是通往出人头地人生巅峰的独木桥。
“只找到人就行了?”他接了烟,一口抽干大半。
“活着,带到局里。就这样。”J警官从不是个好人,没道理老婆还在急诊里,他就要留肇事者一口气。
汪狗没说话,抽完烟,烟蒂扔地上碾成饼,转头上了自己的桑塔纳。
J警官什么也没问,回医院守了一晚上。局里领导私心觉得W女士出事跟他们正在查的案子有关系,让警卫员联系了北京的医生连夜飞来手术。
第二天一早,手术室的灯还没灭,汪狗却拖着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扔在了公安局门口。
“我喝多了,我真的只是喝多了……”男人很慌,跪在地上爬了好几次没起来。
J警官并不在乎他到底是为什么撞人,但他必须是因为地皮。
“我们可以私了。”J警官坐在审讯室里,面对着浪费的中年人,“只要你说实话。”
中年人嘴里说不了一点儿实话,但J警官的私了条件他很心动。
“十万块钱,从此两不相干。”说实话,这话在当时听来有点儿卖老婆的嫌疑,但考虑到J警官并不缺这点儿,其中意味就深了。
“行。”中年人咬咬牙,应了。
他作证,是有人花钱雇他撞人,他的目标本来是J警官,只是昨天晚上确实喝多了,回家路上发生了车祸。
当然,他说的内容没人在意细节,大家只知道现在两家开发商撕破脸了,真正有用的消息一字字一句句漏出来。
案件侦破,W女士也脱离病危转入普通病房,尽管她失去了半个大脑,但是没关系,J警官的升职弥补了一切。
他离开了刑警岗位,转成为国土局的新局长。
至于那个从头到尾都没见过影的中间商……老爹没跟我讲。他只跟我说,一块地皮能换荣华富贵二十年,如果这块地皮能再加上一个二等功,那就是荣华富贵五十年,再如果,在此基础上再加一个因工负伤……
“连小辈,都能荣华富贵一辈子了。”


mode:笑语/求知(写的不太好,但是改不动了)
声明:为了行文便利,所有出场的生物都会被称作“人”即使他们可能不属于智人科
注:这里的人们没有宗族之分,又不是那么清楚自己的出生,因而将所有养育他们的女性长辈称作母亲,男性长辈则称为父亲。
近日迁徙队伍的情绪有些紧张,他们觉得自己似乎被未知的生物追上了。那未知者狡猾地很,如同幽灵一样盘旋在人们的身后,人们的脊背在一天中的某段时间里总是毛毛的。这多少让他们想起了在旧居边缘的林地里那些吃人的巫婆和鬼怪传说。
是夜奈登与星期三密谈。“你将我视作赋予你生命的第二个父亲,”奈登点亮了烛火,放在了小桌上如是说:“但你却违背了我的忠告。瞧瞧你都带了什么来。”星期三站在桌角一侧看着他:“我们需要人口来保证未来。”那个见多识广的年长男人像是终于听到了让自己发笑的东西,从鼻子里喷出一口气:“我看你也是像那些外围的人一样老得健忘了。出发前我是怎么说的,嗯?”“任何时候都可以再找新的。”星期三用树枝扒拉着前面的土,立刻接上了对方的问话:”是,但你放眼看这世界,你能保证我们不会死在路上吗?”闻言奈登仿佛听见了什么新鲜事,他嗤笑一声:“你什么时候...”话头刚起,奈登却好像察觉了什么,借着火光看向看向星期三的脸。
他从那人转瞬即逝的恼怒里捕捉到了一丝真实的忧虑。奈登严肃起来,不自觉地就想要对上星期三的目光,然而那里只有一个空洞的眼眶。他愣了一下,终于随即缓和了态度:”我确实不能保证会不会死路上。但是我能保证,如果你处理不好这些人,就别谈上路了。“
仿佛为了印证这句话,外面传来了喧闹声。只听一人大喊:”头!走散的人找到我们了。”两个男人一起走出屋子。星期三认出了其中一些。他们当中有支持他屠龙那几个神庙里的女人,还有一些则是原来居住地外围经常深入丛林的盗猎者。他们的在人群中的气质总是突出一些,衣着是深色的,时常残破,并粘上一些没有洗干净的兽毛。不过当前他们的外貌十分地统一:这些人显然高强度奔袭了很多天,身上沾满了草叶和泥土,一脸疲惫。
发生这样的事件,对于那些离散的人来说是高兴的,对于那些要考虑怎么多些床铺的人来说却是忧愁的。不过这里的人总是被幸运眷顾,探路的斥候今日下午刚走,剩下好几个铺盖,让这些新来的人不用后半夜在空地上吃西北风。
好在今夜是祥和的。不过星期三还是察觉出了一丝异样:这些神庙里来的人抱作了一团,向他们那个理应没有多余位置的帐篷走去。“你们头子呢?”他这样向那个带着屠龙队的人问。那人仿佛早知道星期三有这一问,答道:“她下午就和斥候一起走了,说是要去前面试试新的草,这几天都不会回来了。”答案略微超出了星期三的预料,于是他只得答道:“那,行吧。”但身后的姜平闻言脸色立马变得难看了起来。然而不等她发作,和她一起的五月就揽过她的肩膀,把她带走了。
那么从这里开始,就正式进入了天鹅篇。这段文字出现在这里大概是有些不合理的。毕竟按照上一篇的行动,我应当把命名放在最后。然而我希望这信息能尽快地被知道,便就放在这里了。至于是出于什么心态,或许是为了凑字数,又或者是再次掉书袋上瘾了。总之能写出这么无聊的东西大概不会是出于什么好心。
篇目本名“李尔”,或者“利尔”,或者“里尔”,叫什么的都有。但个人考虑到用人名做标题个实在是略微有些缺德——毕竟这样一说就好像都默认了所有人都知道某海上岛国在维多利亚时代某个皇家御用著名戏剧作家的著名悲剧——再者,只要去随便哪个地方大喊一句,对这个名字大多数人能想到的还是此剧目当中那个老国王,因此就改了。
事实上,有关李尔与他子女故事的改编在千年见大概是从未断过,就比如更被人知晓的莎士比亚的那一个。然而在最初的故事里,李尔的子女成为了天鹅,他到死也没能见上一面,这大概就是我给这一篇取名天鹅的原因。






6.无面的骰子——卡曼琳
我已经给那个惊恐的流浪汉道了半个月的歉了,在第三次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叫马特提恩,第五次的时候他说想吃烤鸡翅,第八次的时候他让我坐下来陪他一起吃,尽管我并没有带任何吃的,那天我是看他吃完我才离开的
第十次的时候他慢悠悠的跟我说到他有一个有些吵的朋友
今天是第十五次,我有些好奇他今天会不会再多说点什么了,在谈论起他的朋友的时候,他的表情总是很灵动,眉毛有些翻飞,嘴角咧的略带勉强,但是依旧是舒缓的微笑
和那天被我从垃圾桶里翻出来的表情不一样,有些无聊的笑容,但我并不反感他这样
我不太习惯和别人一起吃饭,所以我总是递给他一份餐点之后就坐在他旁边,偶尔我会调试吉他,或者背一背要唱的歌词和乐谱,他的话语就像八分音符一样涌进我的耳朵,并不聒噪,听听也挺不错的
所以我今天也很期待能听到他讲什么样的故事
据说他的朋友有些毛毛躁躁的,头发卷曲,很擅长赌博…
我想象了一下擅长赌博会是怎么样的一种外貌,但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那种地方,所以脑内没有办法勾勒出来他的样子
只能不断的回忆和妹妹一起看过的电视剧里,赌徒狂野,粗犷,强壮的,有些唬人的外貌了
不知不觉的走到了和马提特恩约好的路口,探出身子去看的时候,并没有看到他
倒是有一个人站在马提特恩常蹲着的地方,转着什么东西
虽然四周昏暗看不真切,但我想那应该是一把小手枪
我有些困惑,不知道他在这里等谁,而且他脚踩着的地方,以往我都是坐那里的
看来今天在马提特恩来之前要多等她一会儿了,我低头看了看手表,时候不算太晚,多待一会儿也无妨,袋子里的晚饭也还算温热,索性打算走过去站在那人身边等他
而那个人听到我的脚步声之后立刻变得警惕起来,我听到咔哒一声,应该是把枪握在手里了
他的表情谈不上惊恐,我不喜欢,而是警惕,本来在灯光下就乱糟糟的头发更是把光斑驳的分散在脸上,他暗红的眼睛仿佛激光笔一般,骨碌碌的转了一圈,很快把目标锁定在了视野的正中心似的
他的眼睛是手枪的瞄准镜
感受到一股莫名的杀意,我便停住了脚步,我看到他拉了枪栓
怎么了?这附近有什么需要戒备的人吗?我余光瞥了一圈四周,并没有任何可疑的身影出现,只不过这里是流浪汉的据点之一,或许是需要高度警戒才不会失去什么东西吧
好吧,我也不是不能理解…我正打算继续向前走去,他“簌”的一声抬起了枪
“…别过来”我听到他的声音在地上烧出了一道充满火药味的沟壑
原来是在戒备我吗?我有些困惑的指了指自己
“啧,装什么傻,我知道你也带着枪”他的语气有些凶狠,像一条受惊的流浪犬
用小狗来比喻的话,吉娃娃更合适吗?我看着他,他的手臂还在微微颤抖,另一边借着夕阳和路灯的光晕,我大概能看到他紧紧地咬着牙
不过也不怪他紧张,在杀戮日出现之后,街边的流浪汉总是会对人抱有极度的警惕和恐惧,而且他说的也没错,我今天晚上正好有其他的事情,所以顺手夹了枪在衣服里
他还真敏锐,我歪着头看着他。不过也没必要对我抱有如此大的戒备心吧,我试探着的又往前走了一步
“告诉你别过来了!”他的声音比之前又大了一点
他在赌,我也在赌,我不知道赌约是什么,筹码是什么,骰子是几面的,输赢是怎样的后果,但我很乐意加入到他的赌局里
倘若在这趟街上响起了枪声,后果就是一发不可收拾的麻烦事了
虽然我也有信心在他开枪之前就把枪夺下来,但现在比起对付他,我更想逗逗他
他的不安和马提特恩那晚的惊恐如出一辙的明显和突出,他的戒备心像是一圈带刺的荆棘,把自己团团裹在里面
也许我的出现对他来说就像是外敌入侵了他的领地吧
“嘿,我只是来…”“站在那!”
我试图给他解释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但他一声喝令不许我再靠前了
好吧,那我就站在这里等着吧,我看他依旧颤抖着手臂举着枪,黑洞洞的枪口对着我,我望着他,他混乱的黯色双眼不如他的枪口坚决,举枪威胁只是一种方式,并不是他想实现他的目的而采取的必要手段,只是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可以做点什么,只好无奈的举起双手示意他我没有带任何危险的东西
“我想坐一会儿”“不”
好吧
我们两个面面相觑保持了一会儿沉默,期间他试图放下手枪,但随着我整了整被风吹乱的衣领他又把它举了起来,我看到他的眉毛上下挑起,眼睛中的紧张逐渐转成了一种好奇和疑惑,手也不再抖得厉害,或许是有些酸胀了,也可能他对我这个一直站在他领地里却不作为的陌生人感到奇怪,太阳光即将消失的前夕,我仿佛看到他卷曲的头发翘了起来,像一个问号
没有一个人扣下骰子,一个没有点数的方块就这样在桌上不停地旋转着,我举着双手不碰它,他也举着手不拍下去,时间就在这样奇妙的赌局中莫名其妙的流逝
“哟,卢西亚…卡曼琳?你怎么过来了”终于,我听到了那个有些熟悉的声音,侧过头去,看到马提特恩趿拉着步子正往衣服兜里塞着什么小瓶子,在看到那个黑发瘦削的人影时,他的眼睛忽的亮了起来
“嘿,怎么回事,你认识这个人?”被他称呼为卡曼琳的人依旧不肯放下枪,不过似乎愿意整个转个身子来面对我了
“喔,他啊,他是卢西亚”马提特恩一边说着,一边从我身边轻飘飘地滑过,他比之前似乎更瘦了点,这不对劲,我一直以来给他带的饭量应该足够他吃饱才对
我看到从他衣兜里滑进去的小白粉袋子,皱了皱眉,俯身准备把今天的汉堡和炸鸡从兜子里掏出来递给他
卡曼琳不知道为什么注意力格外的在我身上,这让我有点动了玩心,故作慢慢悠悠的蹲下去,他一定会以为我要拿出什么危险的家伙什,毕竟他现在对我还丝毫不信任,我想赌赌他脸上在得知真相后,一定会露出特别精彩的表情
只是我刚俯下身去,他猛地一把就将马提特恩拉到他的身边去,这不太好,有点挡住我的视线
不过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在害怕我还是在保护他,马提特恩被一脸懵的扯过去还被卡曼琳原地转了个圈,现在结结实实的挡在卡曼琳的面前,卡曼琳那把小手枪从马提特恩的身边露出一段来
“你从哪认识的这家伙,他要干嘛?”他有点嘶吼“是不是你弄的东西被他发现了”
“啊?不是,他不知道啦”我第一次看到马提特恩单纯的手忙脚乱,而不是像那个夜晚一样紧张到不知所措
这个转着圈的骰子,终于被一个慌乱的客人丢了出去
“他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朋友啦,每天都会给我带吃的的那个小哥”
“哈?可是他明明带着枪…”听到卡曼琳这句话,我终于心满意足地拿出了那包打包好的快餐,包装纸袋摩擦的声音和微微被捏扁的外貌,让枪口停下了抖动,卡曼琳一脸困惑的从马提特恩的身后探出了半个身子
“没有手枪腿”我轻笑了一声,看着卡曼琳的表情像一杯冲调咖啡一样被困惑不解,愤怒无语还有无可奈何搅在一起
“…这小子”他从马提特恩身侧走出,嘴唇有些颤抖,似乎在酝酿着什么长短不一的句子
“我知道”马提特恩好像和他共鸣了一样拍了拍他的后背,“他就是那种”
“哪种?”现在只有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了
“闭嘴”卡曼琳上下打量了我一番,挠了挠头,伸出了手“把那个给我”
“我只带了一人份”“我管你那么多,给我”我摇了摇头
“你…!”“这是给马提特恩的”我看着他有点抓耳挠腮的样子,感觉心情有点畅快,把汉堡塞到了马提特恩的手里,卡曼琳有些不满的举起枪朝我比划了一下,只不过这次随着手部动作响起的咔哒声,只是一次普通的转枪
没有人再在赌什么了
“…所以,卡曼琳,你是…”“他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啊,很厉害的”“……赌博的?”
“小哥…你说话真的有点不中听诶”“我叫卢西亚”“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啊”
走出赌场的人就是可以这样轻松交谈的存在,我看着卡曼琳因为不满而不断颤动着的头发,轻出了一口气
“小哥,好吧,卢西亚”“什么?”
“明天会给我也带一个手枪腿吗?”“…有点难度,我会试试…”
“哈哈,我很高兴今天赌赢了”“赢了什么?“
骰子骨碌碌的落地了,上面没有任何的点数
“小哥,没有人说过你有点笨吗”
或许我真的不太适合赌局吧,我冲他摇了摇头
不过看上去未来应该还会再遇见他了,这种事情在之后慢慢请教他就可以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