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你的/你喜欢的角色的问卷:
*所有男性“他”皆可平等替换为女性“她”*
1.“爱”对他意味着什么?
一起做快乐的事
2.他害怕什么?
孤身一人,孤独终老
3.他最为自己感到自豪的一件事或东西是什么?
力气大,跑得快
4.他觉得什么事情很让人难堪?
不小心说错的话被当众拆穿
5.他更喜欢白天还是黑夜?为什么?
白天,因为热闹又明亮
6.他经受噩梦折磨还是拥有无梦睡眠?
不经常做梦,做恶梦的几率更少
7.会让他感到高兴的人或事?
交到朋友,一起玩耍
8.如果他被困在雨里,他会怎么做?
淋雨快跑到避雨处
9.他在音乐方面是否有技能?
偶尔哼哼几句
10.他对于褒奖作何反应?
*´∀`)感到开心
11.他如何面对被拒绝?
另寻它法/再试一次
12.他是否有偶像或者一直崇拜的人?
崇拜英雄一样的人物
13.他是否有对象?
正在考虑中
14.他死活不能忍受谁?
不论他说什么都不回应的沉默寡言的人和悲观过头的人
15.他很容易相信别人吗?
要深思熟虑一番,不过并不是多疑
16.他怎么看待死亡?
早晚的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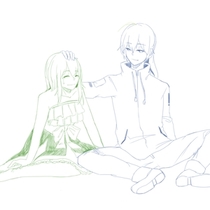
这里放出关于计时结束后的某些设定,具体过程【请胜出者自行决定】。
*在船上只剩下了一个人时,在第九时段开始时封住楼梯口的门会自动开启。
*计时结束前五分钟起会有倒计时,依次为[五分钟,四分钟,三分钟,二分钟,一分钟,三十秒,十秒,五,四,三,二,一,计时结束。]倒计时时广播依旧处于坏掉的状态,但隐约能听出来杂音在慢慢减少。
*在计时结束后C会对胜出者说一些话【自行决定】,此时广播莫名其妙的好了,内容大致为对胜出者的庆贺和安排离船。语气很恶趣味。计时结束后继续在船上停留的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
*离船方式自定,可以开甲板坐直升机也可以直接停泊码头。
最后的互动时间:10/11-11/1 在此之后企划将无法继续接受投稿,请大家转战衍生小组【限时战争-剧组-】。【传送门?那个小组还没建呢【。】
从七月末一路走来也是终于把这个企划完结了呢,请大家好好享受这最后的时光吧。
1、杀青的感想是
Dia:什么我居然不是主角?!?【震惊脸
【Dia娘:喂喂你自我意识是不是有点强啊?!会被别人讨厌的啊喂!
2、伙食好吗【。
Dia:糟糕【一脸嫌弃】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我带好了充足的调料,以及船上食材非常新鲜充足(人肉)
3、平时和哪位演员玩最好
Dia:除了自己以外……大概是楠楠吧?
【Dia娘:所以说你究竟有多自恋?!?你的世界装不下别人嘛?
Dia:装不下
4、拍摄过程中印象最深的事情是
Dia:盒饭难吃,而且导演居然不给我吃人,让我演的时候用其他的肉类代替!简直不敢置信!【咏叹调
5、道具质量怎么样
Dia:钢丝喜欢,手术刀喜欢,在自己身上试了试,疼疼的,有些兴奋【舔唇
6、剧组里最现充的是谁?【。
Dia:……我只顾着自己爽了没注意过
7、剧组里最蛇精病的是谁?
Dia:同上
8、有过NG的时候嘛【。
Dia:经常。因为本色出演有的时候导演说我有些过于变态了观众会接受不了,只能重来。【阴郁脸
9、导演(C)怎样?
Dia:不给我吃真人肉,一点都没有艺术工作者对呈现“真实”的觉悟。而且把我奸尸的片段删掉了啧……
10、你觉得哪位演员台上个台下的差距最大?
Dia:我好像一直都在注意楠楠和其他男演员的菊花,没注意过别人……
11、有决定过要和那位演员组CP嘛ww
Dia:楠弥吧,已经调教的很让人愉快了w
12、感觉剧组的戏整天来说怎样?
Dia:……盒饭难吃
13、最开始构想自己的剧情发展是怎样的?和现在的剧情支线差别大吗?
Dia:本来以为自己能活到最后的吧?结果意外居然还有其他演员也很努力,演最后对手戏的时候非常愉♂悦
14、身为道具的盒饭/F可以吃/用吗……【
Dia:不能!简直侮辱我的味蕾!
15、能吃的话最喜欢哪个口味/用途【。
Dia:衬托自己的厨艺
16、说出整条船上最有病的前三位
Dia:大概是那些不喜欢男人的男人吧
17、那么整条船最正常的前三位
Dia:那几个基佬
【Dia娘:……儿子我没教育好你真是罪孽
18、承包鱼塘嘛【。
Dia:如果楠楠喜欢的话有多少包多少
19、预期工资大约多少hhh
Dia:爷不缺钱,就想吃口人肉操操菊花……
20、……上一题的现实呢【。
Dia:人肉没吃上真的,但是菊花……【笑
21、哪段戏演的最开心w
Dia:每次杀人和被虐w~和楠楠在一起也很开心
22、觉得谁的杀青最可惜
Dia:唔,最后两人吧,因为结束了嘛。
23、如果最后在剧中可以回家,第一句话是什么ww
Dia:楠楠,给我口交,就在客厅。
24、对于即将开始的爱船模式怎么看w?
Dia:菊花不少【笑
25、……如果告诉你还有20题怎么办【。
Dia:我就问问谁写的题目【笑擦刀
低压:大家好我是Dia娘,我儿那么变态……大家能忍他到现在真是辛苦了,以后也请愉♂快♂相♂处~【笑





1 杀青的感想是
Answer:真的是好紧张的过程呢,跟迪亚先生打得手心都冒汗了,非常害怕脱手把道具砸到摄像机上。
2 伙食好吗【。
Answer:对于雪原的居民来说,只要营养搭配够可以什么样的伙食都不会挑剔的。(笑)
3 平时和哪位演员玩最好
Answer:和陈怿纯女士吧,在戏中我们也演过拍档,可是到最后剧本改得好厉害啊,两个人原本对熟了的台词最终也没办法用上。西泽尔先生一开始也会跟我说话,可是在他杀青之后我们就不常联系了,真是遗憾。
4 拍摄过程中印象最深的事情是
Answer:对于我来说每一场戏都是珍贵的故事,体验其中的人生也非常有趣,所以没有“最深”的说法。
5 道具质量怎么样
Answer:还挺好?至少在那么猛烈的打戏中没有出现武器断掉之类的情况。
6 剧组里最现充的是谁?【。
Answer:我觉得是秦氏姐弟吧,两个人的关系令人非常羡慕。
7 剧组里最蛇精病的是谁?
Answer:还真是尖锐的问题,请恕我难以回答。(将食指轻按到嘴唇上)
8 有过NG的时候嘛【。
Answer:有的,第8时段我和陈怿纯女士的戏份因为剧本的临时修改而NG了很多次,当然还有第二场戏份中对谨小姐的吻手礼,导演一路在要求我在逃跑的时候要更加狼狈一些,为此重拍了很多次。
9 导演(C)怎样?
Answer:并不讨厌她,毕竟也是多亏了她才能有最后的成品。(笑)
10 你觉得哪位演员台上个台下的差距最大?
Answer:嗯……我觉得差距最大的还是舒龙陶先生吧……诶,什么?我吗?不,我觉得自己还是非常本色演出的。
11 有决定过要和那位演员组CP嘛ww
Answer:大家都各有归属,而我的归属自在他方。
12 感觉剧组的戏整体来说怎样?
Answer:大家都很卖力呢,我们睡觉的时候往往连妆都来不及卸掉,有些人甚至直接就带着血妆在半夜起来上厕所,回想看那画面还是挺有趣的。
13 最开始构想自己的剧情发展是怎样的?和现在的剧情支线差别大吗?
Answer:最开始没有过太多的思考,因为剧本经常有临时的变动,所以就顺着随遇而安了,可是总体来说风格差异还是并不大的吧?
14 身为道具的盒饭/F可以吃/用吗……【
Answer:我的戏份中从头到尾都没有怎么提到过他,所以这个问题我也便无法回答了,很抱歉。
15 能吃的话最喜欢哪个口味/用途【。
Answer:我的话还是希望他的血浆能够变成画材,那种红是世间独一无二的宝贵颜色。
16 说出整条船上最有病的前三位
Answer:敬请参考第6题的答案。(笑)
17 那么整条船最正常的前三位
Answer:山口崎女士,瑟兰达女士以及古伊先生。
18 承包鱼塘嘛【。
Answer:在俄罗斯的冬天,没选对地方鱼塘是很容易结冰的,为此请允许我拒绝。
19 预期工资大约多少hhh
Answer:看着给就可以了,我不着急用钱。
20 ……上一题的现实呢【。
Answer:这个……大概两百万吧?
21 哪段戏演的最开心w
Answer:约莫是新剧情中为陈怿纯女士系上缎带的那一段,很简单但是有莫名的悸动感——应该可以这么说吧?
22 觉得谁的杀青最可惜
Answer:自然是秦氏姐弟,他们的才能非同小可……至于为什么不是迪亚先生,是因为觉得我们已经“堂堂正正”地交手过而不再有遗憾了。
23 如果最后在剧中可以回家,第一句话是什么ww
Answer:事实上我也回家了不是吗?(笑)但是没放出来的剧情中仍然有这样的一句台词:“如果我能回到家中,那肯定不是旅行的终点,而是开元的初始。”
24 ……如果告诉你还有20题怎么办【。
Answer:能够继续为您讲述我的故事,乐意之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