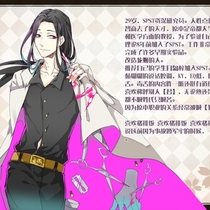生存并非是什么新鲜的话题。
人类早已脱离了为一朝一夕的饱食取暖而奔波的阶段,劳动成为了满足更加深层欲求的有效途径与必要手段,通过对他物种的榨取而获得的能量从很久以前起,便不再仅仅只是作为‘活着’这一单纯状态的支撑,而是为了得到‘更多的’、‘更好的’而运转身体这个机械的燃料。
与之相比,对于妖异来说,生存二字的含义则要单纯得多——摄取足够维持机能的能量,维持足够的空间存在下去,仅此而已。
早幸从前的生活可说这是这样无欲求的妖异的典范。那甚至很难被称作‘活着’,她同雪原上的任何一捧白雪、一从枯木没有太大差别,风雪是她的食粮、寒霜犹如甘露,一族中确实也有靠吸食人类精气生存的雪女,但早幸并非是这样的类型。
在决意走出这种生活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仅仅只是无声无息、了无生趣的‘存在’在那里而已——
“哎呀……”
山中的树林中,有人发出了略带疑惑的轻呼。
月光穿透枝叶斑斑驳驳的投在这处静谧之所,站在林间的女性水色的长发披散着,面庞光洁、五官秀智端庄,她穿着质地高档的和服,从衣袖中伸出的却并非是名门闺秀那样纤葱无暇的柔荑,而是闪烁着莹莹蓝光的鸟羽,精心打理过的长长羽毛顺滑而美丽。
月见里夕颜微微睁大双眼,用一边的羽翅浅浅掩住唇。
在她身前不远处,一颗古树交接盘错的根植处安静的蜷卧着从未在这片山林间出现过的某种异物。以一张隐约可见微微闪烁的白色布匹和一起为圆心蔓延的冰霜为温床,其上侧卧着紧闭双眼的雪肤少女,这不合时宜的出现在此处的女孩肤色如雪近乎苍白,两手交叠贴在脸侧,微微淡粉的唇清浅的张合吐息,白色布匹似有灵性般包裹着少女蜷起的身躯,随着主人的呼吸而微微起伏。
站在夕颜的位置,只要再稍稍向前一步,便能够清晰的感到周遭气温的变化。原本三月末尾透着丝丝凉意的夜风,似乎在这瞬间化作了削骨的利刃,越是靠近便越是寒冷,待到夕颜走至女孩身前,只觉得自己的四肢百骸似乎都缓缓冻结起来。
她若有所思的看了一眼自己翅膀上薄薄一层寒霜,轻描淡写的将之抖落,随即将视线转回到安稳的睡在那里的少女身上,稍稍思索之后做出了一个决定。
苍鹭的半妖面不改色转头离开了。
‘啊呀,今天也没能想到什么好的展开,还是回去早点睡吧。’
……
…………
……………………
等等。
等、等等……等等。
不不不不这不对。这是不是有哪里不对。很明显有哪里不对吧。
这位少侠?刚才是不是稍微手滑了一下?没关系这里有存档,我们再来一遍!
深夜散步途中在家附近的林子里遇到了熟睡的妖异美少女,在这种情况下主人公可以选择——
*抱回家。
*因为叫不醒所以抱回家。
*啊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姑娘赶快抱回家。
(要点脸……)
玩家 月见里 夕颜 选择了——
*关机回家睡觉。
……
这游戏玩不下去了。
月见里家年轻的当家人无声的离开了。林中仍旧是一贯的静谧,有虫鸣偶尔响起,从风中间或传来隐隐约约的兽类长嚎,携卷着莫名冰冷的空气碎裂在空中。
不知过了多久,一道黑影突兀的在林间一闪而逝,那迅捷的影子在熟睡的雪女身边停了下来,蓬松柔软的黑色兽尾轻轻从对方身前拂过,如踏白雪的脚爪悄无声息落在雪女的身旁。
黑狐眯了眯红眸,稍稍张口露出了利齿,似乎是有些无奈的龇了龇牙,狐狸低下头,将脑袋靠近了在睡梦中抿起嘴的雪女。
在它真正将这个毫无防范的家伙蹭起来之前,时刻竖起的尖耳因捕捉到的细微声响而突然抖动了一下,黑狐气势一变,绷紧了身子迅速抬起头来。
从远处树林的一头,隐隐传来稀薄的人声,狐狸再度小小的龇了龇牙,扭头又看了一眼身后窝成一团的雪女,足下稍顿,瞬间又化作一道黑影几下跳动消失在了树林深处。
片刻之后,先前离开的蓝发半妖同另一个生着绒绒双耳的黑发少女一同回到了这里。
在不久之后,对这期间发生的一切毫无察觉的雪女便会醒来,并且正式开始她在人类社会中的新生活。
*
关于去而复返的夕颜:
据本人写道,似乎是之前走丢过一只宠物,因为早幸的感觉和其很像,所以有些在意最后还是决定把她捡回来了。
关于搬运:
再怎么没防备,也不至于被搬回家都不醒过来。事实上早幸在夕颜同家中的帮工猫又的半妖球球试图把她抬起来之前就醒过来了,还因此受惊不小,一瞬间狂风暴雪差点让两位半妖小姐被埋成雪人……最后因为想起自己离开雪原的目的,这才顺利住进月见里家。
——当然之后因此而被夕颜和球球‘重点关照’了好一段时间。
顺便,因为并没有控制自己的妖力就这样睡着,所以那时早幸的身边非常、非~常的冷,夕颜根本没有打算抱着她或是扛(?)着她回去,而是吩咐球球准备了小板车……最后小板车并没有用上就是了。
和人类以及半妖在一起的时候,早幸还是会相当克制妖力,不会时刻都是移动空调的……虽说周身散发出冷气对于她就像是本能一样,并不需要刻意为之,反而要收敛起来有些费力。
打工时假装是个普通人类……露馅了就假装是个普通半妖(
——————————
想了想互动还是分开放吧,总觉得到时候关联一大片人挺不好意思的(((
(然而还是厚脸皮的继续关联了狐狸)
缓慢的进度,接下来消失几天赶死线,回来想继续写写打工同事明比谷、十九小哥和戳炸萌点的雪女小姐姐刹那(开心乱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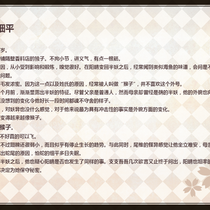



*之前约的419
*偏意识流的R18(为什么写个R都要玩深度我也是不懂自己
*瞎写写就不关联了
——————————————
傍晚的时候夏夜和雷明一起去喝了酒。
酒的度数并不太高,也不至于令人醉到失去理智的地步,但有了酒精作为藉口,放纵也就变得理所当然——并非出于主观的理智,也就无需背负与之相抵的责任,大多数时候人类确乎是如此自欺欺人的生物,并将要如此自欺欺人下去。
脊背重重地撞击在手术室的金属门上,疼痛混合着冰冷的触感从背后传来。
夏夜偏了偏头,露出挑衅般的微笑。
首先是接吻。
呼吸与呼吸交换,舌与舌纠缠。
浓郁的酒气在鼻腔溢散,他们像进攻的野兽般相互撕咬,没有留下丝毫暧昧的余裕。
【亲吻是衔接爱与欲的桥梁。】
夏夜并不厌恶接吻,但也并不太喜欢。比起雷明粗暴的侵袭来他在技巧上更具优势,但也仅此而已——在接吻之中他无法获得乐趣,因而也就成了例行公事般的乏味。
稚名夏夜从未爱过任何人,他和各种各样的人上床,做爱。而他所能够获得满足仅限于肉体,却难以深入感情。
进攻被对方轻易化解,雷明的动作越发急躁起来。原本迫切的侵入变为更激烈的撕咬,像有淡淡的血腥味在口腔中弥漫。
夏夜自顾自哼笑了一声,尤嫌不够似的伸手挑起对方的下巴。
“多练习就好了。”他这样说。
在挑起他人的怒火上稚名夏夜仿佛有着与生具来的天赋,而他自己似乎也同样清楚这一点。
“啪”的一声脆响在空旷的手术室中响起。
夏夜抬手捂住脸颊,却在察觉到对方眼里的懊恼时骤然轻笑。
“你喜欢这样?”雷明沉下脸。
短暂的懊悔一闪而逝,被对方所戏弄产生的愤怒盖过仅存的歉疚,他揪起男人的领子,顺手补上一拳。
——不愧是保安。
这样的赞叹在脑海中一闪而过,夏夜踉跄了一下,摔在身后的手术台上。
痛觉从身体各处传来,耳中传来金属碰撞的声响,以及隐约的耳鸣。然而在痛觉中又仿佛存了某种奇异的快感,情欲伴随着痛楚,在每一根破碎的血管中攀爬蔓延。
他骤然意识到自己此刻正仰躺在手术台上,雷明揪着他的领口。纽扣被用力拽落,“啪”地摔落在地上。
——就像某种身份的置换,解剖他人,被他人解剖,给予疼痛,被疼痛给予。
稚名夏夜沉溺于这种异样的快感,就如毒瘾者渴求罂粟。
【痛苦是活着的证明】
交叠的亲吻中弥漫着血的腥气。
残余的衣物被撤下,凌乱地丢弃在一旁。
扩张简单而草率,周围并没有可以用作润滑的东西,粗暴的挺进伴随着比之前更强烈的痛楚。
雷明并非是很好的床伴,至少对于一夜情的对象是如此。
光就对方在做爱时表现出的野蛮而言,夏夜几乎怀疑自己是在与野兽做爱。
毫无技巧,横冲直撞,雷明在床上的作风近乎是与外表截然相反的粗暴。那种不受理性控制的狂野恰好取悦了他,夏夜颤抖着,发出毫不掩饰的,愉悦的呻吟。
理性抽离于感官,他们放任自己从人性中挣脱,而后沉溺于无关乎感情的性爱。
时间的概念变得模糊,手术台晃动着,发出激烈的响声。
【征服是男性的本能。】
存于本能间的征服欲推动着单方面的暴行,雷明毫无怜悯地冲撞着对方的身体,交合的部位反复抽插,空气中像有血的腥味弥漫开来。
征服,摧毁,抑或单纯的泄欲……这三者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以致于叫人难以分辨。愤怒来得毫无缘由,雷明加大了攻伐的力度,而回应他的却只有夏夜越发肆无忌惮的呻吟。
一方被怒火所取悦,一方因愉悦而恼怒,身体相互契合,然而无关乎情感。
就像天空与海的交界,毫无交集,又确实被地平线所分割。
在高潮的那一刻大脑被空白的空无所填满。
雷明将套子随手甩在地上,夏夜从背后勾住他的肩膀,藉由距离营造出某种近乎于暧昧的氛围。
“承蒙招待。”
刻意压低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又像带着隐约的笑意。雷明一把将对方甩开,头也不回地离去。稚名夏夜凝视他逃离般的背影,忍俊不禁般地低笑。
微笑时牵扯到伤口,起先是脸颊,然后连带着身体各处都开始叫嚣疼痛。手术台上并没有可以用作镜子的事物,但他完全可以想象出此刻自己狼狈不堪的样子。
——战争中本不存在胜者。
夏夜从手术台上支撑起身体,打开清理的开关。
带着刺鼻气味的消毒水洒落下来,血与精液的气味被冲散,除了疼痛,什么也没有剩下。
-f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