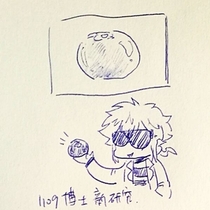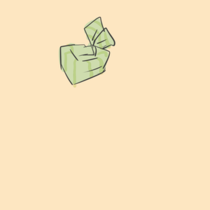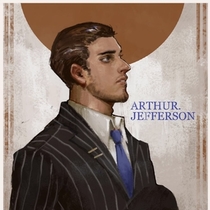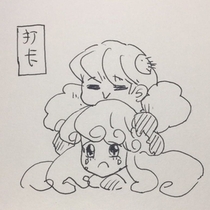上接【http://elfartworld.com/works/139272/】
【這就又要打卡了……銜接用短章,文風文筆都次到爆炸,而且還短】
“付喪神?你接下來是不是要說自己討厭我,然後叫我把煙斗丟掉?我才不要嘞!”來幸原本就對對方不慎信賴,現在又加重了疑慮,“大哥哥,你要是坐夠了,就回去吧!”
對方露出好氣又好笑的神色來,這更叫來幸不舒服了。但為了不叫自己把情緒表現得太明顯,他給自己倒上一杯水。
“那倒是不會,我只是煙斗的付喪神。”閣樓的不速之客說道。
“唔……”來幸從身旁拿起來煙斗,仔細端詳了起來,“那我要是給煙斗添上煙草,你會不舒服嗎?”他說著用手指戳了戳煙嘴,再偷眼看著青年的反應,對方一臉平靜地看著自己。
“雖說我的身體也會因為煙草發燙,但因為煙斗本身就是做這種事情的,所以並不會覺得不舒服。”青年耐心解釋道。
“我該怎麼叫你呢……?”來幸又問,“叫你煙斗先生可以吧……?”叫煙斗聽起來有些生疏,單純叫先生也不太好,來幸便折中選擇了這個叫法。
“沒問題,反正我沒有名字。”自稱是煙斗付喪神的男人這麼說,“倒是你,竟然都不懷疑一下是不是真的付喪神嗎?”
“反正我這裡也沒什麼可偷的……”來幸說,隨即又想起煙斗本身的價格,他於是抱著裝古董的盒子緊緊不鬆手,接著又想起來一件事,“我可以給你取個名字?只有我能看見你?說起來,剛才村上夫人好像也沒看見你。”
“當然?”
“唔……那我想想吧,名字是很重要的。”
“隨便取個名字就好了……!又不是什麼名貴東西。”煙斗先生道。
“唔,不行,名字是很重要的。”來幸說道,“把外套脫下來吧,請您放在椅背上,我要睡覺啦?”來幸說著又攤開床鋪,把自己的古董盒子放在床頭,“對了……煙斗先生,我的名字是來幸。”
“嗯?是賴光的賴字嗎?”
“是未來的來和幸福的幸,幸福會到來的意思!好啦,我真的睡覺啦,晚安。”來幸說著脫下和服羽織和襯衣,給自己換上了寬鬆的睡衣,“煙斗先生,你要睡覺嗎?要睡覺的話就和我擠一擠吧!”他拍了拍身旁的床鋪,自己率先鑽了進去。
“不用,我不需要睡覺。”
“不許把煙斗拿走!”來幸嘟囔著,給對方騰出來位置,“晚安。”
“晚安。”來幸看到煙斗先生坐在桌前,好像獨自思考什麼似的。閣樓昏暗的燈光勾勒出成年男子背影的輪廓。叫他什麼呢,來幸想著,但比起那些,今天發生的事情實在太多了,他的頭一靠上枕頭,疲倦感便輕柔地灌溉過身軀。
算了,明天再想吧。他迷迷糊糊地告訴自己,墜入了夢鄉。
夢裡,他夢到煙斗變成了煙斗先生,然後又變成了一道鎖。他看到在津山的老家的大門被那把鎖牢牢地鎖上了。
逃走吧!那道鎖向他喊道。逃走吧!
隔天早上,他醒來後就忘掉了這件事,滿心想著又要去工廠工作了。煙斗先生已經不見蹤影,不知道是去哪兒了。果然是夢……啊!不對!來幸慌張地打開床頭裝著古董的盒子,看到煙斗還在裡面,忍不住鬆了口氣。他收拾了一番書桌上凌亂的文稿,把之前寫好的稿件裝進信封裡。再蓋上昨天忘了收拾的墨水瓶。
收拾好這些之後,他換上上工時穿的衣服,戴上帽子,正打算離開自己的小閣樓,卻看到黑髮青年站在閣樓門口,手裡端著熱騰騰的米飯。
“不吃早飯?”
“唔……是該吃。”來幸喃喃著,又坐下來,“我先吃一點……”
“慢慢吃吧。”煙斗先生將米飯端上書桌。久別故鄉,來幸還是第一次在東京被人服務。他有些不知所措地拿起筷子,扒拉起來米飯。
“對了,我要去投稿,”來幸想起來什麼似的,突然說道,“祝福我吧!”他吃完最後一口米飯,抱起自己裝著文稿的信封,慌忙地逃走了。
窗外,春季的綠意才初綻頭角。
【文風?不認識的孩子呢。劇情?聽起來好像可以吃。羞恥心?有拯救世界來得重要嗎。】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個小小的少年。
不知是因為什麼緣故,少年無論是個子還是頭腦,都要比同齡的其他孩子來得發育遲緩。或許正是因為這份弱小吧,少年淪為同伴們排斥的對象。
今天也是如此。
少年獨身一人坐在遊樂場的鞦韆上,慢悠悠地晃著寬扁的鞦韆。身上的衣服已經因為被人絆倒而弄髒,腿上也多了淤傷。就這麼回去的話,一定會被自己寄宿的家庭抱怨吧——少年想起來自己現在的媽媽,好像已經能想象對方生氣的臉了。
就這麼回去是不行的,不如就這麼流浪吧。他這麼想著,然後也這麼做了——拿著他小小的書包和豎笛,少年開始了逃開所有事情的旅途。他穿過一條條街道,去往一座座車站,渡過一條條河流,意識到的時候,已經身處在不認識的地方。
我逃離了!我逃離了!我成功地逃離了!少年想著,想為自己找個舒適的地方過夜。可是無論哪裡都不合適,沒有錢也沒有身份,無論哪裡都不可能找到棲身之所。最終,他走到一所兒童遊樂場。
這地方與自己逃離的那個遊樂場,就像是雙胞胎一般相像。
已經可以了吧。感到疲勞的少年就這樣坐在遊樂場的寬扁的鞦韆上摩挲著自己的手指。就先待在這裡吧。他對自己說,抱著自己的書包,看著黑夜中好像要將視線模糊的橙黃燈火。
然後、想起來了自己的媽媽。要是媽媽在身邊的話就好了,他這麼想著,瑟縮成一團,感到眼睛有些酸痛。要是現在就能回到媽媽身邊的話,他這麼想著,我就抱住她,然後告訴她我想她了,希望她能快點回來。
她究竟在哪兒呢?他們說她不會再出現在他的生活裡了。想到這裡,他又感到難受了起來,他抽泣著,想把眼睛裡的酸楚用淚水趕出去,可是已經止不住了。少年就這樣哭著,哭著,直到淚水化成低低的嗚咽。他抱著自己的小書包,踡縮在鞦韆上。
秋季已經禿露露的樹木在瑟瑟風中搖擺著石褐色的枝幹。
年紀小小的少年想到,自己說不定就會在說不清是哪裡的地方待到餓死了。不過,餓死也好,就這麼餓死的話,誰也不會想起來吧。少年回首自己短短的人生,感到世界上或許不存在什麼還在關心自己的人了。
“媽媽!”他一邊哭一邊抱緊自己的身體,隨後,他感覺到身後某人用厚重的手掌拍了拍自己的肩膀。
“這是誰家的孩子啊?”
少年轉過身去,看到身後站著的是個高大、戴著假面騎士頭盔的男人。
“怎麼了?怎麼還在哭啊?男子漢是不能哭的!”對方說著俯下身來,好讓他們兩人的視線維持在一個水平線上,“怎麼回事……?”
因為燈光的反射,看不清楚那頭盔玻璃後面的人的表情,少年能看到的僅僅是自己的哭臉反射出來的倒影。
“我……想媽媽了……”少年吸著鼻涕,不知為何對這個毫無干係、頭一次見面的“假面騎士”產生了傾訴的心緒,“我……不想活啦……”
“怎麼會不想活呢?”高大的騎士看著他——雖然少年看不見那頭盔後的表情,但他能感覺到對方一定在望著他,“為什麼會這麼覺得呢?可以和我說說看嗎……?”
要說起來,其實是有些誇張過頭的語氣,但是不知道為何卻給予了少年安心感。
“我,我,……嗚哇……!”少年想說些什麼,但語言最後都畫成哭泣,他大聲哭著,好像把十幾年份的淚水都給哭出去了,思緒與膨脹的心情猶如潮水,一浪浪蓋過少年薄弱的自製心。最後,他只是緊緊地抓著對方的手。
假面騎士抱住了他,輕輕拍著他的肩膀。
“沒關係的。”
“不會……不會沒有關係的……”少年抽噎著,“我又比大家笨,又很矮,……老師也是,媽媽也是,都不會喜歡我的……”
“不會的。”
“怎麼不會嘛……”少年的聲音已經越來越小,直到完全發不出任何聲音為止。這時,他的頭頂碰觸到某個硬邦邦的東西。
是假面騎士的頭盔。對方輕柔但又有些笨拙地將頭盔套上了少年的頭:“來,你看,只要這樣你就能‘變身’了。”
“變、變身……”少年喃喃著,透過頭盔的鏡片看這個新的世界。
“是啊,只要這樣就可以成為“騎士”。很簡單吧?感覺到了嗎?你現在已經變成自己的英雄了,有沒有自信起來的感覺?”對方的聲音隔著厚重的頭盔傳了過來,少年便慢慢地點頭。
“哎……”確實是,比起來剛才要安心了不少。少年想著,卻仍然有些畏畏縮縮。
眼前的騎士只是笑了笑。
“慢慢地,慢慢地從自己相信自己的‘自信’開始吧。”
“可是……”少年躊躇著,卻被對方被粗糙的老繭包裹的手掌附上了手,“我,那樣也不會有人相信我啊……”
對方停頓了幾秒,隨後少年感覺到對方有力的手臂摟住了自己的背:“並不需要什麼人相信啊,英雄本身即是英雄,不是嗎?好啦,小騎士,來,告訴我你家的地址號碼吧!”
——剩下的事情,少年已經記不清楚了。他只記得接下來,自己被什麼人用摩托車送到了警察局。對方一直溫柔地陪著自己,然後,到了第二天早上,“現在的媽媽”帶著擔心的神色趕到了警察局。
他哭著撲向母親,好像已經很久沒和對方見過面,在後悔與安心的情緒中,靜靜地感覺著對方的愛和關心。
等到少年回過神來時,帶自己來警察局的英雄已經不見了。
***
二十九彰剛咽了口口水,他不知道第幾次調整自己頭上的頭盔。車上的乘客一路都盯著他看,讓他有點不自在。但是這些都沒什麼,他對自己說,比起來會讓臉看到的事實,被他人盯著不過是會讓他有些小小不快的因素罷了。
“請候車的乘客先讓其他乘客下車,請小心夾縫。”他聽到車站廣播那好像救命稻草一樣的廣播,緊緊盯著電車的門,在開門的那一刻沖了出去。
“不好意思,借過一下!借過一下!”他大聲喊著,抓緊肩上的背包,在人流湧向車站的前一秒全速跑了出去,“不好意思啦!太太!”他這麼大聲說著上了扶梯,隨後擠過在車站麵包店前排隊的人群,又躍過忙碌的自動檢票閘口,腳步輕快地向著車站口奔去。
自然,不少人都為這樣的景象而側目。
“御涼亭……御涼亭學院……”二十九在車站出口的地圖前停頓了幾秒,接著頭也不回地向著標識了御涼亭高中的方向跑了過去。路上,能看到不少高校學子和家長向著學院的方向走去,到入學式開始還要再過段時間,行人的腳步稱得上悠閒自在。道旁,累累櫻花壓低枝頭,好像在宣告著已是春季一樣。
開學了,從今天開始就要有新的人生歷程了。二十九對自己說,他看到御涼亭的校門已經近在咫尺。好,就這麼昂首挺胸地走過去。他擺正自己的頭盔,大踏步向著校門沖了過去。來吧!新的校園生活!
“——同學,請停一下,入學式不能戴頭盔進去。”
二十九決定不理會對方的話,當做沒聽見一樣衝過去,卻沒想到對方的態度比自己的要更強硬。他被攔了下來,對方認真地拿出來了記事板,盯著他看。
“同學,請不要在校內戴頭盔。謝謝你配合,快脫下來吧。”
“我,我拒絕……”頭盔之後的二十九輕聲說道,“沒有頭盔是不行的……”
“那我們也不能讓你進去。”
二十九感到有些沮喪,不過,他還是向後退了幾步:“真的不行?一點也不行?”
“當然不行。”對方頓了頓,又補充了一句,“脫掉頭盔,同學你就能過門了。”
“那我就翻墻過去啦!拜拜!”他對對方大聲說道,小跑著離開了。
——十幾分鐘后,二十九彰剛坐在教師辦公室,呆愣愣地看著墻上的鐘錶。分秒的流動慢得出奇。


☆小江这次大概是没力气掐死我了,良心并不会痛
☆借用了一下虚方姐!大胆地响应一下!
明知故犯。
他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头顶上的天空依然是蓝色,太阳没有变成两个,世间的一切也都在井然有序地依照着某种不可视、不可闻、不可触、唯可贸然揣度的法则运作着,仿佛只有他这一个故障的齿轮脱落下来,在长达四十五天的坠落中看见一个幻境。
即是说,可能其实不存在一位不顾御守的劝阻、把呼唤灾厄的物件买下来的松井先生,从没有摔碎的碗碟,没有掉下楼去的棉被和漫天的樱云。付丧神向来对自己——不论是记忆力还是任何别的东西——是抱有过少的自信的,加上这莫名其妙的打击来得是如此突然又绝情,因此他开不了口,他无论如何都无法理直气壮地对着眼前这位将他从徒然堂带出、现在却又询问着他是谁的人类青年开口,说出:我们明明是认识的。
“你没事吗?”松井虽然也是一头雾水,但看见年轻人动摇到这般地步,脸色一会儿白一会儿青好像随时都会倒下,反而担心起对方来,“我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
“也许有吧,我不知道,我已经搞不清楚了。”时江最终这样说,他苦笑着,瞧着甚至有那么点泫然欲泣的意思,“我现在唯一可以确认的事情,就是我现在无处可去了这一点吧。”
他当然不会灰溜溜地回到店里,躺在柜架上等待什么[下一个机会]了,他可以向着天上那些从未护佑过他的神明发誓只有这件事他不会再做。痛楚对于名为鹤见时江的九十九而言是难以去忍耐、难以去承受的,不论是这副虚构的躯体为模仿人类生存而形成的生理上的痛觉,还是一次又一次地失败过后于心底产生的撕心裂肺的痛苦,全都让他备受折磨。他害怕,而一个懦弱的灵魂惧怕疼痛也算是理所当然,这并不是什么稀奇事。
“……你无处可去的话,要不要先留在我这?”
青年沉默了一会儿,侧过身,做出了一个邀请的手势。这幢占地六叠、高有两层的旧式木屋的主人,就是这样又一次将不速之客迎进了家门。
就松井而言,他并不会主动关注别人的私事,然而这位暂住者不愿言明的东西似乎有点太多了。年轻人只报上了自己的名姓,虽是穿着华丽,但却身无分文;他好像懂得很多事,能够写字算账,又常对许多寻常物件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兴趣。于是青年就猜测对方可能是从哪里的大户人家跑出来的少爷,毕竟这小伙儿往好听了说是不擅长做家务事,往不好听了讲就是笨手笨脚,还有点娇嫩。如此结论是三十二秒前得出来的,时江自告奋勇说要帮忙洗洗盘子,接着就在主人家眼皮子底下摔了一个,手心还给陶瓷的碎片划了一道见血的口子。
“很抱歉又摔坏了你的东西,松井先生,但我真没事。”如果他的眼眶没有红,这话听上去还挺有说服力,“反正没伤着……伤得很深,过几天就好了。”“还是处理一下吧。”
松井练过武,觉得自己也算皮糙肉厚,这点小伤不在话下。时江就不一样了,他拉着他往二楼走想找东西包扎伤口的时候,年轻人分外乖巧地跟在后面,什么话都没有说,大概是真的很痛。想着这些,他也就自然而然地忘了对方奇怪的说法、忘了橱柜里奇怪的空缺,忘了这两者之间的简单联想。他本就不是会为这种程度的异常就要追根究底的人。
而对于时江来说,他就算是做不了什么好事、也从来都是个会为主人多做考虑的付丧神,即使被冲击性的事实打击过度,花点时间总归能够重新振作,毕竟两人之间的缘分并没有终结,九十九可以肯定这一点(当然,为了这个[肯定],他偷偷跑回过两条街开外的古董铺专门确认过)。他算不上聪明,也不那么愚笨,几番推敲后总算是明白了对方态度改变的原因——松井忘记了一切与付丧神有关的事。他这是误把他当做了与他一样的人类。
这就不难解释很多事。鹤见心想。比如他现在拉着自己想要找东西包扎包扎,就是因为他忘记了自己就算受伤,只要没有损害到桃纹的御守,再可怖的伤口也能在几日内完全痊愈。
九十九切实地拥有着五感,但他们不会因此产生生理上的需求,单就这一点来讲就已经与人类大相径庭,更不用提人形与本体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又会产生怎样神奇的作用。因此“被视为人类”的体验是十分难得的,时江不可避免地注意到松井的话变多了,这个人不再是礼貌且疏离地与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再是只在他犯下错误时才开口、与他进行着最低限度的交流,不再是、不再是用着和中学教师,和行脚商,和护士,和大学生——用着和其他契约者一样的目光看着他,把他钉死在他从未想要拥有的一切上,让他举步维艰。
瞧,他当真是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呀!自己并不作为他的同族存在于世的事实,源源不断的麻烦皆有来由的真相,还有自己分明就是在卑鄙地蚕食着他的平稳的生活,等等等等,一切的一切,他全都不知道、全都不知道啊……
“时江。”付丧神还不习惯听到别人喊自己的名字,他停下胡思乱想、万分迷茫地望过去,松井便耐心地又问了一遍:“还疼吗?”
他现在终于意识到自己这是沉默太久了,于是赶紧摇了摇头,视线隔着玻璃的镜片顺势落到手掌心细细缠绕的绷带上,粗糙织物的尾端是蝴蝶结拉扯过度后失败的模样。他想告诉他说已经不疼了,喉头却被尚未成形的呜咽声生生哽住,吐不出哪怕一个字来。
这之后的第七天的早晨,即是说鹤见住下来的第十三天兼第五十八天的早晨,年轻人和屋主人说自己等会儿要出门。于是松井把人送到玄关,他就是在这在这儿眼疾手快地扶住平地上也能摔倒的房客。青年看看惊魂未定的小伙子,估算了一下时间,最终还是改了主意、陪他一起走上后街。
五月的街道和四月时并没什么太大的不同,就算连续几日的阴雨停歇了留下一片鼠灰色的沉闷天空,空气也仍旧是湿漉漉的,它将行人与行人之间习惯性的沉默渲染得更加抽象。这次先开口的是时江,他以一种事先准备了答案因而期望他人问询的心境把另一个问题抛给同行者:“你不问问我去哪吗?”
松井则是这样回答的,他的语气一向平平淡淡,此时甚至还有些缺少感情:“你要去哪里都是你的自由,没有告诉我的必要,就算你要离开这里回家去或者哪里都——”“我说过我是无处可去的。”他少见地以略显强硬的语气打断他的话,“除了你这里,我没有任何可以‘回去’的‘家’,我不会对你说谎话,松井先生,所以请不要——”鹤见仿佛被人掐住脖子一般突兀地停下来,“……抱歉,我太激动了。”“没事,我不在意。”
青年伸手,时江的个子比他还高些,所以他轻轻地拍了拍他的后背,这时候他们已经到了路口,他要离开,他也该回去开店了,只是年轻人那副焦急的模样触动到了什么,让他有种难以忘怀的复杂感受。他可能是知道他想说什么的,也可能不知道,他无法确定。
“路上小心。”松井顿了顿,补了一句,“早些回来。”
他猜测这句话是说得对了,因为小伙子总算笑起来、回了声好。
至于付丧神打算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毕竟失忆不是正常现象,既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表现出痊愈的征兆,那么前去咨询专业人士之类的简单事务,就算是他也不至于做不好。
“欢迎光临。”蕪木虚方听到铃铛响,她从椅子上站起身,发现来的是位有些面熟的客人,“哎呀,您是——”“我是那枚招来厄运的御守,蕪木小姐,去年秋分化的形。”付丧神礼貌地点点头,“先前来得匆忙,没有和你打招呼,还请原谅我的失礼……不过这次来访也还是因为我的主人的异常情况,他仍然没有好转。”“那确实很奇怪,狂鲤已经被打倒了,造成的影响也就应该消失了。他的症状是什么?”“失忆,他忘了和九十九有关的一切。”“你是说,他也忘了你吗?”“是的。”鹤见默不作声地移开视线望向窗外,“虽说如此,他也并没有抛弃我,只是把我当做普通人类收留了下来。”“那还好,这样说不定还好办些。”
现任咖啡馆管理人的前·清净屋看出付丧神的疑惑,她如此解释道:“他还能够看见你,那你只要告诉他他忘掉的事情就好了,九十九能够唤醒被狂鲤蛊惑的人,你肯定也可以。”
“只要告诉他,他就能想起来,是吗?”年轻人重复了一遍,“这么简单就可以?肯定还需要别的吧?毕竟,对,我的主人的情况有点不同,他受到的影响比较严重不是吗?不然怎么会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如果真的这么简单就能解决的话,我也不用烦恼那么久了呀?”
“可是你并没有尝试过这个方法吧?”虚方不由得因为对方奇怪的反应而疑惑起来了,“不如说,都过了这么久,为什么你没有试着告诉他——”
时江没能听完这句话,仿佛是将眼球内部的水分瞬间蒸发殆尽一般的剧烈疼痛毫无征兆地灼烧起神经,他哀嚎着倒在地上、鼻梁上架着的眼镜也不知道掉到了哪里去,他挣扎着滚动、尔后瑟缩成一团不受控制地震颤起来,而没有了任何阻碍,手指便毫无顾忌又神经质地狠狠抓挠眼周,指甲在脸颊上划出道道伤口,他这是下意识地想要将痛苦的源头从身体上挖出来以结束这可怕的折磨啊!然而勉强保留下的蛛丝般的理性又勉力拉扯着神智去阻止躯体实践自残的行径,他没有余裕去思考,只有期求这一切能够结束的念头残留在脑海——
也确实结束了,如潮水般席卷而来的痛楚在长达千万年的数秒后也终于如潮水般猛然退去,九十九喘息着扶着墙壁站起来,他不知道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被他吓到的虚方这会儿正为他匆忙奔找着店里的修缮师。年轻人摇摇晃晃地拾起豁了口的物件挪到店门口,他的眼睛不好使了、什么都看不清,所有的所有的一切都在歪曲的视野黏黏糊糊地溶解着混杂在一起,整个世界之中只有松井的声音依旧清晰。
他对他过说早些回来,所以他这就要回去了。
青年注意到自己的房客自从出过一次门之后就有些不对劲,时江开始经常用想要说什么的眼神看着自己,但出口询问的话也只会得到沉默的摇头作为回应,此外,他偶尔会看着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发呆,还会伸出手去,做出抓住什么东西再松开的动作。会不会是回来路上摔到了头?松井如此推测,而这个想法在看到对方豁口的眼镜之后变得更加坚定了。
“你找到它了。”他指指对方手里的遗失物,“这不是都坏了吗,要不要去换一副?”“还能戴,就不用了吧。”“不会妨碍到看东西吗?”“………………能妨碍到就好了……”“什么?”“没什么。”年轻人从房间角落的位置站起身来,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的时候,他就会待在那里,“那个,虽然很突然,不过今天能让我帮忙洗碗吗?”
考虑到上次答应这个请求的时候发生了流血事件,松井本来是想要拒绝的,可时江说这话时的神情是那样认真、甚至带点孤注一掷的意味,他也就只好先一步将绷带准备好以防万一。只是出乎他的意料,搞不好也出乎小伙子本人的意料的是,他这次什么都没摔坏,八个盘子,三个碗,两个杯子,什么都没摔坏,全都完完整整、干干净净地排列在壁橱里。
想做的话不还是做得到的吗!松井对时江这次的完美表现十分满意,他侧过头想要再说些什么、或者夸夸他,可当他看到年轻人脸上的表情的时候,这些话就讲不出来了。
……也不至于开心到哭出来吧……他轻轻拍了拍他的背,不禁这样想到。
鹤见时江知道只要他不开口,松井就会继续将他当做人类来看待,不会将九十九的概念回想起来;他知道这之后后院更后位置的灌木会无故地枯萎,常青的树木会惨遭雷劈;他知道只要他想,他就不会再摔碎任何东西;他知道他看到的是什么、抓在手中的又是什么。
【我其实什么都知道。】他听见自己这样说,即使他并没有开口,【我就是因为知道,所以才会这样做的。】
付丧神一觉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五月二十五日的傍晚,他披挂着屋主人借给他的毛毯从榻榻米上爬起来,看见自己的结缘者正坐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用他再熟悉不过的目光看着他。
“……九十九也会做梦吗?”
松井平静地提问,而被询问者以微笑作答。
他看着摆在自己面前的碗筷和饭食,露出了万分不解的神情:“请问这个是?”“我看你一直没有吃东西。”这么说着,松井在他对面的位置坐下来,“虽然只是粗茶淡饭,但应该也能填饱肚子。我的手艺还是不错的。”“可是我——”“恩?”“啊,不,没什么。”
他没有进食的必要,他并不是依靠食物存活于世上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包括松井,所以他从没有得到过一个机会去尝试所有人类都会尝试的吃东西这件事,好在他已经千百遍地看过别人重复这个过程,所以他能够顺利地拿起筷子、搛起一筷子的菜肴送进嘴里、咀嚼、吞咽,而不使眼前的人的心中升起疑虑。
他确实这样做了,然后狠狠呛住,止不住地咳嗽直到喉咙里泛起腥甜的味道。他向松井摆摆手,示意自己并无大碍,等到能够正常说话了,他耐不住激动地开口,他记得人类在遇到这样的状况时应该给出怎样的感想:“好吃……!”
“好吃你就多吃些,就是吃慢点,不要再呛着了,饭的话锅里还有,你放心吃。”
他看见松井微微地笑了笑,在此之前他从未见他这样笑过,他开始希望时间能够停留在这一刻。
丝线于此刻扭成第二个结。